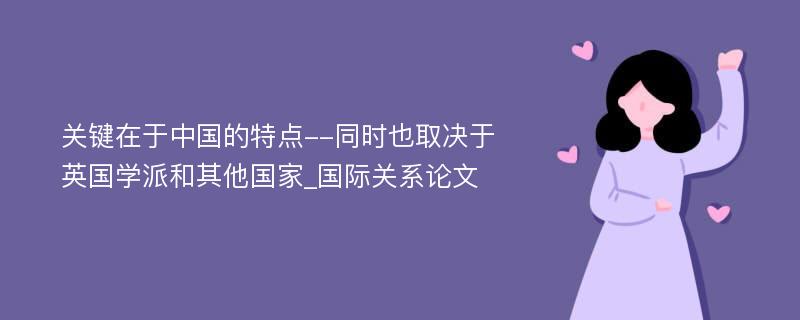
关键在于中国特性——也谈英国学派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学派论文,关键在于论文,中国论文,也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1-0069-04
张小明教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08年第5期中撰文对与英国学派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澄清,提出了他的看法。笔者拜读之余,觉得除了一处地方外,其余皆清晰准确,逻辑严密,行文晓畅,不会引起什么误解。
笔者所说的这处地方在该期杂志第79页,称“英格兰学派”的思想鼻祖是查尔斯·曼宁(C.A.W.Manning)。②从前后文看,张教授可能是引用彼得·威尔逊的话,不是他本人的看法。但尽管如此,这还是可以讨论的。曼宁于1894年出生于南非,1914年来到英国,学成后长期(1930-1962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LSE),期间曾担任国际关系系主任,其代表作为《国际社会的性质》,此书1962年初版,1975年出了一个新版。③当时,年届80岁的曼宁为新版书写了一个长篇序言。但此书大约可以说是一本“怪书”,风格迥异于别的国际关系著作。出版者也说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新颖性和非正式性”,如讨论国际伦理应用、国家的本体论地位、政治信念中迷思的作用以及法律承诺的解释等。
实际上,曼宁与我们通常所了解和理解的“英国学派”关系不大。英国学派源起于1958年开始形成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注意这里用的是“British”而不是“English”,但并无损于什么)。④正是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学派,也就是我们通常了解的英国学派。其中发挥引领作用的要数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马丁·怀特及赫德利·布尔三人。巴特菲尔德是剑桥大学近现代历史教授、杰出的历史学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该委员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有关。随后巴特菲尔德联络了怀特。怀特当时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但时隔不久即转往萨塞克斯大学任欧洲史教授。后来他们又罗致了爱尔兰外交史学家德斯蒙·威廉斯、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唐纳德·麦金农和军事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等人。
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还有亚当·沃尔森——一位学者型的资深高级外交官,他于2007年8月21日在英格兰去世,享年93岁,大约是委员会成员中最长寿的一位。沃尔森对英国学派的成长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作品似乎还未得到中国学者应有的重视。⑤巴特菲尔德、怀特、沃尔森和布尔四人先后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查尔斯·曼宁不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成员,也未发现他参加过委员会的活动,或应邀为委员会集体撰写的著作撰稿。其代表作书名中虽有“国际社会”一语,但该书有明显的特异性。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看不出它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鉴于此,笔者认为,不应把曼宁视为英国学派的“思想鼻祖”。
但这一点,在张小明教授的文章中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而已。他的文章着重要阐明的是,由于英国学派(准确地说应称为“英格兰学派”)不是以国家为名称的,因此,由“英国学派”而生发出“中国学派”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是由于把“英格兰学派”误称为“英国学派”而造成的,作者还引用巴里·布赞的话加强之。笔者觉得,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根据笔者的阅读所及,“中国学派”的提法较早是北京大学的学者梅然和笔者本人开始使用的。梅然在2000年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文章——《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中说,“我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应力求使自己的研究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因为,“如果美国的理论的确科学、合理、全面,那么它独占鳌头倒也无妨,可事实是这些理论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一国把持一个学科也根本不可能是有利于该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打出“中国牌”,“就是要凸现出当前全球国际政治学界的不合理状况,要强调对这种状况进行变革的意义”。⑥笔者本人在同年发表于《欧洲》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有一种志向,一种创新意识,要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进而至于理论系统,因此我比较赞成提出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建立中国的理论,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为了求不同而不同,而是说中国人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要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学说,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走。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的理论贡献”。⑦今天来看,这些话大体上还站得住脚。
迄今为止,对“中国学派”问题进行了最详尽阐发的是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他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文最主要的观点是,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研究问题上一直有着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派的意识。但大都是在考虑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少意识到核心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很难产生一个理论硬核,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中国学派。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什么?他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可以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应该在这一问题框架内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构建具体的研究议程。“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我们才能具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⑧此后秦亚青又著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⑨
现在且让我们假定,如果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英国学派”,那么“中国学派”一语是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呢?我认为,其实不然,它的存在仍然有其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要做出具有足够创造性的工作,赋予“中国学派”以实际的内容。还有的学者说,未闻以国家名字来称呼的学派,其实也不见得,比如经济学中就有以米瑟斯等人为代表的“奥国(奥地利)学派”。⑩正如谁都不会认为奥国学派包括了奥地利的所有经济学家一样,人们也不会认为所有的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或理论家都可以总括到英国学派这个“屋顶”之下。相反,这样一个称呼通常总是指在某个特定国家生活、工作并从事学术活动,学术旨趣相同,学术观点接近,发表了创造性的学术成果,产生了较广泛影响的学术群体。
“中国学派”的提法出现后,引起了一些注意,也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如苏长和认为,“在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过分以国别来强调学科的对立含义,非但无助于所谓‘学派’的产生,相反倒有可能使自家学术研究陷入不必要的情绪化的‘门派’之争,于学科的健康发展不利”。(11)石斌则认为,“‘中国特色’虽然并非学术用语,如果撇开意识形态联想,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未尝不可。如果要抠字眼,‘中国学派’的提法未必就很准确……不过名称并不要紧,关键是人们赋予它怎样的内涵”。(12)石斌本人则使用了“中国式探索”一语。
笔者认为,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我意识增长的一个鲜明表现,其中孕育着产生中国的理论论述的可能性。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可能,而非必然。我对“必然”更为谨慎一些,因为它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一个创造的过程,中国理论是不是会出现(假定现在还没有,但这个假定未必确实),最终要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同时,我也愿意接受中国国际关系学领域应该有多个学派的观点,越是有多个学派相激相长,学术的发展就越是能够得到促进。健康的学术论争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学术论争的结果不应是一方获胜,另一方失败,而应是各方都得到促进和发展。但接受多个学派,仍然不表明“中国学派”一说无意义或不成立。笔者认为,它至少可以起到某种促进的作用,增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工作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
关于这场讨论,笔者曾用英文撰有一文。(13)为了谨慎起见,特地在文章题目后加了一个问号。这篇文章引起了外国同行(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克·斯奈德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彼得·卡赞斯坦教授等)的较大兴趣。虽然他们不一定同意笔者的观点,对“中国学派”一语有所保留,但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正在进行严肃(serious)的探讨和努力。斯奈德教授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说:“我本人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理论上一场活跃的论说(discourse)所要求的并不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场辩论。一场富有意义的辩论标志着在理论的生产中接触到了真正的问题。我不很肯定这一辩论的内容可能是什么。我听到的最与众不同的想法是,中国由于其地区霸权的历史、儒家的社会秩序哲学以及当前的战略情势,需要产生一种和平崛起为合作性地区大国的理论。当然,要成为理论而并非仅仅是公共关系,必须有某种真正的社会理论支撑这一想法,而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清楚那是什么。我也不清楚这一辩论的另一方是什么。为反对美国式的现实主义和/或自由主义而辩论并不是很有意思,它还有一种风险,即下降为自我吸收的争论而非理论上具创新性的辩论。”(14)
卡赞斯坦也称许中国同行的努力,但对“中国学派”一语显然不以为然,对使用国家名称是抱怀疑态度的。他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说:“从你的文章中,关于中国辩论的范围和强度我学到了很多。我确实相信某些学派产生于特定社会之相互关联的问题群(或‘因变量’)。但我很怀疑在解决问题一方(或‘自变量’)存在特定的国家学派。不过在读了你的文章后,我的确相信中国学者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可以凭借,从中还产生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它提供了在理论上做出与众不同贡献的最大的希望。”(15)
平心而论,英国学派理论家们以其人文情怀、历史感觉、伦理内涵和思想深度做出了不同于美国主流或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丰富了国际政治理论,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石斌指出,“英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美国主流话语之外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学术经验和统一与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也不无启发意义”。(16)笔者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17)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学派的学术成就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肯定,(18)其学术贡献得到了普遍的赞赏和认可。笔者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学派及其学术成就,世界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将会逊色许多。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人是否应该有自己的贡献?应该贡献什么?如何进行建设?这些问题恐怕是“中国学派”说的真正起因,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对“中国学派”提法有不同观点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健康的学术论争的表现。笔者在使用时,每每加上引号,意在强调它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现存的事物。毫无疑问的是,严肃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只会促进而不会阻碍学术研究的发展。
在笔者看来,讨论这一问题,关键词在于“中国特性”。那么什么是“中国特性”呢?它似应包括如下几个要素:首先,创新性的工作是由中国人做出的。“中国人”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名词,它可以包括在海外工作、任教的华人学者。但这里所说由“中国人”完成的工作,主要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和工作的研究者。这道理正如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不能算是中国人获奖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美籍华人,他们的工作是在美国完成的,因而只能算做是美国的科学家获奖,对此大家似无异议。其次,中国风格和风骨,它无疑包括中国看待世界以及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和独特眼光,涉及中国置身于国际互动关系之中所获得的经验、感悟、情感和期待。早在1963年,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就指出过中国人办外交的一些哲学思想,例如:其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其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绝不会先对人家不好。其三,礼尚往来。其四,“退避三舍”。“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19)诸如此类的成分会或隐或显地反映到中国的理论建设中。其五,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中国贡献”的来源是什么?最重要的恐怕是唯物史观加中国思想文化的底蕴。就前者而言,唯物史观可以说浓缩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值得在这里引用这段十分精辟的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住、喝、吃、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0)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琢磨和玩味。也是基于此,“实践”是一个颇为关键的概念。笔者十分赞同历史学家黄宗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主张。(21)但这又是个大问题,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的,需要另文讨论。就后者而言,必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积淀。没有中国思想文化的支撑,中国人在国际关系理论化方面的努力很可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方面有了某些积极的开始,其突出表现是对中国“和”的思想哲学的挖掘和探讨,这些学者多半是受“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理念的激发。(22)
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特性的形成、中国贡献的做出,还是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和来源产生成效,最后都将落实到和体现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和理论建设者切实的努力和勤勉的工作上。它一定是一个渐进的和较为长期的过程,必须通过逐渐地累积来达到。同样,中国人的理论成果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得到承认也必定是一个自然的和水到渠成的过程,任何真正的学术承认都与“公关”或炒作无关。
注释:
①张小明:《英国学派还是英格兰学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78~80页。
②张小明:《英国学派还是英格兰学派?》,第79页。
③C.A.W.Manning,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First published by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and G.Bell and Sons Ltd,1962; Reissue published 1975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④Tim Dunne,"A Brit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ck Hayward,Brian Barry,and Archie Brown,eds.,The British Study of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⑤例如,中国学者研究英国学派较为系统的一本书是《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该书就没有关于沃尔森的专章,参见陈志瑞等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沃尔森曾与布尔共同主编了《国际社会的扩展》(1984年)一书。他的个人著述包括:《第三世界问题的性质》(1968年)、《宗教及政治中的宽容》(1980年)、《外交:国家间的对话》(1983年)、《国际社会的演变》(1992年)《独立的局限》(1997年)以及《霸权与历史》(2007年)
⑥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65页。
⑦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载《欧洲》,2000年第4期,第24~25页。
⑧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5~176页。
⑨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⑩[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尤其见“中文版前言”及汉斯-海尔曼·赫伯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与自由主义》一文。
(11)苏长和、彭召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
(12)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9页。
(13)Ren Xiao,"Toward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eds.,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293-309.
(14)杰克·斯奈德于2007年10月26日发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15)彼得·卡赞斯坦于2008年6月12日发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16)石斌:《英国学派的传统与变迁》,载陈志瑞、周桂银、石斌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第22页。
(17)任晓:《向英国学派学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
(18)其中包括美国学者,例如玛莎·费丽莫,参见[美]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
(19)周恩来:《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载《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4页。
(21)[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2)值得一提的是,非国际关系学界“圈内”人士的作品也引起了很大的重视,显著者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书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本篇幅不大、仅160页的书,但在国际关系学者中间引用率颇高。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英国工作论文; 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