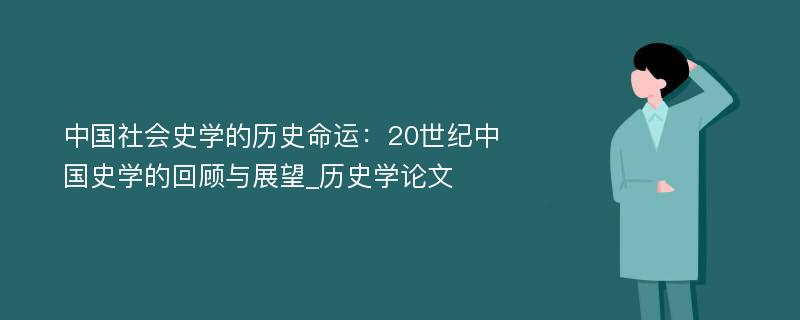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20世纪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命运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1986年聚集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家们正式揭橥“社会史”研究的旗帜时,人们还未曾真正从一个学科的理论高度去评判它的历史走向及其命运。史学家们最真切的感受是,在普遍的“史学危机”的感叹中,“开展社会史研究则是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的一条重要途径”(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走出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禁锢的樊笼,在对以往历史学研究历史的反思中,史学家们发现原本属于历史的内容却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因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评论员文章)这一极具“新时期”史学时代特征的口号,便成为史学家们开创社会史研究的共同起点。1986年应该说是新中国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性年代:极富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与先此兴起的文化史研究,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主潮,被一些学者誉之为“史学奋飞的双翼”(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从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开始,两年一次旨在引导全国社会史研究方向和检阅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围绕着不同的社会史主题,已经召开了五届,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因而,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及其学术成果,理所当然地也成为许多密切关注社会史学学科地位和它的未来走向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一个跨世纪历史学发展趋向的根本性课题时。
一
无论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持多么不同的看法,也不论史学家们对社会史的内涵作出多少相近或相反的界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评价却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近十年走出低谷的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史”旗帜下获得的。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社会史研究方面,且不说译介的许多国外社会史研究著作,单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史丛书”、“中国社会史丛书”和“中国社会史文库”就近40部。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出版的社会史著作就达一百三十多部(见吴吉远、赵东亮《中国社会史主要书目和论文》,《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有关社会史研究论文更是空前繁盛且引人注目。因而,即使是想从学科地位上根本否定社会史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社会史研究虽然被学科化努力所羁绊,但它带给史学工作者的欣喜和取得的成就依然彰明显著”。它显示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对于“新时期”史学发展发生深刻影响而且具有久远启示作用的,大概还不是或主要不是体现为社会史具体研究成果的多与少,而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具有新时代意义的历史趋向。社会史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十分宽广的历史视野,许多过去被认为无足轻重、排斥于历史研究领域之外的内容,都在社会史的意义上获得了重新估量的研究价值。举凡服饰、饮食、生育、婚姻风俗、宗教信仰、乡土习俗、家庭宗族、社会心理、妇女儿童等等,都聚焦在社会史的镜面下,成为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最持久不衰的研究课题。正是在视野开阔、领域拓宽的过程中,它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促进了历史学的改革与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史学以往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社会史引发的理论方法的创新,更加令人瞩目。社会史具有涵盖面宽、内容层次多的特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对此显得无能为力,因而充分借鉴当代社会科学新方法,与其它学科的相互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史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诸如计量史学、心态史学、想象史学、比较史学、家庭组合法、社会测量法等新方法,大跨步地渗入历史学,导致了当代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的革新。正是由于社会史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上的创新,标示了新中国史学时代性的转折,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首先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有人甚至干脆称之为“新史学”。
如果不是纠缠于一些具体课题的学术评价,而是从更为宏阔的时代与学术的相互作用上去透析社会史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历史学发展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觉回应。历史学领域内的这一巨大变化的最重要的趋向,就是史学研究内容开始走向社会。当史学家们肩负着努力超越传统史学模式和摆脱“史学危机”的双重使命,在开辟社会史这一新领域时,都有着一种历史自觉:以整个社会作为研究的基点。由此,它促使历史学在研究内容上发生了令人瞩目的三大转折:
第一,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大多是历史舞台上的精英,虽然新中国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大都接受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在即使以农民战争为主线的史著中,也仍然是以农民起义英雄、领袖为中心,而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农民,却并无研究。社会史却倡导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英雄”们借以出演的历史正剧的社会内容,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因此,许多与社会普通人相关的内容如贱民、娼妓、太监、游民、流民、乞丐、妇女、秘密社会,都成为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课题。这同20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史研究向黑人、妇女、儿童、工人转向的历史趋势如出一辙。社会史导致的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
第二,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随着历史认识的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决不外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聚积着和体现着。传统史学格外关注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或重大的事变本身,而相对漠视事变酝酿、孕育的不经意的历史过程。新时期的社会史则相反。与以往的历史著述侧重于政治事件不同,社会史研究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诸如民俗风情、历史称谓、婚丧嫁娶、灾荒救治以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第三,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
这三个重大转折,标志着历史学的研究内容面向了社会。当然,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既是对传统史学模式反思的结果,更是时代发展要求所致。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变革,导致人们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代,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使得个人的力量——即使是杰出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相对弱化,因而人们的视线逐步离却“英雄”而移注于“民众”或“群体”。同时,在迅猛发展的社会中,人如何适应社会,人的社会化问题,以及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也愈来愈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为紧迫的课题。这就逼迫着史学家不能远离社会,脱离时代去从事“上层”、“宫廷”式研究。因而,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史学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时代要求的一种自觉回应。
当现代社会——时代的要求在历史科学认识领域中得到确认后,随着一些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的不断提出、不断选择、不断精确,就逐步形成了区别于以往史学研究内容的新的体系、新的范畴、新的视野——这就是烙印着强烈时代感的社会史。社会史源于社会,源于时代。正是当代社会不断涌动着的活的生活内容,构成了历史学新的内容,产生了以社会生活为主体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史”是历史学走向社会的必然结果。这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
走出传统史学的视野之后,社会史确曾展示了它领域宽阔的独特优势。社会史具有既深且广的研究领域,从广度来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功能等;从深度来看,近期的社会史有一种与普通人休戚相关的意识,它涉及到诸如社会流动、家庭婚姻、社会犯罪、大众文化以及巫术迷信一类深层次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且,由于社会史是跨度大、范围广、内容多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它诞生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渗透之中,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特点。因此,社会史在发展过程中,围绕“社会”这一主题不断与其它学科进行整合,形成了一批附属于社会史的亚学科,如人口史、婚姻史、妇女史、家庭史、灾荒史、风俗史等等。社会史学科群落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从研究领域上展示了它所独具的诱人的发展前景。然而,正象有些学者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新课题最多只能提供变革的外在形式,而变革的成功与否,将最终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内涵去赋予课题以新的生命,显示其社会史的意义”。否则,“简单地移植新课题,已经有迹象表明,很可能变成罗列奇风异俗、陈规旧习的民俗展览”(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从宏观的学科理论高度来审视近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现状,不能不承认,这距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学科的基本要求还相差甚远。
首先,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现状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更多地侧重于研究领域的开拓和课题的提出,却忽视了对于学科体系和基本规范的理论建设的研究。社会史在近几年内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各种专题社会史如人口史、妇女史、秘密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家族史、服饰史、饮食史、灾荒史等均有大量论文和著作问世,社会史研究显示了领域极为广阔的学科优势。而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却相形见绌,显得清冷沉寂,不具声势。不仅没有系统的专著出版,就是宏观理论体系探讨的文章也不多见。由于“社会”概念的过于宽泛和多义,史学界很多学者采取一种回避态度,强调“目前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不宜过多地去考虑构建体系和框架”问题。因而社会史理论研究与专题研究形成了明显的两个极向:即理论研究的滞后和专题研究的分散。作为一门新学科,如果不能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比较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它的发展前景自然会令人焦虑。因为专题研究并不解决学科理论体系问题,系统的社会史也绝不是各门专题社会史的简单结合。由于宏观学科理论研究的滞后,社会史研究缺乏最基本的理论规范的制约和理论引导,从而导致专题研究呈现出离心的偏向。
大量的专题研究成果,相互之间缺乏学科上内在的联系和共性,不能以一个独特的相对独立的学科获得学术界的真正认同。因而,有人认为许多“社会史”的成果,只是贴上了社会史的标签,而同传统的史学成果并无差别。
其次,由于学科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在社会史研究发展过程中,人们遂大量地借用社会学理论、概念、范畴、方法,使旧有的史学理论体系陷入“失范”状态,而新的理论、范畴并没有在史学学科意义上进行科学的体系化的整合,新的“规范”并没有形成。有些学者在社会史研究中简单地移植社会学或人口学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中的“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概念同“人口”概念相等同,从而把“人口”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使“人口”在社会结构中同阶段、阶层、宗族、家族、家庭等社会关系范畴处于同一层次,导致了基本理论范畴上的疏失。在社会史理论构架上有些学者也大体照搬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把动态性的社会史纳入一种“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或社会意识”的简单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使社会史逐步演变为社会学的历史投影,从而导致社会史史学特征的失落。
当然,诞生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中的社会史,本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趋向的必然结果,因而,社会学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的植入似无可非议。“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而且,“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唯一证据——无论其研究领域多么特殊——只能是历史的证据”(同上)。因而,学科间的交流和渗透势所必然。一些学者也针对性地提出,在社会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学概念、范畴的引入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其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引入的“社会学内容”的多与少,而在于是否将这些最重要的“外来”概念、范畴“赋之以历史内容,确定它们与传统的历史概念之间的联系”(【苏】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第144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从社会史学科意义上对社会学的概念、范畴进行学科整合,使之既具有社会学的某种学科优势,又兼具历史学的学科特征,那么,无论引入的成分有多少,都无助于社会史的真正健康发展。“相反,将社会学的概念、观念、理论和方法机械引入历史学,只会加重困难。……要成功地运用社会学方法,首先必须将它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社会学的专门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才能行之有效,否则是不可能的”(同上)。把理论的彩球抛给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只是将史料填充到社会学家的模式中,这样的“社会史”注定不能独立于社会科学之林。
正因为缺乏理论建树,社会史尽管成果颇多,却未能形成标领一代风骚的宏大史学气势,而真正作为时代意义的系统的中国社会史著作,也以先天理论养分不足一时难以问世。
“社会史还能走得更远吗?灰姑娘能否凭借自身应有的资格成为一名公主,而不再是侍女?”(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4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晚半个多世纪而兴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正面临着西方社会史学曾经面对的一个共同难题。
这是一个从根本上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课题。虽然,有些学者出于功利性的考虑,提出“不必纠缠于学科对象”和宏观理论问题,“然而,哲学从前门被赶了出去,又总是从窗口飞了回来”(【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6页)。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哪怕是极其微观的课题,也很难设想是在“理论真空”中进行的。如果没有特定的理论规范(即使是不完善的理论体系),具体的社会史研究根本无从着手。“每个企图脱离思想的人,最终只会滞留在一些感觉之上”(约·沃·歌德语)。有意逃避理论的做法,只是导致社会史学停留在概念、范畴简单移植、堆砌或浅层的感性意识上,从而使旨在启示人类心智的社会史失去原本应有的认知功能而流于琐屑。
三
社会史因其研究领域的宽阔和蕴含内容的丰富引起研究者持久不衰的学术兴趣,同时,也由于其学科理论研究的滞后而难以获得长足发展。因而,80年代中期关于社会史学科对象及其特征的话题,时隔十年又被一些学者重新提出(见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然而,旧话重提不是为了说明社会史相对独立的学科意义,而是相反。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的贫乏、选题的琐碎,甚至学术领地的难以落实,使社会史学者们深感困惑”(同上)。常文在对近十年中国社会史和半个多世纪的西方社会史“进行彻底的‘体验’”后,作出一个足令许多社会史学者根本不曾想到的结论:“建构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努力归于失败”;“社会史学充其量也只能成为泡沫学科”。
这就是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
这一问题的提出似乎不在于它的深刻性。社会史作为学科存在的前提在于它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1卷284页)。虽然“社会”一词含义过于宽泛,作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通常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有很多重合之处,但二者毕竟不会等同。广义的历史其实包括自然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两大部分,人类历史无论从其实践意义还是从其观念意义上而言,都不能离开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社会的改造及其相互作用而存在。因此,尽管“社会史”与“历史”的研究对象有重合之处,却并不重复;作为学术概念它们的分界尽管模糊,但其内核却并不一致。在当代的社会中,迅猛发展着的科学技术及其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当然是历史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同时,被人类改造着的自然的演变过程也不能被排除在历史学的视野之外。历史概念涵盖了社会,社会却无法包括历史。
从较狭义的意义上而言,人类的活动是具有类型的。现实中,人们的生活领域通常被划分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历史上人类的活动也如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之外,也还有着难以为上述诸项所包容的“社会”内容。正象有些学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化史虽然内容广泛,但却不能包括社会史,比如妓女生活的历史只能归属于社会史,而无法归属于文化史。人类生活的内容本身就存在着区别于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社会”部分,这本身就构成社会史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
从学科意义上而言,历史学是一个高度综合、内容复杂的学科。作为现实的学术研究,任何学者都不会研究历史学的所有内容,而只是致力于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因此才出现人们大体认定的一级学科(历史学)及其属下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划分。对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二级学科的专题史无法囊括的研究内容而言,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学之下的“社会史学”存在呢?
对于勃兴不久正在成长中的社会史学,现在断言其学科努力归于失败,尚为时过早。
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关键在于它的尖锐性。它再度提醒热衷于专题社会史而回避宏观学科理论建设的社会史学者,社会史学的命运及其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主要不在于专题研究成果的多少,而取决于是否有独特的较为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定义尽管分歧犹存,但它毕竟有着大体可以把握的内容。在社会史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的范畴、概念、方法也大量从其它学科涌入,如何在特定的学科定义下,对引入的新理论加以学科整合,建构成比较系统的规范体系,作为引导社会史发展方向的内在因素,从而对各种专题社会史的发展形成中心引力,应该成为社会史学家们的终极关怀。
总之,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关乎着社会史学科发展的前景和命运。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根本不能够疏离其理论体系的探讨而存在,而发展。尤其在学科体系高度开放的当代社会中,诸学科的相互渗透,各种新理论、新范畴、新方法的相互交汇已是必然的趋势。因而,中国社会史如果不加强它的宏观理论学科研究,不从学科体系的层次上对引入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加以科学整合,就无法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学科意义上的规范体系。
社会史崛起于对传统史学模式的深刻反思之中。反思的深刻和重建的成功主要不在于领域的开拓,而在于理论对于时代的魅力。尤其是在世纪转折、同时也伴随社会文化转型之际,中国社会史学是随着本世纪的终结而销匿,还是成为下一世纪初年成果丰硕的史学主潮,理论体系的创新和重建是其关键。
标签:历史学论文; 社会论文; 历史社会学论文; 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社会学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