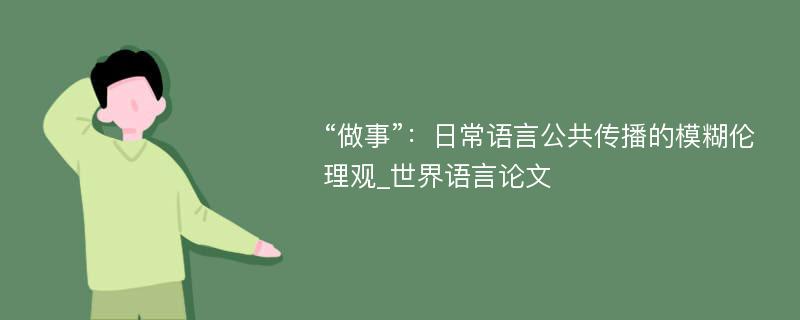
“做事”:日常语言中朦胧的公共交往伦理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朦胧论文,观念论文,日常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汉语日常语言的用法上,“做事”一词有两种主要的意义。一种指生产性、职业性活动。例如,当一个徒工没有完成好一件交代他做的工作时,人们会指教他说“做事要认真”等等。即使在这种意义上,“做事”也同完成一项生产的、技艺性的制作活动的态度上的规范含义相关,而不单纯地是描述性的。另一种指交往性、实践性活动。这似乎是它的更主要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很少被同前一种意义明确地相互区分。“做事”的“事”所指的大都是同“人”有关的“人事”。就这种主要的用法而言,“做事”是一个有关交往实践事务的规范性语汇,与“做人”一词一道,是日常语言中表达交往实践事务的规范含义的两个基本语汇。对于这两个语汇的一般性质,以及“做人”观念,我已在其他地方做了探讨(廖申白)。本文的目的则是对在日常语言中经常伴随着“做人”观念的“做事”观念做一个批评性的考察。这种目的将限制在几个初步的问题上:“做事”观念具有怎样的性质?它是否含有某些规范性的含义?如果是,含有哪些规范性的含义?它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发生哪些变化?不过,由于“做事”观念同“做人”观念有内在的关联,因而讨论在许多地方需要借助与“做人”观念的对照和联系来进行。
这样一种考察的主要意义在于,日常语言中尚保持着生命力的实践性观念表现着一种伦理传统积久塑成的日常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从这样的观念入手,更容易看清这种传统在向现代交往社会转变中的境遇。对于研究这类日常语言中的伦理观念的起点,我已经做过一些说明。(同上)需补充的是,“做事”与“做人”观念在这里一道被看作这类尚保持着生命力的伦理观念,被看作日常语言中表达着交往实践事务的规范性意义的最重要的观念。这一考察所期望的仅仅是,它能够与日常语言中对“做事”这个语汇的主要用法一致,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哲学思考的支持。
二
这一考察需要从日常语言中“做事”观念的性质入手。“做事”观念的第一个重要性质在于,与“做人”观念一样,它是关于交往实践事务的总体性观念。这与实践概念本身的情形是一样的。实践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人同自身的关系和同他人的相互关系上的行为活动。实践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属于具体的范畴,关乎具体的交往活动(亚里士多德,第60页)。它包含一个个行为活动,然而又不能化简为这一个行为或那一个行为。“做人”和“做事”也是这样。它们都是在交往实践事务方面的总体的伦理观念。“做人”是私人交往方面的。它包含了做一个好儿子/女儿、好丈夫/妻子、好兄弟/姐妹,好朋友/伙伴等等,而不等同于这其中的某一项。它毋宁说是“做本己”、“做好人”这样的总体观念。“做事”也是这样。这种总体性在考察“做事”观念时甚至更为重要。
“做事”的“事”在日常语言中有两个相近的意义:一是事务,二是事情。事情是具体的、有始有终的事。事务则一般指经常性的、需要不断处理的事。“事”有道德意义上的和非道德意义上的。道德意义上的“事”都影响到一个人对待他自身、对待他人和处理同他人的关系方面的品质。非道德意义上的“事”表现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在广义上也同人的品格(广义地理解的品质)相关。“做事”的“做”是行动、实践的意思。
“做事”一词有相当广泛的意思:外出经商是“做事”,担任公职是“做事”,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做事”。在日常语言里,“做事”的从事职业的、生计的活动的意义与同外面的人打交道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因为从事职业的、生计的活动就意味着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做事”是在笼统的、总体的意义上指从事职业和生计活动而同各种人交往的事务,而不是指做一件具体事情的活动及技艺。如果一个生意人在做一件具体的事,人们会说“他在算帐”、“他在盘库”、“他在和客人说话”等等,只有说起某人在“外面”的总体活动时,才说“他在做事”。所以,“做事”是关于一个人在职业生涯方面同他人的交往活动的总体的观念。在这个观念里,事的具体性隐退了、消失了,它的总体的意义则具有了可理解性。
中国的父母们常常劝导子女和年轻人“学着‘做人’、‘做事’”,“好好‘做人’、‘做事’”,而关于“做人”和“做事”的意思则很少加以解说,因为这种意思被认为是每个听讲者(包括年轻人)的日常意识所明了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两个关于交往的实践事务的总体观念的含义很难用清楚而概括性的语言说明白。日常语言在关于人生的内容方面常常含义朦胧,很少有人尝试明白地说明。中国的思想,像一些哲学家认为的,是整体性的、非分析的,似乎非要借助含义朦胧的语言才能使人意会,若将它分析了反而会害其本义。另一方面,“做人”、“做事”通常被看作“怎样”的问题,对其含义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生活观察,而不是通过讲解。很少有人会发问“做人”、“做事”意味着什么。看着别人,特别是年长者,怎样同周围的人说话,怎样有时注意礼节有时又不拘礼节,特别是,怎样对待父母亲,怎样同亲戚朋友等等交往,就懂得了“做人”的意思。看看人们怎样出门做生意,同各种人打交道,就懂得了“做事”的意思。在这样的日常教养中,“做人”、“做事”两个语汇纳入了种种复杂内容,成为要求人们在交往事务方面通过观察学习恰当的态度与方式的暗示语。
三
“做事”观念的第二个重要性质在于,它所指的交往实践事务对于说者和听者都意味着相对于某个“内部”而言的外部性。当村落里两个人谈到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说他“在外面做事”时,这个谈话确定着一个他们共同认定的“内部”范围,并且这个范围一般地也是那个被谈论的人所分享的。这个“内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言说的具体上下文,甚至取决于说者和听者构成的谈话共同体的独特性质。两个家庭成员的谈话所指的“内部”可能是他们的家庭,两个村邻的谈话所指的常常是他们的村子,两个狱犯所指的则很可能是他们共在服刑的监狱。家庭与村落通常是这个“内部”所指的稳定范围。这是中国村社社会的独特性质决定的。在城市社会,社区不再是村落,村落的概念消失,家庭与私人交往的范围通常构成这个“内部”的观念边界。不过,由于城市中私人交往关系的频繁变化和家庭生活的边缘化,城市社会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做事”观念所言说的范围。
相对于这个“内部”,“做事”的世界显现为一个外部的世界。这是一个远为广阔的世界,人们似乎探寻不到它的边际。它给予人们一种同在“内部”生活世界里异样的感觉。在这个外部世界,一个人同他人的交往不再是私人间的稳定交往,而是同偶然际遇的私人的偶然交往。交往关系因此也不再是私人的特殊交往关系。每一个他人似乎都隐退到匿名的人群之中,失去了他的具体性。这个交往的世界于是表现为一个同陌生人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感到陌生和紧张,感到自己的孤单和力量的弱小,因而也时时警惕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筹划着应对的策略。
这个“做事”的外部世界所显现的外部性并非在它的所有部分都没有程度上的差别。过去时代的职业生涯通常受着地域和交往手段的限制,范围很狭小。生意人和工匠通常主要同一些老客户做生意。孤单的感觉也使得生意人和工匠们通过直接间接的血缘地缘关系联合起来,形成行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同仁的关系和同生意主顾的关系渐渐地成为一种“准熟人”社会,一种特殊的生活与交往共同体。(注:在这点上我受益于与苏晓离的讨论。)这个共同体与更广大的同陌生人的交往世界在很多方面显现出有意义的区别,兼有私人的熟人交往世界与陌生人交往世界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本质上属于同陌生人的交往领域。另一方面,由于交往范围的相对窄小和自由的市场体系不发育,这个领域中的经常性交往对象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面熟”的特点,因而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陌生人世界。
四
由于“做事”观念的“外部”性和“做人”观念的“内部”性,这两个观念一起构成对人的交往世界范围的完整概括。“做人”是一个人关于他的“内部世界”中的交往事务的观念,表现为一种处理这类事务的实践要求,一种他感觉到别人会对自己提出、他自己也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同时,生活观察也使他体会到身边的每个其他人也同样感觉到这样的要求。“做事”则是一个人关于他在外部世界中的交往事务的观念。它同样表现为一种要求,一种为获得生计资料和财富而同他人打交道的半是策略性、半是同自己关于“人”的观念结合着的要求。就策略性方面来说,这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性的要求;就同“人”的观念相关联这方面说,它又具有一个人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性质。在外部世界的两个相对区别的部分,这两种因素各自起作用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在“准熟人”社会,一个人在他的私人交往生活中形成的“人”的观念常常起着比在那个纯然陌生的交往世界里更大的作用。但是这一点又依那种“人”的观念以及通常伴随着它的“良心”观念对人的影响的强弱程度而不同。总体上说,在“内部世界”“做人”,在“外部世界”“做事”,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人日常意识中交往生活世界的整体,构成了人的实践的生活世界的全幅图景。
总括而言,“做事”是人们对于在密切生活共同体之外的、同陌生人交往的世界中的交往实践事务的朦胧的观念。人们习惯于把一个人在自己人的内部的实践事务,即他在家庭、在私人交往的范围之内同他人共同生活和交往方面的事务,表象为“做人”;而把他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同他人的交往事务,表象为“做事”。一个人在家里是“做人”而不是“做事”,在外面是“做事”而不是“做人”。在这“内”与“外”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在“内部”,一个人应当是他本己,应当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儿、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好朋友、好邻居等等,简言之,做一个好“人”。在“外面”,在那个陌生的世界,由于一个人仿佛不得不扮演某种其他角色,而不是他的本己,因而他不是在“做人”,而只是在“做事”。
五
但是,在“内部世界”“做人”也包含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说那是“做事”?在“外部世界”“做事”也意味着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不说那是“做人”?日常语言为何不用同一个观念,而是用两个相异的观念区分这两种交往事务?合理的解释似乎是:通过这样的命名,日常语言不仅将这两者相互区分,而且确定了它们的一种排序:“内部”事务优先于“外部”事务。
两个观念传递的这种涵义是同中国社会生活的性质吻合的。中国村社社会的基础造成的不仅是“内外有别”的交往世界的格局,即“内部”的关系、准则、态度不为“外部”世界分享,“外部”的关系、准则、态度也不可以移入“内部”,而且是内先于外、由内及外的优先性排序。这原因在于,“内部”世界是通过血缘、地缘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内部”的关系因此都是以感情做纽带的、密切交往的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分“层”的:最坚固的内核是家庭,然后依次是朋友或伙伴,邻里和近亲,同乡或面熟的人们。朋友和邻里两层可称为私人交往圈,到第三圈,即同乡或熟人,可以总合地称作熟人社会圈。熟人社会以内的交往事务都可以算作私人交往事务。从家庭逐层外推,越推越远,感情的联系也就越来越薄。(费孝通,第27页)推到熟人社会以外的“外部”世界,感情的联系就不存在了,所以要通过法律和政治把人们联系起来。重视“内部”的尤其是家庭的人际关系,将“内部”的人际关系看作重于“外部”的人际关系,是中国农耕社会积久形成的基本的交往观念。(杨国枢,第115—116页)
六
那么,为什么在日常语言中“内部”交往事务同“人”联系起来,而“外部”交往事务则同“事”联系起来呢?
对这种特殊的联系需要借助对日常语言中“人”与“事”这对范畴的理解来做出解释。日常语言中对“人”与“事”这对范畴的理解似乎含有一些公认的定式:“人”是人的本身,“事”是附属性的;“人”是主体,“事”是主体行为的印迹;“人”重于“事”,“事”轻于“人”。“内部”交往事务被同“人”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被看得最为重要;“外部”交往事务被同“事”相联系,是表明它们被看作不如“内部”交往事务那么要紧,那么关乎“人”本身。日常语言中的“人”是儒家“成仁(人)”这一核心思想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积淀而成的观念,是儒家“仁”的概念的折射物。儒家最重视“仁(人)”即大写的“人”(“好人”或真正的“人”、完善的“人”),日常意识也最重视“人”的观念。“成为人”是儒家哲学的基本核心,也是日常意识中最重要的关切。“人”的观念在儒家哲学中具有反思主体的性质。“人”自身既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体,又可以作为对象来思考:“人”是人的对象物,人把他自身当作他的对象;日常意识也同样把“人”看作可以也必须由人自己去“做”的。儒家哲学认为人是在其人伦日用的实践中“成为人”的,家庭与私人交往生活实践是人之“成为人”的最重要的场所,日常意识便把这种生活过程表达为在人伦日用实践中“做人”,把“人”表达为通过“做”而“成为”的。在这个交往范围内,一件件交往事件被看作同一个人的“成为人”、同他的品行和人格紧密联系着的,所以被命名为“人”:它们的具体性隐去了,同它们相关的实践也在一种朦胧的意义上被称为“做人”。
“事”被看作轻于“人”,则因为“事”被看作对“人”自身只有偶然性的影响。这种偶然性要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人”是人的自身,“事”则只是加在“人”身上的外来物。人要“成为人”是因为他本身的缘故,做“事”则是由于生计条件这类外在的原因。出于外因的事务对“人”的影响是偶然性的,尽管不是毫无影响。“做事”似乎是一个人人生的一种经验、一些插曲,是他的独特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人”本身。其次,人在“外”不同于在“家”:在“家”他是他自己,在“外面”“做事”则可能“身”不由己。既然“事”有时不是出于己愿,它对人自身就只有偶然的影响。“事”也是有分别的,有些“事”对“人”有较大的影响,有些“事”则不大影响、决定“人”。人们常常说“对事不对人”,这意思是某个人虽然做了不正确的事,但他不是那种“人”,不应当以对待那种“人”的方式对待他;或者,即使他做了那样的事,他还是“人”,应当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他。第三,同样的交往事件,发生在“内部”还是“外部”,产生的影响非常不同。一件非常棘手的交往事件,在私人交往圈里引起“这叫我怎么做人”的问题,在“外部”交往的范围中引起的则是“这让我怎么办”的问题,与“我”的“做人”没有直接关系。第四,“成为人”是在一个人能力以内的(“成仁由己”),成就一项事业(同众多的人打交道)则不取决于人自己(“成事在天”)。因此,是否成就了一项事业并不被看作是决定人的“为人”的,而只被看作衡量他的能力的尺度。最后,决定着人的“为人”的是他在其“内部”世界中而不是“外部”世界中的交往行为。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做了坏事并不妨碍他仍然是一个好“人”——好儿子/女儿、好父亲/母亲、好朋友/伙伴等等。在极端的例子里,甚至一个在“外面”杀人越货的人也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有理由在“家”里得到庇护。这就是法律不能完全有效的重要原因。这类庇护在儒家思想的义理层面是讲不通的,但是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却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
七
这种植根于日常意识的“做事”观念是否可能包含规范性的内涵?如果是,又包含着哪些规范性的内涵?
对中国人来说,“内部”的世界始终是有规矩的,这规矩就是日用人伦的礼俗。在这种规矩失效的“外部”世界,当人们同陌生人的关系还没有成为重要的生活关系,对陌生人还普遍抱着排斥心理,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尊重地对待时,这个世界就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呈现为一个朦胧的、无规矩的世界。中国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总体的实践态度是复杂的。由于“做事”仅仅是一个朦胧的总体性观念,形成于公共交往生活不发育的漫长历史时期,所以它不包含明确的规则。但“做事”又必然意味对“做事”方式上的要求。这种要求通常表现为出于谋生计的需要的策略主义态度与私人自身业已形成的“人”的观念的某种混合。策略主义不是旨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建立共同规则,而是谋划权宜之计。它本质上是“内部”私人交往的特殊主义的一种延伸:在不存在私人感情纽带的情况下,这种特殊主义在极端情况下蜕变为一种纯粹的“策略主义”,即根据交往的对象和场景而决定应对策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句常识劝告,很好地表达了纯粹“策略主义”的要旨。它的注解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必须说的,一切都随对象、场合和气氛而变。这种注解又构成另一常识劝告——“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注解:与“外人”交往不同于家人的共同生活和私人交往,一个人的内心即他的自身要深藏不露,因为在这种交往中倾心相待很可能遭损。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交往世界的不同部分,以及职业生涯领域中的所有私人,都同样没有明确规则。在那个相对狭小的“准熟人”社会,由于人们从其私人交往生活中体验到的“人”的观念对他们有较大的自我约束力,因而常常存在着一些交往的规则。在这个范围内,“策略主义”态度的影响相对较弱。但是在这些规则中,有些规则含义朦胧,在实践中给因人而异的特殊主义留下过大空间;另一些规则又很脆弱(注:我在这一点上也受益于与苏晓离的讨论。),违反行为时常发生,规则形同虚设。在更广大的陌生人世界,规则变得更为朦胧和脆弱,随意行为变得更为普遍,策略主义的实践态度也就变得更为流行。当然,人是分为不同类型的:那些对于在私人交往生活形成的“人”的观念有较深入体验的人,甚至在同陌生的人交往时也自有准则;而那些没有或缺少这种理解的人,则在同熟悉的人交往中也会毫无操守。
从这里便容易理解,为什么诚实在中国主要被当作私人德性,而没有被当作公共交往生活所必需的要求。在私人交往中,由于一个人履行他所处社会关系赋予的各种特殊责任成为首要要求,诚实下降为一种次要要求。所以日常语言常常忽略老实与诚实的区别,把诚实归入老实一类,并将老实视为一种弱者的可欺的品质。在私人交往生活中,诚实只在朋友间的交往方面才被看作一种要求,因为朋友间会相互要求友谊和忠诚。由于公共交往关系极不发育,并且被看作私人交往关系的简单延伸,诚实在中国从未成为公共交往生活的要求,尽管它恰恰是健全的公共交往生活所必需的。公共交往借助规则与契约维系,它只有依靠人们对公共规则与私人契约的尊重和诚实承诺才能成为人们可以信赖的联系纽带。诚实只有在公共交往关系发育到人们可以相互地提出这样的要求时,才可能作为公共交往方面的规范发展起来。而在不健全的公共交往中,产生的只能是单方的“策略主义”。
八
另一方面,私人交往生活中形成的“人”的观念是一个人在“外部”世界赖以把持内心的朦胧观念,它对人在“外部”世界的交往行为间接地发生影响。从“人”的观念中产生了两个同样朦胧的要求。一个是“凭良心做事”。在这一信念下,“做事”朦胧地含有要以“人”的方式处理同他人相关的事的意义。“凭良心做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的“自我规则主义”,而不是可以相互提出的要求。另一个朦胧的要求表达在“认认真真做事”的信念中。“认真”就是要尽力做好,不要马虎对待。“认真”并不是一个伦理的劝诫,它要人努力避免的不是一种伦理过失,而是因疏于认真考虑和未尽力而犯下的错误。在免除了伦理的关切之后,一件事是认真做的还是不认真做的这种区别就非常微小了。前已说明,“做事”本质上被看作同人的能力而不是德性相关。既然“做事”并不必然影响到一个人的“为人”,因而没有“做人”重要,“认真”二字便仅仅是一种弹性的要求。一个人不可以不“做人”,“事”却可做可不做,可做大可做小。从这里便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常常在私下里把在“外面”“做事”称作“混”。“混”是“认真做事”要求的反面,是它的蜕变形式。一个人如果在私人生活圈子里“混”,大家就会远离他、回避他,但在“外面”“混”,则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因为透过这种日常意识的眼光,人人都在“外面”“混”。
这两种朦胧的要求虽然不包含明确的规则,但同“策略主义”仍然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它们诉诸的根据不同。“凭良心做事”诉诸的是好“人”的“心”——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拒绝以“非人”的方式对待哪怕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认真做事”诉诸的是与人交往的规则主义,这种态度拒绝放任主义。所以在根基上,这两种朦胧的要求都与单纯的“策略主义”相矛盾。在“做事”的观念中,交织着各种观念的片断,它们之间时常会发生矛盾、冲突,但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都不能够发展成为贯通整个交往实践观念的中心线索。
九
既然“做事”观念与“做人”观念一样,产生于公共交往不发育的历史生活,那么它会不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随着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而死亡呢?
认为现代化就要抛弃传统中保持的所有东西这种看法是未经反思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同前现代文化传统的彻底断裂,而是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嬗变,即传统中有生命力的因素与新生活方式的文化内涵相互嵌入,共生为新的文化体系。西方民族的基督教并未因现代性而丧失存在的根据,其他一些民族的宗教也是如此。中国没有全民宗教传统,它的世俗传统中那些尚未失去其激励人心的生命力的哲学与伦理精神,可能就是它的可以经现代性文化嬗变而保留下来的东西。一种传统中,只有那些仍然在日常语言所表达的日常意识中具有意义的文化成分才保持着生命力。在交往生活的转变中,有些曾经是核心的成分逐步地边缘化,而有些原来是边缘性的成分逐步核心化;这些成分中的更微观的要素也将不断发生变化;有些渐渐失去生命力,有些则涵入现代生活的文化意蕴而获得新的意义;有些新的要素加入进来,并与那些获得新内涵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吸纳,形成新的成分。现代交往生活在令传统逐步剔除旧成分、改变旧形态的同时,又嵌入到它们共同生成的新文化体系之中。
注意到“做事”与“做人”都是仍然活在人们日常意识中并保持着意义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做事”观念之所以能够保持着生命力,可能同它的三个主要优点有关。首先,它同“做人”观念一道,以通俗的方式在日常意识水准上合理划分着私人交往生活和公共交往生活这两个对中国人而言有着重要区别的生活世界。第二,抛开其蜕变形式,“做事”观念同中国人私人生活中的“人”的观念和“心”的观念有相容性,使人们在公共交往事务上能获得某种朦胧的方向感。第三,“做事”观念同中国人总体地、朦胧地把握实践事务的方式相合。
有理由做这样的展望:在现代性文化嬗变中,“做事”观念会比“做人”观念发生更大变化。因为,尽管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国人重视家庭亲情,使父代与子代家庭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中国人的私人交往生活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面貌,但随着公共交往生活的扩展和发育,大家庭正在分解,家庭正在边缘化,成为更纯粹意义上的私人生活和私人关系的领域。虽然“做人”观念在这个逐渐变得窄小却仍然重要的世界里还有意义,但它在人们日常意识中的地位将会下降,并且将不断地纳入与公共交往生活方面那些有效性要求相容的内容。“做事”观念的情形则可能十分不同。“做事”一向被理解为离开家庭核心世界的、与“外部”陌生人的交往实践。在日常意识中,这种交往实践与其说是出于人的自愿,不如说是出于繁荣家庭的责任和使命。而今,那个不发育的公共交往领域不仅正在迅速发育,而且开始排挤原来的核心世界。这意味着,在这种交往生活方式中人们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将变得更重要。当这种要求具有了公共性时,所形成的公民权利、公民关系、民主观念便将塑造这种交往生活的新面貌。问题是,那个被看作“做事”的目的的核心世界在边缘化之后,它的繁荣是否还将在日常意识中表现为“做事”的目的?这个正在边缘化的核心世界,现在仍表现为中国人的私人感情的寄居之所,那么它是否将以这种“身份”存活于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世界?或许,如同今天可以观察到的那样,它将仍然是中国人的目的和生活意义的所在,但是它将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和生活意义。不言而喻,这些发展都将使一直被理解为“做事”的世界极大地扩展其范围和生活内涵。这种发展未必使“做事”的观念失效,而是将使它具有新的内容。日常语言中的“做事”观念的笼统的总体性,恰好使它能够容纳这些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