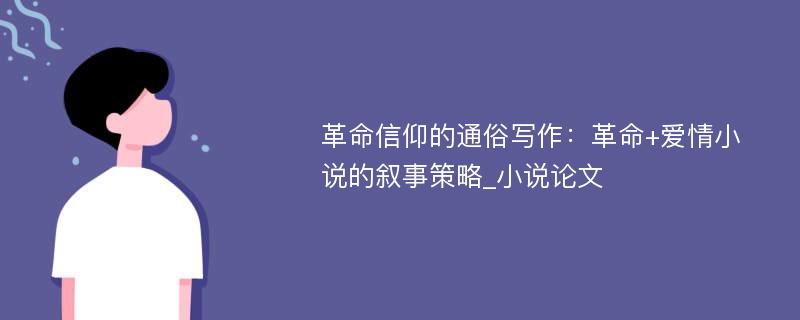
革命信仰的通俗化书写——“革命+恋爱”小说的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恋爱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1)03-0057-05
作为早期普罗文学运动(1928-1930)的主要创作实绩,“革命+恋爱”小说在1928年以后的迅速流行,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由于“革命+恋爱”小说作家的左翼身份,使得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都局限在主流的文学/政治二元评价系统之内,它作为当时市场上受欢迎的畅销小说的事实往往被刻意忽略。因为在传统的文学/政治二元评价体系内,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市场成功、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革命+恋爱”小说作为早期的左翼政治宣传文本,与受读者欢迎的畅销读物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理顺。
而事实上,站在今天新的历史坐标上,将“革命+恋爱”小说置于通俗/商业文学的框架内,对其做一回顾性的俯瞰,上述矛盾即可迎刃而解。90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出现的“主旋律”小说,似乎恰能与“革命+恋爱”小说形成文学史上有趣的呼应,二者都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市场化、商业化之间的矛盾中求得了巧妙的平衡。如同今天的文坛并不把“主旋律”小说当作纯文学文本一样,我们是否也可以将“革命+恋爱”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叙事策略联系起来,从新的角度对它的特质进行考察呢?
一 先锋性与市场化
其实,当时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将其归为“海派”,指责它有文学商业化的种种恶习,虽有失偏颇,却已经提供了另一种批评思路。“革命+恋爱”小说与商业炒作之间的关系在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中已有论述。前些年,随着左翼文学研究的持续升温,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一般都将“革命+恋爱”小说的这一特性定位为“青春特质”(见《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青春特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流行特质”(见王智慧《时代急流和作家之舟——论20年代革命文学的流行特质》,载《东岳论丛》2002年第1期)。事实上,“革命+恋爱”小说,作为那一时代曾一纸风行的最时髦的读物,具有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性,是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存在”。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爱情和革命、性与政治这两大流行和尖端的题材结合起来”① 以通俗文学的话语及其表达方式来诠释革命信仰——将抽象的革命信仰转变成适合一般大众阅读口味的浪漫传奇。它的产生和流行乃是大众心态、商业炒作、文学生产等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如将其与通俗文学的几个代表性的文本类型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在小说的基本元素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通俗文学的特性。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危机使得资产阶级文学再也无力建构它上升期时的宏大叙事,反之,在它内部既产生了现代主义的不肖浪子,又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一“掘墓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早期普罗文学的兴起既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潮流“接轨”的产物,又与现代主义文学有密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某种先锋性。对先锋的追趋,很快就转变为潮流。
由于欧美及日本各国文学创作中的左翼倾向,使得当时国内文坛皆以“左倾”及表现下层民众生活为追赶世界潮流,因而具有某种先锋、前卫姿态。创造社的集体转向,以及太阳社成员受日本左翼文学影响的激进姿态,都成为当时文坛关注的焦点。同时,与左翼、革命相关的书籍也一跃而成为读者心目中的新潮读物,“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一样地平安在上海流行着,《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共产主义ABC》和其他关于社会运动、国际运动等新书,非常畅销”。② 革命成为时髦名词,商业利润的操纵杆迅速地促成了左翼/革命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当时的老牌杂志如《现代小说》纷纷转向,声称要在“新兴文学”方面努力,连唯美主义的《金屋》月刊,也追趋新潮,翻译《一万二千万》招揽读者。用蒋光慈的话来说,“革命文学成为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不但一般激急的文学青年,口口声声地呼喊革命文学,就是一般旧式的作家,无论在思想方面,他们是否是革命的同情者,也没有一个敢起来公然反对。”③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一时风光无限。
在大革命失败后苦闷压抑的时代氛围中,民众因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寄希望于新兴的政革力量,渴望在小说中看到社会变革的希望与曙光。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恋爱”小说的先锋姿态中又融入了现实关怀,因而倍受民众关注。但可惜的是,作为左翼文学的早期创作,它没有能在先锋和现实关怀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而是在小说中掺入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元素,使先锋的批判力量巧妙地变成了对大众心理的抚慰。但这也是它能获得市场成功的关键所在。
另外,“革命+恋爱”小说“作为一种城市先锋文学”,与“新感觉派”小说一样,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有着密切联系,它“创造了一种美学上的强烈震撼与冲击,有力地摧毁了传统的美学范畴和标准,开拓了现代审美新空间”。④ 现代都市景观作为全新的审美对象被引入小说。蒋光慈的《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丁玲的《韦护》、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等,都是以现代化大都市作为背景,电影院、公园、舞厅、夜总会、百货公司、高级旅馆、咖啡厅是小说中常见的场景,都市男女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与传统模式形成极大反差。现代都市摩登气息加上革命、恋爱,给读者提供了最前卫、新潮的生活方式的样板。正是这种先锋姿态,满足了读者追趋时尚的心理,使得小说能迅速占领市场。
二 公式化与类型化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各种原因,众多革命文学青年齐聚上海,这便是“革命+恋爱”小说的创作主体。这些革命文学青年被称为“亭子间作家”,他们的创作心态与“五四”时期经营同人刊物的启蒙先驱已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以及启蒙教育民众的宗旨,这时候已经被现实的生活问题代替,上海对他们的吸引是书局和期刊报纸的众多,稿酬制度的完备,文化市场的成熟,具备了“职业作家”出现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同时,上海的出版商人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大众对革命文学的追趋中所蕴藏的巨大商机,进而用商业手段大力经营左翼/革命文学。
“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分给作家们,便可购得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来中国的事情。”⑤ 沈从文当年对革命文学的评论或许有偏误,但他却发现了商业机制侵入文学领域,使文学创作沦为文学生产的事实,在这种机制下,作家几乎是有意识地按照市场的需要来生产特定类型的小说,“一部分作家或因不太明白政治,或因太明白政治,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名称,随之陆续产生。”而“革命+恋爱”小说恰逢其时,以迅猛的速度成为最受市场欢迎的畅销读物。
以蒋光慈的作品为例,可以看到当时“革命+恋爱”小说的畅销情况:
《野祭》,上海现代书局1927年11月初版,1929年12月5版,1930年6版,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1版;
《菊芬》,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1930年12月4版;
《冲出云围的月亮》,北新书局1930年1月初版,1930年8月8版。⑦
而当时其他作家的小说,只要署上蒋光慈的名字,马上就能成为畅销书。
作为“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蒋光慈受到了来自左翼文学内部和自由主义文人的严厉批判。茅盾批评他小说的公式化,人物的类型化,都切中蒋光慈小说的致命弱点。但以今天对大众文化的评价体系而言,公式化、类型化正是通俗小说的叙事策略,是某种创作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并被不断重复生产的标志。长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有意无意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作家是有意识地自我复制,使自己的创作公式化、类型化,蒋光慈在日本就过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你若要出名,则必须描写恋爱加革命的线索。”⑧ 钱杏邨也曾说过:“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点革命,小说是必须有女人,有恋爱。革命加恋爱小说是风行一时,不胫而走的。”⑨ 从1928—1931年间,蒋光慈的作品被大量复制和模仿,形成了“革命+恋爱”的普遍模式,从主题、思想、形式到人物、风格,所有的“革命+恋爱”小说都长着似曾相识的面孔,“蒋光慈的名字也已经脱离了他的作品成为一个不断被消费的先锋符号。”⑩
“革命+恋爱”小说的成功的公式化,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由两个通俗文学的基本元素构建而成的:政治/革命(隐含暴力因素)与情欲,二者交织的社会景观,将通俗文学用以吸引读者的所有元素共冶为一炉,形成既新鲜刺激又熟悉可读的文本,这是“革命+恋爱”小说与众多的通俗小说文本之所以相似的关键所在。
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最有吸引力的卖点,不论是旧式通俗小说中的宫闱秘事、公案小说、黑幕小说,还是今天的反贪题材的电视剧,都在迎合民众对于高踞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人物及权力运作过程的好奇心理。而“革命”作为那一时代最为激动人心的社会公共领域的重大政治事件,凝聚着民众的热望。读者阅读与政治相关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动机并非全是娱乐,也混合部分严肃的现实关怀。但由于政治事实上不可言说的诸多禁忌,大众文化在对政治的消费过程中只能对它进行巧妙的转移和替代,以金钱、情欲、暴力、命运等元素与政治的纠葛来呈现政治的面貌。而“革命+恋爱”小说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政治的替代,它借用的元素是情欲和革命(暴力)。
当年“革命+恋爱”小说的流行,给大众提供的是了解革命/政治“真相”的窗口(尤其是有关秘密集会、游行、工人运动、暗杀、暴动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流行的反贪/反腐败题材的电视剧给观众提供的也许是同样的东西,都是文学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涂抹上政治色彩的产物。小说中描写恋爱的情节也因此增加了新鲜刺激的魅力。如孟超《爱的映照》中,外面正在革命暴动,男女主人公竟然在亭子间相拥热吻。与今日风靡全球的“007”系列影片中,男女主角在炮火硝烟、惊涛骇浪中的浪漫缠绵,其实是异曲同工的。
另外,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屡屡出现的暗杀(如《菊芬》菊芬刺杀政府W委员)、暴动(如《短裤党》工人处决工贼“小滑头”以及纠察队处决大刀队队长)的情节,都是因披上了“革命”外衣而合法的暴力因素,而适度的血腥暴力在公案、黑幕小说以及今天的反贪题材的电视剧中乃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正是涂抹政治色彩的通俗文学作品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
既然书坊老板和作家们都知道“小说必须有女人,有恋爱”,那么将革命的故事与恋爱内容结合起来无疑是最能新潮,最吸引读者的小说。有意思的是,在将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是如钱杏邨所说的,不少作家又回到了“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的老路。洪灵菲的《前线》中霍之远先有恋人林妙婵,后又与革命同志谭秋英、褚珉秋情志相投。人物风流自赏的性格,流连于“三美”的心态,隐现传统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的旖旎风光。而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里的汪中与玉梅,《破碎了的心》中的汪海平与吴月君,都有些才子佳人的味道。虽标榜新潮,但其实为迎合市场需求而落入前人窠臼,又表现出与老派通俗小说相似的某些特性。
其二,也是较为少见的,是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小说虚构了革命失败而幻灭的女青年王曼英以身体报复社会的故事,某些部分的描写便近乎恶俗,对女主人公以身体引诱男性过程的过于详尽的描述,有迎合读者窥视欲望的嫌疑,如果剔除其中有关革命的内容,几乎可以混同于海派小说中张资平、叶灵凤的作品,然而可以预料的是,这是蒋光慈作品中重版速度最快、版次最多、最受市场欢迎的一本。
有趣的是,在处理个人/情感领域与公共/政治领域的冲突时,革命者与侠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侠客都将情感/情欲视为武功修为的阻碍,要练好武功就必须舍弃个人的儿女私情。在早期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革命信仰与儿女私情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对立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要以放弃爱情的举动来证明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信仰。
但武侠小说发展到后期,侠与情逐渐呈现水乳交融之势,爱情故事的跌宕起伏与侠客武功修为的渐入佳境往往相得益彰。“革命+恋爱”小说发展到后期,革命与恋爱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排斥恋爱转为促进恋爱、甚至决定恋爱,由对立而变为融合。甚至“革命信仰就在恋爱行为的象征性诠释过程中被建构成型,‘恋爱’最终构成‘革命’的具体修辞形态。”(11) 在两种类型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个人/情感领域与公共/政治领域的冲突最终都融合、统一了,其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将男女情爱的内容排斥在小说主人公的生活之外,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势必大打折扣,可能是促使作家寻求二者融合的重要因素。
另外,许多“革命+恋爱”小说中的主人公颇有侠气,蒋光慈开创了“革命+恋爱”模式的《野祭》的主人公就叫“陈季侠”,他的自传性作品《纪念碑》中的男主角就叫“侠生”,而“侠生”和“侠僧”都是蒋光慈的自号。《鸭绿江上》的《自序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我曾忆起幼时爱读游侠的事迹,那时我的小心灵中早种下不平的种子。”(12) 可以说,那个时代的青年投身革命的最简单朴素的动机,正是扫除社会的不平,在这个意义上,侠客行径与革命行动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在武侠文化的熏染下,新生的普罗文学作家的小说中也多有类似于英雄救美、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情节,如《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李尚志对王曼英的拯救,又如《菊芬》中女主人公刺杀政府委员。钱杏邨就曾批评阳翰笙的《转换》(《地泉》三部曲之一)中女主人公获救的情节就像《火烧红莲寺》。(13)
“革命+恋爱”小说中,至少有黑幕、言情、武侠等多种通俗小说文本的特征,或者可以说,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借用了许多通俗文学的叙事策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早期普罗文学的成功之处,将革命的观念混搭在民众易于接受的、富于娱乐性的、与通俗文学相似的畅销小说中,不着痕迹而深入人心,正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三 简单化与理想化
将现实理想化、简单化,是“革命+恋爱”小说采用的另一通俗文学叙事策略。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恋爱”小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时代青年从现实/日常世界中飞升,进入超脱/理想世界的愿望,这二者的冲突是人生无法摆脱的永恒困境,而通俗小说在处理这一冲突时只呈现冲突的形式,而不追究冲突的结果,着重表现这一过程,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超越现实世界的短暂精神享受。
如同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虚拟色彩一样,情种和侠客们从不为生计发愁,革命世界里的男女也基本不用考虑饿肚子之类形而下的问题,他们的世界都被简化统摄于唯一元素之中,这个元素既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核心内容,又是一切价值评判标准:情痴们心无旁骛地投入轰轰烈烈的爱情,侠客们一心一意打抱不平、替天行道,革命青年则专心致志革命,恋爱也成为革命的附属品。
就像其他通俗小说一样,“革命+恋爱”小说中的价值观念呈现简单二元对立,正如茅盾所说的,“常常把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中间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机械”(14),这种价值判断上的简单明了,提供了一般读者熟悉的符码,不需要思考和参与,不需要怀疑精神及批判理性,容易被“不假思索”的读者认同,阅读过程十分酣畅淋漓。在公式化的手法创造出来的表面纷纭复杂、而实则熟悉明朗清晰单纯的文学世界里,革命与反革命的简单二元对立,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对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进行道德、情感上的预判,获得进入虚拟的小说世界的享受。小说结尾时,所有的困难都会被克服,“好人”一定打倒“坏人”,瞿秋白批评这种“没有失败,只有胜利”,“一厢情愿”的写法是“团圆主义”(15),但这恰恰与大众喜欢大团圆结局的习惯心理相吻合。
事实上的革命当然远非小说中那样理想化和简单化,在后来对“革命+恋爱”小说的批判和清算中,茅盾、瞿秋白、钱杏邨都指出它没有正确地反映现实,犯了“革命的浪漫谛克”的错误。考虑到蒋光慈本人在党内的工作经历,可以推断他并不缺少实际工作的体验,其他的作家如张闻天、胡也频、阳翰笙、丁玲等,也都直接和间接地接触过革命工作,并非对革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他们不写革命工作的琐碎、血腥与严酷,而是将革命浪漫化、理想化和简单化,正是干预现实与逃避现实两种矛盾心态共同作用的产物——既不愿放弃以文学作品促进革命斗争的目标,又不能面对大革命失败的现实。这一点,鲁迅看得最透彻,“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同时,鲁迅也指出了这种超越时代的文学“独自飞升”,其实是“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16),取得市场而已。这一分析对于一切“超越时代而独自飞升”的文学反而能获得市场成功的现象都是适用的。
提供虚假的精神安慰比起直面现实来当然更为取巧,在某种程度上,也这也是“革命+恋爱”小说为迎合读者、市场的叙述策略,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沉重、压抑的时代氛围中,读者渴望超越现实的期待视野决定的。作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浪漫谛克”弊端的批判者,茅盾本人的作品《蚀》提供的是“革命+恋爱”的另一种叙事方式,他严格的现实主义笔法呈现了革命低潮的真实面貌——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在革命潮流中的追求、幻灭、激愤、彷徨,因此在《蚀》三部曲中,看不到出路。但或许正如王德威所说的,在茅盾那里,革命低潮的真实呈现反而使得“革命+恋爱”本身成为社会的病症;而蒋光慈式的“单纯而真诚”的乐观,使他小说中的“革命+恋爱”看来正是治愈社会种种疑难杂症的良药(17),这正是小说要完成意识形态宣传使命所需要的效果。
结语
作为左翼文学中带有浓重商业色彩的小说样式,“革命+恋爱”的潮涌潮退在短短几年间就完成了——这正是一时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品很快就被新的潮流代替的缘故。它虽然没有给左翼文学留下什么经典之作,但客观上,由于借助商业/通俗文学的迅速与广泛传播,在左翼文学发展初期使“革命”观念深入人心,直接影响了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小说中,革命是明朗纯粹、无比浪漫的世界,它以无与伦比的魅力吸引着青年人投身其中,这种基于主观臆断的对革命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固然是错误的,但事实上,这正是那一时代无数的年轻人为革命吸引,并投入革命的原始动力,胡耀邦、陶铸就说他们是读了蒋光慈小说以后参加革命的。荒煤曾回忆当年阅读“革命+恋爱”小说的感受,“说实话,对那些革命文学所宣传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我并不懂。但是又朦朦胧胧似乎懂得了四个字,那就是‘革命’和‘爱情’。……‘革命’和‘恋爱’这四个字,概括起来讲,无非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于一个刚刚迈进青年时期的贫困孩子,这都是可以渴望而不能实现的美丽的希望。……这种革命加爱情的作品也就恰好一箭双雕,正中下怀。它至少启发了青年,倘使你要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爱情,你都得革命。它终于使我重新感到还是要面向人生,要革命。”(18) 作为当时的文学青年以及受小说魅力感召的读者,荒煤的话充分证明“革命+恋爱”小说在当时青年中间的巨大影响,这正是左翼文学所追求的文学的社会宣传效果。钱杏邨在评价早期普罗文学运动时曾说过:“这些不健康的,幼稚的,犯着错误的作品,在当时是曾经扮演过大的角色,曾经建立过大的影响。这些作品是确立了中国普洛文学运动的基础。”(19) 对于“革命+恋爱”小说来说,这个评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但却无法体现它“离开革命”而“独自飞升”的特点,以及它与通俗文学样式之间的密切联系。
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出现的“主旋律”小说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宣传运作与市场化、商业化之间完全可以实现有机结合。如果参照今日文坛给“主旋律”小说定位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革命+恋爱”小说这一左翼文学中的“特殊的存在”的评价,以及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注释:
①④⑩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第89页,第40-41页。
②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③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⑥ 沈从文:《“文艺政策”探讨》,《沈从文批评文集》,第73-74页。
⑦ 《蒋光慈研究资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5页。
⑧(13) 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蒋光慈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页。
⑨(19) 钱杏邨:《〈地泉〉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5页,第876页,第877页。
(11) 颜琳:《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2) 蒋光慈:《〈鸭绿江上〉自序诗》,《蒋光慈文集》第2卷,第86页。
(14) 茅盾:《〈地泉〉读后感》,《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第872页。
(15)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第440页。
(16) 鲁迅《文艺与革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17)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18) 荒煤:《一个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荒煤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