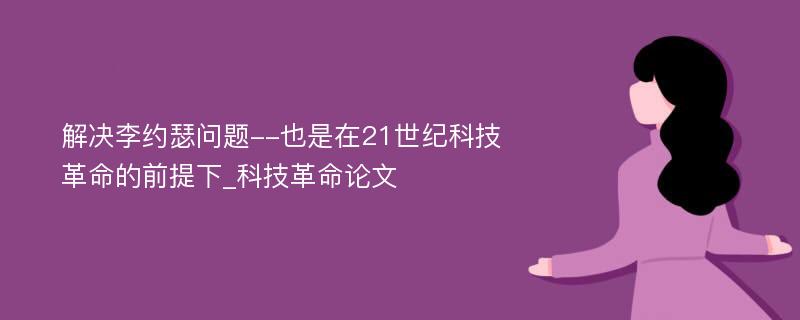
“李约瑟难题”求解——兼论21世纪科技革命的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前提论文,世纪论文,科技革命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1999)05-0029-04
未来的世界经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振兴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与程度。当国人普遍接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预示了在21世纪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也离不开它得以植根的经济基础及文化,但这不是全部。我们的研究者往往过分注重经济与文化因素,并局限于此,而完全忽略了影响并决定社会进程与科技革命的另一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历史表明,社会进程、重大科技革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大。
一 从“李约瑟难题”说开去
致力于中国科技史及中西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李约瑟博士,在穷其一生研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十八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注:李约瑟.四海之内[M].劳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9~80.)这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围绕“李约瑟难题”,中外学者作出种种努力以求解,其中有种意见似乎得到了公认: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在近代中国发生,与中国传统儒学很有关。这种意见认为,与西方文化倡导的天人相分相反,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1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以天为最高原则,讲究的是天人和谐,人顺应自然,但这只注重二者在精神层面的统一,忽略二者的主客体分立关系,而这与科学所要求的超越、征服精神不一;(2)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究的是尽心、 尽性、尽伦、尽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只注重内圣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忽略“事功”精神,以至于最终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而“泛道德主义”恰是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
从文化角度切入“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正确而又深刻的,但仅停留在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分歧中是不够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除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之外,也有天人相分的一面,如荀子认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注: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3.),并强调天命不能干预人命,人能“明于天人之分”,人能“制天命”、“裁万物”(注:夏甄陶.论荀子的哲学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42.)。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并不只是西方文化的必然产物,而是全世界人类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不同文化精华的凝结。“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原始的火药箭和圆筒枪(10至13世纪)很快在欧洲发展成为14世纪的弹药枪炮,摧毁了封建堡垒。”(注:李约瑟.四海之内[M ].劳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0.)正是东方人提供的火药在欧洲发展为枪炮,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扫除了其前进道路上的堡垒,才使新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得以形成与巩固,而这一切正是科技革命发生并成功的先决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经历了数百年的准备、孕育,在此期间,欧洲人处于世界大民族中,吸收了“阿拉伯的学术知识,印度的思想意识和中国的工业技术。”(注:李约瑟.四海之内[M].劳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6.)可以说,没有先辈的记数法,就不可能产生伽利略的物理数学理论;没有中国的铸铁技术,就不可能建成现代的兵工厂与远航的船只……历史总是在超越国界的继承中得以发展与创新,科学技术亦如此。欧洲人与欧洲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盲目排外,而是尽可能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并为己用。正是这种虚心的继承与吸取,孕育了革命的种子,并直接导致了现代科技革命。因此,将现代科技革命仅“归之于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人的天赋才智”(注:李约瑟.四海之内[M].劳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9.)的看法, 乃是目光狭隘的观点,表现出的是自欺欺人的高傲。历史表明,近现代意义的科技革命并非西方文化的必然产物,而是东西方文明共同碰撞、吸收与容纳后的结晶。在西方抑或东方,其产生的可能性都存在,而最终与近代中国失之交臂,主要应当归因于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
二 近现代科技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近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与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直接阻碍了这场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发生。我们肯定文化在科技革命中的作用,也同意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不同一性,但“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694.),文化总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它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和一定的阶级意志服务。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传播与论争不仅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相反还要受到它的制约。所以,我们在讨论科技革命与文化的关系时,避开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不明智亦不可能的。
近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发生在16至18世纪的欧洲。这个时期,欧洲先后出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力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为其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进行不懈的奋斗,并最终取得胜利,这就为代表新兴阶级的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毛泽东说过:“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胜利,保证了其新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而这种新文化正是科技革命的深刻的现实土壤。新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对一切旧的代表落后意识形态及不利于新科学发展的旧科学采取敌视与批判态度。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政治制度上的胜利,是近现代科技革命发生的关键性先决条件。
而与此同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小农经济思想、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直接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与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导致了近代科技革命与中国失之交臂。
第一,“重农抑商”的小农意识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思想强调“以农为本”,视科学技术活动为不务正业,这使近代科技革命缺乏培育土壤和心理支撑。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垄断工商业,并不惜采取闭关锁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这又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如15世纪郑和逝世以后,中国封建制度对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施加压力,彻底摧毁,仅开辟广州、泉州两个通商口。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和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虽然各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经济方面却丝毫没有触动。直到19世纪初鸦片战争发生后,才使中国的文士贵族感觉到现代工业化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了。对商业的抑制特别是闭关锁国,完全斩断了中国科技发展所需的外部刺激和营养。与世界科技进步的脱节,导致中国科技的长期缓慢发展。
第二,“学而优则仕”的官僚政治不利于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仕,即文士官僚,指古代中国掌握文学和行政的优秀知识分子。在“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秩序下,大量知识分子优秀人才不是潜心于各自的研究领域,而是热衷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仕途。一方面,中国人的精神一向反对无原则的权谋、不正直的行为和奢糜的生活,认为争夺和攫取的行为是品德高尚的人不屑做的,从而远离工业生产和商业。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巩固江山、维护统治的功利性目的,其注意力主要放在“文武之道”上,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将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几乎全部拢络在自己身边,造成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而众多的统治者关注科技又往往出于一种猎奇心理,因此对科技人才的挖掘、培养不力,对科技的投入也不充足、不稳定。再次,科技人才追求“仕”的官位,对统治者有很强的依附性,没有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自由权,只是“奉旨”而行,这也是导致近代中国科学理论薄弱、技术不发达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缺乏科研自由、学术自由就根本谈不上科学技术的革命!官僚政治不仅垄断人才,而且垄断科学技术本身及其产品,这也是人才垄断的一个必然结果。封建统治者们或将科技应用于个人生活资料的制造上,或将科技作为装饰,而且严令禁止在民间流传和应用。综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有名有成就的科学家首先就是官府的官员,如张衡、僧一行、沈括等。而其科学成果又何曾流传民间?这就破坏了中国科技自身的继承与发展规律,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第三,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抹杀了成长中的科学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并非先天缺乏科学精神。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8.)认为天并不是在人之上,而是与人一样的自然物,人与天是平等的,他将人作为独立的存在物从“天”的束缚中分离出来,将人的主体性高扬,将人看作一种独立于神之外又不受神所控的自然存在。将人从附属地位解放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本体存在,正是科学精神的先决表现。荀子更视人为“天下贵”的生灵,否定天对人的支配地位,指出天的无意志及其自身的运行变化,从而得出结论:“明于天人之分”,人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努力认识天、驾驭天、利用天,是为“制天命”。由老子的将人作为独立的本体存在到荀子的将人作为天的主宰及认识主体,不正是科学精神的表现吗?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在刘禹锡那里得到更明显的表述。刘禹锡认为,天与人虽然都贵为“万物之尤者”,但二者又各有所长,各有所不能,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交相胜”(注: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89.)的观点。他明确提出天与人的不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不同,人不但不受外在的自然所束,相反,天的神秘只不过是人为的加上的外衣,人的任务就是去掉这层外衣,尽力把握自然界的“数”(内外联系)和“势”(发展趋势),以减少自然的危害。将人由认识主体进一步提升到人的主体性,指明人类对自然的超越及人类自身自觉的选择性,正是科学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充分证明。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科学的种子,但中国古代这些先进的科学理论,却被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扼杀在成长的摇篮中。
科学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便是主客相分、天人相分,发展科技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实证的方法,而这些都与维护封建统治相矛盾,因而为封建统治者所排斥、拒绝。封建主义进行统治的一大法宝就是愚民政策,而这又是与天人合一紧密相关的。封建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将天人合一视为最高境界。封建意识形态秉着内圣外王的需要,认为天是最高存在,人的价值就是达到天的境界,完成个体的超越,但绝不能超越天。因为在封建专制意识形态中,天就是王,超越了天就是超越了王,而这是不允许也不可能的。所以以天人相分为基本特征的科学精神不但不可能融入意识形态中,反而被窒息。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在于,统治者以“天子”的身分来管理人们,人们应该顺应“天意”,服从天命。科学精神及科学技术的研究很容易揭示其荒谬性,将广大人民群众从盲目听从中解放出来,彻底瓦解封建统治的社会思想基础。而对这一点,封建统治者是很担心和很不情愿的。因此,他们从内心抗拒、反感科学精神及其研究。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一面完全为意识形态所压制。在此原则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智统一”的目的,实际变成了智统一于仁。牟宗三先生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先天缺乏科学精神,只是代表科学的“知性主体”屈服于“德性主体”之下,以知性主体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完全为意识形态中的德性主体所窒息。科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慢慢消弱,根本无法发展成近代的科学洪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罪过。
第四,资本主义的商会从未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取得合法地位,无法引起和刺激科技革命的另一根本因素——需要。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着重大的作用”(注:李约瑟.四海之内[M].劳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80.)。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迫切需要,也极力保护更高的商业利润来满足其欲望。这种欲望极大地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只有科技方面的突飞猛进才能更快更直接地满足这一目的。但中国的手工业行会及商会从未在其政府部门取得过任何权力,这是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不会容许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味以德治为本的意识形态认为“无奸不成商”,根本不保障商人的利益,它以圣人式的苦修来压制人们的欲望,只满足王者无止境的贪欲。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制度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限制商会的范围使它只能起福利互助的作用,对矿业课以重税使它不能生存……合乎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观念在中国意识形态里无法找到支撑点,刺激经济的需要被压制,新的生产怎么可能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更不用说了。以此为条件与基础的科技革命当然就不会发生了。
三 21世纪的经济必将建立在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和谐之中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指出世界五大经济板块(“共产主义的终结,技术转向一个由人工智能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前所未见的人口状况,全球性经济,一个没有在经济上、政治上或军事上占主导地位强国的时代”(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9.))后说:“决定我们经济世界形态的五大经济板块也浮动在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混合液之上。这两股力量内部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驱动经济板块相互冲撞的潮流。”(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这种看法是深刻的。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经建立,就有其一定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它只有与意识形态和谐相处,才能组成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共同推进社会的繁荣。古罗马是典型的例子。
古罗马帝国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吸收了古希腊的先进技术与哲学思想,其成功尤在于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罗马人不如高卢人富于创造力,比日耳曼人矮,比西班牙人弱,没有非洲人那么富裕和机敏,在技术领域和人类事物的理性应用方面更劣于希腊人。他们所拥有的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和统治的才能。”(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 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古罗马的意识形态不鼓励个人主人,而提倡集体的组织,对罗马人来说,永存帝国的集体精神比追求个人的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罗马城市格局也讲究公共建筑,公共地盘大大超过了私人地盘,罗马的富人没有自来水,但有公共浴场。这一切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是不适宜的,用现代人的观念构造不出罗马城,建立不了强大的帝国。可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能使其科学技术发挥到极至,能建造出历经上千年而无任何破碎、磨损的道路与桥梁,能保障罗马城一百多万人的消费(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古罗马是在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和谐中成功的。
21世纪全球的经济政治处于一个新的竞争赛局中,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不再是过去那样在自然资源的配置上进行掠夺,而是一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竞争。但,我们强调,“在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与科技同样重要。”(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2.)任何一个时期, 只要意识形态和科技不相匹配,国家的新旧就无法和谐,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不同的价值观可能运用不同的科技,但要成功,二者必须和谐。意识形态与科技和谐了,才能促进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反之则衰落。资本主义在刚建立其意识形态时,追求最大利润将其经济导上了快车道。可是,高科技如果广泛彻底地应用于人生事务中,最终会导致利润的下降,这与其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不管国家的投资与福利如何巧妙的掩饰二者的冲突、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已浮动在了二者的混合液上,最终只能导致新的意识形态与新的科学技术的和谐。
新世纪是个科技竞赛的世纪,全世界要求人类更高意义的科技革命,而这一切要求意识形态的同步。可以肯定,这场科技革命必定是发生在拥有与之相和谐的意识形态的国度,谁拥有了更先进的意识形态,谁便拥有了领导这场革命的资本,谁便在新世纪的主导地位中加重了砝码。过去的中国,凭借中世纪的优越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合适的意识形态。新世纪的意识形态应当是能容纳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技术,并将之应用于人生事务之中,就如列宁评价马克思主义那样,“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2.)未来科技革命适应着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要求多方位多角度的协作,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统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尊重个人的同时,一味追求金钱与享受,不顾人与自然的和谐,不顾人与人之间的至情,不顾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完全与科学技术本身的精神及所需的团体合作背道而驰,其意识形态无法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领导更高意义的科技革命。新的意识形态应当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注重群体意识与集体精神,这才与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与新科技革命所要求的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正在动摇着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根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新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势的唯一来源,最终的赢家属于那种有能力使人们乐意使用新技术去建造新社会的国度,更新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只能发生在拥有最先进意识形态的国度。
标签:科技革命论文; 李约瑟难题论文; 科学精神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李约瑟论文; 科技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