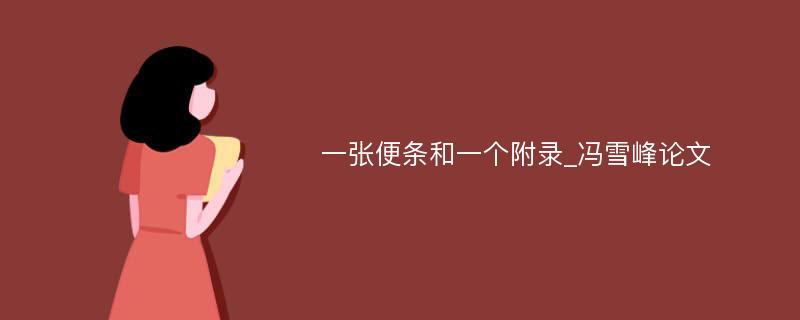
关于一条注释和一篇附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注释论文,附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1980年,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鲁迅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第六卷包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三个集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就在《末编》里面。这一篇的注〔1〕,在发稿时有过一些曲折。
这篇涉及当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许多人事纠纷的文章,其注〔1 〕即题注本来是容易引起是非的。五十年代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的这一条注释,说: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就这样否定了这篇文章,却也注意开脱了鲁迅的责任。至于来信,这只是徐懋庸个人的错误行动,周扬复衍事前并不知道,当然也是并无责任的。徐懋庸冯雪峰在不久前的反右派斗争中刚刚被划为右派分子,正好由他们来承当责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刊出了阮铭、阮若瑛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副题是“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要将争论的责任归之于周扬他们。
我们以为,在新版的注释中,没有必要再这样来谈责任问题,只客观地交代一下本篇发表情况和有关背景就行了。可是,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草拟的注稿在送审时出现了曲折。
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一、二卷是由胡乔木同志审稿的,以后改由林默涵同志审稿了,但一些重要的地方,还是送请乔木去看。这一条注释就送请他看过,他作了一些修订。不久之后,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又给这条注释作了第二次修订。这个第二次修订稿,在倾向上,有点向1958年版的旧注靠拢,个别提法甚至超过了旧注。如旧注说,写信是徐的个人行动,而这回的修订稿则说是他个人的意见了。更加使我感到为难的是,这次修订稿提出参看《新文学史料》所载茅盾作《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文学评论》所载夏衍作《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这两篇文章。当时参加这一编注工作的人员都觉得有必要请乔木同志收回成命,就由我执笔,以参加编注工作的全体人员名义,给乔木写信。我写出第一稿之后,又根据大家所提意见作了修改,写出第二稿。这一段往事已过去多年,我也早已忘记。今天寻东西,无意中发现这两篇信稿,看看觉得还有点意思,也是一点小小掌故,于是拿来发表。这信的第一稿是这样的:乔木同志:
您好!
我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全体人员,仔细研究了您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题注的再次修订稿之后,(感到)现在的注稿中有几处提法使我们在发稿时感到了困难。现在把我们的意见分述于下,请您重新考虑一下。
一、徐懋庸同志写给鲁迅的这信,诚然并不是谁指使他写的,写好之后也没有和谁商量过,但是徐懋庸同志生前在文章和谈话中都反复申述过:信虽是他个人自发地写的,但其中表达的是共同的意见。他是在自己接受了周扬等同志的影响之后,转而又希望鲁迅也接受这种影响才写这信的。在鲁迅方面,也从一开始就并不认为这是徐懋庸的个人意见,所以他在复信中不仅针对徐的来信,同时还涉及了当时周扬同志、何家槐同志等在《文学界》发表的论文。所以,我们认为,徐懋庸的信可以说是个人行动,却决不能说是他个人的意见。
二、关于参看茅盾同志和夏衍同志的两篇文章的事。首先这在注释的体例上就使我们感到了困难。因为《鲁迅全集》应该是多少带有些永久性的书籍,怎么好叫读者去参看期刊上的文章呢?数年之后,如果这一版《鲁迅全集》还有人要看的话,他又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些可参看的文章?再说,《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还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一般读者又怎么能看得到呢?如果真是必须参看,为便利读者计,势必就得把这些文章附在注文之末,这在体例上怎么好办呢?即使抛开体例上的困难不提,即使说可以这样参看,也不好只参看一种意见的文章,关于这问题写过文章的人很不少,例如徐懋庸、冯雪峰、吴奚如、楼适夷等同志就都写过文章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些文章是否都应该参看一下呢?我们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读者中所引起的反响。据我们接触到的一些高等院校讲授现代文学的教师中,反响是颇为强烈的。我们相信,如果作者预料到了这一情况,那么他在决定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必定会更加慎重地考虑一下。当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反应之后,要是我们还在注释中提请读者参看这篇文章,那就不是爱护夏衍同志的态度了。
三、“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采纳了胡风、冯雪峰提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一提法与鲁迅本文有明显的矛盾。鲁迅在本文中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参加商议的人们中,无疑地是包括有胡风和冯雪峰同志的,但不论他们在商议中发表了多少意见,这新口号仍然是经过鲁迅加以肯定才提出来的。[鲁迅明确指出“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如果我们想在这一注文中提到胡风、冯雪峰二人和这一口号的关系,也只能说“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经过和茅盾、胡风、冯雪峰等人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过,这样一改,不是加重了胡风、冯雪峰承担的责任,反而更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这岂不更加会使几位同志感到不快么?]
[再说,这篇文章并不是冯雪峰为鲁迅拟稿的唯一的一篇。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那篇被人们认为具有纲领意义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是冯雪峰根据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加上日常谈话中的意见综合整理而成的。鲁迅在定稿时只增添了极个别的文字,比对这篇《答徐懋庸》的改动要少得多。但是,谁也不会称《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一篇得到鲁迅赞同的冯雪峰的文章”,为什么却要仅仅因为冯雪峰参加过商议就要把这“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说成是冯雪峰提出的呢?]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希望在《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中不要出现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希望所有的注文都能得到普遍的赞同。在一些涉及某些人物评价的注释中,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如果一些情况说出来将会使某些同志感到不快,也可以考虑在可能范围内回避一下,少说几句。但这有一个界限,就是不能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不能歪曲史实。[如果为了迁就少数同志的愿望而把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字句写入注释中去],可以预料必将在多数读者中引起轩然大波。不但有损本版《鲁迅全集》的声誉,而且将成为从另一个方向损害安定团结的因素,这就违背了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初衷了。
我们想,是否可以即按您上次的修订稿发排?或者,仅仅保留注文的开始几句,即简单说明一下该文发表情况,其他一概从略?如果有的同志不愿意如实地反映有关史实,则不如什么都不说。我们相信天下后世的读者是有判别是非的能力,是有把有关史实考证清楚的能力的。〔即使我们愿意一手遮尽天下后世读者的耳目,也将会是力不从心的。〕
由于出版社已和上海出版公司订有合同,发稿期日益迫近,不可能推迟,我们恳望您能早日批复。
肃此布达,顺致敬礼!
一些同事看了这信稿,以为不必写上那些刺激性的字句,我即将方括号([])中的字句删去了。大家以为还不行,于是我又执笔按照大家提出的意见写了第二稿。下面就是这第二稿的原文,原稿上陈早春同志用铅笔略有改动,为排版方便就不具体标明了。乔木同志:
您好!
我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编辑工作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仔细研究了您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题注的再次修订稿,一致认为其中一些提法未尽完善,希望您能重新考虑一下。
一、徐懋庸同志生前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复申述过:他给鲁迅先生的这信虽是他个人自发地写的,但其中表达的意见除了有关巴金部分是他个人的意见之外,其余部分,都是他经常和周扬等同志谈论的题目。所以,人们可以说徐写这信是他个人的行动,却不好说信中所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在鲁迅方面,也是从一开始就并不认为这是徐懋庸个人的意见,所以他在复信中不仅针对徐的来信,同时还涉及了当时周扬同志、何家槐同志等在《文学界》发表的论文。所以,我们以为,似无必要强调徐的这信是否个人意见这一点。
二、关于参看茅盾同志和夏衍同志文章的事。这在注释的体例上就有困难,因为不好叫读者去参看期刊上的文章。再说,《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还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一般读者不易看到。而且,针对茅盾同志的这篇《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在该刊第四辑(1980年1月出版)上发表了一篇《也来澄清一些事实》, 对茅盾同志的“澄清”作了再“澄清”。此外,针对夏衍同志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楼适夷同志也写了一篇文章,大约也将会在某个刊物上发表。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有了不同意见之后,却只是提请读者参看一种意见的文章,恐怕是不很恰当的。据我们所知,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颇为强烈。听荒煤同志说,《文学评论》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论难性质的文章。一些读者认为夏衍同志此文的态度不够客观。如果我们还要在注释中提请读者参看,那就不是爱护夏衍同志。
三、说“鲁迅在复信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他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核对,所以难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是以提请读者参看的两篇文章为依据的。现在既已出现另外的文章公开指出这两篇本身也不尽客观不尽符合事实,是否宜于参看还有待重新考虑,那么,如果仍要保留这几句,似宜提出另外的依据,或具体说明文中何处“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才好。
四、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谁提出的,说“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采纳了胡风、冯雪峰提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似乎也有难处。鲁迅在本文中明说了“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而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参加商议的人们中,无疑地是包括有胡风和冯雪峰同志的,此外,据鲁迅说,“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茅盾同志本人在《我和鲁迅的接触》(《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71页)中谈了一点当时鲁迅先生和他商议这口号的情形,正好和鲁迅本人的文章相印证。我们以为,不论有谁参加了商议,也不论他们在商议中发表了多少意见,这新口号毕竟是经过鲁迅加以肯定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固然没有必要一口咬定说这就是鲁迅一个人提出来的口号,同样,也没有必要说成这完全是别人首先提出来的口号,似乎与鲁迅关系并不很大。鲁迅自己说得好:“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
如果我们冷静地回过头来看历史,两个口号的拥护者都不能说自己是毫无错误和缺点的,但是,比较地说,当时鲁迅本人恐怕要算是错误少些,态度正确些的一个。即以本篇而论,例如,尽管他提出了新的口号,但他依然认为“国防文学”口号“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尽管他在信中对周扬同志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但他依然怀有希望,“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尽管他自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但他在批评徐懋庸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聂绀弩错误地解释这口号。应该认为,在当时参加争论双方中,鲁迅的态度是比较最好的,真不愧是左翼文坛的领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神化鲁迅,而只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其实,在注文中,我们仅仅希望客观地说明有关史实,完全不必涉及是非褒贬的问题。
周扬同志和夏衍同志等后来为革命文艺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有巨大的功绩,这是世所公认的。即使在《鲁迅全集》中的正文和注释中涉及到“左联”时期的一些往事,也不过是一段往事罢了,并不会损伤读者对他们的尊敬。例如周扬同志一九七八年初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那态度比起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来,就使读者认为更加实事求是一些。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怕在注释工作中不够忠实于历史事实,因而遭到读者的谴责,甚至扩大论争。这就违背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初衷。
我们的意见已如上述。我们希望这一条注文仍能按您上次的修订稿发排。第一稿甚好。如果您以为这样不好,那么,仅仅保留注文的开始几句,即简单说明一下该文的发表情况,其他一概从略也行。对一些情况一时不加说明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出版社已和上海印刷公司订有合同,发稿期日益迫近,不能推迟,我们恳望您能早日批复。
肃此布达,顺致敬礼!
乔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后来印成的《鲁迅全集》这条注释中就没有那些内容了。
2
后来,我又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的责任编辑。我建议将《多余的话》作为附录编入,而编辑组不同意,我无法说服他们,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乔木,将两种意见告诉他,问他的意见。他回信说:朱正同志:
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因返京较晚,迟复为歉。
瞿秋白同志多余的话一文,争议较多,因迄今未见手稿,是否经过敌特篡改,难以肯定。全文对了解秋白同志的一生,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究竟情调低沉,编入秋白同志的战斗著作,即作为附录,终不协调,且会给多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以不良影响。这个问题我曾反复考虑,昨晚征求邓力群同志意见,他也认为以不收为好。特告。
来信过誉之处,实不敢当。鲁迅全集新版出版后,又发现了一些失收的佚文,注释中也发现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听说出版社正在准备续出更新的版本,可见作好一件大事之不易。你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所写订正文字之已成册者我也看过了,并且同大家一样表示感佩。近阅周作人回想录,他对鲁迅事迹有些补充,对鲁迅作品的解释也有一些独特的说法,想你早已看过了。
胡乔木
二月六日
为了尊重他的意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也就没有附录《多余的话》。后来看到1991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是附录了这一篇的。我没有把乔木复信的事告诉政治理论编的编辑组。
乔木的这封信中提到我“所写订正文字之已成册者”,是指我的那本《鲁迅回忆录正误》。这书大约给他留下了印象,1984年他看了教育部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之后,在致教育部的信中,提到这一专业“亦可资参考之用”的书籍,就举了姜德明兄的《书叶集》和我的这一本。他的这封信曾在《出版工作》1984年第10期发表,似未收入《胡乔木文集》,现在转录如下,以供关心编辑专业的读者参考。教育部:
7月23日报告阅悉并同意。
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此点姑不置论)。有一些近似编辑回忆、编辑经验一类的书籍,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韬奋的部分著作和一些老报人的回忆里就有这样一些资料;近年出的书叶集(花城出版社)和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前些年出的重庆新华日报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回忆录(?)、三联书店纪念录(?)等,亦可资参考之用。类似的书可能还有。上海出的辞书研究是一种刊物,是专讲辞书编辑的,但内容很多可以举一反三。在历史上,我国著名典籍的编辑经验,也有不少记载,不过需要收集整理而已。(顺带说,我还建议编辑专业应设辞书学、目录学、校勘学〔中国就有这两类的书〕,编目、标题、注释、摘要、插图、索引等的研究和试验,印刷、出版、发行知识等科目。)据我猜测,国外的这类书籍一定是会不少的,例如:三联书店1963年出的《为书籍的一生》就是一本很有用的参考书;循此以求,则参考书究竟必非无法收集,是在有心人的努力罢了。
我的知识太少,如找周振甫、吕叔湘、萧乾、杨宪益、叶君健、张志公(以上只是随意举例)诸先生,以及一些有定评的刊物、丛书、辞书、年鉴的编辑,一定会提出许多具体的指示,使艰难的第一步便于成行。这是就北京说,上海、天津当然也不会缺少这样博学而热心的学者。
这封信写给教育部(因不知直接主管人员),似乎有点大而无当。但为促成这个专业(或编辑、新闻专业)的诞生,我宁愿不惮烦言。教育部高教司可否协助北大、南开、复旦三校具体筹备此专业人员在暑期开一小型讲座,请京、津、沪的几位老编辑略有准备地分头讲几个题目,帮助筹备者能写成一门或几门课的教学大纲?因各出版社老编辑年老任重,请他们到校兼课的希望可能不大,当然我不反对。
胡乔木
1984年7月25日
标签:冯雪峰论文; 胡风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新文学史料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周扬论文; 茅盾论文; 徐懋庸论文; 夏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