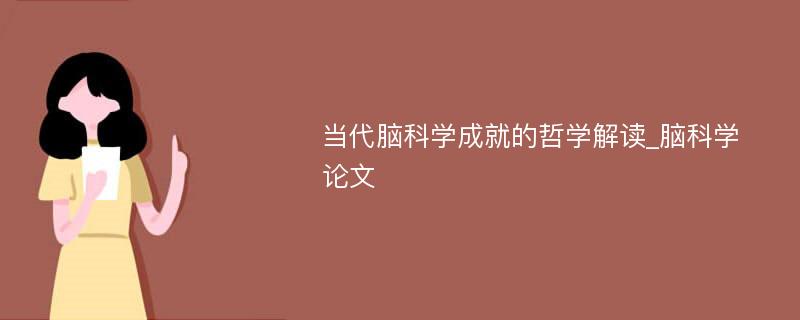
当代脑科学成果的哲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脑科学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7)04—0430—04
在当代,随着无创伤脑成像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神经心理学、脑生物化学、认知科学等新兴边缘科学的研究,科学家深入到人脑内部研究意识,揭示其发生的内在机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但是,由于科学家强调意识的科学解决的方法,拒斥哲学的介入,像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克里克在研究意识时指出,“泛泛的哲学争论无助于解决意识问题,真正需要的是提出有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实验方法”[1],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尔曼也说,“从哲学上探讨意识的本源有其根本局限性”[2],所以尽管脑科学研究成果丰硕,却难以达成对意识的合理解释,甚至不同科学家面对同样的科学成果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理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克尔斯就是根据裂脑人研究成果、李别特(B.Libet)实验而得出了二元论的结论。我们认为,现当代的脑科学成果尚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不是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也不是科学家把实验观察数据、材料放在我们面前,就代替了解释。我们试图利用现有脑科学成果,探求正确解释方法,对其进行转化、升华,引出关于意识的正确的哲学结论。
一、意识是什么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客观反映,同时也对大脑和外部世界有反作用。但是意识如何对大脑和外部世界起作用呢?如果我们不能说明意识的物质作用机制,就有可能认为意识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而导致二元论的结论。我们认为,当代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说明意识的物质作用机制提供合理解释。
第一,无创伤脑成像技术。这项技术是脑科学研究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心灵哲学充满希望的基础。它包括探测脑的静态结构的扫描技术,如计算机辅助X射线断层照相(CAT)、脑电图(EEG)、脑磁图(MEG);探测脑的动态结构的扫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照相术(PET)、磁共振脑成像技术(MRI)。
就PET技术即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术而言,它通过特定的技术和操作,可显示不同脑区活动的状况及特点,甚至可以显示人在阅读、聆听、说出词语甚至思维时脑的情况。有科学家曾经对清醒的被试者的听、看、说到形成词语时大脑区域的细微活动进行PET扫描,拍摄了相应的一组照片,结果显示了大脑区域不同的活动情况[3]。
我们认为:这些图说明的不是语言活动、心理活动的精神基础,就是语言活动、心理活动本身。科学家用PET去拍摄实际上是用另一套话语、另一种方式去描述被试的某一种语言、心理活动及状况,这与被试者用心理语言描述、报告自己的内心活动及状况,如说“我看到了一个字”并无不同。也就是说,被试者说自己听到了什么词,看到了或说出了什么词,的确是对内部活动及状况的报告,不妨就把报告称之为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如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一个词,理解了它的含义,但实际上意识活动不是别的,恰恰就是PET所记录到的整个过程。其次,尽管意识活动就是大脑的活动,但具体的意识活动有不同的脑活动模式,例如“看”、“听”、“说”稍有变化,它们的大脑区域以及相互作用模式就有变化。这正好说明了意识与大脑的同一是多样地实现的。
脑电图捕捉到的东西尽管不那么精确,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记录的电波是由脑表面之下成千上万的脑细胞产生的,它不仅可以显示脑电波的形状,还可显示它们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清醒状态就可以有什么样的波形。这种技术可用来研究大脑的发育、癫痫病和睡眠。有一种睡眠可称作快速眼动睡眠,在这种睡眠中,人肯定会做梦。眼球的快速运动是由于睡眠者观察梦中的移动景物所致。这时用脑电图观察就能发现:有梦睡眠设计脑电图的波形与觉醒时的脑电图的波形是相同的。做梦尤其是可回忆的做梦肯定是一种心理活动,与觉醒时的心理活动并无本质区别,只有形式上、清醒程度上的差别。但它们都不是脑电图所描述的精神活动之外的什么活动。如果认为在大脑的物质活动之外还有纯粹的、没有电化学活动参与的心理活动,那么这种主张与二元论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成果特别多,如“脑电地形图”可帮助人们判断自己的智力类型及特点。此外,MRI、PET等技术还能得到人在视物、形成感觉意识、自言自语、处在清醒状态等时的大脑扫描图像。这些图像所反映的脑活动与被试自己报告的意识经验都是同步的,可见第一人称报告的所谓意识经验其实就是大脑特定物质活动的另一种描述方式。
第二,神经病学的证据。脑损伤通常可由中风、头部受到打击、枪伤、感染等引起。实验观察发现:许多损伤改变了病人视觉意识的某些方面,如“全色盲”、“面容失认症”和“失明否认症”等。但病人的其他一些机能如语言或运动行为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精神过程,也不是神经过程之后或同时发生的过程,它们只是对同一神经过程的另一套描述而已。换言之,视觉意识与神经过程之间不存在谁产生谁、谁影响谁、谁依赖谁的关系,也不能说视觉意识是大脑过程的属性,大脑过程是它的神经基础或机制。两者是同一的,只是因描述的角度、方式不同,才表现为不同的过程。
第三,如果存在着不能等同于、还原于大脑活动的心理活动的层次,那么脑科学尤其是脑解剖学一定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一般认为,高等动物也有心理、意识,如果心理可以形成自己的超越物质之上的层次,那么科学家至少可在这些动物的大脑中发现。可通过对许多动物的分子水平的切割解剖并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既然如此,如还要坚持心理的独立存在,那只有认为它们以非物质、纯神经的形式存在。也许有人会说,心理现象可作为物理、化学、生物属性之上的属性、功能而存在。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么是可以客观观察到的,但至今对它只有猜测。
第四,如果意识有自己的存在层次,那么当然有作用和反作用,当然可以独立地、主动地发挥能动甚至巨大的反作用。问题在于,已有的科学告诉我们,一事物要能产生、发挥作用和反作用,必须有物质、能量、信息,而意识本身显然没有这些东西。其次,世界上也不存在“超距”作用,换句话说,作用要形成,达到它的对象,中间一定有某种媒质起传递作用,如粒子、波或波粒的混合。正如加拿大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本格所述:“对于任何客体X和Y而言,若X作用于Y或Y作用于X,则X是物质的,Y也是物质的。”[4] 最后,即使意识能与大脑相互作用,交流信息,但它们相互作用的联络点何在,交换信息的“接口”何在?难道是笛卡尔的“松果腺”吗?
最后一点是意识经验与相关的脑过程的时间关系问题。如果人们自己所报告的、内部发生的意识经验(如我意识到了我面前树的颜色)与脑内真实发生的神经过程或神经元群的相互作用总是同时的,那么便有根据说两种语言报告的就是同一东西。但问题在于:许多脑科学家发现了两者不一致。李别特在病人的丘脑中埋藏电极。实验发现,人要得到有意识经验,皮层活动必须达到一定时间,如需要500毫秒这样长的适当的皮层活动。李别特推测:皮层活动之所以要达到一定时间,是因为为了从意识上知觉到某种刺激,需要在多个脑区之间不断有再进入的相互作用,因此只有在刺激引起的神经反应持续几百毫秒时,才能产生和维持这种相互作用。我们认为这并不能得出心理活动不同于大脑活动且前者依赖并为后者产生出来的结论。首先,就先有皮层活动后有意识而言,不能把它们说成独立事件,不能认为它们有先后、因果关系。因为大脑中发生的事件和我们所描述的内心状态也许可能就是一回事,可能后来我们所报告的、知觉到的活动就是皮层活动。其次,即便有先后关系,那么整个活动必须是一个物质过程,而意识本身也是一个物质过程。事实也是如此。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人在报告自己在形成自己的意识时,他的整个大脑表面除前部和底部外,都有缓慢升高的负电位,它们集中于运动皮尺区,一般在动作前850毫秒出现。
我们认为,已有的科学成果可引申出一个结论:既不存在独立的实体,也不存在作为独立层次的心理属性或机能,更不存在由它们和别的心理事件所组成的心理王国或精神世界。换句话说,不存在离开物理运动的心理活动,不存在纯粹的、不能还原为物理运动的心理活动,进而也不存在纯粹精神性的,脱离物质过程、事件、状态的心理过程、事件和状态。总之,世界是物质的,除了物质的运动、状态、事件和过程,再没有别的东西。
二、心理语言是对实在的描述吗
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意识”、“知晓”之类的心理语言报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件,也可以用它们描述他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足够诚实,且条件允可,这些报告和描述就是客观的、实在的。如果这些描述是真实的,那么它们所报道的就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事情。当然不是低层次的、原子分子等微观世界中的事件,而是比它们高若干层次且涉及外部世界关系的层次中的过程和事件,如与环境有相互作用、有个体和种系发生发展史的神经元群的相互作用。因此心理语言如果有意义地加以使用的话,其真实的描述对象就不过是物理世界的物理活动、过程、事件和状态。
由于长期以来对心理语言缺乏必要分析,加之对内部心理世界拟人化、非物质化构想,特别是把内省的方式与客观公开的方式对立,从而造成了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常常是对立的,甚至是神秘的。我们可以用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心理语言的实在关系。
在传统的心理图景中,心理语言所描述的事件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第一阶的事件,例如“我认识你”,报告的是我对你有了解这样的事实;第二是第二阶的事件,例如“我知道我认识你”。后一类事件就是通常所说的“意识经验”,它包含有再认、体验、质的感受或现象学性质等形式。由于不能借助功能、机制、工作原理之类的东西予以解释,因此查默斯将它称作意识的“困难问题”。
就已有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说明第一类心理语言或心理事件已非难事。克里克、埃德尔曼、本格等人研究了记忆和视觉过程,把它们看作大脑内发生的神经元群的相互作用或连接模式,例如心理语言所描述的短时记忆,就可作这样神经生理学描述。
首先是输入神经元的持续性或重合性活动,继而大量钙的流入又在靶细胞内触发连锁化学反应,从而释放另一种化学物质,它越过突触,进入输入细胞,起到的作用是使后者释放更多的递质。靶细胞由此变得更活跃,或者说突触更增强了。当被增强的突触的输入细胞又受刺激时,继后的反应将变得更大。至于长时记忆所对应的物理过程和事件,除了上述神经元之间连接的建立之外,还需要细胞粘连分子及生长关联蛋白发挥作用。因为就后一因素来说,它参与了神经元的生长,在长时程增效过程中,生长关联蛋白显然被激活了。在此基础上,可以推测:在执行记忆作业时神经元间接触的增强过程中,钙的流入可能通过生长关联蛋白导致神经元接触的生长的增加,并可借助于细胞粘连分子而使那些接触稳定下来。
“决策”、“计划”和有关的情绪状态也可换成大脑某些部分运动的物理语言,像“欣喜”、“快感”所指的并不是什么纯粹的精神过程。众所周知,药物能影响行为,同时也能在单个突触部位改变化学通讯,甚至导致一些与日常心理语言“快感”相对应的生化过程。服用海洛因会使人产生一种出奇的快感,其实是该药在脑中的物理化学过程。海洛因是吗啡的一种衍生物,而吗啡模拟的是脑内的一种天然递质。大脑释放这种递质,就会出现与“愉悦”等相应的生化过程。因而人脑内的“欣喜”、“快感”可以说是大脑内某种递质的生化反应。
第二类心理现象,即意识之类的二阶心理现象,它们是最难同化的。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其实,人的有意识的经验体验,是其内部发生了两个过程:一是一阶神经活动,二是二阶的对这种活动的自分辨,这种自分辨用埃德尔曼的话说就是大脑神经元集群所形成的“动态核心”的自分辨,它之所以能自分辨,是因为该动态核心中的大量神经元回路的再进入机制。
具体而言,要有二阶意识,首先必须有可以被分辨的脑过程发生,其次是网状上行激动系统要兴奋。因为一个人要报告自己有意识,其前提条件是自己处于清醒状态,处在昏迷或深睡状态不可能有这类报告,而要如此,脑干网状结构中的上行激动系统就必须进入兴奋状态。最后,少数大脑区域出现强烈的、占主导地位的时间兴奋模式。因为一方面,脑内存在强有力的相互抑制系统,因此只有少数的兴奋模式居主导地位。当这种局面出现,人就会体验到所谓的意识状态,即自己意识到了某一对象。如果这种神经兴奋持续不变,人就会体验到围绕一个主题的意识流,即老是想着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如果这种神经兴奋模式发生变化,为另一模式取代,人就会想到,意识到另外的问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注意力转移。
从神经化学的角度看,所谓的主观经验或意识其实也是脑内的物质过程。20世纪70年代,脑科学有一项重大发现,即发现脑内存在着类吗啡物质,即脑啡呔。当这一物质被药物阻断后,则痛觉消失,针刺不再产生疼痛的变化。而通过相同的机制,吗啡可模拟这种自然化学物质,使脑产生大量脑啡呔被释放的错觉。怎样解释这些成果呢?可以这样设想,日常语言所说的主观感觉及其性质,描述的其实就是脑的某种高阶物质过程。
有人会认为我们得出的是同一论的结论,即心理语言同一于物理语言,心理活动就是大脑内神经活动,因而也就无法解释脑科学中出现“多种实现性”问题。如加拿大神经病学家彭菲尔德的实验: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实施电刺激,有时不同时间刺激同一部位,病人会有不同的体验报告,有时不同部位上刺激可出现相同的报告。对于这些事实并不能证伪同一论,而恰恰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一论。从总体上看,所有心理语言如果有意义地使用的话,它们描述的过程、事件就是物理事件、过程。当然有些物理过程不适合用心理语言来描述,尽管一切心理语言可转换为物理语言。另外,就每一心理语言来说,与其对应的物理过程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身上,所指的具体对象可以是不同的。之所以会有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发生,主要根源于神经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因为一个神经元可同时与别的许多神经元处在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由于神经元处在广泛的联系之中,可同时接受那么多的输入,因此神经元激活状态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确切地说,它可处的状态多达10万以上。这种多样性还根源于化学物质传递的多样性。电传递受限于一个神经元接头的被动传导特性,它快而经济,但缺乏多样性。化学传递则不同,它是多样的,因此赋予神经功能以多样性,如一个神经元可同时与1万至10万神经元发生接触;反过来,一个神经元将成为神经网络中下一个神经元的成千上万输入中的一个。
除了由于科学知识限制不能用心理语言对应于具体的物理语言外,还有社会的原因。心理语言不可能完全对等地,不顾及社会文化、习俗而绝对地转化为物理语言。心理语言是一种处在宏观的、大跨度层面的非常抽象、笼统、浓缩而概括的语言,加之根源于隐语和类推,带有隐语、象征的特点,因而它常常用不多的语词或音素,指谓非常复杂、丰富多彩的现象,就像“水”、“大学”、“生气”、“舒服”之类的日常语言一样,它们描述的对象换成微观层次的语言来描述,则很繁琐,且难做到完全的对应。例如要用科学语言说水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可以从构成上说有H[,2]O,也可以从色觉、嗅觉上说无色、无味,等等,但很难把水描述得详尽无遗。心理语言转换成物理语言也是如此,总会有遗漏,这就是两个指谓同一对象的心理语词和物理语词为什么在意义上有差别因而不能完全互换的原因。例如:把心理语词“意识到红色”用物理语言来表达,至少要述及:(1)许多脑区被激活;(2)分布很广的神经元群进入兴奋状态;(3)它们参与激烈而快速的再进入相互作用;(4)这种相互作用的神经元群能够从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模式中进行选择;(5)分布各处的神经元群之间必须有强烈而快速的再进入相互作用;(6)这些相互作用的神经的神经元群的活动模式不停地变化。当然,再考虑到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考虑到这些神经元群的个体和种系发展,那就更加复杂。因而心理语言就其本体论而言是同一于物理语言的,关键是如何同一则要涉及具体经验科学的把握。
总之,当代脑科学为我们描绘了大脑内部复杂机制图景,它对我们研究传统哲学问题如意识问题、心身问题等提供了科学视域。当然我们不赞成的同一论的个别武断结论,而是主张脑科学和心灵哲学的发展应是互为促进的。我们要吸收当今经验科学发展的具体成果,同时要吸收心灵哲学中的取消论、解释主义、工具主义等理论中的合理思想,重新构建心理的地形学、地貌学、结构论和动力学。
收稿日期:2007—03—12
基金项目: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ZX042)“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