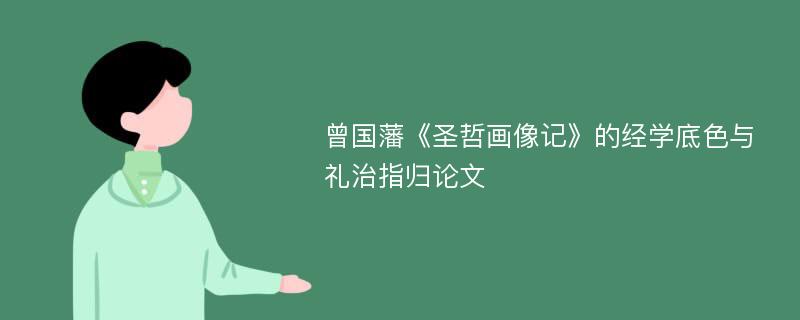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经学底色与礼治指归 *
彭 林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对中国学术史的考察、反思、提炼而成的大纲,作者精择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门类之典范,以儒家经典为主线贯穿始终,吸纳老庄、《史》《汉》,以及诗文诸家,将孔门四科说与姚鼐三分说对接,融为一脉,昭示了以经学为底色的学术蕲向。作者表彰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考究历代礼制之成就,赞美顾炎武以礼移风易俗之理念,凸显了作者推崇的“修齐治平,一秉于礼”礼治思想。
[关键词] 曾国藩;圣哲画象记; 经学;礼治
曾国藩有志于学,出入经史,泛滥百家;戎马半生,笔札尤多,“虽羽檄交驰,而不废书[注] 《曾文正公年谱》 卷六。 ”,“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注]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之四。 ,故久享学名。欲窥曾氏涉猎之淹博,可读其《经史百家杂钞》;而欲知识见之精深,则当味其《圣哲画像记》。前书普及,知之者甚众;后者峻深,好之者较稀。今不揣谫陋,略述学习心得如下,大道君子,有以教我。
一 撰作缘起
《圣哲画像记》(以下简称《画像记》)撰作于咸丰九年(1859),是年曾国藩四十九岁。此事缘何出现于此时,是否为曾氏将晋知天命之年而作?《画像记》起首即有交代:
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来平,而吾年将五十矣。
足见曾氏撰《画像记》,乃由战事与健康两大困扰而起。咸丰元年(1851),洪杨之乱起。两年后,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团练。咸丰四年(1854)起,曾氏率湘军出战。五年(1855)十月,石达开自湖北通城进入江西;叛臣周培春从茶陵进入,与石达开会合于新昌,气焰嚣甚炽,赣江以西,望风瓦解,数月之中,瑞州、抚州等八府,以及临江、袁州等五十多县相继陷落,局势危殆。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剥夺兵权,回湖南老家。后因胡林翼力谏,而被起用。次年6月19日,曾氏于长沙登船,经武昌、湖口、南昌,拟往浙江,然沿途处处遭遇太平军。8月10日,湘军在金溪等三地战败,三地尽失。19日,太平军攻占安仁。22日,湘军在万年受挫,刘隐霞战死。9月4日,太平军攻占扬州。9月26日,湘军后营遭袭,124人被杀。其后,湘军仅萧浚川营病者已达1356人,亡故182人。9月18日,六合、溧水失守。10月10日,湘军大将李续宾与曾国藩四弟曾国华率湘军六千将士于安徽三河战死,湘军家乡湘乡,村村哀嚎,家家白幡。因长期转战,湘军病者已逾三千。17日,庐州失守。19日桐城师溃。12月,河南归德、雎州,江南之徐州,山东之曹县,南安、崇义、定南等,先后失守。湘军屡战屡败,生死未卜,曾氏承受极大压力,身心俱乏,病态迭现。见于曾氏日记者,有如下数端:
1、倦怠。六月十八,“身体极倦”[注] 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一),岳麓书社,2015年,305页。为求简明,下文所引曾氏《日记》,均出此书,故仅标册数与页码。 ;六月廿九,“人倦甚”[注] 《曾国藩日记》(一),307页。 ;七月十一,“会客数次,困甚”[注] 《曾国藩日记》(一),312页。 ;八月十一,“倦甚,久睡”[注] 《曾国藩日记》(一),332页。 ;八月十二,“自寅至亥,倦甚,不能作事”[注] 《曾国藩日记》(一),332页。 。
2、目蒙。因肝气郁郁,曾氏目光昏蒙,十月初二,“日中,目蒙甚,小睡。……下半日,因目蒙,不能事事。[注] 《曾国藩日记》(一),365页。 ”十月初七,“日内眼蒙殊甚,不耐观书,夜中尤甚”[注] 《曾国藩日记》(一),367页。 ;十月十四,“是日眼蒙殊甚,不能作字”[注] 《曾国藩日记》(一),370页。 ;十月十六,“数日内眼蒙,照前略甚”[注] 《曾国藩日记》(一),372页。 ;十月十七,“因目蒙,不敢多看书”[注] 《曾国藩日记》(一),372页。 ;十月廿七,“夜间,眼蒙不能看书”[注] 《曾国藩日记》(一),377页。 ;十一月十三,“夜,眼蒙不能作字,亦未看书”[注] 《曾国藩日记》(一),382页。 。
3、病兆。七月十三,“午刻,身若有病者,在竹床久睡,至灯时稍愈”[注] 《曾国藩日记》(一),312页。 。七月十四,“早,因病晏起。……见客数起,余皆困卧,未能强坐”[注] 《曾国藩日记》(一),313页。 。七月十八,“夜间头闷”[注] 《曾国藩日记》(一),317页。 。七月十九,“日中,又若头痛有病者”[注] 《曾国藩日记》(一),317页。 。九月十二,“(午后)归来,身体不甚爽快。……是日又觉有病,至四更时起腹泻”[注] 《曾国藩日记》(一),352页。 。九月十三,“是日上午,犹觉有病”[注] 《曾国藩日记》(一),353页。 。
4、郁闷。三河败战后,曾氏情绪极之低落。十月廿八日,“六弟与迪庵尚无下落,其必同殉难无疑,公愤私戚,万感交集。三更睡,彻夜不眠”[注] 《曾国藩日记》(一),377页。 ;十一月初三,“是日心绪极恶”[注] 《曾国藩日记》(一),378页。 ;十一月初五,“饭后郁闷”[注] 《曾国藩日记》(一),379页。 ;十一月初七,“心绪恶劣,读书都不能入”[注] 《曾国藩日记》(一),380页。 ;十一月二十一日,“余今老矣,忿不能惩,欲不能窒,客气聚于上焦,深用愧恨”[注] 《曾国藩日记》(一),383页。 ;十二月初二,“下半日作《哀辞》毕。此篇作序凡二日,作辞又二日,可谓迟钝,而又甚不工,盖心力已亏,不能深入耳”[注] 《曾国藩日记》(一),386页。 。十二月廿日,“下半日心绪作恶”[注] 《曾国藩日记》(一),391页。 。
至《画像记》完成之后,曾氏依然情绪低沉,《日记》所记,触目皆是,因前途不明,多次通过占卦卜问未来。如咸丰九年(1859)正月初九,“早起郁郁,若无主者,又占二卦”[注] 《曾国藩日记》(一),400页。 。初十日,“日内,因军事久无头绪,心殊郁闷”[注] 《曾国藩日记》(一),400页。 。十二日,“日内心绪不佳,凡事均觉懊郁”[注] 《曾国藩日记》(一),401页。 。十四日,“夜,阅张凯章各禀,知廿七日之战,阵亡至九十人之多,深为怅惘”[注] 《曾国藩日记》(一),401页。 。十七日:“闻贼将由浮梁绕乐平,抄截我军后路,殊可危及,心绪焦灼。占二卦”[注] 《曾国藩日记》(一),402页。 。
曾氏驽缓多病,生死莫测,加之战场凶险,朝不保夕,身后之事当豫作交代。曾氏一生苦学,以学术为志业,成绩斐然。就自身计,不能不对生平所学所思作一总结;为家族前途计,不能不以毕生心得传之后嗣。曾氏自思“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注] 《圣哲画象记》。下文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咸丰九年正月十八日,曾氏“饭后拟作《圣哲画像记》”。十九日,“作《圣哲画像记》,至未初,‘序’毕”。二十日,“饭后作《圣哲画像记》。……夜仍作《画像记》,未毕,精力倦甚”。廿一日,“辰后作《圣哲画像记》,至灯初毕。意多而不能贯穿,不能割爱,故文颇冗长,至二千余言不能休”[注] 《曾国藩日记》(一),402—403页。 。是前后四日,方得完竣。鄙见,从某种意义而言,《画像记》具有曾氏学术遗言之性质。
《清史稿·本传》论曰:“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注] 《清史稿》405。 ”是为确评。此文乃是曾氏经数十年阅览与思索,权衡轻重,甄别高下之结晶,“意多而不能贯穿,不能割爱,故文颇冗长,至两千语言不能休”[注] 《曾国藩日记》(一),403页。 ,寓意尤深。
二 旨趣与忠告
曾国藩《画像记》,选取历史上文(王)周(公)孔(丘)孟(轲),左(丘明)庄(周)马(司马迁)班(固),葛(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三十二位非圣即贤者,一一述赞,提示其学术贡献,然后仿照汉代武梁祠、鲁灵光殿等图画伟人事迹之故事,命其子曾纪泽描绘遗像,合为一卷,以为斯文之传,藏于家塾,供后嗣取法遵行。《画像记》大旨有二,一是为子孙指点问学之津梁,二是训示治学当持之正确之心态。
周程朱张 德行之科,义理
古人有“不读尽天下书,不妄下雌黄”之说,然庄生已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注] 《庄子·养生主》。 ”之慨叹!中国文献浩瀚,载籍淹博,而良莠不齐,尽数读之,既无可能,亦无必要。《老子》云“大道多歧亡羊”,故曾氏云,为学之先,“要在慎择”,以免误入歧途:
曾氏以经学为立身治学根基之理念,亦贯穿于后辈的读书日课之中,曾氏但凡与父母、叔父母书,必提及子侄读经进展,如“孙儿读《尔雅》,后读《诗经》,已至《凯风》”[注]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与父母书,《曾国藩家书》,124页。 ,“侄孙《诗经》已读至《定之方中》”[注]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与叔父母书,《曾国藩家书》,126页。 ,“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课,……孙男纪泽《郑风》已读毕[注]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廿九日与父母书,《曾国藩家书》,130页。 ”,“孙男读书已至《陈风》[注]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与父母书,《曾国藩家书》,133页。 ”,“甲三读到《滕文公上》,大女儿已经读到《颜渊第十二》了[注]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166页。 ”,“纪泽读书,已读至《太甲上》”[注]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180页。 ,“纪泽读书,已至《酒诰》”[注]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与父母书,《曾国藩家书》,185页。 ,“纪泽《书经》读至《冏命》”[注]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189页。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与父亲书称,九弟“《礼记》九本已读完”[注]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与父母书,《曾国藩家书》,4页。 ;“九弟《礼记》读完,现读《周礼》”[注] 《曾国藩家书》,12页。 ;汝瓷等等,不胜枚举。
曾氏《画像记》之“慎择”,乃是以人物为大纲标揭,典范之选择,面临如下难题:历代学者璨若星河,人选如何兼顾断代与学科,分布均匀,无厚此薄彼之嫌?此其一。此外,中国学术门类众多,因时势而变,形态迥异,如何调和融合为一体,而无杂凑之讥?此其二。
《画像记》三十二圣哲,人分八组,每组四人;学分七类:以周代经学、两汉史学、唐宋文章与诗学、宋代理学、乾嘉考据等为主题,既兼及主要朝代,也包涵了主要学术门类。庄子虽非儒学主流,但学术独特,不可遗漏。
另有“事功”人物一组,关注到魏晋及唐宋无著述名世,而有治国安邦功绩突出之闻人。诸葛亮,陆稼夫、范仲淹、司马光等,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或“坚卓诚信,各有孤诣”,或“以道自持,蔚成风俗”,均为以儒术经济天下、淑世救民之忠臣良相,乃儒学精神之卓越践行者,同样光耀学林。
曾国藩将此诸葛亮等列入“圣哲”,是其学术观与价值观之必然体现,亦是其对自身际遇之期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正义》云:“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曾国藩云:“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曾氏生逢乱世,身不由已,最好之年华被裹入战争,虽无立德、立言之条件,但可以立功为民,同样成为“不朽”之人。
文以载道,文雄则道著。唐宋学术,有文章之胜,气韵与风骨俱佳,韩、柳、欧、曾,足称范型,其渊源乃出自西汉:扬雄、司马相如之雄伟,刘向、匡衡之渊懿。“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聩矣”,是其缺憾之处,但文章气势依然犹在,韩愈、柳宗元,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曾巩效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
曾国藩二十五岁留京访学,接触桐城派与宋诗派,其后曾专注于诗,并钞古今诗,自魏晋至清,得十九家,曾氏主张学者取其一二即可,足敷应用,无愧词臣之名即可,“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不必依自己所好,强求后学必读,“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曾氏“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
曾国藩三十一岁始从理学家唐鉴研习程朱理学,从此醉心于此。两宋理学勃兴,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孔孟之道不坠于乱世,且能赓续不断,实为五子之功。入清,乾嘉考据之学盛行,处处与义理之学对立,流风所至,宋学备受鄙薄与排斥,以致后学多望而却步,曾氏怒斥此等之人为“诋毁日月”:
6种导线方案在考虑大风、覆冰等条件下的铁塔荷载及其投资费用如表6所示。其中假设钢材单价1万元/t、混凝土单价0.2万元/t、导线单价2万元/t、金具单价2.5万元/t、420 kN和550 kN绝缘子单价分别为240元/片和360元/片。
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侮。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注] 《送唐先生南归序》,《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75页。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供给体制是指供给主体在提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体系和制度,主要包括职责划分、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三大部分。职责划分是指各级政府所承担的职责权限,这是前提条件;组织体系是指所承担新农合供给职能的组织和组织之间相互合作,这是基础条件;运行机制是指新农合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决策机制、财政机制、监管机制、绩效评估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竞争机制等,这是保障和实现途径。
他已经在心里把这首诗朗诵了一千遍,一万遍。他渴望在五月里深情朗诵这首诗。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在眼前展开:尖利的麦芒上闪动着晶亮的太阳,早起的鸟儿们开始啄食麦粒。熏风徐来,亮闪闪的太阳顺着熟透的叶尖滚落尘埃。十字木架穿一件破旧衣裳作的稻草人,在簌簌麦浪声中,扬起细细的柔软胳膊,鸟儿便腾空而起,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像撒开一张巨大的鱼网。他想象着,在五月的麦香里,在金色的阳光里,与雪萤完婚。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注] 《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一,《书学案小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72页。 。
曾国藩将周程张朱列入“圣哲”名单,旨在表达对清代考据派的抗争。曾氏虽以宋学为立身根基,然并不贬斥乾嘉考据之学,对其所长,亦予充分肯定,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谈及,此处从略。末了,曾氏谈及为何将姚鼐于王念孙亦列入《画像记》:
本文简要介绍了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流行病学、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国内外新认识,重点阐述了用于本病的中药临床试验的临床定位、总体设计、诊断标准、受试者选择、评价方法及试验流程等关键技术要素,指出了试验实施中的注意事项,以期为用于儿童功能性便秘的中药临床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夐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曾氏坦言姚鼐对自己的多方启迪,故志此不忘,钱穆云,曾国藩“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632页。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故以为殿军。曾氏所列三十二圣哲,学术尽皆杰出,“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
其次,学科纷繁,学说各异,当如何归纳?《论语·先进》载,孔门之学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是为学术门类之源,影响深远;而姚鼐提出词章、义理、考据三分之说,经过戴震等人宣扬,盛行于学界。孔门四科与姚氏三分,若均加采择,则二者关系又当如何说明?
《圣哲画像记》所选三十二人,除文、周、孔、孟属于圣人,左、庄、马、班为旷世奇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其余诸人均可以纳入其中:
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着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
通过信息化系统,提供了项目考核与绩效测量的基准所需要的工作内容、工作量、完成时间、完成效果等关键要素的数据,有助于军工科研单位建立一套以贡献为导向、以执行率为参考、以效果为考核的评价体系,实现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充分发挥人员工作积极性。
经由这一归纳,从先秦至清,学术之发展,并非乱麻一团,无章可循,而是有一以贯之之脉络贯彻其中,试列表如下:
文周孔孟 圣人
班马左庄 旷世奇才
葛陆范马 德行兼政事
闹春楼里,常有一帮黑汉在此聚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叫上了劲,有人拍案而起,指天骂地;有人捶胸顿足,失声痛哭;有人捧腹嘻笑,笑眼泪流……席间,常有个操外地口音的年轻女子坐着弹琵琶。她叫郑九娘,艺名“琵琶仙”。她能边弹边唱,成为蕲州一绝。每逢九娘弹唱,汉子们全都停住闹酒。一曲未尽,常有人酒性发作。
韩柳欧曾 言语之科,词章(文)
杜李苏黄 言语之科,词章(诗)
许郑杜马 文学之科,考据
纵观历史,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之人,何处不有?如乾嘉学派大盛时,姚鼐独排众议,提出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然“当时孤立无助”,五六十年之后,方有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洪杨之乱后,四方乱离,独湘乡少安,似有重振桐城派之可能,然新秀如舒焘早卒,欧阳勋年二十有几而殁,其它,“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欤”[注] 《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87页。 ?因此,个人之名与书,“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曾氏论天意云:
顾秦姚王 文学之科,考据
《画像记》之另一主题为读书之目的与心态之训诫。
宋儒读书,讲究改变自身气象,提倡读书与做人一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最终成就了自己。故宋儒讨论颜回所学何学?所乐何乐?
《画像记》另一不可或缺之重点,乃是为学心态之忠告。三十二人非圣即贤,并非仅仅学术出众,学术之外尚有德行。故读三十二人之书,不可不知三十二人之为人,此为至关紧要之处。宋真宗《励学篇》“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语,消极影响甚广,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俗儒无不奉为真谛。曾氏谆谆告诫如下:
其一,君子忧乐在道。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
君子志于道,忧乐不离于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忧道之不明,忧自己沦为无识乡民,忧一息之懈怠渐起。《孟子》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光明磊落,求仁得仁,何怨之有?既无所祈求,又何报之有?三十二位圣哲,除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均不以功名为念。而庄周等三人之所以伤悼怨悱,因皆有不世之才而不遇钟期,故尚在情理之中。若“无实而汲汲时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
其二,勿信因果报应之说。
唐宋以后,佛教流行,因果报应之说侵入学界,读书必有名利之报,殆成天经地义之论。曾氏告诫子孙,勿信此说,勿生求功名之心: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篇,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
士有在“占毕咿唔”、“少读古书”、“纂述未及终篇”之时,便“期报于科第禄仕”,“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腾播人人之耳”;希冀“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若是名利皆未获,则以“孔子生不得位,殁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自慰,名利之心始终不泯。
青年习近平也想上大学,但由于一些问题迟迟不能如愿,他却始终淡定自若。他认为,学习的方式不是固定的,上大学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文学、哲学都有所涉猎。他深信“书到用时方恨少”,知识总有用到的那一天。读遍了携带的书籍之后,凡是能借到的书他都去借来看。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不断学习,才造就了今天学富五车的习近平。
《画像记》所选七个门类、三十二位圣哲,并非均衡分摊,分门角力,恰恰相反,除庄子一人外,无不以儒学为核心而展开,具有鲜明的经学底色。
为学当秉持尽人事、听天命之心态。人事由己,天命无人能左右。曾氏以贸易为譬,若是小本生意,锱铢必较,即使百钱之负,亦会怨及孙子。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数十百缗之费,自然不愿计较。天覆万物,无法顾及“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
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他继而向记者介绍了医院当前能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医院自1958年建院以来,已有60年的历史,建筑类型较多,修建时间跨度大,不同类型的建筑能耗特点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医院业务量的逐年攀升,人们对于医院环境和安全等各方面要求的提升,大量医疗、信息化等高新技术设备的持续推广应用,均使得能耗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趋势。
2.3 不同红小豆品种数量性状主成分分析 试验对红小豆7个主要农艺数量性状进行了主成分综合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根据累积贡献率≥85%的标准,前3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86.68%,说明表3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可以概括出红小豆主要数量性状信息量。
魁岸之材,有深自韬匿者,去键羡,识止足,天乃使之驰驱后先,殚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锐意进取者,天或反阨之,使之蓄其光彩,亦昌其后而永其年,迹似阨之,实则厚之。材,均也。或显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处也,天也[注] 《郭璧斋年伯六十寿序》,《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76页。 。
以上三节,子嗣不可不知,知之,方能有为万民忧乐、不谋一己名利之胸怀,有宠辱不惊、百折不回折之强大心理,随遇而安。
三 经学底色
其三,达人知命。
曾国藩十五岁始刻苦攻读经史与《文选》之学,二十四岁中乡举,二十八岁中进士,毕生浸润于儒学,作为一代鸿儒,对儒家经典情怀殊深,笃信“《十三经注疏》为学问之根柢”[注] 《覆何子贞太史》,《曾国藩书信》卷三十三,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420页。 。曾氏治学,最重经史,“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注]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5页。以下再引此书,仅标页码。 。曾氏以经史之学为立身之本,锲而不舍,“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注]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35页。 ,“近因体气日强,每天发愤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注]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与父亲书,《曾国藩家书》,15页。 。曾氏读经,务求精熟,深入腠理,“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注]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55页。 。“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注]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56页。 ;“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鹜,一无所得”[注]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与父亲书,《曾国藩家书》,10页。 。
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睹《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曾国藩以经学为学术文化之最高形态、经世致用之宝贵资源。咸丰八年,为曾氏一生最为艰难之时,然犹诵经不止,如九月十日起,连日温《论语》《孟子》《大学》,至廿四日止,随即开始温《诗经》,至十月十二日止;间隔一日之后,连日温《尚书》,至廿三日止。足见经典为曾氏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精神资源。
如在门诊遇到这样的问题,医生通常会说,不好讲,挺复杂。这不是医生敷衍,而是确实不太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生长痛这个概念虽然已提出近200年,但对于其病因的阐释,却仍难以让人满意,只有一些假说,在此不妨与好奇的家长分享一下。
乾隆中期以后,学风丕变,学者忽视经典精神,而以讲究诗词、追慕文章华美为时髦。乾隆四十四年(1779),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以提倡“古文法”为主旨,选录战国至清代古文,包括《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所作古文。全书分为十三类: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又有“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书首有序目,介绍各类文体之特点、源流及义例。姚氏此书,重心在文章作法与技巧,在“术”不在“道”,故此书《论辩类》始于贾谊《过秦论》,《序跋类》始于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奏议类》始于《楚莫敖子华对威王》;而均不及《六经》。姚说影响极大,四方学者多“以姚氏为文家正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注] 《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87页。 。
曾国藩编撰《经史百家杂钞》,都十一类,与姚氏《类纂》大体相同,而境界实则大相异趣。曾氏不满姚氏“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注]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14页。 。古文与经关系密切,唐宋古文运动,乃由反对六朝骈俪之文而起,主张回归三代两汉之儒家经典,“今舍经而将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为此,曾氏《杂钞》“每类必以《六经》贯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注] 《经史百家杂钞序》。 。如《著述类》,以《洪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为首;《序跋类》以《易》之《系辞》,《礼记》之《冠义》《昏义》为首;《书牍类》,以《书》之《君奭》,《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为首;《杂记类》,以《礼记》之《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为首。以经引领群籍,是曾氏念兹在兹,无时或忘者。
曾国藩上述理念,亦为《画像记》铨选学术典范的主要原则,除庄子之外,无不以儒学为取舍依据,故具有鲜明的经学底色。如《画像记》首选文王,认为孔子推戴知尧舜,不过是“史臣记言”,而“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方为经典文本文化之肇端。随后,“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从周公到孔子,“六经”体系成为儒家文化之基石,教育化民之道确立,是故以文王、周公、孔子为“三圣”,尊经之义显然。
孟子私淑孔子,原本为诸子之一,司马迁《史记》将孟子与荀子等同,列入《孟荀列传》。宋儒慧眼独具,“以为(孟子)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孟子》由此列入《十三经》,故曾氏以孟子为“亚于三圣人后”者,得与文、周、孔相并,冠于三十二人之首。
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为朝廷藏书专门建造的楼阁是石渠阁和天禄阁。始建于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位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未央宫宫殿群的石渠阁和天禄阁,用于贮藏图书典籍。后人由此引申,把官府典籍收藏的处所,别称为“石渠”和“天禄”。
《春秋》三传,均为阐发经义而作,“《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周公制作之史料,由此留存,是其长于《公羊》《谷梁》之处。两汉史学以《史记》《汉书》为楷模,“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此其所长,而曾氏以为《史记》之缺憾,在于对经典之《礼》之价值估计不足,“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注] 《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00页。 ,此消极举影响至后世史家。两汉经生,去古未远,如田何之《易》,申培之《诗》,张苍之《春秋》,无不得之于七十子后学,“各有渊源,源源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研究儒学,不能不求溯于此,是故,于经学史上有其特殊地位。
魏晋至宋,天下大乱,儒者当扰攘之世,无法静心读书,唯能“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中庸》云: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云:“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疏:“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等,于患难之境地,“被服儒者,从容中道”,“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坚卓诚信,各有孤诣”,“以道自持,蔚成风俗”,践行经典精神,以事功名世,立身报国。
文以载道。姚鼐提出文有阴阳之说,曾氏深以为然,并延伸出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之说,并将文之阴阳与孔子倡导之仁,与孟子倡导之义挂钩,从而植入了儒家的经典精神:
6.来稿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统一排在文末。按在正文中使用的先后顺序用数字加方括号标出(正文),同一参考文献如果多次引用,用同一序号标出。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曾国藩于诗颇有兴趣,道光十五年(1835)开始学习诗,认为“诗文之业亦可因以进德”[注]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记》。 。曾氏诗作甚多,同治十二年陶甓勤刻印之《曾文正公诗集》所收曾氏之诗,达316首之多。咸丰初年编《十八家诗钞》,曾氏以为,诗家分派过多,不必尽学,“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氏仅“笃守夫四人”: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如此而已。
在风景园林建设的多种要素中,植物和植物景观是与碳循环有着密切联系的核心要素[4]。因为在绿道建设中其他要素低碳效应在于减少碳排放,而植物和植物景观既与减少碳排放有关,又与碳固定有联系,因此在绿道规划设计中,需要找到合适的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策略,才能最大化的减少碳排放。
宋代义理之学极盛,流风余韵,入清之后犹在。干嘉学派兴起后,饱受诟病,以为空论心性,清谈误国。曾国藩认定宋儒有经学传播之功,极赞两宋五子“绍孔氏之绝学”“究群经要旨”之贡献:
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其说允矣[注] 《送唐先生南归序》,《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74页。 。
在曾氏而言,理学与经学,内在精神统一,故其立言,“大者多合乎洙泗”;因其重心在诠释经典大旨,于名物训诂,难免“小有不当”,取清人训诂成果辅翼之即可,岂可全盘否定:
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注] 《圣哲画像记》。 。
曾国藩维护宋学,但不抹杀乾嘉汉学,儒家经典文本需要从音声、故训、校勘等领域深入考证。曾氏清儒在上述领域之创新与贡献,堪称“卓绝”,破解之疑难,堪称“度越前世”:
惟校雠之学,我朝独为卓绝。干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注] 《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经史百家简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16页。 。
曾国藩主张汉宋兼治,包含百家,格局宏大,非时贤之气量所限,然以二家为经学之两翼,不得彼此排斥,是为曾氏之卓识。
四 礼治指归
儒家经典,凡有十三,群经之中,曾国藩最为关注之核心何在?《圣哲记》如下一语道出答案,堪称全文谋篇布局之“眼”: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
《圣哲记》三十二圣哲,以研礼者为最多;判断所列各书价值高下,无不以礼为标准。曾氏以《左传》一书之可贵,在“多述二周典礼”,故虽“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亦可忽略不计。《史记》之长,在“网罗旧闻,贯串三古”,不足之处在记述三代制度, “颇病其略”;而“班氏《志》较详矣,然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足见曾氏评判《史记》《汉书》价值,关键在典制。“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是汉儒之成就,皆在保存、研治三代之礼。
曾国藩以礼为贯穿唐宋至有清学术之脊梁,赞美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之言随处可见,皆缘其能详载周代“经世大法”、“辨后世因革之要”;而“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注]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00页。 。故《画像记》云:“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此外,清儒治小学成绩斐然,文字、音韵、训诂,各有专精之作,究其价值,亦在“考先王制作之源”,谓其学术指向与杜、马一致,同为“实事求是”求证周代礼乐制度之源流,《画像记》云:
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即便是宋代理学诸大家所论,与礼亦相表里,绝无背离,“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清儒之文献研究,独步古今,然贯穿其中之主线亦是礼,清代大儒顾炎武云:“ 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注] 《亭林文集》卷二,以《仪礼郑注句读序》,中华书局,1983年,32页。 ”以礼纲领一切之立场,跃然纸上。在曾国藩而言,由于顾氏倡导,其后大儒无不隆礼,“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敎为己任;江愼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注]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00页。 ”,张尔歧、江永、戴震、秦蕙田等前赴后继,大旨无不在礼: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
足见曾国藩乃彻头彻尾之礼治主义者,其推戴礼治之论述,于书信、笔札中堪称俯拾皆是,如“葢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注]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00页。 。“治国以礼为本”,“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注] 《王船山遗书序》。 ,“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岀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注] 《江宁府学记》,《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17页。 云云,不胜枚举。李鸿章所撰《曾文正公神道碑》云:“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故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注]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曾国藩诗文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506页。 ”《清史稿·本传》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注] 《清史稿》405。 ”皆是深知曾氏者也。
曾国藩臧否学者识见高下,一是皆以礼为要旨。《画像记》以顾炎武为清代礼学之发端者,而以秦蕙田为集大成者,冠于清儒之首,曾氏所谓“微旨”者即在于此。
曾国藩推崇礼治,除以周孔之道为人生信仰之外,尚有其它原因,笔者揆之,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腍熟《三礼》,深层认同。
《三礼》古称难读,故除少数专门之家,留心于此之学者极少。而曾国藩九岁读《五经》毕,是《礼记》已通读一过。十四岁读《周礼》《仪礼》,二经文字古奥,经义渊深,而曾氏于未成童之年即已讽诵,殊属难能。其后,为研治《三礼》计,广为搜集文本与著述,其中以《仪礼》为最。近年坊间发现之《求阙斋书目》,“是曾氏早期藏书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注] 胡卫平:《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岳麓书社,2014年,212页。 ,其中“地字一号”著录十八种书目,内有《周礼义疏》与《礼记义疏》,其余均属《仪礼》类著作:《宋本仪礼疏》《明版仪礼注疏》而外,尚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朱轼刻《仪礼节略》、方苞《仪礼析疑》、郑珍《仪礼私笺》、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胡培翚《仪礼正义》等。
《仪礼》一经,韩文公已称“难读”,王安石熙宁改革废罢《仪礼》一科,斯学日衰,不绝如缕,曾氏居然私心好之,精读覃思,终身不辍。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曾氏《日记》云:“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读《仪礼》,至是粗毕。[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375页。 ”今检同治五年九月一日以及前后十日之《日记》,均无读《仪礼》之记载,殆记忆有误。读同治四年四月初十《日记》,云“阅《仪礼·士冠礼》,将张蒿庵、张皋文、江慎修、秦味经诸家之说参证”[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161页。 ,此后之《日记》时有今日读《仪礼》某篇之语,记之颇详。同治四年四月初九,当为曾氏精读《仪礼》之始,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日记》云“读《仪礼》初毕”,前后凡二十月,是年曾国藩五十七岁。读毕《仪礼》之日,曾氏颇为感慨:
老年能治此经,虽嫌其晚,犹胜于终不措意者。昔张蒿庵三十而读《仪礼》,至五十九而通此经,为国朝有数大儒。余今五十七岁略通此经,稍增炳烛之明。[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375页。
曾国藩阅《仪礼》,似以张尔歧《仪礼郑注句读》为读本而加校点批注。湖南省图书馆藏有曾氏读《仪礼郑注句读》批点稿本。据吴仰湘、包凯先生研究,“曾氏不仅用朱笔将《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圏点一过,还精校细读,时有会心,在页眉及正文间留下朱、墨两色批注一千多处[注] 吴仰湘、包凯:《曾国藩批点〈仪礼郑注句读〉稿本述评》。 ”,若有心得,即作笔札;用力之深,超乎想象。
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湘潭王启原编辑之曾氏《求阙斋读书录》十卷,依经、史、子、集为序排列,以札记形式条陈曾氏读书心得。卷一为经部,收入《周易》《周官》《仪礼》《礼记》四种,其中《礼记》所记最略,仅《檀弓》“子畴昔之夜”一条;《周礼》稍大;《仪礼》最详,《觐礼》之外,其余十六篇均有涉及,都百十一条,王先谦将其名之为《读仪礼记》,收入《清经解续编》。《读仪礼录》征引引用诸家之说甚多,如敖继公、郝敬、张尔岐、顾炎武、王夫之、张尔岐、张惠言、方氏、盛世佐、秦蕙田、姜兆锡、杨大堉,以及《钦定仪礼义疏》等。引用最多者为张尔岐,达十九次。间有未加引用,而实则用力甚多者,如江永《礼书纲目》,曾氏很少引及,而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曾氏谕曾纪泽书云:“《三礼注疏》,非将江慎修《礼书纲目》识得大段,则注疏亦殊难领会,尔可暂缓。[注] 《曾国藩家训》,岳麓书社,1999年,第19页。 ”足见渠于此书着力匪浅。
《仪礼》记述周代仪式,揖让进退,升降周还,极之曲折,历代学者多以图示为辅,而以宋人杨复与清人张惠言(皋文)所撰《仪礼图》最为著名。曾国藩颇重张氏《仪礼图》,同治四年四月初九日《日记》,有“阅张皋文《仪礼图》”之记载[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161页。 ,是年曾氏55岁。湖南图书馆藏有曾国藩手批《仪礼图》清嘉庆刊本一部,所载批识凡二十余条。蒋鹏翔《曾国藩批校〈仪礼图〉稿本述评》称,曾氏“补正了张氏《仪礼图》的各种疏误”,“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对《仪礼图》的看法”,以及“研治礼学的原则、过程及心态”[注] 载《图书工作与研究》,2017年12期。 。
曾氏于《礼记》亦颇用心。王夫之著书三百馀卷,中有《礼记章句》,曾氏说“为先生说经之最精者,拟细看一遍,以便作序”[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287页。 。自同治五年五月初三日起,至六月二十日读毕,凡四十七日,阅读不辍。其间或以徐乾学《读礼通考》与之校对者[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302页。 。曾氏云:“余阅此书,本为校对讹字,以便修版再行印刷,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盖非校雠家之体例,然其中亦有可存者。[注] 《曾国藩日记》(三),303页。 ”
是曾氏主张礼治,并非人云亦云,亦非虚言浮词,乃是基于对经注疏之精读深研,洞知其宏纲细目后,由衷拥护之理念。
其二,笃信《周礼》乃周公“官政大法”。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无所不包,周公之道即体现在官制体系之中,为后世治平之道的源头活水。故曾氏云,揅究《周礼》,意在“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注] 《覆劉霞仙中丞》,《曾文正公書札》卷十四。 ”,既有“体国经野”之大,亦有“夭鸟蛊虫”之小,宏纤毕贯,孔子权衡万变之本,多在此“周之旧典”,故笃信《周礼》为周代政教之典:
《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小缮稾、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耶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注]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00页。
儒家自古以教育立国,《周礼》所载教育制度,在官及于国学,在民则及于乡、州、党、族、闾、比,教尊而礼严;此外,乡大夫以“乡三物”教民,以“八政”以防淫,又教之以乐舞,曾国藩赞美其粲然大备: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子弟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俦,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衣而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辑业以兴其财。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注] 《送唐先生南归序》,《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75页。 。
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敎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注] 《江宁府学记》,《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17页。 。
《通典》《五礼通考》等考订职官体系之著作,乃由《周礼》而衍生,既可由此上溯周公制作之本源,亦可考察后世之因袭与变化,甚至可以直接运用于国务、军务。曾国藩推戴杜佑、顾炎武、江永、秦蕙田等礼家所撰典制之作,惟因其多存先王经世遗意,不务空谈:
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注] 《覆夏弢甫》,《曾国藩书信》卷十三,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144页。
咸丰九年三月,孙芝房以所撰《刍论》二十五篇抵曾国藩军中,相与论讨,内容涉及论治、论盐、论漕、论币、论兵、论明赋饷等。其后,曾氏为《刍论》作序,盛赞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但又叹惜此书“食货稍缺”,思欲为之补缀,以成完帙,“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已,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注]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00页。 ”
曾氏覆刘仙霞书,慨叹《三礼》记载之缺憾至多,痛感“沮滞而不达者”,在郊庙祭祀、军礼、乐教三项,甚至不能得其仿佛:
盖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庙。而郊祀祼献之节,宗庙时享之仪,久失其传。虽经后儒殷勤修补,而疏漏不完。较之《特牲》《少牢馈食》两篇,详略迥殊,无由窥见天子诸侯大祭致严之典。军礼既居五礼之一,吾意必有专篇细目,如戚元敬氏所纪各号令者,使伍两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进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类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古礼残阙若此,则其它虽可详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礼乐并重。而国子之教乐,乃专精乐之至者,能使凤仪兽舞。后圣千载闻之忘味,欲窥圣神制作,岂能置声乐于不讲。国藩于律吕乐舞,茫无所解。而历算之学,有关于制器审音者,亦终身不及问津,老钝无闻,用为深耻。夫不明古乐,终不能揅究古礼,国藩之私憾也。郊庙祭仪及军礼等残阙无征,千古之公憾也。[注] 《覆劉霞仙中丞》,《曾文正公書札》卷十四。
曾国藩认为,礼书所载典制具有极强之操作性,或可直接借鉴,或可由此了解因革源流。《三礼》之外,《五礼通考》所载历代制度最为详备,故曾氏攻读尤勤。由《日记》可知,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曾氏先后读秦蕙田《五礼通考》之《飨燕礼》《昏礼》《大射仪》《乡射礼》《投壶礼》《乡饮酒礼》《饮食礼》《学礼》《巡狩礼》《观象授时》等篇,其时身体欠佳,但锲而不舍,颇有其“扎硬寨,打死仗”之风。
《五礼通考》之天文历法部分最为难读,堪称绝学。曾氏对此早有兴致,某日二更“与儿子、甥、婿辈看星,三更睡”[注] 《曾国藩日记》(三),161页。 。同治六年五月《日记》,密集记载每日读《五礼通考》诸章进度:初九日,“阅《巡狩礼》,巳正小睡,午初再阅《五礼通考》”;十二日,“阅《观象授时》十叶”,“是日亢晴燥热而无雨意,忧灼之至”![注] 《曾国藩日记》(三),404页。 廿一日,“中饭后阅《观象授时》十叶。余于天文全无所解,故茫然不入,特好秦味经之条理井然,故须遍观一过耳”,“近日常疲困思睡”[注] 《曾国藩日记》(三),408页。 ;二十五日,“午刻阅《观象授时》六叶。江慎修纠正梅勿庵‘岁实’之说,读之茫无所解”[注] 《曾国藩日记》(三),409页。 ;二十六日,“午刻阅《观象授时》,江慎修辩梅氏‘平气’、‘定气’之说,亦无所解”;二十七日,“午刻阅《观象授时》中《冬至权度》,虽无所解,亦勉为细读一过”,“近日,常觉疲乏不支,老境摧颓[注] 《曾国藩日记》(三),410页。 。氏致刘蓉书云:“去岁盛暑困人,自五月至八月,竟日汗下如洗,两目昏花,不能复辨细字。齿牙虽仅脱其一,而动摇几遍,说话至二十句后,舌便蹇涩,气亦不属”[注] 《曾国藩书信》卷二十四,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267页。 。六月初一,“午刻阅《观象授时》十馀叶”[注] 《曾国藩日记》(三),411页。 ;初二日,“午刻阅《观象授时》”,“三点睡,屡次梦魇。余向来神思疲困则魇,惫极则屡魇,本日困惫尤甚”[注] 《曾国藩日记》(三),412页。 ;初五日,“午刻阅《观象授时·步天歌》,中饭后天气奇热,馀畏特甚,坐卧不安”;初六日,“午刻阅《观象授时》中之推步法、《勾股割圆记》,一无所解,殊用为耻”[注] 《曾国藩日记》(三),413页。 ,初八日,“午刻阅《观象授时》”,“大局日坏,军势难振,不胜焦灼”[注] 《曾国藩日记》(三),414页。 ;十二日,“阅《观象授时》中《历代正朔》”;十三日,“病乏殊甚,行坐不安”;十四日:“疲病殊甚,不能治事。”十五日,“午刻阅《观象授时》中之《读时令》条,《观象授时》门阅毕。素不晓天文算学,阅如未阅也”[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416页。 ;十六日:“午正,阅《通鉴辑览》,从宋看起。因《五礼通考》义蕴较深,病中难以用心,故改阅史耳”[注] 《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2015年,417页。 。
其三,修齐治平,一秉于礼。
儒家以修齐治平为人生之轨迹,亦为治国理民之方略,人舍礼无以立,国舍礼则无以治,曾国藩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注] 《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全集》十四册,410页。 。从学理上说,礼本于太一,起于微妙,自有形而上之内涵,但礼又散布于民生日用之中,故圣人以礼为教,以为移风易俗之器械,《礼记乐记》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
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敎,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则圣人虽没,而鲁中诸儒犹肄乡饮、大射礼于冢旁,至数百年不绝,又乌有窈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注] 《江宁府学记》,《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18页。。
君子教育始于少年,通过礼仪教育,达到童蒙养正,培根固本之目标,“少成若天性,习贯之为常”[注] 《大戴礼记解诂》卷三,《保傅》,中华书局,1983年,51页。 ,是为周人贵胄子弟教育之精髓。宋儒深谙此道,推广传播,用力甚勤。流传海内之《小学》,相传为朱子所辑,此书备述童蒙养正之法,详列礼仪基本规范。曾国藩于此书大为赞扬,认为“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大有裨益于人身修养: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埽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未知焉耳[注] 《钞朱子小学书后》,《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45页。 。
儒家文化以营建和谐之伦常关系为读书明理之基本要求。曾国藩认为,《礼记》中《曲礼》《内则》所记日用之礼,便是走向“蔼然有恩,秩然有序”境地之不二法门,具有普适性,故任何人都必须由此起步,“句句依他做出”,家族伦理故可由此大明,故乃“真大学问”。反之,文章做得再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做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注]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70页。
《仪礼》文古义奥,普通人难以卒独,而且看似满纸繁文缛节,真懂者寥若晨星。曾国藩洞悉其背后蕴藏之教化之道,其作《江宁府学记》,历数《仪礼》冠、昏、丧、祭等人生礼仪,以及士相见、乡饮、乡射、朝觐等社会礼义,以为无不教民向善,旨在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感慨先王之道,“隆礼而已矣”: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埽沃盥有常仪,羮食肴胾有定位,緌缨绅佩有恒度。旣长,则敎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敎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注] 《江宁府学记》,《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17页。
清代有识之士中,不乏本儒家童蒙教育精神创办书院者,湖北巡抚胡林翼“以移风易俗为己任”,治鄂六载,功成化洽,人才极盛。后于其故乡益阳建箴言书院,推行其父胡达源所编《弟子箴言》提倡之育才之法,书中纲目十六条:“奋志气,勤学问,正身心,慎言语,笃伦纪,睦族邻,亲君子,远小人,明礼教,辨义利,学谦让,尚节俭,儆骄情,戒奢侈,扩才识,裕经济。”引导学子自洒扫应对做起,“自幼而端所习”,长年践行,“徐底于成”。曾氏赞叹云,“即汉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闽渊源,于是乎在”[注] 《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箴言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18页。 :
自洒扫应对,以暨天地经纶,百家学术,靡不毕具。衷以己意,辞浅而指深,要使学者自幼而端所习,随其材之小大,董劝渐摩,徐底于成而已[注] 《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箴言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17页。 。
曾国藩乃儒家修身、齐家之说最虔诚之践行者之一,故注重家风、家教,注重子弟言语、容貌、礼仪规范之养成。其与父母书中谈及,孙儿“朔望行礼,颇无失仪”[注]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与父母书,《曾国藩家书》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4页。 ,引以为欣喜。九弟曾国荃欲与刘霞仙同伴读书,征求曾国藩意见,答云:“霞仙近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语容止、规格气象如何?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注]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家书》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01页。 ”鄙见,曾氏若未被卷入战场,而久为亲民之官,则必定为以礼为教,化民成俗者。
曾国藩括囊诸家,博学多才,根之以六经,以礼为持守之基,轻重有别,尽得千年文化之大旨。李鸿章之兄李翰章赞扬曾氏之学云:
其于学广收博取,掎挈百王之心法,证以国家之礼文掌故,根极理要,不为口耳附和,而尤以礼为持守之基。其为文朴茂闳肆,取涂于汉魏唐宋,上泝周秦,中之以六经,而修辞必以立诚为本。[注] 《曾文公全集序》,《曾国藩诗文集》附录二,451页。
要之,曾国藩《画像记》以儒学为主线,将历代学者典范与各种学科门类融为一体,而以礼治为指归,以为修齐治平之魂,是为其学术史观之最高总结,研究曾国藩之学,此尤不可不知。
Zeng Guo -fan 's Confucianism Background and Intention of Rule by Rites in Sage Portrait Record
PENG Lin
(School of Humanites,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Sage Portrait Record is an outline of Zeng Guo-fan's investigation, reflection and refinement of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It takes Confucian classics as the main thread throughout the book, chooses model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disciplines , absorbs Laozi, Zhuangzi, Historical Records, Han Shu, and poetry and articles of various schools, and integrates the four disciplines theory of confucianism and Yao Nai's three-point theory into a single line, which shows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based on Confucian classics. The author commends Du You's Tong Dian, Ma Duan-lin's Wen Xian Tong Kao and Qin Hui-tian's Five Rites Tong Kao for their achievements in investigating achievements of norms of etiquettes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speaks highly of Gu Yan-wu's idea of changing customs with etiquettes. The author's thought of rule by rites of "Confucian cultivation, country and the world, adhering to etiquettes" has been highlighted.
Key words : Zeng Guo-fan; Sage Portrait Record ;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rule by rites
[中图分类号] K250.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63( 2019) 04— 0102— 12
*[收稿日期] 2019-04-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041509065)
[作者简介] 彭 林(1949—),男,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历史文献、儒家三礼研究。
标签:曾国藩论文; 圣哲画象记论文; 经学论文; 礼治论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