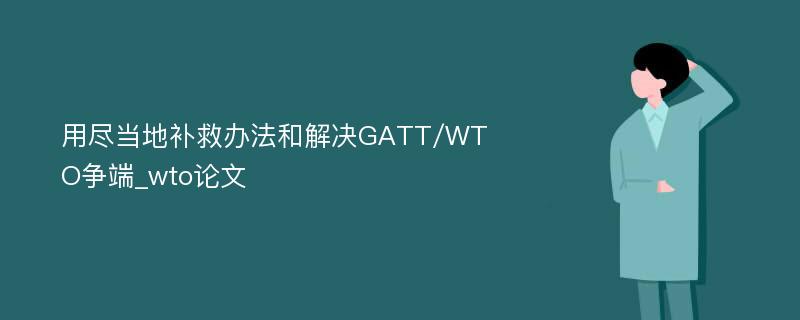
用尽当地救济与GATT/WTO争端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端论文,GATT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尽当地救济(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是一项一般国际法原则。按照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要求,一国启动与他国的争端解决国际程序,应以本国人用尽在所在国的所有国内救济程序为前提。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成员间的贸易争端,是争端解决的国际程序。那么,它作为相对封闭的争端解决程序,是否也要受到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制约?这一问题在GATT/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中一直广受争议。解决这一争议的基点在于:GATT/WTO争端解决程序的性质和目标是什么?它能否例外于一般国际法原则?
一、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一般是指:当个人(包括自然人、法人等)受到其所在国的国际不法行为侵害后,在该个人没有用尽其所在国所有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之前,该个人的国籍国不能进行外交保护,国际性法庭也不能受理其本国代表他进行的国际求偿案件。在争端解决的意义上,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要求国内程序优于国际程序。在东道国与国籍国的权利安排上,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强调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优于国籍国的外交保护权。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际法上确立的法理依据,理论上有种种解说。英国学者布朗利则认为:它是一项其合理性得到了各种实际政治考虑而非国际法衍生的任何逻辑必要性证明的规则。(注:[英]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页。)从“实际政治考虑”,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大体上具有以下的意义:尊重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国际不法行为既然在东道国境内发生,国际法应当给予东道国自我纠正的机会;东道国解决争端具有便利性;有利于减轻国际机构受理案件的负担等等。
用尽当地救济是国际习惯法原则。在美国诉瑞士的INTERHANDEL一案中,国际法院作出了如下确认:在国际程序之前必须用尽当地救济是一项已经建立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在一些案件中,它适用于一国接受了它的国民的案件(cause),它的国民主张其权利由于他国违反国际法而被漠视(disregarded)。(注:Interhandel case,ICJ Reports,1959,p.6.)用尽当地救济作为国际习惯法原则,在国际社会具有普遍拘束力。除了国际习惯这一渊源外,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还为许多国际投资公约和人权公约所重申。例如,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华盛顿公约)第26条规定:“缔约国可以要求用尽当地各种行政或司法补救办法,作为其同意根据本公约交付仲裁的一个条件”。该公约所建立的仲裁程序用于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争端,属于国际程序。但是该条确立的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不同于习惯法上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自动适用:用尽当地救济不是提请ICSID中心仲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外国投资者的当然义务,只有应东道国的要求订入同意条款中,才能产生投资者的这种义务。(注: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7-458页。)因为《公约》所建立的仲裁程序本身就具有排斥东道国当地救济的意义,ICSID的仲裁管辖权是自愿管辖,如果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订立的仲裁协议或条款中约定直接将争端提交ICSID解决,而没有要求用尽当地救济,这意味着东道国放弃了这一程序上的权利。反之,如果东道国在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中有这种要求,则意味着用尽当地救济是国际仲裁的前置条件。因此,《公约》第26条的条文并没有确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自动适用。在实践中,《公约》的多数缔约国一般并未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因为《公约》的主要目的不是解决侵害外国人的国家责任问题,而是要为解决投资争议提供一种中立的程序,用尽当地救济的必要性不是很明显。(注:石静遐:《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用尽当地救济作为习惯规则,它能否为条约的规定所排除?在1989年ELSI公司案中,意大利主张美国股东没有用尽在意大利的当地救济程序,而美国辩称:美意FCN条约没有明文要求当事人必须用尽当地救济,因此美国股东不需承担这项义务。国际法院否定了美国的主张,它表示难以接受一项重要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可以通过默示的方式予以免除的观点。也就是说,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可以通过条约以明示的方式予以排除。(注:M.N.Shaw,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569.)国际法院这一论断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为习惯规则的性质。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不存在效力等级上的差别,(注:当然,对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列举的各种渊源是否存在层次问题,国际法的学者们持有不同意见。参见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但是,按照后法优于前法原则,条约可以以明示的条文修改或排除现有的习惯规则的效力,除非该习惯规则同时为强行法规则。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是被申诉国的权利,它当然可以通过与申诉国的条约放弃这一权利。如果条约没有提及某习惯规则,那么该习惯规则对于该条约的缔约国具有普遍而自动的效力。
当个人用尽在东道国的救济程序后,其本国可以在国际层面实施外交保护,代表该个人向侵害国进行国际求偿。依此推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适用于个人的权利受到东道国侵害的场合。反之,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不适用于求偿国的权利受到他国的直接侵害。在前述ELSI公司案中,国际法院感到难以发现与直接侵害美国股东相互区别和独立的侵害美国国家的违反条约的争端,但是如果该求偿中混合了国家的利益及其国民的利益,那么用尽当地救济仍然适用,因为如果一国基于该国利益受他国直接侵害的国际求偿也以用尽当地救济为前提,这将意味着该国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主张将受到侵害国国内法律秩序的限制,即使这种求偿在侵害国的国内法律程序中也能实现。理论界在外交保护权的性质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外交保护上,国家没有直接的利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代理性地行使源自个人授予的权利,因此,国家在外交保护的行使上具有自由裁量权。(注:See ILC Report 1998,Chapter 5.)但是,不管外交保护究竟基于何种权利,对于国家的直接损害来说,国家肯定是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因此而进行的国际求偿不属于外交保护的范畴。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当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受到他国的侵害后,它具有直接的国际求偿权,而不受制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本身的性质,国际法理论上存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种对立的学说。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认为一国导致外国人损害这一事实本身就产生国际责任;而后者主张,单纯的损害事实不能构成国家责任的充分根据,除非该外国人用尽当地救济而未获得补救。(注:邹立刚:《试论国际法上的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日本学者认为:学说一般将这一原则作为提出国际请求的程序要件对待。参见[日]松田芳郎等:《国际法》,辛崇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本文同意程序法说的观点。从法理上看,一项不法行为(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只要实施,其不法行为就已经存在,其法律责任随之可予以追究。退一步讲,即使受害国没有追究该国际责任,这仍然不影响该行为的不法性。用尽当地救济只能构成国际程序的延缓条件。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在许多案件中,待遇(对外国人的——引者注)本身构成了违反,而用尽当地救济是求偿可受理性成立的标准的程序性条件。(注:ILC Report 1999,Chapter 5.)国际法委员会的国家责任条款二读草案第1条规定: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它对不法行为要素的列举未包括用尽当地救济。用尽当地救济在该草案中为第三部分第一章“一国责任的援引”下的内容(第44条),也即,用尽当地救济与否将决定能否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从该草案的条文体系看,用尽当地救济应为程序性条件。(注:与二读草案不同的是,一读草案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第三章“违背国际义务”项下的内容,以此作为违背国际义务的判断标准。由此可见,一读草案似乎采取了实体法说。但是,即便如此,按照一读草案,用尽当地救济作为实体性标准的限制性条件是“该项国际义务容许该国以其后的行为达成这项结果或相当的结果”。)
二、GATT/WTO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与实践
作为多边贸易协议的GATT/WTO协议,它们具有一套独立的争端解决程序。那么,该争端解决程序的启动是不是也要以出口商或其他私人当事人用尽被申诉成员国内的救济程序为前提?GATT/WTO协议对用尽当地救济没有作出明文的规定。在争端解决实践中被申诉方以此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管辖的抗辩的实例也不多。可以说,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没有得到争端解决机构的确认。相反地,在许多贸易争端中,被申诉方国内的法院程序与GATT/WTO的争端解决程序经常平行地进行。
在GATT时期,涉及当地救济与争端解决相互关系的一个著名案件是1992年墨西哥——美国对灰色波特兰水泥的反倾销案。在该案中,美国主张:墨西哥没有将启动调查和进口计算的有关问题在美国国内行政程序中提出,也没有在磋商中提出,因此,墨西哥应被禁止将这些问题在GATT专家组程序中提出。美国的法律依据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反倾销守则》(注:该守则指1979年东京回合谈判达成的反倾销协议。)第3-6条和第15条中都得到显示。对于美国的主张,专家组分两个步骤进行了反驳。首先,专家组认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对诉诸《守则》争端解决程序的权利的根本性限制(fundamental restriction),如果《守则》的起草者有意适用这一原则,那么他们应当为这一原则提供明文的条款(explicit provision)。(注:GATT document ADP/82(1992),para.5.9.)其次,专家组考察了《守则》的条文,认为《守则》没有明文要求用尽行政救济程序作为专家组解决争端的条件,至于美国所援引的《守则》条文仅仅用于保证进口国调查机关为外国供应商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和维护利益以足够的程序上的机会。(注:GATT document ADP/82(1992),paras.5.9-5.10.专家组专门提及守则第6条第7款的条文:“在反倾销调查的全部过程中,所有当事人应当具有充分的机会为其利益辩护”。)
专家组意见的实质是否定了用尽当地救济在反倾销争端中的适用。美国在本案中仅仅以墨西哥未用尽在美国的行政救济作为对专家组管辖权的抗辩,没有涉及当地司法救济问题。从逻辑上看,专家组既然否定了用尽行政救济,当然也就否定了用尽司法救济。有意思的是,美国对用尽行政救济的主张和专家组的相应反驳均未直接涉及用尽当地救济是否国际习惯规则的问题。按照前述“ELSI公司案”中国际法院的裁决,用尽当地救济是习惯规则,如果当事国没有以条约或其他方式明文排除,则它应当自动地适用。但是在本案中,专家组则要求《守则》中应当对用尽当地救济有明文的规定。从这个角度看,专家组并没有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习惯规则来看待。当然,专家组这一证明逻辑是与美国的主张相对应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所依据的《守则》第15条第5款,专家组认为它与用尽行政救济无关,而仅仅涉及专家组在事实认定上的限制。这一条款与之后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议第17条第5款几乎完全相同。专家组的这一论断将为WTO反倾销争端解决涉及到的同样问题提供参考。本文以为,即使出口商没有在进口国调查程序中提供证据(即美国所说的行政救济),从而成为之后的争端解决中的不利因素,但这只是构成案件实体上的障碍,而与出口成员能否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无关。
在乌拉圭回合关于反倾销协议的谈判中,美国曾经建议设置用尽行政救济的条款。这一建议没有为协议的最终文本所采纳。但是,美国所主张的“用尽行政救济”的范围和评审标准与国际法上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并不相同。(注:J.H.J.Bourgeois,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Antidumping Law,in E.-U.Petersmann(ed.),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p.291.)美国强调用尽行政救济可能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个是美国希望以此减少它在反倾销方面被其他成员提起争端解决程序;另一个是用尽行政救济本身也是美国行政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美国法上的用尽行政救济原则是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该原则的目的在于避免司法程序不必要的和不合时宜地干预行政程序。(注: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652页。)该原则的设计在于分配美国的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保障行政权力一定的自主性,限制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它能不能被照搬到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则不无疑问。美国学者Croley和Jackson就指出:“在一国国内的行政程序中,有关私人当事方经常是真正的参与者,而在WTO专家组程序中,一国政府才是当事方,在国内程序中它可能未曾有现实的机会陈述事实。”(注:[美]杰克逊:《GATT/WTO法理与实践》,张玉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特别是,当某成员仅仅在DSB指控另一成员的国内法律时,用尽行政救济原则更无适用的余地。在WTO成立以后,涉及用尽当地救济的重要案件是1997年美国——阿根廷鞋类等物品进口措施案。在该案中,阿根廷主张:它的国内异议(challenge)程序可以作为其违反GATT第2条的抗辩。按照阿根廷宪法,国际法优于国内法,阿根廷任何法官都可以在利害关系人的请求下宣布违反WTO协议的措施违宪。如果进口商是违反WTO协议的国内法的受害者,进口商可以启动快速和免费的国内异议程序。专家组对阿根廷的抗辩予以了否定:一成员违反GATT义务,而不管它的国内法律制度中是否提供了对这种违反的救济。不管该国内法院系统如何有效,在法院系统启动前,它已经违反了WTO的义务。而且国内程序不可避免的迟延和不确定性将与WTO原则和GATT/WTO关税约束的目标相左。后者则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可预见性和安全性。(注:WT/DS56/R,paras.6.66-6.68.)
与前述水泥反倾销案不同的是,阿根廷主张用尽法院救济,但WTO专家组同样予以了否定。阿根廷强调的“快速”、“免费”的司法救济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上的“有效救济”条件相似。专家组认为国内程序是否有效与阿根廷是否违反WTO义务无关,只要其海关征收了高于减让表的关税,它就构成违反义务。这一点从侧面论证了本文前述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程序法说。退一步说,即使专家组承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未用尽当地救济也只能成为WTO争端解决在程序上的障碍。另外,WTO专家组对用尽当地救济予以否定的方法与水泥反倾销案也不相同:后者从反倾销守则的条文直接入手,而不考虑用尽当地救济是否习惯规则;前者从GATT/WTO义务的性质入手,认为用尽当地救济与GATT/WTO义务本身存在抵触。可以说,WTO专家组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否定更为彻底和全面。
三、WTO协议的权利主体与用尽当地救济
如前所述,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条件之一是个人的权利受到外国国际不法行为的侵害。易言之,个人享有国际法上直接赋予的实体权利。个人在外交保护中的地位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在传统的外交保护的概念中,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而是违反国际法的牺牲者(victim)。但是,外交保护的最新发展是:个人作为国际法的直接受益人(direct beneficiary),已经被授予某种法律人格。国家仅仅是其拥有国际法合法保护的利益的国民的代理人(agent)。(注:ILC Report 1998,Chapter 5.)例如,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适用最为发达的国际人权保护领域,个人已被确认为国际人权法的主体。在国际投资领域,双边投资条约所规定的投资待遇都是赋予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
同样地,在WTO中,WTO协议所设定的权利主体究竟是国家还是个人,也直接影响到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WTO协议中的适用。在权利补救方面,在GATT/WTO争端解决中,申诉方所主张维护的利益究竟是其自己的利益还是它所代表的本国贸易商的利益?因为,当地程序所保护的利益必须和根据实际情况与此后的国际求偿中保护的利益接近一致。(注:N.J.Udombana,So Far,So Fair:the Local Remedies Rule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7,No.1,2003,p.6.)如果申诉方在国际程序中仅仅是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国际程序就无须以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为前提。
德国学者彼德斯曼就认为:因为GATT争端解决程序主要被设计为保护缔约方的“条约利益”,而不是它们国民的私人权利,GATT申诉的可受理性从来不需要以用尽当地救济为前提。(注:E.-U.Petersmann,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1948-1996:An Introduction,in E.-U.Petersmann(ed.),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p.117.)P.J.Kuyper则认为彼德斯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外交保护的场合,如果国家明确地支持其国民的求偿,这种求偿也归于(attributed to)该国家。国民在条约中被赋予权利以及之后国家在国际性法庭进行求偿的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注:See A.Marschik:Too Much Order?The Impact of Special Secondary Norms on the Unity and Effic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No.1,1998.)本文以为,就外交保护而言,国家在国际程序中的求偿当然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但是求偿之后的结果是由个人来承受的(例如,得到东道国的赔偿)。在GATT/WTO争端解决中,被申诉方败诉的结果是给予有关国家补偿,但这种补偿是被申诉方在市场开放上给予申诉方贸易减让,而不是给予贸易商赔偿。此外,Kuyper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是:GATT/WTO协议究竟有没有赋予个人以权利?
在WTO协议的主体部分——货物贸易规则中,WTO协议并没有直接给予贸易商国际法上的权利。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取消数量限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的减少等贸易自由化规则虽然能够给各成员的贸易商带来市场开放的好处,但是这些协议规则的权利义务主体均是WTO各成员,而不是贸易商。货物贸易规则均以“货物”为核心,这些货物与各成员方的“连接点”是原产地,而不是本国国民(公司)生产的产品。各成员在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基础是本国与外国的进出口利益的大体对等,而不是相互地直接赋予对方国家的国民以贸易权利。可以说,WTO协议的形成充分体现了缔约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双向便利”的特征。《建立WTO的协议》的目标是“为谋求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实质减少而作出互惠互利的安排”,“互惠互利的安排”一词表明《协议》“关注的不是单个的商人,而是政府间贸易政策的协调”。(注:[美]查诺维兹:《WTO与个人权利》,张若思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340页。)也就是说,WTO协议所确立的是各成员围绕针对产品进出口的贸易政策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进口国与外国出口商的法律关系。
虽然一国进入WTO争端解决程序往往是由于受到外国贸易壁垒损害的本国产业的驱动,但是该国在决定是否提请争端解决时并不以本国产业的实际损害为依据。我国2002年《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第29条规定:如果被指控的措施或做法构成贸易壁垒,我国视情况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同样地,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无论是“违法之诉”还是“非违法之诉”,都不以申诉方个人的贸易权利受到对方贸易措施的侵害为启动的条件。在“违法之诉”中,只要存在违反某适用协议义务的情况,即认为该行为构成了对申诉方利益的损害。在“非违法之诉”中,不管被申诉方的行为是否与GATT冲突,只要它导致申诉方依GATT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行为也是可以被申诉的。总之,它们均以申诉方利益的损害为前提。正如前述阿根廷鞋类案的专家组报告所言:GATT协议不仅仅为了保护实际贸易流量,而且为了创造未来贸易的可预见性,(注:WT/DS56/R,para.6.68.)GATT/WTO协议所关注的并不是个别贸易商因贸易措施所受的具体损害,而是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即使某一成员的出口贸易并没有受到其他成员贸易措施的现实损害,按照DSU,它仍然可以对其他成员进行申诉,因为其他成员的贸易措施将影响到它未来的贸易利益。
在WTO成立后,WTO协议的规范对象与之前的GATT可能有所不同,特别是TRIPs和GATS协议。TRIPs序言强调:“承认知识产权属于私权”。GATS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赋予各成员的服务和服务的提供者。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由于TRIPs和GATS协议包含了保护私人当事人的法律义务,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当在这些领域中适用。(注:R.S.J.Martha,World Trade Disputes Settlement and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Rules,Journal of World Trade,1996,pp.119-129.)对于这种观点,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没有任何明示的参照(reference)的情况下,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者们不可能有意在GATS、TRIPs协议(要求用尽当地救济)和其他协议(不要求)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注:P.Lichtenbaum,Procedural Issues in WTO Dispute Resolution,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9,1998,p.1224.)本文同意后者的观点。很难想象,在一个一揽子协议里可以存在两套不同的权利义务主体。DSU为各适用协议设立了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虽然TRIPs和GATS都有关于本协议争端解决的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规定并没有涉及它们在权利义务主体上的特殊性,更没有涉及用尽当地救济。不仅如此,本文以为,在协议适用的权利义务主体上,GATS和TRIPs并没有特殊性。仅以TRIPs为例,虽然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求各成员按照国际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但它的直接目标是保证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序言)。在TRIPs中,“WTO可轻易免去政府尊重这些核心权利的义务,因为这些权利只是间接延伸到个人”,“2000年,WTO首次允许以取消知识产权作为补救手段。尤其是,WTO还准许厄瓜多尔政府径直中止它对欧共体的TRIPs的义务。”(注:[美]查诺维兹:《WTO与个人权利》,张若思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342页。)如果知识产权是发明者们依据TRIPs协议而直接获得的权利,它们就不应当因为本国政府的非法贸易措施而被他国剥夺。此处厄瓜多尔的TRIPs义务并不是针对欧共体国民的义务,而是针对欧共体的义务。
四、余论:WTO司法审查制度与用尽当地救济的关系
与GATT相比,WTO协议建立了相对完善和详尽的司法审查制度。例如,《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各成员对最终裁决和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应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快速进行审查。此外,《补贴与反补贴协议》、GATT第10条、TRIPs、GATS、《海关估价协议》等协议中也设置了司法审查制度。P.J.Kuyper认为,WTO协议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可以支持在WTO中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注:P.J.Kuyper,The New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The Impact on the Community.See J.H.J.Bourgeois,W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Field of Anti-dumping La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1998,pp.265-266.)司法审查当然属于进口成员方的国内救济程序,但是,WTO协议对司法审查程序的要求是不是等于它建立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本文不同意Kuyper的观点。司法审查在WTO协议中不是一个普适性的制度,有些协议对司法审查根本没有任何规定(例如《保障措施协议》),很难想象在一揽子适用的WTO协议下,有些协议的争端解决必须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而有些协议则不需要。即便以《反倾销协议》为例,它虽然规定了详细的司法审查规则,但是按照它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如果进口成员的行政当局已经决定采取最终措施(最终反倾销税或价格承诺)或者具有重大影响的临时措施,另一成员可将此事提交DSB处理。也就是说,反倾销争端解决不需要以利害关系人提交进口成员进行司法审查为前提。
德国学者M·Hilf认为:就保护个人权利而言,WTO框架内存在两套机制,一套是新增强的争端解决程序,另一套是国内法院的司法审查。这两个水平上的司法保护之间没有制度上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age)。(注:M.Hilf,The Role of National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in E.-U.Petersmann(ed.),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p.571.另外他在该文中专门提及:WTO之所以不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因为GATT的争端关系到市场扰乱,由于它们的特殊性质,争端应当被迅速地解决。)也就是说,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成员方国内司法审查程序是相互独立和平行的司法机制,彼此无管辖隶属和审级关系。成员方可以建立比WTO协议要求更为广泛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于同一宗贸易争端,利害关系人在进口成员方国内的司法程序和其本国在DSB起诉进口成员方的国际程序可以同时进行。进口成员方可以适用本国的国内法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WTO协议的解释无须等待DSB作出初步裁决。
“在无需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法院或者行政执法机关没有公信力,外国的企业和个人大可不必寻求国内救济,而应直接通过其本国政府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注:孔祥俊:《WTO法律的国内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WTO协议建立的司法审查制度,其目的是为受不法贸易措施侵害的贸易商提供更多的救济程序。对实施不法贸易措施的成员方来说,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可以对国内行政权力被贸易保护利益集团随意驱动进行宪政控制,为该成员提供自我纠错的机会。但是,国内司法审查程序并不是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前置条件,因为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宗旨是寻求成员方之间利益损害情势的“迅速解决”(prompt settlement)。
标签:wto论文; gatt论文; 国际法论文;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论文; 法律论文; 个人习惯论文; 行政救济论文;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