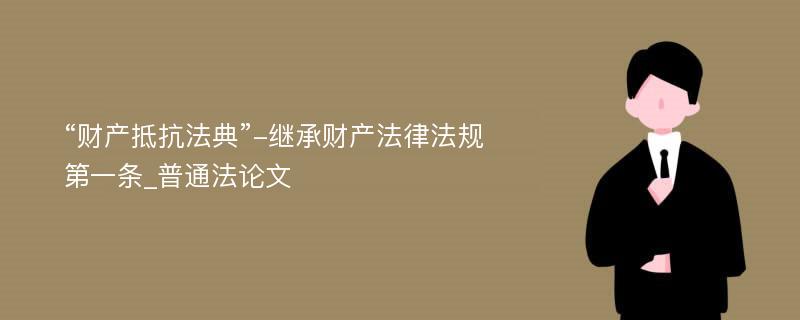
财产权利的对抗力规范——从继承①中的财产法规则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产法论文,抗力论文,财产论文,权利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从继承看财产法
继承是每个自然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基本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转型后,身份继承不复存在,财产的继承成为继承法的惟一内容。②按照大陆法系的通常做法,继承是与财产法(物权法与债法)并行的独立法部门,这种体例安排固然有利于提炼系统的继承规范,但也容易忽视继承中蕴含的财产内核。事实上,继承规范与财产规范有相当大的交集:正如Ugo Mattei所言,代际继承(Intergenerational)是土地价值得以累积的重要原因(此论点实际也适用于动产),而财产增值是财产法的重要课题。③作为一种财产分配制度,无论是意定(遗嘱)或法定(无遗嘱或遗嘱无效)继承都要遵循既定的财产法规则,这要求财产法必须回应继承领域的现实诉求;反过来,从继承看财产法会为财产法的更新与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
继承与财产法的紧密联系,在财富观念的现代转型背景下尤显突出。根据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考察,从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的“物质经济学”将物质本身视为财富[1](P.52)④。但近代社会的财产观念发生了变革,物质(资源)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纯然产生于控制交易的法律工作的那种无形的和无形体的财产概念”[2](P.10、19、200-208),物质本身没有价格或价值;市场关注的是针对不同物质的不同财产权利,后者取代了具体的物质,成了现代社会财富的载体。由此看来,继承的本质是财产权利的(法定或意定)移转和分配;被继承人处分的、也是继承人在争取的是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利;这使得继承不仅仅具有经济内涵,更具有法律(权利)内涵。
作为一种法律概念,权利代表了公权力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许可与保护。但在许可和保护的同时,法律中的权利形态会塑造、影响乃至限制现实的经济活动。萨维尼对这一点有过深刻的认识,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萨维尼认为具体的法判决(也就是权利)受到法律规则的支配,而法律规则的基础则是实证法律制度[3](P.12-13)。这颇有实证主义的味道,因为它表明具体权利不取决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和意志,而决定于(法官所依据的)实证法律制度。⑤实证主义或许不是好的政治哲学,但却提供了一种有效理解现实的路径:不能进入实证法框架成为权利的经济利益会大大贬值,因此实证法的权利形式和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的经济意图能否实现。在大陆法系(德国法系),这里的实证法主要来自物权法与债法。与一般的财产行为(如买卖、租赁或借贷等)直接面向财产法(物权法与合同法)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行为,继承必须在既有的财产权利框架内展开,也必然受到财产法的影响甚至支配。然而,将继承单列的大陆法系往往忽视了这一事实,财产法的分析不重视继承;而对继承法的讨论也忽视财产法。比如我国继承法第3条列举了若干可继承的财产,但仍以不同的物质类型为标准,忽视了从物质到权利的财产观念转型,掩盖了继承内容会受到财产法约束的事实。要言之,继承的本质是财产权利分配,而财产权利形式一定会落入财产法的范畴,因此财产法的研究就必须考虑到对继承的顺应与适用。
不难想见,继承是特定稀缺财产的分配计划:无论是遗嘱继承(包括遗赠)还是法定继承,往往是多个有继承权的主体围绕着一个客体主张权利。这正是被继承人处分财产时的困境:由于涉及多方当事人(配偶、父母、子女甚至朋友等等)的利益,被继承人无疑希望能够自由安排遗产,最大限度地利用财产以满足各方需求。作为财产权利人处分财产的重要方式,继承规范必须反映和保证被继承人处分财产的意思自治,⑥因为财产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但这个要求针对的不是继承法,而是财产法,因为财产法提供的权利规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基础。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涉及财产价值的累计与增值,继承不仅仅是个人事务,更具有社会意义,合理的财产权利规范会有力地促成良好的继承方案,不仅会充分满足被继承人作为财产权利人的意思自治,还将发挥继承财产的经济价值,更能有效地降低因继承纠纷而支出的无谓成本。然而,目前的财产法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颇值反思。
二、传统财产法之不足:形式有限,对抗力不足
众所周知,在传统大陆法系的财产法体系中,物权与债权是基本支柱。究其原因,物权与债权的客体(物与行为)和效力(支配权与请求权)可以涵盖传统世界基本的财产形态。而物权与债权不单纯是两项权利,更代表了一整套系统的规则与制度。正因如此,现实中大部分财产权利均被纳入了这一二元体系。然而,传统财产体系的缺陷在继承领域体现得非常明显。试举一例,甲(男)知悉自己得绝症,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子女,但担心子女将房屋出售导致妻子无处安身;但若把房子留给妻子,又怕妻子(尤其是妻子与子女非自然血亲)再婚影响子女继承房屋利益。这要求妻子可以在其有生之年用益该财产,但该用益不得侵犯子女最终的财产利益。大陆法系有如下几种选择:第一是利用合同约定,但按照传统财产法,债权缺乏对世性,无法对抗第三人,风险较大。另一种是创设物权(比如居住权),但如果关系再多几层(比如希望妻子死后将房屋交由自己妹妹使用,然后再归子女),再或者假设被继承人甲希望,只要乙不破产便可终生使用该房屋(可撤销的利益),或者希望把房屋给乙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子嗣(附条件的利益),或者希望把财产全部留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胎儿),物权法会疲于奔命。这些都是现实的经济需求,如果权利分配明确,各方完全可以和谐共处,但在传统财产法之下却束手无策乃至纠纷不断。
传统财产法的弱点何在?笔者将其总结为财产权利形式有限,且对抗力不足。现代社会坚持财产自由,只要不违反强行性规范和公共利益,权利人就有权利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而处分的关键就是自由创设财产权利。合同法(债权)无疑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处分的有效性同时取决于实证权利的形式与法律效力:债权固然能够满足内容的多样性,但传统财产法认为合同权利仅有对人性,因此其效力不强,无法对抗除债务人以外的其他人。合同法(债法)在实践中仅能规制继承的过程(如意思表示的有效性以及违约责任等等),正是因为合同权利(债权)不仅无法满足继承人的心理预期(谁会满足于一项对抗力不强的财产权利?),更不能解决继承人的最终权利享有。要言之,合同法固然承认意思自治,承认当事人自由创设各种形式的债权,但对人性债权的对抗力几近为零,⑦那么,具有对世性的物权呢?
根据德国法,物权是对世权,对世性基本等同于物权性,绝对性是物权的最大特征[4](P.13)。如果说以直接支配为核心的物权具有对世性,可以排除他人违背意愿的利用,这并无错误;但如果反过来将绝对性认定为物权的最大特征,则大谬不然。就概念而言,这不符合逻辑:物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对物的直接支配,对世性并非物权独有的特性,它只是物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学界对此已有认识。⑧从规范上讲,物权的对世性衍生了物权法定原则,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立法垄断(后文将详述之):由于只有物权才能对世,而物权又要法定,这意味着立法限制了具有对世性的权利范围,当事人意欲具有对世性的约定无效,除非采取法律规定的权利形式。这明显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当干预,是典型的家长主义。
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对世性的关系非常紧密。考诸私法史,物权法定源自19世纪私法体系对纯粹所有权的创造:由于所有权概念被简化为对有体物的管领控制,作为一种“物上最纯粹和最完整的权利”(萨维尼语),所有权上存在负担是暂时的,而纯粹的所有权才是永恒的。正是为了维护这一所有权概念,权利人不再具有任意分离权能的权利。从简化封建权利结构推动交易顺畅的角度看,物权法定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5](P.87-105),但发挥了时代作用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继续存在。事实上,纯粹所有权本身就是19世纪德国浪漫派挪用唯理论的虚构,现实中没有不存在限制的所有权!正如克里斯特曼指出,“财产权包含绝对统治的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是狭隘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有争论的,而且显然是虚假的。没有一种法律制度会把这样的权力赋予所有者。”[6](P.37)有鉴于此,承认物权法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物权的对世性:由于物权可以对抗一般人,如果许可契约或习惯创设“有害公益实甚”;具有对世性物权之得丧变更也要力求透明,故物权要予以法定而有利于公示,目的是保障交易安全。⑨对世性与交易安全成了物权法定的重要理由。但这个理由实际是不成立的。交易安全的关键是信息披露与加强风险意识,而不是通过压缩意思自治来削足适履。英国法上承认大量的土地负担(Land Charge)可以对抗第三人,而作为优先利益(Overriding Interests)的负担甚至无需登记[7](P.36、40-41),不见得英国就不保护交易安全。
应当看到,普通法系同样有类似的类型法定(Numerus Clausus)原则,目的是为了增加可交易性(Transferability),避免“财产权”太过独特引发不必要调查成本(Measurement Cost)而进行的标准化[8]。这似乎证明物权法定是两大法系共有的趋势。但相似的原则在基础不同的时候不宜加以等同。普通法系固然削减了财产权的种类,但普通法系的产权和大陆法系的纯粹所有权完全不同:美国的产权本身就是相对性产权;而英国在保留两种普通法地产的同时,还承认了大量衡平法利益,而这些利益同样具有对抗力。而普通法系还有灵活的信托规范与实践为补充。即便如此,仍然有普通法的学者批评这一原则,主张以公示制度代替物权法定来保护当事人的信赖,这一点也为我国学者所赞同。⑩
事实上,对世性本身是一种无效的概括,它缺乏对财产权利对抗力的准确把握。以普拉尼奥为首的法国“人格主义”学者就认为,任何权利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权实际是非物权人对物权人承担的债务性法律关系,而物权人正是这项普遍消极债务的债权人[9](P.173-174)。这种观点将物权抽象的对世性具体化为针对每一个义务人的债务关系,从而模糊了物权与债权之间的区分。尽管类似的观点“不够严密”,但它准确而有力地看到了对世性概念的问题:它是一种修辞,一种虚构,一种自我循环。所谓可以对抗一切人,恰恰因为没有人来对抗;一旦有人来对抗,对世权还得通过针对特定人来获得实现。用抽象的对世性来概括权利的对抗力是不够的,它无法把握现实中复杂的财产状况。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一般认为物权的对抗力要强于债权,因为物权是对世权,债权是对人权。但当我顺手将手上的矿泉水遗忘于闹市,我对这瓶矿泉水的物权效力,难道真能强过中国政府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协议的债权效力?(该协议总价值达190亿美元,按当日汇率计算约为1250亿元人民币。)我们应当看到,具体权利的对抗力并不单单取决于权利的性质,还取决于每个权利的标的、主体以及其他多种因素。仅仅根据权利的性质来判断权利的对抗力是根本不够的;而再加上“法定”的限制更是错上加错。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财产权规范,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法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它不当地限制了当事人约定的效力与自由;其次,它人为地构建了一个无效的幻象(即物权-所有权可以对抗一切人)。但权利的对抗力不单取决于权利的性质;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权利性质的区分,不能以这种区分单一地决定权利的效力。可以说,财产法在继承领域的缺陷说明,必须抛弃这种“性质-效力”的立法技术,转而构建更为合理的对抗力规范。在这个问题上,英美财产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
三、来自普通法的借鉴:以定序授予与信托出售为例
熟悉英美财产法的人都清楚,普通法系的财产形式本来就较为多样。在英国,尽管1925年财产法改革仅保留了两种普通法地产利益(即非限嗣继承不动产与租赁),但终生产权、剩余产权、附条件产权与可撤销产权、限嗣继承产权等权利仍然大量地以衡平法利益的形式存在。(11)美国法的类型法定原则虽然限制了新型地产的出现,(12)但美国的地产权利形式仍然非常繁多[10](P.100)。不过仅财产形式多样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对抗力。衡平法利益不得对抗善意购买人,这使受托人(因为衡平法利益一定需要通过信托创设)在利益刺激下有违约激励,这会损害继承人(受益人)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如果直接使继承人享有某种形式的地产权(如终生地产)又缺乏弹性,未来权益人会对终生权益人的利益持有施加过大的干涉[10](P.100),这同样会影响继承的分配效果。因此需要一种制度来调和继承人之间的利益,英美法的选择是借助信托,这就是定序授予以及信托出售。
众所周知,普通法地产以存续期间(Duration)为标准进行类型划分。完全产权是无期间限制的地产,为在多人之间进行分配,英国普通法把一项完全产权分为不同的数段时间从而构成数项地产,这就是定序授予(Settlements),即在一个地产上依序创设若干权利。早期定序授予往往被用来实现将地产保持在某一家族手中的封建目的,造成了土地流转不畅:因为定序授予之下常常没有人有全面的处分权,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无法容忍着这种“社会与经济的双重邪恶”。(13)1882年的定序授予土地法(Settle Land Act 1882)着力改变这一局面,这一努力经1925年的定序授予土地法,最终形成了现代的定序授予法。(14)从1926年起,定序授予必须借助信托方式:或为严格定序授予(Strict Settlement),或为信托出售(Trust for Sale)。其中一定有某人持有普通法的地产,一般来说是定序授予中的终生租户(Tenant for life),是定序授予的衡平法利益享有者中第一个有权占有土地的人。他一方面持有普通法地产;另一方面,为自己(一般而言终生租户均为享有终生利益的受益人)以及其他受益人持有信托。(15)但如果没有定序授予中的终生租户(比如受让对方是婴儿无权持有普通法地产),则需有定序授予人指定成文法上的所有人(The Statutory Owner),后者享有终生租户的一切权力。如果连成文法上的所有人也没有,则归定序授予的受托人。这里的受托人是定序授予创设人指定或由法律规定的,对土地不享有地产,但执行监督终生租户的主体,或为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者为信托公司。定序授予的受托人有义务监督终生租户对土地的利用和处分。在没有终生租户和成文法上所有人的情况下,普通法地产由定序授予的受托人持有。而定序授予的受托人是一定会存在的(定序授予人没有指定,则由法院指定)。(16)终生租户(以及成文法的所有人)持有普通法地产,(17)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利:可以出卖(且无须拍卖)、出租、互换、抵押以及改进土地,但不得对土地进行不当利用(受到Waste原则的约束)或不当交易(受到定序授予的受托人的监督)。在终生租户死后,该普通法地产移转于严格定序授予协议认定的下一任终生租户(而非第一任终生租户的继承人手中),直至该信托终止。(18)
严格定序授予在现代社会已不再普遍,原因不外乎如下:一方面是土地不再是最重要的财富,而动产的定序授予成本过高;(19)另一方面根据英国税法,严格定序授予中每次变换终生租户都要纳税,这无疑非常不划算。另外严格定序授予的后位受益人如果不希望土地被出售,他无权要求现在的终生租户不得出售土地。另外,定序授予设计了善意第三人规则的例外:只要购买价金交由受托人,(20)即便买受人知悉衡平利益的存在,其仍可以取得无衡平法限制的地产;而其他衡平法利益的客体从土地变成了购买人支付的价金(即“以钱代地”)。这意味着在流动性更强的货币上建立信托,对受托人更为有利。因此现代英国普遍采用了即刻(Immediate)、有限制(Binding)的信托出售方式。(21)与严格定序授予相比,信托出售有如下优点:第一,如果信托出售在活人之间(Inter vivos),由于受托人有义务直接出售土地,因此无需使用两份文件;第二,信托出售受托人有出售遗产的义务,然后信托建立在该出售价金之上,故方便了一切遗产的适用;第三,委托人可以对受托人的出售义务进行规制(如要求其不得推迟(postpone),因为受托人享有推迟出售的法定权利,前提是一致同意推迟出售;或者约定何时/是否出售土地要取得受益人或其他人的同意),这更加简便,也更有利于委托人(被继承人)。同时,信托出售适用衡平法的转换(Equitable Conversion),即在信托出售之下,由于受托人有出售(或者当遗产是货币进行投资)土地的义务,则该土地(或者货币)被视为货币(或者投资之后购买的新物,如土地),因为“衡平法将应当做成之事看成已做成之事”(Equity looks on that as done which ought to be done)。(22)因此可以说,信托出售是定序授予的改进版本。美国同样在遗嘱继承中采用了信托,后者作为遗嘱的一部分,在委托人死亡时生效。遗嘱继承的信托既包括传统的遗嘱信托,也包括晚近出现的生前信托。信托的优点就是可以灵活执行委托人意图,当然也有助于财产获得更专业的管理和避税[10](P.456-461)。
英美法的借鉴意义是多重的。比如,英美法的继承规范与财产法(尤其是不动产法)紧密相连,这一立法理念有助于将财产逻辑与继承接轨;再如,针对受托人存在的违约激励风险,普通法改造了既有的信托制度,通过“以钱代地”规则保证了受益人(继承人)不会受到善意第三人取得信托财产而造成的损失。另外,定序授予与信托出售的“以钱代地”规则,实际是实现了物(土地)与货币的置换,“物权”标的物可以从实物转化为货币,这明显优于固执“有体性”的大陆法系。但本文最关注的是,英美法如何实现权利的多样化?诚然,丰富的产权/利益框架是一方面原因,但正如前文所言,仅有产权形式的多样化是不够的,关键是产权的对抗力。在英美法中,衡平法利益本身就不是单纯的合同权利,而是具有一定对抗力的财产权利;同时,英美法通过定序授予中的善意购买人的例外规则,保证了继承领域中衡平法利益的对抗力非常强大。实际上,从定序授予向信托出售的转变正是为了加强权利的对抗力——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最具对抗力的财产,因为市场上没有人会质疑持有货币的正当性。这再次证明了本文的观点:财产权制度的关键是对抗力规范。
四、对抗力规范:比较普通法与大陆法
在对抗力规范的问题上,普通法与大陆法存在相当大的技术性差异。
我们首先看德国法。物权作为对物的直接支配,以有体物为对象,以抽象的所有权为核心,(23)目的是反对封建时期多层级、多内容、多负担的财产权利,(24)代之以对有体物进行管领控制的抽象概念[5](P.92)。而债权则是从罗马法的诉(actio)中抽象出来、以请求权为核心、以债务责任为担保的财产权利,其目的是最终转变为物权或“与物权具有相等价值之权利”。(25)物权(尤其是纯粹所有权)具有绝对对世性,而债权除了特殊情况(如“物权化”的债权)皆不具有对世性。可见德国财产法的对抗力规范呈现出如下模式:要么根本不具有对世性(债权),要么可以对抗一切人(物权)。笔者将这种规范称为“全有-全无”的绝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相得益彰的是物权法定的限制:具有对世性权力的范围与内容被明确限定。正如前文所言,这种绝对主义有助于终结封建时期复杂的财产权利以便交易,同时还符合古典罗马法中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在后世的法学延续。(26)但立法垄断的阴影遮蔽了这些历史的光辉;在古代社会理所当然的结论,在现代社会财产自由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越发可疑。
经济意义上的垄断,是指某种产品只存在一个无相近替代品的卖主[11](P.165)。从严格的意义讲,立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垄断。但本文所说的立法垄断系狭义,即以立法方式垄断财产权利形式以及对抗力。由于现实经济行为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规定的权利行使,立法垄断就意味着立法提供了有限的、无法自由选择且无替代品的商品(财产权利)。这是不正当的,因为它扰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我们必须看到,财产权利的创设和交易本质上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在财产自由的现代社会,创设何种权利、权利的具体内容(实际就是对抗力),在不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抉择。但绝对主义的立法只提供全有或全无对抗力的权利,且具有对抗力权利的内容和形式都明确限定,这实际就是对民事主体的“强买强卖”:只能选择或不选择有限种类的物权,自由决定权利内容的权利被剥夺了。(由于无法决定权利的对抗力,因此非物权的财产权风险极大!)与此同时,当事人对权利的对抗力需求不是刚性的,但根据对风险的判断和对对方的信赖,有可能仅仅需要一定程度的对抗力即可,无需达到绝对对世的效果。但绝对主义立法否定了这些现实需求,前文提到的继承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事人要么放弃行为,要么就要花费更多的价格来换取其不需要的权利,实际是立法造成的浪费,更不用说由此引发纠纷而带来的社会成本。
反观普通法的对抗力规范是柔性的(Mud)。(27)美国财产法上的产权具有相对性,没有绝对对世性的财产权,任何人的财产权利仅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对抗特定人,但并不一定可以对抗所有人。让我们借用Armory v.Delamirie一案说明之。甲(案外人)遗失的珠宝被乙(原告)捡到,后者将其送到丙(被告)处进行鉴定,但丙嗣后以乙非所有权人为由拒绝返还珠宝。法院判决丙须返还,因为乙在这里是可以对抗丙的产权人。也就是说,虽然甲仍然是产权人,但在甲未出现取回珠宝之前,乙就是(更优的)产权人[10](P.37-38)。在相对产权体系之下,法官所判定的仅是两造谁更具有优势。而英国财产法虽然承认有可以对抗一切人的财产权利(即普通法产权),但仍然保留了大量衡平法利益,后者具有一定的对抗力(即可以对抗一切非善意的第三人)。这一规则在英国的登记体系之下仍然有效,并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8)这种对抗力规范借助英美财产法的信托制度变得更为普遍而灵活。正如英国学者指出,信托的一个要义就是为了“绕开”(Circumvent)合同的相对性(Privity)。(29)这使得信托既是一种合同,更是一种财产结构。这有力地保障了普通法的双重所有权:受托人持有普通法上的产权,而受益人持有衡平法上的产权。这一点在英美财产法的继承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笔者认为,英美财产法体现了现代财产法的应然之义:为了更好地保证意思自治,就必须保证财产权利对抗力的多样化和个人化。也就是说,大陆法系(德国法系)所采取的绝对主义对抗力规范是行不通的,英美法系的相对主义对抗力规范要更加科学。何谓相对主义对抗力?也就是承认一切财产权都可以对抗某些人,但这里的对抗力不取决于权利的性质(是物权还是债权),而是取决于其它因素。关于这一问题,英美法的选择是根据权利做成的形式,也就是根据信托以及相应的文据来决定。这一做法固然仍有形式主义色彩,但毕竟向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权利的对抗力不宜采取一刀切的绝对主义,而应当充分承认由当事人的自主意志来明确不同权利的对抗力。
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的话,大陆法系之下财产继承规则的尴尬局面将被消解:不用再论证诸如“居住权”等是否可以构成物权,我们可以充分承认当事人自主意志(比如合同)创设权利的可能性,且这些权利均具有对抗力。只是对抗力的大小有所不同,而这完全取决于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取决于当事人(如继承人和被继承人)针对自身偏好和未来风险预期而为权利的对抗力所进行的“保全”活动。要言之,以对抗力制度为核心的财产权规范,充分地保证意思自治,真正地实现权利的多样化,同时也无损甚至有利于交易安全。但我们并没有普通法系的信托传统,应当如何建构属于我们的对抗力制度?
五、以知悉义务为核心的对抗力制度
知悉义务是财产权的哲学基础。美国学者Carol Rose曾指出,诸如占有、用益等现实控制形式实际是向公众宣告权利人对财产的权利意图,此种宣示使得他人知悉该财产权利,这是财产权的关键。(30)这一理论沿袭了自然法的传统,后者强调(如普芬道夫)普遍承认(Universal Agreement)在事实性占有转变为权利中的重要作用,(31)而普遍承认不过是知悉的另一种表述。涂尔干也有类似的观点,即财产的本质是宗教禁忌(Taboo):与只允许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接触圣物一样,只有财产权人才能接触财产;这是一种将某物从公共状态中隔绝出来的神圣性质,其本质是“以物质形式人格化和结晶化了的集体力”[12](P.149-167),也就是表现为集体共识的普遍承认。从理论上讲,一切财产权都包含事实性与法权性要素构成,而后者的核心就是普遍承认以及衍生的知悉。这一财产哲学史的考察启发我们,应当以知悉义务(Notice)为核心构建对抗力制度。
知悉与对抗力的关系是,取得权利知悉权利客体上存在他人权利者,将无法对抗该在先权利人。这一原理适用于一切财产权利。由此看来,所谓债权仅具有对人性,是由于知悉债权存在成本较高,因此对抗力较弱而已,但这并不能使债权与物权在对抗力层面上失去可比性。在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争夺中,知悉(他人权利)将作为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可以想见,权利人和非权利人(希望取得权利者)的合理反应是:对权利人来讲,保证自己的权利为他人知悉,可以有效地对抗其他人的权利要求,这将激励权利人使自己的财产权尽量为他人所知;而从非权利人的角度看,取得权利除了要满足其他条件之外(如支付对价),还需要了解是否存在他人在先的冲突权利。而这两点又各自衍生出如下结论:权利人保证他人知悉自己权利的程度与范围取决于对权利的价值以及风险的判断,因为无限制地令一切人知悉权利,不仅会损害个人的隐私,成本也太高而没有必要;(32)而对非权利人而言,了解他人在先的冲突权利也需存在限制,否则意味着交易将无法进行。由此看来,对抗力制度的关键是知悉义务:知悉义务过重会限制交易效率,而过轻则不利于权利人的权利保障。如何平衡这一困境?
两大法系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认识。德国法的做法是,因重大过失不知悉权利者,排除善意取得。如在动产善意取得中,重大过失而不知不构成善意[13](P.412-420)。举轻以明重,实际的知悉同样可以排除权利。但德国法的进路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由于认为登记簿能提供“更坚实”的信赖基础,故此规则不适用于不动产,这是毫无道理的,德国法学家对此已有批评[13](P.500-502);第二,排除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除了异议登记之外,惟一的可能是真实权利人证明取得人明知登记簿不正确。也就是说,当且仅当登记簿出现了错误,才能被排除公信力。这不仅使登记簿具有了某种巫术性质,徒增了交易成本,更排除了知悉在不动产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不是所有的权利都会被记载于登记簿(尤其是德国物权法包含登记能力概念,这使可登记的不动产权利类型被严格限制)。权利是否能够对抗其他权利,取决于该权利获得知悉的范围与程度,而不取决于权利的表象。德国法固然希望为不动产权利寻找到重要的权利表象依托(即登记簿),但这使得登记簿成了权利的本体,是不正确的。而且德国法将知悉问题局限于物权法(公示),确切地讲是局限于限于善意取得(于非权利人手中取得权利),忽视了这一问题在财产法领域的基础性意义,也就无法将其作为一个普适性的逻辑适用于一切财产权利,人为地造成了财产权利效力规范的分裂与隔膜。
英美财产法设计了较为完善的知悉规则,包括实际知悉(Actual Notice)与推定知悉(Constructive Notice)。前者指实际了解并知悉物权真实归属(至少是应存疑点),后者则指应当了解并知悉物权归属(也就是具有注意义务)[10](P.381-394)。英美法的知悉规则的关键在于范围广泛:任何与权利有关的信息都有可能(而非必然)构成知悉义务。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28年的Hexter v.Pratt一案,(33)该案中甲与甲的母亲(共同被告)就某一地产发生了纠纷,甲声称自己是该地产的衡平法所有人,但该纠纷因程序问题被撤销。就在此期间,原告购买了这一地产,但甲提起了纠错令(Writ of Error),于是原告起诉,理由是认为既然之前的诉讼已经被撤销,故其有权利作为善意购买人获得该地产。但法官认为,即便此撤销是甲自愿所为,原告也对其构成了实际的知悉,何况该行为非甲自愿,故坚持了初级法院的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可见被撤销的诉讼纠纷同样有可能对当事人构成知悉义务,另外还可能知悉义务的也包含占有。(34)
不能否认,德国法的用意是通过占有-登记的二元化方式,为财产权利的知悉义务设定具体的形式要求。这可以有效地简化当事人的调查/交易成本,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德国法忽视了权利规范对未来经济行为的激励意义,在现代社会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交易成本的简化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代价;而且基于现代商品经济对信赖的高度依赖,知悉义务的外在形式必然呈现多样化趋势:统一的权利外观规则是没有必要、且非常浪费的家长主义设计。正确的立法选择是,承认占有与登记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承认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知悉义务;法律要明确不同权利外观的知悉效力比较。这一规则的基本理念是,自由社会中的每个人要承担自己行为的成本和风险,法律不应要求当事人必为某种特定的权利“保全”行为,后者取决于当事人的判断。不同行为所构成的知悉效力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占有和登记簿的记载具有最广泛的推定知悉效力,但占有和登记都不能对抗实际的知悉,也就是说,即便完成了登记,实际知悉在先权利者仍然不能取得权利,但是否构成实际知悉,应当由真实权利人承认证明责任(包括主观与客观)。这是很重的证明责任,因为实际知悉并非总可以成功证明!正因如此,权利人则须结合未来的风险(包括权利的价格、标的、内容以及对未来交易的预期和对方的信赖等作综合考虑),决定采取何种权利形式以明确知悉的范围与强度。而非权利人需进行适当的调查以履行知悉义务,而这种调查同样要基于对交易对方的信赖以及标的的价格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或许有学者会质疑本文规则会有损于交易安全。事实上,交易安全是整体的结构性问题,涉及交易各方的利益均衡。单纯保护某一方的规则往往会无效,因为在一定的供需背景之下,对某一方的保护会引发交易规则(尤其是交易价格)的自发转变。对财产法而言,保障交易安全的本质与关键是明确交易风险的分配,而这意味着加强当事人的风险意识,明确行为可能具有的风险并进行风险分散与降低举措,本文的规则恰恰关注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原权利人需要承担权利取得人实际知悉权利的证明责任,对善意第三人而言已是相当程度的保护。更关键的是,由于不再坚持只有物权能够对抗一切人,而是转而将对抗力与知悉义务相结合,这意味着债权以及其他形式的财产权利都有可能具有对抗力,这一方面对恶意串通处分权利者具有相当大的制约功能,将更好地实现实质正义;同时也将有效地满足个人约定的有效性,从而彻底地解决(如继承领域)权利形式不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悉义务为核心的对抗力规则不仅不会损害交易安全,而是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不再是单纯地保障善意第三人,而是通过明确不同行为的风险将决定权交由当事人判断,将交易安全与意思自治形成了有效地契合。
除了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之外,本文设计的权利对抗力规则还有如下优点:第一,它强调自由,并且将当事人的风险交由当事人判断,节省了公权力统一要求的立法与司法成本;第二,它可以与现有的公示制度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形成有效的契合,并且将推动后二者的现代化;第三,它涉及并符合罗森贝克的规范理论,(35)对证明责任的规定将有助于将权利规范与诉讼制度结合;第四,它将充分地推动权利形式的多样化,不仅有助于解决之前提到的继承领域问题,更将推动物权法与债法(合同法)在对抗力层面上的融合与统一。将知悉义务/效力作为权利对抗力的惟一标准,从理念上讲,它放弃了传统财产法的家长主义与立法垄断,进而走向自由的必然王国;而从制度上看,这一标准将有效地融合公示理论与证明责任,从而兼顾了权利的多样化与对抗力,对财产法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本文的继承、遗产、遗嘱等概念均取广义,也就是说,除非有明确的限定,否则继承就是指自然人死亡后财产的分配、遗产就是指自然人死后留下的一切财产,而遗嘱也包括遗赠。
②因此有学者将继承法称为特殊的财产法,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01页。
③Ugo Mattei,Basic Principles of Property Law,Greenwood Press,p.101(2000).
④这一点也体现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中,物质被认为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具有了价值。
⑤根据林端先生的考察,萨维尼的早期作品就秉承实证主义。参见林端:“德国历史法学派——兼论其与法律解释学、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的关系”,载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⑥法定继承同样是在保护被继承人的意思自治,因为这是在其无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时,由立法者通过立法推定其“意思自治”,本质上仍然是对被继承人意思自治的维护。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法定继承的对象以及顺位是按照与被继承人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就更能理解这一观点。美国法上的无遗嘱继承即坚持这一认识,参见[美]斯普兰克林:《财产法精解》,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⑦当且仅当在特定的条件下债权具有对抗他人的效力,也就是“债权的物权化”。事实上,并非债权被物权化而具有了对世性,而是因为债务关系中的存在可以对抗他人的物权关系。参见孟勤国、张淞纶:“论民法对合同当事人权利的整体性判断——以租赁权与物权行为理论为范例”,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⑧很多学者有过类似的观点,如冉昊:《论“中间型权利”与财产法二元架构——兼论分类的方法论意义》,《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第70-71页;温世扬、武亦文:“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再证成”,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金可可:“论绝对权与相对权——以德国民法学为中心”,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⑨类似论述主要来自台湾学者,如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⑩这一点在国内外均有认识,国外如Ugo Mattei,Basic Principles of Property Law,Greenwood Press,p.92(2000);国内如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第132-134页。
(11)Riddall,Introduction to Land Law,3[rd]ed,Butterworths &Co.Ltd,pp.90-94(1983).
(12)早如霍姆斯在Johnson v.Whiton一案中就指出了这一点,参见[美]杜克米尼尔、克里尔:《财产法》,第5版,中信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215页。
(13)Cheshire & Burn,Modern Law of Real Property,13[th]ed,London:Butterworths,p.69-75(1982)。正因此,美国干脆就拒绝了定序授予以及限嗣继承不动产,以防止封建因素的蔓延。参见[美]斯普兰克林:《财产法精解》,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
(14)定序授予的对象不限于不动产,但其更广泛地使用于不动产之中。因此本文的介绍与讨论也基于土地等不动产。
(15)双重身份要求双重文件:一是移转地产的契据,另一则是创设信托的法律文件。前者决定了持有土地的人是终生租户:后者决定了该人为受托人(毕竟受托人不一定是受益人)。
(16)Riddall,Introduction to Land Law,3[rd]ed,Butterworths & Co.Ltd,pp.102-104(1983).
(17)具有绝对对抗力的普通法地产是土地交易的基础,也是登记体系的中心。在产权登记之下,受益人的权利被作为次级利益进行登记;如果土地未进行初次登记,普通法设计了“以钱代地”的原则(下文会提到),同时辅以查看地契予以保障善意购买人。值得说明的是,在“面纱原则”(Curtain)下,购买人仅有权利查看地契,而无权利查看信托文件。
(18)Riddall,Introduction to Land Law,3[rd]ed,Butterworths & Co.Ltd,pp.97-114(1983).
(19)劳森和拉登则更加直接地指出,现在财产保值的“惟一途径是投资证券”,而非投资土地。[英]劳森和拉登:《财产法》,施天涛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20)定序授予地产出售的价金不是交由终生租户,而是交由定序授予的受托人,由后者为定序授予中的受益人继续持有信托。参见Riddall,Introduction to Land Law,3rd ed,Butterworths &Co.Ltd,p.101-102(1983).
(21)信托出售最早起源自19世纪,正是针对传统定序授予的弊端而诞生,参见Cheshire & Burn,Modern Law of Real Property,13[th]ed,London:Butterworths,p.78(1982).
(22)Riddall,Introduction to Land Law,3[rd]ed,Butterworths & Co.Ltd,pp.78-79(1983).
(23)按照传统物权法,限制物权是所有权不完满的情况,是必将消失的暂时性权利。参见[德]维甘德:“物权类型法定原则”,迟颖译,载《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24)封建时期的财产权利实际是以其负担的封建义务作为分类标准,既包含对上层领主的劳役与货币负担,又包含一定的公共负担,可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9页;[法]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5-280页。
(25)类似的观点请参见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德]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83页。
(26)按照罗马法学家的考察,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主要差别来自于程式,而物权对世、债权对人的说法实际上是后来法学家借助罗马法二分法的发展,原本意义上的二分法要狭窄的多。参见[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10页。
(27)这里借用了C.M.Rose的著名隐喻:水晶与泥淖(Crystals and Mud),意指刚性与柔性规范,参见C.M.Rose,Crystals and Mud in Property Law,40 Stan.L.Rev.(1988).
(28)Riddall,Introduction to Land Law,3rd ed,Butterworths & Co.Ltd,pp.410-411(1983).
(29)严格地讲,这个privity指双方存在法律关系,与我们平时所言的合同相对性并不完全等同,但在这里可以近似理解。Carol Rose,Possession as the Origin of Property,52 U.Chi.L.Rev,p.17(1985)。
(30)Carol Rose,Possession as the Origin of Property,52 U.Chi.L.Rev(1985).
(31)Jeremy Waldron,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Oxford Uni.Press,p.150(1988).
(32)借用Filmer的讽刺,让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取得同样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Filmer在此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知悉是有成本的,因此其手段与范围都取决于当事人的自主判断。关于Filmer的观点,参见See Filmer,Partiarcha,p.273,from Alison Clark & Paul Kohler,Property Law:Commentary and Materia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2(2005).
(33)Hexter v.Pratt,10 S.W.2d 692.
(34)美国的判例,参见Pelfresne v.Village of Williams Bay,U.S Count of Ap.,Seventh Circuit,1990 917 F.2d 1017;英国的判例,参见Williams and Glyn's Bank v.Boland,[1981]A.C.487; [1980]2 All E.R.408。
(35)即每个人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法规范的条件,参见[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以下。尽管大陆法系已经对以罗森贝克为代表的要件分类理论提出了各种,如德国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新说”讨论,以及日本学者石田穰引发的争论,并将要件分类学说修正以利益衡量为标准的新理论。但诚如学者所言,“新说”实际是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修正,且尚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因此罗森贝克的传统要件说仍然应当作为主要的标准。参见罗玉珍等主编:《民事证明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331页。
标签:普通法论文; 信托受托人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财产权信托论文; 法律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信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