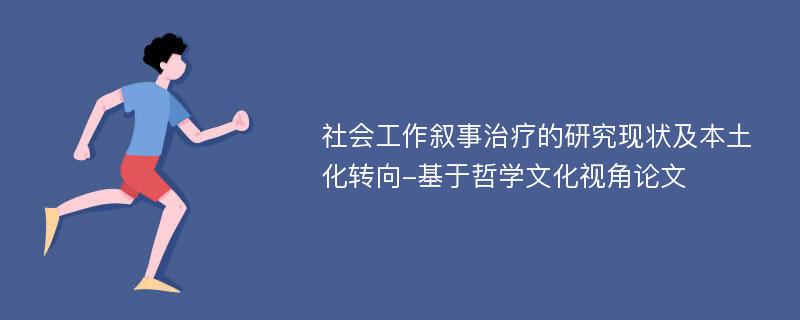
社会工作叙事治疗的研究现状及本土化转向
——基于哲学文化视角
尹新瑞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叙事治疗是基于社会建构论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和社会工作治疗模式。近年来随着叙事治疗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运用,西方学界关于叙事治疗的研究由对该疗法在家庭、儿童等领域的应用及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探索转向对叙事治疗本土化的探究。由于该疗法传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当前国内相关研究在对西方社会工作叙事治疗的学习、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将其应用于本土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与此同时反思叙事治疗的本土化问题。
关键词: 叙事治疗;现状;本土化
叙事治疗是基于社会建构论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治疗和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20世纪80年代,叙事治疗的创始人麦克·怀特把Bateson的诠释论,福柯的权力分析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综合应用于家庭治疗,在澳大利亚开展了叙事治疗方法。此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叙事治疗传遍了世界多个角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成为时下最具影响力的治疗法之一。
一、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社会工作叙事疗法研究的回顾
叙事治疗是西方社会工作学界和心理学界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治疗方式。O'Hanlon认为治疗的叙事方法“代表治疗世界的一个全新方向”,并且是“第三波”心理治疗改革的主要内容[1]。叙事疗法是指一系列社会建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治疗变革过程。通过探索语言如何用于构建和维护问题来实现变革,经验被折叠成叙事结构或故事,为理解和使经验可理解提供参考框架,解读一个人在世界上的经历是叙事治疗方法的本质。White和Epson指出,叙事治疗的基础是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制造问题,为了加深理解,必须从它们所处的背景来看待问题。观察背景包括探索整个社会,探索各种影响有助于创建或维护问题的文化方面[2]。在我们的文化中,经历过艰辛的人有时被视为失败或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他们可能将自己视为问题,并创造自己的故事,描绘缺乏力量和价值[3]。他们可能不会将问题看作是影响和影响他们生活的外部事件,因此问题本身也会得到维护。叙事治疗专门针对这些故事作为有效治疗目标设定的场所。
叙事治疗是目标导向的。Monk,Winslade,Crocket和Epson认为,叙事治疗的主要目标是与案主建立联盟,以获得,鼓励和促进增强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的能力。叙事治疗的目的是拒绝将人视为问题,并帮助他们将自己与问题分开[4]。White和Epson指出,一旦一个人将问题看作与人的身份分开,就有机会改变与创建。这种变化可以采取不同的行为,如抵制或抗议问题的形式,或以其他方式协商与问题的关系。叙事疗法的目标以独特的视角影响治疗进程,在其中替代故事的创造锚定了叙事疗法的治疗方向。在治疗过程中,通过利用创造另类故事的机会帮助个体建立期望的结果,以实现令人满意的生活。具体而言,叙事治疗的目标在于抵制破坏性故事或描写的历史行为对案主的消极影响,并通过协助案主探索自我和人际关系帮助他们创造替代故事。在此期间,借助外化对话的技巧进行“抵抗”,并利用“抵抗”技巧帮助人们创建替代故事。叙事疗法明确的目标导向的特质以及较易掌握的技巧使其在家庭、儿童、青少年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3 D细胞培养是肿瘤细胞缺氧较好的研究模型,而缺氧诱导因子HIF-1α是糖酵解通路及Warburg效应重要调节因子,在无紫云英苷作用时,3 D细胞培养条件HIF-1α蛋白表达较2 D培养明显升高,而紫云英苷作用可明显减少HIF-1α蛋白表达,且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效应关系(图5)。
叙事疗法在家庭治疗领域的研究。Besa研究了叙事治疗在减少亲子冲突中的有效性。运用的叙事技术包括外化(将问题与个人分开),相对影响质疑(探究问题对个人和个人对问题的影响),确定独特的结果和独特的叙述(确定有例外的时间),带来独特的重新描述(为行为附加新的含义),以及分配会话间任务(在会话之间的会话中开始的持续工作)[5]。St.James-O’Connor,Meakes,Pickering和Schuman等学者检视了家庭对他们的叙事治疗经验的看法,试图在他们的治疗经验中发现对家庭成长有帮助作用的技术和方法。作者发现叙事疗法在协调家庭成员关系减少家庭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叙事治疗中,长期参与治疗的家庭比短期参与治疗的家庭减少问题的程度更大[6]。Weston、Boxer和Heatherington通过叙事治疗和探索性研究认为,重视儿童的故事以及对家庭冲突的归因可以帮助整个家庭的治疗工作,同时表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叙事疗法有重要意义[7]。
必须确保母线槽安装位置的正确性并确保可靠性,确保已安装水平和垂直对齐。另外,母线槽的安装距离应保持合理,以保证后期维护工作的便利性。在安装时,用于连接公交专用道的螺旋接头不应放置在地板上,距离地板或地板至少600mm。在特定连接过程中,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段连接措施。在公交专用道的安装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对公交专用道产品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通过这种措施,在电气设备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母线壳体损坏或任何水流入现象的可能性,在公交专用道的安装质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叙事治疗也被广泛应用于针对青少年问题、女性问题的介入。通过对叙事疗法的应用一方面检视了该疗法的有效性,拓展了叙事疗法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问题、不同服务对象的介入,不断完善叙事治疗的治疗体系和技术手段。运用实验研究法,引入实验组和对照组,学者Parisa Rahmani等探讨了叙事疗法对存在识字困难的儿童的介入效果,研究发现叙事疗法可以有效降低儿童的阅读障碍问题[8]。Wolter,DiLollo和Apel等人的研究同样证实了叙事疗法在治疗儿童识字、阅读障碍等方面的有效性[9]。叙述疗法在介入女性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方面也卓有成效,该疗法能有效减轻乳腺癌康复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问题[10]。
关于叙事治疗具体技术的研究。Coulehan、Friedlander和Heatherington以Carlos Sluzki的叙事治疗方法为基础,研究了在最初的治疗中案主从个人内部视角向人际系统或关系视角转变中,他们对呈现问题的构建的过程,试图明确治疗师在促进案主成功转换叙述过程中所涉及变化过程的组成部分[11]。叙述暴露疗法(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NET)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一种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短期治疗方法,用于介入全面治疗复杂创伤患者[12]。该疗法认为创伤处理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始终嵌入创伤事件的背景和整个案主的生命史中。
ACT是一种广泛用于评价哮喘控制效果的评分标准,其能够准确、客观、简单、有效地评估哮喘病情;痰EOS检测能够直观地反映支气管哮喘气道炎症情况[17]。本研究结果显示,MP感染组患儿ACT评分明显低于非MP感染组,痰EOS高于非MP感染组,非MP感染组ACT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痰EOS高于对照组,与周彩丽等人[18]研究结果一致。张皓等[19]在儿童肺功能检测及专家共识中指出,支气管哮喘患儿肺功能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且伴随肺炎支原体等病原菌感染的患儿肺功能下降更严重。
2015年以来,她在全市首创“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制度”,聘请了54名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充当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力量薄弱等问题,还将监管重心下移,将监管触角由区、乡向村延伸,实现了区、乡、村三级监管和信息网络。这项工作得到新华社等中央、省、市各大媒体的关注。2016年9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走基层”采访组,专门对仙女湖区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工作制度进行了深入采访和报道。
随着叙事疗法在心理和社会工作领域运用的不断发展,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叙事疗法的本土化问题。特别是在社会工作领域,众多一线社会工作者将该疗法应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案主群体中,同时众多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也在不断向本土引介叙事疗法。在此过程中,叙事疗法本身是否能够契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案主的需要,以及是否满足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的本土实践,以上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近年来随着叙事疗法在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逐步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在运用叙事疗法过程中的文化敏感性和本土化问题。在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社会工作者面临的问题显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西欧和北美的社会工作将案主问题视为个人与环境之间在相互适应方面出现的问题或者将其视作个人能力不足,传统心理动力学理论则结合精神分析理论将案主问题视作人格发展冲突等。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强调个案和临床工作,通过微观技术和临床社会工作方法处理个体情绪、心理、精神和政治参与等人的高层次需求问题。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服务范畴不同,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面对的是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宏观层面密切相关的问题,如艾滋病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等等。单纯依托微观层面的叙事疗法、心理动力学方法等难以有效解决案主面临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而言,他们不仅仅着眼于对案主微观层面的介入,还承担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角色,西方家庭治疗理论被认为不足以应对案主面临的客观外部危机。
第二,针对叙事治疗的方法论、具体方法和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叙事治疗技术的最新进展的研究。叙事治疗理论和方法论直接影响了叙事治疗的具体技术和行动程式。有学者指出叙事治疗模式强调语言在治疗过程中的中心性,话语既是案主表达思想的过程,同时也是意义诠释的过程,具有意义建构的作用,不同的话语方式会影响个体自我建构的取向[37]。受问题故事压制的话语方式是无力的、消极的,它会使个体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叙事治疗就是通过对话,使来访者摆脱这种消极的话语方式,采用积极的话语方式,以建构更有生命力的人生故事,语言的建构与作用在治疗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8]。同时叙事治疗也非常重视信件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本质而言信件是治疗的延伸,通过信件将治疗室之内的治疗过程延续到治疗室之外从而稳定治疗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治疗向前发展。除了信件之外,视频、录像、纪录片等影音资料亦是叙事治疗的常用工具之一,在叙事治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叙事疗法的本土化探索中,艺术和写作的重要性伴随着人们对叙事治疗的本土化思考而逐渐显现,艺术和写作治疗的方法在叙事治疗中也得到广泛应用。艺术和写作作为语言表达的辅助手段可以用来补足语言表达的限制,为案主表达和反思提供多元化的媒介,作为一种指示物(referent)用以探索案主深层次的情感和意义,并提高案主的洞察力以及引导案主做出改变。有学者指出,人们是从故事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这反映了文化故事中关于生活应该如何进行的某些版本[23],这种本土心理通过故事,神话和其他象征性事物进行表达。在关于南非本土艺术叙事治疗方式的研究中,Solomon认为艺术和手工艺品可以治愈种族主义和贫穷的给当地民众带来的创伤[24],同时成功的本土叙事艺术治疗需要更多的对治疗方法本身和治疗师的培训和尊重。
由于产生于欧美文化背景的叙事疗法与其他社会在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治疗中片面依赖以欧美文化为背景的概念和假设难以有效回应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需求。在前殖民地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叙事疗法本身具有的西方社会工作知识背景使得该疗法比本土实践方法更受尊重,然而却与本土的信仰、规范和实践相抵触。尽管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希望帮助案主,但所使用的叙事治疗的理论和模型阻碍了他们帮助当地社区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治疗师自身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他们必须找出与本土案主更加相关的工作方法。同时在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工作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家庭治疗方法的本土相关性问题,认为西方的家庭治疗方法难以契合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实践,他们是被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欧美科学知识的一部分,有必要使家庭治疗本土化以便为当地社区的利益服务。在非洲等前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很多学者认为西方家庭治疗方法延续了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目的在于使本土传统助人方法失效从而获取知识垄断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土叙事疗法,治疗师应该更多地关注当地的精神和政治叙事,使本土治疗方法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和认可。另外本土知识和文化传统中同样蕴含了叙事治疗的方法和技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必须注意考察所运用技术和理论的本土相关性,挖掘本土知识中蕴含的传统治疗方法。在这方面学者Ngazimbi深入研究了叙事疗法与非洲传统家庭治疗方式之间的相关性,认为非洲家庭治疗是运用重视本土传统和知识理论为当地社区服务的一种模式。非洲本土知识是整体的、统一了经验、理性和直觉的认识方式。它们认为人是包括精神在内的认识层次的一部分,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17]。人类通过启蒙和启示获得知识。这说明知识获取不仅是理性的、经验的,而且是直观的。知识通过口头语言、象征、仪式和艺术传播。非洲本土的家庭治疗师不将案主某一方面的问题与其整体的精神状况、生存环境、社会关系割裂开来而是采取综合性的视角看待案主的问题,并且传统治疗师主动引导案主谈论他们的问题,以案主视角诠释问题的缘起、影响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在治疗过程中,传统治疗师扮演了支持者、顾问者和治疗师的角色。Bakker和Sny-ders指出,要成为非洲有效的家庭治疗师,重要的是尊重当地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工作中,并将叙事治疗方式进一步本土化[18]。同样Nwoye也认为由于不同于西方家庭的家庭关系模式,在非洲国家的叙事家庭治疗中,叙事家庭治疗应该采取更加具有文化相关性的策略。非洲儿童对父母的重视和情感显然不适合运用联合叙事家庭治疗的方法,可以通过循环面谈的方式将困境儿童和家长分开进行面谈并循环进行[19]。
LU Wen-juan, CHEN Jing, ZHANG Jing-qing, JIANG Xin-hui
近年来在叙事治疗领域西方学界开始进行不同治疗方法的整合运用,如将理性情绪疗法、仪式疗法等与叙事治疗进行综合运用、将认知疗法与叙事疗法进行整合运用等。在针对非洲艾滋病患者的叙事治疗中,学者Nwoye将仪式治疗与叙事疗法相结合,重构艾滋病患者自我统一性,在减少艾滋病对患者带来生活叙事断裂的同时激发了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以及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力[13]。Robert J Lieb和StevenKanofsky就曾将系统控制论和叙事心理治疗相结合,发展出一种综合的治疗模式[14]。Oscar F Goncalves和Paulo PP Machado则将认知疗法和叙事疗法整合使用,发展出认知叙事心理疗法;实践表明,运用此疗法不仅可以明显缩短治疗疗程,而且其疗效也十分显著[15]。
在问题解决向度和叙事疗法的有效性等方面同样需要考虑本土特殊性问题。比如有学者认为,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难民家庭和事故受害者或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等问题与传统的西方家庭治疗模式基本无关,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家庭内部冲突的受害者,而是外部侵害的受害者,单纯通过叙事疗法无助于解决他们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问题[20]。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发展本土叙事疗法需要注意本土文化可能具有的压迫性功能,不能将本土知识视为对破解案主主流叙事的绝对有效的策略[21]。在叙事治疗中,某种主导地位的精神叙事和本土文化很可能阻碍而不是有助于案主的恢复。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者如何将西方叙事治疗的主要精神和策略与主流叙事对事件的诠释进行整合,并对主流叙事进行批判是叙事治疗本土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主要问题。针对此,有学者指出应该就专业的和案主的两种不同叙事诠释框架各自的分歧点以及对心理治疗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公开对话,而非假设任何一种框架都具有较高的有效性[22]。通过对两种视角的再认知、重构和关联的方式对传统和西方解释框架进行审查。
一个配镜师教一个新上岗的雇员如何向顾客要价:“当你给顾客配眼镜时,如果他问多少钱,你就说:75美元。如果他的眼睛没有颤动,你就说,这是镜架的价格。镜片50美元。如果他的眼睛还是没有颤动,你就补上:每片。”
此外,通过与人本主义治疗模式的横向比较,有学者也分析了两者之间进行融合的可能性。叙事治疗与人本主义治疗在治疗程式上存在差异,人本主义认为问题内在于人,案主在中期目标中承担主要责任;叙事治疗则认为案主与问题是分离的,即案主是案主,问题是问题,并将问题外化作为治疗的核心。治疗程式上的不同源于两者在元理论方面的差异,人本主义治疗模式主要基于存在主义哲学,而叙事治疗的哲学基础则是现象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34]。不过,虽然两种治疗方式存在诸多差异不过由于两者对人性理论和预设层面存在相似点,因此也使得两种治疗模式之间的整合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学者从跨学科领域试图打通叙事治疗与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跨学科之间的关系,促进叙事治疗与其他学科的整合发展。如叶舒宪教授认为叙事治疗是一种治愈仪式,通过叙事仪式个人心理得到康复和愉悦,叙事仪式本身能够给讲述者带来强大的心理能量促进患者自愈[35]。同时,他也指出我国民间流传的巫医、传统文学作品中蕴含了大量的叙事治疗思想和案例[36],这是叙事治疗与文学、民俗学等学科交流互鉴、整合发展的基础。
在资源能力方面,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权重依次为0.667、0.333,说明有形资源能力影响效果较大,无形资源影响效果略微;在管理能力方面,资源协调与经营管理具有相同的权重,说明其影响效果相同;在技术能力方面,核心技术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的权重依次为0.667、0.333,说明核心技术水平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运营能力方面,市场营销与产品服务的权重依次为0.333、0.667,说明产品服务能力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二、国内社会工作叙事疗法的研究现状
第一,针对叙事治疗方法的引介与分析。随着学界对叙事治疗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叙事治疗本身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体系。从哲学基础看叙事治疗受现象学、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论和福柯思想广泛影响,并成为其治疗方法的理论根基。同时以上理论和哲学基础对叙事治疗的影响是不同的,由此也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叙事治疗模式。在这方面,学者尤娜进行了深入分析,她认为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叙事治疗模式,即现象学叙事治疗和社会建构主义叙事治疗,这两种叙事治疗模式具有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脉络。现象学叙事治疗是以现象学为哲学根基的叙事心理学,它并不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否定绝对真理的相对主义立场[29]。学者赵梅认为,现象学立场的心理学者注重原初经验的真实性和人生意义的超越性,强调文化建构所依据的普遍性,以及人类的共同命运和目的,因而与超越主义和世界性范围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契合。以社会建构论和建构主义为基础的叙事心理学,主要以Epston、White以及Gergen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意义和行为的社会语境,认为自我和同一性是由社会群体的话语实践塑造而成的社会建构,即一切都是语言实践的建构物,意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化作用[30]。在社会工作领域特别是在家庭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和心理辅导学者深受Epston和White的影响,多秉持社会建构主义的叙事治疗。建构主义叙事治疗的哲学基础可概括为:现实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现实是经由语言构成的;现实是藉以叙事组成和维持的;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就在最基础的方面颠覆了以问题解决为治疗目标的传统治疗方式,治疗师不再专注于案主“问题”的成因,而是参与对话,对何谓问题、谁构成问题、谁要负责任、谁要做出改变等一连串相关的话题,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协助当事人以说故事的方式,做出重新探索、澄清、扩展、删除以及创造[31]。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对案主语言和生命故事的重新解读,协助案主重构生命故事并在解读故事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力量。因此,社会工作者运用叙事疗法为案主提供服务的过程同时也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由于叙事疗法在重新建构来访者人生故事的同时,也有可能会消解权威的力量[32]。因此,不论是从事家庭婚姻治疗领域的工作者,还是在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者,都应该要谨慎的使用这种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方法的力量[33]。作为家庭治疗领域的重要方法,近年来叙事治疗成为家庭治疗领域的一种前沿性治疗模式,作为家庭治疗整合模式的重要类型,叙事治疗的兴起以及对家庭组织多种形式的尊重,提倡非等级制方式和反对强加于人的影响,使家庭治疗拥抱了后现代主义的两个伟大价值:多样性和民主。
叙事治疗传入中国并被用于实践的时间不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麦克·怀特应邀来香港举行讲座,直到2000年后叙事治疗才在香港开始流行。2000年,Freedman和Combs的《叙事治疗:解构并重写生活的故事》中文版在我国台湾地区翻译出版。在中国内地,叙事治疗在大陆社会工作中运用的实践则刚刚起步[28]。通过对当前叙事治疗研究的爬梳、分析来看,国内社会工作领域针对叙事治疗的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是针对叙事治疗模式的引介与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集中在对叙事治疗的哲学基础、理论来源、基本方法的介绍以及与其他传统治疗模式的比较、整合等进行的梳理和研究;其次,针对叙事治疗的方法论、具体方法和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叙事治疗技术的最新进展进行介绍;再次,通过将叙事治疗的模式引入社会工作实务领域,通过实践不断反思社会工作叙事治疗的本土化路径。在该阶段叙事治疗被广泛应用于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等专业和服务领域,在反思实践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摸索叙事治疗的本土化模式。
在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社会工作者在为不同移民群体进行服务的过程中也不断探索与他们更加具有文化相关性的介入模式。面对不同的移民群体、少数民族群体,社会工作者所运用的治疗方法、技术和理论模式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以与服务群体具有文化相关性的方法来为他们提供服务。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发展契合不同服务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首先应该了解当地的文化、知识,人们思考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认知模式。Ngazimbi通过将叙事治疗与非洲传统文化和治疗模式相结合对非洲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外来移民不但面临母国主流文化的控制和制约,同时面临与迁入国文化相融合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更加努力才能得到迁入国社会和公众的认可,这有可能导致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问题[25]。因此,针对外来移民的叙事治疗应将叙事治疗的语言、概念、技术与移民身上具有的本土知识和价值理念相契合,而不是僵化使用主流叙事治疗模式。在对印度女性移民的叙事治疗过程中,社会工作师充分考虑到印度女性的自尊、不愿意向外人求助等特点,运用绘画和写作的方式在维护她们自尊的同时保证了治疗的顺利进行[26]。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哈特曼认为“有多种了解事物的方式”[27],采用哪种认知方式主要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文化塑造了我们的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和价值预设,而这些反过来又反映和表达了我们的文化。此外语言、文化与交流的过程和风格密不可分,因此发展本土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需要了解社区民众的沟通形式和过程,防止社会工作者自身的文化负载(culture Laden)与社区民众的语言和沟通模式相脱节。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在运用叙事疗法进行介入过程中要懂得“包装”,要及时调整原有的技术和语言,采用为服务群体所熟悉的语言、概念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此外,在当前国际社会工作学界,欧美家庭治疗方式似乎已经成为普遍社会工作的一种类型,在全世界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国家中推广统一的治疗模式和技术。在多元文化时代,支持单一流行的家庭治疗模式是没有价值的,需要给予不同文化认可的多种家庭治疗方式发言权。就叙事疗法而言也需要形成符合目前全球化性质以及与多元文化相关的治疗方法。有学者指出应以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视角看待源于欧美文化的治疗方法与非欧洲民族疗法之间的关系[16]。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疗法可能与以欧美文化为背景的叙事疗法相似,但在文化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差异既不是肤浅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文化民主观挑战了欧美社会工作疗法在世界其他地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优越性以及前殖民地社会工作者可能存在的情感—心理殖民联系。这种文化民主的观点主张在叙事疗法以及其他欧美文化疗法与非欧美本土疗法之间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
第三,叙事疗法在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应用与本土化探索研究。在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尝试将叙事治疗应用于家庭社会工作、老年人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中,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不断探索适合我国本土社会文化情境的治疗技术和工作模式。黄耀明通过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运用叙事治疗的策略重构失独家庭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叙事,在此基础上初步探索了失独家庭个案工作的方式和路径[39]。余瑞平则将叙事治疗的方法用于团体工作中,试图通过团体治疗的方式构建失独老人的集体叙事[40]。在医务社会工作领域,叙事治疗主要被运用于癌症患者、中风患者、创伤性暴露者等群体面临的情感、心理等问题领域。有学者认为作为后现代“生命文化”视角下的主要议题,疾病叙事、叙事治疗以及叙事医学的兴起是对“生命医学”模式重视疾病、漠视人性的反抗[41]。叙事取向的医学理念,这一原始主义与先锋精神的文化结合体,建立在后现代哲思和社会建构理论基础上,是疾病叙事阅读治疗和创作治疗在临床和教学上的实践。
随着叙事治疗方式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不断发展,有学者开始反思叙事治疗方式与中国文化和案主的心理特点、行为本身的契合性问题,同时也逐渐探索适合中国人心理和文化特点的叙事治疗技术和理论。如李昀鋆在分析叙事治疗基本原理基础上,指出在中国社会工作情境下运用叙事治疗模式受到案主对该方法的接受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度以及社会工作者对该方法的熟悉度等影响[43]。针对案主对治疗方法的接受度问题,曾文星认为案主主要受干预方法与工作者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44]。具体而言在叙事治疗中,工作者将案主问题与案主本身分开,呼应了中国文化中对“人情、面子”等的强调,同时文本的使用能够避免案主与社会工作者由于缺乏熟人关系的原因而无法建立专业关系的问题。在大陆学界中李明是较早对叙事治疗的本土化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叙事治疗本土化方面他主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叙事治疗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契合性探索叙事治疗本土化的路径和模式[44]。
三、关于社会工作叙事疗法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随着国外叙事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探索不同治疗方法的综合以及将叙事疗法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并且随着国外学术界对叙事疗法本土化意识的逐步提高,关于该疗法的本土化研究也日益增多。国外相关研究者逐渐认识到,面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案主,除了在叙事治疗术语和技术等方面需要进行及时调整外还应在价值伦理层面进行调节以符合本土社会工作实践。
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若没有采取体现案主价值观念的干预措施则会对案主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伤害。换句话说,社会工作者运用的治疗框架若对案主的现象学现实而言是陌生的,那么这种治疗模式将对案主造成潜在性危害。反之,运用与案主价值相一致的治疗模式可能产生对案主更加有益的效果。叙事疗法的价值伦理原则在于建构主义的信念和假设、关于权力的观点、关于人的潜能和主体性的观点、关于问题和改变的本质的观点。具体而言指的是反压迫实践价值观、投身社会正义、赋权、实际照顾、助人和选择,以及接受那些优先于专业伦理实践原则的原则。
从叙事疗法的价值基础来看该疗法本质上仍然是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哲学,强调来访者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能力及潜质,尊重其价值观及生活的模糊性,通过引导来访者将已有的对生活经验或问题的说法,转换为新的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新叙说,从而改变原有叙说的负面意义从而有助于案主问题的解决。这种隐含的西方价值伦理原则与东方集体主义、家长主义、关系取向的价值观念存在冲突和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具体实践中仍需要进一步的本土化。在中东或者东方文化中,案主可能不习惯于详细叙事的治疗模式以及向陌生人透露有可能损伤自尊心或者颜面的事件。此外,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家庭对个体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案主的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自我实现(self-actualisation)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社区等的制约。同时命定观念、宿命论等思想在东方文化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观念对案主发现例外叙事并改变负面叙事具有重要影响,在叙事治疗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就国内关于社会工作叙事疗法的研究而言,当前研究还停留在对该方法的运用及验证方面,尚缺乏对叙事治疗本身的深入研究和反思,尤其是在本土化探索领域当前研究仍然十分不足,仅有的文献主要关注叙事疗法在语言、方法、理论等方面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工作情境的适用性和相关性的探索等方面,在本土概念提炼、系统的叙事疗法的本土介入研究、叙事疗法实践策略的反思与概括等方面仍有诸多不足。
此外,国内学者对叙事治疗本土化的研究往往将本土化割裂开来看,即将叙事治疗的具体技术与中国文化中的某个方面相对照,以此说明叙事治疗在中国本土中的适用性。叙事治疗的本土化既不是将该疗法进行单纯的调整和适应,同时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治疗方法,而是适应当地的社会工作实践和地方性文化的治疗方法,这种疗法对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生活场域中的人来说是有效的。在实务过程中还需要从当地人本身的生活经验、心理特点、提供的经验材料出发总结具体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应注意考察中国人的一般心理特点,中国人所思、所想、所感,以此出发探索和积累社会工作辅导技术、研究视角、理论观点。同时还应加强对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亲属关系为网络、熟人关系为纽带的助人方法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发展本土治疗策略的重要知识来源,并且在叙事治疗中应选择案主熟悉的语言和概念,考察社会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民间习俗、市井文化(民间俗语、俚语),社会制度体系等对案主主流故事建构的影响,寻找具有文化相关性和符合案主心理和行为特点的叙事治疗技巧和方法。
参考文献:
[1]O’HANLON B.The promise of narrative:The third wave[J].The Family Therapy Networker,1998,9(18):19-29.
[2]WHITE MICHAEL.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M].NewYork:WW Norton&Company,1990:18-19.
[3]CHERYL W,DENBOROUGH D.Introducting Narrative Therapy:A Collection of Practice-Based Writings[M].Adelaide: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1998:5.
[4]MONK C,WHISLADE J,CROCKET K,et al.Narrative therapy in practice,the archaeolog of hope[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7:7.
[5]BESA D.Evaluating Narrative Family Therapy Using Single-System Research Designs[J].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1994,4(3):309-325.
[6]O'CONNOR T S J,MEAKES E,PICKERING M R,et al.On the Right Track:Client Experience of Narrative Therapy[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1997,19(4):479-495.
[7]WESTON H E,BOXER P,HRATHERINGTON L.Children's Attributions about Family Arguments:Implications for Family Therapy[J].Family Process,1998,37(1):35-49.
[8]RAHMANI P.The efficacy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storytelling in reducing reading error of dyslexic children[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1(29):780-785.
[9]WOLTER J A,DILOLLO A,APEL K.A Narrative Therapy Approach to Counseling:A Modelfor Working With Adolescents and Adults With Language-Literacy Deficits[J].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s,2006,37(3):168.
[10]PETERSEN S,BULL C,PROPST O,et al.Narrative Therapy to Prevent Illnessâ Related Stress Disorder[J].Journal of Counseling&Development,2005,83(1):41-47.
[11]COULEHAN R,FFIEDLANDER M L,HEATHERINGTON L.Transforming Narratives:A Change Eventin Constructivist Family Therapy[J].Family process,1998,37(1):17-33.
[12]HAMMACK P L.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J].Pers SocPsychol Rev,2008,12(3):222-247.
[13]NWOYE A.Memory and Narrative Healing Processes in HIV Counseling:A View from Africa[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2008,30(1):15-30.
[14]LIEB R J,KANOFSKY S.Toward a Constructivist Control Mastery Theory:An Integration With Narrative Therapy[J].Psychotherapy:Theory,Research,Practice,Training,2003,40(3):187-202.
[15]OSCAR F G,PAULO P P M.Cognitive narrativepsychotherapy:research foundations[J].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1999,55(10):1179-1191.
[16]ROSSITER A.Circle Works:Transforming Eurocentric Consciousness.Fyre Jean Graveline[J].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Letters,2000,11(4):212-215.
[17]SHORTER A.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J].African Affairs,1970,69(277):391-393.
[18]BAKKER T M,SNYDERS F J A.The histories we live by:Power/knowledge and family therapy in Africa[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1999,21(2):133-154.
[19]NWOYE A.A narrative approach to child and family therapy in Africa[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2006,28(1):1-23.
[20]O'CONNOR K.Ecosystemic play therap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y Therapy,2001,10(2):33-44.
[21]GOFF B S N,SMITH D B.Systemic traumatic stress:the couple adaptation to traumatic stress model[J].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2016,31(2):145-157.
[22]EAGLE G T.Therapy at the Cultural Interface:Implications of African Cosmology for Traumatic Stress Intervention[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2005,35(2):199-209.
[23]FITHIAN E.Intelligence reframed:Multiple intelligences for the 21st century[J].Digect of Foreign Social Sciences,2000,35(1):204-205.
[24]SOLOMON G.Development of art therapy in South Africa:Dominant narratives and marginalized stories[J].Canadi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 Journal,2006,19(1):17-32.
[25]KEELING M L,REECE N L.India Women’s Experience of a Narrative Intervention Using Art and Writing[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2005,27(3):435-452.
[26]Al-KRENAWI A,GRAHAM J R.Social work and traditional healing rituals among the Bedoui-n of the Negev,Israel[J].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1996,39(2):177-188.
[27]HARTMAN A.Many ways of knowing[J].Social Work,1990,35(1):3-4.
[28]陈红莉.叙事治疗在团体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1(1):114-116.
[29]尤娜.诠释的现象学实践:叙事心理学及叙事治疗[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3):29-35.
[30]赵梅.后现代心理学与心理咨询流派[J].理论学刊,2005(6):64-65.
[31]黄锐.论叙事治疗模式的形成及其运用[J].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9(4):27-29.
[32]肖来付.家庭叙事疗法及其启示[J].医学与社会,2009,22(2):57-59.
[33]茆正洪,赵旭东.西方家庭治疗的新趋向[J].医学与哲学,2010,31(9):35-37.
[34]郑晓芳,崔酣.叙事疗法与人本——存在疗法的元理论比较[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30(4):82-85.
[35]叶舒宪.叙事治疗论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8(7):53-55.
[36]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77-87.
[37]杨世欣.叙事疗法:话语下绽放的叙事自我[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7(4):134-137.
[39]赵兆,赵燕.心理治疗信件在叙事治疗中的应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3):161-166.
[39]黄耀明.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的哲学渊源、方法和个案实践[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15(2):16-21.
[40]余瑞萍.失独老人的集体叙事与生命意义的建构[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50-55.
[41]杨晓霖.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叙事革命:后现代“生命文化”视角[J].医学与哲学,2011,32(17):64-65.
[42]李昀鋆.中国社会工作情境下叙事治疗的理论技术应用及其可推广性研究[J].社会工作,2014(4):93-99.
[43]曾文星.文化与适合华人的心理治疗[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4):241-243.
[44]李明.后现代叙事心理治疗探幽[J].医学与哲学,2006,27(15):33-35.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767(2019)05-0105-08
[DOI] 10.19810/j.issn.1007-4767.2019.05.018
收稿日期: 2019-07-29
作者简介: 尹新瑞(1986-),男,山东滨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责任编辑:梅 林]
标签:叙事治疗论文; 现状论文; 本土化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