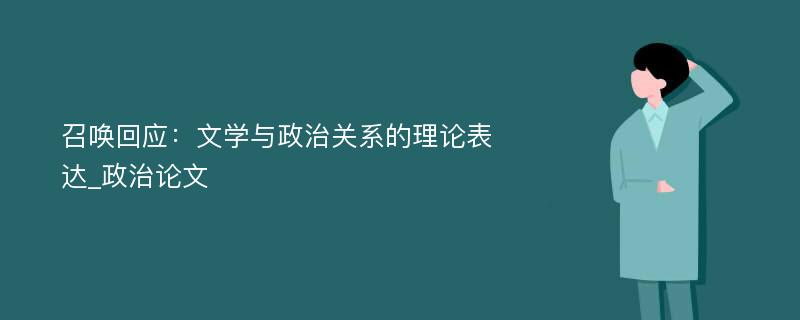
召唤-应答: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这样说绝对无意苛求当时的人们),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是极其困难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也不意味着就不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并非文学一沾上政治的边就会贬值乃至毫无价值。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像屈原这样名垂千古的诗人,如果从其作品中剔除那种强烈而真诚的政治激情和政治理想,还剩下多少动人和有价值的东西?中外文学史上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在今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看得更清楚了:那些在当时引起热烈反响的作品像《班主任》《伤痕》《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啊,人!》等,几乎都有明显的政治效应。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认定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见《批评的批评》一书)。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是人类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是男权社会等级政治的基础和基本模式),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与中国的情形对比,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政治论诗学在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受到质疑和否定时,在西方,它却大行其道;这种对比,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而是提示我们,尽管有意无意地使文学和文学理论远离政治也许有好多正当的理由或迫不得已的苦衷,但真要使文学远离政治,和政治毫无干系,不管在创作还是理论上都既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戈尔德曼颇有创意的“发生学结构主义”,仍然用阶级论来解释作家作品;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些都是从我们许多学人已厌烦的“阶级论”和“经济决定论”中发展出来的。传统政治论诗学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的运用往往有简单化、庸俗化、机械化和片面化之嫌,在极左时期,这些缺陷被恶性发展和膨胀从而导致其走向理论的荒谬,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还不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就一无是处,它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在中国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新的阶级分野已露端倪的今天尤其如此),杰姆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文学确实可以从政治的维度来言说和定位,但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惟一言说和定位文学的维度,它只是众多可能的言说和定位维度中的一种;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平行论”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见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象——〈红楼梦〉》一书),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以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以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可以这样界定“应答”:对一方召唤的任何回应都是应答,而不只是认同。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召唤—应答”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而不一定是简单的认同(当然文学对政治也可以认同);在这里,由于文学是一个最个人化、多样化的世界,对政治召唤的应答必定是多样指向的,正是这种多样指向的应答使它与政治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如果强求文学只能对政治有一种认同性应答而不允许有其它的应答方式,则那种张力关系必定解体,对话关系必将结束,双向对话将变成政治的单向独白,文学对政治的应答关系也必变成同声复制关系;一种单向独白状态中的文学即使不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和传声筒,也是非常单调的。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但从文学所执守的审美理想的高度看,仍然有许多方面是需要否定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确认了文学与政治双向互动互渗的召唤—应答关系之后,我们再来审视政治论诗学,将不难发现,传统政治论诗学远未穷尽其可能的疆域,诗学的政治维度还大有天地。由于篇幅的限制,关于文学与政治召唤—应答关系的许多方面在此都无法展开论述,笔者将另著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