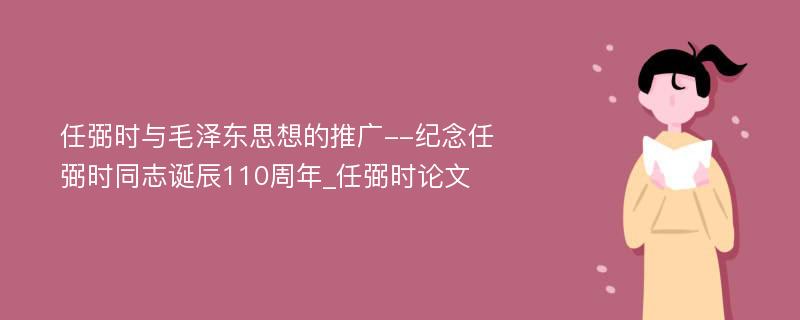
任弼时与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任弼时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周年论文,同志诞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任弼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这一革命的指导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军事和党建、经济领域中的系列诠释、宣传、贯彻工作,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和实践。
一、任弼时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众化
虽然早在进入中央苏区时,任弼时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有过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对它的积极传播却始于长征途中。尤其在领导山西抗战期间,他大力促进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播。
(一)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实践毛泽东北上抗日方针
北上抗日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明确的一条重要路线。这一路线实施的障碍主要为张国焘的挑衅和分裂。1935年9月,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则向党内指出:“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央应该继续坚持北上。”①与张国焘部会合于甘孜地区后,任弼时为解决争取张国焘一道北上的难题贡献了力量和才智。
任弼时就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必要的教育工作。他批判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驳斥了他对毛泽东北上路线的无端指责;他识破了张国焘分化和并吞红二、六兵团的图谋,声明了各部“唯有在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严正立场;他抵制了受张国焘指使而至红二方面军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的“工作团”;②他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出发北上后,多次与傅钟等主要干部彻夜长谈,教育他们团聚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下。③这些斗争和教育工作,有力削弱、杜绝了张国焘分裂行径在红军中的负面影响。
在与张国焘坚决斗争时,任弼时并没忘记对自己之前所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的继续引领。他先后致电贺龙、王震等军中干部,强调“建立党、军统一集权最高领导机关”的迫切性以及促成一、二、四方面军顺利会合的重大责任。④从而及时争取了红二方面军共同反对分裂势力,扩大了对张国焘的震慑力。
在引领部队坚定北上方针的过程中,任弼时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利用有利局势在会合后召集中央扩大会议并请国际派代表出席,并通知张国焘在我方意见均已告共产国际后应不论将来是否向西北转移都协同迎击进犯之敌,⑤还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建议马上集体指挥作战。这些努力实际上提出了应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组织方案,并促成了全军的进一步团结和统一。
任弼时的多方努力,对北上抗战方针的实现和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提及红四方面军对中央路线的拥护时,曾特别强调红二方面军的赞助这一重要因素。⑥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朱德亦回忆说:“因为二方面军拥护中央,迫使他(指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⑦而红二方面军能在其中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显然是与其引领者任弼时的努力分不开的。
(二)推广山西抗战经验,传播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
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先后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解释》、《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解释》、《在山西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意见》等多个文件或函电,明确了游击战略对于坚持抗战的重要性。对于毛泽东频繁下达的游击战争指示,任弼时不仅在山西军队中作了全面贯彻,而且结合自己的实战经历广泛宣传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
发表于1938年1月的《山西抗战的回忆》,即为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宣传游击战争方针的代表作。此文从敌人的围剿、群众动员举措、八路军作战方针等五个方面呈现了山西的游击战争开展情形,总结了有效抗击强敌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模范的游击战争有破坏与威胁敌后交通、使伪组织无法建立、使几百万同胞免遭亡国奴之苦等独特作用。他指出,正因为“敌人以正规战争从正面击退我军比较容易,而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则成为不可能”,今后领导组织民众游击战争就成为一个“急迫的战斗任务”。⑧任弼时以实践为基础的综合论证,有力说明了游击战争是敌强我弱的首要作战方式。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新华日报》,后又被《群众》、《解放》、《前线》杂志先后转载。⑨这些都是当时销售数在万份以上的、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任弼时这一文章对于游击战争方针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
任弼时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访的各方人士重点介绍了游击战争开展的显赫成就。当时,先后有美国记者斯特朗、作家史沫特莱、《法兰克福报》记者、中国作家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等来到前线,⑩任弼时都抽空一一耐心接待,并详尽介绍了抗战情形,描述了游击队员在“冬无寒衣、食不果腹”的恶劣条件仍与敌寇拼搏的牺牲精神,并给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卡尔逊等留下了“真理、理想和智慧”的美好印象。(11)他的这些努力,使外界对八路军所开展的游击战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游击战争的在抗击日军中的重要地位有了全新的判断。
(三)分析能够抗战到底的优势,论证毛泽东持久战观点
1935年底,毛泽东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12)作为军事指挥中的一个具体原则提出。1937年8月,他又在洛川会议上指出,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13)。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军事方针,任弼时在其系统化之前就做过数次具体阐述。
他从如何坚持持久战、为何能实现持久战两方面论证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方针。1938年1月,他指出:“与日本军队作战,是一种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队作战”,“应当采用新的战法,求得能够消耗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使战争能持久”。(14)这显然是从作战方式上对我军如何坚持持久战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从战法上谋求结果的突破无疑具有可行性。1938年2月,任弼时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此文针对民众中的某些消极悲观情绪,阐述了“是否有力量继续抗战到底”和“继续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两大问题。他坚信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抗战必定能持久和胜利,中国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愈能得到国际间的同情与帮助,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的困难将愈增加,其国际地位愈孤立,故“中国的持久抗战将产生由失利而取得许多小的胜利,由不利局势转入有利局势,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的战略上反攻的新过程”(14)。这实际上是论述了中国的持久战何以可能,这种论述细化了毛泽东的持久战号召,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毛泽东曾经分析人民对抗日战争过程和结果迷惑时说:“一半因为宣传解释工作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尚未完全暴露其固有性质以致无从看出其趋势和前途。”(15)任弼时对抗日前途的分析和宣传,有利于人民对持久战方针获得更为清晰的认知,又为毛泽东后来《论持久战》专题演讲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铺垫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938年3月,任弼时入驻共产国际后,仍不遗余力地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宣传。如他所作《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口头报告,围绕着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所坚持的“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原则”而进行,从而使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6)决议案;他还指导了对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作品的俄文翻译,并亲自撰文向中外读者介绍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17)等精彩观点。他的这些努力,使毛泽东对党的正确领导进一步获得组织和国际认可,使共产国际继三十年代初期后又一次掀起毛泽东思想宣传的热潮,如在其驻守期间,《真理报》上有二十余篇文章论及毛泽东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和八路军。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极大重视反过来又促进了它在国内的大众化。
二、任弼时与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大众化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在延安各界欢迎大会上,以“苏联人民对毛泽东极为怀念,并深信在其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克服妥协投降危险”(18)的发言,开启了他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新篇章。从莫斯科归来的任弼时,以延安整风运动为契机,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传播和运用功不可没。
(一)论述整顿三风的具体方式,宣传毛泽东延安整风精神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发起的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一场重要运动。任弼时在负责陕甘宁边区整风、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央党校整风、组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中,数度论述党员干部转变思想和作风的重要性和具体途径,深入把握并有效宣传了毛泽东整风运动的精髓。
第一次论述是在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上倡议实现思想方法的转变以整顿三风。他号召两千多名与会干部主动积极地整顿工作中的不良倾向,并指出,整顿三风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我们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和方法看问题”,从而使我党能应付各种黑暗局面,迎接光明的到来。(19)这无疑是对毛泽东整风思想精神的准确把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反复强调党员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整风运动有着“一体两面”,即要“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错误的作风,又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任弼时的这种深度动员,助推了陕甘宁边区“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21)。
第二次论述是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整顿宗派主义的具体任务的分析。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讲中,针对某些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对军队组织纪律的错误认识,提出要肃清军阀主义倾向,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导,并且党员要“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22)。这一演讲,实际上是贯彻和宣传了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党内宗派主义残余的表现“首先就是闹独立性”,因而,只有铲除宗派主义这一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23)。任弼时的建设性意见,为党员干部明确了整顿方向。
第三次论述是在中央党校所作辅导报告中对宗派主义危害的具体分析。针对中央党校学员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整风文件的较多疑问,任弼时作了一个长篇辅导报告。这一报告诠释了党中央将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的必要性,并以探讨增强党性的途径为契机,重点强调了反对宗派主义问题。他指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正因为宗派主义有很大的危害性,所以“毛泽东把反对宗派主义与反对主观主义同时提出来”。他详尽阐述了毛泽东所说的宗派主义在党内外排斥性的种种表现,继而探讨了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的种种有效途径。(24)这些辅导,是任弼时结合毛泽东的新论述对增强党性文件的与时俱进解读,既突出了毛泽东整顿宗派主义的主旨,又使学员对党性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第四次论述是在历史决议的起草中对主观主义两种表现形式的深度剖析。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且在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25)在修改历史决议草案时,任弼时对毛泽东的论述作了宣传和发挥:缺乏马列主义修养的经验主义者,“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而受过将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德波林学派教育的教条主义者,“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从而使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26)这些分析,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的观点,揭露了反对两种主观主义尤其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深层原因,其基本精神被历史决议的最终稿所采纳。
胡乔木回忆说,经过整风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达成了“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像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的团结,“终于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27)而任弼时对整风精神的四次宣传,为党内这种统一局面的到来、为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落实毛泽东“治病救人”的号召
对错误思想进行必要的斗争,是统一党内思想的重要方式。毛泽东多次肯定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意义。他认为,必要的斗争“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有利于战斗的武器”(28),号召党员干部拿起斗争的武器不留情面地揭发以前的错误(29),以达到我们党“有原则的团结”,并真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30)可见,毛泽东是从维护党内团结、保障工作顺利进展的高度强调思想斗争的意义的。任弼时不仅口头动员党内同志要“以文件作标准”,“深入地检查分析自己的缺点、产生根源,找出改正办法”,(31)而且通过自我批评、帮扶王明反省,卓有成效地践行了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方针。
任弼时多次联系自身的认识曲折作了诚恳检讨。1941年,在毛泽东提出要改造党员的学习后,他就做了积极发言,认为二十年的党史说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并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32)1942年,任弼时在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心得笔记中写道:“毛泽东科学地提出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联系这种新认识,他从马列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作实践。”(33)1943年,他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上,就自己1931年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认识作了检讨,坦诚曾经将毛泽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指责为富农路线,曾认为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狭隘经验论”、在军事上有“游击习气”、在政权中“过于包办”,并在宁都会议上主张伸出击敌,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34)1945年,任弼时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又再次检讨自己的认识局限,并强调自己“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由于看到《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小册子,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嘱咐,由于看到皖南事变后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后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与信赖”(35)。时为重要领袖的任弼时敢于直面错误、深挖思想根源的自我批评,身体力行地贯彻了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思想斗争方针,为其他领导干部的自我批评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同时,他所披露的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曲折认识过程,从反面论证了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策略的科学性,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是一种极有说服力的“现身说法”式的宣传。
为了促使王明检讨自己思想上的严重错误,任弼时对其进行了多次教育和帮助。在1941年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当王明向毛泽东发难并为自己争权夺利行为辩解时,任弼时首次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批评内容在会议上了公开传达,又提到曼奴伊尔斯基对王明擅用党中央旗号、在党内拉帮结派的担忧,还分析了王明党内错误的思想症结。(36)1943年11月,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两条路线期间,任弼时向王明解释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和弄通党内思想问题的目标,并叮嘱孟庆树帮助王明从党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进行反省。(37)1945年4月,任弼时又两次找到王明,征求他对某些党史问题的看法,并取得了他对“左”倾错误路线时间跨度的认同。(38)任弼时的这些工作对于促成王明反省自身错误、促进毛泽东领导权威的全面树立都意义非凡。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往往“自称为‘国际路线’”(39),任弼时依据共产国际领导人意见而对王明的“釜底抽薪”式批评,在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又为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扫清了障碍。
(三)制定土改整党方案,细化毛泽东加强基层组织的总体要求
1947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指出:抗日时期收到了实效的整风运动,并未解决党员大跃进至二百七十万而出现的作风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因而,他提出了当时的迫切任务:“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40)1948年,他又谈到,“‘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必须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忽视了党对群众应有的教育和领导,助长了工作中的尾巴主义错误。(41)任弼时以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为重心,探讨了如何整顿党的队伍、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方案。
1948年,他两次致电中共晋绥分局,分析了如何整顿党的组织并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发于5月8日的第一封电报明确指出:完全抛开党支部,仅仅依靠贫农团进行土改是不妥当的。以晋察冀土改整党的成功经验为基础,他号召对党员和支部作应作恰如其分的估计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如党员和支部比较好的,应采取团结和协同的做法;比较差的,应进行清洗并超越;处于中间状态的,应进行教育并改造。这些区别对待政策的执行,能保障土改整党工作的顺利进行。(42)发于6月28日的第二封电报,继续强调:“贫雇农”路线以及自流主义的放任态度,会削弱党在土改中的领导。电报提及,党员个人与地富关系密切,并不代表整个支部受到地主影响,而且,在农村整党过程中,应重视发扬民主。(43)任弼时起草的这两封电报,以晋绥地区为中心,将毛泽东整党的方针具体化成党内指示,提出了整顿和加强党对土改领导的有力措施。得到毛泽东认同的这些方案,为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和加强提供了其实可行的办法。
三、任弼时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大众化
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他认为革命是以建设为最终目的,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就领导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变革和调整,在革命胜利前夕又规划了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普及和实践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任弼时革命生涯中的一份重要工作。
(一)领导中央机构的调整,贯彻毛泽东的精兵简政理念
在边区物质严重困难时期,毛泽东曾采纳李鼎铭“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议,并撰文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这一困难的极其重要的政策。(44)后来,他又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经问题》指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对于经济、财政工作关系极大,即减少消费支出,增加生产收入,能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并影响人民的经济。”(45)对于毛泽东在战时采用的这项特殊经济方案,任弼时在中央机构作了及时贯彻。
继1942年12月批示下发《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的精兵简政方针具体化为对各根据地“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并“建立领导核心”(46)的号召后,任弼时又承担了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的重任。他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的报告,提出书记处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将中央青委、工委和妇委合并成民运委员会等五点建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方案,对中央机构作了调整和精简:中央书记处从1941年8月政治局确定的七人减至三人,实现了领导身兼两职甚至更多职务的精简,重新组成的领导机关更加统一、高效。中央机构的大幅调整,模范地实践了毛泽东精简人员、减少消费、计划经济的政策,带动了各根据地对精兵简政主义的执行,促进了以节约来推动建设的经济目标的实现。
(二)区分农村中的不同阶层,诠释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政策
1947年夏,解放军在全国进入反攻阶段后,深化土地改革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而要合理地分配土地,必须对农村阶级作出准确区分。当时的各解放区在分配土地时实际采用的标准却五花八门。如仅仅在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就有着单看政治思想表现,或是追查祖辈三代历史,或由贫农团主观判定等多种轻率划分法。(47)在多重标准之下,错划成员的乱象时有发生。熟知毛泽东思想的任弼时,通过修订划分标准、区分对待各个阶层,诠释并运用了毛泽东土地改革政策,促进了各解放区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深感各地划分阶级的盲目和武断,任弼时历尽周折派人找来中央苏区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前者是毛泽东在1933年为纠正土地改革中错误偏向而写就的文章,该文按土地和工具占有情况、劳动参与及剥削程度而对农村阶级做出了科学划分;后者是1933年的苏维埃政府以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发布的一道政令,它明确了对于不同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政策。任弼时在建议中央“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划分阶级的文件”(48)后,又根据实践需要对毛泽东的划分标准作了一些补充。如,他指出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为生产资料的占用和使用情况,并应兼顾孤寡残疾人等特殊情况和医生、教员等特殊职业;他将界定中农的剥削依据从1933年规定的不超过15%提高至25%;等等。任弼时的建议和补充得到中央的很大重视。中央在1947年11月29日指示各中央局、分局:以1933年的两文件作为参考,(49)1948年5月25日,又将任弼时找出的文件“作为正式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还特别提到《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未提到的中富农分界问题,应以中央其他文件及任弼时的相关阐述为准。(50)
为确保土地改革的正确航向,任弼时按照毛泽东团结大多数的统战精神探讨了对于各阶级的具体分配方案。对于土地改革如何具体开展,毛泽东曾多次明确“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改革命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51),“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52),“要牢记团结全体农村劳动人民以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53)。以此为指南,任弼时就土地改革中如何更好地联合农村中的不同阶级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地主,应消灭其阶级剥削制度而非地主本人;(54)对于富农,不应将其与地主平列,(55)并应在选举权、土地和财产的分配上区分吴满友式的新富农与旧式富农(56);对于中农,实行毛泽东的领导原则即可团结这一具有软弱性的“永久同盟者”,并应将解放区政权名称由“农民代表会”改为“人民代表会”;(57)对于知识分子,他们虽出身于地主或富农甚至资本家,但从事的是应受保护的“脑力劳动”;对于开明人士,应采取慎重态度,分给土地而不是对其随便打斗。任弼时的分析既贯彻了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精神,又为土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操作标准。集其观点之大成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稿,深受毛泽东重视,他曾亲自批示将其用明码电报拍发、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在一切报纸上发表、印成小册子。(58)任弼时这些原则的普及,无疑为各解放区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提供了具体指导,促进了毛泽东统战精神在土地改革中的全面贯彻。而土改运动的胜利进行,又为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翻身农民中的普及和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强调不同时期的经济任务,介绍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方略
任弼时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中积极宣传了毛泽东关于革命时期不应忽略经济建设的理念。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应与建设并举,而且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的。这一理念体现在他的多次论述中。如1933年,他在中央根据地作了“必须要注意经济工作”(59)的报告;1934年,他向全国工农兵代表强调“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从而以“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并“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60)1944年3月,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政治、军事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61)任弼时在指导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整顿和发展中,向其他干部反复宣传了开展经济工作的建设需要。如1941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指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62)1943年,他又撰文指出:发展经济建设,是边区“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1944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中,他阐释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63)的财经总方针,并将毛泽东就革命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必要性总结为“革命就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64)的道理。在战争期间,许多领导干部实际上“不愿意做经济工作”(65),任弼时的这些论述是对毛泽东革命时期经济建设方略的有力宣传,他的观点很受毛泽东赏识。毛泽东亲自部署了任弼时演讲稿的广泛传达,批示“印五千本发给五千个干部阅读”,并“在高干会”和“中央党校第一部”进行讲述。(66)在这种广泛传达中,更多的领导干部开始响应经济建设号召,带动了各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普遍开展。
任弼时对于毛泽东的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目标也做过集中论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党内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迫切性和奋斗目标,如在1944年,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强调工业关系到国防的巩固、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富强;(67)1949年,论述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68)的时代任务。任弼时对毛泽东这些工业思想的介绍体现在两次较有影响力的阐释。第一次是在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论述了工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并提出应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各项建设应以工业为中心、各项工作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还提到“必须认识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69)。这实际是结合党的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换对如何工业化作了部署,从而将毛泽东描绘的新中国工业化蓝图具体化为各行业的建设任务。一个月之后,任弼时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再次宣传了毛泽东的工业思想。他介绍了毛泽东对我国工业建设基础的分析,阐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对于实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使青年团员对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70)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任弼时的这番阐发,使青年朋友对于毛泽东的工业化目标有了基本的掌握,并产生正视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困难并投身工业化建设大军的行动自觉。
综观任弼时在以上领域对于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具体推动,主要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岁月中,其传播主要以党员干部和组织机构为重点对象,较之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针对于广大群众的普及工作有其特殊性。也正因为任弼时为中共高层领导人物,他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大众化起到了独特的铺垫和促进作用。如薄一波曾指出,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加上幼年时期的党深受教条主义之害,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领袖“这个过程是曲折的,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高层包括任弼时同志在内的一部分觉悟较早的同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71)任弼时始终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工作。1950年10月,在其去世的前几天,他仍谆谆勉励《中国青年》结合实际生动地宣传毛泽东思想,(72)用实际行动为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和运用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任弼时能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作出重大贡献,绝非偶尔,而是与其理论风格、独特经历、思想水平密切相关:
他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有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理论自觉。他尚在青年时代就较为全面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留苏期间所在中共旅莫支部又注重思想和研究方面的系统训练,延安时期的党史回顾和整风学习使其在理论方面有了新的收获,这些为其在毛泽东思想宣传和阐发中的游刃有余铺垫了基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其归国时“对于实际和政治问题还须特别注意”(73)的思想鉴定,使任弼时更加重视实际与理论之间的联系。延安整风使其愈发意识到: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全盘了解中国,“不然就是无的放矢”(74)。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进行调研。如为深入了解土地改革的真实情况,他多次抱病听取农村土地分配和阶级划分情况的汇报。正因为有着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格,他能根据现实情景或操作之需对毛泽东思想作出阐发和细化。
他很早就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各种运动,又有在莫斯科的求学和参会经历。任弼时年仅二十周岁就投身中国水深火热的革命战争,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历史作用。为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大业的奋斗生涯,一方面,使任弼时切身感受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伟大从而激发更大的宣传热情;另一方面,其卓著功勋使他赢得了全党和全民的热爱从而增进其传播实效。任弼时也不乏莫斯科求学和参会的经历,并有幸见过革命导师列宁,甚至在其逝世后获得“代表东方民族荣誉守灵五分钟”的殊荣,还出席过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和共青团代表大会。这些经历直接为其后来的国际宣传提供了驾轻就熟的便利条件,也能使他对王明等人的说服工作更有影响力。胡乔木在分析毛泽东委托任弼时组织历史决议起草的原因时,就提到“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一微妙关系。(75)可见,任弼时的学习、工作和革命等重要经历,使其在党内德高望重,也使其具备了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独特自身条件。
他有不断修正认识的超常勇气,又能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要。不得不承认,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但是,正是在认识的修正和比较中,任弼时真正感受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魅力。这种曲折的历程也使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拥护态度坚如磐石,并将自己对毛泽东的爱戴之情外化为与主观主义作斗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决心。如果说,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的曲折认识,使其真正意识到了它的科学性而长期致力这一理论的运用和宣传的话,那么,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的准备把握则是这种传播和阐发成为可能。毛泽东的思想无疑是宏富的,而任弼时在宣传中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精深地抓住其中的关键点。比如,他在文中提到过,“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而“发展力量有三个方面,一是巩固扩大自己的力量,二是瓦解争取敌方的力量,三是扶助争取同盟者”。(76)这一认识对于任弼时的宣传工作也产生了启发,无论是在对张国焘分裂行径的坚决斗争,在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介绍,还是土地改革阶级成分和具体待遇的制定中,他都贯彻了毛泽东“发展力量”的策略。再如,在任弼时看来,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77),联系任弼时在整风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正确学习方法和立场的多次强调来看,这一认识直接影响着他的宣传。从此可见,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的准确把握和体会,使他能科学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走样,也使宣传的受众能准确接受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内容。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4页。
②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36页。
③《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④⑤⑥⑨(11)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286、282、298、364、355-362页。
⑦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⑧(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148、138-147页。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508页。
(1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1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16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1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页。
(1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三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379页。
(18)(19)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42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381页。
(22)(2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274、238-255页。
(23)(25)(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819、827-828页。
(26)(2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310、76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页。
(31)(32)(33)(34)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407-408、431、452页。
(35)(36)(37)(38)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410、453、478页。
(3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40)(4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1253、1268-1310页。
(42)(4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453页。
(4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5页。
(4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7页。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603页。
(48)(52)(55)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563、768、569-570页。
(49)《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5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51)(5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6、1307页。
(54)(56)(5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411、411页。
(58)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00-801页。
(59)(63)(6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891、1080-1081页。
(6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6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0页。
(62)(64)(69)(7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8、343-344、464-470、476-478页。
(6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66)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460页。
(6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71)薄一波:《怀念任弼时同志》,《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72)(7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4、388页。
(73)(77)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53页。
(74)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页。
(7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标签:任弼时论文; 张国焘论文; 王明论文; 土地改革运动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论持久战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游击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