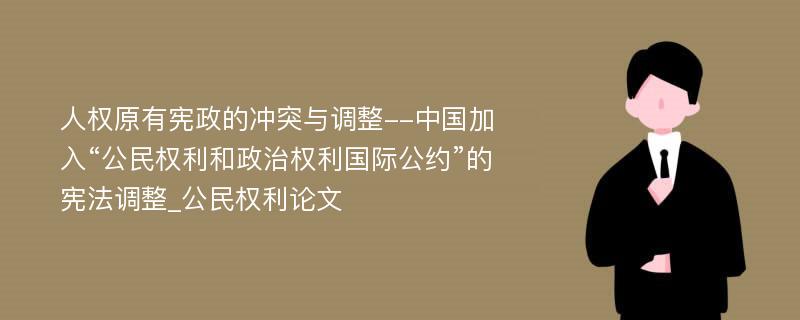
人权本源宪政理念的冲突与调适——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宪法调整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权利论文,政治权利论文,宪政论文,本源论文,公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自通过和生效以来,至今已有大约150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公约起草形成的过程是具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持各种不同人权主张国家共同参与的过程,因此,公约本身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各种人权价值理念、人权主张相互妥协的结果。特别是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公约》的认同更是反映其所具有的人权理念价值的普遍性。《公约》不是对某种特定形态的人权、特定的人权宪政体制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认同,它本身的开放性表明了其对各种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人权宪政制度的兼收与宽容,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公约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加入和批准。
但是,任何妥协不可能超越价值理念上的不同,不能完全抹平由于这种价值理念上的不同而带来的人权主张上的差异。从总体上说,《公约》更多地体现的是西方社会基本的人权价值理念。在《公约》越来越为大多数国家承认的过程中,准确地理解分析《公约》所体现的人权价值理念与缔约国人权价值理念的差异、冲突,从中找出协调的途径与方法,对使缔约国人权宪政体制规范与《公约》确立的人权体制规范相协调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实,理念上的不同导致规范上的不同,仅仅比较分析《公约》与我国宪法规范上的不同是远远不够的。
一
《公约》是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人权宪政理念与国际人权宪章的人权宪政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人权本源的宪政理念上,更是集中体现了西方宪政理论中固有的“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理论,认为权利“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人权是一种自然权利、道德权利。这也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与文件所固守的人权本源理论。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条就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则更是明确宣布“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应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应积极参与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公约》在人权本源问题上重申继承了《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思想,在其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考虑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确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1] (第4页)。
虽然这种人权“源于人自身的固有尊严”的“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理论是西方社会固有的人权本源上的宪政理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开始并且始终只有这一理论,更不意味着这一理念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公约》所体现的人权宪政理念时,必须动态地把握其人权宪政理念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筛选与评价。众所周知,格劳修斯和霍布斯是古典自然法学的创始人,格劳修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专章论证“人的普遍权利”,并首次使用“人权”一词。斯宾诺莎在其著作《神学政治论》中指出:“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从个人的天赋权利出发,个人的天赋权利是与个人的欲望和力量同样广大的。”[2] (第16页)自由主义奠基人思想家洛克则进一步地以社会契约论为立论的根据,把天赋人权思想系统化,指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3] (第136页)此后的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杰佛逊、潘思等进一步把这种“天赋人权”理论加以规范化、法律化。卢梭从“天赋人权”中引申出“主权在民”,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如果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放弃是不合人性的”。[4] (第12页)潘思则甚至认为政治权利也是天赋人权中派生出来的,“每一种公民权利都以个人原有的天赋权利为基础。”[5] (第142页)这些思想直接成为早期人权宣言和宪法的基本人权宪政理念。
然而,这种理论即便是在西方社会中并不是没有受到质疑甚至批判和否定。19世纪功利主义法学的兴起对古典的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认为,“天赋人权”理论是胡言乱语的“浮夸的无稽之谈”,进而提出了所谓“法律权利说”,认为自然的“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假设,权利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便没有权利,即“权利是法律之子,自然权利是无父之子。”[6] (第125页)边沁以法律权利否认道德权利、应有权利的存在根源于他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沿着这种功利主义的法律权利理论的轨迹,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兴起了实证主义法学,几乎成为19世纪法律思想的主流,古典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理论衰落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们在对法西斯暴行及其与实证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使古典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真正得以复兴。法律的正当性、道德性,道德权利、应有权利再次被强调,法律正当性的根基在于它自身宣示并保障的人民的自然的、道德的权利。人类自身固有尊严的自然权利成为法律正当性的基础,国际组织、国际公约中对人权的本源问题加以明示性的回答,构成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承认的基本的人权宪政理念。
人权源于人自身的本性和人自身固有的尊严,人权不仅仅是法律的权利,更是作为人自身所固有的应有的道德权利。“这些权利高于宪法”,“它们是上帝赋予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给予权利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宪法的创始人”[7] (第21页)。基于以上理念,《公约》大量地吸收了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以及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等早期宪法中所反映的人权思想、原则乃至规范,如美国1791年的《权利法案》中“不得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和“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等内容,在《公约》中都有所体现。
在古典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复归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并成为《公约》主流人权宪政理念的同时,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诞生,其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人权宪政观念,也客观上反映在国际人权公约之中。即便在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与传统的人权宪政理念有所不同的新的人权价值观,社群主义人权观的兴起就是这种人权宪政理念发展的一个外在表现。这些不同于传统“天赋人权”观念的人权宪政理念在人权的本源上,反对以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权利优先论”,认为权利从来就不是先验的、普遍的,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保护个人正当利益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多元的人权宪政理念的影响下,国际人权宪章和《公约》在人权本源问题上肯定、认同主流的自然权利理论的同时,也对这种多元的人权宪政理念作了安排,这主要反映在《公约》中“民族自决权”以及其他人权宪章中对“集体权利”的规定和安排上。
二
由于各国宪法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价值传统、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宪法所体现宪政理念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就人权本源这一人权宪政理念来说,并非各国宪法都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国宪法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的宪政观念与价值理念就没有完全地明示在这部宪法之中,但这些观念与价值理念直接影响我们对宪法规范的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人权本源的最早理念是所谓的“斗争本源说”。此种观点最早源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些国家法的教科书。此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权利观认为权利不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而是斗争得来的,这种思想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影响较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观点的影响逐渐减小,与此有着某种学理上的渊源的人权本源观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人权是个历史范畴,人权根源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这种“物质本源说”似乎非常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原理,因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自然会因此而得出这样的逻辑:“物质本源说”是对资产阶级的“天赋权利说”、“自然权利说”或“道德权利说”的批判和否定。这种“物质本源说”的人权本源宪政理念在我国宪法的序言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宪法序言强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正是在这种宪政理念指导下,在我国宪法与宪政实践中,关注的重心是所谓权利的“现实性”,而忽视宪法权利的“基本性”,许多基本的权利借口现实性而无法体现在宪法之中,而这种“现实性”在许多时候又主要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进行考虑,因而显得缺乏科学性、远见性,有的甚至缺乏常识性。在历次的制宪修宪报告中,涉及基本权利内容的说明很少。可见,宪法在设定公民基本权利时,其工具理性超越了其权利本身应具有的价值理性,权利的“基本性”要求权利、人权是终极的价值与目的,因为这些权利是宪法权利、基本权利,所以是基本的,源于“其人之为人”的根据、源于人自身所固有的尊严与价值,而不是源于国家的制度——无论这种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种人权宪政理念上的差别导致我们对宪法权利、基本人权上的理解有多么大的差别!
其实,“物质本源说”理论强调的是权利的受制约性,即人权是受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准确地说,权利的实现是受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物质本源说”和“斗争本源说”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从人权的实现形式来思考人权的本源问题,以此来代替人权本源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解决人权本源问题。
与“物质本源说”相呼应的是所谓“法律权利说”。这种观点表现形式较多,较为代表的观点有所谓的“国赋人权”、“法赋人权”说。如有学者认为“人民掌握了国家主权,才能获得人权,人权是经过革命、经过夺取政权争来的,不是‘天赋人权’,也不是‘商赋人权’,而是‘国赋人权’。”[8] (第2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国赋人权”、“法赋人权”说对中国人权宪政理念的影响是较大的。这种人权宪政理念把法律、国家置于人的基本权利之前,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的“天赋人权”、“道德权利”之说,造成了我们在对人权、权利观念上与西方社会差异较大的理解。在这种人权宪政理念的引导下,也就不难理解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所说的“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在这里,基本权利、宪法权利、人权都是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延伸,是国家权力、国家制度赋予的。
这种人权本源的人权宪政理念与《公约》所蕴含的“固有权利”人权宪政理念差别较大。在《公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内容均属人自身所固有人权(Inborn rights),当然为公民所享有。但是,根据我国惯行的这种人权宪政理念以及司法实践,公民应当享有,而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则公民不能享有。应然权利在人权宪政理念上通常被理解为“法律不禁止的权利”,这种权利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支持因而得不到国家法律的确认、保护和救济。但同时,法律又并没有对这种权利作出明确的否定性的评价,公民行使这些权利时的法律责任问题并不明确。这种人权宪政价值理念上的不同,是我们加入《公约》后面临的最大问题。这种人权宪政理念上的协调与调适也是加入《公约》后的当务之急。如《公约》中规定的一些权利如迁徙自由、罢工自由等问题,我国法律宪法并未禁止,但又不是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协调、理解、适用这些权利必须从人权本源的宪政理念的调适上加以思考与回答。从人权宪政理念上确立“法不禁止即自由”,法律、宪法保障这些法律没有禁止的权利等这样一些观念,本质上必须超越传统的“法赋权利”“国赋权利”的观念,树立人权自身固有、源自人自身固有的尊严的人权宪政理念。正因此即便是法律未赋予的基本权利,只要是法律未禁止的,国家应该保障、确认与救济,因为权利、人权并不源自于法律。正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所言:“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被轻视。”第10条“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
在我国学术界还有一种所谓的“商赋人权说”。此种观点与“物质本源说”有着某种理论逻辑关系。此种观点认为人权是由作为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所决定的。这种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认识到人权观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联系,认识到资本主义使人权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马克思也曾指出过:“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9] (第197页)准确地说,这里应该说揭示了人权概念、人权观念和人权思想起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能因此而断定人权本身只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出现以后才开始产生。应该说,这种理论正确地揭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权思想发展的巨大影响。这种“商赋人权说”的影响更多地只停留在理论学术界,而且它的出现也只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因此,对我国人权宪政理念的影响有限,这里我们也就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
既然《公约》和我国宪法的人权宪政理念存在着这样大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直接影响我们对人权规范、基本权利制度的不同理解,整合、调适它们之间的差别乃至冲突是协调《公约》与我国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国际人权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颈》明确表述,并也成为《公约》理论基础的一个关于人本本源的共识性观点:人权是基于人固有的人格和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这一共识性的观点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来理解,西方传统的古典“天赋人权观”、新自然法学的“道德权利论”都是与这一观点契合,问题在于由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如何去调适中间的差别,完全照搬西方的“天赋人权论”、“道德权利说”,还是拒斥这些理论进而无视《公约》和国际人权宪章已经表达出来的国际社会共识性的观点,这恐怕是我们从事法学理论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从《公约》所表述的共识性观点即“人权是基于人固有的人格和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价值”的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思路:人权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即应该从人自身去寻找人权的本源,简单地说,人权源于人的本性。这一观点应该说也是共识性的观点,即不论处于何种价值文化传统中的社会都可以接受的理念。问题在于人的本性如何把握,人性、人的本质是什么,从不同的理论观点出发有不同的认识。作为我国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古典启蒙思想超越与继承的结果,在人权起源问题上也是如此。马克思在继承与批判古典“天赋人权”理论抽象人性论基础上超越这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也决定了他对古典“天赋人权论”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超越。这就表现在对抽象人性论基础的超越,那种简单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人权本源论思想与古典“天赋人权”是割裂联系的超越思想,不是辨证的,更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辨证逻辑。
因此,从《公约》所表述的在人权本源问题上的共识性观点出发,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社会现实调适、建构起新的人权本源宪政理念,即人权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基于人自身的本性所产生的,因而是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不是以法律、国家是否规定为转移的。从这种人权本源的宪政理念出发思考我国人权宪政制度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我们除了在进一步扩大宪法基本权利范围和保障制度的同时,也要确立这样的宪政规范即宪法未被列举的基本权利,不能视作对该权利的轻视和否定,从而树立起“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治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