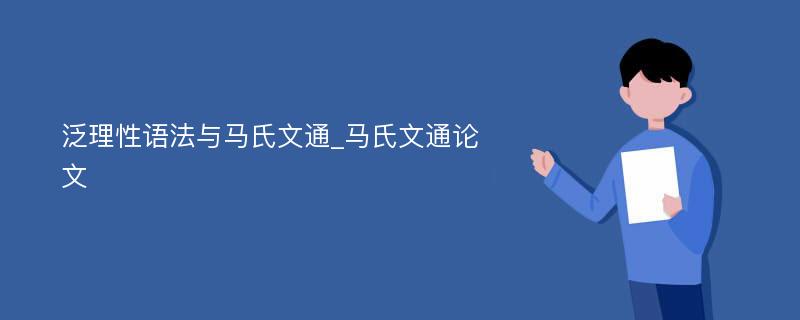
普遍唯理语法和《马氏文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论文,马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年前笔者读研究生时曾在北京大学听郭锡良教授讲《马氏文通》,获教益匪浅,本文初稿即当时呈交给郭教授的期末论文;本文第二稿蒙王海棻、姚小平教授审阅斧正,在此特向郭、王二位教授深表谢意。
《马氏文通》[1]是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自1898年出版以来,语法学界一般承认它有荜路蓝缕之功,批评者则主要说它机械模仿西洋(主要是拉丁)语法,削足适履。也有学者注意到作者马建忠的语言哲学。高名凯(1953)曾断言:“马建忠在法兰西学习语法学,他多少受了波尔-洛瓦雅耳(Port-Royal)理性主义语法学的影响。”许国璋视马建忠为普遍语法理论在中国的倡导者,他(1986)指出,“《马氏文通》后序多处表露了唯理语法的观念。”
法国普遍唯理语法的创始和代表作是1660年问世的《普遍唯理语法》,[2]一般认为作者是Arnauld(1612-1694)和Lancelot(1615-1695)二人,因为这两个人同在法国凡尔赛南部的波尔-洛瓦雅尔修道院任职,所以这部语法又称《波尔-洛瓦雅尔语法》(以下简称《语法》)。本文拿《语法》与《文通》进行对比,以探究普遍唯理语法在语言哲学、语法编写原则和语法体系上对《文通》的影响,并分析《文通》不同于普遍唯理语法之处。
一
今天难以找到具体证据证明马建忠读过或没读过《语法》,不过我们推断他很可能读过。
据《语法》英译本的译者Rieux和Rouin(1975:21-29)介绍,《语法》于1660年4月2日在巴黎出版,很快成为几乎全国通用的语法教科书,到1709年共再版了四次。后来出版的许多普遍语法和法语语法都直接受其影响,形成一个理性主义传统。不久英国和德国也相继出版了《语法》的译本和普遍语法的著作。普遍语法的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那时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语法》的影响才受到削弱。然而它并没有被人遗忘。从1803年到1846年,《语法》在法国共再版了六次。1874年,即在马建忠到达法国前夕,J.Tell(1874,56页)在其《1520-1874年的法国语法家》一书中宣布,“如果在语法方面有什么人人皆知的名字,那肯定就是波尔-洛瓦雅尔了。”二十世纪研究法国语言学史的Guy Harris(1929:33)评论说:“从1660年开始到以后的很长时期,对于一切与语言有关的人来说,此书都是权威性的。”
马建忠1876年以郎中资格被李鸿章派往法国(见吕叔湘、王海棻1986:1),[3]曾在巴黎大学政治学院学习(见陈士林1951;吴文祺1959;林玉山1983:41),[4]1877年在法国考院通过法文、物理、律师、政治、外交等五项考试(见马建忠1960:89)。19世纪外语教学,特别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学,盛行的是语法翻译法,马建忠通晓希腊、拉丁、英、法四门外语,不会不关心语法问题。对当时这样一部人人皆知的权威性语法著作不可能毫无所闻,既闻之而不读之也是近乎不可能的。
二
普遍唯理语法对马建忠的影响首先反映在马建忠的语言哲学上。
唯理主义是普遍唯理语法的哲学基础,只有承认理性人人皆有,才会想到不同语言里应该有一些共性或普遍现象以表达人类共有的理性。在理性和语言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语法》和《文通》作者的观点十分相似。《语法》由上下两部组成。上部分析言语的物质成分(包括元音、辅音、音节、重音、字母、字母读音的改革等6章);下部研究言语的精神成分,即人们遣词造句表达思想的原则和道理。作者在下部一开始便指出:“言语的精神成分是人类超越所有其他动物的一个最大长处,也是人类理性的一个最好证据。”(22页)马建忠在《文通(12页)里引用荀子的话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夫曰群者,岂惟群其形乎哉!亦曰群其意耳。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今人之意者则惟字。”马建忠不同于《语法》作者的地方是,他首先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在语言是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标志这一点上,他(以及荀子)和《语法》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理性和语言的关系,马建忠(13页)还说:“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言语不达者,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矣,形声或异者,通训诂而经义孔昭矣。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已形已声之字,皆人为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12页)。马建忠所谓的“理”,与孟子(1960:261)所说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的“理”和普遍唯理语法学家所谓的理性也是一致的。
如果说在理性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马建忠的观点和《语法》作者的观点只是碰巧一致,属于英雄所见略同,在语言的共性问题上,马建忠显然接受了普遍语法的基本观点。《语法》的作者之一Lancelot是一位语法学家,此人精通多国语言,曾编写过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语法(见Rieux and Rollin 1975:29-30)。通过长期的语法研究他发现,各种语言不仅有各自的特点,而且还有许多共同之处。他通过向逻辑学家Arnauld请教,明白了各种语言存有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的道理,于是合著了这本《普遍唯理语法》。《语法》的首页宣布,其宗旨是“解释所有语言的共同之处和主要不同之处”。再看马建忠,他从7岁起入上海天主教会所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在校时“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经过长达13年的苦心钻研,自称“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马建忠1960:91)由于通晓多门外语,他“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马建忠1983:12)既然各种语言都有“一定不易之律”,“其大纲盖无不同”,那么“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同上,13),自然是理所应当,名正言顺的事情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西文已有之规矩”中的“西文”泛指西方语言,“西文已有之规矩”即当时的普遍语法,不是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这样的特定语法。
退一步说,即使马建忠没有读过《语法》,理性主义哲学和普遍语法论也是马建忠写《文通》的理论依据。
三
在语法的编写原则上也可以看到普遍语法对《文通》的影响。
自索绪尔以来,语言研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历时的,研究语言的演变;一种是共时的,研究语言的状态。索绪尔有一种误解,以为传统(即19世纪新语法学派兴起之前的)语法学家遵循的是共时原则,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1972:118)说:
例如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试图描写路易十四时期法语的状态,并确定其价值体系。为此它不需要中世纪语言;它忠实地遵循横轴线,从来没有背离过。[5]
《教程》中译本的校注者也说,“《普遍唯理语法》完全以逻辑为基础,试图描写路易十四时代法语的状态”(岑麒祥、叶蜚声1980:121)。其实,《普遍唯理语法》虽然是用法语写的,而且也常以法语为例,却不是一部法语语法,更不是描写路易十四时期法语的语法。书中所论,除法、德、西、意等现代地方(vernacular)语言外,还有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古典语言,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普遍语法。《语法》对例句的引用,完全不讲时代的早晚。上自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的拉丁文作品和公元一至二世纪希腊文本的《新约》,下至十七世纪笛卡儿的名言和《语法》作者自己造的句子,《语法》都照收不误(见陈国华1988:68),不知索绪尔因何说“一切所谓‘普遍语法’的东西都属于共时态”(141页)。由于《语法》既不是共时研究,又基本不讲语言的演变,而是阐述超越时空的普遍现象,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泛时语法。
那么《马氏文通》属于哪一种语法呢?马建忠声称自己研究的是“中国古文词”(15页)。在马建忠之前,国内没有人对汉语史的分期进行过研究,什么时期的汉语算是“古文词”,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对于清朝末年的人来说,离当是通行的文言文较远一些(譬如唐代)的文章,大概都可能称为古文词。然而马建忠心目中的古文词,范围要具体得多。他在《文通》的例言(16页)里说:
古文之运,有三变焉。春秋之世,文运以神,《论语》之神淡,《系辞》之神化,《左传》之神隽,《檀弓》之神疏,《庄周》之神逸。周秦以后,文运以气,《国语》之气朴,《国策》之气劲,《史记》之气郁,《汉书》之气凝,而《孟子》则独得浩然之气。下此则韩愈氏之文,较诸以上之运神运气者,愈为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而止。先乎韩文而非以上所数者,如《公羊》、《谷梁》、《荀子》、《管子》、亦间取焉。惟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
这样,马建忠给我们勾划出了他所谓古文词的大致范围:
(一)春秋之世;(二)周秦以后;(三)韩愈之文。
马建忠看到了古文文运的“三变”,这“三变”又发生在从春秋到中唐这样一个1500年的漫长时期。本来,他完全有可能对这个时期丰富的语言材料进行历时的研究,阐明这“三变”的具体内容,从而写出一部古汉语史或古汉语历时语法。不仅有这种可能,事实上马建忠在《文通》里时常指出不同时代的文本在用词方面的特点。这方面的例子,除了吕叔湘、王海棻(1984)和王海棻(1991:147-149)列举的之外,还可以找出一些,例如:
(1)名有一字不成词,间加“有”字以配之者,《诗》《书》习用之。(39页)
(2)秦汉文虚字最少者莫若《汉书》。(247页)
(3)《史记》之用“始”字,与左氏之用“初”字,《汉书》之用“前”字同,可见诸书皆各有字例也。(234页)
(4)夫“之”字以间倒文,此种句法《左氏》、《论语》最所习见。后则韩文袭用者最多。(252页)
(5)《论语》习用“斯”字,《孟子》间用之,后此用之者仅矣。(345页)
(6)“邪”字在《四书》、《左传》不多见,自《语》、《策》诸子始用之。(370页)
然而,这些例子仅证明马建忠对语言材料的观察比较细腻。有一定的历史观念,却并不足以说明《文通》是一部历时语法,因为整部《文通》不是用历史比较法写出来的。对于不同时期的文本所反映的古汉语语法的演变,马建忠仅仅不时地、附带性地评论一两句而已。单从马建忠在“例言”里为自己限定的研究范围来看,《文通》大体上是一部上古汉语语法。因为按照王力对汉语史的分期,公元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汉语的上古期(见王力1980:35),[6]而前面马建忠提到的著作,除韩愈之文外,都不出此范围。在“例言”里,马建忠还提到他引证的另外三部著作,即《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后汉书》虽然为南朝范晔(398-445)所编撰,却以东汉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而且范晔本人去上古时期未远,《后汉书》的语言与上古汉语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三国志》为西晋陈寿(223-297)所撰,此书于3世纪末,属于上古汉语不成问题。《晋书》修于唐初,房玄龄等编撰此书,主要依据南朝臧荣绪(416-488)著的《晋书》,不论哪一种《晋书》都算不得上古汉语。不过通览《文通》,仅发现引自《晋书》的一个例句,这个单例可以不论。
至于韩愈之文,则另当别论。韩愈虽然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倡导者,自己也身体力行,竭力摹仿先秦时期的文体写作,达到了马建忠所谓“仅知文理”的水平。所以,学习和掌握一种语言,“仅知文理”是远远不够的。身处中唐而言追秦汉,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象一个人在本国学外语,学得再好,也不及外国人说自己的母语地道。马建忠自己也观察到,韩愈象其他同代人一样,“者”字的使用不符合上古汉语的规范(见361页)。马建忠还说:“助字之妙,惟古人能用之,周秦以下无继之者。”(381页)既然周秦以下的人不算古人,那么周秦以下的文词,特别是韩愈之文,就不能算古文词。其实韩愈本人并没有把写出与先秦古文一模一样的文章作为自己的目标。摈弃骈体,取法古文,这是他的基本原则;写作时,他却要求自己作到“惟陈言之务去”(韩愈1980:112),就是说,不因袭别人,要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取法于古文而以不因袭古人,结果就写一种“新体的古文”(朱自清1980:129)。马建忠把这种新体古文或仿古文与真正的古文摆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选材方面的问题不止于此。《文通》“例言”所列著作共17种,而《文通》正文实际引用的文本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现将这些文本按其大致年代顺序排列如下,引证不到10次的文本,后面括号里附有其在《文通》里的页码。
1《周易》的《经》和《系辞》之外的各《传》;
2《尚书》;
3《诗经》;
4《春秋》(296页);
5《老子》(71,199,204页);
6《周礼》(35,36,38,80,201,203,204,206,239页);
7《礼记》(《檀弓》、《大学》、《中庸》之外的各篇);
8《晏子春秋》(141页);
9《墨子》(194,239,357,358,364,374页);
10《孝经》(199页);
11《庄子》(372页);
12《楚辞》(44,273,322,357,358页);
13《吕氏春秋》;
14《韩非子》(313,368页);
15《尔雅》(200,204,205页);
16《大戴记》(239,266,374,378,382页);
17《山海经》(358页);
18《诗序》(37页);
19贾谊,《过秦论》(196页),《淮难篇》(400页);
20刘安等,《淮南子》(35页);
21刘向,《说苑》(383页);
22扬雄,《解嘲》(35页);
23张揖,《博雅》(37页);
24《孔子家语》(204页);
25曹丕,《与吴质书》(236页);
26束皙,《补亡诗》(35页);
27《列子》(156,262,268,358页);
28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236页);
29范宁,《谷梁序》(236页);
30郭璞,《尔雅·郭叙》(80,277页);
31郦道元,《水经注》(237,279页);
32刘义庆,《世说新语》(199页);
33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393页);
34魏收,《魏书》(268页);
35颜之推,《颜氏家训》(81页);
36魏徵,《隋书》(37页);
37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98页);
38欧阳玄等,《宋史》(36页);
39张自烈,《正字通》(199页)。
以上统计难免有遗漏,却足以证明,1)马建忠并没有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惟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文通》中不少例子取自《诗经》和《楚辞》;2)《文通》引用了《易经》、《尚书》(其中一部分)之类早于春秋时期的典籍;3)从班固到韩愈之间并不是一片空白(有23-35诸条);4)“所取为凭证者”也并非“至韩愈氏而止”,晚于韩愈的例子共有4条(36-39)。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所说的“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司马迁1959:3300),那么从演《周易》的周文王到明末编《正字通》的张自烈,上下有差不多2700年的时间。不可想象哪一种语言的共时状态能有如此长的跨度。好在这些出格的例句在例句总数中占的比例很小,不足以改变《文通》的根本性质。我们只能批评马建忠在选择例句时没有严守自己规定的范围,或者说,没有严格遵守共时的原则。
另外,《文通》的例句虽然有的大致按照先春秋,后秦汉,再韩愈之文的顺序排列,相当数量的例句都是一锅煮,不分时间顺序,不讲历史原则。这也是马建忠历时观念不很明确的表现。
马建忠之所以缺乏明确的共时和历时的观念,究其思想根源,还是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认为“古选造字,点画音韵,千变万化,其赋以形而命以声音,原无不变之理,而所形其形而声其声,以神其形声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9页)写《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这样的普遍语法,似乎有理由从泛时的观点来看问题,因为“语言学像下棋一样,有一些比任何事件都更长寿的规则。但这些都是不依赖于具体事实而独立存在的普遍原则。一谈到特定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就没有泛时观点了。”(Saussure 1972:135)《文通》是一部研究“古文词”这一具体语言事实的特定语法,在例句的选择和排列上却既没有严守共时的原则,又没有遵循历史原则,采取了一种近似泛时的观点。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相当成熟的时代,马建忠采取了这样一种观点和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四
马建忠本人在《文通》的例言(1983:15)里直言不讳地说,“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文通》模仿了西洋语法,这点语言学界向无异议。然而许国璋(1991:83-89)通过比较《文通》和Harkness(1883)所编《拉丁文法》对名词、代词和动词的不同定义,又对《文通》和《语法》在作者宗旨和对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状词的定义这六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是:
《文通》之成书,不像是模仿学校《拉丁文法》,也不像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之结果。
凭“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和个人的哲学自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不是不可能写出一部汉语语法。可是既然马建忠自己承认《文通》模仿了西洋语法,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否认这一点。问题不是《文通》是否模仿了西洋语法,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模仿了西洋语法,模仿得好还是不好。王海棻(1991:189-199)的看法是,《文通》在词的分类和归类、次的设立和分析、句子成分的处理以及句子的分析这四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模仿西方语法的痕迹”。她紧接着又说:
但这些模仿之处只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文通》全书并不占主导地位,甚至也不占据重要地位。《文通》主导的方面是,它的作者对古汉语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全方位考察,从语言材料的实际考察中,全面揭示了古汉语的特点及其语法规律,创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颇为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
这样一个“相当完备、颇为精深”的语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即马建忠所谓“大纲”)究竟是哪里来的,是马建忠自己白手起家发明创造的,还是他从西洋语法那里借鉴的?就语法体系而言,《普遍唯理语法》没有什么创见,它注重的是各种不同语言的共性,因此其体系在西洋语法中较具代表性。下面我们把《语法》的体系和《文通》的体系加以对照,有对应关系的语法范畴并列,缺乏对应关系的范畴单列,看看二者同在何处,异在何处。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对应只是大致而言,不是完全对应,因为马建忠在借用西洋语法的范围时,往往扩大或缩小其含义,以适应汉语分析的需要。
表1 《波尔-洛瓦雅尔语法》和《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
《语法》《文通》
Nom(名词,25页)名字(20页)
Substantif(本体名词,25页) 公名(33页)
群名(34页)
Adjectif(属性名词,25页)通名(34页)
Propre(专有名词,28页) 本名(33页)
Général/Commun(普通名词,28,58页) 公名(33页)
Article(冠词,39页)
Pronom(代词,43页) 代字(20,41页)
Antécédent(先行词语,49页) 前词(41页)
指名代字(43页)
指所语者(43页)
Première personne(第一人称,44页)发语者(43页)
Seconde personne(第二人称,44页) 与语者(43页)
Troisième personne(第三人称,44页)
所为语者(43页)
指前文者(43页)
Réciproque(反身代词,44页)
重指代字(55页)
Démonstratif(指示代词,44页) 指示代字(78页)
特指(78,80页)
逐指(78页)
约指(78,83页)
互指(78,87页)
Possessif(领属代词,48页) 代字用作偏次(43页)
Relatif(关系代词,48页)
接读代字(58页)
Interrogatif(疑问代词,102页) 询问代字(71页)
Préposition(前置词,62页)介字(22,246页)
Adverbe(副词,65页)
状字(21,227页)
Adjectif(形容词,26,82页) 静字(21,111页)
象静(111页)
滋静(111页)
平比(135页)
差比(138页)
极比(140页)
Verbe(谓词,66页) 动字(21,144页)
Temp(时,75页)
Mode(式,语气,77页)
Actif(主动,82页) 施动(144,160页)
Passif(被动,82页)受动(160页)
Neutre(中性,82页)内动(25,166页)
Transitif(及物,84页) 外动(25,144页)
Intransitif(不及物,101页)内动(25,166页)
Impersonnel(无人称,86页) 无属(189页)
Gérondif(主动动名词,90页)
Supin(被动动名词,90页)
同动(177页)
坐动(208页)
Infinitif(不定式,80页)
散动(208页)
Participe(分词,89页) 读,散动(208页)
Auxiliaire(助谓词,92页) 助动(177页)
Interjection(叹词,102页)
叹字(23页)
Conjonction(连词,102页)连字(22页)
提起(277页)
承接(281页)
转捩(311页)
推拓(316页)
助字(23,323页)
传信(323页)
传疑(323页)
合助(377页)
Nombre(数,29页)
Genre(性,30页)
Cas(格,33页)次(24,27页)
Nominatif(主格,33页)主次(27页)
Vocatif(呼格,34页) 主次(89页)
Accusatif(客格,37页) 宾次,止词,司词(25,97页)
Génetif(生格,35页) 偏次(90页)
正次(90页)
Datif(与格,36页) 转词(145页)
Ablative(夺格,37页) 转词(166页)
Apposition(同位,36页)同次,加词(102,106页)
前次(102页)
Proposition(命题,23页) 句,读(24,28,385页)
Sujet(主项,23页) 起词(24,385页)
Attribut(谓项,24页)语词,表词(24,26,385页)
Liaison(连项,24页) 决辞/决词/断辞/断词(26,129页)
Objet(客体,83页) 止词,司词(25,28页)
从表1可以看出,《语法》和《文通》在体系上大同小异,后者在某些方面(如指示代字、静字、连字的再分类)比前者更细密。《语法》里有一些《文通》里没有的语法范畴,如数、性、时等,古汉语里至今也找不出与之对应的范畴;《文通》里也有一些《语法》里没有的小范畴,如“群名”(集体名词)、“滋静”(数词)、“比”等,这些在19世纪下半叶通行的各种西洋语法书里很容易找到;“助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句末语气词,其作用与《语法》中谓词的Mood(式,语气)相当,是马建忠求出的“华文所独”的唯一词类,王力(1981:177)将这一发现称之为“很大的创造”。
《文通》模仿的也许不是一本特定的语法,但它确系“仿葛郎玛而作”,否则无法解释二者何以在体系上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到目前为止,论者说到“模仿”,一般持鄙夷态度,以为不如创新,无足称道。不过,站在马建忠的立场上看问题,既然“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在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同上),把外国的葛郎玛拿来仿效一下,为我所用,有何不可?马建忠在建立古汉语语法体系的过程中有取舍、有创造性地仿效西洋语法,做到了“基本符合古汉语实际”(王海棻1988:12),结果是成功的。
马建忠虽然在语言哲学、语法的编写方针和体系上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他的《文通》却不是《语法》的翻版。在语法研究的方法上,在对某些基本的语法范畴和结构的解释上,《文通》和《语法》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语法》贯彻始终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理性的演绎法。《语法》从分析人的思维方式出发,探索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是怎样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表现出来的。按照《语法》的观点,人的思维过程有三步。首先是形成概念,然后是作出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再进行推理。人们发明出来用以指称各种概念的声符就是词,人们对事物进行的判断表达出来则称为命题。每个命题都包含主谓这两个项,主项是判断的对象,谓项是对该对象的判断。除了主谓这两项外,命题还包括连系主项和谓项的连项。人的思维既然可以分解为思维对象和思维方式,词也可以分成与此相应的两大类。《语法》把其认为表示思维对象的名词(包括本体名词和属性名词)、冠词、代词、分词、前置词、副词等归为一大类;把表示思维方式的谓词、连词和叹词归为另一大类(见Arnauld et Lancelot 1670:24页)。
马建忠没有走《语法》的道路,没有从分析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归纳上古汉语中与思维方式相适应的各种语言形式,对这些语言形式的存在给予理性主义的解释。首先,他虽然求出了与拉丁语的八大词类相似的上古汉语的名、代、动、静、状、介、连、叹诸类字和“华文所独”的助字,可是并没有像《语法》的作者那样,把这些字类归入表示思维对象的字和表示思维方式的字这两大类。他的作法是,按照有无事理可解这一语义标准,把他求出的九类字归入“有事理可解”的实字和“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的虚字这两大类。名、代、动、静、状诸类字被视为有事理可解,归入实字;剩下的介、连、助、叹这4类字被视为无事理可解,归入虚字。字的虚实之分是中国古代学者对普遍语法理论的重要贡献。[7]马建忠继承和发展了古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它是“字法之大宗”(20页),然而这一“字法之大宗”与《语法》归纳词类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
在原则上,马建忠对于语言本质的认识与《语法》的作者没有什么不同。《语法》(7页)说:“言语,就是用特地发明的符号表达自己的思想。”马建忠(13页)也认为言语就是人们“以口舌点画以达其心中之意”。可是一到对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马建忠就把理性主义的原则扔到一边。在对语言符号的看法上,《文通》和《语法》就有明显和重要的不同之处。
《语法》(28页)认为,词是表示各种概念的声音符号,而不是客观事物的名称。这一观点在其给专有名词和普遍名词下的定义里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有两种概念。首先,有一些概念代表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如每个人对其父母、朋友、马、狗、自己所形成的概念。
另一些概念代表对我们来说是好几样相似的事物,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几样事物都同等适合,例如我们对一般的人或一般的马所形成的概念。
人们需要不同的名称来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于是就产生了专有名词和普遍名词。
马建忠没有这样给名词下定义。他继承了先秦学者“称器有名”,“名者,名形者也”(尹文子,转引自洪诚1982:28)的形名观,把名字看成是客观事物的名称:
名字所以名一切事物者,省曰名。
名字共分两宗,一以名同类之人物,曰公名。
〔……〕
一以名某人某物者,曰本名。(33页)
马建忠大概认为,思维(心中之意)和语言符号的关系不言而喻,所以他跳过概念这一环,把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直接挂钩。《文通》的定义符合一般人对语言的认识,简单明了,易被人接受,也是传统学校语法对名词的定义,但这种定义却没有《语法》的定义那样严谨、科学。
《语法》和《文通》对谓词/动字的不同处理,更反映出二者在语法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在《语法》里,断定被认为是“我们思维的主要形式”(66页),谓词的定义是:“主要用以表示断定的词。”(同上)。Est(是)是表示单纯断定的谓词,其他谓词除了表示断定之外,还同时表示某种属性。例如Pierre vit(皮埃尔活着)就可以理解为Pierreest vivant(皮埃尔是活着)。这样,vivit这个词实际上即表示断定又表示“活着”这一属性。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把命题的主项也并进谓词里,这样一来,单独一个词因表达了某种断定,也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如拉丁语的vivo(我活着)。谓词还可以通过形态变化同时表示与断定相关的时间关系,由此而产生了谓词的各种时态。可见《语法》对谓词的定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任何谓词,不论其形态怎样因人称、数和时态而变化,其基本功能总是表示断定。
马建忠在《文通》里也说到决断,可是他所说的决断,其内涵大大小于《语法》作者所说的判断。马建忠(24页)认为:“句者,所以达心中之意。而意有两端焉:一则所意之事物也,夫事物不能虚意也,一则事物之情或动或静也。”表面上看,马建忠所说的“意”和《语法》里所说的判断很相似,可是马建忠没有说“事物之情或动或静”就是人们对所意之事物的决断。他从语义出发,把事物的动和静截然分开,说:“夫事物之可为语者,不外动静两境,故动境语以动字,静境语以静字”(127页)。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有些字,如“有”、“无”、“似”、“在”,“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177页),却被归入动字,称为“同动”;还有一些字,象“是”、“非”、“为”、“即”、“乃”,即不表示事物的动境,又不表示事物的静境,只是“参于起表两词之间”起一种连系作用,“以表决断口气”(26页),那么应该把它们划到哪一类字里呢?既然动字和静字里都没有它们的位置,马建忠只好为它们单立一类,含糊地称之为“决辞”(同上),又称“决词”、“断辞”、“断词”(129页)。在《文通》里,“辞”不是一个语法单位,而“决词”或“断词”的“词”显然又与“起词”、“语词”、“表词”的“词”不在一个层次上。读完《马氏文通》,人们始终搞不清楚“是”、“非”、“为”、“即”、“乃”这类词在马氏语法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没有把决断作为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来对待,马建忠也就不可能象《语法》的作者那样提纲挈领地把握verb的本质,只好象传统学校语法那样将之定义为表示动作的字,并不顾其词源意义,将之译为“动字”。
作为一部唯理语法,《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致力于发掘各种语言现象背后的道理,对这些现象给于理性主义的解释。《马氏文通》不是一部唯理语法,因为它没有对所分析的语言现象进行理性主义的解释。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在《语法》里,第9章专论关系代词。《语法》认为关系代词有两个特点:1)它总是与另一个名词或代词有关,这个名词或代词称为先行词;2)关系代词引导的命题可以成为另一个命题的主项或谓项的一部分,这另一个命题可以称为主命题。在分析Dieu,qui est invisible,est lecréateur du monde,qui est visible(见不到的上帝是见得到的世界的创造者)这句话时,《语法》认为该句实际上表达了三个判断:
(1)Dieu est invisible(上帝是见不到的);
(2)Il a créé le monde(他创造了世界);
(3)Le monde est visible(世界是见得到的)。
在这三个命题中,第二个命题是原先命题的主要成分,第一和第三个命题只在这三个命题中,通过关系代词分别进入主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后,这两项各自成为复合项(见50页)。复合项表达的思想要比简单项更丰富。
马建忠也求出了上古汉语的三个接读代字:“其”、“所”和“者”。关于接代字的作用,他(58页)说:“接读代字,顶接前文,自成一读也。”这一点和《语法》指出的关系代词的第一个特点是一致的。“自成一读”是什么意思呢?马建忠(28页)解释说:“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在此之前,他(25页)在给句下定义时说:“盖意非两端不明,而句非两语不成。”现在有了起、语两词,辞意为何不全,马建忠没有解释;文章里为什么要有接读代字“自成一读”,马建忠也没有解释,全靠读者自己通过大量例句揣摩其中的道理。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看到,《文通》的语法是参照西文现成的语法体系建立起来的,马建忠在《文通》里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和归纳法,比较出上古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一些差别,归纳出他认为是“华文所独”的助字,但这两种方法不是他研究上古汉语的主要方法;他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但没有严格地遵守历时或共时的原则;他虽然接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自信“人苟能玩索〔《文通》〕而有得焉,不独读中书者可以引通西文,即读西书者亦易于引通中文,而中西行文之道,不难豁然贯通矣”(245页),他的《文通》却不是一部《波尔-洛瓦雅尔语法》式的普遍唯理语法。
一句话,《马氏文通》是一部以普遍唯理语法作为理论基础,摹仿西洋语法体系而充分注意汉语特点,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汉语语法。
Arnauld et Lancelot,1670,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Nouvelle édition(republication).Paris:Repubications Paulet.
Arnauld,Antoine and Lancelot,Claude,1975.General and RationalGrammar:The Port-Royal Grammar,ed.and trans.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acques Rieux and Bernard E.Rollin,and witha Preface by Arthur C.Danto and a critical essay by NormanKretzmann.The Hague:Mouton.
Harkness,Albert,1883,A Latin Grammar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New York.
Harnois,Guy,1929,Les théories du langage en France de 1660-1821,Paris:Société d'E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Rieux,Jacques and Bernard E Rollin,1975."Translators'Introduction",in Arnauld and Lancelot 1975,21-31.
Saussure,Ferdinand de,1972,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ublié par Charles Bally et Albert Sechehaye,aveclacollaboration de Albert Riedlinger,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e par Tullio de Mauro.Paris:Payot.
Tell,J.1874.Les grammairiens fran cais 1520-1874.Paris(Reprinted in Geneva:Slatkine Reprints,1967).
注释:
[1]以下简称《文通》,引文据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以下简称《语法》,引文据1670年新版(1969年Republications Paulct复制本)。
[3]也有人认为马建忠是1875年去法国的(见任继愈1958,赖汉纲1981:138-143)。
[4]许国璋(1991:91)根据马建忠本人所著《适可斋记言》里的记载推断,马建忠是被李鸿章派到法国修习外交业务的,“似乎不曾在法国正式上大学读书”。
[5]译文参考了高名凯(1980)中译本和Harris(1983)英译本。
[6]王力没有说明往前上溯到何时,大概从有甲骨文时起。
[7]“实字”和“虚字”的区分始于南宋的张炎(见林玉山1983:28),起初用以从修辞的角度分析诗词,元代卢以纬的《助语辞》是论述“虚字用法的最早著作”(胡裕树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