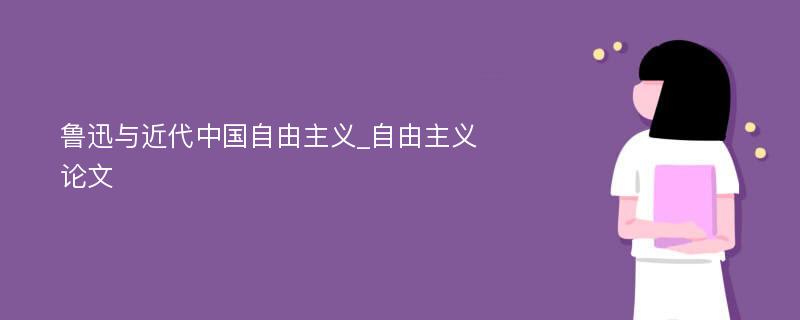
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鲁迅的“个人主义”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虽没有具体提到自由主义对他的影响,但在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传播为主导的近现代中国,鲁迅不可能不受到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就像郜元宝所说: “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自命新派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罢。鲁迅当然也不例外。”① 鲁迅立人思想的来源是施蒂纳、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这些反西方近代文化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施蒂纳、尼采等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反思,主要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在个性主义的立场上仍然承接的是西方的近代自由主义文化。鲁迅对自由的理解是施蒂纳、尼采式的绝对自由主义,法律甚至也成为一种束缚,这是比自由主义理论中规定的自由更见其自由的一种“自由主义”,而且这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对鲁迅一生追求个性自由反对一切专制束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施蒂纳、尼采在反西方的现代自由文明时,恰恰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孕育了施蒂纳、尼采的绝对个人主义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土壤是产生施蒂纳、尼采的绝对个人主义的原因。同时,施蒂纳、尼采的个人主义又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的极致。胡适曾说过: “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② 不同的阶段,个人主义于鲁迅又有不同的意义。五四之前和五四期间,鲁迅之个人主义是: “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③ 并且此时期鲁迅的个人主义是与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立人”思想的精神来源。五四落潮之后,孤独彷徨特别是在目睹了很多血的事实以及被疏离、误解之后,鲁迅的个人主义概念又明显倾向于“为我”的意思,是指的一种庸俗的生活上的个人主义。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④ 在这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对立的。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但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还很多,所以终于是言行不一致。”⑤ 鲁迅自称倾向个人主义只不过是愤激之语,这种庸俗的生活上的个人主义在他身上找不到影子,更别说他一向视之为个人独立自由意志的个人主义精神。这里的个人主义与鲁迅当初的个人主义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一个是哲学上的,一个是生活上的。鲁迅当初所说的“个人主义”是以自我为本位,不是指的自由主义体制中的人,只是一个纯粹的人,还没找到一种体制容纳它,也即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在鲁迅来说,正是因为他把个人主义庸俗化了,使他晚年看起来似乎已是放弃了个人主义。其实早年鲁迅信奉的个人主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反而成为一种精神实质,成为他加入左联追求将来的绝对的自由的一个因素。
本文不是想把鲁迅列入自由主义者之列,这无疑与鲁迅的历史现实不符。但鲁迅显然又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不同,不论是其文学的观点还是革命的观点。刘川鄂称之为“鲁迅的超越”。他认为: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频繁的文学论争中,因其强烈的现实感和厚重的理论分量,明显地具有一种‘超越性’。不仅超越了他的对手,而且也超出了他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这种‘超越性’特征源于鲁迅的理性精神、独立意识和艺术本体观。这三者与自由主义肯定的基本原则并不相悖。但从个体自觉和思想资源而言,从学理的意义上,鲁迅从来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⑥ 刘川鄂这里的个体自觉和思想资源是相对于中国欧美自由主义者所接受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文化而言的。如果不考虑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些具体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条例,只是从文化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鲁迅的个人主义的渊源,其无疑是来自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文化孕育的19世纪末“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⑦ 的神思新宗一脉。鲁迅认为其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 “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⑧,也即是“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想。可知,鲁迅所受的个人主义影响是来自于西方19世纪末的反自由主义文化的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以反思自由主义文化的理性特别是现代技术、工具文明对人的压抑异化开始,极力追求人的生命意志,力图深入人的心灵、思维空间探索人的生命和存在。也可以这么理解,施蒂纳、尼采等反的是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政治上的,不是文化上的。他们对于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承继与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二 “作为文化自由主义者的鲁迅”
一般把鲁迅列入非自由主义者的原因是: “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制度诉求。”⑨ 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不是自由主义者。这些都是基于没有把自由主义内含的概念分开的结果。自由主义一般主要分为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等。丹尼尔·贝尔认为他自己:在经济领域里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领域里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⑩ 他认为这三者并不是分裂的,而是有其内在一致性,或者说,这种“一分为三”恰是现代社会被分裂为三大领域的对应。按照贝尔对自己立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三分法,也可以给我们研究鲁迅一种启示。一般否定鲁迅为自由主义者是基于鲁迅对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不感兴趣,在经济领域更倾向于平等而不是自由。但如果我们从文化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鲁迅,无疑鲁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文化自由主义者,而且他比胡适、傅斯年等在政府、学院任职的口口声声都在声称争取自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具有不依附于权力、体制和金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应该说,从文化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鲁迅的自由思想是站得住脚的。一般认为鲁迅之不是自由主义者,除了他对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外,还在于他表明的对自由主义不感兴趣的态度。在早期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激烈抨击“以众虐独”的“社会民主”,认为对于舍个人自由不谈的群体自由,要么形成“以骄矜不逊者为全局之主人”的现代独裁,要么形成群众专制。鲁迅反对的并不是民主政体这种制度,而是它在中国实行能否真正带来个人自由的问题。对于一种新的体制和道德标准,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社会群众基础,只会带来民主自由制度在异地的变形,最终导致更严重的专制,这也是鲁迅被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11) 者的原因。鲁迅也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和无所属,他曾说: “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12) 1928年,鲁迅在翻译日本学者鹤见佑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的“题记”中明白地说:“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13) 鲁迅这段话意思很明确,因为“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以才不感兴趣的,而对于其中国民性的观察却是鲁迅所关注的。说明鲁迅的兴趣是思想,而他一生也确是从未参与过政治。“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今译歌德)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14) 同时,鲁迅也表示过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认同,这也就是在通向自由的途中,鲁迅是否赞成暴力,是否允许暂时的专政的问题。显然,鲁迅出现了两难,一方面,他希望能有言论自由,能用不流血换来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他对专制压抑是时时反抗着的,决不允许半点自己的自由被压抑。“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15) 鲁迅把平等的要求放在自由的前面,其实是为了追求一种终极的自由,他实际上从未真正放弃过自由,都可以看做是鲁迅早期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那么,如果,这个专制的时间较长,鲁迅能忍受多久?是一劳永逸地去获得最大的自由,况且还不知道这种自由的黄金世界到底能允诺多大的自由?还是在永远以人为本、为最高利益的自由民主制度中一边享受个人的自由,一边创造大众的幸福条件?鲁迅在这里所希望的与他所感受到的出现了冲突,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终极自由的虚幻性和平等与自由的不可两存。
鲁迅说过: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16) 鲁迅还是承认“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的,从来没听他说中国人也有文明人的。而鲁迅一直认为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是吃人文化,不是“真的人”的文化。鲁迅的反自由主义不是反自由主义的自由精神,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竞争不甚感兴趣。
1999年,周策纵为国内举办的胡适思想研讨会作诗两首:
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
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17)
周策纵说:“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18) 从周策纵的诗歌和对胡适话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是从鲁迅的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不屈服任何外来权威来定义鲁迅是“我辈人”的。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大多是从思想自由来论的。张东荪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就设想了一条希望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之外的文化自由主义之路,也就是保住那点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拿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著名人物胡适来说,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政治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为了人民的“思想自由”的,特殊时代有特殊的不完善的自由民主政治,但是却不能让人民失去基本的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在这里,自由和特殊时代的政治必会出现矛盾,就像鲁迅所认为的平等不能和较高级的自由并存是一样的。这也是鲁迅认为那些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自由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其实一直都在坚持一种施蒂纳、尼采式的绝对自由,只是早期的绝对自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晚期的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大多数时候成为一种理想,为了坚持这种绝对自由的理想,鲁迅把平等似乎放在了第一位。王富仁曾经指出: “中国30年代的英美派知识分子则是不结盟式的个人主义,他们反对群众性的联合行动,同时又不能不在国家的(不论这种国家是什么形式的国家)统一法制形式下约束自己的言行。这种个人主义使他们变得极端无力,不但无法把他们的学理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实际力量,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相互救助的力量。”(19) 从这也可看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书生论政性质,一旦当压迫袭来,他们是无还手之力的。所以,鲁迅认为他们的自由也即是一种伪自由,不是“帮闲”就是“帮凶”,不管是帮闲还是帮凶,都是对专制体制和权势的屈服。
鲁迅在上海曾参加过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会,从未参加过政治组织。曹聚仁认为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或是戏剧工作者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等, “他们对于鲁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路线,并非要鲁迅来领导。我们且看鲁迅和徐懋庸的往来信件,就可以明白鲁迅与中共之间也不一定十分协调。”(20)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他自己并不愿处于领导地位,同时‘左联’也不让他去领导,直到他死后才奉他为神明,好似他是那时期的领导者。”(21)“不过,那时期的政治环境,在国共政治斗争尖锐化的当中,迫着他接近了被压迫的一面,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这也是他的倔强个性使然)。依我的看法,他还是孤军作战的,并不受中共的领导。”(22) 鲁迅曾指责周扬等人为“英雄”、 “元帅”、 “奴隶总管”,这些人“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23)。他认为那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前进作家”,“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是一批“拉大旗,作虎皮”的假共产主义者。鲁迅和周扬等人的冲突,实质上就是专制思想与个人主义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鲁迅是困惑的,但他又否认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 “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24) 鲁迅对于真正的知识阶级的追求表现出比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加彻底的对于自由独立的追求。当一个知识分子的活动仅仅限制在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他是可以保持自己个体精神的相对独立与自由的,但一旦进入社会运动,他的独立与自由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必然要和某种潜在的权力发生关系。自由脱离权力的管制,这种绝对的自由是不现实的,鲁迅对绝对自由的追求毋宁说是一种堂·吉诃德的幻想。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特殊的现实条件下鼓吹英美自由主义的最终终结,同样也可看作文化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失败。
虽然鲁迅曾经表示出对自由主义的不感兴趣,但鲁迅对于自由思想、独立品格的保有使他与左联发生矛盾成为必然。鲁迅曾说:“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致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25) 在给曹聚仁的信里,鲁迅写道:“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26) 李霁野写过一篇《忆鲁迅先生》,其中提到他曾经亲耳听到鲁迅与F君(即冯雪峰)的一次谈话: “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连摇头摆手地说: “那弗会,那弗会!”(27) 可见,鲁迅是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专制的一面的,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自由主义于中国苦难、救亡现实的不合时宜,他只能抱着一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来参加左联,并且付诸一定的文字行动。
三 鲁迅的虚妄和启蒙主义
一般认为是鲁迅的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决定了他的启蒙意识,其实,鲁迅的个人主义才是他启蒙的重要思想资源。本节主要讨论两个问题:(1)鲁迅的虚妄被启蒙主义遮蔽; (2)鲁迅的启蒙和虚妄与其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关系。
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其所受到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西方的反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派思想的影响。鲁迅的启蒙主义包括立人思想和“为人生的文学”的主张。同时启蒙思想中又蕴涵着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交织。“立人”思想来自于其个性主义, “为人生的文学”更多倾向于其人道主义方面。对虚幻的克服又是通过个人主义的意志和人道主义的博爱同情来体现的。作为革命家的鲁迅负有启蒙的使命,而虚无是对应于鲁迅的哲学思想,是哲学意义上的。启蒙是希望,人生终极是虚幻,只有用现世的斗争才能体现生命的本质。和黑暗捣乱,可看出鲁迅的虚无思想,而最终鲁迅以启蒙跨越了他的虚幻。同时,虚妄之于希望的实在又使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者。
李长之认为鲁迅“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28)。对于一个探索者、启蒙者来说,面对中国复杂的历史现实和沉重的传统文化背景,要为中国的青年指出一条路谈何容易。启蒙者自己的迷惘也是情有可原的,彷徨、迷惘不是虚无主义的表现,真正的虚无是既无迷惘、彷徨,也无探求。竹内好也认同李长之的思想,他认为: “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称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底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29)我宁愿把竹内好所说的鲁迅的“无”理解成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无”,一种混沌的思想和清醒的文学者的自觉。周作人曾论《鲁迅评传》“云其(按:鲁迅)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30)。虚无对于鲁迅来说是哲学意义上的,而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中,鲁迅崇尚的是反抗的启蒙主义的哲学,启蒙最终遮蔽了鲁迅的虚无主义;在人生实践上,鲁迅是积极的、反抗的,对未来抱着希望的。应该说,启蒙主义是鲁迅的主要人生意义。周作人曾说: “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31) 虽然鲁迅也曾经说过: “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32),可是他还是“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33)。可见鲁迅所说的虚无是一种哲学终极意义上的虚无,它在实践上表现为列宁所称的否定旧世界的“革命的虚无主义”。
关于诸多学者称鲁迅为虚无主义者,我一直都不能理解。如果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的虚无主义也应该是一种直面现实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如果鲁迅是虚无主义者,那何以解释鲁迅一生所遵从的启蒙主义?鲁迅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否定、抗争的自由精神。鲁迅曾希望自己的文字“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34)。不断地否定自己,去催促新的生命。这就是鲁迅的生存的进化论哲学。如果没有对未来的希望,他不会“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5)。“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36) 用对艰难的心理准备和长久承担来抵消生命的虚幻,用真理的寻求和对现实的斗争来抵消生命的虚幻,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精神。捣乱、消磨,其实并不是虚无的表现,更应该看做是一种进取的精神,体现生命意志的酒神精神。 “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37) 可见,鲁迅的虚妄对于他只不过是一种关于生命和人生的思考, “向绝望抗争”也是每一个诗人或哲人需要考虑的哲学问题。最重要的是鲁迅的行动,他不仅仅是“麻痹”或“忘却”,或者如林语堂所认同的“蛰伏”或“装死”,而是为了更有效的抗争。鲁迅的哲学是一种抗争的哲学。在虚妄和希望的斗争中,鲁迅拼命用斗争来消除生命的虚幻和梦幻,体现着表现生命、表现自我、凸显自我的精神生命意志。他是用生命意志和生命强力与虚幻斗,用启蒙的精神和肩住黑暗的闸门的勇气与虚幻斗。
生命的终点是坟是谁都知道的,如果像老庄一样躲起来远离尘嚣,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但鲁迅还是在寻求一条怎么走完生命的路,而不是把自己冬眠起来或囚居于象牙之塔。欲启蒙却又不敢坚信自己应是鲁迅之所以一直用文学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原因。可是他又不满于《语丝》“时时有疲劳的颜色”,说:“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 “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38) 曹聚仁认为鲁迅在《语丝》时“是一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39),并认为“《语丝》社那一群人有这么一种趋向”(40)。 “因为深深知道改变现实的不易,知晓除了依靠现有的力量对它加以培育之外别无他途,所以鲁迅思想中包含了超越幻想及作为其反面的绝望的因素,这和卑俗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完全不同。”(41)
鲁迅的启蒙主义对虚妄的克服,也即人道主义对“自我”的压缩。这也是鲁迅后期转向杂文的原因。通过看鲁迅的作品,我更加确信鲁迅作品不仅仅是“为人生”,准确地说是“为启蒙”。鲁迅早期从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易卜生那里所受的影响,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接受和排斥的双重性,是鲁迅没有走上完全相信自由主义的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影响对于鲁迅的创作来说就是坚信中的怀疑和希望中的绝望。鲁迅的启蒙是拿什么来启蒙的,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鲁迅在《新青年》时期显然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立场上倡西方民主科学、个人解放的。
虚无主义的“虚无”源于拉丁文“Nihil,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雅科比(1743—1819)首先使用,因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著名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形象而得到广泛传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虚无主义者成为了那些反叛传统和社会秩序、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横和虚伪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列宁曾把合理否定旧世界称为“革命的虚无主义”,把盲目崇尚恐怖和破坏活动称为“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鲁迅最早接触虚无主义大约是在1907年。当时他在日本读到了克鲁泡特金撰写的《一个革命家的自序传》,就认识到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跟当时采用恐怖手段的“虚无党”的区别。(42) 该时期,周作人曾经以“独应”为笔名在《天义报》发表过《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中国人之爱国》等文,据悉这些文章是鲁迅鼓励他写的,而且有的经过鲁迅的修改,也有可能“独应”是在日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共同使用过的笔名。(43) 在以“独应”为笔名发表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一文中,周氏兄弟强调“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综,为哲学之一支,去伪振蔽,其效至溥”,对虚无主义的“不服权威”, “行贵率真,最嫉文明习惯之虚伪”(44) 最为心服。可以看出周氏兄弟对虚无主义的接受是立基于“诚”的“不服权威”的反抗精神上的,是对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的唯物主义、俄罗斯启蒙运动的一种激进精神的继承。在1926年7月2日的《马上支日记》中,鲁迅又重申了俄国的“虚无党”和中国的“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到鲁迅对俄国“有特操”的“虚无党”的崇仰指的是“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45),可以看到俄国虚无主义者对鲁迅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反抗一切权威和传统习俗的自由精神。而鲁迅对虚无主义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却又是警惕甚至是排斥的。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 “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46) 曹聚仁认为鲁迅“只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义感很强烈,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驱战士”(47)。
鲁迅的虚无是继承的俄国虚无主义的否定旧传统思想,结合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启蒙主义又表现出对虚无的终极意义的遮蔽,使鲁迅的虚无主义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反抗旧的文化传统、启发民智的启蒙思想。竹内好认为鲁迅的创作来自于“无”。这个“无”是很不清晰的,即使无幻灯片事件,不考虑鲁迅的主观意识,专从鲁迅本身的创作来看,我们仍可看出鲁迅创作强烈的“为人生”的品质和现实性。何况鲁迅在1930年代仍声称恋恋不舍于十几年前的启蒙主义。竹内好说: “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48) 鲁迅不是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支撑他的文学,但鲁迅是以文化启蒙者的角色来统领文学的。是鲁迅作品的终极意义构成鲁迅小说的文学性,但是,没有启蒙主义这个主体思想,鲁迅的文学就相当于没米没菜的晚餐。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孤独者》《在酒楼上》《祝福》等都可看出作者的笔直接伸向的反封建宗法制度、反传统礼教的启蒙主题,同时也可看到鲁迅在虚无、疑惑意义上给文本带来的文学性及其个体自由话语性质。鲁迅在《〈竖琴〉前记》中说: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49) 这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众所周知,鲁迅的《狂人日记》的题目与果戈里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同名,果戈里小说中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揭露手法于鲁迅对于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制度的揭露有很大的启示。 “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50) 鲁迅认为文学革命的目的就是立人的启蒙主义。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所不同。西方的启蒙运动主要是反抗神权和封建专制政权对人性的束缚,中国启蒙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把人从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鲁迅在1903年的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中歌颂了民族主义的精神,而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又力倡“排众数而张个人”,这也许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处境。民族和个人成为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和民族富强独立的双重愿望。其时,他还写了《自题小像》诗题赠日本友人,表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志。王富仁认为鲁迅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是从起初的“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回归而来的”(51)。这使得鲁迅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经常处于一种看似矛盾的状态中。同时,我们也可看到这两种主义在鲁迅身上是统一的,就是坚持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的博爱和同情心。
鲁迅的虚无是时时被启蒙的使命覆盖的,所以才有鲁迅《新青年》之前的沉默和五四热潮过后的《彷徨》和《野草》,这两部作品都是写于五四之后的彷徨期,特别是在《野草》中,透露出鲁迅关于爱、死和虚无的思考。鲁迅的启蒙是现实意义上的,而鲁迅的虚无则是哲学意义上的。当现实很匆忙时,鲁迅的虚无就会弃置一旁,当现实没有什么具体事物来充满时,虚无就占据了鲁迅的头脑,使他更注重于从哲学的意义上来思考写作和人生。
四 启蒙文学就是“革命文学”
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理解是它的反抗和先锋精神,而不是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也即是一种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不同于“合群的自大”的“个人的自大”,不是其讥之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文学。(52)“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53) 可看出鲁迅对革命和革命文学的理解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重在反抗的不满意于现状的不断革新的精神。鲁迅曾说《新青年》的提倡“文学革命”“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54),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55) 这段话写于1932年,这可以说是对于革命文学的最好概括,和1920年代末兴起的革命文学重在一套唯物辩证法的写作手法和把文学当做政治的留声机的文学观绝然不同。在之前,鲁迅也曾提倡过需要“革命人”才能写的革命文学,也是重在革命意识,而不是1920年代末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需要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我们一般所称之的革命文学就是这种特定时代把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而鲁迅所说的革命文学是一种更广义的革命文学,它的意义重在它的反抗性和先锋性。
鲁迅对于革命的看法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希望革命,捣毁一切旧的成法;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做流血的牺牲。所以,李长之认为鲁迅“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很厉害”(56),是“诚实无伪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57)。与那些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鲁迅更关注于“下等人”和弱者,后期把平等看得比自由更重要,但如果真正要他放弃内心精神的自由,他丝毫都不会答应。但起码,鲁迅已意识到在中国现代社会,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奢侈的。所以,对于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者无视大多数人温饱尚未解决,一味鼓吹个人自由,鲁迅是极为反感的。虽然鲁迅清醒地说过: “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58) 但是对于徒手的牺牲,他向来是不赞成的。在他自己来说,他也知道:“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59) 做不了盲目遵命的革命者,鲁迅的这种怀疑就是一种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的犹豫,他得自己多疑多虑地来估量这个牺牲的值不值。可是,对于思想上的革命,鲁迅从来都不会问是否太彻底,对于这种不流血的革命,他从来都是反传统最彻底的。鲁迅的倾向革命其实倾向的就是一种反抗的精神。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却又说: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沉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60) 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的矛盾,革命需要流血牺牲,鲁迅渴望有一次真正的革命,但最终,鲁迅不愿意看到流血。如果是他自己能为革命开路,他也会“咬着牙关忍受”。关键是这个革命到底能承诺什么,鲁迅从来都表示出对黄金世界的怀疑:“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61) 对黄金世界的怀疑是鲁迅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
鲁迅的革命意义就是反对现有体制,就是一种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体现。比如鲁迅不同国民党合作和与国民党合作时的批判反抗精神,对革命文学的阐释还是偏于“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62)。鲁迅强调最好是思想解放了的无产者自己来写革命文学, “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63)“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64)
竹内好认为政治与文学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对政治投以白眼,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消却了自己影子的东西。所谓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同一的关系。鲁迅把革命同样当做历史中间物的一环,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革命,不是去流血牺牲,而是为了大多数的自由。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认为: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中。”(65) 鲁迅把文艺家当做是与政治家对立的角色来看待,他们的使命是说出真话,说出真理。在左联时期,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的自由独立的个性使他敏锐地感觉到了革命内部的专制的苗头。从鲁迅与左联的矛盾,可看出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解和期盼与左翼的不同,鲁迅的“革命文学”重在指一种反抗现有体制和传统的启蒙文学,左翼的革命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是提倡革命文学,对于“革命文学”的性质和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理解不同。
注释:
① 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1页。
②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页。
③⑦⑧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9、50页。以下《鲁迅全集》皆出自此版本。
④⑤(12)(32)(33)(37)(38)(46)(59)(61)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249、31、21、249、23、33、21、32、20页。
⑥ 刘川鄂:《鲁迅的超越:在左联与自由主义文学派别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⑨ 邵建:《误读鲁迅(一)》,《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⑩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一九七八年再版序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24页。
(11)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13)(14) 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2、273页。
(15) 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第4卷),第430~431页。
(16)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89页。
(17)(18)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9)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13页。
(20)(21)(22)(39)(40)(47) 参见曹聚仁《鲁迅评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1、128、128、83、83、86页。
(23) 鲁迅:《书信·360515·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9页。
(24)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190页。
(25) 鲁迅:《“醉眼”中的蒙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6页。
(26) 鲁迅:《书信·340430·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7页。
(27) 李霁野:《忆鲁迅先生》,《文季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12月1日。
(28)(56)(57)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154、154页。
(29)(48) [日]竹内好著,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8、57~58页。
(30)(42)(44) 参见陈漱渝《“毋求备于一夫”——读曹著〈鲁迅评传〉》,曹聚仁:《鲁迅评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11、11页。
(31) 周作人著,止庵校对:《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356页。
(34)(36)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286页。
(35)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0页。
(41) [日]丸山升著,王俊文译:《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s年版,第201页。
(43) 参见陈漱渝《再谈〈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见《鲁迅史实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48页。
(45) 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28页。
(49)(50) 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20页。
(51)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52)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53)(65)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9、117页。
(54)(55)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455页。
(58)(62)(6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23、418、418页。
(60) 鲁迅:《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628页。
(63)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0页。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鲁迅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虚无空间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