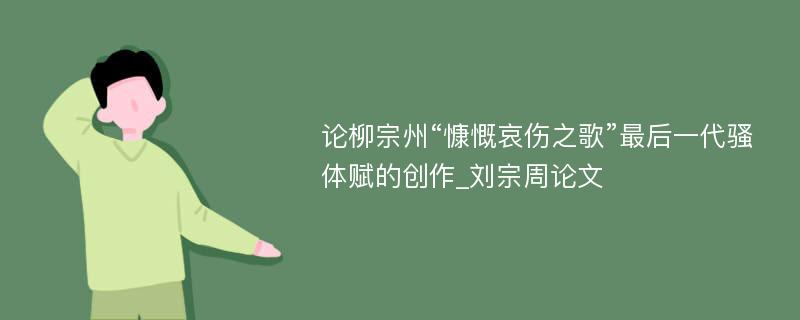
慷慨悲歌 末代木铎——刘宗周骚体赋创作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骚体论文,慷慨悲歌论文,刍议论文,末代论文,刘宗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08)04-0098-05
刘宗周(1578-1645),乃明末著名思想家,又是赫赫有名的黄宗羲的业师,以倡行“慎独”之学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宋明理学之殿军。宗周人格高俊,名德岿然,无论当时还是身后,均获明清两朝最高统治者首肯。宗周在世,明崇祯帝认为“大臣如刘某,清执敢言,廷臣莫及也”[1];死后,清乾隆帝评价“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懔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2]。
正由于刘宗周的贡献更多在于义理,其辞章之学反而湮没不彰,各类文学史著述均不涉及,学界对刘宗周文学的研究尚属空白。实际上,刘宗周的辞章修养是十分丰厚的,即就他的骚体赋创作而言,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笔者以为,至少在明代辞赋史上,刘宗周的骚体赋创作理应占据一席之地,其创作体现出宗周堂堂正正之人格、慷慨愤激之精神。其文直抒胸臆,无意于文而辞自工,在惨无天光的明季之世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刘宗周的文学创作相较于他的理学著述,在分量上当然居于次要地位,但是数量也绝不算少,即使以当今的纯文学观念来看,在二十二卷诗文类著作中,除去奏疏等实用文体,甚至连序、行状、传等亦不计其内,尚有赋一卷、诗两卷的篇幅。且不说丰富的诗体创作,这区区一卷的赋体制作就很值得关注。
刘宗周的赋,全都为骚体赋,共五篇,分别为《淮南赋》、《吊六君子赋》、《知命赋》、《逝哀赋》、《招魂》。
《淮南赋》,是悼念道学同好刘永澄(静之)的,作于万历四十一年。年谱载:“二月,过宝应吊刘静之。去年,先生北上,过淮南访静之。静之病,相与究养心之旨而别。别三月,静之卒。比先生出使闻变,登堂哭之恸。至是再上淮南,重访其里而哭之,操文以祭,复作《淮南赋》以哀之,私谥曰‘贞修’,君子以为称情。”[3]刘永澄也是明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黄宗羲《明儒学案》列其于《东林学案》中,谓其生前“与东林诸君子为性命之交”[4],年仅三十七而卒。年谱(万历四十年条)记载:刘宗周“生平为道交者,惟周宁宇、高景逸、丁长孺、刘静之、魏廓园五人而已,而景逸洎静之,尤以德业资丽泽,称最挚云。”[5]除此赋之外,刘宗周复有《祭年兄刘静之文》[6],即年谱提及的“操文以祭”,辞长情深,悲知己,哀同道,足见两人交谊之笃。
《吊六君子赋》作于天启五年,先生四十八岁。六君子即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东林党冤案的受害者,被逆阉魏忠贤矫诏下狱的六位大臣: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位大臣弹劾魏忠贤之大罪,而被恶口反噬,均惨死狱中。此乃著名的“六君子事件”,其中左光斗之事更因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一文而为人熟知。与此案有牵连的著名将领熊廷弼亦于是年八月被杀。时局险恶,缇骑四出,钩党之捕遍天下。是年冬天,“先生伤杨、左六君子之死,作《吊六君子赋》,上述诸贤正直之概,下数逆阉毒忠之辜,悲歌慷慨,若旦暮从而游者。”在阉焰方炽的情势下,刘宗周撰文公祭东林君子,这是极端危险的,以致高攀龙答书说:“此何异公子无忌约宾客入秦军乎?杜门谢客,此为正当道理。彼欲杀我,岂杜门所能免?然即死是尽道而死,非立岩墙而死也。大抵道理极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于极痛愤时未之思也。”[7]除此赋外,刘宗周还撰文祭吊魏大中、周朝瑞等人,其《祭魏廓园给谏》大声疾呼,控诉东林之禁的罪行:“煌煌大明,而申学禁。学禁伊何?东林射的。二十年来,飞矢孔亟。一朝发难,忠谏骈首。诏狱株连,积尸如阜。”[8]
《知命赋》与《逝哀赋》同作于天启七年,先生五十岁。年谱云:“是年正月,为先生五旬初度,有慨于夫子知命之学,作赋以自谂。复追悼丙寅诸君子之死,作《逝哀》以哭之。”[9]《逝哀赋》之作,“追悼丙寅诸君子之死”,即天启六年“东林七君子”。时局危殆,刘宗周本人亦岌岌乎难保,颇受株连,险遭不测。“逻卒分布天下,踪迹群贤,调得状即锻錬成罪,至缙绅不敢偶语……未几,逮高景逸先生,周公起元、缪公昌期、周公顺昌、周公宗建、李公应昇、黄公尊素七君子,而黄公则吾乡余姚人也。缇骑至姑苏逮顺昌,士民愤激,殴杀缇骑一人,余党鼠窜。”[10]在此过程中,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投水自杀,其余六人均遭酷刑拷掠,惨死于狱中。这就是明代后期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此处所述“缇骑至姑苏逮顺昌,士民愤激,殴杀缇骑一人,余党鼠窜”事,亦即张溥名篇《五人墓碑记》所记之事。
《招魂》盖作于崇祯十六年,时当明朝覆灭之前夕。此赋前有序,述其创作之由:“岁壬午仲冬八日,东兵入边,首破蓟城,分道而下,过京师东,自霸州出河间,直趋临清。其西者破兖州等处,则鲁藩被难,还至河北,薄山西界。又移临清之师围青、登间。久之,不克,直抵郯、宿,乃捆载其子女玉帛北折,与西股合图闯边以出,则时已逾年,为癸未之四月尽矣。我官兵始终无一格斗者。计此七阅月中,相传城破至百余,官民之死于家、死于国、死于道路而逃者,不知几万万。祸未艾也,于时元辅出而视师矣,计旦夕得饱飏去,普天下幸再造焉。宗周以闰十一月月晦日夺官,待罪邸下者两阅月,出次通城者两阅月,又徘徊务关、津门者半月,乃解维南下。一路浮尸满河,且夹岸而积者日相望,至目不忍睹。宗周自伤在官无状,不能为斯民请命于万一,徒碌碌偷生以去,是可怀也。因挥涕作招魂之词,以吊死者,且以谢罪焉。”[11]由此序可知,该赋作于内忧外患、兵连祸结之时,内有李自成之逼迫,外有清兵之破关。序中所述即为清兵骚扰入寇,所过势如破竹,官兵无一抵抗,致使“一路浮尸满河,且夹岸而积者日相望,至目不忍睹”的惨绝人寰的情状。刘宗周因直言进谏而被革职,于京畿迟滞有日,而后乘舟南下,此赋乃沿途所见之实录。
由以上所述刘宗周骚体赋之创作缘由及背景概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宗周之赋皆系有为而作。与其倡明正学、济世拯民的为学、为政主张相一致,刘宗周在其赋体文中也表现出匡救时艰、肃正人心的强烈愿望。其思想心态大致分为两端:
一是,褒正直,揭邪恶,正人心。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内外交困,社会动荡。刘宗周的赋体创作首先出于正人心,挽狂澜,回颓波的总体意图。这一总体意图既体现在他的“慎独”说的提出上,又贯穿于他的屡次奏章献策之中,更体现在他的个人讲学实践之中。时局愈是动乱,愈能激发刘宗周拯救人心沦失的迫切感。比如在缇骑逮捕著名东林党人,亦即黄宗羲父亲黄尊素之时,刘宗周为之饯行。“促膝谈国是,危言深论,涕泣流涟而别。……先生返谓门人曰:‘吾生平自谓于生死关打得过,今利害当前,此中怦怦欲动,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当也。’遂携子汋课读于韩山草堂,专用慎独之功。谓独只在静存,静时不得力,动时如何用功夫。”[12]又比如,他的政治献策《救世第一要义疏》谓:“夫宇宙之所以纲维而不毁者,恃有人心以为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则学术之明晦为之也。”[13]所以,刘宗周骚体赋的主要意图即在于褒奖直士,指斥奸邪,他的序跋、祭文等也主要关系于此一主要意图,即“倦倦于正人心、息邪说,辨晰人禽凡圣之所以分”[14]。
在《淮南赋》序文中,刘宗周的揄扬直士是与指斥凶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淮南》,诔亡友也。亡友刘静之氏,禀狷特之资,钟清明之气,苦心慕古,矢志匡时。其大节辨辞受出处之几,而躬行笃父子君臣之教。筮仕京学,量移辟雍。狐鼠纵横,振衣冠于涂炭;桑榆崦逼,慰朝暮之门闾。(时沈四明、钱给舍等朋邪乱政,诬罔善良,先生官大学,耻与同朝,遂谢病。会先生大父家居,念孙不置,先生益决归宁云。)处江河而悬廊庙之忧,怀瑜瑾而奋尘埃之迹。慨方正之不容,谩谓清流可浊;会谗邪之交搆,几令白日无光。(沈、钱去,余氛未净。会东林顾先生以清议自任,不容于宵小,遂被谗中。而先生于顾先生固忘年友也,呶呶者切齿先生辈,几罹一网。自是海内分门户云。)”[15]该序文言辞之间已将此赋之立场态度和盘托出。刘静之作为东林党的同志,刘宗周毫不迟疑地引为知己,其《祭年兄刘静之文》叙述自己“闻变入,甫逾一旬,拊棺而哭,哭且恸,越宿再哭之,又三哭之。酬酒几筵乃去。明年还朝,为癸丑之春仲,再上淮南,访其里,重呼我静之而哭之”[16],可见其悲伤之情浓。一赋一文作于此时,则其哭亡友不仅是伤知己,而兼寓宣泄愤慨不平之气。
《吊六君子赋》揭露冤狱黑暗与歌颂节烈之士并陈:“胡一朝而罹缯弋兮,连铩羽以遄归。岂君眷之难终兮?汔雨露而风霾。忽苍素温凉之变易兮,问党人以渠魁。录有虞之四凶兮,凛震叠以天威。缇骑纵横兮,诏狱穷推。五日一讞兮,斧锧钳鎚。鬻狱几人兮,苞苴几珻。六臣骈首兮,视死如归。魂渺渺其何之兮,俯帝京而徘徊。骨藉藉以凝尘兮,出圜土而如骴。”[17]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并不是一味地歌颂忠直,他对忠直之士被一网打尽也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指出正义一方的弱点与不足,以便汲取教训。“果邪曲之害公兮,将方正之累也。纵谗谄之蔽明兮,亦蹇谔之疵也。镜往事于今日兮,越千载而同揆。”[18]包括六君子在内的东林党一方虽然代表着正义(东林党成员复杂,这里仅指中坚骨干),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讲究斗争策略,不掌握斗争的灵活性,甚至未曾想到要暂时联合那些介于邪正之间或虽然邪恶但可资利用的力量,而犯了“人至察则无徒”的错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一味地排斥猛击,不遗余力,最终逼得邪恶势力狗急跳墙,杀人灭口。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比之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党争,一方面固然是恶势力所致,但也与正人君子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有极大的关系,逼得小人乃至中间人士无所遁形,只能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地与正义力量决一死战,导致玉石俱焚,伴随王朝一起终结。这些正直之士固然死得轰轰烈烈,但却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削弱了正义力量,导致朝政正不压邪,此消彼长,以致加速了政治的败坏进程。所以,刘宗周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蹇谔之疵”就显得极其宝贵。当高攀龙提醒他这种公开写赋、写祭文凭吊死士的做法过于危险,无异于自投罗网时,宗周也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遂辍讲遁迹,一意韬晦”[19]。
二是,愤时艰,哀民生,系家国。
明末之衰世,由来非一朝。作为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刘宗周对这种政治危机与时代艰难有着切肤之痛。在他的很多奏章与廷对中,他都直言不讳地向最高统治者表露这种末日将临的危机感。但是,这些还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从维护现行政权的角度立言的。而刘宗周的纯文学创作,则更多地是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与耳闻目睹,出于对百姓众生的同情而作,这就使得其文学创作更多了一层深沉厚重的家国之悲。这集中体现在《招魂》赋与《时艰行》、《用韵寄怀冯跻仲兼呈留仙津抚》、《伤哉行》等前此或同时的诗歌作品之中,今当合取互参,而不必拘泥于赋体。
《时艰行》写于崇祯九年,叙述的是清兵内扰,明军溃不成军,不作抵抗,任凭清兵从容劫掠的情景,特别谴责了将领畏敌如鼠而又骄横跋扈的卑劣行径:“辇金数万万,道路子女填。从容饱所掠,乃从隘口穿。我师出两月,不敢一控弦。元戎无节制,诸帅相轾轩。惟有高中贵,斩获传百千。复传我兵失,不啻相当焉。叛将与逃吏,纷纷安足言。哀哉十万师,送行殊可怜。朝廷不敢问,一手或障天。”[20]
《用韵寄怀冯跻仲兼呈留仙津抚》、《伤哉行》与《招魂》乃系同时期所作,所述同是清兵寇犯之事。五古长篇《用韵寄怀冯跻仲兼呈留仙津抚》云:“胡骑方狐狡,汉兵多鼠驯。烽烟断南北,积骸枕水滨。”(原文“胡”字缺,当系清代因避讳而删空,今据诗意补出。下诗“胡”字亦如此。)《伤哉行》云:“一自渔阳报鼙鼓,胡尘动地分道奔。西逼三晋东全齐,纵横千里烟无村。名藩大郡皆失守,殉及高皇之子孙。此时天下多勤王,总以两督恇莫当。突骑出前数百里,撄城画地如处囊。料敌计从饱飏去,子女玉帛委道旁。争戒行间莫浪战,天子三驱开一面,尚方续赐金帛多,赢得全师为彼殿。零星功级上幕府,都是良民头颈贱。一场兵事今且休,百万生灵付蹂躏。”[21]触目惊心地揭露明朝将领胆小如鼠,自私暴虐,一味龟缩,纵敌抢掠,甚至拿良民头颅冒充军功的暴行,导致了“流离载道不忍见,劫掠公行无净土”的人间地狱之惨景。
对照这些内容类似的诗篇,更能理解《招魂》赋的意义。《招魂》赋以深沉的情感直写乘舟南下时的水路所见,笔致较诗歌详细,也更为惊心动魄。它描述了百姓流离载道,生不如死,既死为幸,而又死无葬身之地,纵横满河,夹岸填积,随波出没的惨状。“孰载道而流离兮,既死者之幸生。独尔命之蹇蹇兮,罹锋镝以纵横。泛流沙而出没兮,夹岸渍以崩泓。舣余舟而不前兮,亦如诉以如瞠。”面对此等惨绝人寰的景象,刘宗周的悲悯忧伤之情可知:“余乃彷徨失次,载寝载兴。停桡倚舷,风驶云蒸。怒涛飞兮迴波立,蛟宫舞兮鱼龙泣。哀些助兮青衫湿,前致辞兮气悒悒。悼余生之不辰兮,遭纷扰以猖披。况频年之旱蝗兮,亦号寒而啼饥。急县官之征繕兮,复敲骨以吸脂。冀须臾以缓死兮,保乡井之孑遗。先年吾父死兵兮,复吾兄以继之。今年邻人死寇兮,并亲戚以捐縻。胡丧乱之日长兮,越己丙戊以于兹。痛渔阳之首祸兮,跨京邑而出郊圻。幸吾皇之无恙兮,俾我等以疮痍。或从戎而守戍兮,或为贾而为籽。或远奔而近窜兮,或走耄而携儿。流血聚以成川兮,骨肉蹂以如齑。横鸢狸之啄搏兮,骋游魂以安随。荷仁人之盻睐兮,早拯若于阽危。”[22]这些文句均直写目不忍睹之惨状,并以死者的口吻控诉了在明末“况频年之旱蝗兮,亦号寒而啼饥。急县官之征繕兮,复敲骨以吸脂”的灾荒频仍之下,官府仍然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以至民不聊生的罪恶现实。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官僚大员,能如此感情沉挚地为百姓代言确实难能可贵。
综而论之,刘宗周赋体文既有深沉哀悯的伤时忧民的一面,还有自责自省的一面,更有斥贪斥虐,特别是控诉揭露武将罪行的一面。这其中蕴含着刘宗周对于大明江山社稷的担忧,对于家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痛心。如《招魂》赋谴责武将:“总诸路之援兵兮,皆乌合而蜂从。环三镇以犄角兮,屈帷幄之上公。尔乃一矢不遗,累诏如充。指帑为获,杀良冒功。前驱后殿,卫其辎重。倏分倏合,飙颺以东。大法不灵,薄赏无封。”面对“指帑为获,杀良冒功”的无耻暴虐,作者痛心疾首,以至大声疾呼:“胡为乎罹昊天之成命兮?贷雷霆而罔赫。斥埃氛于一指兮,盻欃枪于永夕。迨玄运之既颓兮,倏朱明之半掷。日月耀而不光兮,星辰行而失则。天柱倾兮地维折,人纲坏兮臣子贼,裔猾夏兮兽相食,梦梦兮无凭,苍苍兮失职。”刘宗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天崩地扯、大厦倾圮、纲常沦丧、率兽食人的乱局之逼近。他唯一能做的又只能是在自我谴责、为官谢罪的同时,祈求上苍保佑了:“乞余言兮天听回,旻下民兮天眼开。”甚至保佑自己能够得行己志,荡涤乾坤,重整山河,“俾余戈兮鞭风雷,披四裔兮落三台。诛佞臣兮先中台,横江湖兮及草莱。”[23]
然而,时局已颓,回天无力。作《招魂》赋后仅一年,而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再一年,彻底绝望的刘宗周乃绝食而殉国。其先前五十岁时所作《知命赋》之末云:“静鑑祗今,仁是当兮。伯玉知非,何足方兮。庶几持此,效家邦兮。”[24]刘宗周终于以生命为代价,兑现了“仁是当”、“效家邦”的知命之承诺。
《论语·八佾》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作为一代大儒的刘宗周,亦于天下无道之时,以倡明正学、重振道德为首务,立朝则积极建言或批难时政,居野则讲学传道。其为学、为政、为文均致力于正风俗、成教化,使人知耻而奋起,这不啻为封建末世的木铎金声,具有警世醒世之社会功效。
刘宗周的五篇骚体赋作品大多作于忧患之世,多事之秋,均感于时事,有所触发而作。其文充于中而形于外,饱满丰厚,慷慨淋漓,饶有一唱三叹之致。这几篇骚体赋,远绍屈原,却又出以新意。既继承了屈原爱国忠君的传统精神,又在思想上超出了屈原的固有局限。就屈赋而言,尚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耀才扬己”,主要抒发一己的愤懑不得志情绪。而刘宗周的骚体赋大体上摆脱了这种自我局限,心胸与视界更为豁朗,以天下为己任。他把更多的笔墨用于描述自我之外的世界,歌颂仁人志士,揭露斥责邪恶势力,悲悯战争劫掠造成的人间惨景,堪称“诗史”。这是因为,刘宗周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他的儒学修养较为深厚醇净,无往而非仁者胸次,因而文气洒落浩荡。其愤时艰、哀民生的诗作如《时艰行》、《伤哉行》等,受杜甫沾溉尤多,甚至与杜诗的相关诗作相较,亦略无愧色。
刘宗周论为文激赏于一“真境”,崇祯十五年他为陶奭龄《今是堂集》作序,称道石梁“不轻事著述,而兴会所乘,自备诸体,一种真机流露,动成妙契,别有语录系之喃喃,尤其极口痛切处,转不落语言伎俩者。”[25]“真机流露”,无意于言而言的内充外显,也是宗周所崇尚的,我们完全可以将他对陶文的这一评语拿来,用以评论宗周的文学创作。
激昂悲慨以抒情,无意于文而自工。刘宗周上述作品虽然在具体的艺术技巧上并不刻意讲究,乃至与专业文士相比,可能显得不那么精工修饰,但是它却以丰沛的情感、高尚的人格、充实的内容取胜,较诸同时代的妆束作态之辈,确实是超迈群伦。日本桑原忱评价说:“刘子非以文章屑屑者,然其文雄厚俊迈,辩而不浮,直不至刻,激不失正,遇事辄发,无有穷极,所谓盈乎内,发乎外,无意为文而为文者也。”[26]特别是《吊六君子赋》诸篇,都是直写现实,反映了明代后期著名的东林党人“六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等重大历史,其《招魂》赋及相关诗歌真实地记录了清兵入关带来的严重兵患,呐喊出被无辜劫掠宰杀的百姓的心声,堪称晚明“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