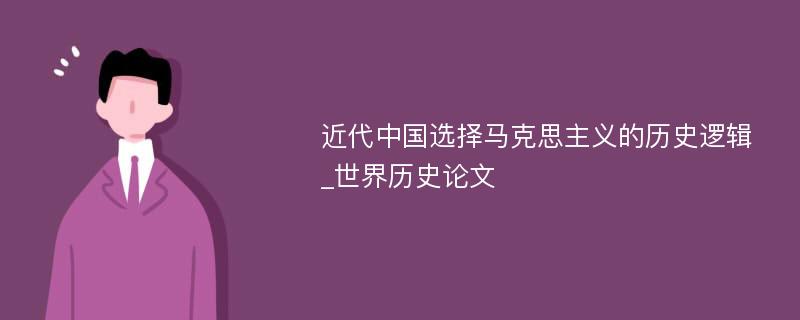
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8-0142-07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5.08.021 近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一极具战略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直至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世界,亦影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实践取向、社会发展道路及历史命运。因此,从历史发展本身的内在节律厘清近代中国何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逻辑,对于历史性地理解近现代中国何以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并走向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意义。 究其历史根底,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动因,既源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逻辑,亦源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逻辑。它乃是此双重逻辑在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叠加互动使然。 一、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逻辑 鸦片战争后,中国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性地转向以科技化、工业化、世俗化、市场化等为历史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转向的直接性的初始动因无疑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节律。正是现代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中国才被裹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性现代化变迁的大潮中来。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中国历史这一被动性的近代转向,其所面临的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中国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正如时人所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带给中国的挑战与危机是多维的而非单维的,是军事、民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多维危机的叠加爆发。这在以往中国历史的“变局”中从未有过!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引发这个“大变局”的直接动因是“世界历史”性的,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性现代社会变迁,历史必然性地催生了中国的这一“大变局”。正因如此,要有效应对这一“大变局”,要扭转“大变局”带给中国的全方位的空前危机,传统的“华”“夷”世界观与国际观绝难有效。中国需要新的契合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焦点水平上的新世界观与国际观。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科学研判“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根本趋势的前提下,正确选择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恰好满足了近代中国这一战略性的历史实践需要。 16~17世纪以来“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从空间维度看,它是一个由欧洲地域性事实弥散为“世界历史”性事实的过程;从制度维度看,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初始社会形态载体和开端的。这一现代社会变迁,在其出现于人类文明地平线之初,就带有极其鲜明的“善”“恶”矛盾二重性。 一方面,现代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催生了工业革命,开辟了世界市场,也“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②。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④。这一世界历史性变迁,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理性的觉醒,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裕,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它较封建社会成百上千倍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也把人本身和人的社会提升到了全新的现代水平。它也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弥散和扩张。这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其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社会历史变迁进步的一面。 另一方面,这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其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社会历史变迁,也同时伴随着“恶”的一面。它是“羊吃人”的血腥,是殖民战争的罪恶,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被毁、种族被屠杀,是“非洲三角奴隶贸易”和华人奴隶贸易之路上的皑皑白骨,是市场竞争的无情,是人性的异化,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⑤。它给人类带来的又是比以前更大的现代性的血腥、罪恶、战争、灾难、贫富悬殊及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与暴力。这使现代社会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一出现,就同时被置于质疑、批判与超越的焦点上。并且,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展开,这种质疑、批判与超越的努力,也如现代化浪潮一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现象。 与之相伴,这种以资本主义为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社会变迁在其弥散和扩张中,因其二重性,也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双重性的挑战与示范效应。一方面,通过现代西方国家与各落后国家、民族的冲突、较量,它表征了现代工业文明对后发国家之传统农业文明的巨大优势。面对西方的挑战与示范,这些国家只有走出自己的封闭、保守、落后及地域的狭隘性;全面地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才可能改变自己的被动与劣势,有效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其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世界历史变迁本身的殖民性、侵略性、剥削性、暴力性、异化性等否定性特征,它同样也带给这些国家一个巨大的困惑:难道自己的现代化未来就是已经表现出诸多罪恶、血腥、战争、灾难、贫富悬殊及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与暴力等否定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吗?那么,自己的未来不也就是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恶”吗?于是,伴随现代社会变迁而源起于西方社会的对现代性的诘难,就在这些国家扩展为世界性的,比西方社会更为强烈,更多的时候还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⑥。因此,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趋势,怎样选择自己的更合理、更正义、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就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的实践课题。“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彰显着超越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历史必然性与价值正当性。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对以资本主义为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社会变迁之矛盾二重性的分析、批判、诊断及治疗,早在现代社会变迁之初即已开始,并一直伴随至当代。如,始于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中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再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连绵不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扬弃空想社会化主义基础上建构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有,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与民族主义甚至文化复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绵延于20世纪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当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晚近兴起的人道主义、生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各种反省、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与运动;等等。这些思想理论流派及其实践运动,虽然阶级立场、理论基础、实践策略各有不同,但其锋芒所指无不是这种现代社会变迁的矛盾二重性,其价值指向亦不能不是要建构一种更合理、更正义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 上述思想理论流派关于现代社会变迁之矛盾二重性的分析、批判、诊断及治疗,虽然都从各自不同的视域不同程度地切中了这一问题,但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更为科学、准确、全面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趋势。 第一,它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二,它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解剖,对世界现代变迁之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第三,它关于世界现代化中矛盾二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又是最理性、最客观、最具建构性的。其一,它明确批判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这使其根本区别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其二,它对西方现代化中罪恶性、负面性的批判、针砭,又是最坚决、最革命、最彻底的。这使其根本区别于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强调,要解决世界现代化的负面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基础之上。既不能简单地拒斥现代社会发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顾,情绪化地炸毁现代性简单了事;也不能忽视现代社会应有的必要的生产力基础,在落后的前现代社会基础上浪漫化地建设空想的现代社会。并且,它还指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些,则使其明显有别于无政府主义、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各种民粹主义及当下的后现代主义。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之所以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就在于它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路径。这也就根本地解开了近代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始终为西方之“恶”所困扰的心里纠结,从而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前途和历史的最终归宿。正如史华慈所恰当地指出那样,它为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从西方观点来评价并批评资本主义西方的可能性”⑦。 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路及1910~1920年代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使然,也有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层实践逻辑。它乃是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互动影响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实践性选择。 中国近代之始,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撼了古老的中国。炮火的震撼下,以往游弋于中国边缘的朦胧“泰西”,既呈现给中国一个坚船炮利的切近形象,也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中心”的陈腐世界观。于是,“开眼看世界”的一代“经世派”仁人,开始认真地了解、介绍西方,开始倡导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式的“长技”。因之,在“经世致用”传统与察知“夷情”的现实结合中,中西历史开始了最初的汇通。随着中西冲突的深入,内焦外困下的主流政治集团渐渐接受了“师夷长技”思想,始而有了洋务运动及其“中体西用”的实践选择与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既表征了近代中国对现代性器物—技术的被动性认同和现实追求,也表征了近代之初中国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认知限度。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的坚船利炮量出了中国的器物——技术之短,此时的中国却未看到自身社会的整体性落后;表层呈现的是西方坚船炮利的迅疾威猛,殊不知背后还有制度性、价值性的支撑;虽然在传统社会的边缘打开了一个缺口,却未能动摇传统社会的深层根基。毕竟,此时的中西冲突还主要限于物质——器物的层面,几千年封建性的经济政治结构也还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而走向坍崩。 甲午战争后,外临“瓜分豆剖”之危,内显“揭竿斩木”之急。日益严峻的危机,蜕去了“同光中兴”的虚幻;近邻日本的崛起,彰显了制度鼎革的必需。于是,效日而学“西政”,成了进步之士的共识。因之,有了戊戌维新的变法与自强。然而,既缺乏充分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无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更面临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因此,维新失败也就势所必然了。随之,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迎然而生。然而,同样的原因,这个革命亦无法避免夭折的命运。 辛亥革命摧毁了满清王朝这一封建主义的特殊,却表征着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的一般及专制制度身影背后的落后社会心理与思想文化;满清旧势力的轰然倒地,才显露出汉族封建旧势力的强势;制度鼎革唤起了社会对新制度的巨大希望,鼎革后的社会现实却是依旧的残破与黑暗。即使否定了1911年的中国旧制度,按照法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国也并未处在1789年,更非处在20世纪初现代历史的焦点上!显然,1910~1920年代的中国,民族救亡与现代化步履依旧踯躅蹒跚。于是,继器物与制度之后,是现代西方同传统中国的整体对立。“80年新旧之争一变而为民主和科学的巨响”⑧,因之而有新文化运动的轰然鸣响。 从“师夷长技”到制度鼎革与文化革命,“欧风美雨”的持续冲蚀,使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日益走向解体,以至于旧制度彻底坍崩。与之相伴,朦胧的“泰西”也日益清晰为令中国人爱恨交织的矛盾统一体。 中国的旧制度虽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彻底坍崩,却未消解掉道德千年王国的“大同”之梦。毕竟,先进的、现代的西方虽然符合世界历史性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却因其殖民的强盗逻辑及侵略的野蛮行径而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地占据道德的道义高点。“泰西”清晰,却是现代文明与现代野蛮的一体并呈:有船坚炮利、民主、科学,也有西方激烈的社会冲突、尖锐的社会危机,及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的斑斑血痕。于是,在鼎革旧制与改良“西制”的羼杂中,有了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五权宪法”的实践选择与理论选择。然而,因既乏成熟现代性因子积累的必要根基,又乏有效动员工农大众的实践策略,辛亥革命也便成了“最乏力的革命”⑨而中途夭折。中国走到了徘徊、彷徨的十字路口。 恰值此时,世界历史进程上出现了“一战”和苏俄革命。这二者共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化,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于是,近代中国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亦有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灾难性结果的影响巨大。“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困难,信念的消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及个人关系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归罪于1914年7月所作决定的愚蠢。”一战昭显着“死亡、破坏、恐怖、荒芜”⑩。它使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恶”效应达到了极致的水平,使其全方位地、“世界历史”性地清晰地呈现给全世界。这既彻底地击碎了启蒙以来“现代性神话”的全面承诺,也极大的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合理性。“在这样一场人类大灾难中,人们的个人痛苦与精神上遭受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11)。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莱斯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不仅使人们感到了物质上的破坏,而且同样使每个欧洲人在意识上遭到蹂躏”(12)“工业的和国际的非公正性最终将变成自我毁灭性而使一个更为合理和公正的社会关系执行成为必然”。(13)它使中国人看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4)这令近代中国“学欧”“效美”的既有历史选择变得极为犹疑。而巴黎和会则更加剧了这一犹疑。“巴黎和会”击碎的不仅仅是中国对自身正当性要求的幻想,更击碎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仅存的最后一点虚幻的正义和希望。它清楚地表明了外国帝国主义之于中国民族解放和走向现代化的障碍性本质。 反过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因“一战”灾难的凸显,也就远超出了俄国的民族史层面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价值。一方面,这个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俄国社会本身,还在于“一战”的影响。它直接是在一战的废墟上,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革命而实现的。因此,这个革命所指向和否定的不仅仅是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更有通过俄国资本主义特殊所表征着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它具有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性,根本性地改变国际力量格局,并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对西方世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更系统的批判”“对于交战双方阵营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颇具诱惑力”(15)。正是“苏联的存在”“也吸引着西方的赞赏者,因为据说它提供了一种‘新文明’”(16)。另一方面,这个革命的思想理论纲领正是马克思主义。它实质上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出的实践之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因此,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实质上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新前途。并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既显的“魔魇性”,它还具有了更大的正义感召力和普遍合理性。它的这种正义感召力和普遍合理性,恰通过苏俄政府的对华外交直接传递给了中国。新苏俄政府的对华外交所呈现给中国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平等以待我的民族”(孙中山语)形象而已;它呈显于中国的,还是一种更具正义性、合理性、普遍性的另一种社会发展的美好前途。这为处于徘徊、彷徨、苦闷之际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崭新选择。于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也就由昔日的学欧、仿日、效美,转到了“以俄为师”(孙中山),也自然而然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17) 马克思主义之于近代中国而言,它既解开中国对帝国主义之“恨”的理论谜底,也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指明了新途:以俄为师。它对资本主义的充分肯定和彻底批判,契合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既“羡”又“恨”的复杂情结;它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则为中国积淀深厚的道德“大同”之梦找到了现代归宿。 三、中国文化传统的底蕴与马克思主义之理论精神的相契性 近代中国之选择马克思主义,既是当时历史发展的社会、时代、实践等客观条件使然,也同样有着中国自身的文化语境因素。可以说,积淀深厚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文化特质,亦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前理解”意义上的“视界”性前提与介质。 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长期积淀形成的中国文化系统,从其产生形成的时代性、地域性及其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等各个维度去看,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互释关系时,必须对这些差异性加以充分关注,注意互释的限度,不要出现过度解读。但另一方面,从更宽广的视域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国家各民族,所以能够实现跨时代跨民族性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又必然有其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根基。这个根基即是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一些本己性问题的普遍关切与思考。如人何以为人、人以何而在、人从何而来、人向何而去、人生有何意义、人生何为幸福,等等。正是这些普遍性的关切与思考把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具体”的人整合为一个物种和文化意义上“类”的人,也才有了人“类”社会。正是以这些人“类”普遍关切与思考为共同根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才有了能够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最根本的可能性。作为时代性、地域性及植根之经济基础都明显殊异的两种思想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能够实现相互间的“融合”互释,其深层根基也在于此。实质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追求、思维方式、文化经验、实践取向等维度上的文化特质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的底蕴和中介。 第一,普遍主义的社会理想及其社会价值追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始终贯穿与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普遍主义的社会文化理想与社会价值追求,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一种相对周边民族而言极高的文化势位及超民族、跨地域的普遍性。正是这种普遍主义的文化特质、文化精神使其与马克思主义有了文化精神追求上的相通相契。 中国文化的这种普遍主义的文化理想与社会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既有研究文献中,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间的相通性都有过研究和思考。然而,这些研究与思考的关注点,一般都在中国“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间的内容关联维度,而极少被赋予文化特质及文化精神的维度。这恰恰似是而实非。毕竟,就其内容的维度,在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间,不管是地域性上抑或是时代性上,二者都有着实质性的差异。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学者在联结二者后,都要再追述一点,即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意义的社会理想。其实,二者的关联与相通恰不在具体内容的维度,而在于文化特质和精神追求上。关键点在“天下”与“大同”的普遍性的特质与精神维度上。“天”这一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体系中有着极为尊崇的地位,以至于在中国文化的日常语言言说中以“天”为中心词的成语俯拾皆是,如“天理良心”、“顺天应人”、“天理昭昭”、“天经地义”、“天公地道”、“天诛地灭”“天怒人怨”“天网恢恢”,等等。其实,在中国的传统话语观念中,“天”这个词既表征为一切社会事理的最高和最为终极的根据,也表征为超越时空的跨地域跨民族跨时代的普遍性。所以,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核心和关键之处在“天下大同”。其实质,是要在“跨”“超”地域性的普“天”之“下”实现人“类”社会的“公”与“平”、“信”与“睦”、“饱”与“暖”、“选贤”与“任能”,以及“终”“用”“长”“养”而至“大同”。反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其根本旨归恰恰就是要在“人类解放”的终极意义上实现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性的公平与正义,从而达到人的本质的整体性全面性的回归。正是在这种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的终极指向上而非具体路径上,中国“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间才有了在文化视位和价值普遍层面的相通相契,才有了中国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时自然而然的“视界融合”。 第二,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与辨证统一的文化思维方式。在世界观和辩证法方面,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文化的深厚底蕴。它为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视界融合”提供了哲学思想上的文化纽带。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而孕化万物的朴素的具有辩证性的唯物思想。后来,孔子对“怪力乱神”的悬置,荀子对“形具神生”的思想阐发,王充的“气”物论,范缜“形质神用”的辨析,直到王夫之的“天下唯器”,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唯物论思想脉络。《易经》一书丰富的辩证思想,以《老子》一书为先河的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对一系列相反相成性矛盾概念的辨析及其辩证法思想,《孙子》一书开创的兵家对战争中各种构成要素的辩证性分析及实践等等。这些,作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源头,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得以继承、发展和丰富,从而也培育形成了中国文化鲜明的辩证统一的文化思维方式。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为代表的哲学著作中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结合、相融通也就具有了自然而然、浑然一体的特征。 第三,“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取向。重视社会实践中的“知”“行”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突出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知”“行”统一,与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经常言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是相同相契的。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知”“行”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域,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有过非常多的论述。《左传》中就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也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后来,《荀子·儒效》中亦详加阐释,“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许多中国思想家都对此问题作过论述。到了清代,王夫之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知行相资思想。他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庸》中,他把二者关系阐述为“知行始终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在近代,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亲身经验和深刻感触,孙中山则专门就“知”“行”关系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正因如此,我们也就看到,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著作《实践论》中,毛泽东用的副标题即是“知和行的关系”。 第四,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跨民族文化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身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它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实践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实质上,它本身即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之历史实践的文化反映与文化表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形成发展即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结果,其文化形态、文化内容本身即具有着突出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内涵。而且,在其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在与西亚、南亚、东亚等周边其他亚州民族、国家的文化交往与交流中,它还不断地吸收借鉴周边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思想使之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合,并使之中国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如此,这就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蓄性,也更凸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性的文化特征、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使之具有了浓厚的“跨民族文化经验”的实践支撑。这也就为中国在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吸收、借鉴、消化外来的西方文化,并转化生成自己的现代性文化系统提供了历史文化的内生性机理机制。以此观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不能不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兼容并蓄的历史过程。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276、277、276页。 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⑥参见[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5. ⑧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 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⑩(11)(15)(1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350、357、358页。 (12)(13)[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4)《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现代性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大变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