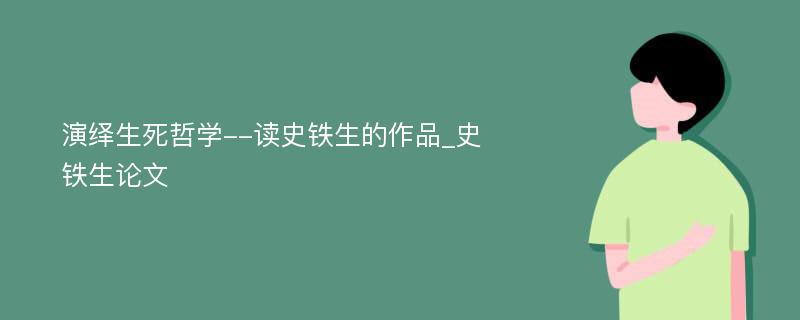
演绎生命和死亡的哲理——读史铁生的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理论文,生命论文,作品论文,史铁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6365 (2000)02—0066—03
读史铁生的作品会感到有一种哲学气息迎面扑来,他的作品通体贯注着一种对人及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那种对人生根本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讳的揭示,以及作者为此所受的精神磨难,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文学大潮中,这是一种来自人类精神高空的极为纯净的声音。
一
1.“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人最怕什么?死。但是人生来就在走向死,这是大自然不可逆转的规律。在生活的缝隙里,对死亡的恐惧会不时袭来,如同一只蓦地伸出的冷手,攫住你的心魂。对死亡的这种恐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人生的无奈和寒冷。今朝欢颜,明日枯骨,生死之间一线之隔。那么,这个以死为归根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空空的生存之果到底有什么价值?人类的共同困境、人生的最高问题平等地摆在所有人面前,但是不同的人解答的方式不一样,不同的人探索的机缘不相同。
史铁生的机缘出现在他21岁那年。那年,一辆轮椅在静悄悄地等待着这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从此,人生彻底改变,他被从正常人中抛出,打入一个被歧视、被践踏、被遗忘的角落,成为“废物、累赘、负担”(注:《没有太阳的角落》)。这种变难对身心的打击,恐怕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尽述。值得庆幸的是,身困轮椅的史铁生,心灵、情感和思想却从此异常敏感、丰富和深厚起来。当他结束了以腿行走的历史后,很快便开始了用心著述的旅程,别无选择地进入了命运预定的角色:书写苦难,穷究生死。本来生命意识的形成和人生境界的升华往往就是在生存艰难或理想受挫的时候,这时人在悲观失望、困惑痛苦中认识了自己,从而超越出自身的局限,走向更高境界。史铁生正是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开始了“走穷碧落下黄泉”的思想探险,开始了对生命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苦苦追寻。当他十几年如一日摇着轮椅走向地坛时,当他如达摩面壁、沉思冥想时,在平静的外表下,是一幕幕挣扎搏斗的心灵图景,思想的飓风挟裹着他的病残之躯在生命的极地和绝境横冲直撞,知道撞得头破血流,直到把无边的黑暗撞出一片希望的光亮。
成就史铁生的不仅是冰冷的轮椅,还有慈悲的地坛。在人生路上遭遇地坛是命运对史铁生最大的补偿和馈赠。这座废弃的古园“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注:《我与地坛》),历尽沧桑等待着史铁生的到来。就在这个荒芜冷落之地,史铁生经年累月地默坐、沉思、阅读和写作,成长为一个优秀作家,写下了经典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等,地坛成为他大难之后的再生之地,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精神避难所。所以史铁生说:“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注:《我与地坛》)
2.“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
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从“死”开始。
病残之后的史铁生曾经强烈地渴望死、祈求死,常常一个人把轮椅摇向地坛,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自己为什么要出生。人生遭此不幸,产生轻生之念实属正常,因为死虽可怕,但残疾人的生活常常比死更可怕。残疾人的痛苦、不幸以及因之而来的死亡意识是史铁生人生情感的最深基础,表现这种痛苦和死亡意识便自然成为他创作的母题。
围绕这个问题,史铁生描写残疾人对爱情的渴望与无望,记述他们自卑与自弃的心灵体验,表现他们苦难的沉重和希望的空茫。没有爱情,没有平等,没有尊严,如此寄身于世,生出“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注:《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幸亏人可以死”的极端念头(注:《没有太阳的角落》),便不足为怪了。在史铁生这类题材的作品中,《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最为细腻和柔软,它表现一对残疾夫妇的善良无助,读后令人为他们对对方、对世界的温情与关爱而落泪。《原罪》的故事则令人不忍卒听。真不知道,那个一辈子被钉死在床上的可怜人,那寂寞、空洞而漫长的时间该如何度过,生命该怎样才能获得拯救!所以史铁生常常忍不住要为这些残疾人的遭遇伤怀叹息,要借一些吟唱死亡的歌曲为这些卑贱如泥的生命祈祷安魂,如“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这首黑人的灵歌在他的一个短篇中便反复吟唱了十几次,布散着浓郁的悲伤气息。这种对死神的呼唤在《夏天的玫瑰》中得以坐实。此文与《来到人间》可以视作姊妹篇。两个生下来注定残疾的孩子,一个由于父母的爱,来到人间,从此痛苦要跟她一辈子;另一个也是由于父母的爱,却在尚无生命意识时就被安排安静地离世,从此获得了永远的解脱。相比之下,哪一种做法更人道呢?在这个似乎两难的问题上,史铁生的选择却毫不含糊:“不是把什么样的人救活都是人道,你们得为孩子的一辈子想想……”(注:《夏天的玫瑰》)“我们何必不让这些注定要倍受折磨的灵魂回去,而让一些更幸运的孩子来呢?”(注:《安乐死断想》)
正是因为身在其中的切肤之痛,史铁生由衷地感叹:“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注:《来到人间》)在他的精神自传《山顶上的传说》中亦频频自问:“可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直接而强烈地表达着自己对生命的怀疑和否定。在人生的黑暗时期,史铁生一边痛苦地思考,一边寻求着突围的出口,想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想为空无所依的灵魂找到一个支点,在出路找到之前,他只有听命于内心那“毁容的激情”,让自己在死神的身边徘徊。终于,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平息下来,史铁生的目光也渐渐穿过死亡的峡谷,进入了开阔而深邃的人类精神的高空。
二
1.“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把握和了悟也肇端于“死”。
把史铁生从死神的悬索中解救出来的首先是卓别林,是卓别林的一句妙语:“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史铁生觉得,卓别林轻而易举地把死的绝望变成了一种希望。的确,死神是人生最守信用的伙伴,早晚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在你再没有力气生存的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在几年的精神炼狱之后,史铁生也终于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注:《我与地坛》)那么何不再试试活下去?活着已经苦到了头,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这样,眼前的一切便不再可怕,因为即使你尝遍人间万苦,但是这苦难总有尽头,不会没完没了,在生命的那一端,你会有一个永远的假期。这种了悟使史铁生直接赢得了生存的勇气,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走进了实实在在的真正的人生。不仅如此,史铁生进一步认识到,对于人世来说,死亡是必须的,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人生的魅力正在于人生的短暂,人若有如木石一般悠悠,虽然可以无烦无恼,但是“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塌塌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注:《答自己问》)正是死亡映照出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也赋予人生以不可抗拒的魅力。所以,死是生命的前提,有生有死,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这种觉悟使史铁生关于死亡的思考变得冷静而理智。此外视死亡为“节日”的达观,则深透地反映出人类死亡情感的另一面。人类有着强烈的怕死的本能,同时,也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微妙的“死欲”。在不少文人笔下,死被当作生命的最高享受和人生的最大修饰与安慰,甚至被等同于母亲的怀抱。诗人朱湘命赴清流前有“伊怀里我拥白絮安眠”的向往,在荷马史诗中,也常有“投向死的怀抱求庇护”的说法。可以想象,一旦死亡的压力转化成一种动力,人生的绝境转化成一种诱惑,那么它不但不会成为重负,反而会带来生命的愉悦。所以智者面临死亡,不但不感到可畏可憎,反觉可庆可喜。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休谟临终泰然自若,而苏格拉底迎接死神时甚至欢喜若狂。史铁生的“节日”之说深得个中三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死亡的全面接受和认同。
死是必然的,死是必须的,死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些理解使史铁生的死亡观超越出世俗的生命感受,从自然层面跃升到了哲理层面。这种突破在史铁生的整个精神历程中十分关键,它提升着史铁生的人生境界,赋予他以哲人的智慧、宽容和达观,使史铁生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求变得现实而可能。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海子的自杀,死亡意识被空前张扬,“绝望使我的哲学”成为一种思想时尚。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有些人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口袋里时刻揣着一粒氰化钾。这种绝望哲学从对生命的怀疑与困惑,发展到对生命的轻视、否定和抛弃,走入了死胡同。相比之下,史铁生对死亡痛苦的前思后想和最终的大彻大悟,虽不如前者那般悲壮,但是更具人性和亲和力,更能表现对人类对生命的尊重、关爱和珍惜。
在史铁生最优秀的作品《我与地坛》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这段话十分精彩,它把死写得那么从容美丽,达到了诗与哲学谐美的境界,而且它把生命的生死两端连接在一起,揭示出生命、人类和宇宙的真谛:生死相依,生死相继,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生不息。
2.“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注:《我与地坛》)
对于史铁生来说,活下来之后最大的事情是如何面对残酷的命运和现实。受苦是个体生存的永恒境域,因为“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注:《我的梦想》)”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之后史铁生开始试图理解自己的命运,试图勘破命运的真相。在《对话练习》中,史铁生通过一场虚虚实实的对话阐明命运是一条任意组合的因果链,是一种偶然。命运=偶然,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是“偶然是唯一的真实”,生命的根本特征就是偶然,每一部人生交响乐都是上帝没有乐谱的即兴演奏。《中篇1 或短篇4》中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的情缘在五岁时就已注定, 但是人看不见它,人对它一无所知。《宿命》里一段辉煌的前程与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之间仅仅一秒之差,一步之遥。所谓姻缘、祸福、生死,操纵这一切的其实全都是偶然,在人生的独木桥上,你必然地遭逢偶然,必然地走向自己的宿命,在劫难逃。对命运之谜的破译,平息了史铁生的愤恨、挣扎和绝望,使史铁生表现出对命运的充分理解和宽容:“偶然——你说不清它,但是得接受。”“何必不承认命运呢?不承认有什么用呢……不承认那种超人的力量,可你还是受着它的影响。”(注:《山顶上的传说》)于是史铁生振作精神,接受了命运的挑战,接受了命运赋予他的不幸、脆弱和失败,在人生的悲剧舞台上担当起悲剧英雄的使命:“上帝给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如果注定有人倒运,那么还是让我来吧,没有谁能比我应付得更好了。”(注:《山顶上的传说》)
在对上帝与命运之神的信仰与求助崩塌以后,史铁生为苦难里的心魂找到了救路,这就是信心和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注:《一封信》)“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向前走。”(注:《一封信》)就是这种信心和精神使史铁生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用写作支撑起沉沦无助的生命。写作是什么?“也许写作从来就只是一种机会吧?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从真实的苦役中解脱出来,重返梦境。”(注:《〈务虚笔记〉备忘》)在艰难的思考和写作中,史铁生修炼着自己的意志和品格,完成了生命困境的突围和自我苦难的救赎,获得了在更高层面上接受和体验绝望与虚无的力量。他睿智地写道:“神不给人指路。神知道,不给人指路,它还是会去找。不停地去找,就是神指给你路。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注:《山顶上的传说》)
3.“事实上你唯一拥有的就是过程。”
在史铁生的全部哲学思考中,“过程哲学”是最深厚最动人的一章。
在广大的尘世,人只是一种瞬息和有限的存在,偶然地诞生,又必然地死去,生命的无限循环,使“生”和“死”都变得无足轻重。“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高更的画题是人类精神领域中最具形而上深度的终极问题,它与人类的思考相伴始终。命运赋予史铁生以人类关怀的博大精神,也赋予他直面人生根本缺陷和终极虚无的勇气和智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多处看到他对这种人本困境的焦虑和疑惑,比如,“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里?我们再朝哪里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正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注:《好运设计》)在危机和焦灼中史铁生终于发现对付绝境的办法只有过程,过程是人类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寄托。
《命若琴弦》是史铁生“过程哲学”的形象演绎。
这是一个关于瞎子艺人的故事。老少两个瞎子弹琴说书为生。他们的生存信念是,当一个瞎子弹断了一定数量的琴弦,就可以在琴槽里找到一张让他重见光明的药方。而所谓的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的白纸。如此代代相传,重复地支撑着瞎子们在人间流浪说唱。老瞎子用五十年弹断一千根琴弦,方知这是谎言,“那目的原来是空的”。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消失,但是他省悟到了这谎言的意义:“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命若琴弦》是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寓含着关于目的的和过程的哲学构想。
生存需要目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目的都不具备终极意义,都不是绝境的对手,都不足以与死亡相抗衡,死会把任何目的铲平,变为虚无。但是倘若没有目的,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漂泊无依,生命的过程便会变得不堪忍受,那么,人最大的恐惧将不再是死亡,而是漫长而空洞的时间,是生命本身。所以只好虚设目的。但是明知目的是空,还能自欺欺人继续追求下去么?比如倘若小瞎子知道那是谎言,还能奔那个目的而去么?这就是人类现实生存的悖论性处境。对此,史铁生的回答是:“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因为“如果我们不信目的是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注:《答自己问》)
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与绝望后,史铁生从目的转向了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了对过程的关注,他甚至想,也许“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注:《好运设计》)转向了过程便意味着找到了救助,走出了绝境。因为“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把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注:《好运设计》)是的,人生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虚设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而是为了引出这个美好的故事,为了为过程确立一个方向,让人在必死的生命途中远离孤独、寂寞和无聊,使每一个无望的瞬间都充盈着饱满的生命和泰然自由的精神。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尽管被判定受终身绝望之苦,但是他终于跨过绝望而把生命灌注到顽石无尽的滚动之中,西西弗斯因此成为美丽而悲壮的生命过程的象征。
史铁生的写作也被赋予了这种“过程”意义,即“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注:《答自己问》)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史铁生展示着自己不屈的生命意志,艺术地实现着人生的梦想,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健康而自由的生命形态。
创作是作家主体精神历程的艺术再现。在漫长的精神旅途上,史铁生始终立足于人类终极关怀的哲学制高点,让思想之翼折冲于最细密的现实关怀和最迂阔的生死忧思之间,将一己之人生体验上升为普遍的人类情感,惟其如此,史铁生的创作才能既满贮着高蹈飞扬的生命激情,又深藏着力求彻底和无限的理性精神;才能接通人类的终极地平线,向我们昭示“向死而生”的生命真谛;才能集束成一道哲学的追光去烛照无边的生存黑暗。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收稿日期:2000—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