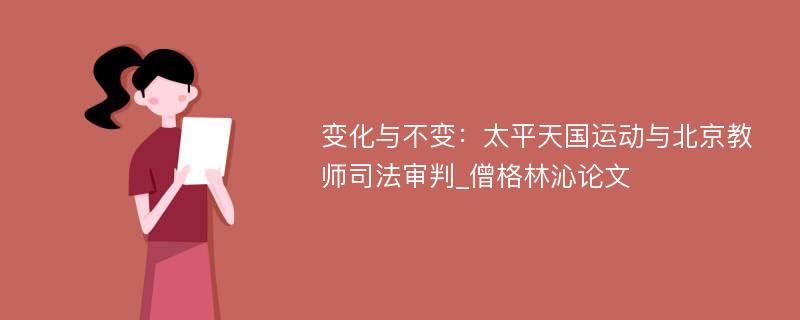
变与不变:太平天国运动与京师司法审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京师论文,司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9.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2-0089-12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其势力不久直接影响到京师。清廷为应对危局,在京师以及近畿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成立京城巡防处、加强保甲等。清廷的一系列措施,对京师的司法审判产生影响。其中,京城巡防处的影响尤为明显,而且留下了不少有关审判的档案①。太平天国运动破坏了清朝的审判制度。为了平息叛乱,清廷在各地施行“就地正法”②之制。而京师作为帝都,清廷的政策则相对谨慎。但以往的研究者,均未注意到京师是否施行“就地正法”之制。对于京城巡防处,“时人批云‘巡防处稽查形迹可疑之人,勾捕过严,有无辜而死于西市者’”③。后来的研究者们也认为京城巡防处杀了不少无辜百姓④。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京城巡防处对京师审判制度产生了何种影响⑤?
本文研究表明,尽管太平军北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师审判制度,但这种变化一方面仍然是中国传统的自我演化,并未渗入任何近代的因素;另一方面,与各直省相比,太平天国运动对京师司法的影响要小。清廷并未在京师实行“就地正法”之制,京城巡防处对案件的审理也大体遵循清朝制度。完善于乾隆时期的京师审判制度⑥在清末新政以前变更极少,即便是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给京师审判制度带来新的变化。
一、京城巡防处的设立
京城巡防处是清廷为防范太平军北伐而专门设立的军事联络与指挥机构,统筹京师防务。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部队进入河南,因京师为根本重地,咸丰皇帝特于五月十八日“著派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步军统领·左都御史花沙纳、右翼总兵达洪阿、军机大臣·内阁学士穆荫专办京城各旗营巡防事宜”。同时令已经革职的赛尚阿随同僧格林沁等办理巡防事宜⑦。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僧格林沁前往通州、黄村、卢沟桥等地查看,布置京畿防务,并于二十四日拟定京师《稽查章程》十二条,得到皇帝批准。《稽查章程》除对赌博、讹诈、私造火器、酗酒、斗殴、犯夜禁、米石出城等严行禁止外,还特意强调严查奸细、严禁议论是非、严禁妄造谣言,并限制迁徙,“如系无故迁徙,有心运寄躲避者,即将起意之人按律治罪,资财入官;傥实有事故,必须回籍者,亦应报明地方官。除盘费银两外,其余资财暂行交官,仍由在京地方官发给知照,由原籍地方官照数发给”。同时,加重对上述各种犯罪的处罚⑧。
咸丰三年九月,因太平军进入直隶,京师震动,清廷立即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务与治安。九月初六、初七日,清廷连发谕旨令步军统领、五城等认真稽查弹压。九月初七日清廷派惠亲王绵愉总理巡防事宜⑨。九月初八日,命工部员外郎耆英在巡防处效力。九月初九日咸丰帝在乾清宫举行仪式,授予惠亲王奉命大将军印、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参赞大臣关防,令僧格林沁出京。又因僧格林沁统兵出京,添派亲王衔定郡王载铨、内大臣璧昌办理巡防事宜。同日再次谕:“顺天府所属各营,向系直隶总督管辖。现在军务殷繁,自应权宜办理。所有顺天府属各营将弁兵丁,著暂归该兼尹、府尹管辖调遣,以资防卫。”初十日,又加派恭亲王办理巡防事宜。九月二十日,添派户部尚书孙瑞珍、刑部左侍郎罗惇衍办理巡防事宜⑩。
据曾经参与巡防事宜的成琦所述:“大将军、王大臣言事用军机折,许随时陈奏。大将军有面陈,得请见。大将军行文,内惟军机处、宗人府、内阁、各部、院及侍卫处用咨,余用扎;外惟钦差暨参赞用咨,余用扎。中外行文大将军,用咨呈;惟宗人府、内阁用移会。”(11)而负责巡防处的惠亲王是道光帝的兄弟,也就是咸丰帝的叔叔,从中不难看出巡防处的地位。
京城巡防处设立本身以及清廷的一系列举措,可见京师管理已经空前强化。风雨飘摇中,清廷必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力挽危局。而所谓“乱世用重典”,也是统治者的一贯手法。当时,清廷对各地叛逆重犯予以“就地正法”,不再按常规审判途径处理。京城巡防处是否也对叛逆重犯予以“就地正法”?京城巡防处在京师审判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
二、京城巡防处的审判职能
京城巡防处作为军事协调和指挥机构,有权审理涉及军事方面的犯罪。据成琦所述,“先是,巡防办事借值军旗衙署”,九月巡防处“设公所于地安门外东不量桥之东,谓总理巡防事宜处”,下设文案、审案、营务、粮台等办事机构。其中审案处负责审理案件,设总司二人,余俱帮审(12)。巡防处审讯事宜由驻守京城的惠亲王绵愉等人负责,僧格林沁等统兵大员则在外打仗。据档案,自咸丰三年九月十三日起,巡防处开始审理京师涉及军事方面的案件(13)。在此之前,京师涉及军事的案件仍按正规途径由刑部等衙门审理。如咸丰三年七月,北城御史拿获一可疑人犯,即奏交刑部审理(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京城巡防处档案》保存了巡防处所审案件的部分案由、部分案件的奏折、供词等,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已经出版。在《刑(法)部档案》中,笔者发现有咸丰四年(1854)巡防处所审案件案由的残片。笔者试依据这些档案,并结合相关材料进行论述。京城巡防处所审案件主要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也偶尔审理命盗、债务、铸钱、天主教等各种案件,但基本没有超出僧格林沁五月所拟《稽查章程》的案件范围;后来,巡防处还审理大钱案件。笔者将巡防处所审案件分为涉及军事的案件(包括相关普通案件)和大钱案件两类,分别予以论述。
(一)涉及军事的案件
据档案可知,京城巡防处主要审理与军事相关的案件,另外也处理越城等案件。京师各衙门,遇有此类案件,会送至巡防处审理,如果情罪重大则奏明皇帝再送巡防处。步军统领所属步军和各门门军常将可疑人犯直接呈解到巡防处审理,而没有按常规途径由步军统领转解。对于重大案件,步军统领衙门则奏交巡防处审讯。即使顺天府、刑部遇有此类案件,也会送到巡防处审理。巡防处对于涉及军事的案件可以全权处理,但对于一般的案件,则交由相应衙门处理。例如偷盗案件,有些送刑部审理,有些则交由顺天府审理。对于钱文案件,既有巡防处自行拟结者,也有送刑部审理者。自咸丰五年(1855)三月起,大钱案件,概归巡防处审理,详见下文。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巡防处所审案犯多由京师各衙门拿获,少见有呈诉者。当时军事形势紧张,让百姓前往巡防处控诉显然不利于保密及管理。除兵丁、衙役盘查拿获之外,也有为了某种目的诬陷别人者。不过,这种案件非常少见。档案中,被判斩监候朝审勾决的许城即为一例。许城有一女于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经内务府镶黄旗包衣王四儿为媒许给太监刘得幅的义子刘玉山为妻,尚未过门。咸丰三年四月间,许城听说刘玉山逃走。十月十四日许城听说刘玉山回京,又于十七日不知所踪。许城即向王四儿抱怨,要求退婚。王四儿问许城有什么办法,许城就说写一封信捏称刘玉山已经投奔太平王,这样刘得幅自然害怕可以退婚。王四儿答应,即写了一封信由其表弟张虎儿抄写后交给许城。许城将信塞入刘得幅门缝内,刘得幅拾到信后立即呈告京城巡防处。京城巡防处讯得大概情形后立即请奏严讯。最后巡防处判许城除悔婚轻罪不议外,应照诬告叛逆之人未决者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咨送刑部监禁,归入来年朝审办理。王四儿于许城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系旗人照例折枷鞭责发落。张虎儿应照谋害他人不即阻挡律,杖一百酌加枷号一个月。其余无干之人均毋庸议。巡防处拟律后即上奏请旨(15)。
对于拿获案件的审理过程,笔者试以杨可望一案进行分析。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步军统领衙门兵丁在查店时拿获杨可望。不久,兵丁又将杨可望之义父杨起信拿获。步军统领联顺随督饬司员详加审讯。杨可望供曾经被贼(指太平军)裹胁打仗,打死官兵二人。杨起信供不知其义子从贼打仗之事。步军统领衙门审讯后,于咸丰四年正月十七日上奏,将案犯所供情形叙述明白并请将案件交巡防王大臣审讯。皇帝于即日朱批“杨可望、杨起信均著交巡防处严讯”(16)。注意步军统领衙门虽将案犯供词一并上奏,但并未拟律,与平时送刑部案件类似。其他各衙门送往巡防处的案件,也如京师初级审判之例,均不拟律。
步军统领衙门将人犯解到之后,京城巡防处立即督饬司员严加研鞫。杨可望和杨起信所供情节与前在步军统领衙门所供一致。经司员审讯后,巡防王大臣等亲加复讯,“核与供无异,应即拟结”。杨可望被贼裹胁,听从打仗,应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杨起信虽不知杨可望从逆之事,亦未便轻纵,应于“乞养异姓义子为嗣,杖罪上加等。拟为杖六十、徒一年。虽年逾七十,不准收赎。札交顺天府定地解配,折责拘役”。巡防处拟律后即上奏请旨(17)。
巡防处对案件的处理程序基本上与刑部一致,不过稍有区别。如果系奏送案件,则不论罪之轻重,一律请旨发落。对于各衙门呈送案件,如果巡防处觉得情罪重大,亦会由咨改奏;如果是巡防处所辖兵营呈送者,案情重大也会在拟律后上奏请旨。对于呈送案件徒、流罪犯的判决,一般不单独上奏,说明可直接产生法律效力。以上程序都和刑部一致。各衙门将人犯送到后,即督饬司员审讯。就所见档案,一般都是由司员将案情问讯明白,再由巡防王大臣亲加覆讯。如果案情无异,则即拟律,未见司官先行拟律。刑部则由各司审讯明白后,各司自行拟律后再由刑部堂官复核。对于重案,刑部堂官也会亲提人犯复讯。如果复讯无异,一般会按各司所拟办理。
和刑部以及外省各问刑衙门一样,巡防处对一般犯罪也照《大清律例》拟律。但是对死罪则未说明所引律例,只是如前文那样照“军法从事”。同时档案中大量案件巡防处均在律例上加重处罚。如上文杨可望之义父,虽然年老而且不知其子从“贼”之事,亦加重处罚。又如巡防处审理李秋儿、寇希智一案,李秋儿打仗杀人并奸淫妇女,巡防处拟李秋儿应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从重加拟枭示;寇希智被贼裹胁,服役一日即乘空逃回,但“现当军务吃紧之际,未便照刑例被掳从贼自投来归免罪,致滋轻纵,寇希智酌拟杖六十、徒一年,劄交顺天府定地配解”(18)。
由案由中的时间差可知,巡防处办理案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和京师日常案件一致,巡防处对徒流案件定拟(如系奏案经皇帝批准)后,徒、流罪犯由顺天府定地发配;军罪案犯则由兵部定地。上文二例徒犯均指明由顺天府定地配解。再步军统领衙门奏送高付溃一案,巡防处审得高付溃被裹胁仅止服役旋即逃出,拟于被胁随同打仗未伤人遣罪上量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劄交顺天府定地发配。巡防处拟律后即奏闻请旨。巡防处审讯杨二一案,即将其中一犯黄泳淦拟发黑龙江为奴,咨送兵部即行发配(19)。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巡防处对死罪案件的判决,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方可执行。在档案中,有关死罪的判决,巡防处叙明案情并拟律后均道:“所有臣等审拟缘由,谨恭折具奏。请旨。”当然有时是意思类似的话。咸丰四年四月十三日上谕中亦提到:“巡防处叠次拿获形迹可疑人犯,经该王大臣等审明定拟具奏。朕核其情罪,较重者即立正典刑。”(20)这也表明巡防处所拟死罪案件不需要刑部复核,但需要皇帝的核准。尽管京师一度风声鹤唳,但始终没有像外地那样施行“就地正法”之制,死刑的判决均须皇帝批准。
据档案可知,京城巡防处所审案件不限于京师,而以巡防所涉及的地方为限。成琦《巡防纪略》载有京师及附近地区兵丁数目及分布情况,这些兵丁主要用于京师防御(21)。各路军营盘获的可疑人犯,均由该路领队大臣送交或奏交巡防处审理。其中文瑞、乌尔棍泰统率的东路军营因拿获奸细较多,得到咸丰皇帝的嘉奖(22)。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令乌尔棍泰等将“寻常可疑人犯,著送至载龄处转解;若要紧头目,著直交巡防处。统不必奏,以归画一。若实有至紧至要机密之事,仍著知奏”。同月二十五日,乌尔棍泰仍将二可疑人犯李秋儿、寇希智审录情况上奏,请交巡防处审理。咸丰帝除照常例将该犯送巡防处审理外,还严厉批评乌尔棍泰:“上次朱批岂尚未看见耶!抑并未遵行耶。著乌尔棍泰明白回奏。钦此。”(23)
根据《刑(法)部档案》(新整)所藏咸丰四年巡防处所审案件案由的残片可知,巡防处每日所审案件远少于咸丰三年年底。尤其是到了咸丰四年七月以后,案件更是稀少。说明巡防处所审案件和当时的军事形势紧密相连,也表明巡防处将其所审案件规定在与军事及其相关范围内。此档案中,只见总统各路巡防官兵大臣载龄呈解案件,未见各路领队大臣呈解。咸丰四年三月二十日上谕,著载龄统筹守御,将所有现审未结案件,俟文瑞抵营后移交审办。二十五日,因文瑞生病开缺,“所有现审未结案件,仍著载龄迅速审办,分别定拟具奏”(24)。按此二道谕旨,载龄对转审案件可以定拟。由于缺少史料,不知详情如何。但档案中,载龄仍将可疑人犯解送巡防处审理。
虽然巡防处官兵在近畿拿获的案犯有许多送至巡防处审理,但清廷在京畿各州县实行的政策不同于京师。咸丰三年九月中旬,清廷令顺天府府尹和直隶总督督饬所属办理团练,明确谕令在京畿各地方官“出示晓谕,如遇有本地匪徒及外来贼伙乘间抢掠者,准该绅民人等格杀勿论”(25)。而京城巡防处及京城官兵则没有这样的权力。
至于在外打仗之各统兵大员,对拿获人犯的处理权力也非常大。所有案件中只见有胜保将一幼犯送到巡防处审理,其余未见有前方所获俘虏。僧格林沁等统兵大员在外打仗,也偶尔对其拿获的一些罪犯进行审讯,有时将供词送巡防处查照(26),但未见送巡防处审理者。不过,对于太平军首领,如林凤祥、李开芳等,均交巡防处审讯。实际上,僧格林沁等统兵大员在京畿地区一样施行“就地正法”之制,其对于拿获的人犯,拥有比京城巡防处更大的权力。咸丰三年十二月,僧格林沁表示“现在逆氛逼近之区,无赖之徒未免心萌乘机妄为之念,必须尽法重惩”。僧格林沁将张永等犯人委托通永道会同武清县审理。经审,张永等四人或入室伤人,或认代为纠邀,情形较重。僧格林沁令将此四犯于犯事地方立正军法,枭首示儆。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六僧格林沁上奏办理情形,皇帝朱批:“办理俱是。”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僧格林沁奏已将活埋官兵之武举张攀桂等正法,咸丰帝也表示同意(27)。
(二)大钱案件的审理
咸丰三年,清廷因无力筹集军饷,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清廷为此一方面节省开销,于咸丰三年九月下旨宗室觉罗及八旗官员红白事赏恤或是停止,或是减半给与(28);另一方面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行官票、宝钞,不久又下令户、工二部铸铜、铁大钱(29)。然而,由于大钱分量不足,立即遭到市场的抵制。清廷无力也无心使货币物有所值,甚至认为“大钱之畅行与否,全视在上之信与不信”(30)。同时,大钱因分量不足,还引起大量的私铸,更给大钱的流通带来障碍。咸丰同年六月,清廷因私铸之案层见叠出,认为大钱使用不畅是因为私铸太多,从而加重对私铸犯罪的惩罚。咸丰帝批准刑部所议,将私铸之犯为首者及匠役人等不论是否已及十千均从重拟斩监候,并在刑部所拟于秋审时区别实缓基础上亲自拟定“私铸大钱案内为首及匠人问拟斩候之犯,无论钱数次数,均著入于秋审情实”(31)。
尽管清廷加重对私铸的打击,但大钱的使用仍不理想,市面上多将其按面值打折使用。清廷不得不动用官方力量强制使用,甚至不惜使用严刑酷法。咸丰四年七月初六,清廷下令凡有将当百以下大钱(当百以上大钱已经下旨停铸)不遵钱面数目使用,妄行折减者,拿交刑部治罪,并著刑部速拟罪名。七月初十,刑部遵旨奏加等严定私铸大钱罪名并奸商阻扰钱法从重治罪折,咸丰帝著照所请:“嗣后私铸当百以下大钱人犯如系为首及匠人,数至十千以上或未及十千而私铸不止一次者,即于斩候罪上从重请旨即行正法。其私铸仅止一次为数又在十千以下者,仍照前拟,定为斩候,入于秋审情实”。“至为首阻扰任意折算之商民人等即照所拟杖八十、徒二年,再加枷号两个月;为从杖六十、徒一年,枷号一个月。”同时令户、工二部提高大钱质量。虽然如此,大钱使用仍陷入壅滞,清廷为此于同年八月下令再铸制钱,与大钱相辅而行(32)。据崇实所记他于咸丰四年四五月间,实署户部左侍郎,“彼时都中之困莫过于当千当五百之大钱”,甚至有人每月捐铸大钱,“名为报效,其实暗中射利”。他在被皇帝召见时即痛陈其弊(33)。可能考虑到当五百、当千大钱使用过于困难,清廷于咸丰四年将其停铸。咸丰五年(1855),又奏准宝泉局停铸当百、当五十大钱(34)。
即便如此,大钱使用仍困难重重,清廷于咸丰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谕内阁,批准惠亲王、恭亲王所拟《钱法亟宜整顿酌拟章程》五条,对阻扰当十大钱使用或因大钱加价者,初犯枷号,再犯发极边烟瘴充军,遇赦不赦。对私铸罪犯,除按例办理外,还将该犯财产全部入官。并著巡防王大臣、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出示晓谕,务期家喻户晓(35)。
据档案,自咸丰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阻扰当十大钱之犯归巡防处办理。同时巡防处声明到案被告悔过情愿行使者即当堂开释,如坚执挑剔初犯予以枷示再犯拟发极边烟瘴充军,奉旨允准。据巡防处统计,自咸丰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初九日,巡防处共审理大钱案件五十八件。《京城巡防处档案》存有此五十八件案件的案由。其中到案即肯行使免其议罪者共四十三起;不肯行使初犯予以枷示者共六起;咨送宗人府会同刑部办理者一起;劄交步军统领查办者共四起;劄交顺天府查办者共三起;劄交北城御史查办者一起(36)。
从案由可知,拒用大钱的情况出现在商品买卖、还帐、交房租等多种场合,但以买卖为主。这些案件一般均由须接受钱文的一方(被告)拒绝使用而引起支付方的控诉。也有因使用大钱增价而招致控诉。当然,某些涨价案件中没有原告,也被拿至巡防处审办,说明官方对此类案件主动介入。控诉的地方包括步军统领衙门及其所辖之各旗营、北城察院、顺天府所辖之宛平县以及巡防处。由于步军统领衙门所辖兵丁遍及京城内外,故百姓多往其所辖兵丁处喊告。步军统领衙门所辖之各旗营并无收受词讼的权力,正常情况下他们应将词讼送到步军统领衙门处理。但此处,各旗营均直接送巡防处审办,而未交步军统领衙门转解。其原因当为此时大钱案件不论罪之轻重均归巡防处审理,步军统领不能参与,直接交巡防处显然更为快捷。
巡防处接到案子后,多半自行审办,但也有些交与其他衙门审理。例如,涉及皇族的案件送刑部会同宗人府审办;有一个案件讯明非大钱案件送至大兴县审办;有些案件在巡防处控告,但原告皆顺天府人,故均送顺天府“就近”办理;有些则并非大钱案件,故送回步军统领衙门审理。另外,一些涉及斗殴的案子,不论打人者是原告还是被告,均据《大清律例》给与了相应的惩处。
上文已经说明,巡防处对大钱案件,只要案犯同意使用大钱,就可以无罪释放。显然,迫于权威,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同意使用,但也有坚决不用而被拟枷示者。不过,如果是因使用大钱而增价的,则不管情形如何,均给与惩罚。由于再犯者按新奏之例将发极边烟瘴充军,这在清代是极为严厉的处罚,所以巡防处所审案件中无一人再犯。按巡防处在奉旨裁撤之后奏请大钱案件仍归地方官管理的奏底所陈,到咸丰五年五月份后,阻扰减少,大钱可冀流通。
根据《京城巡防处档案》的一份奏底,大钱案件归巡防处办理;在巡防处裁撤之后,大钱案件仍归地方官管理。即此后凡京营兵丁拿获者送步军统领衙门办理;五城巡役获案者,送五城御使办理;由顺天府地面巡役获案者送顺天府办理。遇初犯之案即由各衙门照章发落。所有再犯之案仍照例即由各该衙门迳送刑部办理。其有牵涉宗室觉罗者应由刑部会同宗人府审办(37)。据此推断,巡防处裁撤之前是京师大钱案件惟一的审判机构。不过,笔者认为,实际执行中可能并没有照此办理,五城察院也审理大钱案件。
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五十八件案子中,没有一件是由五城察院呈送的,而且顺天府及其所辖的大兴、宛平二县也只有两件。尽管从衙门的空间分布和所辖兵役来看,五城察院接受呈词数量远远低于步军统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至于只有一件。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五城察院对这些案件自行审结。因为如按巡防处裁撤后的奏底推断,五城察院当将大钱案件送至巡防处处理,但档案里惟一由五城察院所送的案件也被巡防处拒绝审理。此案中,吕魁告吴德不肯收使大钱。原告吕魁先在北城控诉而后又到巡防处呈告,巡防处居然以其在北城控告为由札北城察院审办。巡防处所持理由是“此案该原告在北城察院控告有案”。这一理由显然承认北城察院可以对此案进行审办,否则将会追究其未及时呈送之责。
同样,顺天府亦未见呈送。当然,顺天府接受控诉的可能性较小。巡防处将两个案件札顺天府就近办理,并特意强调二位原告分别来自顺天府大兴、房山二县。巡防处的解释是此二案送顺天府可以就近办理。但从衙门的空间分布上看,巡防处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除房山县外,其余三者衙署(顺天府、大兴县、京城巡防处)均在北京内城,且顺天府和巡防处相隔不远。若说房山县民札顺天府饬房山县就近办理,还可以成立;大兴县民的案件交顺天府“就近”办理则十分勉强。笔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顺天府属大钱案件仍按常例,即顺天府属民人在顺天府所属地方犯罪,仍由顺天府或其所辖衙门办理(38)。档案中有两个案件由宛平县送巡防处,但没有解释原被告住在何地。另外有一案系大兴县民在巡防处喊告,巡防处也予以审理。此三案极有可能发生在京城,故京城巡防处予以结案。
三、京城巡防处与京师审判制度的关系
由于特殊的军事环境,清廷赋予京城巡防处一定的审判职能,使得京师审判制度发生变化。对于涉及军事或其他相关的刑事案件,京城巡防处拥有审判全权。这样,京师的二级审判机构在原有的户、刑二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从审判管辖来说,京城巡防处实际上是分担了部分原属于刑部的职能。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清廷将此类案件归军事机构管理,有其合理性。通过对京城巡防处案件职能的分析,不难发现,巡防处依然遵循清朝的审判制度,如按照律例拟律,将重要案件及奏交之案上奏,对徒、流、军、遣人犯的判决和执行均和刑部一致等。其中最为关键的对死刑的判拟,和刑部并无二致。至于大钱案件,大部分实际上都无关罪名,由京城巡防处审理,且将审判权凌驾于步军统领等衙门之上,则与清代京师审判制度多有不合。这从侧面反映出清廷在财政上的困境以及当时大钱流通不畅的事实。
至于当时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认为巡防处勾捕过严,有无辜死于西市者,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先对巡防处所审案件作一个整体上的统计。据巡防审案处统计,自咸丰三年九月十三日起至咸丰五年五月初七日止,巡防处审理案件共计三百五十五件,涉及人犯七百七十九名口。其中,凌迟枭示、斩枭、斩决、绞决人犯一百人,监候一人。笔者试据档案将罪犯人数和处理情况整理成下表(39)。
表1 巡防处所审案件处理方式及人数统计
处理方式 人数
所占比例(40)(%)
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19 2.44
斩决、枭示示众
20 2.57
斩决60 7.70
绞决 1 0.13
斩监候 1(许城 咸丰四年 朝审勾决) 0.13
(死罪总数)101 12.97
发黑龙江 44 5.65
发极边烟瘴充军2 0.26
流罪17 2.18
徒罪55 7.06
枷号31 3.98
杖责56 7.19
递籍77 9.88
毋庸议保释235 30.17
送刑部审办 82 10.52
递解查办 79 10.14
合计
779 100
由上表可知,巡防处所审之案犯,有近13%被判死罪,同时至少有30.17%被无罪释放。考虑到递籍、送刑部审办、递解查办者中,也有无罪之人,总的无罪人数当超过1/3。
再看案犯的拘捕途径。据档案,巡防处所审涉及谋反的案件由兵丁拿获者占绝大多数。清廷自咸丰三年五月起,加强了对京师的治安管理。咸丰三年十月,清廷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等认真盘诘,严防太平军假扮难民入城(41)。咸丰三年十一月,步军统领衙门兵丁在客店拿获来京探信之太平军人员。咸丰帝得到奏报后即日谕令顺天府、五城派人对京内外各客店不动声色地严行盘查,如有来历不明或形迹可疑之人,立即连同开店之人一并拿获(42)。京城巡捕人员除如平时那样对有伤痕的人予以盘问外,还对留有长须或是服装怪异者予以盘获,对难民的防范也更为严格。在当时形势下,查拿叛逆之事要影响平民的生活是在所难免的。
如咸丰三年十二月,张瞬、李幅、陇贵、万得福因肩上有圈,刘汰因生疮头上没有发辫,陇贵同时有木莲蓬,即被步军统领衙门兵丁拿获送巡防处审理。巡防处讯得此五人均系轿夫,湖北人,抬送越南陪臣贡差进京。张瞬等四人肩上之圈皆因生疮用针刺血而成,刘汰确因生疮头发未齐,陇贵所买木莲蓬是作为烟袋别子使用,均无为匪不法之事。巡防处拟将此五人抬送越南陪臣出京后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具奏允准(43)。咸丰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山东道御史奏请嗣后遇有发长及寸之人,立即详细盘诘(44)。
从上不难看出,京师各衙役、兵丁拿人范围十分宽泛。另外,也有利用太平军诬陷他人者,如上文提到的许城。根据上表巡防处案件处理的统计,有相当多的疑犯送到巡防处后都无罪释放,由此可知京师各巡捕衙门及巡防官兵相当卖力,所拿获之人至少有30.17%是无罪的。换句话说,各衙门送巡防处之案犯有相当多无辜者是毋庸置疑的。
京师官兵及各衙门捕役为了避免遗漏,将更多的人送往巡防处审理自在情理之中。那么,巡防处的审理又如何呢?能够使无辜者死于西市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巡防处拟律不当;一是巡防处逼供,致使无辜者妄供。就前者而言,我们不必怀疑巡防处审案人员对律例的精熟。上文所举案例表明巡防处是按《大清律例》拟律的。例如对杨起信的审判,依据的律例是“乞养异姓义子为嗣”,在杖罪上加等判徒一年的,而这是户律里的内容(45)。再如许城一案,巡防处将其拟斩监候,《大清律例》的例文为:“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拟斩立决,未决者拟斩监候,俱不及妻子家产。”(46)
不过,尽管巡防处的拟律水平不成问题,但它可能会在明知律例的情况下加重处罚,将罪不致死之人拟死罪。前文就有不少案件,巡防处在律例基础上加重拟律。一般情况下,巡防处所拟死罪都与太平军有牵连。由于参加太平军属叛逆重罪,对于参加太平军并且杀过人的罪犯,其处罚往往非常严厉。
《大清律例》对于叛逆重罪,处罚非常残酷:“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已未行,皆凌迟处死。”如果系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若谋而未行,为首者,绞;为从者(不分多少),皆杖一百、流三千里”(47)。对于谋反谋叛之亲属,也有非常严厉的惩罚。但清代律例并不严谨,往往有许多具体案子并无律例可直接引用,需要比拟。即便谋反、谋叛这样重要的律例,也弊端百出。在谋叛律下,嘉庆五年(1800)例规定:“谋叛案内被胁入伙,并无随同焚汛戕官,抗拒官兵情事,一闻查拿,悔罪自行投首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薛允升指出:“反逆案内,此等被胁入伙之犯,应否一体照办,并无明文。”而更加麻烦的是,在“犯罪自首”律下,乾隆五年(1740)定例:“被掳从贼,不忘故土,乘间来归者,俱著免罪。”薛允升指出此二例“一免罪,一发遣,轻重相去悬绝,援引不无窒碍”(48)。
至于被胁后打仗伤人,律例更是没有明文。巡防处开始对被胁伤人者拟发黑龙江,但后来全部处死。一般此类案件关系重大,由于律例本身有缺陷,往往只能看当时皇帝的旨意。根据档案,巡防处对于参加(或被裹胁)太平军并且打仗杀人致死者,往往都拟以死罪。到后来,即使被裹胁打仗伤人也拟以死罪。如果只是被裹胁而未打仗,处罚则较轻(49)。巡防处对此类死罪的审断,拟律时一般都未引用《大清律例》,而只是说某犯“应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有时是凌迟处死枭示或斩首枭示)。咸丰帝给各统兵大员的谕旨中也常常提到“军法从事”。咸丰二年(1852)十月十二日,令徐广缙对迁延观望、畏缩不前、贻误战机之带兵之员,即用皇帝所赐之遏必隆刀军法从事。十一月十五日,再次著徐广缙将追剿不力、临阵退缩、坐视不援之将领“一面奏闻,一面以军法从事”(50)。按照皇帝的意思,照军法从事,应当就是指即行处死。巡防处拟定死罪人犯所说“应照军法从事”,当指即行处死,具体而言还有不通过刑部复核的意思。其实即使按律例拟律,这些人也该死罪。如果案犯所供情节没有错误的话,巡防处将这些人按“军法从事”是合乎律例的。之所以不按《大清律例》拟律,而称按军法从事,可能因为巡防处本身是一个军事机构。
不过,有时巡防处将不承认的罪犯仍然拟以死刑。咸丰三年十月,巡防处审讯杨二等人。杨二供郑大曾经被贼裹胁后又逃回,今又起意投贼。但郑大并不承认曾经从贼,只承认杨二抢火药要秦五托他照应。巡防处仍认为杨二供词确凿,“未便因其(指郑大)坚不承招,致逃显戮”,将郑大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该案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51)。这里将郑大拟以死罪证据并不充分,巡防处的意见亦表明判郑大斩刑有避免漏网的因素。
但总的看来,档案里巡防处加重拟律主要针对死罪以下的案犯,对死罪的拟定仍然相对谨慎。其实,更加严重的惩罚常常来自皇帝本人。有时皇帝在接到奏折后即对案情甚至惩罚作了判断,如步军统领衙门奏送拿获从逆奸细一案,皇帝在咸丰三年十月十一日朱批:“着巡防王大臣速行严讯正法”(52),而不是惯常的交巡防王大臣审办。有时候皇帝对巡防处拟律不满,要求加重处罚。咸丰四年正月,绵愉等审拟石宝山被胁代买火硝一案,石宝山虽被胁代买火硝两次,但仅止引路,并未打仗杀人,“应于斩罪上减一等,发黑龙江给兵丁为奴”。咸丰帝见到奏折后大怒,十七日朱批:“石宝山代买火硝,情节尤重,岂能仅科以指引道路,究与甘心代买火药者有间?试问火硝何用?与火药何所分别?又岂能以并未打仗为从宽之据?愚民无知,从贼杀人尚迫于不得已。甘心代买,心迹背乱已极。石宝山著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53)
再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绵愉等奏报审拟被敌裹胁打仗伤人之陈敬汶等一案,因陈敬汶、李春业被太平军裹胁打仗伤人未死,拟于斩罪上减一等,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被胁打仗伤人之犯,一般均是被太平军裹胁,以前都是将其发往黑龙江。咸丰帝却认为:“该犯等或连伤两人,或只伤一人,是该犯用枪刀砍扎,实系有心致死,并非出于无奈。且仅据逆供伤而未死,焉知非避重就轻?即使当时未死,贼去后焉知不已殒命?著再详讯定拟具奏,以昭军法而归核实。”(54)
咸丰帝对陈敬汶一案的朱批,使得日后巡防处凡遇被胁打仗只要伤人者一律拟以死罪。而这一决定,不久就遭到官员的反对。第一个就是刑部左侍郎罗惇衍。继陈敬汶案之后,又有四起打仗伤人之案犯被拟死罪。作为京城巡防处成员,罗惇衍觉得情罪未当,奏请“将被胁打仗、伤人未死之犯,照原办发遣”。结果此折引来咸丰帝的严厉批评,于咸丰四年四月十三日谕内阁对罗惇衍传旨申饬。咸丰帝认为:“若该犯等如果实有冤抑,罗惇衍亦系巡防大臣,即不应随同画稿,何竟待数月之后始为此奏?又称李春业、尚克明、李四儿、郑帼华四案,皆伤人未死,亦从严照陈敬汶一案办理。是该侍郎以此四案之拟结,均照陈敬汶案办理,情罪多有未当。如果属实,该侍郎又何不于定案时单衔具奏,据理建白?且既以该犯等不当立正典刑,又何不随时奏闻?俟有四案之多,数月之久,始行入奏,假使死者果有含冤,已无救矣。而罗惇衍平日毫无定识,徒好虚名,已可概见。至所称屡怀是念,欲言而止者再三,尤不成话。试思身为大臣,秉心如果忠正,又有何避忌而不言耶?”(55)罗惇衍作为巡防处人员,没有及时奏请,可能有其原因。而咸丰帝不仅拒绝减轻惩罚,反由此对罗惇衍的为人严厉抨击。
咸丰四年五月中,京师降雨稀少,清廷因“清理庶狱,冀可感召天和”,即令刑部和顺天府将现审案件逐一清厘;对于实有冤抑者,务当悉心推求,即予平反(56)。趁此机会,兵部右侍郎王茂荫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奏,认为太平军将裹胁良民加以烙印,且各审判衙门严刑逼供,故被贼裹胁杀伤兵丁之犯,其中亦或有可矜者,请从缓定拟。咸丰虽下旨对刑讯者予以纠查,但不同意对被胁人犯从缓定拟,其理由是他自己对巡防处所拟死罪人犯“权衡至当,其实系甘心从逆之犯,断不能为之曲宥,如系愚民被胁,原未尝概予骈诛,亦非以烙印为凭,定为从逆,遂置重典。乃该侍郎辄请从缓定拟,试思执法贵在持平明慎,期无留狱。若使辗转迟延,案多积压,转非清理庶狱之意”。显然,咸丰对裹胁杀人犯当中可能也存在可矜者这个问题予以回避,而以案件不可迟延积压为由拒绝了王茂荫的请求。王茂荫在奏折中承认“曾伤官兵者照律论死”,“原非法之过严”,但由于官不能护民,故请皇帝对被胁人犯暂缓定拟(57)。也就是说咸丰帝下旨对被胁伤人之犯处以死罪也不违背律例。
按清制,常规情况下只有皇帝才有权力使死刑发生效力。京城巡防处所拟死罪人犯,全部经过皇帝的核准方可执行。如果京城巡防处拟律有误的话,皇帝可以驳回。只不过由于当时形势特殊,未见有皇帝将死罪人犯减等的。如果有无辜者因拟律有误而被冤杀的话,更大的责任承担者应是皇帝本人。而在清代,皇帝本人拥有最高权力,拥有超越《大清律例》的杀人特权。何况,参与叛乱谋反之犯,按律例皆可拟死罪。清廷将被胁之犯区别对待,更多的是出于形势而非律例的考虑。
至于严刑逼供,在清代本来就是合法的;不过,清代对刑供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涉及到谋反的案件,审案者往往不顾及律例。在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的奏折中,兵部右侍郎王茂荫提到:“闻各处拿获形迹可疑人犯,先自严讯取供,熏以香烟,往往有实未杀伤官兵者,因熏急难受,又不知杀伤官兵之必死,遂亦妄供,迨至辗转交审,前供难改,因而诬服。”(58)王茂荫指的是各衙门送巡防处之前的审讯有逼供情事,从而导致冤狱。咸丰帝下旨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是巡防处审案时并未刑讯(59)。至于其他衙门是否有刑讯逼供,因无材料故无法判断。但王茂荫的奏折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巡防处档案中亦可见蛛丝马迹。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巡防处在审拟李伏一案的奏折中提到对李伏“连日熬审,加以刑吓”(60),可能就是严刑逼供的另一种表达。
故巡防处所拟死罪案件中,很可能有无辜者。但京城巡防处仍在清代制度范围内运作,其审理案件程序,基本上与刑部一致。而且即便是刑部以及其他审判机构,一样存在刑讯逼供或是审判时受到皇帝的干涉,何况涉及叛逆的案件,皇帝常常超越常规。
四、小结
咸丰五年五月初十日,清廷因太平军已被消灭,下旨裁撤京城巡防处(61)。此后,京师之审判制度仍循旧制。从长远看,京城巡防处给京师治安和审判制度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即便太平天国运动对清代司法制度有所影响,也是在清朝原有的轨道上进行。
太平天国运动破坏了清朝的审判制度。为了平息叛乱,清廷在各地施行“就地正法”之制。本来,“就地正法”并非新鲜事物,只不过清廷意料不到太平军被扑灭后,自己已无力将死刑之审判恢复正常。而京师作为帝都,其政策则谨慎得多。据当时人的记述,早在咸丰三年二三月间,京师就因太平军军势甚炽而人心惶惶(62)。但清廷仍只是加强原有的治安体系,至于审判之制则仍如往常。直到九月在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的情况下,京师审判制度才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皇帝始终控制着生杀大权。与外地相比,清廷在京师的政策尽管相对谨慎,但仍有臣子力劝皇帝慎杀。清廷在京师的特殊政策当与其独特地位有关。
京城巡防处的设立,给京师的审判制度兴起一些涟漪。出于战时需要,清廷将涉及叛逆的案件归巡防处审理,实际上分担了刑部的部分职能。尽管时局艰危,巡防处的审判仍遵循清朝制度。尤其是对死刑的审判,尽管多按“军法从事”,但仍需得到皇帝的批准方可生效,和刑部或三法司所拟立决之犯相同。甚至其所拟定的斩监候,也一体归入朝审办理,更是和平常完全一致。尽管巡防处很可能有因刑讯逼供而冤杀无辜之人,但毕竟与外省先斩后奏或是边斩边奏式的处决方式有天壤之别。在太平天国北伐军败局已定、巡防处事务日少的情况下,清廷又令其审理大钱案件,可以称得上是违反常规。这从侧面反映出清廷的财政困境,也说明巡防处的审案效率较清廷原有的步军统领、五城以及刑部要高。这一特殊机构,在军事危机消失之后很快被撤销,京师的审判制度仍如往常。
咸丰帝虽然对参与叛乱的罪犯处罚较严,但清朝法制的诸多传统,仍然得到传承。在京师少雨的情况下,他仍如往常下旨清理刑狱。虽然有些按律例罪不致死之人可能因为刑讯逼供或皇帝本人加重处罚而死于无辜,但他们均经过审讯而且经过皇帝的批准。而按清制,在常规情况下,皇帝是惟一可以使死刑生效的人,同时也是有权超越律例杀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尽管“圣意”已明,还是有大臣上奏对皇帝加重处罚表示反对。他们虽未能说服皇帝,至少也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两年中,巡防处所拟的死罪也就一百人,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各路巡防官兵在京畿地区拿获的。用咸丰皇帝自己的话说,死罪人犯是“权衡至当”之后才杀的。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运动对京师审判制度影响甚微;京城巡防处对案件的审理大体上遵循了清朝制度。而且即便有所影响,就如外省实行的“就地正法”之制一样,也是中国内在传统的延续,而缺乏新因素。在京师,由于清廷控制力更强,“就地正法”亦不存在。换言之,清廷并未改变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承袭。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传统制度有相当的韧性。即便在19世纪50年代,清廷处在内外交困之际,种种内外压力也远不足以推动清廷进行司法变革。直到庚子之役,清廷败于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廷不仅实行“就地正法”(63),而且马上宣布实行“新政”,改革司法制度。
注释:
①《京城巡防处档案》全宗,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部分内容已经发表。
②有关就地正法之制,请参阅: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218—220页);李贵连《晚清“就地正法”考》(《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页。
④梁义群:《清廷京城巡防处与太平军的失败》,《济宁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李惠民:《太平军在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⑤以往的研究者多关注太平军北伐,基本没有涉及京城巡防处的审判职能,如赵蕙蓉:《太平天国北伐军对京师的冲击与影响——纪念太平天国北伐失利130周年》(《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梁义群:《清廷京城巡防处与太平军的失败》(《济宁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梁义群、丁进军:《清廷京城巡防处与太平军北伐的失败》(载河北、北京、天津历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1—263页)。
⑥关于清代京师地区审判制度,详见胡祥雨:《清前期京师初级审判制度之变更》,《历史档案》2007年第2期。大体而言,乾隆以后京师初级审判在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察院、内务府、八旗都统、佐领等处。轻罪(笞杖)案件,五城和步军统领衙门等衙门均可自行审结。徒以上案件交刑部审理,称现审案件。各衙门所审案件如涉及内务府所属人员(上三旗包衣、宫女、太监),轻罪则交由内务府审理,徒以上案件一般仍由刑部审理。涉及皇族人员之案,不论罪之轻重,一般均由宗人府会同户(田土案件)、刑二部审理。各衙门送交刑部之案不拟律。民人徒、流人犯,由顺天府定地发配;军罪人犯由兵部定地发配。系旗人折枷。监候者入朝审。其他与各直省大体类似。
⑦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7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7—218,312—315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95、608、609页。
⑩《文宗显皇帝实录》,《清实录》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105,第591、594、592、597页,卷106,第622—62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7、75、216页。
(11)成琦:《主善堂主人年谱·巡防纪略》,转引自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552页。
(12)成琦:《主善堂主人年谱·巡防纪略》,转引自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551页。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第6页。
(13)《京城巡防处档案》第2卷,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4)《文宗显皇帝实录》卷99,《清实录》第41册,第444—445页。
(15)《京城巡防处档案》第6卷,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2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95—297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6—178页。
(18)(19)《京城巡防处档案》第2卷,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页;《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27,《清实录》第4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页。
(21)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552—553页。
(22)“奖励东路军营出力人员”,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第28—29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72—174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29—330、403—404页。
(25)《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06,《清实录》第41册,第619—620页。
(26)“僧格林沁咨呈审录王自发供词文”,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75—176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2册,第77—78页;第13册,第347—348页。
(28)《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05,《清实录》第41册,第573页。
(29)相关背景可参阅梁义群:《咸丰朝三次财政危机述论》(《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0)《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13,《清实录》第41册,第760页。
(31)《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34,《清实录》第42册,第376—378页。
(32)《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35,《清实录》第42册,第387—388,391页;卷141,第475—477、488页。
(33)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540—541页。
(3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214,第498—499页。
(35)《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63,《清实录》第42册,第785页。
(36)《京城巡防处档案》第6卷,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7)《京城巡防处档案》第6卷,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8)关于顺天府审判职能,详见胡祥雨:《清代顺天府司法审判职能研究》,《明清论丛》第四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217—223页。
(39)《京城巡防处档案》第2卷,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0)采用四舍五入法,送刑部审办人犯当为10.53%,此处只舍不入,否则总数将超过100%。
(41)《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08,《清实录》第41册,第663页。
(42)(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09—212页。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3册,第443—444页。
(45)律文为“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见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卷9,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246页。
(46)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卷39,第1004页。
(47)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卷25,第555、558—559页。
(48)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卷4,第108页;卷25,第561页。薛允升对此二例参差之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参阅。
(49)李惠民在《关于太平天国北伐战役的战俘问题》(《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对此亦有分析,可参阅。
(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99—100页。
(51)(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第23—26,13页。
(53)(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2册,第293—294,637—638页。
(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4册,第3页。
(56)《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30,《清实录》第42册,第305—306页。
(57)(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4册,第391—393页。
(59)《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33,《清实录》第42册,第358页。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第12—13页。
(61)《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67,《清实录》第42册,第847页。
(62)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528—538页。
(63)当时留守的刑部奏请将京城案情重大之犯先行正法,得到批准。光绪二十七(1901)年五到九月,至少有56人经刑部审讯后即行正法,再行奏闻。《刑(法)部档案》(新整),《律例馆》第94号。
标签:僧格林沁论文; 咸丰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京师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许城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