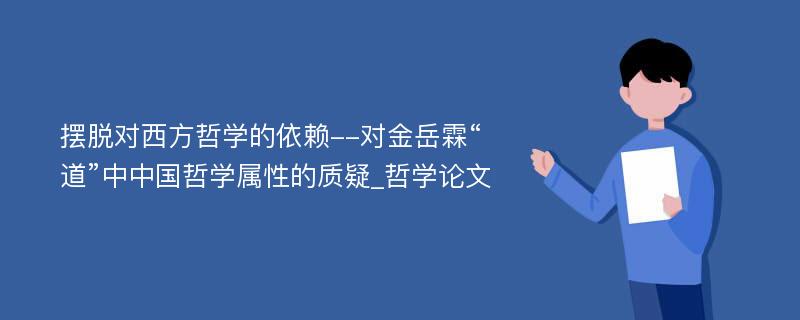
走出对西方哲学的依傍——对金岳霖《论道》之中国哲学属性的疑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窦论文,中国论文,出对论文,属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金岳霖因其专门研究纯粹哲学(形而上学问题)而享有崇高声誉和地位。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单列一章,评价金岳霖先生论道的体系,确认为其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注: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冯友兰同时又说,金岳霖的《知识论》和《逻辑》都是体大思精的著作,但它们都是知识论、逻辑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知识论和逻辑。)。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也论述道:“独惜金先生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又过于谨严,……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别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深入研究金岳霖先生的《论道》,特别是结合反思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是论”(又译本体论)以后,我们就难免会产生疑问:《论道》是“中国哲学”吗?
《论道》是金岳霖构建自己哲学体系之作,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纯粹哲学”类的典型作品。金先生自称《论道》属于纯粹哲学(元学)的范围,试图构造的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它的任务是把基本的概念整理出来,调和起来……使所有的基本概念成为一套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注:《金岳霖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他进而认为:“道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注: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页。);“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注: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他并指出,“道是式——能”,“式类似理与气,能类似气与质”(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具体事物是形式(可能)与质料的结合,而居式由能,莫不为道。他视“道”为“无极而太极”的历程,达到太极便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如”(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这里,金先生试图将所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转移为《论道》的一部分概念,以此来演示一整套概念的逻辑体系。“宇宙及其中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可能’到现实的历程。古今中外的大哲学系统,都以说明这个历程为主要内容。金岳霖的《论道》的内容,也是说明这个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有许多阶段、环节,金岳霖在《论道》中也都说明了。”(注:参见金岳霖:《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版,第436页。)金岳霖这种构造哲学体系的思路和方法正是依循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是论”,《论道》一书借助西方“是论”哲学的方法,只不过它的术语是中国传统的。换言之,金岳霖的《论道》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模仿“是论”,而且是在创造中国式的“是论”。除非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否则很难解读金岳霖先生的哲学体系——中国式的“是论”。正如冯友兰先生后来所说:“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消息传到北京,哲学界都感到很诧异……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的性质。试看金岳霖的《论道》不就是把许多概念摆来摆去吗?岂但《论道》如此,我的哲学体系,当时自称‘新统’者,也是如此”(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界,金岳霖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有着深刻理解的人物之一。早在1930年金岳霖就提出了“普遍哲学”是一种“空架子”的说法。金岳霖提出的“普遍哲学”即指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或者“是论”部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始注意“纯粹哲学”的研究。张东荪曾经从语言的构造以及逻辑、范畴等方面揭示了中西哲学的异同,但仅仅是一些散论,并且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冯友兰的“新理学”则是借助于西方“是论”的哲学方法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的形而上学”。如其自称,“新理学”是一个专门讲“真际”、“不著实际”的纯粹哲学体系。正如西方哲学的“是论”是运用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范畴体系,是纯粹概念的思辨哲学,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友兰也提出了四个形式的概念,即理、气、道体及大全,这四个观念,都是没有积极内容的,是四个空的观念。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四组主要命题都是形式命题,四个形式观念就是从四组形式命题出来的。冯友兰认为,提出和说明上述观点是真正的形而上学的任务。而到了金岳霖的论道体系,所谓思想不是历程而是所思的结构,静的思想没有时间上的历程,只有条理上的秩序。
如上所述,从张东荪、冯友兰到金岳霖,中国现代哲学家已经开始深入探索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一部西方传统哲学史是对“是论”的意义进行探求的历史,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则是不断地逼近“是论”的历史。
以金岳霖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哲学家试图以西方传统的“是论”的哲学方法来改造和创新现代中国哲学,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成功。为什么不能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来改造和创新现代中国哲学?这关涉到近年来哲学界对“是论”的突破性研究和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成果的出现。
“是论”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是将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或“是者”)作为范畴,通过逻辑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作为形而上学的一般性或理论性部分,“是论”常常用以指整个形而上学。“是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它的形式,即它是用西方语言中特有的系词“是”和“是者”作为普遍范畴来表达第一原理;其二是对逻辑的运用;第三个特点是其所展示的是一片与经验世界相脱离的纯粹概念的领域。质言之,“是论”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哲学家在创作“是论”哲学的过程中,在利用西方语言相对形式化的特征时加以改造而成的。这使得哲学范畴的意义从逻辑规定性方面得以表达,哲学范畴因此获得了逻辑的活力,靠概念自身运动得以展开。对“是论”的语言特征的研究,反过来也使“是论”这种特殊哲学形态的面目更加清晰,即它是靠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构筑起来的先天的原理系统。因此,“是论”是在独立的特殊的语言王国里展开的纯粹思辨哲学。
“是论”的基本特征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国哲学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的哲学,是西方特有的哲学形态。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质疑“是论”特征的形而上学,这无论是从中国哲学的起源还是它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可以证明。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探索也许要依靠对哲学本身的反思,但有一点相当清楚:比起西方传统哲学纯粹思辨的“是论”,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中国哲学更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和“生活世界”。也正由于此,黑格尔才对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曾经是对那片超越于经验领域的研究,那么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更多地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上升到道的境界。因此,无论是金岳霖的“论道”还是冯友兰的“新理学”,那种用西方特有的哲学形态“是论”的方式来建构和创造的中国的现代哲学,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哲学”。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追问,如果说“是论”就像金岳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普遍哲学”,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模仿和依傍它来建构和创作现代中国哲学呢?对此我们只能诉求于西方哲学史,来看一看“是论”是否是一种“普遍哲学”,或者说,“是论”究竟是不是西方哲学的永恒形式和唯一形态。
由柏拉图肇始的西方传统的“是论”哲学,在被黑格尔推上“绝对理念”和“纯粹思辨”的顶峰后,开始崩溃。M·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中说,现代西方哲学的“每一种重要的活动都是以攻击这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注: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既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又使西方传统的“是论”哲学开始解体。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则从根本上对被西方哲学誉为“第一哲学”的“是论”发起了挑战。与绝大多数粗暴地“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同,胡塞尔从纯粹意识的分析入手,认为作为意向对象的那些范畴之呈现在意识中,不仅伴随着一定的意向指向的方式,而且是由意向指向的方式所决定的。在海德格尔那里,胡塞尔的思想更推进了一步,不再局限于意识的范围而是提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思考。这已经不仅仅要求范畴的意义的自明性,而且表露出对“是论”解体后建构西方新的哲学形态的探求。因此,任何试图以在西方业已没落和解体的“是论”哲学的思路和方法来重构中国现代哲学的做法,只能是没有出路的。
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主流形态的“是论”的解体,有着它自身深刻的原因。首先,虽然“是论”的思想方法在西方哲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因为它刻意主张有某种脱离经验世界的观念性的原理主宰着世界,这种世界观随着近现代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怀疑。其次,尽管“是论”也提到了人,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中人和自然界都被认为是绝对理念的外化,但这种外化是主体、主词逻辑地演绎出来的客体、宾词,于是这里的主体不是指真正的人和自然,而是指作为绝对理念的人和自然。最后,“是论”曾经是至高无上的最高原理,哲学的其他分支都根据它得到说明,现在这种“第一哲学”的地位遭到了空前的挑战。海德格尔曾提出过一种“基本本体论”,用以阐明传统本体论的来龙去脉,后来他甚至连“基本本体论”也不再提起,而是着意于探索新的西方哲学形态。因此,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主流形态的“是论”的解体并没有使西方形而上学或哲学消亡,反而促成了“现象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这既说明“是论”曾经作为一个阶段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形态而笼罩一切,也表明了“是论”非但不是西方哲学的永恒形式,更不是哲学的普遍形式。
综上所述,金岳霖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方式建构自己《论道》的哲学体系,而在中国哲学中不存在运用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或者说不存在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的“是论”。金岳霖可能意识到了中西方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差别,因此《论道》在构造中国式的“是论”时,用了许多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但金岳霖同时特别强调,虽然引用了诸多相同的名词,可是它们的意义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只能遗憾地说,金岳霖的《论道》不是“中国哲学”。张岱年先生在评论金岳霖的体系时就曾说过: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就连金岳霖本人后来也曾感叹: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体系中活了几十年,他是不容易出来的(注: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68页。)。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走出“是论”为标志。对“是论”的突破性研究,使得我们相当清楚地理解了传统的西方哲学,并明白了“是论”既不是西方哲学的永恒形式,也不是哲学的普遍形式。这就为我们探索哲学之为哲学乃至重写中国哲学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舞台。
标签:哲学论文; 金岳霖论文; 冯友兰论文; 论道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现代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