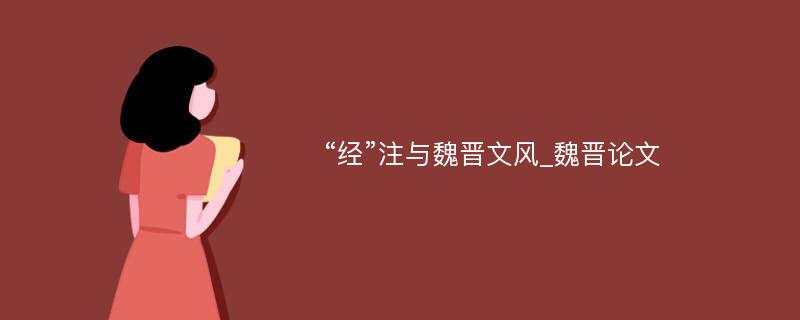
经注与魏晋论体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论体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6)02-0131-06 魏晋是文章大盛的时期,论体文在各种文体中最为引人瞩目,章太炎于魏晋文章中就尤重论体,推其为论家之准式,“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可以为百世师矣。”[1]论体文既是一种文章体裁,但同时也是魏晋玄学思想的主要阐释形式之一。 两汉经师通过注释儒家经典阐发经文大义,并纳入个体的思考,建立了包含阴阳五行等学说在内的经学思想体系。到了魏晋时期,何晏、王弼等人摆落汉儒的注经思路,通过对经典的重新注解建立了玄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经注与论体文虽属不同的文体形式,但二者共同构成了玄学思想的阐述形式,二者在思想表达等问题上存在什么样的异同之处?刘宁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2]本文拟就经注在主题内容、体例及思维方式上对论体文的影响略作考察,揭示二者的关联,加深对论体文的理解,并借以观察魏晋学术与文章的关系。本文所论的“论体文”指的是以“论”为名的单篇文章,并不包括以“论”为名的子书。所论的“经注”并非仅指儒家经典的注释,而是广义上的经典注释。魏晋以来士人对《老子》、《庄子》等经典的注释基本采用的是汉儒的经注体例,故本文在讨论时将其纳入“经注”的范畴。 一、经注论体文与魏晋思想的表达 经注与论体文属于不同的文体,二者差异十分明显。经注依经起义,随文注释,不论是章句还是传注等解经形式,都受到经文文本及经义的制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解经方式都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本身而展开,即便如西汉章句的过度引申与发挥,仍然需要假借经文的某句话或某一经义。即使注经者有自我树立的愿望,试图通过注经来发扬治学方法或建构思想体系,但由于经注的文体属性,他仍然不能脱离经文或经义。①相较而言论体文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文章体式,不必像经注那样依附经文,只要为围绕一个中心论题便可展开,更有利于作者的自由发挥。虽然经注与论体文的文体差异显著,但并不意味他们之间没有共通之处。 《世说新语·文学篇》曰: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3] 这段材料可注意者有两点:一、何晏见王弼所注《老子》,认为可与其论“天人之际”,也就是说“天人之际”是二人思想的共同主题,也是何晏注经与著论体文的共同主旨。二、何晏以《老子》注更为论体文,经注可以转化为论体文,二者在文体上必然存在一致之处。要寻找经典注疏与论体文之间的共通处,当对二者在说理上的特质做点考察。 经注的功能主要在于解说经文与阐发经义,经师注经或训诂名物,解说字词,使经文句意明畅易解。赵岐《孟子章句》就是如此: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则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则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为欲小勇,而自谓有疾。[4] 孟子以为周公虽知管叔不贤,亦必不知其将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爱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亲亲之恩也,周公之此过谬,不亦宜乎?[4] 赵岐的章句常以“孟子言”“孟子曰”“孟子以为”行文,这表明他在解说经文时是以合于《孟子》经旨为目的,而非借以阐释自己的主观见解。经师注经往往更注重解说经旨,对经典中的某一概念或某一命题加以阐释申述,呈现出很强的说理色彩。以《易》“乾卦”为例,卦辞曰:“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王弼注: 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阳也。阳,刚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至治,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也。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龙之为德,不为妄者也。潜而勿用,何乎?必穷处于下也;见而在田,必以时之通舍也。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人不妄动,则时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5] 王弼这段经注是对“乾卦”的总结,他将人事与卦辞结合,以人事论卦象,是典型的说理之文。何晏作《论语集解》杂以己注往往也是如此,如《里仁》篇云“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何晏注:“时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贫贱,此则不以其道得之,虽是人之所恶,不可违而去之。”[6]何晏通过注经来疏通经义,旨在理解经文意旨,而并不杂以现实考虑做过多的引申发挥。这些经注遵循了“以义解经”的阐释传统,意在探求经文蕴含的意旨与价值,其中许多是针对经典中的义理问题,或关注“天道”,或言“人事”,或探求“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经注与魏晋论体文十分相近。魏晋论体文是一种说理的文体,其往往关注的是较为抽象的义理问题,如延笃《仁孝论》辨析了儒家的“仁”与“孝”的观念,杨义《刑礼论》讨论的是“刑治”与“礼治”的问题,这确实与经注之辞很相近。刘勰也注意到了二者的关联: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7] 刘勰认为经注之辞,拆解开来看其实与论体文相近,二者是相通的,并且认为诸家注经可以作为论体的典范。刘勰所谓“总会是同”应当是就经注与论体文说理的特质而言,由于这两种文体都重义理,且与魏晋玄学抽象思辨的理论色彩十分契合,在魏晋时期成为了玄学思想的主要阐述形式。 虽然经注与论体文都是阐释玄学的,但无疑经注是玄学最重要的阐述形式,魏晋玄学的理论建构是通过经注完成的。王弼通过《周易注》与《老子注》一扫汉人阴阳术数之学,确立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体系;何晏《论语集解》援老庄入经,会通儒道;郭象注《庄子》提出“独化”思想,丰富了玄学的思想内涵。随着汉晋思想的变迁,《老》《庄》成为了玄学的理论资源,为士人熟习。 (裴)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8] (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8] (殷)浩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8] (王)济字武子。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老》。[8] 魏晋时期《老》《庄》成为士人基本的文化素养,其地位也逐渐提高,被士人视为经典加以学习。 魏晋时期儒学失去了独尊地位,玄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经典地位下降。从目前的研究看,儒学在魏晋社会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士大夫阶层中一些重要的玄学家仍然是儒家的信徒。②《三国志·钟会传》裴注载钟会自叙学习经历道: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9] 从这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儒家经典依然是士族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学也是知识层基本的文化素养。儒家经典的道德教化与经义是魏晋士人文化思想的基本底色,并未因玄学的兴盛而消隐。这不仅可以从士人对魏晋社会弊政的批评中窥探一二,更可从六朝人的文章观念中得到印证。六朝人论文章渊源常本之于儒经,刘勰认为: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7] 颜之推言: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10] 刘、颜二人虽对每种文体源流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文章源于五经。经为体,文章为用,其中包含了高下尊卑的文体意识。虽然论体文与经著分别属于“文章”与“著述”两个不同范畴,但经注地位在魏晋高于论体文,何晏以经注更为论体文就是经注品格高于论体的一个例证。经典注释与论体文二者是玄学思想的两面,二者构成了“体”与“用”的关系,论体文的诸多方面都体现出经注的影响。 二、经注的主题内容、体例对论体文的影响 经注对论体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注主题对论体文主题内容的介入、经注体例与论体文的写作方式上。 第一,经注对论体文主题内容的介入。刘勰将论体文视为阐发经义的文体,所谓“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因而他认为“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7]论体文中很大一部分的主题与经学关系紧密。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了“得意忘言”的主张,这一见解奠定了魏晋玄学的方法论基础,许多论体文其主题都是针对王弼的这一见解。如张韩《不用舌论》道:“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谓至精,愈不可闻。”[11]张韩的意见大约与王弼相同,王弼“得意忘言”的命题激起了士人著论思考这一问题。欧阳建《言尽意论》则是对王弼这一见解的反驳,“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11]此论开头“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王弼之说成为魏晋间流行之观点自不须言,由此可以看到欧阳建受到了王弼观点的刺激与影响,其论是针对王弼“得意忘言”之说的。一些论体文的表述也受到了“得意忘言”的影响,如曹羲《至公论》言“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文。”[12]“义”与“心”同“意”,“文”同“言”,曹羲的主张受到了“得意忘言”这一方法的影响。还有一些论体文是对抽象的经学概念进行阐释的,如纪瞻《易太极论》是解释《易经》中“太极”一词的所指,殷浩《易象论》是对《易经》“象”的问题加以阐释,与王弼注《周易》的“明象”篇有共通之处。殷浩《易象论》曰: 圣人知观器不足以达变,故表圆应于蓍龟;圆应不可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适。故虽一画,而吉凶并彰,微一则失之矣。拟器托象,而庆咎交著,系器则失之矣。故设八卦者,盖缘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11] 殷浩认为象可以反映世界普遍的道,“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因为道形之于器,化万物殊不相同,象不过是道的体现。这与王弼注《易》中“得象忘言”是一致的,王弼认为“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5]再如刘智《丧服释疑论》、成洽《孙为祖持重论》、吴商《难成洽孙为祖持重论》、成粲《嫂叔服论》、贺循《防墓论》、蔡谟《已拜时成妇论》、范宣《礼二墓论》及郑袭《难范宁论丧遇闰》等等都是有关“三礼”中服丧、丧礼、入葬等问题的讨论,他们观点的分歧往往也与经注有关,各家注经观点解释不尽相同,后人议论往往据以分别持论。如孙盛《太伯三让论》: 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郑玄以为托采药而行,一让也;不奔丧,二让也;断发文身,三让也。三者之美,皆蔽而不著。王肃曰:“其让隐,故民无得而称焉。”盛谓玄既失之,而肃亦未为畅也。玄之所云,三迹显然,天下所共见也,何得云隐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则高让可知,亦复不得云其让隐也。[11] 孙盛讨论“太伯三让”的问题是从郑玄、王肃二家的注经入手,通过辨析二家的观点进而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此论主题内容源于经著,论题的提出也是通过辨析前人注经的见解,其受到经学之影响可见一斑。 第二,经注体例与论体文的写作。魏晋注经往往通过对经文中的某句进行疏解,以阐明经旨大义。《论语》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何晏注曰:“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6]《论语》曰:“吾道一以贯之哉!”王弼注曰:“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5]可晏、王弼解经采用了经注体例,随文释义,对经文的某句进行集中解释,在阐释发挥时不像今文经师那样随意,而是紧紧围绕经旨。刘勰称毛苌训《诗经》、孔安国传《尚书》、郑玄释《周礼》、王弼解《易经》有“要约明畅”的特点,此点颇可注意。东汉中期之后古学复兴,治经倡行训诂通大义,重视博通,力求回到经旨理解微言大义。魏晋人注经正是在这一学术思路的延长线上展开,王弼注经讲求会通,也并做引申发挥。东汉至魏晋的治经一反今文学章句的繁琐,主张举大义,不做过多的牵涉发挥,经注便呈现出“要约”的特点;古文学治经提倡博通,魏晋人更以会通的精神注经,使得经义畅达明晰,是刘勰所谓的“明畅”。 这一解经体例影响了论体文的写作。论体文是以说理致思为特征的,在论述时往往张举纲目,标示中心论题,进而围绕这一主题加以论证阐释。如阮籍《乐论》立论言“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对乐的本质做出概括,再围绕这一论题展开阐释与论述。论体文条分缕析的篇章结构也受到了这种解经体例的影响,其开篇或各段都标宗立意,然后论证阐述,这与“以事解经”及“以义解经”的体例很相似。[13]阮籍《通易论》就有解经的特点,阮籍此论旨在说明天地万物的规则与《易》的道理是相通的,在文中最后总结道: 君子曰: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事业有所丽,鸟兽有所萃,故万物莫不一也。[12] 这段文字大体出于《易传》,旨在点明主题,这也是全文立论点。他的《通老论》曰: 圣人明於天人之理,达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体,审於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12] 这两段中分别讨论了《老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即“圣人”与“道”,我们对照一下王弼注《老子》来考察一下二者的联系。《老子》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王弼注曰: 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为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5] 《老子》曰“天地不仁”,王弼注曰: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5] 王弼注《老子》与阮籍的《通老论》有相近之处,王弼注解释“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主要围绕“妙”展开,释“妙”之含义,再言何以“无欲”以“观其妙”。阮籍是以“圣人”为论述核心,言“圣人”之特质,进而言圣人之治。王弼注“天地不仁”,解释何为“不仁”,阮籍言何为“道”。如果将王弼注文与经文分离来看,其行文表达与阮籍并无不同,阮籍之文也十分近似注经中阐释经义概念之辞,可以说阮籍的这篇论体文具有经注的特征。 三、注经的思维方式与论体文写作 经学对论体文的影响除了上述几个层面,最重要的是治经的思维方式对论体文的影响。汉魏注经方式的差异前文已述,王弼、何晏注经开创玄学,经注呈现出抽象、玄远的特点,如王弼注《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5]对“有”“无”的关系所做的是抽象的讨论,并不涉及现象和具体事物,这也影响到论体文,造成论体文玄远抽象的特征。阮籍的论体文中包含他对“天道”的认识,其《达庄论》云:“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12]他认为宇宙最初的状态是“混沌”,同时宇宙也是“阴阳不测,变化无伦”的。[12]《通老论》言:“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12]“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12]阮籍认为老子是“圣人”,能够体察天道与人事的玄理,自然万物互有性分,治化之道在明于性分,为无为之道。纵观阮籍的论体文,主题内容往往抽象玄远,《晋书》本传称其“发言玄远”,其论体文也符合这一特征,而这与何晏、王弼经注的抽象思辨是契合的。 汉魏注经常运用“正名”的思路,如王弼注《周易·乾卦》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5]王弼也是先辨析“天”“乾”的意义,进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再将二者会通。这一思路是汉晋人注经的基本思路,论体文在论述形式上受到这一思路影响,在分析问题时首先辨析名物,进而予以解释。如刘智《论天》: 日,太阳也。施温万物主,施光则阴以明,众所禀为倡先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阴也。禀照于阳,亏盈随时,有所禀受,臣卑之道也。 日尊,君象也;月卑,臣象也。晦朔之会交则同道,同道则形蔽。天道前为尊。臣由臣道,虽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由臣道,月掩日体,卑陵尊也。[11] 刘智这段论述先言“日”“月”之象,后申述二者象征关系,这一论述形式上仍然是与经注相似。阮籍作《通易论》与韩非子《解老》相近,都是解释经典,具有经注的特点。阮籍此论开篇即为《易》正名:“《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变经也。”[12]随后围绕这一判断展开对《易经》一书的讨论,“《易》之为书也,本天地,因阴阳,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易》之为书也,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极而致。”[12]这与注经的“正名”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王弼通过注《周易》为魏晋玄学的提供了“寄言出意”的解释模式,这一思维与解释模式对论体文的影响十分显著。王弼《周易略例》说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5]王弼将“尽意莫若象”的观点拋开,以“超言绝象”的姿态去寻求“意”,主张“得意而忘言”。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曰: 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放达,无为而自得,故极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14] 在郭象看来,“言”是为了“出意”,我们应“以言达意”,而不能拘泥于“言”。王弼与郭象的意思是寄旨于言,本以出意,故而“象”“言”的驳杂、抵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求其中蕴含的“意”“旨”。这一解释模式对于会通儒释道是十分重要的,如孙绰《喻道论》曰: 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圣有深浅之迹……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11] 王弼、郭象等人以为“言”“意”可能是不统一的,这就为“寄言出意”提供了可能,既然言意不统一,那就不能拘泥于“言”,而应寻求“意”。孙绰会通儒释即采用了“寄言出意”的思维方式,儒释的差异不过是表面的,“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理解儒释不能拘泥在字义的表达上,而要深入理解二者在本质上的共通性。玄学家通过注经开创的阐释模式与思维方法对魏晋论体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论题的展开与论述都是在这一影响下进行的。 魏晋是文体大备的时期,各类文体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文体在萌生、定型的过程中必然受到时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论体文也不例外。一方面,论体文在写作中标举纲目的写作方式与经注随文释义的体例具有相似处,在论体文中很多主题内容都是研讨经义的,甚至一些论题的展开都是从经典的解说入手。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家通过注释经典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论体文,如“正名”的注经方法影响了论体文的行文表达,而“寄言出意”等阐释模式与思维方法又成为论体文会通不同学说的重要工具。通过对经注与论体文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虽然二者文体形式不同,但是在思想表达上却有共通之处。对二者文体形式与思想表达上的殊趣还可以深入探讨。 刘宁先生指出魏晋经注与论体文在形式上的区别在于论辩内容的有无,经注“以直接阐发大义为主,很少针对分歧的言论进行辨析”,[15]而论体文则重视辨析群言,对分歧的意见进行论辩。二者体现的精神亦有不同,王弼、郭象创作经典注释是追求会通,嵇康、阮籍倾向于论体文的创作在于别异,注经与著论在思想表达上的差异由此可见。15除此之外,作为理论资源的经典注释是玄学之“体”,而论体文为玄学之“用”,二者在思想表达功能上亦有分工。经典注疏是玄学理论建构的主体,这自不待言。玄学的基本原则与思维方法是通过经注建立的,进而通过论体文拓展到思想学术及社会现实等各个方面。何晏、王弼与郭象等人注释经典确立了“以无为本”、“寄言出意”等基本原则与方法,论体文则以这些原则与方法来论述具体的学术问题,如刑礼论、养生论、乐论等,与此同时士人在借助论体文批判社会现实问题时也贯穿着这些玄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傅巽《奢俭论》、刘寔《崇让论》、王沈《释时论》及鲁褒《钱神论》等文章都是是针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其中的理论依据多与玄学思想有关,这些都是有待继续深发的问题。从对经注与论体文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学术与文章间不可分离的联系,也可以看到不同文体在思想表达上的影响与异同,对于魏晋文章的研究是颇有裨益的。 ①关于这一问题林庆彰、刘宁两位先生已有论述,详见林庆彰:《两汉章句之学重探》,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所主编《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汤用彤先生说道:“汉武以来,儒家独尊,虽学风亦随时变,然基本教育固以正经为中心,其理想人格亦依儒学而特推周、孔。三国、晋初,教育在于家庭,而家庭之礼教未堕。故名士原均研儒经,仍以孔子为圣人。玄学中人于儒学不但未尝废弃,而且多有著作。”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31-32页。闫春新以《论语》为个案,窥探汉晋以来经学的继承、并行、扬弃关系,我们从这一个案也可以看到儒家经典阐释的多元化,这与传统的经学衰落的印象是不大相同的。参见:闫春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焦桂美的《南北朝经学史》也揭示出南北朝时期经学之传播、接受状况,还原了这一时期经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期的经学并非如以往认识的那样衰落与式微。详见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