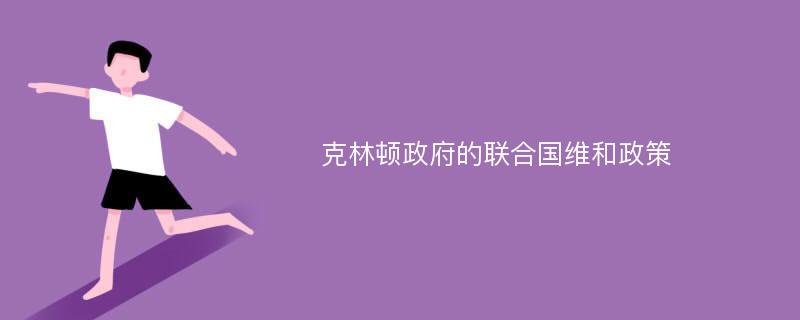
赵磊[1]2011年在《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文中提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义"到"坚定的多边主义",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陈素娟[2]2013年在《论冷战后美国的维和政策》文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安全一直是各国人民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国际维和行动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人们始终将目光放在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上,对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大国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政策与方针上有些忽视。实际上,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世界主要大国的维和政策对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大国,其维和政策的调整与实施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尤为重要。美国的维和政策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美国对联合国主导的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维和政策;二是美国自行制定的,经联合国授权,但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强制和平政策;三是未经联合国授权,美国单独实施的稳定行动政策。美国将强制和平政策与稳定行动政策都归结为维和政策,这正是美国维和政策的特别之处。简言之,美国的维和政策包括联合国体制内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和联合国体制外的单边维和政策。冷战后,美国的维和政策随着四任总统的更替而不断演变。老布什时期,美国奉行激进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其维和行动主要在联合国体制内展开。克林顿时期,美国一面实行有选择的联合国维和政策,一面实行有效的单边维和政策。小布什时期,美国则奉行消极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同时力主积极的单边维和政策。奥巴马上任后,主张灵巧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和多元化的单边维和政策。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不仅反映出历任总统的政治与外交政策,同时体现了美国浓厚的“单边主义”维和色彩。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维和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灵活性、实用性、矛盾性。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维和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与安全秩序。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表现,也是其国内各种因素与国际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随着国际维和行动的不断变化,美国的维和政策面临各种各样的新挑战。通过研究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可以了解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来源与理论依据。这对于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树立良好的国际维和形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牛纪涛[3]2000年在《克林顿政府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文中提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始于1948年。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争霸,自1948至1988年的40年间,联合国安理会仅批准了十三次维和行动。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大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并且从干预国际纷争发展到干涉国内冲突。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直接发起、推动和参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美国的维和政策直接影响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起伏变化。 冷战期间,美国没有正式的维和政策。冷战之后,国际冲突和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不断,美国参与的维和行动大大增多,布什政府开始评估维和政策。制定一个维和政策也成为克林顿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一届任期之初,克林顿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布什政府的维和政策。在布什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断扩大。克林顿政府亦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表现出以人道主义干预为藉口积极干涉国际冲突的态势。同时,克林顿政府制定PRD13(Presidential Review Directive 13)对维和政策进行评估,以进一步制定一个全面的维和政策。与克林顿的新干涉主义相对,新保守主义者以联合国维和行动在1993年初在索马里的失利为契机攻击克林顿政府的维和政策,进而攻击联合国。经过外交政策的大辩论,最终,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5月制定了美国第一份全面的正式维和政策PDD25(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25)。美国政府从积极的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转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实行有选择的、有所节制的政策。但美国积极干涉的政策没有变。在攻击联合国的同时,美国进一步扩大维和概念,刻意加强北约的作用,使维和超出联合国的范围。1999年3月至6月,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科索沃问题为由轰炸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美国领导的这次军事行动有意避开联合国安理会,却又不能够完全抛开联合国,最终美国还要以联合国的名义解决问题,使联合国处于尴尬境地。另外,美国还支持利用联合国维和行动处理对美国没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冲突,如东帝汶和塞拉利昂等地。为进行积极干涉,美国强调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从过去干涉地区冲突扩展到干涉国内的种族冲突。人道主义干预为美国进行积极干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宣传依据。 维和政策成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回 h eC且盈"ton一一L止】min豆st之一白山上且ons互一o且Icyfor互习eace马亡eepingD 战略…保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一促使美国采取积极于涉的态度。维和行动;二 亢 二 岩 二 二 二 箩 了 署 工gD 大国地位,为建立和维护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格局,继续扩大维和的概念。当l 二二糕二置盆二’””即“”“””’利”““””l。嘉二z器翼裟浩慕器默?2D 边”的辩论愈演愈烈。以共和党议员为首的国会强烈抨击联合国维和行动乃至 联合国本身,同时攻击克林顿政府的维和政策乃至整个外交战略。辩论的焦点D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但辩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美国冷战后外交战略的大辩论。回 二算罕二二二二二二声二篡篡z二二二二二二歼二了二二霎二言二二二袁篡嘉回 二二二夸二纂嚣z二二二二二兰二黑纂二二于大二尝二昔三二二二二蒙皋产;D 扬“美国价值与使命”’克林顿政府明确表示美国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目的 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外交战略的制定者们越来越明确的提出美国的D 第一国家利益就是做“世界的民主领袖”,确保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一即回 二二二工:二工二二二二霆二二二署二工二二i寡二轰皋工二二二吉了三二回 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并加强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强调 要在联合国和北约占据领导地位。I 以维护和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为战略目标,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具有明显实回 二工二孟二二嚣竿尹二森二二皋置蚤羹二二二三二又嚣孟二三玄7z器二>二回 二二二二::: i了艺二二二二二二厂:::/二二二纂二之芜歹治二二二,,弄D 但从根本上说’联合国的机制是建立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之上的,更符合多 极世界的格局,显然与美国日益表现出来的“领导战略”不相符。因此,美国回回 *;“冷落”联合国是其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冷落”归“冷落”,美国政府不会象国会新保守主义提议的那样,完全抛弃联合国。在许多方面,包括维和行动,联合国还是有一定用处的。美国政府强调使命感,大有“世界领袖,舍我其谁”的感觉,因此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国际战争、国内冲突都感到负有“维和”的义务。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经媒体报道后,美国政府在“道义’”上都必须做出一定的反应,但要做世界警察尚感力不从心。另外,美国要到处派兵,也难以说服国内舆论,在国际上也过于孤单。如果能够让别国分担兵力和财务,同时又保证美国的“领导”,美国何乐而不为呢?因此,美国选择在非?
刘铁娃[4]2017年在《中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较与合作空间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都有较大投入,但在具体的维和过程中,两国的侧重点、原则理念和影响力也各不相同。美国在经费、人员培训和设备供给方面投入更多,而中国在维和人员的派遣方面贡献更大,近些年中国也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以及重要岗位的人才培养和人员输送;在维和理念上,中国强调在尊重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坚持维和三原则,而美国通常会要求他国接受美国民主制度的原则,并对武力使用标准更为宽松;在维和议程的设置上,美国一直以来都有较大影响力,中国相对较弱。中美两国未来在维和行动及在联合国框架下介入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方面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因此,中美在维和问题上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扈大威[5]2004年在《预防性外交研究:从设想到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冷战后兴起的预防性外交的主张及其实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析了这个主张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把预防性外交主要限定为在国际局势总体缓和的条件下,通过大国多边安全合作而对地区冲突进行的国际干预和提前预防。预防性外交与国际法上的和平解决争端思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二战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冲突解决理论则为预防性外交提供了基本的学理论证。 在对当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本文系统回顾了预防性外交概念和定义的形成过程,介绍了预防性外交的两种基本模式。作为普遍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预防性外交的发祥地,本文对联合国开展预防性外交和冲突预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侧重对其机构调整的介绍。在区域安全组织层面,则集中介绍了在开展冲突预防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欧安组织,包括少数民族高级专员和长期任务团等专门的预防性外交工具。论文的第五章采用案例分析的办法,选取马其顿维和和卢旺达种族屠杀的事例,对预防性外交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的最后部分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预防性外交的可行性。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认为预防性外交是必要的,可行的,但也是困难的。预防性外交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多样性,不可能对它进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重要的是对它采取正确的态度,在实践当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还认为,9·11事件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国际安全机制处于低潮期,预防性外交的发展面临重重阻碍,任重而道远。
史晓曦, 蒋余浩[6]2016年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保护的责任”立场》文中提出综观克林顿政府以来的美国对"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变化和政策调整,可以看出:随着近年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已经在逐步改变其倡导的单边行动的外交政策,转而寻求在国际合作中维持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依然受制于其内政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实用主义考虑,依然是美国决策者的首要关注点,因此能否成为有效推进"保护的责任"发展的力量,尚需进一步观察。
陈鲁直[7]2001年在《美国与冷战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文中指出冷战结束期间及冷战后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急剧增加的时期,我们看到大量分析冷战后维和行动形势变化的材料,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形势中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冷战剩下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动向。很少有人把联合国维和行动面对的形势变化同美国冷战后的战略策略变化联系起来,本文拟就此略加填补。
牛海彬[8]2006年在《有限的合作:美国国会与联合国》文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主义范式轻视国内政治和国际制度等重要行为体。国际制度面临着从国家凝聚共识、获取支持的挑战。权力、合法性、国家利益与国际民主等是涉及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互动的重要变量。本文选取美国国会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文章在回顾美国国会与联合国之间关系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与联合国改革两个案例。文章主要采用国际制度理论和文本解读方法,试图理解美国国会在美国与联合国关系中的作用,深入认知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局限和改革。基于此,本文得出下述基本观点。美国国会拥有影响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权力基础,包括财政支持、条约批准、人事任命、偏好塑造等。美国国会在联合国形成、联合国宪章制定、联合国改革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财务运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例外主义、保守主义、分裂政府、党派竞争和部门利益是影响美国国会对联合国态度的主要国内因素。美国的实力地位赋予美国国会以工具主义态度看待联合国的特权。保守主义信念导致美国国会对联合国持怀疑主义的态度。例外主义情结促使美国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塑造联合国。美国国会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狭隘关注给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拥有合法性、成本分担、确认大国地位、树立全球规范等优势。因为这些优势,美国国会内主张美国脱离联合国的声音难以获得实质影响。联合国在维和行动、财政运转以及自身改革中的困难说明,它需要通过改革来消除会员国的疑虑。联合国改革的目标应是建设高效、民主、负责的全球性制度。
冯志明[9]2012年在《坎坷的民族和解之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短短三个月内,有将近一百万人被杀害。当时的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没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导致灾难性后果。卢旺达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实际上近代西方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种族分离政策早已埋下了卢旺达民族冲突的火种,而独立后卢旺达两届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使局势雪上加霜,并不断恶化,最终爆发了卢旺达大屠杀。大屠杀过后,卢旺达新成立的卡加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民族和解的措施,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卢旺达的民族和解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完全实现民族和解,由于长期积淀的民族问题,一时难以根除,因此其道路还十分漫长。本文通过分析,指出解决卢民族问题最核心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民族和解能否实现和巩固。
刘金质[10]1998年在《试论冷战后美国的干涉主义》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凭借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广泛实行干涉主义。美国通过政治干涉、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各种途径,力图把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推向全世界,以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克林顿称,为了建立一个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安全的新时代”,“美国必须抵制极端民族主义有害的诱惑”。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J]. 赵磊. 美国研究. 2011
[2]. 论冷战后美国的维和政策[D]. 陈素娟. 湘潭大学. 2013
[3]. 克林顿政府的联合国维和政策[D]. 牛纪涛. 外交学院. 2000
[4]. 中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较与合作空间分析[J]. 刘铁娃. 国际政治研究. 2017
[5]. 预防性外交研究:从设想到实践[D]. 扈大威. 外交学院. 2004
[6].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保护的责任”立场[J]. 史晓曦, 蒋余浩. 美国研究. 2016
[7]. 美国与冷战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J]. 陈鲁直. 国际问题研究. 2001
[8]. 有限的合作:美国国会与联合国[D]. 牛海彬. 复旦大学. 2006
[9]. 坎坷的民族和解之路[D]. 冯志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10]. 试论冷战后美国的干涉主义[J]. 刘金质. 国际政治研究. 1998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不干涉他国内政论文; 联合国论文; 美国国会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