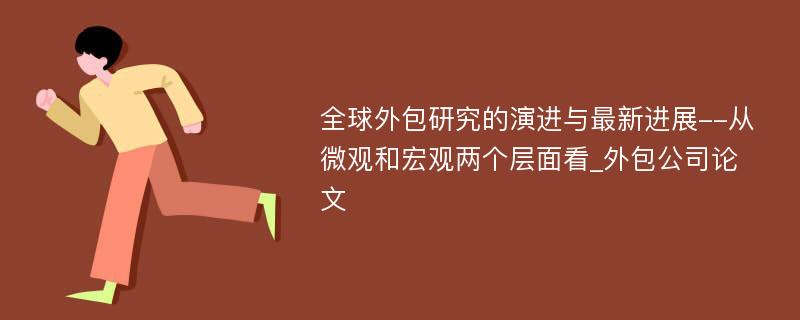
全球外包研究的演进及最新进展——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外包论文,视角论文,层面论文,最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11)03-0111-08
一、引言
对全球外包的研究兴于2000年,当年有200多篇以“外包”为主题的学术论文。2008年有超过1100篇学术论文讨论“外包”问题。具体来讲,在2003年以前,学者主要用“外包”一词来解释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新现象。但是,在最近几年,“离岸”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从2003~2010年的七年间使用率增加了14倍之多(从2003年的9篇以“离岸”为主题到2010年的142篇)。究其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离岸”一词更适于解释目前的国际经济活动,因为“离岸”一词不仅包括了外包行为,还包括了跨国公司对外包所采取的策略,它涉及了任何海外生产活动的转移(芬斯卓Feenstra,2010[1])。在2003~2004年间,以“外包”和“离岸”一词为主题的学术论文突然大量增加,这一现象可以由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来解释(曼昆 Mankiw和斯瓦格尔 Swagel,2006[2])。参与选举的候选人把当时美国的工人失业归咎于离岸外包,并宣称会推出企业税提案,旨在抑制美国公司进一步将工作外包到海外。此后,关于“外包/离岸”的研究就再也没有停止,而且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2000~2006年间,跨国公司的商业活动远比前几年发展得快。据统计,从2003~2006年的三年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每年的增速达到了15%,其中销售和出口的增长分别达到了15.575%和14.875%①。当跨国公司做外包决策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如下的选择:国内一体化、国际一体化、国内外包、国际外包,这些选择也是学者们讨论参与全球外包的企业组织形式时所涉及的问题。关于企业组织形式决策研究的发展主要基于产权理论和企业异质性模型。最初,我们也许会认为一体化面临着巨大的管理成本,但不存在合同中不完全信息所产生的摩擦,然而,安卓斯(Antràs,2003)[3]证明了事实上合同中的不完全信息也会在一体化公司中产生。因为外包中的发包商面临着搜寻配对成本,并直接面临合同中的不完全信息摩擦,接包商也可能面临“受制于人”(Hold-up)的问题。因此,目前的许多模型都是基于企业组织形式选择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发展起来的,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对此做详尽的讨论。
在企业异质性模型产生之前,国际贸易的研究视角集中在更加宏观的层面,即外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工资差距成为外包领域的研究重点。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重要变化,也就是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就业结构倾向于技术工人。于是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研究集中于解释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一变化。当一些可以很好解释这一现象的外包模型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却发现了近年来发生的新变化:自2000年以来,美国技术工人的相对就业也开始下降。而已有的外包模型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技术工人的就业也会下降。但是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8]对此做出了解释。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分析全球外包对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这样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外包文献都是在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发生的原因。然而,安卓斯和斯泰格尔(Antràs and Staiger,2010)[9]致力于解释其中的问题,他们证明了如果对中间品贸易征收适当的补贴和税收将会改进国际合约的可合约度,那么由合约的不完全性带来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同时,安卓斯和科斯蒂诺德(Antràs and Costinot,2010)[10]将外包与经济一体化相结合,研究构成外包的主体——中间品贸易的一体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从而拓展了外包研究的新视角。
二、微观层面:合约的不完全性对外包决策的影响
在全球外包决策的文献中,主要的理论分析框架有三种:一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动因;二是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动因;三是考虑交易成本的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本文重点讨论第三种,即研究当企业面对全球外包的经济环境时,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决策,以及全球外包中合约的不完全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这类文献首先由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2)[11]发展起来,并由安卓斯(Antràs,2003)[3],安卓斯和赫尔普曼(Antràs and Helpman,2004)[12]对此作了拓展,其理论基础是产权理论(格罗斯曼 Grossman和哈特 Hart,1986);哈特 Hart和摩尔 Moore,1990)和企业异质性模型(梅里茨 Melitz,2003)。
(一)不完全信息和外包决策
外包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组织形式决策。克莱因等人(Klein et al.,1978)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合约不可能写下所有要求,因此就会存在对合约收益的不清晰界定,从而在独立的买方与卖方合约关系中存在着机会主义和无效行为。
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把合约的权利分为两类:明确的权利和剩余的无法明确权利,并求解了在最优合约下如何分配无法明确的权利,即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式下不存在合约的不完全性所产生的摩擦。然而安卓斯[3]证明了在贸易环境下,这样的结论可能是不成立的。事实上,一方面在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式下,最终产品生产商面临着对零部件供应商的不充分激励;另一方面,由于中间品的质量在事前是无法证实的,因此在外包的企业组织形式下,最终产品生产商可能面临着被迫按合约规定的数量和价格购买质量并不满意的产品;如果最终产品生产商拒绝购买这些中间产品,那么零部件供应商面临不得不低于合同价格出售,或者返工生产等情况,因此面临着“受制于人”(Hold-up)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供应商专供某些中间品时更加明显。
此外,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1]强调了在一体化组织形式下,公司总部所面临的高管制成本问题,以及外包组织形式下的搜寻合作伙伴的问题。在他们的模型中,假设差异化产品具有固定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对于选择外包组织形式的公司来说,将要经历五个阶段的过程:进入市场,搜寻合作伙伴,生产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对收益讨价还价,生产并销售最终产品。在这个模型中存在两类稳定的均衡:所有企业参与一体化或者是所有企业参与外包。企业做出组织形式决策的时候遵循一个总的原则是:“企业利润为正时进入市场,企业利润为负时退出市场”(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2[11])。
(二)企业异质性与合约摩擦
随着梅里茨(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模型的提出,企业异质性的思想也被应用于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分析中。安卓斯、赫尔普曼[3][12]首先将企业异质性的思想应用到了外包的分析当中。
安卓斯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2)[11]模型从两方面进行了扩展:一方面是将原有的单一要素模型扩展为两要素模型,两种要素分别由最终产品生产商和零部件供应商控制,新的模型将要素密集度内生化,使之成为决定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卓斯可以否定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所认为的“在一体化企业组织形式下不存在合约摩擦的问题”,因为安卓斯的模型证明了中间投入品的资本要素使用越密集,那么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就越受青睐。这样的结论使安卓斯[6]的模型有了两个贡献,即在特定的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下,产权并没有给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带来优势。安卓斯和赫尔普曼[12]进一步将企业异质性加入到这个中间品贸易的两要素李嘉图模型中。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组织形式选择有了新的决定因素,即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通过确定企业生产率的临界值,低于这个水平的企业退出市场,而高于这个水平的企业有如下四种选择:本国外包,本国一体化,离岸外包,离岸一体化(外国直接投资,FDI)。从而企业也被区分为低技术部门和高技术部门,对于低技术部门来说,理性的企业不会选择一体化,因此所有的企业选择外包的组织形式,而且对于在这个部门中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来说,他们会选择离岸外包,较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则选择在本国外包;对于高技术部门来说,存在四种选择,而且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一体化。
(三)合约不完全性的内生化
安卓斯和赫尔普曼[13]通过考虑不同程度的合约摩擦对模型做了更一般化处理,即可合约度(The Degree of Contractibility)内生化。因此,他们的贡献是将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扩展到了合同本身,即可合约度。尽管在这个模型出现之前,正如我们所讨论的,也有许多文献涉及了合同不完全性对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作用,但是那些文献仅集中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问题② ——或者一体化,或者外包,却没有讨论具体是怎样产生影响的。在不完全信息下,由于只有对中间品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要求是可以在事前通过合约明确的,剩下的活动都是不可明文规定的。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合约质量就是由合约中可以明文规定的生产活动的比重来衡量的,越大比例的生产活动可以被明文规定,那么合约的质量就越高,反之,合约质量就较低。关于合约质量改进对企业组织形式选择决策的影响体现了这一影响的不对称性,即“来自于最终产品生产方对中间品合约的改进会鼓励企业参与外包组织形式,而来自于中间品供应商一方的改进则有助于鼓励企业参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13]。这样的结论也构成了对已有文献的补充,因为已有的文献认为无论任何形式的合约改进都会鼓励企业参与外包的组织形式(如威廉姆森 Williamson,1975,1985)。
埃斯莫格鲁,安卓斯和赫尔普曼[14]的模型是安卓斯和赫尔普曼[13]模型的一个应用,并将原有模型的局部均衡扩展为一般均衡。由于受特定关系下限制的技术选择③ 是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模型检验了可合约度和中间品之间的技术互补性对技术选择的影响,进而明确技术选择对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他们的结果表明,中间品之间的互补性越强,技术选择就越具有“合约依赖性”。这意味着当中间品之间的技术互补程度足够高的时候,合约中可以明确活动的比例(可合约度)发生很小的变化,就会使生产率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面对较弱的合约机制和可信的市场完全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可合约度相对不稳定),从而在这样的合约关系中生产率会发生较大波动,因此对于风险规避型企业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式。通过这样的模型设计,这篇文章在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框架下,将由技术决定的比较优势内生化了④。
(四)最新进展Ⅰ:合约不完全性的改善
总结已有的文献来看,合约不完全性对外包决策影响的研究已经内生化了许多影响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因素,比如企业异质性(内生化了生产率),可合约度(内生化了可合约比重),以及技术选择导向的比较优势内生化。然而,这些文献仅仅注重研究合约不完全性的影响因素,却忽略了对问题本身的研究,即如何改善合约的不完全性。安卓斯和斯泰格尔[9]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证明了合约不完全性的存在会造成非有效的纳什均衡政策,包括较低的无效率的中间品贸易量和最终产品价格;但是,如果对中间品贸易的补贴和税收水平选择适当,那么会大大改进国际合约的可合约度,进而将贸易量和贸易价格推向较为有效的水平。因此,这篇文章的意义也在于将内生化的贸易政策考虑到了外包模型中。
这个模型的另一个贡献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应用。既然适当的贸易政策可以将贸易价格调整到一个有效的水平,那么该模型认为对制造业部门来说,最优价格水平的决定将要依赖于市场出清机制的调整;而对服务业来说,最优价格水平的决定依赖于买卖双方议价能力。因此,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建议是制造业应该遵循关贸总协定(GATT)框架下传统的关税减免协议,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而对于服务业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应该注重协调成员国的双边议价能力。
(五)最新进展Ⅱ:中间品贸易与经济一体化
尽管经济一体化属于宏观范畴,但是它在中间品贸易中的研究是起源于微观层面的。随着安卓斯和斯泰格尔[9]内生化贸易政策模型的提出,将贸易政策引入外包模型成为最新的研究分支。中间品贸易下经济一体化的讨论是其中之一。安卓斯和科斯蒂诺德[10]研究了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一体化下的中间品贸易:W型一体化⑤ (这样的市场类似于国内外包)和M型一体化⑥ (这样的市场类似于离岸外包)。尽管该模型在一个简单的李嘉图模型框架下研究农民和贸易商两个主体的中间品贸易,似乎看起来与全球外包的背景无关,但是正如约翰森和诺格拉(Johnson and Noguera,2009)所指出的,现代的中间品贸易多是来源于全球外包:根据2001年的数据,从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国家来看,商品进口的三分之二是中间品的进口。
模型假设在南北两岛有农民生产中间品:咖啡或糖,而贸易商负责在一岛之内或两岛之间交易这两种中间品。在全球外包的背景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香港的贸易公司利丰,负责在全球分配并整合中间品的生产流程。该模型发现,通过使中间品内生化,W型一体化扩大了贸易的总福利,但是减少了贸易商的利润;而由于M型一体化一定会造成一失一得的局面,因此有可能会导致总福利的下降。这个结果对以往关于外包是否会使参与者各方都受益还是只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讨论,有一些启示,即它是与市场本身的状况有关的。另一方面的应用是,由于符合W型一体化的市场,之前是两个相互隔离的市场,因此一体化之后两个市场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从而会促使两国的趋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议价能力也得到提高,这样会鼓励农民去专业化生产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中间品,因此会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三、宏观层面:外包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在全球外包的文献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研究全球外包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中讨论较多的是对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本文在这一部分集中讨论外包对相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类文献首先由芬斯卓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1996[4,5],1997[6],1999[7])提出并发展,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8]根据21世纪工资和就业变化的新特点将其进一步扩展。
(一)经验数据与传统贸易理论的违背
当芬斯卓和汉森[4,5]将美国劳动力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归咎于外包的时候,另外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观点,如邦德和约翰森(Bound and Johnson,1992)以及伯曼,邦德和格里利谢斯(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偏向性技术增长的结果。他们的理由从多个方面提出。劳伦斯等人(Lawrence et al.,1993)分别检验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进出口价格数据,结果证明生产性劳动力密集的进口产品价格相对非生产性劳动力密集的进口产品价格并没有下降。然而,传统的斯托尔帕-萨谬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认为,进出口价格上升会导致该产品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上升,而另一种要素的价格下降。然而,这样的数据与传统的斯托尔帕-萨谬尔森定理相违背,因为并没有进出口产品价格的变动导致要素价格的相应变动。利默(Leamer,1994)也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斯托尔帕-萨谬尔森悖论。
然而,芬斯卓和汉森[4]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在李嘉图模型框架下修正了传统的斯托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并提出了最早的外包对工资影响的模型。基于均衡条件,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得到中间产品的生产范围在南北两个国家分配的临界值,高于这个临界值的中间产品由北方国家生产,而低于这个值的中间产品就由南方国家生产。资本在南北两国间的流动和技术的变化会引起这个临界值的变动。由于离岸外包必然引起资本从本国向外国的流动,在假设本国外包给外国产品的技术都高于外国固有产品的技术下,外国通过承接外包获得了技术进步,那么对当地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从而技术工人相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那么技术性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增加。
当运用修正的斯托尔帕-萨谬尔森定理来解释劳伦斯等人(Lawrence et al.,1993)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结论与理论的一致性:对于所检验的国家和指标来说,国内价格的上涨超过了进口价格的上涨,也就是说,非生产性中间品的相对价格随着非生产性工人相对工资的上涨而增加。从而,结论是离岸外包是非生产性工人与生产性工人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
(二)外包的衡量低估了实际规模
许多模型的检验结果拒绝了外包是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上述解释外,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外包”作为一个变量,并没有统一的衡量方法,而许多模型所采用的外包衡量方法考虑的范围通常较窄,从而低估了外包的数量。
比如,芬斯卓和汉森[4]指出了伯曼、邦德和格里利谢斯(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利用中间产品的进口来衡量美国制造业的外包。之所以说这样的衡量范围较窄,是因为:一方面是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增值有关。按上述方法,我们通常只在商品进入这个国家通关的时候记录商品的价值,但是由于所讨论的是中间品,因此就涉及进口后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产生新的附加值,那么这些新的产品增值并没有计入外包中,而事实上,这些由中间品带来的新价值确实在经济中产生作用,从而外包对经济的影响在这里被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与外包本身的定义有关。外包不仅仅包含零部件、中间材料,还包括生产过程以及OEM所购买的产品。那么,上述的衡量方法显然范围较窄,缩小了外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此外,仅考虑跨国公司的活动是低估外包影响力的另外一个方面。例如,劳伦斯(Lawrence,1993)用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就业量来衡量外包,进而用来解释外包对本国生产性劳动力就业相对减少的影响。数据显示:外国子公司的总就业量上涨6万人,而同期美国制造业生产性工人就业却下降了170万人。因此,结论认为外包对相对就业变化的解释力太小了以至于不足以构成主要原因。
然而,芬斯卓和汉森[4]却采用了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衡量外包的方法,即将上述两种方法综合在一起:美国的外包价值不仅仅包括“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口价值,也包括所有用于生产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价值,以及以美国品牌销售的所有商品价值”。实证检验证明了这样的衡量方法更为恰当:模型重新检验了伯曼、邦德和格里利谢斯(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的数据,发现在1979-1987这几年间,非生产性工人工资的上涨与增加的进口存在着很强的正向关系,并可以用进口的增长解释15%~33%的非生产性工人工资的上涨。
接着,芬斯卓和汉森[5]运用相同的理论,鲍德温和希尔顿(Baldwin and Hilton,1984)以及鲍德温和凯恩(Baldwin and Cain,1994)⑦ 的实证方法,利用1972-1992年间的行业数据再次做了外包对相对工资影响的检验。这篇文章的贡献是,一方面,外包的定义更加明确地分成了两部分:一是零部件的价值;二是与第三方因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发现了外包衡量的新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发现外包对相对工资变化的解释力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20世纪70年代的解释力较差,而80年代的解释较强。原因是,模型将美国从所有国家的中间品进口都视作了外包的一部分,然而,事实是只有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进口才属于外包的范围;而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模式正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多于从发达国家的进口,从而与70年代相比更符合理论模型的要求。
尽管在实证中,芬斯卓和汉森对于外包的这个定义更适于解释外包对相对工资和就业变化的影响,但是理论模型中,学者们更愿意用零部件(中间品)这个定义来描述外包,比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2[11],2005[15])就将模型中的生产者简单地分为了中间品生产者和最终产品生产者两类来分析行业均衡;相类似的用法也出现在了芬斯卓、赫尔普曼[3][12]的模型中,他们借此用来分析新的贸易模式。
(三)最新进展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新变化
在21世纪初期,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新变化,技术工人的相对就业开始下降。高德纳(Gartner)和弗雷斯特(Forrester)这两家研究咨询公司在2003年的调研报告显示,美国2003年从事高技术工作的人员有1035万,此后的12年,即到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个高技术工作岗位因外包而流失到海外⑧。这一现象在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8]的模型中得到了解释。该模型采用“离岸”这个概念来代替“外包”,集中讨论了国际分工贸易(Task Trading)。由于传统的贸易理论不再适用当今的国际分工贸易现象,因此他们修改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将一个商品的生产分为多个连续的生产过程。通过将这些具有不同外包成本⑨ 的生产过程外包到不同的国家,外包企业可以利用不同国家所具有的成本优势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此外,模型强调了生产过程的外包,而非技能含量的外包,因此,与已有的外包模型相区别,该模型将高技术生产过程的外包考虑在其中,从而解释了美国高技术工作岗位的离岸外移,而以前的模型仅考虑了低技术工人的外包。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外包会带来工资的变化,而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8]又进一步将这样的工资变化分解为三个部分,其中生产率效应是该模型的贡献。这一效应等同于“要素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因此可以与芬斯卓和汉森[4]的模型相类比,即资本从北方国家流入南方国家,从而增加了两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产生的作用相当于“内生性技术进步”。这两个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进步的来源不同,前者来自于外包生产过程,从而不同地理位置重组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而后者来源于外包使两国的工作难度增加而带来的技术进步。
(四)最新进展Ⅱ: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凯瑞贝和麦克拉伦(Karabay and McLaren,2009)[16]抓住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工关系特征,即随着国际贸易流动(国际商品市场一体化)而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离岸外包现象(国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并考虑了劳工关系中的风险因素对工资的影响,从而回答了“是否随着国际一体化规模的扩张会导致削弱劳工关系,从而带来更大的工资波动?”
通过在不完全信息合约下建立包含风险分担的劳工关系,凯瑞贝和麦克拉伦[16]发现在雇主与员工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握手”,从而将二者限制在长期的雇佣关系中。也就是所谓的“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方面,工人可以从与雇主的长期合约中保证工资的稳定,而工人对企业的长期忠诚度也会使雇主受益;另一方面,如果任何一方违背了合约,双方都会遭受损失。因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带来的问题会增加或减少搜寻合作伙伴的成本,从而对风险分担的劳工关系稳定性产生影响,并带来工资的波动。模型通过考虑劳工关系中对风险分担影响的不确定性,内生化了实际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发现了自由贸易(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减少了富裕国家的工资波动,但却降低了富裕国家工人的福利;而离岸外包(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尽管会带来富裕国家的工资波动,但却增加了工人的福利。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全球外包的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致力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探究公司在全球外包中对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另外一方面研究宏观经济影响,集中探讨外包对一国技能型与非技能型劳动力相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可见,已有的文献较多关注了全球外包的静态影响;最新的文献考虑了经济主体对全球外包行为的动态反应,从而通过实施适当贸易政策来改善外包合约的不完全性,以及怎样的外包形式(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同时也考虑了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动态变化,从而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外包对工资及就业的影响。
尽管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8]的理论模型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基于这一理论模型的实证文献还较少,因此可以成为未来研究技术工人相对工资和就业的基础。此外,安卓斯和赫尔普曼[13]内生化了合同依赖性因素,因此,进一步扩展合同依赖性问题成为微观企业视角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安卓斯和罗西-汉斯伯格[17]也提出了外包模型动态化的未来研究方向。至今研究国际生产动态效应的文献还较少,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比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产性分工对于技术升级的作用,外包活动中“边学边干”效应的动态作用都值得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地位的提升也是动态化研究的一个视角。
收稿日期:2011-03-10
注释:
① 来源:2008年UNCTAD年报第31页,图“国际生产指标统计,1991-2006”。
② 根据Grossman和Helpman(2002)的模型,仅有所有企业都参与一体化和所有企业都参与外包的均衡是稳定的。
③ 所要采用的技术越先进,所需要的投资越多。
④ Costinot(2004)的模型也将比较优势内生化,所不同的是Costinot的模型是基于专业化的基础上,而Acemoglu,Antràs和Helpman(2007)是基于合约摩擦和技术互补性的基础上;另外,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简化形式。
⑤ 两个相互隔离的瓦尔拉斯市场的一体化。
⑥ 两个相互有经济往来的市场的一体化。
⑦ 他们的方法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化对单位要素投入的变化做回归来检验商品价格与要素价格之间的一般均衡关系。因此,在Feenstra和Hanson(1996b)的模型里,因变量是非生产性工人工资份额的变化,自变量是log(资本/产出)的变化,log(实际产出)的变化,以及外包的变化。
⑧ Forrester,Gartner Co.The Job's Outsourcing of the High Technologies,Global News,2003(8).
⑨ 已有的外包文献假设中间投入品的运输成本为零,见Feenstra and Hanson(1996,1997,1999),Grossman and Helpman(2002,2005),Antràs(2003),Antràs and Helpman(200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