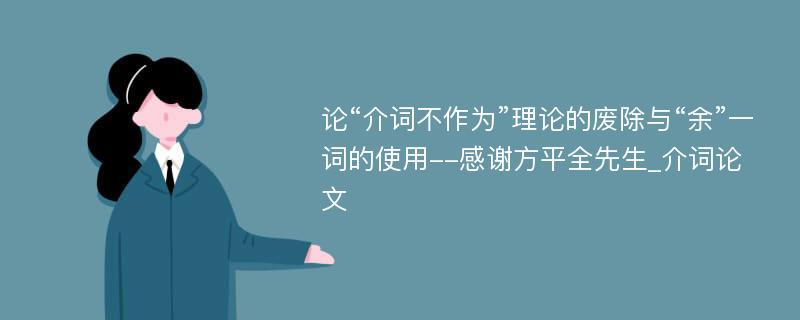
关于取消“介词省略”说以及“于”字的用法问题——答谢方平权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介词论文,方平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2)03-0069-06
《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刊载方平权先生《关于介词“于”由先秦到汉发展变化的两种结论》文,对拙文《关于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意见》(下简称《意见》)[1]提出的取消“介词省略”说提出异议,对介词“于”由先秦到汉的发展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读了之后,甚为欢欣、鼓舞,想不到笔者的《意见》文及其他有关论著引起方先生的关注和重视。方先生既然将问题提了出来,我也谈几点意见,权作答复。
首先说明两点:一是取消“介词省略”说,包括取消“介词结构”(或名之为“介名短语”“介宾短语”),是我主张的一个语法观点。此主张在拙文《汉语句法分析问题》[2]、《从汉代注释书论汉语介词的表义功能——兼谈否定介词结构的合理性》[3]、《〈马氏文通刊误〉省略说质疑》(下简称《质疑》)[4]以及方先生提到的拙作《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下简称《变化》)[5]中都讲述到。二是我主张取消“介词省略”说,不是针对一个“于”字而言。在《变化》书中谈到的介词有“在”“自”“以”“为”“与”“于”“用”“顺”等;(注:“用”“顺”是否介词,有不同认识;笔者姑为这样处理。)在《意见》文中举的例词是“以”。方先生文中说:“‘介词省略’说”,“主要是‘于’字问题”,此话下注说:“见孙良明《〈马氏文通刊误〉省略说质疑》。”笔者《质疑》文中是这样讲的:
以上诸例是注文较原文多了介词“于”“以”。几部传注书中注文较原文多的介词不止于“于”“以”,因《刊误》讲省略只列了这两个字,本文也就仅举此为例。当然,传注书中也有原文有“于”“以”而注文无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于传注书中极少。
可见笔者讲的“介词省略”即使在《质疑》文中也不止是指“于”字的省略。这是首先要说明的两点。下面就介词省略问题,(注:吕淑湘说:省略有广义、狭义之分:“严格意义上的省略应该只用来指可以补出来并且只有一种补法的词语,否则不能叫做省略,只能叫做隐含。”(《中国语文》,1986年第1期)笔者所说省略,是指此“严格意义上的省略”。)在笔者已有论著的基础上,再从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补充论述。
一、我主张取消“介词省略”说,是据汉语事实而提出的。
汉语(实词)无词形变化,动词无如印欧语系的及物(外动)、不及物(内动)之别。名词(N)、动词(V)的组合相当自由,如组成谓词性短语可用介词(P)介绍,也可不用介词介绍。N在V前的,在古汉语有N—P—V(古老式)、P—N—V、N—V三格式;N在V后的,有V—P—N、V—N两格式。笔者认为,这N—V、V—N是古汉语本有之句式(包括V—N之N表示处所),不是介词的省略式。杨树达批评马建忠“不明理论”“不明省略”;说:“马氏不明省略,但据类例之多少,以关系内动与转语之间无介字者为常,有介字者为变,不合于理论。”又说:“古书记所在所经所至之地,本当有介字‘于’字先者也。……此类例有介字者,正例也;省介字者,变例也。”杨氏认为V—N之N表示处所,V—N间必须有P(“于”);有P为正例;无P则是省略,为变例。笔者在《质疑》文中说明杨氏所说之“理论”,乃是印欧语不及物动词(intransitive verbs)必须有介词(prepositions)才能跟名词(nouns)组合的语法规律;而此“规律”不适用于汉语。这方面黎锦熙的处理相当宽容;其《比较文法》“副位”章,第二节讲“前有介词之副位”,第四节讲“省略(或本无)介词之副位”,说:“表时或地之‘副位’,有不须介而直接附于内动后者,则多为关系内动词所带‘副词性的宾语’。”[6](p69)黎氏认为这样的“副词性的宾语前”,“不须介”,而不是“省略介”。
从V—N所隐含的实际语义关系情况来看,如果N表示时地、工具、方式等与介词“于”“以”用法有关,可以说中间省略了“于”“以”;如果N表示目的、与事等,则难说中间省略了介词。如:
(1)伯氏不出而图吾尹。[郑玄笺:图犹谋也;不出为君谋国家之政。](《礼记·檀弓上》)
(2)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郑玄笺:与我期于桑中,而要见我于上宫。](《诗经·鄘风·桑中》)
如果加上介词“为”“与”,则V—N结构变为P—N—V结构,这只能说明同一语义关系可有不同的句法形式;以句式变换说明N表示目的、与事则可,不能说V—N中间省略了“为”“与”(再看下第三部分现代汉语例)。
V—N之N还可以表示施事:
(3)(儒)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郑玄注:慁犹辱也;累犹系也;闵,病也。言不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违道。](《礼记·儒行》)
(4)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高诱注:为日光所照无景柱也。](《淮南子·原道训》)
为—N—所—V是共认的被动结构;这可说明V—N之N表示施事,不能说明V—N之间省略了“为……所”(“慁君王”“累长上”“闵有司”“照日光”之间可加上“于”;但这是句式变换,不能说原文省“于”)。
笔者在《质疑》文中说:“句法结构隐层隐含着的语义成分,显层结构未必有相应的形式,此乃语言现象之正常,不能看作是省略。”文中举古代汉语“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现代汉语“□墙上挂着一幅画”,不能看为省略了判断词(“是”)、介词(“在”)。众所共认,汉语并列结构短语的两项之间可不用连词,复句结构的分句与分句关系也可不用连词表示(所谓“意合法”);可没有见过有“连词省略”说。
薛凤生(1998)说汉语句式特色之一是“语法词”(“虚词”)常有省略“,列例有“于”“者、也”“而、则”。[7]笔者认为这是汉语句式本所无,不是“省略”。
二、我主张取消“介词省略”说,是从语义关系(语义结构)、句法关系(句法结构)结合分析而提出的。
名词、动词组合后,名词表示动词的施事、受事、与事、结果、对象、目的、工具、方式、时间、处所等是语义关系分析。名词、动词组合而产生的主谓结构、述(动)宾结构、述(动)补结构、状述结构是句法关系分析。按现在通用的语法(句法)分析体系,N—P—V、P—N—V、N—V不管是否有P,都是状述结构;而V—N、V—P—N前者是述宾结构,后者是述补结构(即所谓“介词结构”作补语)。古汉语语法分析有所谓“特殊动宾意义关系”提法,或名之为“X动”,或名之为“X宾”,王克仲先生(1987)曾作过统计,学者们列出的有近二十种;[8]笔者(1993)也曾据汉代注释书中的表现,计有十五种。[9]笔者这里要谈一个不用言喻的事实,即所谓“特殊动宾意义关系”,种种“X动”“X宾”是指V—N结构的意义关系,决不是指V—P—N结构中由P所表示的N和V的意义关系。而如果认为V—N结构中省略了P,则V—N=V—[P]—N结构。这样,分析V—[P]—N句法,当同于V—P—N句法,[P]—N也就是所谓“介词结构”作V的补语。照此,种种特殊动宾意义关系根本就不存在;分析省略了的P所表示的语义关系就是了。所以,须要分清V—N跟V—[P]—N的句法结构之别;须要分清V—N述宾结构所隐含的语义关系跟V—[P]—N述补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之别。另外,众所共认,V—N[,1]—N[,2](如“与人规矩”)是双宾结构;而V—N[,1]—N[,2]可以变换为V—N[,1]—以—N[,2]、V—N[,2]—于—N[,1]、以—N[,2]—V—N[,1],可从来没人说过V—N[,1]—N[,2]结构中省了介词并按所省介词分析语义关系。如果按V—N[,1]—N[,2]的变换式分析,那双宾结构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方先生文中说“介词省略说有利于进行语义分析”,并提到王克仲《古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的制约因素》[10]所说的“语义介词对动宾关系的作用”;“动宾语义的支配关系和补充关系的区别,关键在于动词的后面或者前面能否加进语义介词”。
“语义介词”是王克仲先生多年主张的一个语法观点,除方先生提的文章外,又见王先生的专著《古汉语词类活用》(1989)[11]和文章《古汉语的"NV"结构》(1988)[12]。关于“语义介词”说,出于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尊重,笔者本不想、不愿评论;方先生既然提了出来并用以反对取消“介词省略”说,笔者只好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所谓“语义介词”的有无不能作为支配关系、补充关系的区别标志。
王先生说动宾形式结构D+M(D,动词;M,宾语)含语义结构支配关系d+M和补充关系d+[(j)+M]/[(j)+m]+d(j,语义介词)。在方先生引话之后,王先生说:“不能加进语义介词的,是支配关系;能加进语义介词并且同M构成介宾词组而在语义上充当补语或状语的,是补充关系。”王先生说的支配关系,是指宾语是名词的受事;王先生说的补充关系,是指使动、意动、(注:王先生分析“士民不亲附”中的“亲附”说:“‘附民’是补充关系,是说‘民’不受‘附’的行为;相反,它却是‘附’的语义施动者。”(即“使民附”之意);分析“(秦)死吾君而弱其孤”说:“‘死吾君’既不是表示处置,也不表示致使,而是表示意为。……是‘秦认为吾君故去而嗣君软弱’”。前者一般认为是使动用法,后者一般认为是意动用法;王先生均归入补充关系。)与事、目的、对象、工具、处所等,即一般所谓“X动”“X宾”等“特殊动宾意义关系”。古汉语的事实是,表示支配关系的V—N,也可加入所谓“语义介词”,同M构成所谓介宾词组;而表示补充关系的V—N,并不都可加入所谓“语义介词”。如:
(1)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郑玄注:抗犹举也;谓举以世子之法使与成王居而学之。](《礼记·文王世子》)
(2)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毛传:将,请也。孔疏:……请于仲子兮,女当无逾越我居之里垣,无折损我所树之杞木。](《诗经·郑风·将仲子》)
(1)“抗”与“世子”、(2)“将”与“仲子”是支配关系,可以加入介词“以”“于”。再看下例:
(3)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忧不己。[司马贞索隐:忌,忧也。言罹霜露寒凉之疾,轻;何忧于病不止。](《史记·公孙弘列传》)
(4)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司马贞索隐:不讲习,谓不论习之。](《史记·刺客列传》)
(3)支配关系“忧不己”无“于”,“索隐”加入;(4)支配关系“讲于刺剑之术”有“于”,“索隐”删去。可见,N表示受事,有“于”、无“于”也是相当自由的。而“于”可以引出受事,姚振武(1999)作过专门论述。[13]
王先生将V—N表示的致动、意动现象也归入补充关系。众所共识,这两种现象表示的语义关系是V[,1](使/令)—N—V[,2]、V[,1](表示认定义的“以”)—N—[V,2]。这样的V—N结构之间是不能加入介词的。
第二,所谓“语义介词”混淆了句法关系(句法结构)、语义关系(语义结构)分析的用语。
“语义介词”是分析隐层的语义结构提出的;而名词、介词、介词结构(介宾词组)是句法单位,是分析显层的句法结构用语。故分析语义关系不当用分析句法关系的名称、术语,而说什么“介词”;更不当说隐层的“语义介词”跟显层的句法单位名词构成“介宾词组”。当然,如果认为V—N间省略了介词,补出介词,说[P]—N为介宾词组是成立的;但不能说“语义介词”跟名词构成介宾词组。这不是名称、术语之辨别,而是语义、句法两个平面之区分(分析V—N语义关系,硬要跟介词联系的话,倒可以说“介词语义”,即隐含着介词所表示的语义;但不能说“语义介词”)。
需要指出的是,跟“语义介词”说相拟的,有尹日高的“‘使动’‘意动’‘介动’鼎足三分”说。[14]主张者认为,古汉语特殊动宾意义关系,使动、意动之外,其他种种关系“语义上含有一个介词”,故称为“介动用法”。这也是将分析句法的介词用于分析语义了。不同于“语义介词”说的是,将使动、意动划在“介动”之外(这也说明表示使动、意动义的V—N间不能加入介词)。
第三,“介词省略”说、“语义介词”说颠倒了语义分析程序,无助于进行语义分析。
方先生说“介词省略说有利于进行语义分析”,接着引出了王克仲先生的“语义介词”说。
看来方先生是将“介词省略”说等同于“语义介词”说了。上面已说明,前者是从显层的句法结构平面的分析提出的,后者是从隐层的语义结构平面的分析提出的。两说所指语言事实虽然同一,但必须明确两说在语法分析平面的不同。
笔者认为,“介词省略”说、“语义介词”说都是颠倒了语义分析程序。名、动组成V—N结构,句法分析是述(动)宾关系;语义分析则相当复杂,如前所述N可表示V的受事、结果之外,还可以是施事、与事、对象、目的、原因、方式、时间、处所等。介词是关系词,特定的介词表示特定的关系语义;这样,分析V—N的种种语义关系,似乎可以认为省略了相应的介词,或隐含着相应的“语义介词”。但是,语义关系分析的操作程序是,先确定了具体的意义关系,才能看出是省略了哪个相应的介词或隐含着什么样的“语义介词”;决不是先找出省略了的某个介词、或认为隐含着什么样的“语义介词”,再确定某种意义关系。如:
(1)汤又让于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请相吾子。”[高诱注:胡,何也;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己请为吾子为相。](《吕氏春秋·离俗》)
(2)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权。[高诱注:欲以鲍权为齐相也。](《吕氏春秋·赞能》)
(3)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孙奭疏:万章又问孟子……尧帝而以二女妻于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妻者,以女嫁人谓之妻也。](《孟子·万章上》)
(4)悼公之母死,[郑玄注:母,哀公之妾。]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与?”公曰:“吾得己乎哉!鲁人以妻我。”[郑玄注:言国人皆名之为我妻。](《礼记·檀弓下》)
(5)以金镯节鼓。[郑玄注: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贾公彦疏:节鼓,与鼓为节也。](《周礼·地官·鼓人》)
以上5例是名词做述语(所谓名词活用)构成的V—N结构。(1)“相吾子”确定N是表示V之所为(对象),(3)“妻舜”确定N是表示V之所给与,才能认定分别省略了介词或隐含着“语义介词”“为”“于”。(2)“相鲍叔”确定是意动关系,(4)“妻我”确定关系相当特殊,(注:笔者《变化》书中说,古汉语名词作述语构成的V—N结构,其间语义关系有的相当复杂,很难归入某类型,只能具体分析。)这样就认为其中未省略介词或不隐含“语义介词”。(5)“节鼓”,据郑玄注是意动关系;据贾公彦疏N是表示V之所与(与事),则就认为省略了介词或隐含着“语义介词”“与”。这样看来,“介词省略”说、“语义介词”说,不但颠倒了语义分析程序,而且似乎是“赘余”;语义关系已经明确了,何必再去“寻找”省略了哪个介词、隐含着什么样的“语义介词”呢?同理,分析“意合法”复句结构,既然逻辑语义关系(假设、条件、因果等)清楚了,就无须再说省略了哪个连词或隐含着什么样的“语义连词”了。
以上三点是对“语义介词”说的评述。因为方先生提了出来并用以反对取消“介词省略”说,故笔者只好谈这些浅见;当然这也只是个人看法,未必正确。
三、我主张取消“介词省略”说,是从古汉语语法分析跟现代汉语语法分析接轨而提出的。
丁声树等先生早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说:“有各种不同的动词,因此动词跟宾语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其实就是同一个动词也常带各种关系不同的宾语。”举例有:“‘写文章’是写出来才成为文章”,“‘写黑板’是在黑板上写”,“‘写魏碑’是摹仿魏碑写字”。“‘洗衣裳’是把衣裳放在水里洗”,“‘洗凉水、洗热水’是用凉水、用热水洗澡”。“‘跑街、跑路’是在街上、在路上跑”,“‘跑公事、跑买卖’是为公事、为买卖奔跑”。“‘下山、下楼、下车’是从山上、从楼上、从车上下来,是离开那个地方”,“‘下水、下田、下乡’是往水里、往田里、往乡里去,是走向那个地方”。[15]这些都是以用介词造出的变化句式表现原来述(动)宾结构的意义关系。这些现象可以说同于古汉语,可此书上既未说述(动)宾结构间省略了介词,也未说隐含着“语义介词”。
原名《动词用法词典》、现改名《汉语动词用法词典》“说明书”说名词宾语有十四类,如受事宾语、结果宾语、施事宾语、致使宾语、对象宾语、工具宾语、方式宾语、处所宾语、时间宾语、目的宾语、原因宾语等。每类宾语写明“形式特点”,用句式变化表明宾语跟动词的意义关系。对象宾语说:“一般都可用‘对/向/与……相’把名词提到动词前面。如:教育孩子→对孩子进行教育|敬老师[一杯酒]→向老师敬[一杯酒]|结合具体情况→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工具宾语说:“一般都可用‘用’把名词提到动词前面来。如:抽鞭子→用鞭子抽|盛大碗→用大碗盛。”方式宾语说:“一般都可用‘用’把名词提到动词前面。如:唱A调→用A调唱|写仿宋体→用仿宋体写。”处所宾语说:“有些处所宾语可放在‘在……上’‘在……里’之中,整个短语或放在动词前或放在动词后。如:走小道→在小道上走|坐火车→坐在火车里。”“有些处所宾语可以加‘从’字或放在‘从……里’之中提到动词之前。如:经过赤道→从赤道经过|退会→从会里退出。”时间宾语说:“宾语大都可放在‘在……里/时’之中提到动词前面。如:起五更→在五更起床。”目的宾语说:“宾语可用‘为’提到动词之前。如:逼租→为租子而逼迫人|接洽业务→为业务问题而接洽。”原因宾语说:“宾语可用加‘因为’而提到动词的前面。如:避雨→因为下雨而躲避|躲债→因债而躲。”[16]这些也都是以用介词造出的变化句式表现原来述(动)宾语结构的意义关系,同样也未说述(动)宾结构间省略了介词,或隐含着“语义介词”。
这是讲的现代汉语的种种宾语类型,也即现代汉语V—N结构的意义关系类型。这可看出,这些关系类型跟古汉语语法论著中讲的所谓“特殊动宾关系”“X动”“X宾”类型多少大致相同。笔者在《意见》文提出取消“特殊动宾关系”提法,说:“所谓‘X动’或‘X宾’均是古汉语本身固有的语义现象,怎么能名之为‘特殊’呢?”这里再补充说明,笔者主张取消“特殊动宾关系”提法,也是从古汉语语法分析跟现代汉语语法分析接轨而提出的。
以上就笔者主张的取消“介词省略”说从三个方面作了补充论述。这从而也说明笔者为什么否定“介词结构”说。笔者认为,汉语V、N组合可以无介词组成N—V、V—N,也可用介词组成P—N—V、V—P—N。但不管有无P,结构项皆是V、N;P仅起关系作用,不成其为结构项,P—N不能作为造句单位而独立存在(如果单独使用,则P成V)。
下面谈谈自己对方平权先生文章的态度——充分肯定,表示感谢。
首先,笔者讲的介词省略,虽然不是仅指一个“于”字,但在《变化》书中谈到这一问题时,“于”字例证最多。故方先生以“于”字行文是成立的,论证有据,结论可信。
其次,方先生说在笔者所指出的语法发展“逐渐缜密化”之外,“似乎同时还有另一个规律,即也可以不断简化”。这一点笔者认为也是成立的。语言现象是复杂的,其发展趋势不可能是单一的(再看下“又再其次”)。
再其次,笔者《变化》书中说:“《史记》《汉书》中N—V、V—N结构中隐含介词而未出现的,似可看作是古代书面语的继承,历史现象的遗留。”方先生指出论断不当,批评也是中肯的。本书“代前言”明确说:“本书仅是根据汉代注释书材料……所谈的一些语法变化,所谈的几条发展规律,能否成立,是否周延,尚需别的语言材料验证。”故不该论及《史记》《汉书》。
又再其次,方先生提出汉代注释书语言的时代性问题,这实质上是原文、注文语言的历史差异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笔者在写《变化》书时、特别是书出版后所考虑、思索到的。笔者观察原文、注文的语法差异,已经看出有的是历史变化(语法的历史发展),有的是共时变换(时人对原文语义的句式变换分析)。本书重在说明从注释书看先秦到汉代的语法发展,故写了十三个历时变化;同时也写了两个共时变换。现在看来所谈某些历时变化,未免简单化,是形式主义的看问题。如原文、注文之间既有N—V→P—N—V/V—P—N、V—N→V—P—N/P—N—V,也有P—N—V→N—V、V—P—N→V—N;也就是既有加介词现象,也有减介词现象。不过前者是多见的、大量的,后者是少见的、少量的。这一点笔者在《质疑》中已有说明。其所以如此,盖时人为了用变化句式分析原文的语义关系,故加介词多见;减介词不能表现原文语义关系,故少见。这样如果据汉代注释书加介词说明是语法发展逐渐缜密化的趋势、规律,那据汉代注释书减介词也可说明如方先生所说的“不断简化”的趋势、规律。所以汉代注释书原文N—V、V—N结构注文加入P,笔者据以论证否定“介词省略”说似为可信;但据以认定就是语法发展趋势、规律而忽略了另一面,则是简单、片面。
以上是对方平权先生文章的肯定与感谢。最后说明三点。一是对方先生读书细心、研究覃思精神,表示敬佩。二是语法研究不易,既要掌握大量而又翔实的语料,还需具备新的科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切不可据自己掌握的一面材料、懂得的一面道理而作论断,定规律。老夫髦矣,这方面愿与方先生共勉而“瞠乎其后”。三是希望《古汉语研究》尽可能多发表些批评、讨论性的文章,开展学术争鸣;让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交锋”、论辩,以促进学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