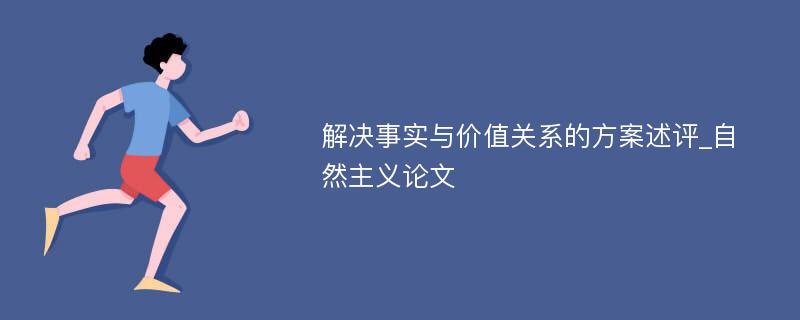
求解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诸方案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事实论文,价值论文,关系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即休谟问题提出以后,西方哲学依其天人相分,注重科学、理性、特别是推崇实证分析的传统演进,其结果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裂隙越来越大,终于形成根深蒂固的二分信念。但同时,自休谟以来的价值论史,几乎也是不断缝合事实与价值这把破裂的大伞的历史。即便是“分析的时代”,也蠕动着一股求解休谟问题的潮流,只是大多时它并不那么显赫。挑选一些最有影响的思想,对之作一必要的历史考察、批判,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具有启发意义、能将我们的思绪引入深处的东西;至少我们会从这些尚称不上成功的尝试中,找到其失误之处,以调整我们的视角,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
1.从自然主义到新自然主义
“休谟法则”或“自然主义谬误”等,是针对自然主义的。因此现当代自然主义的历史,几乎就是不断设法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威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道德评价领域,认为应当把伦理学说、价值判断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他把他为自然科学总结的“实验探索方法”运用到伦理领域,这包括如下几个步骤:首先是根据道德问题情境提出要加以解决的道德问题;其次是针对问题提出一个假设性的价值判断,即关于要达到什么目的的判断;再次是联系道德问题情境对假设性的价值判断进行观念的、符号的分析,并以之指导具体行为,改造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如果行为结果与预期目的相符,那么价值判断便被接受,否则便被拒绝。这样,村威就通过所谓“实验法”,把事实和价值联结起来了。另一代表人物培里则通过把价值定义为“兴趣”的对象,来联结事实与价值。培里认为,兴趣就是这样一组词,它标明如“喜欢或不喜欢”、“欲望或回避”、“满意或不满意”、“爱或恨”这样一些肯定态度或否定态度。如果某人对某物持肯定态度,那么此物便是善的。由这种态度所生发出来的具体判断就是肯定的价值判断;如果某人对某物持否定态度,那么此物就是恶的,由这种态度所生发出来的具体判断就是否定的价值判断。这样,培里就通过一系列心理状态或心理事实,说明了什么是价值,或过渡到了价值判断。
现代自然主义者诸如杜威、培里等人探索事实与价值之统一的努力并不成功,至少正如摩尔的追随者所说的,他们仍旧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他们主要侧重探讨什么是善(或价值)以及善(或价值)的根据、标准之类问题,而并不重视对价值语言的性质、意义、功能及证明等问题的研究,甚至对“自然主义谬误”之类并不是怎么特别关心,因而他们并没根本改变传统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休谟、摩尔等人提出的问题,更不可能有效地回答休谟、摩尔、情感主义者等的诘难与攻击。当然,这并不是说,回答休谟等人的问题必须接受其研究前提与分析哲学方法,而仅仅是说,剖析、批判某人的观点,回答某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它、真正弄懂它。如果一个人对实证主义思潮或分析哲学运动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其批判必是不彻底的,对他们的问题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予以回答。
20世纪50—60年代崛起的新自然主义,其代表人物W·K·弗兰克纳、A·塞森斯格、F·福特等人,试图改变以往的自然主义者不重视理论证明和逻辑分析的缺陷,同时也改变分析哲学只重视逻辑与语言分析的形式化倾向。他们在分析道德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同时展开自己的观点。例如,福特并不像传统自然主义者一样,主张价值实际上就是事实,而认为价值还不能还原为事实,事实也不能还原为价值;但她仍认为价值与事实是紧密相联的。针对黑尔等人将价值与事实区分为规定性的和描述性的观点,福特指出,概念的思考表明价值与事实在逻辑上是相联的,将它们分成两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类型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如“危险的”之类概念都具有所谓事实与价值相缠绕的特性,以至不能区分其中的事实成分与价值成分;而且,概念的行为指导特征与事实特征不是凭借把它们分为价值与事实两个组成部分之类方式来辨别的。可见,福特已接受了事实与价值的必要区分,并从对一些特殊的概念进行分析出发,证明关于语言的绝然二分是不成立的。从而找到了事实与价值相联系的一个关键点;既具有事实意义又具有价值意义的概念。这对反驳二分对立者的诘难显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2.直觉主义与直觉方法
价值论直觉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即事物的价值是不能靠经验和理性的方法来认识的,而只能靠直觉去把握。它大约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正式形成于英国。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季威克、摩尔、普里查德、尤因、罗斯等人。当然,他们主要都是从伦理学角度展开其研究的。
直觉主义认为,价值是不同于事实的。诸如“善”、“应该”、“正当”之类表达价值属性的最基本的价值词是不能通过感觉经验,或者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方法加以认识的,这些价值词也不能以自然主义的词语、通过某种逻辑定义方法加以定义。如果一定要对之加以定义的话,就会犯“自然主义谬误”(摩尔语);以上述基本的价值词为谓词的那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是不能通过经验的或逻辑的方法,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但直觉主义却并不认为价值是不可认知的,他们认为,通过人类自身的某种特殊能力与特殊思维方式——直觉,就能不证自明地察知、领悟价值与价值(伦理)原则。
不过,在直觉主义阵营内部,他们的观点也并不是一致的。英国著名伦理学家西季威克认为,伦理学方法既不是经验的,如功利主义那样;也不能是社会的,像进化论那样;更不能是神学的,像基督教那样;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直觉。他指出:“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是符合某种无条件命令的义务法则或指令”[①a]。这些义务法则或指令可以由直觉得知,然后用确定、清楚的语言陈述出来,从而使之不证自明地普遍有效,成为自明原则,具体地说,这些自明原则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用以陈述它们的概念必须清楚、精确;它们的自明性是非常详尽地确定下来的;它们必须是相互一致的;必须有专家们对其真理性的普遍同意。西季威克否证了功利主义、快乐主义等的论证方法,认为功利原则、快乐原则等必须通过直觉才能得到。“如果要说这快乐主义原则,无论在个人幸福,还是在普遍幸福方面,都被合法地证实了的话,那么,它就或者是直接得知为真的——由此,我们可说是一个道德直觉——或者是由某种包括至少一个这种道德直觉的前提中最终推论出来的。无论是哪种快乐主义,都可以合法地说是在一定直觉意义之上的”[②a]。总之,只有通过直觉方法而非经验方法,才能把握价值(道德)原则。
摩尔区分了“善”与善的事物,认为善本身是独立的、简单的、不可定义的和不可分析的。对于善本身只能依靠那种具有“自明性”的直觉才能加以把握。而表达善本身的基本的价值原理“仅仅凭它本身是昭然若揭的或真实的,它不是除它本身以外的任何其他命题之推论”,即“不可能根据逻辑从任何其他命题演绎出来,必须直截了当地接受它或否定它”[③a]。也即凭直觉不证自明地我们就能获得这些基本价值原理,并接受它为真的或假的。
普里查德认为,“义务”才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不能把“善”和“我应当做……”视为同一,我们可以承认某件事是善,但我在做这件事时,却是出于内心的一种义务感,它独立存在。特别是当两种道德原则互相冲突,而每一种道德原则都可以解释为善时,一个人必须知道他应当怎样做,此时,行为的根据即“义务”就在于我们日常的义务判断和“常识”道德,即对价值的常识直觉。
尤因则认为,“应当”才是伦理学的最基本概念,必须由直觉去把握它。但尤因指出,应正确看待直觉在价值论中的作用,既不能否定,也不能夸大。当某一种理由最后不能推论下去,否则可能陷入无限循环时,就要诉诸直觉。并且由于对“直觉”的非难与反对者众,尤因认为使用“直接认知”(directcognition)一词更为适当。
直觉主义产生以后,曾一度在价值论(伦理学)领域占据过统治地位。确实,在关于一些基本的价值概念、价值判断可以依靠直觉去识别、把握、获得等观点上,特别是基本的价值原理、价值原则的领悟与确立上,直觉主义的观点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毕竟,直觉是人脑特有的一种精神官能,一种能力;毕竟,直觉是人类现实实践中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现代人类对于自身能力与认识方法论的反思,以及科学实践与生活现实,都已一再表明,直觉的意义是不能忽视与低估的。
但直觉主义自产生以后,就一直为各种各样的批评所包围;它在西方风行了几十年后,便遭到了几乎彻底地否弃。究其原因,表面看来,一是因为其内部的严重分歧,如到底“善”还是“应该”、“正当”才是伦理学之最基本概念?二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崛起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可检验性原则和意义标准,只有那些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检验的事实判断和分析性的数学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价值(道德)判断,特别是价值(道德)原理——直觉主义宣称只能通过直觉才能获得——并不陈述经验事实,而且它与通过数学直觉获得的数学公理也不一样,因为数学公理的真实性来自对有关概念、术语的定义,而直觉主义认为基本价值(道德)概念是不能加以定义的。这使得价值(道德)判断及价值(道德)直觉的合理性,也失去了传统的与数学相较进行类比论证的基础。
但实际上,直觉主义的衰落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直觉主义认为基本的价值判断或价值原理只能依靠直觉获得,而绝对排斥经验与逻辑的作用。这既与现实实际不符,而且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毕竟,直觉有其局限性,例如,不借助任何形式的事实根据的支持,我们如何判定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真假呢?直觉主义的回答是“直觉”和“不证自明”就能知道,而仅仅诉诸直觉,那么人类的一切理论,包括极端偏激的理论似乎也能够为一些人所坚持,直觉主义对于解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价值分歧与冲突,就将是无能为力的;这导致不少人认为直觉主义放弃了对价值(道德)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更一般地,现实一再证明,直觉是或然性的,它必须以经验和逻辑为补充。其次,在关于直觉的本质与发生机制问题上,直觉主义的说法是含混、苍白、甚至是神秘主义的。直觉主义者常常把直觉与“自明性”概念联系起来,如摩尔说:“我把这样的诸命题称为‘直觉’,我的意思仅仅是断言它们是不能证明的。”[①b]但“自明性”概念本身却是不自明的。如罗斯把“有教养的人的深思熟虑的确信”视为判断直觉的根据,而“有教养的人的深思熟虑的确信”本身却显得含混费解,难以把握。还有些直觉主义者往往把直觉神秘地说成是人先天具有的一种本能,这种似玄学的说法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把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推给天赋直觉,问题似乎解决了,但人们仍不着边际,无从理解,这种解决方式在西方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感,从而使直觉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
我们以为,尽管直觉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直觉也不像价值直觉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是唯一的孤立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直觉在价值思维中,在价值评价中确实具有独特的价值。对直觉予以合理、科学的界定,对实践中价值直觉作如实的考察与提炼,将为我们求解休谟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3.科学人本主义的新思路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简单二分,尽管比较正确地映射了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时的“分裂意识”,但用来指涉目前却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当代西方已出现了将科学与人性(价值)重新塑合起来的倾向和努力,即科学人本主义的尝试,其思想先驱有G·萨顿、波兰尼等,但其真正的代表人物,当推A·H·马斯洛。
马斯洛的科学人本主义思路是从对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反思开始的。马斯洛指出,现代心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已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完全丧失了“热爱、创造性、价值、美、想象、道德和欢乐”,而似乎成了一种丧失了“人味”的、离开人而自行运转的客体。科学哲学崇尚“价值中立”、“道德中立”,奉行客观至上,在理论深层支撑着那种非人的科学观。马斯洛认为,科学本应是人性与认知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由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②b]这就是说,科学也是人学,也只能是人学。另一方面,马斯洛认为,传统人本主义也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纯粹形而上学玄想的水平上,人学始终未能得实证科学的性质。马斯洛指出,其实人性本身就是具有生物科学意义的。人所特有的天性如爱、尊重、安全等也类似生物本能,都是可以从实证科学的意义上加以确证的。这样,通过在科学中发现人的因素,揭示科学的人学化、主体化,以及在人与价值的本质中找到实证的经验基础,马斯洛就将科学与人(价值)融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科学人本主义的整体构架。以之为基础,马斯洛就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断裂的事实与价值之间架设起了桥梁。
马斯洛指出,一般的人容易患有“是认识”而“应该盲”的痛苦,即太现实化,而看不到人的潜在本性方面的偏向。这些“应该盲”“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现在的是’(包括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当作标准”[①c]。而另有些人又是过分抽象强调理想化“应该认识”的“是盲”,他们总是把现实(“是”)看成是与应该达到的人的本质格格不入的,他们常常依据人的某一先在本质规定人之“应该”的尺度,然后以之谴责人类的现实状态(“是”);在他们眼里,一切过去和现存的都是不合理的,人类从未达到应该的某种理想状态。在马斯洛看来,是与应该的这种互相排斥的古老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二者是完全可以贯通与统一的,即通过某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②c]的“统一的意识”[③c],来实现是与应该的融合与统一。具体地,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从“是”过渡到“应该”的前提,是先认识自己,弄清自己的本性、能力、需要、愿望等。“一个人要弄清他应该做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出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达到伦理的和价值的决定、达到聪明选择、达到应该的途径是经过‘是’,经过事实、真理、现实而发现的,是经过特定的人的本性而发现的。他越了解他的本性,他的深蕴愿望,他的气质,他的体质,他寻求和渴望什么,以及什么能真正使他满足,他的价值选择也变得越不费力,越自动,越成为一种副现象”[④c]。
其次,要对事实有深刻理解与认识,从而倾听事实的声音。这是因为,“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⑤c]。“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并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别一方向前进。建筑家谈论地基重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⑥c]也就是说,事实会以其现实状况和客观必然性,对人的行为给出建议、提出要求。当然,“事实是不会高声说话的,理解事实是困难的”[⑦c]。
再次,“事实创造应该!”[⑧c]一个事物被认识或理解得越清楚、确定、真实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应性,从而就会具有更多的应该性质,它要求某些行动而不要求其他行动,从而变为行动的更佳向导。例如,一名医生在诊断时如果不能确诊,他就会犹豫不决,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但一旦他反复观察研究核实而确诊后,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他会不顾任何反对意见,而采取行动。可见,“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⑨c]。“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⑩c]。当然,不能简单地把现在的‘是’当作标准,就如同亚里士多德考察奴隶时,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因此断定“奴隶是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①①c]。而应当看到事实的内在本性,看到对“是”的未来可能、变化、发展和潜能。
而且,马斯洛认为“是”与“应该”的统一往往是以“高峰体验”的方式揭示的,在这种高峰体验中,人们往往是进入了一种痴迷的领悟状态,物我皆忘,达到主体和客体的高度融合,达到“真、美、完整、二歧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①②c]等融合。在这里,主体性不会有任何丧失,而似乎只有它的无限展开,主体从而认识到什么是“应该”的。
总之,应该性是由事实性创造的,应该是事实性认识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也就是说,事实之“是”与价值之“应该”本来就融合在一起的,对它们的割裂只能使人性受到扭曲。而马斯洛的理论通过对人性规定和生存现实的整合,既肯定了人之“应该”的超越取向,又肯定了人之现实存在作为达到应该的基础环节的意义,从而使科学人本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超越科学与人性、“是”与“应该”二歧鸿沟的理论。
马斯洛显然与自然主义者不同,他不是把价值定义等同或还原为某种事实来解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而是从人与人性出发,通过揭示科学或事实的人学意义,以及人性或价值的实证基础,凭借高峰体验或自我实现等,来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尽管马斯洛不可能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历史地、现实地去理解人与人性,也不懂得人的实践的意义,从而不可能真正解决事实与价值的分裂问题,但其人学思路、其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努力,却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从休谟到情感主义者已一再证明了,单纯从客体或客体性事实是不可能过渡到价值的,但从人或主体出发,从人的本性与规定性出发,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
4.塞尔的技术性尝试
在当代西方价值思想史上,如果说马斯洛在指出如何从“是”导出“应该”的理论基础方面的最具启发意义的话,那么,塞尔(J·R·Searle)所做的技术性尝试则是最具影响,也极富创造性的。
1964年,塞尔在《哲学评论》第73期上,发表了《如何从“是”导出“应该”》一文。在此文中,塞尔联系一个后来变得著名的反例,通过诉诸“惯例性事实”,比较精致地作了从“是”导出“应该”的尝试。
塞尔的工作是从提出一个反例开始的。当然,塞尔并不认为一个反例就能驳倒一个哲学观点,但他认为,如果能给一个有影响的反例以适当的说明或解释,并进而依据此反例提出一种理论(一种理论将生成无数反例),那么,这至少是对原有理论及其适用范围作出了某种限制。塞尔正是这样做的,他从一些纯粹事实性或描述性的判断出发,表明它们是如何与价值判断相关联的。
塞尔的例子由以下五个判断构成:
(1)琼斯说:“史密斯,我允诺付给你5元钱”。
(2)琼斯允诺付给史密斯5元钱。
(3)琼斯将自己置于付给史密斯5元钱这一义务之下。
(4)琼斯有义务付给史密斯5元钱。
(5)琼斯应该付给史密斯5元钱。
塞尔仔细地证明了,以上每一判断及其后继判断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偶然关系:从前一判断推出后一判断可能要涉及到一些其他判断,但不必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伦理判断等。例如,从(1)导出(2)是比较显明的。在一切正常情况下均成立;而从(2)到(5),所根据的主要是“允诺”、“义务”、“应该”之间在定义(内涵)上的联系,如根据“允诺”的定义,任何允诺都将人置于实施这一允诺的义务之下,所以从(2)也就能导出(3);在其他情况相同即没有推卸义务的理由时,由(3)导出(4)、由(4)导出(5)就是顺理成章的。可见,这一推导过程中的每一步,有时即便要涉及一些其他判断,但都没有依据价值判断。
于是,这里的关键在于,“允诺”、“义务”、“应该”的定义之间,为什么会具有内在联系呢?这种联系是否涉及其他的价值原则呢?例如,当一个人“允诺”了什么后,他就应该遵守他的诺言,这是否就是一个道德原则呢?塞尔则认为,无论“一个人应该遵守他的诺言”是不是一个道德原则,但它却是从两个重言式推导出来的,即从“所有允诺都是义务”和“一个人应该完成他的义务”推导出来的,可见问题仍然在“允诺”、“义务”与“应该”是否具有内在联系上。
塞尔指出,传统的“是”与“应该”、“描述性”与“评价性”(规范性)的二分图景,诸如评价性判断不过是说话者情感、态度、命令等的表达,是主观的、无真假可言的;描述性判断则是对客观存在的描述,是客观的有真假意义的;等等,这些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存在许多错误,其中之一便在于它不能解释如约定、允诺、责任、义务等概念表达的不同类型的描述性事实。例如,“琼斯结婚了”,“史密斯有5元钱”这类判断与“琼斯身高6英尺,“史密斯的汽车最高时速80公里”之类判断尽管都是客观事实,但它们是有区别的。因为包含“结婚”、“5元钱”之类术语的判断预设了一定的惯例,如一个人有5元钱便预设了钱的惯例,撇开这一惯例,剩下的不过是一张有颜色的图案的纸。塞尔把这类事实称之为“惯例性事实”,以与那些非惯例的或说原始的事实相对照。经验主义的二分图景显然不能解释这两类事实之间的区别。
为了说明“惯例”一词,塞尔区分了两类规则或协定:有一些规则是对先前存在的行为加以约束的,如饭桌上礼仪规则就是这样,因为饮食行为在这些规则出现之前就独立存在;另一些规则则不仅规范约束行为,而且还创造或规定行为的新形式,如下棋的规则与棋的存在就密不可分。前一类规则可称之为调节性规则,后一类规则则可称之为构成性或要素性规则,所谓惯例即是指由构成性规则组成的系统,而惯例性事实即是指含有这些惯例的事实。
塞尔发现,有些构成性规则系统涉及到义务、承诺、权力、责任等的多种形式,它们亦可构成惯例性事实。在这些系统中,我们就可由“是”导出“应该”。在前面的反例中,正是通过援引义务、允诺的惯例形式,才由“是”导出了“应该”。这一推导过程从琼斯说了一句话这一原始事实开始,然后援引关于“允诺”、“义务”的惯例而构成惯例性事实,从而得出琼斯应该付给史密斯5元钱的结论。整个推导过程是建立在对“作出一个允诺就要承担一定义务”这一构成性规则的诉求之上的,正是这一规则赋予了“允诺”以意义;当一个人“允诺”了什么之后,而又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他就应该去做它。当然,这样一来,有人会说“允诺”是一个评价性术语;但它又确实也可以是纯粹描述性的;因而塞尔认为,描述性与评价性之间区分必须重新加以考察,有些术语可能既不是纯描述性的,也不是纯评价性的,传统的区分并不能成立。
从塞尔以上煞费苦心,充满机智的解决方案中,我们确实可以受到许多启发。首先,塞尔关于描述性与评价性绝然二分的传统观念的责难是极有意义的。特别是他对涉及允诺、义务、责任、权力等所谓惯例性事实的研究,或者如有些人所说,对“蕴含价值的事实”的研究,给这种二分对立观念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塞尔通过诉诸惯例性事实,所作的由“是”导出“应该”的尝试是西方价值思想史上比较精致、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尝试。自休谟问题提出以来,塞尔之前或之后都不断有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性的),但多是一些原则性的、定性式的或结论式的方案与论证;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的例示性分析思路就更显独到与可贵,也使之在20世纪西方分析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更能为人理解与接受。而且历史也证明,对那些理性主义者、分析哲学家、“科学”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和所做的研究,完全用形而上的、思辨的或神学的方式去理解、去阐释、去批判、去解答,这常常可能是混乱、无效的,毕竟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风格、哲学思维方式。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塞尔的工作是局部的、不彻底的。尽管他希望通过反例举一反三,然后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理论,但他的视野与工作方式决定了其局限性。首先,塞尔看到了描述性与评价性的区分的缺陷,看到了惯例性事实的价值内涵。但他并没有更进一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根据:事实与价值均是与人相关、基于人的实践主体性的一种客观存在。在人的实践基础上,它们具有统一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事实(哪怕是“原始事实”)与价值,或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事实与价值,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均是相互关联的。其次,塞尔大体上是按照分析哲学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的,其论证也比经较清晰、明确,因而极为引人注目。但问题是,对于重大哲学问题的解决,仅仅或主要凭借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常常是不够的;分析哲学诚然有助于发现与明确哲学问题,但其功能却主要在“看病”而不在“开药方”。而哲学上的一些涉及形而上或本体论的重大问题,分析方法显然无力去根本解决它;恰恰“是—应该”问题或“事实—价值”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因而塞尔的成果也就只能是局部的、不彻底的。甚至塞尔的这种局部性的工作,其论证理由也显得不充分。例如对规则、惯例的来源、根据、哲学基础等都缺乏合理性说明,也就是说,这关键的一环还尚成疑问。分析思维的局限由此也可见一斑。
注释:
①a ②a 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8页。
③a 摩尔:《伦理学原理》,第152页。
①b 摩尔:《伦理学原理》,第3页。
②b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①c ②c ③c ④c ⑤c ⑥c ⑦c ⑧c ⑨c ⑩c ①①c①②c 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18、116、112、124、120、126、122、122、123、125、106页。
标签:自然主义论文;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论文; 伦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