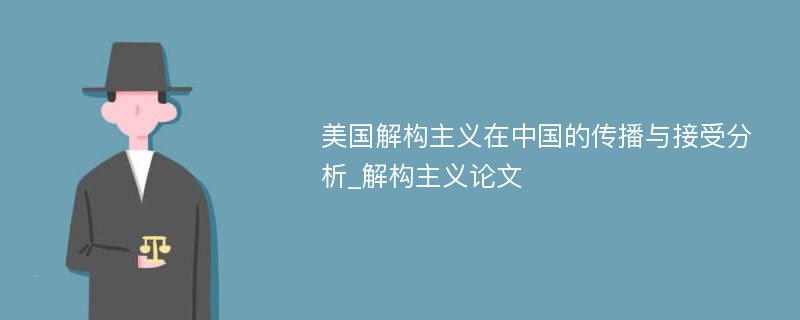
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引介与传播,可以说生不逢时而且困难重重。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法国的德里达思想为主导,而美国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则只是作为附加的介绍起辅助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文学界追求思潮的渴望超过追求方法的热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作为一种思潮进入中国的,而美国的解构主义难以承担起思潮的重任,只是作为批评方法来引介,其影响就要小得多。当然,这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构成,以及文学批评方法的前提与根基有直接关系。固然,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文学界有过“方法论”热,自然科学界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对文学批评方法起过相当大的影响。但仔细推敲,这次“方法论”的影响,还是思潮性质的影响。因为那个阶段正是科学主义影响中国的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时代的意识形态,所有西方外来的影响都要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名下才具有合法性,而科学主义则抹去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作为方法论的文学批评引入中国一直水土不服,因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方法始终是观念性的和价值论的(根本上则是道德主义的)批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自“新批评”以来的欧美现代批评方法,并未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当代批评没有一个对欧美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的训练、接受和吸收过程,解构主义这样的批评,也只是作为一种批评观念起作用,作为方法吸收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则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一、德里达“麾下”的美国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前所述,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的产物。80年代,为了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思想界寻求西方现代思潮破解单一僵化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意识引领下,现代主义开始进入当代中国。①这也注定了解构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潮观念影响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说,解构主义在文学界的影响要远大于哲学界,但文学界寻求观念性的变革的渴望也大于实际的方法论。顽强地破解历史的客观性与必然性,逃离真理的绝对性与整体性的支配,这构成了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界的先锋性思潮。在这一意义上,解构主义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思想资源。因此,以法国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先导的影响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方天地。在很长时间里,解构主义几乎是以德里达一人之名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作用的。只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作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补充,美国的解构主义才开始有所引介。
徐崇温撰写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1986)一书在当时是介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对后结构主义的介绍也还是限于法国理论,对美国的解构主义则未能提及。但在这两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在引介解构主义的同时,也涉猎到美国的解构主义,主要是对耶鲁学派做了相关阐述。1986年,两部当代西方文论的译著出版,即安纳·杰弗森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罗里·赖安等编著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这些译著均有专章涉及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或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1987年,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由伍晓明翻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顿的这本著作还有两个译本,一部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文学原理引论》,由刘峰等人翻译,另一部是由王逢振翻译的《文学理论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罗里·赖安编著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似更全面,在颇为深入讨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之后,也讨论了希尔斯·米勒和保罗·德曼的解构批评。②显然,罗里·赖安是把德里达作为解构批评的祖师爷来对待,不只是把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作为德里达理论在美国派生的成果,而且对这些成果的评价也依照它们是否保持了德里达理论的原汁原味来展开。他对米勒的批评的主要观点在于:“米勒极其害怕分解程序的虚无主义,将德里达的理论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文学本文的价值稳定论,这样,给分解程序安了一个‘底座’”。③赖安认为,在所有受德里达影响的美国理论家中,“保尔·德·曼最为始终如一地运用了德里达的理论框架”,因而他对具体本文的研究,就不仅只是有点德里达策略的味道了”(罗里·赖安138)。
赖安的这一说法值得玩味,美国的解构主义只有在始终如一地运用德里达的理论框架时,才有超出德里达的新的解构意味出现。很多年之后,德里达在为纪念德曼而做的《多义的记忆》一书中说道:“战后过了二十余年,德曼发现了解构”。德曼最初谈论解构是在《盲视与洞察》这部论文集中,但这部论文集直到1971年才出第1版,1983年再版,其中的论文如果谈到了解构的话,也不会早于1966年。如此说来,德里达称德曼“发现了解构”,只能理解为德里达把德曼过去做的修辞学批评也视为解构批评,当然,也是德曼不遗余力,才把德里达的“解构”引进到美国。1966年,他们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一见如故,开始了他们的坚定同盟。德里达认为德曼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中坚,是他的真正同道,是解构的开创者和实践家。德里达说道:如果没有保罗·德曼,在美国的解构就不可能是其所是。很显然,德里达是坚持认为德曼的解构批评有其自身的起源与开启,但欧美和中国的翻译家和研究者大都把美国的解构主义只是当作引介德里达的补充,即使在欧美学界也是持这种态度。
伊格尔顿的这本著作以伍晓明的译本较为著名,传播甚广。这本书堪称大家手笔,概述全面,左右开弓,针砭点评,文风犀利泼辣,看似随意与率性的行文,却处处有精辟独到的睿智。伊格尔顿基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立场,对解构主义批评显然持批判态度。对于美国的解构主义,准确地说,对于耶鲁学派,他更为重视德曼。他看到德曼的解构批评所具有的修辞学意义,他认为德曼的批评是在证明文学语言不断地在破坏自身的意义,文学语言恰好在好些最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显露出自己的虚构与武断的本质。这在德曼视为最为得意的创见的地方,伊格尔顿显然很不以为然。但他也肯定德曼对隐喻的重视也揭示出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意味。鉴于特里·伊格尔顿的译著《文学原理引论》在中国影响颇大,他的这些见解当给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者以深刻印象。
1987年,王宁发表《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这篇文章在详细介绍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同时,也介绍并概括了耶鲁学派的理论及其特征:(1)耶鲁学派的理论是一种“危机的理论”,即他们发现了原先所接受的理论孕育着危机;(2)耶鲁学派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解构实践中恪守自己的原则;(3)耶鲁学派因其仍然注重本文和结构分析而未完全摆脱形式主义的轨迹(150)。王宁对耶鲁学派的分析开始具有研究的眼光,去探究美国解构主义兴起的批评理论的背景,以及美国解构主义在理论上独具的特性,其文学性特征还是与德里达的基于哲学的解构有明显不同。
1988年,赵一凡在《读书》发表《耶鲁批评家及其学术天地》,算是较早直接介绍探讨美国解构主义的文章。当然,这还是一篇随笔式的文章,轻松俏皮的文风颇得当时《读书》杂志的风尚。这篇文章前两部分相当巧妙地介绍了耶鲁学派在美国文学批评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在批评转向中的变化。后一部分对耶鲁批评家的简要评析还是透示出米勒、德曼、布鲁姆、哈特曼各自的批评要点及风格。赵一凡看到,在文学批评方法陷入困局与价值虚无之后,耶鲁学派还是以它的方式开启当代文学批评的另一条路径,历史最终何去何从,固然不是耶鲁学派几个人可以左右的,但他们无疑在语言学兴盛时代,使批评具有了语言哲学的意义,并且与主流语言哲学抗衡,开启文学批评的一方天地。赵一凡的文章相当鲜明地透示出一个信息,即当代批评正在历经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中国当代理论批评界与其说具有指示意义,不如说如同当头一棒。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还在新批评、符号学、阐释学、结构主义等20世纪上半期的批评理论流派中初尝禁果,不想“流水落花人去也”,形式主义的补课,还未开始怎么就结束呢?好在关注这种信息只是极少数人,甚至追寻“新批评”一类的现代文论也是少数人,中国当代理论批评才保持住了自己一如既往的体制与惯性。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一方面受制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意识,另一方面为思想解放运动所推动。前者生发出对西方现代理论批评的引介热情,后者则使人道主义、主体论、“大写的人”的美学占据理论批评的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佘碧平在《“无底的棋盘”:解构主义思想概要》一文中比较耶鲁学派与德里达的差异(佘碧平10-16)。文章先分析了耶鲁学派的主要观点。作者分析说,在耶鲁学派中,最为突出的是保罗·德曼的文学批评。他一直试图证明文学语言在不断地破坏自身的意义。因为所有的语言必定都是隐喻式的,它们对知识的一切主张都是通过各种比喻和形象的结构来表达的,这就是文本自行解构的依据。作者认为,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上,德曼比德里达走得更远。佘碧平似乎试图为德里达的“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辩护,而赋予德曼的解构以更为激进的色彩。但陆扬的看法则倾向于认为德里达更彻底激进。在《德里达:颠覆传统的二项对立概念》一文中,陆扬认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存在“相对主义的危险”(68)。陆扬在《意义阐说的困顿——从巴巴拉·琼生观解构批评》一文中指出,就德里达之后的解构批评而言,这种解构阅读并不等同于随心所欲的相对主义模式,因为这种解构阅读给予文本以能动性,使文本自身有一种“生产性”(44)。陈晓明也认为,德里达热衷于发现非文学因素是如何决定文学因素的,从而把文学推向了一个非文学的疑难重重的领域,这种偏离文学的立场在打开阐释空间的同时,也使文学性无法辨认。而耶鲁学派的思想家们却始终关注文学文本,尽管他们在解构文学的意义的同一性,但他们并不从根本上偏离文学,而是具有相应的建设性态度(陈晓明98-105)。
二、与新批评及叙事学共存的美国解构主义
80年代是寻求思想观念变革的时代,因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才有广泛的影响力。美国的解构主义尽管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更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但它也不得不附属于德里达的思想旗帜之下。很显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其实限度清晰,知识分子都知道界限在哪里。并不是因为解放的吁求太过激烈才有风起云涌的思想博弈,实在是因为限度太窄意外触礁,才有事故频仍。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恰恰是因为语焉不详,晦涩难懂,才在八九十年代不胫而走。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像一场哑剧表演,有很热闹的手势语,但并没有声音——声音是不在场的,因为只有能指而没有所指。解构主义在中国就这样不知不觉形成一种声势,其意义也逐渐明确了起来。但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在中国则有脱离德里达的迹象,实际上,在中国的理论批评语境中,美国的解构主义略为丰富些之后,它却显得与法国人的解构主义大异其趣。把美国的解构主义安置在新批评、阐释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序列里,似乎更为妥当。事实上可能也正是如此,美国的解构主义徒有解构主义的虚名,而行振兴文学批评之实。它们在“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米彻尔语)应运而生也正说明了这点。直至多年后,米勒说“文学死了”,人们这才看清,耶鲁学派实则是文学史上抱残守缺的未亡人。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不过是长歌当哭,负隅顽抗的证词。
80年代后期,经历过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洗礼,也经历过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论以及科学主义的“新三论”的讨论,袁可嘉先生那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影响甚大,创作界对西方现代派也是顶礼膜拜。《上海文学》放出“现代派”的“四只小风筝”,④理论批评界对西方现代文论投入了充足的热情。1988年,王逢振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本书汇集了欧美14位著名的批评家访谈记录,其中对“耶鲁学派”的访谈,可以说是在当时介绍最为详尽的资料。例如,对“耶鲁激进分子”米勒的访谈,讨论了米勒对弥尔顿《失乐园》第四部的解读方式,由此透示出耶鲁解构学派修辞性分析的批评特征。米勒的解构式的修辞阅读努力去揭示出内在的矛盾关系(王逢振62-63),这样的解构,与其说解构了文学作品,不如说以独特的方式释放出了独特的文学性。因为人们关注的并不是那些意义的非完整性、矛盾和悖论,而是批评能以如此细致复杂的方式运作,文本可以展示出如此细密的修辞层次。
1988年,陆扬的《解构主义批评简述》就德曼对卢梭的《忏悔录》的“解构”展开分析。这是较早的在介绍中就有自己的观点的文章。陆扬认为德曼对卢梭的诘难明显有东一锤西一棒似是而非的解构批评特征,其偏见狭识,更是无庸赘述的。在陆扬看来,德曼的解构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一面使出全身解数,遏阻作者意向的实现,另一方面又苦心孤诣,鼎力开掘另一意义。陆扬说德曼之前早有人对卢梭的作品做过类似的批评发挥,德曼的观点算不上是一种新见。陆扬甚至认为,德曼的局限事实上也是整个解构主义的局限(22)。陆扬批评解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同时批评话语不够明晰。陆扬在那个时期就试图发现解构主义的问题,这种理论意识是可贵的,但他对德曼的批评显然还是没有抓住德曼解读卢梭的要义所在,德曼的修辞学解构,其内在意义也相当复杂,在解构的同时,也释放了卢梭的《忏悔录》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在德曼要把批评变成更为复杂的理论结构时,如果把它还原到明晰性这一点上加以质疑,可能还显得不够充分。
包亚明的《躺在解剖台上的〈忏悔录〉》(1991年)也关注到了保罗·德曼对卢梭《忏悔录》的解构式重读。包亚明试图打开德曼的重读,他阐释说,德曼就《忏悔录》中的辩解与忏悔、羞耻心与暴露欲构成的多重歧义和差异展开分析。他这样描述德曼阅读的独特方式:“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互相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5)。这些引介未必十分周密和到位,但给当时的中国文坛输送的理论批评信息则是令人兴奋的。
郑敏的《20世纪大陆文学评论与西方解构思维的撞击》对解构主义理论与批评做了肯定性的引介,主要是探讨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未涉及美国解构主义。在90年代对耶鲁学派介绍较为详细的论文当推盛宁的《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文本”的解构》。这篇文章分别评析了德曼、米勒、布鲁姆、哈特曼的解构批评,对各自的解构批评的特点要点做了相当精当的概括,比较清晰地勾勒了耶鲁学派的批评图景。
对耶鲁学派的关注重点一直在德曼和米勒身上,这或许在于这二人的解构特征更为鲜明。也可能是因为,德曼在耶鲁解构学派一直是领头羊,而米勒与中国关系密切,多次来过中国。相比较而言,对布鲁姆和哈特曼的关注则少得多。张德兴的《哈特曼解构主义理论述评:在批评的“荒野”中求索》(1988年)一文较早关注到哈特曼的解构批评。作者分别从语言的错综复杂、意义的不确定性、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英美批评与德法哲学结合起来的思路等方面归纳哈特曼的批评思想,比较准确全面地概括了哈特曼的批评理论。当然,作者只是依据《在荒野中的批评》一书,哈特曼著述甚丰,一篇文章也未必能全面反映哈特曼的批评思想。罗选民、杨小滨的《超越批评的批评》是一篇对哈特曼的访谈录。在访谈中,哈特曼谈到了自己对阐释学、英美批评、比较文学、福柯的看法,并提及了对诗人华兹华斯的解读,对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97-105)。
哈罗德·布鲁姆在中国的研究则要晚近得多,在引介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时,顺便谈到耶鲁解构批评,主要也是德曼和米勒,有时提到哈特曼,布鲁姆则更是少见。王万昌在《解构主义美学观及其方法论》(1994年)中对“耶鲁四君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这篇文章论述到布鲁姆,他主要是对布鲁姆写于1973年的《影响的焦虑》一书的观点做评述。他认为:布鲁姆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而提出“影响的焦渴”这一理论。每个诗人(包括作家)都面对传统的压力,要追求独创性就要同前辈对抗,但又摆脱不了前辈阴影,因而陷于影响的两难处境。这篇文章还讨论到布鲁姆的《误读与指南》(后翻译为《误读图示》),王万昌认为这部著作超越了“文本交织”的新批评理论,而使批评转向解构方法,开启了更为活跃的解构批评空间(92)。这篇文章同时也看到,耶鲁批评家们去除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区别,文学批评家们因此获得极大的精神自由,这就是文学批评的解放。
1995年,张德劭翻译的阿布拉姆斯(M.H.Abrams,1912— )的《解构主义的天使》一文分析了德里达和米勒的思想,尤其对米勒进行了尖刻的批评。这篇文章在美国影响甚大,在中国则反应平平。在美国,这篇文章几乎标志了新批评与解构学派的决战;在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语境,也没有这样的预期。阿布拉姆斯在中国以《镜与灯》著名,影响早于米勒。他这篇文章的英文原文发表于1977年,正是美国耶鲁解构批评方兴未艾之时。阿布拉姆斯作为新批评的宿儒,此番出马对米勒开刀,文章写得酣畅淋漓,可见宝刀未老。针对米勒宣称的文本无法确立自身的意义,文本的内在分裂倾向于文本没有意义。阿布拉姆斯则首先承认他选择的文本意义是含混的,不能完全确定的,但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是有意义的,而这一种意义对于他要讲述的故事就足够了。阿布拉姆斯认为,米勒的问题在于认为“所有的意义都是不可能正确的”,这种说法难以成立。而且他也不同意米勒下述的说法:文本没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一旦确立一种正确的解释,其他不同的解释就会抵制这种解释。米勒受到尼采的影响,文本的意义是从外部注入的,而文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取决于谁是主人,谁输入了意义。阿布拉姆斯不认同米勒这种说法。阿布拉姆斯也引述米勒的“迷宫说”,但他认为,阅读与批评就是阿里阿德涅的那根线,忒修斯就是循着这根线走出迷宫的。米勒则认为,文本有这样的一根线,批评家循着这根线则要走到死胡同,那就是文本/解释的终点。这根线与其说指明逃出迷宫,不如说制造了迷宫。
阿布拉姆斯分析了米勒的那些鲜明而极端的说法,从而使其自相矛盾。这是对解构的解构,虽然坚持的是新批评立场。阿布拉姆斯说,所幸的是,米勒并非对自己所言是认真的,他是“双面间谍”,一套是解构主义的言说,另一套是可以与他交谈的言论。他确信,米勒是可以准确表达他的思想及意图的,也能为大家理解接受。思考的主体表现出独特而稳定的气质,带有自我的情感。让米勒回归意义的可理解性,阿布拉姆斯也用这种方式解构了米勒。解构“解构批评”的方式,可能就是让其回归可理解性,以及意义的准确与完整。阿布拉姆斯对解构的批评,也给国内批评理论提示了一个反思的角度,但实际的情形是,国内的文学批评并不在乎米勒们是否否定文本意义的可理解性和完整性,而是从他们解读文本的细致方法中去探寻中国文学批评的新途径。
进入90年代后,女权主义批评在中国开始崭露头角,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也陆续介绍到中国,而这些女权主义批评有相当多都受到解构主义影响,也可以归属于解构主义批评的行列。张京媛翻译的美国批评家玛丽·朴维的论文《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朴维试图把解构主义引入女性主义,以此达到双重改写的目的。既去除解构主义的父权制残余,也去除女性主义的神秘性。这篇文章同时指出法国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结合存在的问题,即依然与父权主义有同谋的嫌疑。作者要使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达成一种更有效的境地。“如果解构主义认真对待女性主义,它将不再是解构主义;如果女性主义按照解构主义所说的来理解解构主义,我们就可以开始拆毁把所有妇女都归纳到单一特征和边缘位置的系统”(玛丽·朴维69-74,20)。作者给出了一种理想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太过完美和理想,以至于它很有可能也留下了更多的解构的把柄。
林树明翻译的克里斯·威登的《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试图拓展女性主义的理论空间,建构一种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关注语言的意义问题,把阶级、种族以及与之相关的父权社会的局限性结合在一起来考察,由此揭示女性的审美途径。作者指出,只有广泛而缜密的当代分析才能展示妇女特性的范围及其成因。作者试图从解构主义的内在对立项,引向对外在的社会情境考察,去关注主体性、话语与权力,寻求一种对所有的社会与政治实践都适应的框架(68-70)。
王宁在1998年发表《解构、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评》,从解构的角度来论述斯皮瓦克的批评理论,王宁把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方法归结为解构,这是有见解的。斯皮瓦克通过翻译德里达的《文字学》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她的女权主义锐利之处也在于她较早掌握了解构主义的方法。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是在观念意义上强调女性的立场和价值关怀,因为缺乏解构的观念与方法,中国的女性研究还很难具有激进性和批判性。斯皮瓦克后来把女权主义观念与后殖民理论结合起来,女权主义一旦打上种族的烙印,实际上是被种族问题所替换。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套“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这套书由王逢振任主编,另一主编名下希利斯·米勒赫然在目。这应该是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有力度的一个事件,尽管很可能米勒的主编只是一个象征,但这一象征足以表明美国的解构批评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这套丛书在90年代后期直至21世纪初期影响甚大,其中有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陆扬译),希尔斯·米勒的《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保罗·德曼的《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可以说是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最为隆重的一次集体登陆。这几本书都是美国解构批评的代表之作,《论解构》是乔纳森单独成书的作品,《重申解构主义》则是米勒专为中国读者选择的代表论文的汇集,《解构之图》没有版本出处,封底有说明是米勒和德曼遗孀共同选定的编目。陆扬的翻译因为是个译,功夫到家,另二本是多人合译,显得有些匆忙。但这几本书作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示范与普及,也是绰绰有余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因其哲学性较强,且涉猎的哲学背景和思路怪异,可以启迪,难以仿效;美国的解构批评毕竟是直接拿文学作品操刀,故而方法论的示范意义就现实得多。
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一套由申丹主编的“新叙事理论译丛”,首先面世的米勒的《解读叙事》,可以说是解构主义的叙事理论。当然,解构主义根本上是反叙事学的理论化倾向的,米勒的《解构叙事》也视为“反叙事”。随后陆续出版的几本叙事理论著作,如《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修辞性叙事理论》、《新叙事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等,在不同的程度与方式上,都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关联。
200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由朱立元主编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德曼《阅读的寓言》(沈勇译),米勒《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布鲁姆《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这套书包括了耶鲁学派的代表作,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可以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三、中国视域中的美国解构批评
相对于德里达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国的研究传播,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则直至90年代后半期才陆续展开,介绍性的文章居多,深入的研究就较为有限。这些文章主要还是关注它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之同异比较,国内的接受也乐于在新批评与叙事(述)学的这个理论框架里来讨论耶鲁学派,并未更多关注它与新批评和叙事学的区别。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也一直想补上文本细读这一环节,这与文学创作“向内转”的先锋派文学潮流多少能够呼应上。但批评实践显然没有跟上趟,只是有限的浏览和局部的借鉴;而研究性的评述要多于在批评实践中运用的借鉴。
如前所述,王逢振较早介绍耶鲁学派及米勒的批评,他依据当时国内对现代派的形式主义研究,在文学理论的意义上则是尽可能与叙事学相结合。因为当时国内对文学理论与批评最为焦虑的创新追求,那就是形式方面的意义。王逢振的书一俟出版,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程代熙先生就写有书评发表,这篇文章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其页末标注时间是1989年1月16日。那时正值新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了了之,国内改革呼声重新抬头,思想解放运动又有所推进,也就是改革的思潮占据主动地位,故而一向批判西方现代派的程代熙也撰文对西方现代派宽容有加,甚至认为米勒这种解构批评学派也很有启发意义。但是,显然与著者王逢振偏向于叙事学和修辞学方面对米勒的介绍不同,程代熙从王逢振对米勒的介绍中,读出了米勒对九十年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预测的核心思想是:文学创作要走出作家的象牙之塔,文学以及文化的研究决不是对文学和文化自身的研究。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要进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
程代熙认为:米勒的这个思想比起那种认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文学“内部规律”的所谓理论来,倒更符合文学的实际。他依据的是米勒下列言论:“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对实际条件做出反应的唯一方式,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得以展开的文化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做出反应的唯一方式”。他说:“退一步讲,分解主义者希·米勒的这些预言即使在下一个十年全都没有言中,他的这个启示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113)。程代熙对米勒的肯定,在于把米勒的批评理论与现实、时代发展这些现实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有些误读。对于程代熙先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来说,他要肯定西方某种理论批评,只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相悖离才有可能。他对王逢振这部书的关注,也是关注那些能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论题,如杰姆逊的第三世界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对新历史主义批评,他引述有巴勒斯坦背景的赛义德的观点,强调新历史主义回到历史实际的可能性,对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则试图发掘它与现实主义的基本规范不相矛盾,这些都显示了程代熙先生“独具慧眼”的发挥。这也说明一个时期的外来的理论,如何被本土的理论批评语境所“规训”,理论旅行终究在归属地获得了另一种意义。
中国当代对耶鲁学派解构批评的翻译和研究,并未追究其解构思路的运作,而是关注其文本细读方法。在国内的研究者看来,耶鲁解构学派与新批评、叙事学相去未远,或者说同属于一个批评谱系。这一点可能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态势使然。因为,新批评和叙事学也才方兴未艾,正在打基础,猛然间出现耶鲁的解构学派,新批评和叙事学似乎已经被超越。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建设,只有把耶鲁解构学派融进新批评和叙事学的语境,可能才有利于其传播与理解。如果没有新批评和叙事学的知识前提,要理解耶鲁解构批评可能会困难得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的研究者在叙事(述)学的谱系中来讨论耶鲁解构学派。
也是在这种语境中,申丹在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年)中对米勒关于小说重复的理论展开讨论。申丹着重探讨了米勒对《德伯家的苔丝》的重复问题的研究,申丹也关注米勒的重复问题引向文本之外的社会现实、生活心理等等。重复再现了作家在其他文本中出现的因素,也再现了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神话和传奇的模式。申丹谙熟欧美批评的知识谱系,她指出了米勒对互文性的探讨与叙述学和文体学的差异,把解构批评放在叙述学中来探讨,目的还是着眼于解构批评的文本细读和对文学性的更为自由的释放。2003年,申丹在《结构与解构——评J.希尔斯·米勒的“反叙事”》一文中相当全面地评析了米勒的“反叙事学”(271)。围绕米勒的《解读叙事》,申丹一直关注米勒的解构批评与叙事学融合的地方。她认为,米勒对解构主义的信念从根本上说没有动摇,但他在新的形势下“对解构主义批评显然也进行了一些反思”。申丹对米勒的“反叙事学”的解读表明,米勒这样的解构批评也在吸收一些文化批评的因素,名之曰“反叙事学”,实则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对立,米勒明显有意吸取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些批评术语和概念,“这给他的解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分析工具;与此同时,米勒的‘反叙事学’也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宏观层次,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照和借鉴”(271)。申丹也力图把米勒后期的批评思想赋予更充足的建设性意义,与中国当代的叙事学研究语境有更大程度的协调。这一路径可能更具有实践意义,中国当代的观念性解构由德里达给予的解构理论已经足以承担(本来就是有限的解构),而批评方法和文本细读的理论借鉴,则需要更加多样的理论批评的参照,把米勒归为新批评和叙事学这一脉落,可能更具有现实感。申丹对米勒的分析表明,米勒在《解读叙事》中,实际上还是包含了相当充足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因素。这与他早年的《小说与重复》对那些英美小说与诗歌的分析相去未远,根本在于米勒的批评方法始终是文学话语的形式构成方式切入分析,那些语词的修辞、叙述结构上的对应、悖离或重复关系,都有一种形式上的关联所在。结果是它们的解构并未完全拆除它们的内在关联。
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深受观念性的支配,尽管现在的意识形态规训实际并不能直接起作用,但长期形成的在观念意义和价值意义上讨论文学的思维方式难以改变,这就是“新批评”以来的文本细读批评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扎下根来的缘由。耶鲁的解构学派要直接与“新批评”对抗,在“新批评”把文学文本神圣化和审美化之后,新一代的文学批评如何开拓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耶鲁的解构学派声称要往外拓展出社会现实内容,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在修辞的天地里扯开一道裂罅,透进一点社会现实的光亮而已。耶鲁学派也只是扰乱了“新批评”的意义整合性和完整的内在结构,它们本质上都属于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在渴望批评全部外部世界的文学批评群体中,这样的文本细读显然不能满足其从来没有压抑下去的社会现实关切心理。在欧美,文本细读的解构批评方法也必然要被更加宽泛和广阔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研究、女权主义、性别身份研究、流散研究等更具有社会现实性的批评视角所取代,文学批评已经不可抗拒地转化为文化批评,但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则是其文化/政治观念表达的基础。这里面也可看出耶鲁解构学派的文本分析方法已经深深渗透进欧美的批评实践,只是被观念性的弥漫所遮蔽而已。布鲁姆后来在《西方正典》(英文版1994年,中文版2005年)里批评那些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形成的各种流派,不无严厉地斥责为“憎恨学派”,但布鲁姆也回天无力,文学批评之衰落,其被文化研究所取代是难以避免的学术潮流,历史总是在变异中重新开始,但文化研究涵盖一切的做法,仿佛在表明变异的终结,甚至方法论的终结,这倒是一个不祥的后果。
但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可能还有自我更新的机遇。因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没有补上文本细读这一课,也始终没有真正深入全面地吸取欧美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它还是停留在浏览与“拿来主义”的阶段。因为它没有欧美批评那种秩序井然的替代式进步,如此,它可以在重新综合与广泛吸取的基础上,寻求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还是相当旺盛,传统文学的写作者业已老道,汉语白话文学的语言也已炉火纯青,这给文本细读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场域。当然,这有赖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摒除浮躁功利的学风,真正立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以开放、自由、睿智的形式,广泛吸取欧美文学理论批评已经取得的成果,形成能充分体现汉语文学艺术品质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才可能真正在世界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注释:
①参见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1982):115-17。徐迟的文章引发了那个时期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可见现代派引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现代化”的前提下。
②有关论述亦可参见陈晓明、杨鹏:《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2002年)186。本文有少量资料参考这本我多年前与杨鹏合作的著作,在此向杨鹏表示感谢。
③这段话出自罗里·赖安引述里德尔的话,显然,赖安是十分赞同里德尔的观点的。里德尔的原文参见:Riddell, J.N.“A Miller’s Tale.”Diacritics 5(1975):65.
④高行健于1981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起王蒙、李陀、冯骥才和高行健之间讨论,他们四人之间的通信和讨论被称为“现代派的四只小风筝”。参见《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专栏。随后《文艺报》、《人民日报》、《读书》展开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
标签:解构主义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哈特曼论文; 布鲁姆论文; 德里达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忏悔录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