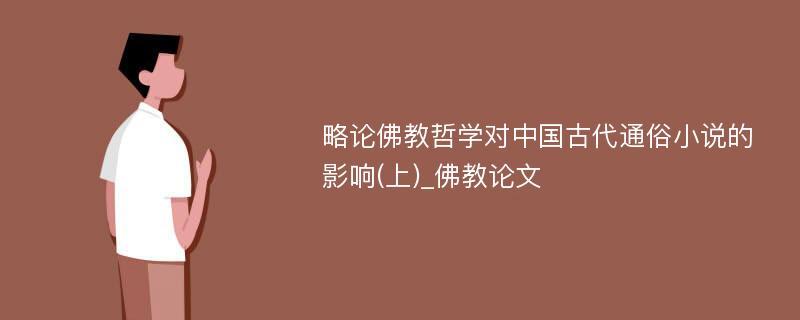
略述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影响*(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中国古代论文,通俗论文,哲学论文,略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研讨
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以来,至今已经延续了2500多年。它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逐步生根、成长,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结构,形成了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佛教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不断改造、补充,从而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互融汇;另一方面,佛教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广泛的、深刻的、持久的影响。佛教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影响就不可忽视。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从语言媒体上看,大致可分为两股脉流:一是以魏晋志怪、唐人传奇为代表的文言笔记体;一是以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为代表的通俗说话体。文言笔记小说与佛教的关系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此处我们仅就佛教对古代通俗小说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概括和粗勒的描述[①]。
佛教对古代通俗小说的影响,具体说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哲学对通俗小说思想内容的渗透,一是佛教文学对通俗小说写作艺术的启发。
本文重点探讨前一方面的内容,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另文专论。佛教哲学是佛教全部教义的思想基础,换句话说,就是佛教教义中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部分。佛教著作都是从其宗教道德实践要求出发的,都是为了论证人生寻求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它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归根到底都是为解脱论提供论据的。因此,佛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包融于佛教的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的。所以可以说,佛教哲学是一种宗教哲学,也是一种人生哲学。而“文学是人学”,文学也是以对人生问题的探求为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属的。对人生的探寻可说是佛教与文学的一个交汇点。佛教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思想观念。佛教六道轮回,善恶报应、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等哲学观念,给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注入了新的因素。这里,我们侧重从因果报应理论和空幻思想在古代通俗小说中的体现作些描述与探讨。
首先,我们谈谈通俗小说中的因果报应问题。
大家知道,因果报应亦即业报轮回。它是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并支持其宗教体系的基本理论。释迦牟尼宣传业力是众生所受果报的前因,是众生生死流转的动力。众生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志,从本质上说就是“业力”。“业”,是行动或作为的意思。作一件事先有心理活动,是意业;后发之于口,是口业;表现于身体上的行动,为身业。佛教认为,众生的身、口、意三业往往是由无明即无知决定的。众生是无我、无常的,没有自体,终归要消灭的,众生却要求它有我,要求它永恒不变。众生的行为往往就是这种无知的表现。众生由于这种无知而发生的行为,就是痛苦的总根源。业,体现着力量和作用,功德和过失。释迦牟尼认为业力的影响是不会消除的,众生所作的善业和恶业都会引起相应的果报。业力千差万别,感召的结果也大相迥异,但概括起来无非是有漏、无漏二果。有漏是指生死轮回,无漏是指超脱轮回。有漏果是有漏业因所致,有漏业因分善恶两类,善有善报,可在六道轮回中得天、人果报;恶有恶报,只能得畜生、地狱果报。无漏果是无漏善业所致,可成就阿罗汉、菩萨和佛。
佛教这种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理论,与中国儒家的善恶报应说和传统的鬼神崇拜融合起来,变得更加形象具体,也更加简化通俗。佛教的教义玄奥而繁杂,制度和仪轨多如牛毛,各类典籍浩如烟海。但对中国下层民众来说,佛教又是极其简单易懂的,人们甚至把全部佛教哲学都归之于因果报应。这一点,太虚法师在《中国佛学》的开篇就谈得很清楚。他指出:
佛法由梵僧传入,在通俗的农工商方面,即成为报应之信仰。在士人方面,以士人思想之玄要、言语之隽朴、品行之恬逸、生活之力俭,遂形成如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等简要的佛学。可见,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其教理在一般士人和普通民众中都有简化的趋势,只不过简化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世俗民众主要接受了轮回业报观念,士人则偏于禅悦。后者影响所及,主要是文人雅士的诗文书画,此处不论。前者的影响却与通俗小说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中国的小说在封建时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一直比较接近下层民众。早期文人创作的志怪和传奇就多取民间传说,宋、元以后的长篇、短篇白话通俗小说更是与民间说唱文学血脉相通。通俗小说的流传面与接受者较之正统的诗文,也更偏向社会下层民众;而通俗小说的作者、编者也多为下层文人,他们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心理、审美情趣都比较了解。与小说相似,佛教的传播,从一开始也是比较重视普通民众的。在中国,民俗佛教有着它独特的内容和更为普及的发展天地。佛教关于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佛法无边等等思想观念,以粗俗、幼稚但又富于形象的感性形式流传于民间,并被纳入民间文学艺术之中。这样,民俗佛教信仰和佛教观念,就很容易与通俗小说结合起来。[②]另外,我国通俗小说盛于明清两朝,而这一时期佛教是净土宗占统治地位。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故有此名。净土宗奉慧远为主,极力提倡业报轮回;其理论简单,法门简易,适合于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明清佛教中净土宗的昌盛,自然也助长了通俗小说的写因果之风。
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思想在世情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中都有充分的展示。分别举例说明。
1.世情小说中的人物命运
鲁迅先生把记人事的小说归类为世情小说。这类作品主要写世俗社会、世态人情,写发迹变泰、离合悲欢,贴近现实,反映人生。因为这类小说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心理隔得很近,因此作者十分重视其劝诫作用。他们往往把小说作为人生的一面镜子。这样一来,果报不爽、六道轮回、佛法无边等思想观念就常常浸润着长长短短的世情小说了。
《金瓶梅》是世情长篇小说中开风气的作品,也是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市井恶棍西门庆为中心人物,描写了他的经商、理刑、结交官吏、仰攀权贵,尤其是嫖妓请客,偷奸淫占以及妻妾争风等故事;暴露了流氓恶霸的横行无道,荒淫无耻;描绘出一幅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百丑图。小说通过西门庆由发迹到灭亡的丑恶史,形象地说明欲海无厌的可悲下场。但又把人生的命运归结为生前命定,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倾向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又一部以婚姻为题材,以一个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这部长达百万字的百回本通俗世情小说,具有明显的、浓厚的佛教思想色彩。作品主要描写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历史背景是从明代英宗正统年间到宪宗成化以后。头22回为前世姻缘。写山东武城县官僚地主之子晁源无行,娶娼妓珍哥为妾,携妾围场,射死一只仙狐。又纵妾虐待正妻计氏,将计氏冷落一隅。计氏次兄告到县衙,晁源上下贿赂,县葫芦提结案。后遇一个清正的李观察巡视武城,才把珍哥判死刑押监。晁源又与一皮匠之妻通奸,被皮匠发现后杀死。第23回以后,作品仍不时继续述及武城晁家。晁源之母鉴于丈夫、儿子的恶果,一心行“善”,扶难救灾,救助穷人,和睦乡亲,结果是百姓感戴,皇帝嘉奖,寿过百岁而登仙。珍哥在狱中与狱吏通奸,用调包计潜出监狱,案发后被拷打而死。小说后来着重写的是今世姻缘,地点移至绣江县明水镇:晁源脱生为地主之子狄希陈,顽而不学,凭侥幸和银子捞了个秀才、捐了个廪生,靠走后门做了城都府经历,敲榨5000两银子致仕还乡。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恣意凌虐丈夫。新婚之夜,拒丈夫于门外。后又不断地把狄希陈监禁在屋中,用针遍身扎刺,用嘴咬掉狄希陈胳膊一大块肉,又用棍棒毒打600下,把炭火倾在狄的衣领之中,以至于用箭射狄,要结果他的性命,种种悍泼,无所不用其极,为避薛氏之虐,狄希陈躲到京城,又娶计氏脱生的童寄姐为妾,这小妾对他也是手打口咬,倍加欺凌。珍哥托生为寄姐的婢女珍珠,受冻挨饿,时常被锁在屋里,终被寄姐逼凌自杀身亡。最后,经高僧点明因果,狄希陈诵一万遍《金刚宝经》,终于才“福至祸消,冤除恨解”。通览整部作品,复杂的人物关系、人物命运,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因果相报的循环链,其间的佛教思想无疑是消极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佛教与小说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我们又不能视而不见。
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从内容题材或思潮流派上看,也当归入世情一类。“三言”“二拍”中涉及善恶有报的作品可说俯拾即是。《喻世明言》(初名《古今小说》)的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体现了善恶报应的思想观念。小说大意是:商人陈大郎设计奸骗了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从此恶运迭降,人财两空:财物被劫,自己重病身亡,妻子被迫改嫁,而所嫁之人正是已与王三巧离异的蒋兴哥。这可谓恶有恶报。与陈大郎命运完全相反,蒋兴哥是善有善报,“捷报频传”:他识破了妻子奸情后,宽厚仁义,给王三巧一条生路,结果在生死关头巧遇王氏,幸得救援,并且破境重圆。小说的作者还生怕读者不能体会这因果报应的意旨,因而一再出面教诲。小说开头说“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中间又有“一报还一报”的字句,篇终再强调“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可见,这篇小说是通过一个市井商人的家庭婚姻纠葛,来宣扬善恶有报的观念,是“劝善惩恶”的老套子。但就作品整体看,“形象大于思想”,作品的思想蕴含是丰富的,其中也有积极的、进步的因素,这里不多说。
《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写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小手工业者之间的友谊,其中也流露出因果报应的创作意旨。小说主人公施润泽拾金不昧,归还失主;危难之时,幸得那位失主无私援助,家道日盛,富甲一方。作者着意指出前后事件的联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祸福,自作自受。”
“三言”“二拍”中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一些。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即宋元之后的佛教是与儒、道相融汇的,是三教合一。因此,佛教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往往是与儒家和道家相结合而进行的。我们还是举一篇《醒世恒言》中的作品来谈谈这个问题。《灌园叟晚遇仙女》一篇,写“花痴”秋先爱花如命,乐善好施;而宦家恶少张委恃势作恶,欲霸占秋先的花园,欺负善良。结果是乐善之人得仙女相助,得道升天;作恶之徒被仙女惩处,一命呜呼。这篇小说写的是出世入道的道教人事,里面却包孕着善恶有报的佛家思想。
清初的《金云翘》也是一篇佛、道、儒思想相互交融的世情小说。作品写一个妓女半生颠沛流离、倍受磨难的经历,中间穿插了观音阁写《华严经》、招隐庵写盂兰大会等有关佛事的情节。这些又都与主人公王翠翘命运的转折有关:写经使她有机会逃出妒妇宦氏的魔掌,写盂兰会使她逃难得逢徐明山。这都属于紧要“关目”。小说最后借一个道姑之口解释王翠翘“以何因缘,堕此恶趣”,道是:“大凡人生世间,福必德修,苦因情受。翠翘有才有色,只为情多,遂成苦境。”又说:“功德大而宿孽可消,新缘得结矣。……俟其钱塘消劫时,棹一苇作宝筏,渡之续其前盟,亦福田中一种也。”这是标准的佛家口吻,宣传的是因果报应,其中一些用语如“因缘”、“苦境”、“一苇”、“宝筏”、“福田”等纯系佛门行话,有趣的是这些言语出自一个道姑之口,而议论中还涉及一些“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信条。这可说是一段典型的三教合一的描写。顺便提及,《金云翘》曾传入越南,被改写成叙事长诗,影响很大。
在一些世情小说中,作者虽然意在宣扬善恶有报、劝善惩恶,而实际上作品的客观内容却揭示出更深刻的道理,《警世通言》中的《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便是如此。小说写浮浪子弟张荩与潘寿儿有情,市井无赖陈五汉乘暗夜骗奸了潘寿儿,并杀了她的父母,杀人罪却落到了张荩头上。后来张荩使银子买通了牢狱看守,得以和潘寿儿对证,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作品中,作者也一再宣扬因果报应,开头的诗句有“爽口食多应损胃,快心事过必为殃”最后又说“奸赌两般都不染,太平无事做人家”。其劝诫味一目了然。从作品中看,人物的命运似乎是果报不爽的反映,而实际上是“银子”这个最世俗的东西起了作用。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城市经济发达的社会条件下“金钱”的力量。而作者把它曲解为冥冥中的佛的力量,显然是用佛教义理曲解现实问题。[③]
业报轮回是世情小说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为什么它如此盛行不衰、深受作者与读者喜爱呢?这要作点具体分析。众所周知,业报轮回说强调个人作“业”的作用,强调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这客观上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劝诫和约束作用;主张人们的活动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得到报应,这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善恶有报是有条件的,在阶级社会,人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阶级地位,而非个人作“业”。行善者蒙祸,行恶者得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佛教在伦理道德上笼统地宣扬因果报应的善恶祸福一致论,至多只是对个人心理的安慰而已。它把现世的祸福归结于前生所作的“业”,而现世所作的“业”要待死后由神明裁判,这种神学构实际上也等于承认现实中的善恶与祸福是不一致的。由于这种佛教理论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让人们安于现实,因而统治阶级是提倡的,支持的。它在通俗小说中被以艺术的形式加以宣扬,自然是统治者所欢迎的。另外,从小说的主要读者——下层民众看,善恶有报与其说是他们的生活现实,还不如说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封建社会是个等级结构,如果从伦理角度去看社会矛盾,那就是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伦理型的对立。但是现实中的天平总是向坏的恶的方面倾斜。马克思曾指出:“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有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④]这种情况,就形成了人们从不平衡中求平衡的伦理心理定势,希望好的方面压倒坏的方面,将现实颠倒了的矛盾,从意念上再颠倒过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使在现实中无法达到,在小说世界中体现也是一种精神的抚慰。就像佛洛伊德所认为的,“梦是人生愿望的替代性满足”,通俗小说中的善恶报应论也正是普通民众心理补偿和满足的一种替代品。这也正是报应论主题通俗小说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2.历史题材小说中的果报观念
佛教强调因果律的普遍性。在时间上,因果遍于过去、现在、未来三时,因果相应,如环无端,本无生起之时,也无终止之日。在空间上,宇宙结构中的人类社会、各种天界和地狱等,因果率都发生作用。佛祖释迦牟尼把十二因缘和业力、轮回的思想联系、统一起来,用业报轮回说,来说明众生的不同命运。佛教认为,芸芸众生的生死流转,永无终期,犹如车轮旋转不停一般。佛教这种业报轮回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影响颇大。
在宋元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中,作家常常用业报轮回来解释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因由。宋代讲史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就写道:
刘季杀了项羽,立着国号曰汉。只因疑忌功臣,如韩王信、彭越、陈豨之徒,皆不免族灭诛夷。这三个功臣抱屈衔冤,诉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着个曹操,彭越去孙家托生做着个孙权,陈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个刘备。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
这部作品概述梁、唐、晋、汉周五代盛衰变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阀混战、封建暴政的罪恶和人民在不义战争的长期混乱中所受的屠杀和掠夺。但作者把历史事变套到因果报应、灵魂不死的框子里,无疑对作品的思想认识价值有所削弱。这种因果报应、死生轮回的写法,在元人编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等作品中也出现过,《古今小说》中的“司马貌断狱”亦有类似的情节。元人编刊的另一部讲史话本《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是一部纯粹的通俗历史小说,忠于历史,朴实无华,但其中对历代兴亡的评论也明显带有佛教果报色彩[⑤]。如作品结尾写道:
则知秦尚诈力,三世而亡。三代仁义,享国长久。后之有天下者尚鉴于兹。在佛家看来,大至时代兴亡,小至人物遭迹,皆无不与作业有关。前世善恶今世报,今生作业系来生。《梁武帝演义》中郄后生前为非作歹,死后地狱受刑;《警世阴阳梦》中的魏忠贤活着祸国殃民,死后阴间受审。古代通俗小说中这类情节、故事随处可见。真可谓“佛光普照”,不仅现实中的人,而且连已作古的历史人物也难逃业报轮回的定律。芸芸众生在无边的佛法中,都难逃“魔掌”。
更有甚者,像《说岳全传》这样的小说,本来是写民族斗争和忠奸之争的,但由于佛教思想的流行,也深受佛教思想的浸染。《说岳全传》,全称《新增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清代康熙年间钱彩、金丰在岳飞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的基本史实基础上,集南宋元明以来民间传说、戏曲、小说的岳飞故事之大成,编订成一部八十回本的章回体通俗白话小说。这部小说一问世,就以其深厚感人的思想内容、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群众喜闻乐见的讲史形式和通俗晓畅的语言风格,吸引了广大读者。但它对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过分宣扬,又用因果轮回报应给岳飞故事戴帽穿靴、开头结尾,显然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且看业报轮回在小说中的反映:在该书第一、二回里,把金兵的入侵描绘成是因宋徽宗得罪了玉皇大帝,玉皇遂令赤须龙下界,降生此地女真国,扰乱宋室江山,是为金兀术;而岳飞则是如来佛头顶上的护法神大鹏金翘明王所变,因如来怕无人能制服赤须龙,故遣其下凡,保卫宋室江山。岳飞与秦桧、王氏的斗争,在书中变成是一种因果报业——因岳飞之前身大鹏金翘鸟曾啄死女土蝠,故女土蝠投胎王氏,嫁给秦桧,专门残害忠良,以报前仇;大鹏鸟在下凡之前又曾把铁背虬王左眼啄伤,后虬龙投胎秦氏,即为秦桧,故秦桧后来之陷害岳飞,也是报大鹏啄眼之仇。如此等等,一切都是上苍安排,因果报应。这些内容无疑是牵强附会、十分荒谬的。
《梁武帝演义》的模式用的也是“转世”的框架。作者在小说主体部分外,套上一个因果关系,说明故事中的发生的一切都是前缘注定。作品中的人物是身负宿因投胎转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在生前注定,而结局则完全是宿命的。在《梁武帝演义》中,主人公梁武帝与郄皇后为佛前两株仙草——菖蒲与水仙下凡,历经劫难后又同归佛前。小说写仙草(且为素雅之草卉)转世,这与《红楼梦》的绛珠之构思有些类似。作品写水仙下界投胎母腹中时,恰好碰上其母“一点怒僧之念,一如火发”,结果使这佛门名卉改铸了性格,变得嫉妒残暴、视僧如仇。这样,她的命运也套进了两重因果框架:由前世的仙缘而得享富贵,受宠爱,得善报;由今世的孽缘而倒行逆施,谤僧毁佛,终得恶报。[⑥]
因果报应观在另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后水浒》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后水浒》是写杨幺起义的故事。这本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题材的,但作者却把这原本独立、完整的故事套到了一个前世因果的框架中。小说开端借罗真人之口交待出宋江等三十六人将转世重聚,“以完劫数,以报奸仇”,而杨幺即为宋江转世;篇来写杨幺等人“脱去躯壳,各现本来面目”,业消而劫完。
诸如此类关涉果报观念的历史题材小说世情小说还颇不少。虽说这种佛教观念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只是表层的、外在的、粗浅的,但却是全面的、广泛的。这种因果报应思想的反复出现,对作品的思想价值有所削弱,对读者的影响也主要是消极的。但是也应看到,这种报应观念、轮回思想的艺术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还是有劝诫和约束作用的。此外,袭用因果报应模式翻奇出新、增强作品思想内蕴的也不乏其例,《红楼梦》就是这样。这部名著不仅采用了“转世”的因果框架,而且别出新裁地同时设计了两个框架,一齐套上去。一个框架是石头幻形人世,历劫以悟色空;一个则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结下还泪前缘,下凡以了夙愿。整个贾府兴衰、木石盟金玉缘的故事都套在这两重框架中。作品所叙写的神瑛、绛珠的前缘,已经对宝、黛的悲剧情缘做出了因果性交待,请看这段描写: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暇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化,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宝、黛的爱情悲剧实际是前世已定,作品在这里以“浇灌”之因引出“还因”之果,极富诗意地预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结局。在这层因果框架上,作品又架设了一个“石头”框子。通过“石头所记”,一方面给全书以特定身份的叙事者,书中所记为身历目击,因而有自传性质,一切均从石头眼中见出,故作品叙事为主观性、为特定视角;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深化了作品哲理意味的象征功能,使作品具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内涵。[⑦]看来,对近乎幼稚、迷信的因果观念在通俗小说中的体现,也不可一概而论,全盘否定。再说,在古代通俗小说中,“形象大于思想”的作品实在不少,许多优秀作品的思想内含远不是因果框架所能束缚的。
*本文系笔者《佛教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系列论文之一。
注释:
①本文旨在概括与评述,故对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所借鉴,未能一一标明,在此一并致谢。本文主要参考论著:《佛教哲学》(方立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方立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佛教文化论稿》(魏承思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佛教与美学》(曾祖荫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陈洪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灵尘化境——佛教文学》(龙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佛道诗禅》(赖永海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② ③参阅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第260、26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⑤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下册第72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⑥ ⑦详参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第152-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