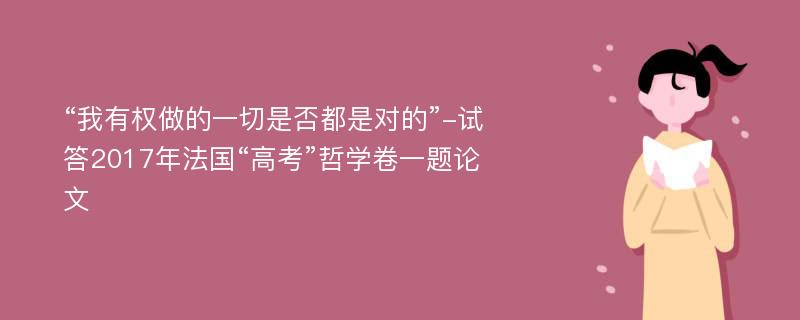
文艺新论
“我有权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对的”
——试答2017年法国“高考”哲学卷一题①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对于“我有权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对的”这个貌似现实的提问,可以做一种极其复杂的哲学描述与分析,它区分为外与内两种情形。所谓外,就是对照、引用、提到、反思的态度,这是一种对象性的旁观者的思维态度,其性质是理论的;所谓内,就是亲历、使用、消费、沉浸其中的“我能”或者精神的冲动,它是一种行为或者实践的态度。这两种态度的区别,也是传统形而上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区别,由此所引起的哲学争论,导致了哲学问题的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 :权利;正当性;后现代哲学
①这里指该年度文科试卷第二题:“我有权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对的?”对应的法文是“Tout ce que j’ ai droit de faire est-il juste? ”其中的“权”对应droit,指的是区别于权力的权利。“对的”对应juste,这个法文词的含义还有:正义的、公正的、正直的、恰当的、有充分理由的、准确的、真实的。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逐渐加重,老年人群由于各项生理机能逐渐衰退,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逐渐下降,大大增加了其患病几率。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变容易引发心力衰竭、心律不齐等不良反应,病情严重患者还会出现猝死现象,因此,提高诊断准确率对于抑制患者病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此次研究专就2016年8月—2017年7月我院收治的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变患者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诊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究,现做如下报告。
一、辨析之一:究竟是对照还是亲历
现在我假设这样的情形,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个出题者,让一个诗人或者艺术家回答:“我有权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对的?”如果我现在扮演诗人的角色,如何应对政治家的题目呢?我会对这个政治家说:您这是一个很不清晰的提问,它其实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把“我有权做的一切”与“是否是对的”分开,我做了某件事,然后有一个“对错”,等着我加以对照——如果这就是出题者的意向,那么这个意向在学理上值得商榷。换句话说,我要批评它,因为它既不深刻又导致无趣,简单的生活体验就足以证明了:我品尝了一道美味大菜,但我不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难道你要质问我“吃得不对”或“没有正确的吃”吗?姑且我暂时同意你的说法,我吃得不对,但我吃得津津有味,我已经享受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叫不出菜名(甚至区分不出鹅肝酱还是鱼子酱)或者“没有正确的吃法(甚至包括吃相)”又有什么要紧呢?此时此刻或此情此景,“我有权做的一切”就是正在有滋有味地吃,它就是一切。
常用的平面编织技法有十字编织、矩形编织、米字编织、斜纹编织等。十字形编织法是将经条与纬条垂直相交,纬条穿于经条下3根,压于经条上1~3根,构成平行直线纹与大方格纹,编出十字纹样。矩形编织法是将若干根竹篾平行列为经条,再将纬条分不同道数上下压住,织成长方形的空花纹样[2]。
当我说“它就是一切”,同时就意味着“它就是对的”,但后一种说法非常别扭,通常聚餐时大家都不这么说,因为这么说话很扫兴,即使最严肃的学者做完讲座在被请吃饭的餐桌上,也绝少这样说话。此刻吃饭升华为精神消遣,它就是美食的意义,此刻根本不存在所谓对错问题。我津津有味吃过之后,现在和你讲道理:当你逼着我回答“是否对的”,你暗中设定了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你把“对的”标准强加于我,然后让我参照执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因为对错的标准在你手里,你是对错的判官,而我只充当了执行命令的角色。但是,你凭什么资格当这个审判官呢?究竟谁有资格当这个判官,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它其实是公共权利问题、立法权问题。如果判官就是一个人决断一切公众事务,他就是独裁者。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就是推翻独裁者。在关于“什么是对的”问题上,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即公正的投票表达公意,这意味着关于“什么是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公意是可以改变的。
针对ELV充电站设施选址研究,在保证物流车自身充电需量的前提下,满足客户个性化配送服务的需求。充电站在选址时需要考虑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解释如下。
第二种情况,其实以上已经有所涉及,但说得还远远不够,即“我有权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对的”可以自动转化成我现在正在有滋有味地吃,忘乎所以地吃,它就是一切,如果聊得开心,碰杯的次数已经足够多,趁着微微的醉意,话也开始放肆,我对着和我碰杯的知心朋友(他脸已经很红啦,但我脸没红)高声说:“我有权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这话绝对是肺腑之言,不仅是因为这话只是针对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更因为这话只表达了我的亲自性,就像我必须亲自吃饭一样(还有很多场合人都必须亲自体验,例如终极体验:每个人都得亲自死)——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开玩笑,它绝对严肃。我所表达的,其实是“不可替换性”这个极其严肃的哲学话题。你(出题者)一定看过《廊桥遗梦》这部电影,很多观众掉泪了,很多人在看这影片之前抱着谴责的立场,在观影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忘记“正确的立场”。为什么呢?不仅因为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更因为他对她说的一句话直逼魂灵:“我们这样的感情,别人能有吗?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经历过。”这话别的情侣肯定会有意见,但其实这话只是一个象征,他象征着所有男人,她象征着所有女人,也就是德里达说的,“我不能回答什么是爱,爱是关于爱谁的问题,我爱你因为你是你”。这就把个人独享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廊桥遗梦》只描写四天的奇遇,从哲学上讲,这叫“进去”,尽管有复杂的感情纠结,但事实上四天之中,她与他的心理语言,就是“我有权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显然出题者忽略了“对的”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而含义却大相径庭。观影的很多观众哭了,回到家还在心里哭,这很奢侈,但它是真实的梦。据说影片放映后,社会后果很严重。
现在可以归纳一下:“我有权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对的?”可以分为“在内部说”(说话人既是当事人又是判断者-感受者,进去、沉浸其中,描述行为本身,这里的判断只是描述自身的亲自性),还是在“外部说”(说话人或者提问者只是所问的问题的旁观者,他把这个问题只是当成一个可以回答的对象,无论怎样的回答,它们在性质上都是一个关于“正确与否”或“对与错”的观念性回答)。
正统的哲学史告诉我们,只有观念性质的回答(所谓“讲道理”)才是理性的或者正确的回答,在这个意义上唯物论和唯心论都是“正确的”,它们争论的只是立场,但在坚持观念论的意义上,两者其实是一样的。但这种旁观者的态度根本就没有进入活生生的生命内部,它们完全无视“我吃得津津有味”和《廊桥遗梦》中的“我有权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就不仅导致了无趣,甚至也导致虚假,因为它们外于生命的热情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甚至是不道德的——从人性之外强加给人的所谓道德,是不道德的。原则总是干不过生命的,因为原则是人制定的。倘若有一天原则彻底战胜了生命,就是人类纯粹思想感情的死亡之日,人也就成为完全的物,就像一块石头那样不再拥有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要区分行为语言(“我能”)与判断句(“我知道”):行为语言是正在产生实际效果的描述性语言。在很多时候,行为语言也冒充“判断句”,以便“大树底下好乘凉”。也就是说,行为语言也不得不使用一堆“是”与“不是”。哲学家能写哲学诗的奇妙之处,或者说别一种“思辨能力”(理性想象力),就是在这样的大树下面好乘凉。行为语言表面上在说话,其实却是“沉默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此刻应该沉默,因为它不是具有逻辑理据的表达式),即行为语言中的“陈述”(其实是沉浸中的描述)不是在对某个对象做判断,它相当于“只干没说”( 它只描述此情此景的思绪-思想感情。在一般判断的意义上,它是沉默的,即使表面上在说话)。行为语言大量存在于三种情形之中,都充满了热情的冲动(分成抽象的冲动和具体的冲动):1.宗教忏悔,孤独地对耶稣说“我爱你!”(它相当于对“虚无”独语)2.性爱过程当事人的“语言”,即那些不由自主脱口而出的一切。3.污秽语言,侮辱人格的语言(特定情境的强烈情绪冲动,也属于广义上的“热情”)。这三种语言,都属于没有能力表达的“表达”,它们都是思想感情(包括身体语言)向深刻的“黑光”延伸,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与爱的眼神、恨的眼神类似,但只是“类似”,因为眼神与语言性质不同,眼神毕竟不能代替语言。行为语言仍旧是“语言”,而且是最贴近内心真实的语言。哲学诗属于思想感情的行为语言。
“尽管我现在知道我在和您说话,我知道,因为我的语言是理智的,直到我对某个全然的他者表述时,从这个时刻起,我就不再是理智的了,因为受话者(destinataire)的无法确定性,诞生了缄默的痕迹,神(Dieu)就是这样的痕迹——是永远不会被知道的他者,我的话语不仅都是从这样的痕迹出发的,而且自始至终浸透着这样的痕迹。当然,我在这里所谓受话者的痕迹最好的例子,就是陌生的去处。这陌生的去处,不可能是理论的态度,不是某种理论语言活动,而是某种前理论语言行为、一种祈祷。它并不发生在我请求上帝帮我一个忙的时刻,也不发生在我屈从的时刻,而只是说此刻我对一个他者说话,此刻我留下一个印象、一处踪迹、一种遗迹或记忆(此处还可以说一种精神创伤、一种思想感情气氛,泛指缄默却意味深长的一切,所谓魔力-幽灵-魂儿的问题,也包含其中——引注)。我注定不知道受话者,因为受话者永远不在场。我向您提出某个问题,我说‘请您回答我’。即使您没有回答我,我断言我是对您说话,我给您留下一个印象。上帝就是这个永远不确定的绝对未知的受话者,其去处可能含在遗留下的所有踪迹之中,不仅仅只是人类留下的痕迹,而且包括一切生命体留下的遗迹。”[2](P.77)德里达上段话里的“痕迹”(trace),与中国的“味儿”文化,不期而遇,这是一次异域哲学的相互碰撞。
有开始就有丧失,就像有生就有死,因此以上的意思还可以接着说,丧失是痛苦的却又是必须的,这就是爱的折磨。一个真正的人,是有能力复活的人。就是说,有重新开始的能力,他有很多次机会像他自己!他是精神碎片的万花筒,可以活在不同的精神年代里。
二、辨析之二:究竟是“引用”还是“使用”
延伸上述区分对照与亲历的思路,就是要区分“引用”与“使用”:“引用”相当于在谈论自己(也就是反思),它相当于自我判断: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坏人,诸如此类——它的要害,是对一个被假定为暂时不变的、清晰明白的对象做判断,形成某种二元对立的间接关系(“我思故我在”暗中设定了意识与被意识的对象的关系)。但是,“使用”相当于沉浸其中,正在消费自己,即使其中反复出现“我”(例如奥古斯丁和卢梭的两本《忏悔录》中),这样的“我”并非自我指涉,而是处于不同情境改变着的我。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真实存在着的不是“存在”(不是being)而是描述。作为描述,尽管不得不出现“我”、“是”、“不是”等字眼,但它们都处于变形过程之中,具体变形为怎样的状态,有赖于上下文的语境,但它不是指狭义上的文本,而是指世界这本“大书”。
当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与卢梭)以“使用”的方式写作《忏悔录》时,思想同时处于哲学与文学之间,思想“不清不白”即同样一个词语或者概念不是逻辑判断或词典上的意思,它同时有好几个含义,究竟是什么含义,还有待于接下来的字句,而后者还没有发生,或者它正在发生但没有结束。例如,在《忏悔录》中,卢梭说他的手淫行为同时拯救他与毁灭他,这不是在反思,而是在描述。描述过程不但同时也是思想过程,而且是原汁原味的思想,是思想的原样,它是不由自主的处于流动之中的思想。这情形的真实性,古希腊智者赫拉克利特描述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在批评以反思或“引用”的方式判断事物的所谓本质)和“事物的真相喜欢躲藏起来”。同样,当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写他偷梨的动机不是为了吃梨,而是为了偷东西这种惊险刺激的行为本身而偷东西,是为了享受偷的行为给他带来的快乐,这也不属于反思,而属于描述。总之,当一个思想者处于描述状态时,他的思想就是流动过程的思绪,而一旦出现静止,就形成自我判断,思想就凝固为“思想的雕像”。这个雕像是建立在逻辑同一性基础上的,它在提到和再次提到同一个词语或者概念时,其含义不变,可以无数次的重复。
换句话说,在反思态度下,是不存在时间的,它的时间和空间,相当于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而以“使用”或者描述(沉醉)的方式使用词语或者概念时,相当于生命永远从现在开始,它强调当下瞬间(偶然性)的厚度或者悖谬性,它含有过去的记忆与对将来的渴望,但过去与将来都凝聚为当下的力量,而当下或者笔下(或者生活本身)究竟朝哪个方向走,还有待于实现,笔者或者生活者本人,并不能准确预料到。
在反思状态下,反思者其实处于“知道”状态,他只是说出了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或者活出他已经活出的状态,也就是平庸,因为这里并没有发生新鲜事儿,也就是没有意外事件,没有迎来真正的陌生。在“使用”或者描述(沉醉)状态下,所迎来的是真正的思想事件或者生活事件,所谓“你好,忧愁”、自寻烦恼、深度无聊感之类,就发生在其中,它们都不是习惯的或重复的感受,而是使当事人深感震惊。
当然,以上只是出于理智的划分。在划分时,我的思想处于停顿与未停顿之间,我不可能完全排斥反思。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时而出于“引用”或反思状态,时而出于使用(描述、沉醉)状态,两者纠缠在一起,虽然难解难分,但我自己的内心得透亮,要清楚自己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究竟是处于两者之中的哪种状态。从逻辑角度,“我思故我在”是一种垂直方向的形式逻辑,总体看这里不存在陌生,因为关于什么是“我”、“思”“在”的意思,笛卡尔事先已经知道了,而“你好,忧愁”则属于本来无法推论出来的思想关系,属于哲学诗的逻辑,我称之为“自由增补式的横向的逻辑关系”。犹如天才诗人洛特雷阿蒙的诗句:“忧郁得像宇宙,美丽得像自杀。”还有象征派诗人魏尔兰的呻吟:“没有爱也没有恨,我的内心充满着悲伤”——从这里“横”出来的,是陌生关系,也就是含义上的不对称性。“你好”对应“忧愁”,它打破了心理预期,它揭示了某种自相矛盾的情形。晦涩地说,就像法国诗人兰波说的“我是一切人”,或当代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说的名言:“我是一个全然的他者”,从此出发能迎来什么,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不仅具有哲学与文学意义,作为思想与语言的事实,它也是科学与逻辑面临的难题,也就是语言悖论,例如“我在说假话”——如果从谈论(或者引用)角度,它就是一句真话;如果从使用(奥古斯丁或卢梭的《忏悔录》之描述)角度,它就是一句假话。
高校图书馆的个性化定制学科服务是对现有资源、人力面向用户需求所进行的有效整合与推送,是实现图书馆价值和服务转型的重要途径。具体的服务方式是指学科馆员从分析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入手,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基础,以专业的服务队伍为依托,以多元的服务渠道为手段,通过嵌入用户研究过程、满足个性化需求来实现图书馆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能更加体现高校图书馆服务至上、以人为本的服务特点和发展思路。
“我死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正是我在写“我死了”,倘若我真的死了,我就没有能力写出“我死了”。我写“我死了”故我存在,我存在故我有能力写出“我死了”。在我不存在的地方,在我不思的地方,我才存在。我死去活来了,故我存在。“我死了”是最为典型的描述句式,也就是沉醉其中,因为它没有对象。它有意义,却不是对象型的意义,而是荒谬的意义。所谓荒谬,就是说我处于不死不活状态,或者既死又活状态,死而复活状态,总之是亦此亦彼状态、不清不白状态,我在我不思的空白处书写哲学诗。我死了,死了很多次,死而复生,然后又死,又死而复生。我极其倔强,能重新复活。我会做出使人深感意外的事情。我宽恕这个“忽视”,因为这个“忽视”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我沉醉于倔强之中,我倔强故我存在,我以头撞墙故我写哲学诗。我既是倔强的或是以头撞墙的真实感受的当事人,又是这种真实感受的判断者。沿着这种感受无论我写出怎样的句子,都处于沉醉状态,即亲自感受与判断合二而一状态,这与身体处于激情状态的语言完全一致,即使此刻的语言像是在承诺,实质上却是在描述,也就是同时消费自己的身体与心灵。这个“身体”是广义上的,尽管两性之爱可以作为它最为直接简明的表现形式,但它有点狭隘,我宁可称其为广义上的精神冲动,必须把身体冲动升华为精神冲动,是思想感情在跃跃欲试,势不可挡。
与引用不同,“我死了”属于描述或者使用,“我曾经偷梨”也属于同样性质的表达式。德里达著有《割礼忏悔录》(Circon fession),其中提到他小时候偷过葡萄。[注] 转引自John D. Caputo , Jacques Derrida -Saint Augustin ,Des Conffssions , Stock , 2007 . p . 68。“我偷过葡萄(德里达刚刚提到奥古斯丁和卢梭都在16岁时偷过梨),直到今天,这仍旧是我的一道伤口,它支配了我的生命!它既是严肃的又是野蛮的,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学体验,我觉得奥古斯丁开创了这种文体,我对它的起源极有兴趣。”[2](P.68)一个看似并不太起眼的生活事件,却导致心灵的巨大伤口,这是不对等的。“偷”的意味绵延不绝,朝向不知所往的四面八方。无论是梨子还是葡萄,这些哲学家大都曾经被自己匪夷所思的热情所折磨,他们的巨大热情坠入虚无,一个无比巨大的思绪黑洞,无底深渊,并因此留下了永远的精神创伤。
不同时代有才华的头脑之间的相似性,竟然到了如此的细节(它们实现了不可能的可能性,就像是以头撞墙),它的哲学意义在于:为了还原历史,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在物理空间上返回人类的原始状态,而只需像奥古斯丁和卢梭那样极其逼真地、毫不隐瞒地描述自己的心思是如何发生的(在这里,要把事实与正确区分开来):原始就是内心的真实,就是“不由自主的烦恼”。这些类似的念头,痛苦与快乐,永远重新回来——尼采如是说。这就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心魔。
要以沉浸与描述抵抗反思的习惯。要活在自己的历史之中,而不要站在自己的历史之外对“历史”指手画脚。与其评价历史,不如创造自身的历史。“我”是一个绝对神奇的字眼,如果抱着“我思故我在”的态度,相当于我与自身同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我如何描述自己,都相当于自我评价或者反思,因为“我”本身的含义没有改变,相当于我没有经历时间。但是,读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会知道,“我忏悔”中的“我”沉浸于生活本身之中,经历着时间,由于遭遇陌生的刺激而且融入陌生,我是怎样的甚至我到底是谁,与我融入的片刻有关。我被诱惑其中,而“其中”又随着场景的改变而改变,不断出现“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或者使别人大呼意外。我的身份无法确定,我自相矛盾。将要发生的才是我,以往的我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即生活的真相,就是永远从现在开始。
往年过年回家去看他,姥爷总会想方设法给我做一些好吃的,打小他就对我疼爱有加,加之后来母亲去世,他的舐犊之情便愈加深沉。
上述的“引用”又相当于“提到”,“使用”又相当于“消费”。关于“提到”与“消费”的区分:“我们”的情形,属于“提到”,也就是判断(对象性思维、概念思维),即理论的态度,而“我”等值于消费我、描述我、我沉浸其中。这个过程中,我改变着我。所谓魔力、某种气氛、鉴赏或者“味儿”,都是其中的元素,它天然与可理解性(可交流性)的语言相冲突,因此才有所谓哲学诗。哲学诗是后现代哲学的写作文体与描述方式,其中思想感情和理性直觉的天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针对该类型小流域主要存在的地表硬化程度高、径流系数增加、排洪压力大、水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应配置以下主要技术措施:
以上,也是对“我”的解构,是所谓“作者”消失的学理依据。“作者”总是处于行为之中,它只干不说,因为一旦说出来,就是一个假签名。进一步说,由于签名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因此典型的“作者之书”即自传中的我,就可能处于撒谎状态。就像当我说我在思想,真实的情形可能是我在回忆。就像我不能说“我是我”,因为真实的我处于溜号走神状态。因此,一切思想的真实状态,都是处于尝试摸索状态,处于未知状态,而不是已知状态或者理论状态。思想正在或就要发生,一旦它被凝固为理论,就成为思想的雕塑,就僵死了。
我引用以上德里达大段话,因为它清晰表达了什么是他所谓“解构”:解构不采取“提到”的态度,例如不像当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提到“上帝”时,并没有处于享受信仰的沉醉中,而是将“上帝”单纯作为一个解释的概念或者词语,从而建立起索绪尔那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解释学关系、一种停顿下来的“逻辑理性”关系。德里达的“解构”,就是我所谓“沉醉”于某任意“x”(这里的“x”可以是任意一个概念、传统的思路及其理解方式,它存在于任何一个领域之中,解构无所不在)之中。例如他会说,你不能问我什么是爱、什么是时间,因为我已经在爱之中,我已经处于时间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爱和时间都在变形、都在改变着自身面貌。这变形和改变,都意味着旧词语-概念正在被消解-解构,也就是被转换为另外一个问题,呈现出别一种即时的思绪-思想感情,例如把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转化-消解-解构为存在着宗教和信徒的真挚感情,这就是德里达的阅读与写作态度,也就是在接触任何一个词语-概念时,采取消费-使用的态度,即强调行为的效果,将“存在”的问题变身为是否产生实际效果的问题(即使有时表面上看似乎是“提到”或理论的态度,例如回答了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一切都无法事先确定,一切都有待于确定,它就要来,却不是以我们预先想到的样子来,因此生活-生命的真谛就是永远都从现在开始,事物在推迟实现自身的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已经处于某某之中”(它类似于“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与“某某已经实现了自身的意思”(它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差别,是本质的差别。
我已经处于某某之中,这种阅读-写作-生活态度,就是以复杂眼光看待一切,因为“我”说的意思决不是字面所表达的意思,它的意思在别的方向,这使得思考变成一种有趣而深刻的诗意哲学,其中的逻辑是“生成逻辑”。
总之,沉醉就是我在使用“我”,在这个时刻我不同于我自认为我所是的东西(“我”的真实含义不同于词典里对该词的注解),因为“我”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过程,前途莫测,我处于不知道状态,因为“我”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词语。沉醉就是不再用词语进行思考,我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我”(或任何一个词语句子)意味着什么,我不再处于解释世界的态度,不再处于某种理论的态度,而是改变我的形态的态度,我的幽灵就活跃其中。
利用电化学工作站CHI660E中循环伏安法对二极管1N4007和2AP10分别测试了它们的伏安特性,将对极和参比电极同时夹在二极管的一端,将工作电极夹在二极管的另一端,此时二极管构成模拟电解池。初始电位和高电位都设为1.0 V,低电位设在1.0 V,灵敏度设在1.0e~003A/V。
三、辨析之三:究竟是反思“已经”还是创造或陌生的精神冲动
与历史学家的判断相反,历史不是由“已经”而是由“陌生”构成的,“历史”意味着去创造历史。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判断历史,既不代表智慧,也不尊重历史当事人。算命先生断定某个人或者人类历史将要发生什么,这样的承诺是靠不住的。有生活阅历的人,只看重一个人当下的行为,而不会太在意这个人在承诺什么。当一个人在承诺时,就相当于在告诉你,这个人已经事先知道了自己甚至人类的未来历史,如上所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在承诺一件自己不可能按原样做到的事情,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承诺是在故意对你说谎。我们总是以承诺的口吻说话,我们在说着不可能完全落实的事情,这就是陈述性语言的乏味之处。为了深刻有趣更接近真实,可以将承诺性质的句子,变身为行为句:“哎呀”、“快活死啦”、“你给我滚”如此等等。所谓行为语言,就是或者仿佛是亲临其境,它们正在发生,而不是已经发生。
哲学家进行创造性思维时,具有抽象的、陌生的、独特的精神冲动能力。这种抽象冲动的魅力-魔力,在于它属于我以上所谓消费-沉醉-描述,有证据表明德里达的写作始终处于“抽象冲动”状态,因为他这样说过:“我从来不说‘我忏悔’。”[2](P.71)为什么呢?因为“我忏悔”相当于我以上说过的“反思”,也就是丧失了思想冲动。它处于自我指称的谎言状态,属于同义反复。德里达又说:“也许我写出我忏悔,但是如果某人说‘我忏悔’,我会说‘你在撒谎’,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说‘我忏悔’,相当于说我是我所是的东西,即我是我,与自身同一。我忏悔所犯的罪,我对这罪的忏悔意味着我此刻并没有和我的犯罪行为本身在一起,我摆脱了我忏悔时所述的罪行。”[2](P.72)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忏悔的我,其实是置身事外的我。另一个是正在犯罪的我,沉迷于犯罪行为之中。这就出现如下的悖论或荒谬:如果我有能力忏悔,我就没有在忏悔。换句话说,忏悔的“我”其实处于缺失状态,因为没有人有能力在这份忏悔书上签字,因为这个签字的人其实是一个撒谎者。
当然,也许对上帝(你)的忏悔可以被排除在外,这种行为属于抽象的热情冲动,因为神-你是一个全然的他者,这里不存在“我是我”的情形,但如此情景,德里达认为不适合用“忏悔”,因为容易和以上“我忏悔”的情形混淆。为了有真正的忏悔,就像一切概念为了真实的存在,它必须处于沉浸(se traverser)行为或者情景过程之中,它被消解的同时化身为别的行为,它是不由自主的过程,像是无意识的意识、处于消解过程的意识流动之中,就是我以上所谓消费自己、自己在诱惑自己(在这些过程中“自己”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我是我”的我),而不是停顿下来的判断。因此“忏悔”化身为正在心痛或精神的创伤,它只适合在消化自身中描述自身,而一旦判断出来说“我忏悔”,就可能导致撒谎——同理,“我决定”、“我原谅”等类似的承诺句和“我忏悔”一样,具有朝向撒谎的自然倾向。总之,不可能归纳出某心思的总体状态,因为这就把流动着的瞬间心思化为永恒,纠结着的心思才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处于沉默之中的才华。
“提到”与“消费”(使用)的区分,取代了传统思维询问“是”与“不是”。在回答是与不是之前,首先要区分问题是从“提到”还是“消费”的角度提出来的。德里达说:“我母亲问我:‘你相信上帝存在吗?’她害怕我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她无法理解无神论。但我是不同于我自认为我所是的东西吗?‘我被当成一个无神论者’。在某个圈子里,这有赖于语境。在某种交往的语境中,人们视我为无神论者。在别的语境中,我又被认为是有神论者,而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我的生活就由这些所组成,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明信片》一书中,我不承认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能区分‘提到’(mention)与‘消费’(usage)。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当我说‘上帝’、‘我’,人们能加以区分。当我说‘我要去坐火车’,我这不是在引用,不是在提到,而是在使用‘我’。但是,在陈述结构中,不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区分某陈述句到底属于‘提到’还是‘使用’。我认为在说到上帝时,就更难以区分到底属于‘提到’还是‘使用’。如果你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意味着你只是简单地提到‘上帝’这个词,这就意味着人们认为你是在理解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你是在你继承下来的文化环境中接受这个词的,在这种文化中‘上帝’一词有其意味。对于我来说,即使当我说上帝不存在的时候,我所说的意思也恰恰相反,即在人们相信上帝存在的范围内,上帝就存在,有宗教的历史。在我看来,宗教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即使上帝真的不存在。这就是问题所在,即使我有能力证明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教规是错误的,即使我能证明上帝不存在,也不表明上帝不存在,因为宗教是存在的,上帝在宗教里存在着,人们相信上帝存在(这里用得上我说过多次的一种克尔凯郭尔式的信仰上帝的表白,他以类似这样的口吻对无神论者说道:‘无论你说得多么有道理,我都不相信’——引注),信仰者根据这样的信仰做事并组织起他们的生活。”[2](PP.84-85)
换句话说,一切思想的真实状态,都是以着迷-魔力-魅力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它流动、它变异、它在勾魂儿,它非假非真,这就是所谓到处在蹦蹦跳跳的幽灵状态,也可以说在弥漫、在游荡,一种思想感情气氛,如此等等。“这就是我对迷幻[注] Fantasme ,法文词,意味着幻想、幻影、幻觉,沉湎,它也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 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沉湎本身一定是一个事件。”[2](P.73)
这就涉及到“魂儿”的问题,科学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但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上帝的存在不成问题,因为想到上帝的恩惠,他们已经泪流满面。泪流满面作为事实存在,这里就有魂儿-幽灵(spectral)。它们在永远不在场的意义上存在,也就是说,卢梭式的纯粹思念(在她不在场时,他才会感到多么怀念她-爱她)在性质上与对神的爱-信仰是一样的。当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被转化为纯粹思念问题,转化为幽灵般的效果时,宗教感情就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纯粹感情了。一个无神论者也是有纯粹感情的,但与上述情形有所不同,因为无神论者倾向于认为纯粹虚无(不在场)的情形,不如在场的情景更有积极意义。无神论者更想拥抱实际存在的东西,其口头禅是“不要脱离实际”。在这里,出现了怎样才算“在实际”之中的分歧。在无神论者和爱神者都处于“想心思”状态时,爱神者会觉得幻觉本身就是真实的“在实际”之中,无神论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无神论者的思想会在自认为毫无意义的边界线上自动终止。换句话说,爱神者倾向于鼓励自由想象并自觉地培养自己的这种纯粹感情的能力,而无神论经常对“脱离实际”的人说:“不要胡思乱想”,它不鼓励幻觉,以为是毫无意义的。
在上述意义上,一个爱幻觉的人肯定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人,敏感体现在将瞬间的美好从感官印象迅速生长成“纯粹脱离事实”的思绪-思想,敏感把记忆力自动转化为虚构力,敏感非但不阻拦而且鼓励纯粹虚构-设想可以走得任意远。于是,纯粹任意性的问题,只有在爱幻想的语境下才能被充分理解,它是一个属于很多学科领域里的共同问题,但首先具有哲学意义,它培养起怀疑一切的能力。反之,由于无神论不鼓励“毫无根据的、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它的精神敏感性停止于记忆知识的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在它这里,思想可以被记忆替换,但绝不可以把记忆换成纯粹的幻觉,因此不可能出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幻觉艺术,这样无神论也就丧失了享受一种最为真实的纯粹幻觉艺术的能力,后者只是貌似脱离实际。
预制光缆采用预制舱内集中配线方式时,由于集中转屏柜的预制光缆根数较多,若直接将光缆余长收纳在屏柜周边光缆槽盒内或集中转屏柜下方,对空间要求较大,且日后检修、维护困难。针对该问题的余长收纳方案有两种:
紧接着上述问题,当我们说一个人有灵气,其实指的是具有幻觉-虚构能力,而不是世俗世界里“不脱离实际”的算计能力。虚构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方向,爱神意义上的虚构朝向纯粹的幻觉、朝向逻辑上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荒谬,而类似《西游记》那样的虚构,不过是把完全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故事,搬到天上而已,换句话说,它并没有违反人间世界里的逻辑,根据就在于其中唱主角儿的情节,也是“算计来算计去”的,这甚至限制了《红楼梦》的思想感情高度,因为它只是悟到了“好了歌”,梦到此为止了,宝玉去做了和尚,这里的惆怅仍旧是人世间的,也就是说,当梦幻本应开始的时刻,它却戛然而止,因此类似黛玉葬花那样的中国古代诗词,都不是洛特雷阿蒙、兰波、波德莱尔、马拉美那样的。虽然中国古典诗词里也有“梦幻”(甚至魂儿),但缺少一种“纯粹脱离实际”的哲学-宗教层次上的自由想象力,极少会朝这个维度“胡思乱想”。中国古典诗词艺术之美,出不来普鲁斯特那种类型的纯粹之美(问题并非在于是否“食人间烟火”,而在于从哪个思想感情的维度“食人间烟火”),因为后者暗含着哲学-宗教维度,即使“哲学”与“宗教”的概念,不必在作品中出现。
以上问题也可以这样说:纯粹的泪流满面的宗教意义,并非中国传统精神风俗意义上的人间悲喜剧,而是象征着非人际关系的纯粹精神孤独问题,从中涌现出纯粹抽象的冲动,它对着一个永远不在场的“你”吐露纯粹的热情,这些热情是超越的,它搁置了人类生活世界里自然而然的感情。这里存在着一个类似扭转“黛玉葬花诗”的精神维度的问题,也就是把“没有希望”(绝望)作为纯粹抽象的热情冲动的出发点,这里鼓励“莫名其妙”。换句话说,在这里不是由于欲望太多了而导致人间悲剧,而是纯粹精神的“欲望”还远远不够,这也是与禅宗的世界不一样的。
四、辨析之四:究竟是“我知道”的理还是“我能”留下的迹
以反思为特征的思辨哲学也把“自由”放在最高层次,但这是已经被知道了的“自由”,是服从必然性的自由(黑格尔的名言具有代表性: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康德认为没有概念,直觉就是盲目的;没有直觉,概念就是空洞的。在这里,康德完全没有像胡塞尔那样往“圆方”的方向思考,康德只是将两样含义已经清晰明白的“东西”(概念与直觉)生硬地或者强行地粘贴在一起,就像强行捆绑的夫妻,难以有真正的爱情。康德没有像德里达那样,把“概念”消解融化在某种思想感情的情景之中。换句话说,康德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对象思维”,它的弱点就在于它是一个“知道”,也就是“已经”(已经知道)。它的要害是排除了“盲”,因为在康德看来,“盲点”是不可理喻的,尽管他在论及实践理性(道德形而上学)尤其是艺术审美(他竟然笨拙地把艺术鉴赏纳入“判断力批判”的主题。从后现代的目光,艺术鉴赏不是“判断力”所能解决的问题)过程中,肯定了实践行为本身和“无概念的纯粹趣味”的合理性,但是概念思维始终贯穿于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中,他的“自在之物”(意志自由、灵魂不灭、上帝存在)本是他思想中最精彩部分,只可惜他止步于“荒谬”。康德否认“不知道”(盲点)本身就是哲学的内容,而不仅仅是艺术与宗教的内容。
那么,康德哲学的死胡同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当他努力划清思想领域的界限(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应当怎样)时,没有想到他的这三大问题的性质,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用概念去思维。其实,康德始终是处于自问自答状态,即他事先就已经有了答案,然后再以“走形式”的方式推论,这就相当于先做判断,然后才寻找证据,而证据总是能被他发明出来。换句话说,康德始终在用逻辑“讲(他设定好了的或已经知道了的)道理”。康德没有意识到德里达以上所说的另一个重要思想界限,即没有区分“提到”(即“引用”,这是理论态度的标志,即跳出事物自身之外,成为一个旁观者)与“消费”,后者是我以上反复描述的思想感情的沉醉状态,这个过程充满精神的盲点,因此才会有魔力与幽灵问题。
进一步说,当康德问“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应当怎样”时,其实已经暗中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样,不但知道了什么是“我”,而且“我”永远是自身同一的(可以无限次的重复,即我就是我),康德没有想到这个“我”的身份是一个假签名,我究竟是“谁”成为一个可怀疑的问题。当德里达把康德的“理论的态度”转变为“沉醉的态度”时,“我”被消解为不是虚无的虚无,即幽灵一般的“x”:“ 我们总是能对神(Dieu)呼唤,在语言中被任意虚构的x都是神灵。”[2](P.76)
“我”现在就去受折磨,你同时是折磨“我”与鼓舞“我”的力量,折磨鼓舞着“我”,这就是爱的悖谬,这是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无解难题。要在黑暗中,写出寂静之声。
既然我已经从学理上梳理了可以分别从内部(相当于“消费”)和外部(相当于“提到”)说“我有权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对的?”那么我从内部说,就不能算跑题。从内部说,这个问题就转变为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形下,我有权享有我的一切亲自性——在这个思想感情的氛围中,我有权做的一切,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而是我愿意与否、是否有兴趣,也就是享有个体生命的问题,这里不能像“从外部说”那样能说得清楚明白,但这里有诗意,也就是艺术,热爱或享受生命,就是以艺术的方式活出自己,它不是国人常说的顺从自然或自然而然,而是放纵自己的想象力,与自然状态较劲。一个持知识论立场的人信誓旦旦地和我说:“人是一个癌细胞”,他以为我会反驳他,他不曾想我听到这话欣喜若狂。“您说得太好了!”我说,“您这是一句好诗!但说的还不够,我要接着说:人还是一种无用的激情,而死亡对人的最终馈赠,是不能再死一次,如此等等。”
极其耐人寻味的“x”,它就活跃在日常生活之中,仿佛是“鸡尾酒里的现象学”,萨特听到这话激动得脸都变白了,因为他立刻懂得了生活的真谛,就是把现场实景“原封不动地”飘起来,会飘到任意一个预想不到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德里达的话:“我们不知道真正与我们说话的人是谁。”[2](PP.76-77)例如,萨特在《恶心》中这样描写:自学者说道,“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向他们微笑,我想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努力的目的,而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这就是快乐,先生”[3](P.128)。以这样的口吻说话,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绝不陌生,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因为它说得实在太正确了,是大家口头上的共识。对自学者的这番表白,萨特继续写道:“他用眼光探寻我,我点头赞同(不得不,谁能不赞同呢——引注),但我感到他稍稍失望,他希望我更热情些。可我能怎样呢?在他的全部表白里,我看出他在模仿和引用别人的话(自学者可以被当作学究式学者的象征,他这些正确而热情的表白,其实是把别人的话当成自己的话,但这个表白者自己,却浑然不知。用德里达的话说,理解就是在误解,但理解者永远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误解——引注),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在他谈话时,我仿佛看见我见识过的所有人道主义者都再次出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3](P.128)
聚焦“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既要打赢,也要打好。打赢,就是要确保低收入人口收入和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达标,稳定实现低收入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经济薄弱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打好,就是要体现我省2020年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确保政策落实到位,确保人民群众满意,同时,要建立健全巩固脱贫成效、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和制度框架。
至于“真正的自己”,其实是不存在的。所谓“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蹦蹦跳跳的极其耐人寻味的“x”,幽灵就是无法署名,不必嘲笑这个自学者,因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每个人都在受别人的影响,所以任何一个人说话时的真相,就是时而持引用的态度,时而吐露自己的亲自性,它们是混在一起的。
从表3中可以看出,工作绩效3个维度均值整体都比较高,可能与本次绩效评估采用自评的形式有关,评价结果受企业员工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分数偏高。工作绩效量表中3个因素之间以及和总绩效之间相关系数皆通过了P<0.01的显著检验,说明3个因素方向一致,但是彼此都独立对总绩效起作用,其中知识型员工的关系绩效(工作奉献、人际关系)与总绩效的相关程度要大于任务绩效与总绩效的相关程度,因此,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评估中要重视对关系绩效的考核。笔者又对量表的实际测量信度进行分析(表4)。
知识要解决对错问题,但纯粹感情是生命之树的果实,这里并不存在面对对错的“你必须”的问题。也就是说,知识与纯粹感情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关于“有用”与“无用”,我还有话要说。斯宾诺莎说:“要理解,不要哭泣、不要笑。”他的意思,就是把思想等同于理解,哲学与哭泣和笑无关,与具体的感情无关,这就把哲学搞死了,把读书人搞呆了。没有感情,知识还有什么用呢?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活得正确吗?如果这样的话,悲剧就诞生了:一个人终生都在和别人辩论如何才算是正确的活着,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活死人!人要活出滋味,活出美,活得艺术,而不是为了让别人判断你活得非常正确。活着,说到底,只是纯粹私人的事情,甚至柏拉图也是这样活着的,帕斯卡尔说柏拉图独处时感到郁闷寡欢,想排遣深度的无聊,于是就怀着消遣的心情写出了《理想国》,不曾想后来的哲学家和国王们当真了,争论个你死我活,柏拉图这个哲学王一边偷窥一边偷笑,他嘲笑这些人不懂得消遣本身就已经是真理。
在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资金投入上,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起相应的新机制来专门管理其资金分配,并逐渐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同时,对于参与投资小型农田建设的民众,政府应适当地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另外,政府部门应对其财政收入的分配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得新的分配制度中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身处不知道却沉醉其中的状态,也是克尔凯郭尔面对的哲学问题,在他的《哲学片段》第一章的第一个命题,就是“问题来自甚至不知是何原因令他做如是追问的无知者”。[4](P.8)就是说,思想是从搁置“知道”开始的,这个开端毫无根据,因为如果思想从“知道”开始,对知道本身,就会一路追问到底,它的尽头,就是不知道。于是,思想的尽头是自己在推动自己,其动力就是瞬间之爱,就像旷野里一切都自然而然,什么都没有,突然降临了人的一声呐喊,大地山川的意义,就在这呐喊之中降临了。如果这呐喊有意义的话,它只是发疯的意义,因为呐喊处于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其实,这也是文学与哲学的共同开端,它是在梦幻中降临的:“就像从亚当的肋叉里生出夏娃似的,有一个女人趁我熟睡之际,从我摆错了位置的大腿里钻了出来。其实,她是我即将品尝到的快感的产物,但是,我偏偏想象是她给我送来了快感。我在她的怀抱中感到自己的体温,我正打算同她肌肤相亲,正巧这时我醒了。同我刚才分手的那位女子相比,普天之下无论是谁都似乎不及她更可亲,我的脸上还感到她的热吻的余温,我的身子还感到她的肢体的重量。”[5](PP.4-5)所谓开端,就是瞬间梦幻的结果,而梦幻本身,是自由任意的,不知从何而来,不知向何而去。普鲁斯特以上说不愿意让自己醒来,就是这个“道理”。
梦是光的开端,宇宙原本一片黑暗,《旧约·创世纪》第一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有个关键时刻,神说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的,哲学家只关注“时刻”本身的意义,就像普鲁斯特的巨著第一句话这样发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5](P.3)只有毫无鉴赏力的人,才会追问普鲁斯特究竟是什么时间,它是任意的时间,任意的时刻,它只是意味着开端,开端就闭着眼睛熬夜,相当于做梦,是梦里的光。
五、结论:“我”的生命是享受超越对与错的“完美的折磨”
受折磨时想到光,光来自神对人类的爱,耶稣降临人间带给人类光明的代价,就是他自己得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遍体鳞伤,饱受折磨——这是一个永恒的象征,耶稣把自己的神性传染给人类,从此,一个人去爱,就意味着永无休止地接受折磨,所谓“以头撞墙”。最痛苦的折磨并不来自肉体,而来自对灵魂的拷问,被折磨着意味着已经处于爱。这里的神只是虚无的另一种说法,它折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存在。但事情如果到此结束,就毫无意义了。奇迹在于,神是以如此的方式“存在”着,它随时都可以开始,比如我现在写出一句话,是胳膊、手指、大脑、心情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新念头诞生了,它开始存在,但它原本完全可以不存在,只要我下笔的瞬间别有用心,就蕴育出别的意思。我写字就相当于在发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孤独到了极点,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都有自我发光的能力。于是,“想到”这个行为本身,就相当于在发光。发光是意愿与兴趣的双重产物。因此,自己的意愿与兴趣本身,就是自己的神,其中有爱和折磨,它们是不可能分开的。
如果一定要在“证明为什么如此开始”之后,才有资格开始,那么将永远不可能有开始。所谓“开始”的意思,只是灵光一现。换句话说,可以从任意一个时刻、任意一个场所、任意一个念头开始。“开始”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发生了奇迹,就像每个人的出生一样,它来自纯粹的偶然性。
真正的哲学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甚至没有答案,就像人生,其实是无所谓目的的,人最终只是一个虚无,但一路的风景很美,非常具有诗意,它甚至使抑郁的天才诗人波德莱尔也满怀激情:“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1](PP.215-216)对于这句诗,我们只是品味它,任何来自它的感情气氛之外的评价,都显得软弱无力。政治家的目的是改变世界,但是诗人对改变物质世界的事情根本就不关心。外部环境其实永远是大同小异的,诗人无力改变生活环境,但可以变化抒情方式。
总之,康德的哲学是理性的哲学,德里达的哲学是“非理性的理性哲学”,因为理性之光,就像启蒙之光一样,可以有不一样的光。黑光或者x光,也是光,而且可能是更贴近科学事实的光线。当传统哲学在努力正确地解释世界时,德里达和马克思一样,诉诸于改变世界。它并不在天上,就在生活世界之中,例如一切思想其实就是记忆的变形,一切努力去“正确理解”的善良愿望,其实就是不间断地溜号走神的过程,因此“误解”(循着我以上所谓“发现与发明的增补式逻辑”)就是“正确理解”——这里强调的是“实际效果”,而不是“我应当”。
这就像是西西弗神话中描写的无效劳动,但只有平庸者才会嘲笑西西弗。人总是要死的,死赋予活着以伟大的意义。“无效劳动”本身的有效,就在于它“无效”。每个人的出生都是从呐喊般的啼哭开始的,这是形而上学的终极难题,前面的死亡等待着每个人。但人终究是伟大的,死亡只是一个物理生命的现象,死是生命的终点但死本身并不是活着的目的。
终点与目的是两码事。个体生命确实存在一个终点,但“目的”并不在未来,“活着的目的”这种说法在很多时候只是一句空话,它使人们的目光转向了生命的未来,似乎生命的意义在于某种筹划与选择,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什么目的、未来、选择、筹划,因为这些词语只是一些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生命本身。生命本身的含义,就是经历爱的折磨,西西弗一次次推着石头上山,相当于在爱的折磨中创造性的行为本身,它就是生命的意义,它并非未来的事情,它永远发生在当下,就像所谓时间,只有当下才是无比真实的。
既不要悔恨过去,也不要展望未来——如果这个表达还难以理解,那么西西弗的例子就足以表明问题的关键了,西西弗的过去与未来全都一个样,他被命运判罚要永无休止地推一块巨石上山,到了山顶巨石又自动滚到山脚下,他又开始推石上山,如此反复,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那么,在如此痛苦的折磨之中,他凭什么还能嘲笑自己的痛苦并且从这种嘲笑的态度中感到由衷的幸福呢?就凭他想到自己有一颗骄傲不屈、深邃无比的灵魂!俄狄浦斯也是这样想的,虽然他对自己的命运奈何不得,但命运也对他嘲笑命运的态度奈何不得,他在精神上已经战胜了命运,这象征着人对死亡的态度,象征着人的伟大和尊严,他展示了人会思想这一终极的骄傲来源!这是一种荒谬的幸福感。为什么荒谬呢?就因为这种幸福感并没有顺从自然!让命运感到失望,就意味着西西弗的幸福!西西弗是不可能被打败的,因为折磨他的事情同时就是鼓舞他的事情,这两种事情的力量不分彼此,合二为一。他的思想有崇高之美,就在于他没有被自己的自然状态打败,他决不顺从自然。自然状态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是人类赋予自然状态以意义,但人类的思想之所以崇高,就在于人可以给予自身的自然状态以任意的意义。
为快速占领市场,普拉公司选择在游人如织的迈阿密推广这款新产品。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迈阿密海边浴场人山人海,众多游客中,有一位穿着泳衣的美丽少女引人注目,只见她慢慢走向大海,随即像美人鱼一般钻入海中,她一会儿蛙泳,一会儿仰泳,不停变换游泳姿势。正当大家欣赏着她的优美姿态时,那女子双手忽然一阵胡乱扑腾,在水中挣扎了起来,游客们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出事了,快救人!”
从哲学上说,西西弗的幸福来自思想本身是无穷无尽的,我指的是思想的方向-意向可以朝着任意的方向!加缪认为,西西弗无声的快乐就在于此!这甚至就是他的全部快乐。可以自主地想到任何事情的快乐。总有神秘的心理召唤可以被随时唤醒,它们是灵魂的生命,是黑暗中的寂静之声。
从哲学上说,西西弗当然清楚他的物质生活是悲惨的。当他对悲惨满不在乎时,他的精神生命才真正起航。他自己给自己的精神生命加冕,亲手给自己带上皇冠。他永无休止地推石上山的行为,与这些时刻他在心里想什么,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只有想法本身才属于哲学。具有哲学性质的想法或者哲学问题,无法与物质行为无缝对接,这就是哲学想法的荒谬之处。只有荒谬的想法,才属于哲学的最高也是最后的想法,这正是哲学家区别于普通人的根本所在。真正的哲学家,只享受自己的想法本身。想法永远不能落实,因此普通人认为光想不做是无用的,但哲学家不这么看,因为想法本身就已经是享受,哲学家已经享受过爱的思绪,这就是他永远无法被人打败的快乐。没有任何人能左右别人的想法,这才是思想的最大尊严。物质生活是痛苦的,但是当一个人真能做到轻蔑这些痛苦时,他就具有了和哲学家一样的态度。
这就是冷漠的积极意义,对广义上的物质生活(还包括庸俗的人际关系、功名利禄)的冷漠态度,是获得思想自由的前提,西西弗可以热情地拥抱精神的自由。
因此,当西西弗走下山坡时,他既悲伤又由衷地快乐,两者都是真实的。但是,西西弗活得自相矛盾,他的精神是分裂的,也就是荒谬,如果将这样的情形在广义上推及到所有人,也同样适用。人生是由荒谬(自相矛盾的生活与思想)构成的,这是实情。换句话说,荒谬并没有脱离实际,它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人们只是懒得或者没有能力想到它,一旦正视它,想彻底,就会拷问灵魂,于是就获得了精神升华。
西西弗总是能战胜那块导致他悲惨命运的大石头,因为石头只是物,它就自在地摆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自然节奏运行,就像是春夏秋冬。但是石头没有属于它自己的世界,西西弗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自然界让人必死,但人的精神可以不死。人性之根本,在于人有永不服气、永不相信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英雄!人的精神永远不可能耗尽,这就是人的希望,绝望之中的希望。
1) 上述M,L,动态仿真观察周期TV,腹地货物产生周期T0,α,β,H,λ,ω,Pi,pi,DGT,IDGT,1,IDGT,2,Ts等赋值,并给定初始值T=0,j=0。
西西弗只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每个人的命运,其实和他是一样的。他的故事不过是把问题尖锐化、简单化了而已。
关于命运,我还有话要说,人的真正命运只有一个,就是人必死,其他都好商量。我的意思是说,其他都只是以可能性的状态潜伏着的,即使是极高的可能性,在它没有真正实现之前,也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唯有死亡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所谓命运也好,死亡也好,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抱着“我不知道”的态度,“我”只关心手头在做的事(它是“我”的意愿和兴趣之所在),而且永远如此,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生活本身。
在以上意义上,其实有两个神,一个是命运之神,它奴役人,告诉人什么都是天上早就写好了的;另一个神,就是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人的精神就是要让命运之神失望,以换取被折磨之中的快乐。反抗象征着人性的高贵。一味顺从命运的人,一味屈从他人的人,就把自己当成物了,不啻于一块石头,不再拥有自己的世界。
参考文献:
[1] 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2] John D. Caputo , Jacques Derrida -Saint Augustin ,Des Conffssions , Paris:Stock , 2007 .
[3] 萨特:《萨特精选集》,沈志明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4] 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段》,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5] M · 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李恒基、徐继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
Is It Right That I Can Do Everything That I Am Entitled To Do ?——A Tentativ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n Baccalaur éat G én éral Session 2017:Philosophie
SHANG Ji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plausible question “Is it right that I can do everything that I am entitled to do?” can b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philosophically from outside and inside. From outside, the question itself become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leading to an attitude of contrast, quotation, mention, and reflection. From inside, it turns into “I can” or a mental impulse of experience, employ, consumption and immersion leading to acts and practice. These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how a sharp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difference will enable a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philosophy.
Key words: right; justification; post-modern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9)01-0079-12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9.01.007
收稿日期 :2018-05-0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时间哲学研究”(14AZX01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尚杰,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吴 芳)
标签:权利论文; 正当性论文; 后现代哲学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