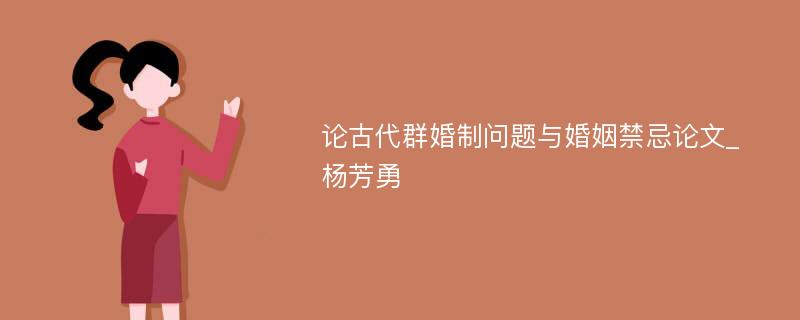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330077)
摘要:在婚姻与家庭的起源方面,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婚姻禁忌并非原始状态的婚姻形式,而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基于某种文化原因的一种婚姻制度的特例。我国古代有许多婚姻禁忌,其中属于永久性禁忌的包括“非偶嫁娶”和“干分嫁娶”;而原始时代开始就普遍地存在着的近亲禁忌,一方面形成家庭、氏族等稳定的血缘共同体;另一方面加强和改善了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从而产生了语言,创造了文化。
关键词:古代;群婚制;婚姻禁忌
中国古代,以家庭为核心的婚姻制度、宗族制度等等,一方面有如一张无形的巨网包罗着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又像一根无所不在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个人。因此,在中国,一切都是由血缘关系所支配和控制,个人不但没有主体意识,甚至也没有主体性;而家庭则不但是产生血缘文化的温床,同时也是传授这种文化的课堂,维护这种文化的堡垒。《易传•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古代的中国人对婚姻、家庭、乃至国家以及行为规范之起源的看法。
一、关于群婚制的探讨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兴起,人们试图通过对现代原始民族的比较研究,以揭示出生活在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从而弄清楚婚姻、家庭、国家以及社会的行为规范与行为控制的起源等问题。恩格斯便是在充分吸取了当时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起源的看法,长期以来,被我国学术界奉为经典。
恩格斯说:“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代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接着,他指出,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约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们和母亲们,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们,则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
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性交关系的话,那末,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姊妹与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血亲婚姻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
对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组织的渐趋发达,随着不许相互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类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在这个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便成为婚姻关系的惯例。
一夫一妻制家庭。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出来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父亲的子女,以便使家庭财产不致为他人所占有。一夫一妻制家庭与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因而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
最后,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总结:“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在对婚姻与家庭制度起源及其演化的论述中,恩格斯还肯定了继嗣制度和氏族制度所发生的转换,即母权制被父权制所取代。他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他认为,“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种中间形式上”。“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这种家长制家庭的产生,不但导致了财产的私有制,而且还导致了人对人的奴役和剥削。在此,恩格斯特别征引了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的一段批语:“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1]
二、婚姻禁忌中的干分嫁娶
我国古代有许多婚姻禁忌,其中属于永久性禁忌的包括“非偶嫁娶”和“干分嫁娶”,其中非偶嫁娶,指的是根据礼法不应匹配的婚姻。这种婚姻是社会文化因素限制而人为设定的禁忌,具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而干分嫁娶,是指干犯辈行和亲属关系名分的婚姻。这种婚姻如果脱离宋明理学封建礼教的成分,站在人类学研究的角度看,就是婚姻中的近亲禁忌,不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是严格禁止的,而且亲兄妹之间的性关系也是严格禁止的,这种禁忌从远古以来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限于篇幅,本文仅突出干分嫁娶中的近亲禁忌进行论述。
在我国远古的传说中,有女娲与伏羲的兄妹而夫妻的故事,并且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神与创造神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这似乎证明血亲婚配的存在。但是,他们之作为始祖神并不是因为他们生育了后代,而只是因为女娲抟黄土作人。所以,这只能表明原始人还不知道男性在生殖后代中的作用,而不能证明血亲婚配的存在。在远古的传说中有过兄妹互为婚姻的故事;而印加帝国、夏威夷皇室、古埃及法老都是兄妹通婚的合法,并且贵族内部甚至实行兄妹、父女、母子之间的通婚。这种情形,在实行内婚制的族群中是相当普遍的。对于中国原始时代的近亲禁忌,虽然我们还一无所知;而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之说,固然有人认为与原始时代的性禁忌有关,但据《礼记•大传注疏》所说:“殷人五世以后,则相与通婚。”且《大传》有云:“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所以,实则与近亲禁忌无关。不过,《礼记•内则》中所说的:“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筐;其无筐则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不言出,外不言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左,女子由右。”此外,《淮南子•齐俗训》也有所谓“帝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上者,拂之于四达之衢”之说。如此等等,作为近亲禁忌的防范措施的性隔离制度,虽然是后人的记载,但却不能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远古时代的近亲禁忌。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之所以敢于作出这一判断,是因为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同《礼记•内则》相似的性隔离的案件:
在美拉尼西亚,男孩和他母亲、姊妹间的交往,有着种种限制。例如在里皮斯岛,新海布里地族的一支,男孩到达某一年龄后便不可再属于家中,而必须迁入“营舍”内吃、住。当然他尚有权回到父亲的家中寻求食物,但如他的姊妹在家中,他便难免于徒劳往返之累了;若无姊妹在家,他可坐在门口吃食。在野外兄妹不期而遇时,她必须跑开或躲起来。男孩若在路上认出他姊妹的足印,他便不再顺那条路走。女孩亦然。事实上,他不但不可以说出她的名字,甚且在言语中避讳着它。此种“四避”始自成年仪式,而后持续终生。儿子和母亲间的冷漠随年龄而增加,通常世亲方面的态度变化得更为明显。一个母亲要送食物给她的儿子时,她只把东西放在地上,等他来拿,和他谈话时她不再表现出所谓的母子亲情,而系使用着对待外人般的礼节。类似的情形在新苏格兰群岛也很普遍,兄妹在路上相遇时,女的进入丛林内,男的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进。
在新麦克林堡群岛堂兄妹间也遭受如斯限制,彼此间互相不能接近,不可握手,不可互送礼物;不过尚被许可站在远处交谈。与姊妹乱伦则必需处以吊刑。在飞枝群岛禁制尤其严格,不仅施于血亲,而且兼及远房堂表。在南非戴拉果阿湾的巴罗恩果族,最严格的禁律系施于一个男人与其小舅(妻子的兄弟)的妻子间。他无论在何处一见这“可怕的人”,便赶快躲开她。他不可与她同桌而食,他与她谈话时神态不安,绝不踏入她的房间,与她打招呼时甚至连声音都会颤抖。在英属A—Kamba(或Wa—Kamba)族……女孩子在青春期后与成婚前需回避她的父亲。在街上相遇时,她需躲开待他走过,她绝不可走近他或坐在她父亲身旁。如此一直持续到订婚礼仪完后。婚后她就再也不必回避她的父亲了。总而
言之,最普遍最严格的(也是文明民族最感兴趣的)回避,存在于男子与其丈母娘之间。这种情形在澳洲很普遍,美拉尼西亚、波里尼西亚、黑色非洲,亦在所多有,……有此地方尚有媳妇与公公间交往的禁制,但较少见也较不严重。在罕见的例子里,公婆或泰山岳母,都是回避的对象[2]。如此等等,令我们不能不相信,中国古代的性隔离制度,绝不是古人的杜撰。对于近亲禁忌成因的解释,尽管直到现在依然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泰勒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他说:“族外婚能使一个发展中的部落,通过与其分散的氏族的长期联姻而保持自身的紧密团结,能使它战胜任何一个小型的孤立无助的族内婚群体。这种现象在世界史上曾经是屡次出现,这样,原始部落的人们在他们头脑中必定直接面临着一个简单而实际的抉择:或进行族外婚,或被彻底根绝。”不过,正如怀特所指出:“近亲禁忌的起源远远先于氏族组织”,因而泰勒的解释虽然为“理解近亲禁忌和族外婚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线索。”[3]但却并没有解决在氏族制度形成之前是否有杂乱性交、血亲婚姻等等的问题。所以,对泰勒的说法还须作一些补充和修正。
三、婚姻禁忌保障了人类的种族群繁衍
任何一种生物体都具有维持个体存在和种群繁衍的本能。前者表现为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需要,后者则表现为与异性进行性结合而生殖后代的需要,这就是食本能和性本能。为了保证这两种需要的实现,许多动物、尤其是比较高级的动物,还具有第三种本能,即攻击本能。然而,任何动物,如果为了满足食的需要或性的需要,而互相攻击、争斗不休,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遭致整个物种的绝灭。因此,动物的这种攻击性虽然是必要的,但必须有所限制。正如现代行为科学创始人康罗•洛伦兹所指出的:“利用进化的最精密办法——攻击的修正和调整,可以引导攻击行为至许多无害的路线上。”[4]于是,在许多动物中便形成了某些为同种个体所共同遵守的习性、仪式和固定化的行为规则以及相应的行为样式;而“行为样式与某种环境条件交互作用而获得一种完全新的功能——沟通。……从沟通中产生两种同样重要的功能,这两种也仍包含一些沟通的效果。第一种是引导攻击性到无害的出路。第二种是在个体间形成结合力。”[5]人类是从灵长目动物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物种。虽然人类所遵守的仪式是文化性的,而不像动物那样是进化而来的本能仪式。但是,“文化性仪式和本能仪式的进化中,有两个发展步骤十分类似,就是从沟通到攻击性的控制,再到结合力的形成。”[6]洛伦兹断言:“传统仪式的形成必始于人类文明初期,如同进化仪式的形成对于较高等动物社会组织的初创一样是必须的。”[5]其所以如此,便在于人类也只有借助于种种仪式化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样式,才能对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禁忌的划出一个界限,从而使攻击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受到控制。洛伦兹说:“我曾经提到在许多社会动物里的禁忌控制了攻击行为,防止他们伤害或杀死同种族的分子。”[7]遗憾的是,人类没有这样的幸运。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禁忌控制机制,以致为了国家、民族以及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互相残杀,甚而至于随时都可能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不过,人类确也由于有了近亲禁忌,才在一方面避免了父子、兄弟之间的情杀,从而才可能形成家庭、氏族等稳定的血缘共同体;而另一方面才加强和改善了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从而产生了语言,创造了文化。怀特指出,在低级灵长目动物中几乎完全没有相互合作。诚然,在一些极简单的活动中,一个类人猿会和另一个类人猿合作,但它们的合作是很有限的和极不完善的。猴和类人猿能通过信号——嗓子发音或手势比划——进行信息交流,但用这类方式所能 交流的思想范围确是非常狭窄的。唯有清晰的发音才会使广泛的和多方面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而这却正是类人猿所缺乏的。[8]所以,音节清晰的言语能力对于人类及其社会组织、婚姻与家庭制度,以及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如果没有近亲禁忌(当然,还可能包括其他种种性禁忌),没有族外婚制,人类不但不可能脱离其原始状态,甚至也不可能从类人猿中分化出来。不过,近亲禁忌和族外婚制是人类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有的,还是在其进化过程中才创造出来的,我们还不清楚。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中,便存在着母子不交配的禁忌。因此,人类的近亲禁忌是自己创造的,还是从类人猿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可以大胆推测:如果有一个像摩尔根—恩格斯所说的“杂乱性交的原始状态”时期,那末,恐怕人类早就绝种了。别的且不说,只要把动物的与人类的性冲动的频率相比较,绝种之说就绝不是危言耸听的。
四、结语
在婚姻关系上,由于婚姻禁忌而使内婚制受到严格禁止,这样,外婚制便成为了唯一可能的婚姻制度。众所周知,黄帝族也炎帝族是两个半偶族,姬姓与姜姓之间也长期地存在着相当稳定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甚至一直持续到东周时期。通过这种长久而稳定的婚姻关系,不但使两个半偶族成为了构成华夏民族的主干,而且还通过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而形成了华夏民族的血缘文化。因为华夏民族的根蒂是建立在相当牢固的血缘基础之上的,所以,即使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个民族也没有像其他原始民族那样因激烈的社会变动而解体,而重新组构,而形成新的民族。不仅如此,正因为华夏民族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剧烈而重大的变化而解体,所以,华夏民族的文化也就得以长存和弘扬。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中国的婚姻与家庭制度,不仅反映出了华夏民族文化的适应性、连续性,同时也反映出了这种文化的坚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09,《图腾与禁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3][8]怀特,1988,《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4][5][6][7](奥)康罗•洛伦兹,1987,《攻击与人性》,北京:作家出版社.
作者简介:杨芳勇(1968年-),男,江西黎川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社会人类学研究。
论文作者:杨芳勇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4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