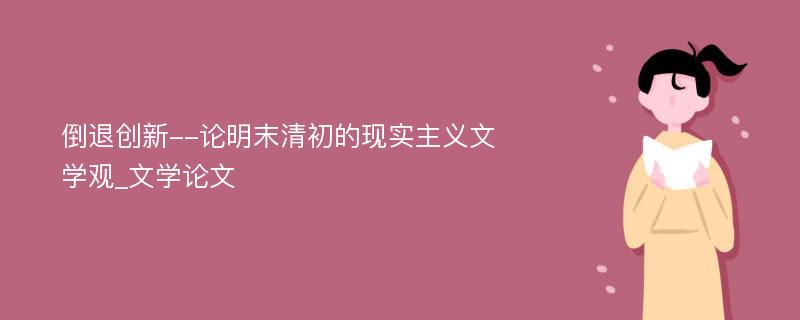
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清初论文,求实论文,观念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了求实文学观念的实际内涵和本质特征,指出求实文学观念纠正了主情文学观念淡化甚至放弃文学社会责任的偏向,要求文学家要有政治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因而具有革新倾向,但它否定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和超越性,从而又恢复了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因而是倒退的革新。
关键词 求实文学观念 主情文学观念 责任 功利主义文学
一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的思想文化界有两股主要的思潮,一股是以李贽等人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叛逆思潮,一股是以顾宪成等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改良思潮。这两股思潮之间有着深切的因缘关系,但在学风上却各标赤帜:前者务虚,后者务实。东林党人明确主张“论学以世为体”,反对“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强调“念头”要“在世道上”[1],这种思想直接触发了明末清初批判晚明“空疏无本”[2]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的时代文化思潮。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陈子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塨等人,“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3],针对“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4]的腐败现状,明确标举“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倡导求实学风。这无疑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陈子龙提倡“知今”,他辑录了《皇明经世文编》,在《序》中批判当时的务虚之风说:
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常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以继,故曰:“士无实学。”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明季士大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举世这般“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怎能不造成“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悲惨结局呢[5]?李塨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也尖锐地指出:由于空谈性理、轻视实务之风弥漫士林,“自明之季世,天下无一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恃之臣。”那些独当一面的地方官,成天埋头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还有闲情赋诗进讲。甚至朝廷的文臣武将们,都觉得建功立业只是琐屑小事,不值挂齿,而“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荼毒,呜呼,谁实为之?”[6]
求实学风的倡导,直接引发了求实文学观念的萌生。在《日知录》卷十九中,顾炎武提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时代命题,说:
文之不可绝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他还强烈地要求:“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学家须以“救民于水火之心”贯注于诗文之中[7]。
我们不难从这种“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中,辨析出它和儒家“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然而,由于现实社会和时代精神的影响,求实文学观念在传统观念的底色上,不能不涂染上一层耀眼的时代色彩。既然求实文学观念有两种价值尺度:一是现实的,即“当世之务”;一是理论的,即“六经之指”。那么,这一文学观念岂不是在复归传统儒家伦理精神的同时,又执著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岂不是在依恋古代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关注近代文化的风姿吗?
求实文学观念的这一特性,与求实学风内在的双重意向有关。求实学风一方面倡导面向现实,对自然现象、社会状况和政治弊端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如方以智著《通雅》一书,考核物理知识;顾炎武周历边塞,巡游内地,以所见所闻著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另一方面,求实学风也讲求“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提倡反思历史,援古证今,不发空论,所以顾炎武撰《日知录》,“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8]这种双重意向,前者以“当世之务”为趋归,后者则以“六经之指”为鹄的,由此构成求实文学观念的两种价值尺度。
那么,求实文学观念具有何种实际内涵和本质特征呢?本文拟从“帜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的理论展开中加以考察。
二
首先,改朝易代的严酷现实强烈地刺激了明清之际的文学家,酃他们头脑中源远流长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空前活跃。这就赋予“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以高度重视文学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的含义,即前引顾炎武《日知录》所说的,文学应具备“纪政事”、“察民隐”的功能。
黄宗羲认为,明朝亡国以后,历史的记载并不足以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反而是那些“从亡之士”或“章皇草泽之民”有感而发的诗歌,堪称“故国之鉴”,“不可不谓之史也”[9]。钱谦益临危变节,投降清朝,人品固然不足称道。但是他认识到“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10],发奋编辑《列朝诗集》这一皇皇大作,的确是存着一份以诗系史的苦心的。朱彝尊编选《明诗综》,不也明确表示,要“备一朝之掌故,而补史乘所不及”吗[1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代初年的诗人们,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吴伟业、钱谦益、吴嘉纪、屈大均、施润章等,有的直书国家民族的兴亡大事,有的歌咏动荡骚乱的社会现实,有的描写兵祸惨烈和民生苦难,有的抒发悲愤情感和矛盾心理。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天崩地陷的社会历史风貌。
清初散文创作最富于时代特征的有两类:一类是政论或史论文章,如顾炎武的《生员论》,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等等。这些政论或史论文章,大多以历史和现实相对照,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笔锋犀利,论述透辟,流荡着一股强烈的政治激情。另外一类散文是人物传记,如王猷定的《李一足传》、《汤琵琶传》,魏禧的《江天一传》、《大铁椎传》,侯方域的《李姬传》、《马伶传》等。这些传记以小说传奇的活脱笔法,作生动细腻的艺术描写,为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传神写照。这两类散文,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精神。
明清之际的小说创作,也突破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世俗生活的题材范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征实尚史倾向,产生了一大批“动关政务,事系章疏”[12],直接描写现实政治大事的时事小说。如反映明代天启年间客氏、魏忠贤乱政始末的,有吴越草莽臣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李清的《梼杌闲评》等;描写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事实的,有西湖懒道人的《新编剿闯通俗小说》,江左樵子的《樵史通俗演义》等;展示清兵南下和南明诸朝史事的,有阙名的《江阴城守记》、《七峰遗编》、《陆沉纪事》等。这些小说大多浸透着政治历史的浓度。
无独有偶,历来以“寓言”、“虚构”、“游戏”著称的戏曲创作,在明清之际也产生了数以十计的时事剧作品,并表现出鲜明的“以曲为史”的创作意识。如李玉择取明天启间东林党人周顺昌等和司礼太监魏忠贤“阉党”的政治斗争为题材,创作了一代“曲史”《清忠谱》传奇,声称:“锄奸律吕作《阳秋》”,“词场正史,千载口碑香”[13]。吴伟业为《清忠谱》作序,称扬道:“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戏曲家们明确地以“信史”为标准,创作戏曲,评论戏曲,展示了时代的风貌。到康熙年间,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先后问世,以写实的笔调融和着审美的精神,深入思考明清易代的史实所昭示的社会哲理,于是“词人多以征实为尚,不复为凿空之谈”[14],征史尚实成为戏曲创作的主要倾向。
顾炎武所说的“纪政事”、“察民隐”,这本是历史的职责,在明末清初文学家那里则成为文学的要务。因此,在“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中,我们不难辨析出这样的潜台词:文学必须攀附于历史之尊,有益于现实政治,才能忝登大雅之堂,“不可绝于天地间”。求实文学观念的这一价值取向,显然和十六世纪以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主情文学观念背道而驰。主情文学观念主张:“天下之至友,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15],衡量文学是否“至文”的标准,不是文学的内涵、社会功能,而是文学的情感深度、个性意义;因此,文学不应是体现、捍卫和传播某种社会价值的工具和手段,而应成为高居于任何社会目的之上的目的本身,具有独立自足的真实性和审美性。这种文学观念在本质上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观念相通,表现出鲜明的近代文化色彩。
固然,求实文学观念要求文学直面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直面严酷的人生和社会,要求文学家应有政治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从而纠正了主情文学观念的倡导者淡化甚至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极端偏向,这无疑具有革新的意义。但是它明确地否定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和超越性,把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重新付与历史、社会和政治,要求文学只能以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作为自身的价值,这就回复了儒家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这种向后倒退的革新,构成求实文学观念的本质特征。
三
但是,主情文学观念既然已经标示了近代文化精神的风向,那么,传统文化意识的再度复苏,就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近代文化意识的冲击,而偏离了惯常的轨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末清初的“发愤著书”说见出。
“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本身还有另一层含义,这就是倡导文学的批判精神,要求文学肩负起挽救民族命运、寻求社会出路、指导历史发展的重任。这是文人士大夫“士志于道”的“道统”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参与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突出表现。正是这种自觉的“道统”意识和积极的参与意识,使明末清初文学家的“发愤著书”说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背道而驰,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只有抒愤托志,才能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有抒愤托志之作,才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陈子龙《六子诗叙》指出:“诗之本”是“忧时托志”。在《诗论》中他痛斥“后之儒者”秉持“忠厚”诗教,“曰‘居下位不言上之非’,以自文其缩然。自儒者之言出,而小人以文章杀人也日益甚。”这就从反面论证了文学“言上之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顾炎武则从正面极力提倡诗歌直言讽刺的传统,在《日知录》卷十九《直言》中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要求诗人的个人兴感必须饱含社会意义,崇尚大胆的揭露与切直的批评,说:
诗教虽云敦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中,要求文学必须“积理”,所“积”之“理”,即“关系天下之故”;而“事理不足关系天下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廖燕在《狂简论》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从来著书人,类皆自抒愤懑,方将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以为快。”
人们不但用“发愤著书”说论诗文,还用它论词,如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论戏曲,如吴伟业为李玉的《北词广正谱》作序,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笔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论小说,如蒲松龄《聊斋自志》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宴》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以“发愤著书”说为动力,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们把文学的批判触角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道德、文化等等。而且,文学的批判精神也十分激烈,特别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王,表现出空前未有的勇气和胆略。如黄宗羲的《原君》,根据古代“公天下”和天子禅让的历史传说,认为君位的设立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而后世君王把天下当作私人产业,给天下造成了无穷的罪恶。因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对如此残暴的君王,天下百姓怎能不“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这实际上是针对明末清初的现实,有感而发的。如此激烈的言论,犹如石破天惊。
合而观之,明末清初的“发愤著书”说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认为抒愤托志之作比温柔敦厚之作具有更丰富社会意义,因此就有更高的审美价值。这是一种背逆于传统批判精神,闪耀着近代意识的熠熠光辉。另一方面,认为文学创作所抒发的不是个人的愤郁,而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真实感受,作家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内化为个人的孤愤,用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在这里,个人的命运必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自抒愤懑”的不谐和音是以个人和社会的高度谐和为基调的,这不正是儒家传统意识的真谛吗?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求实文学观念革新中向后倒退的一面。
“发愤著书”说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精神为其内在含蕴的。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精神本身就包含着双重涵义:即使是匹夫也应该把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是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精神;而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内化为匹夫的个人意志、个性精神,或者说要求匹夫的个人意志、个性精神浸透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这却染上了近代的色彩。在这双重涵义中,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精神显然占居主导地位,这就赋予“发愤著书”说以浓厚的现实感、时代感。
四
“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还要求文学具有“明道”、“乐道人之善”的本体意义。因此,求实文学观念渗透到文学本体观里,就是提倡作家的个人情感和传统的文化意识的高度统一。
在《马雪航诗序》中,黄宗羲重提“诗道性情”的古老命题,并作了新的诠释。他既不像程朱理学那样把“性情”完全等同于“天理”,也不像李贽、汤显祖和公安派那样赋予性情以个性自由的内涵,而是更重视超越个体情感而热爱国家民族的悲天悯人的怀抱,要求把“一时之性情”升华为“万古之性情”,也就是要求个人情感具有普遍而深远的社会意义。这种思想在表面上似乎比晚明公安派所谓“独抒性灵”要略高一筹,但当他论及“性情”的内涵时,却不免露出了复古的底蕴。他说:
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换句话说,只有“孔子之性情”才是“万古之性情”,如果个人“一时之性情”背离了“孔子之性情”,或者不能升华到“孔子之性情”的高度,那不是贬低价值,甚至毫无价值了吗?这实际上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说的翻版。其实,只要个人“一时之性情”是真实的、深切的,本来也可以升华为“万古之性情”的,大可不必以“孔子之性情”为旨归。然而,黄宗羲所信持的儒家传统文学观,是建立在以国家、民族、社会、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又怎能坐视文学驻足于个人“一时之性情”,怎能不倡导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呢?
力图赋予飘逸空灵的“情”以实实在在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从而自觉地给“情”套上紧箍,使之就范于儒家传统的文化思想,黄宗羲的这一理论思路在明末清初是有着普遍性的。如明末陈子龙《白云草自序》说:“诗者,非仅以适己,将以施诸远也。《诗》三百篇虽愁喜之言不在,而大约必极于治乱盛衰之际。远则怨,怨则爱;近则欲,欲则规。怨之与欲,其文异也;爱之与规,其情均也。”王夫之在《天问》题解中说:“篇内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
如果说,“发愤著书”说所主张的个人情感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而更多地富于革新意义的话,那么,经由“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而达到情理交融、情理合一的理论思路,则明显地昭示了求实文学观念向后倒退的特征。这一特点,在明末清初以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评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明末冯梦龙曾经提出“情教”的口号,他在《情史叙》中说:“情始于男女”,“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使情“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就可以达到“情教”的目的,发挥与《六经》不相上下的社会功能。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作家,往往强调“才情”,进而主张要正“性”定“情”,即以传统的伦理道德约束个人的自然感情,使“情”归附于“性”,同化于“理”。天花藏主人为《定情人》小说作序,详言道:
情一动于物则昏而欲,迷荡而忘返,匪独情自受亏,并心性亦不免不为其所牵累。故欲收心正性,又不得不先定其情。……情定则由此而收心正性,以合于圣贤之大道。这不正是明白地宣称要以封建正统观念和道德规范,即所谓“圣贤之大道”,来约束自由不羁的个人自然感情吗?
金圣叹批评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时,极力赞赏、肯定了男女主人公张生和崔莺莺的“必至之情”。他认为,才子佳人的“必至之情”本来是只能藏在胸中,不得一泻无遗的,否则就有违“先王之礼”。但是,由于老夫人已经许过婚,所以张生和崔莺莺的结合就不违反“礼”,张生“虽至死而无所忌惮”的爱情追求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的。按金圣叹的逻辑,张生和崔莺莺的至情是符合礼教的,因此值得肯定;如果违背礼教,“生必为狂且,旦必为倡女”,那不仅不应该肯定,还要口诛笔伐了。
这种以理制情、以情合理的观念,成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戏曲的共同审美趣味,作家的审美注意已经不是情理对立、以情反理,而是情理合一、以理制情,是尽可能地用理作为情的合理内核,尽可能地在情中输入理的血液。不仅风流佻挞的李渔,在《笠翁十种曲》中标树“风流、道学合而为一”[16]的理想人格;就连洪昇在脍炙人口的一代名剧《长生殿》中,也宣扬:“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17]
从文学观念演变的角度来审视叶燮“理”、“事”、“情”三者合一的诗歌主张,我们也许更能看出它的文化根柢。叶燮在《原诗》中认为,“理”、“事”、“情”是古今天下万物的规律、现象、本质等特征:“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而诗歌则必须三者皆得,才能“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诗之旨”是在“情”,而不是在“理”与“事”,于是他提出一个折中的看法:
唯不可明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可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不可明言之理”还是古今天下万物之理吗?“不可施见之事”还是古今天下万物之事吗?“不可径达之情”还是古今天下万物之情吗?如果不是的话,其间转变的契机是什么?撇开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中介、联系,而只注意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果关系,叶燮的诗说在辩证公允的外壳下不免包含着观念倒退的内核。
经过明末清初文学家的努力,“情”终于争得了自身在文学观念、审美观念中的合法地位。从此以后,即使再顽固的封建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情”的客观合理性,尽管时或以其主观不合理性为前提,对其横加贬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观念的真正进展,在实质上,勿宁说是文学观念的深层倒退——以牺牲对情理冲突的鲜明认识为代价,经由情的社会化、伦理化,换取情理和谐的廉价满足。这是何其得不偿失的兑换!这同样体现出向后倒退的革新的特征。
于是,在文学创作观上,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们有鉴于明代前后七子的摹拟涂泽之风和公安、竟陵的新奇幽僻之习,提出了性情与学问统一、创新与学古兼备的观点。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说:“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诗歌的最高造诣就是这种真和美的统一。叶燮在《原诗》中,虽然特别强调作家自出性情的创造,但他论述作家的“智慧心思”时又说:“唯叛于道,戾于经,乖于事理,则为反古之愚贱耳。”这就把人的主体精神一古脑儿地笼罩在古道儒经的罗网之中了。
在明末清初文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观,是既肯定文学家自身的独创精神,又要求这种独创性应不悖于古道儒经;既要求诗言性情,不依傍古人,又主张必须学古,追求“学于古人而自得之”[18];既尊崇以自然为法,追求无法之法,又提倡揣摩古人创作之法,以之为奉行不二的典型。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成为宗经、载道文学观念在清代中叶再度复兴的温床。
五
文学,就其社会本性来说,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求实文学观念及其所提出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无论是其重视文学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是其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主张“发愤著书”,还是其要求作家的个人情感和传统的文化意识的高度统一,在“天崩地陷”、改朝换代的明末清初社会中,无疑都体现了时代的愿望,表达了时代的思想,我们无法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延续主情文学观念或构建其他的文学观念;我们更不能不肯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求实文学观念显然处于时代进步思想的前锋。
但是,如果从文学观念发展和社会文化演变的角度着眼,我们不能不无遗憾地说,相对于16世纪以李贽的“童心说”为代表的主情文学观念而言,求实文学观念实质上呈现为一种向后倒退的革新。说它是革新的,因为求实观念一方面彻底纠正了明代前、后七子一味拟古、摹古、消泯作家真情实感的文风,另一方面也纠正了公安派、竟陵派局限于狭窄的个人情感而脱离社会、逃避现实的文风,这就促使文学面向现实社会、时代政治,浸透浓郁的时代感、现实感、历史感,升华到更高的社会历史层面。说它是向后倒退的,是因为求实文学观念所追求、所强调的,已不是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极力倡导的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和冲突,而是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的调解与和谐;已不是自觉地背逆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本体观、文学创作观,而是主动地趋同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本体观、文学创作观。中国古代的传统意识,偏向于绝对地要求以国家、民族、社会、群体为本位而贬抑个人的独立存在,偏向于单纯地在社会关系之中判定事物的价值而贬抑人的个性价值,因此总是要求文学表现并适合道德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求实文学观念正是以这种传统意识为文化根柢的。
总之,历史提供了“选择什么”的必然性,而文化则提供了“为什么这么选择”的可然性。在无可回避的历史选择中,明末清初的文化精英阶层凭借巨大的传统力量,对求实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状貌作出了自觉的选择,从而步入了向后倒退的革新的轨道。
随着时光的推移,进入历史上的所谓“乾嘉盛世”以后,求实文学观念的革新色彩渐渐消褪,凝聚为新的微弱的主情文学观念,如袁枚继公安派之后再一次“论诗主抒写性灵”[19],曹雪芹更以“情”构成《红楼梦》一书的主旋律。相反的,求实文学观念向后倒退的步调却渐渐加快,显现为传统意识的全面复归,包括文学在内的封建文化意识进入了它的最后一个极盛时期——回光返照的末世时期。
收稿日期:1996年6月3日
注释:
[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
[2][8]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日知录》卷首。
[3][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卷首。
[4]《明史》卷二五《杨嗣昌传·赞》。
[5]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
[6]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苞书》。
[7]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四《与友人书三》。
[9]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卷上《万履安先生诗序》。
[10][清]钱谦益:《有学集·胡致果诗序》。
[11]曾燠:《静志居诗话序》,《静志居诗话》卷首。
[12]峥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
[13]李玉:《清忠谱》传奇第一折《谱概》。
[14]吴梅:《中国戏曲概论》下。
[15][明]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
[16][明]李渔:《慎鸾交》传奇第二出《送远》。
[17][清]洪昇:《长生殿》第一出《传概》。
[18]汪琬:《尧峰文钞》卷三二《答陈蔼公书二》。
[19]《清史稿·袁枚传》。
标签:文学论文; 黄宗羲论文; 儒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明末清初论文; 读书论文; 日知录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顾炎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长生殿论文; 国学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