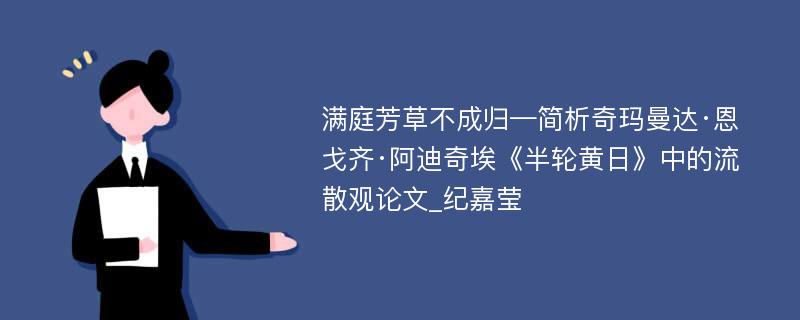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 130000)
摘要: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作为正迅速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尼日利亚作家的领军人物,尤其自2007年因其描写尼日利亚内战的作品《半轮黄日》获得橘子小说奖后,更是迅速蜚声国际文坛。阿迪奇埃在她的成名作中大胆运用自己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描述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大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探讨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当下的政治腐败在尼日利亚各种冲突和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后殖民理论的关照下对作品中的“流散观”进行阐释,解读流亡者去国还乡的苦痛及其在颠沛流离中获得全球多元文化观的潜在意义。
关键词:《半轮黄日》,流散身份,后殖民
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作为正迅速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尼日利亚作家的领军人物,迄今为止虽只出版了长篇小说《紫芙蓉》(Purple Hibiscus,2003)、《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06),短篇小说《绕在你脖子上的那个东西》(The Things Around Your Neck,2009),剧作《因为热爱比夫拉》(For Love of Biafra,1998)和诗集《决定》(Decision,1998),还有零星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但她赢得的国际奖项已超过十项,获得的提名亦不低于这个数目。尤其自2007年因其描写尼日利亚内战(又称“比夫拉战争”)的作品《半轮黄日》获得橘子小说奖(又名“女性文学奖”)后,更是迅速蜚声国际文坛,并受邀在TED发表演说。阿迪奇埃在她的成名作中大胆运用自己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描述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大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探讨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当下的政治腐败在尼日利亚各种冲突和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但她拒绝把问题简单化,把答案简单化,而是赋予作品以丰富内涵,因而一经出版,便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议题。
(1)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半轮黄日》一经出版,《纽约时报书评》、《卫报》、《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等权威媒体便争相发表书评。学术界亦紧随其后,相关的学术研究最早见于2006年,但多将它与其他第三代尼日利亚作家的作品一并纳入研究,其中,Pius Adesanmi与Chris Dunton合著的文章 “Introduction: Everything Good is Raining: Provisional Notes on the Nigerian Novel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将阿迪奇埃与海伦·哈比拉、克里斯·阿巴尼列为第三代作家的核心人物,并将《半轮黄日》视为以尼日利亚内战为主题的小说中最富创造力的作品,认为它的历史主题和叙事手法均独具特色,文章既肯定了作品的学术潜在价值也奠定了日后的研究方向。而对于该作品的针对性研究则始于2008年,并在进入2010年后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相继出版了从多方面对该作品进行解读的学术专著、文章,硕博士论文,大多以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J) 和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J) 作为其研究阵地,近来热度更是有增无减。相关研究大致沿以下几个方向进行:
1.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相关研究:
① Lily Mabura的文章 “Breaking Gods: An African Postcolonial Gothic Reading of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Purple Hibiscus and Half of a Yellow Sun” (2008)从“非洲后殖民哥特式书写”的视角对《半轮黄日》进行阐释,首先回顾了在殖民地化以前及殖民地时期,非洲文学中的哥特式描写传统,继而通过分析阿迪奇埃在作品中对伊博族诸如乌库艺术、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哥特式描写,指出她对于非洲人民焦虑心理的剖析及殖民统治下民族传统对于保持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这一研究首次敲开了后殖民主义的大门,其中对于部落传统文化的关注恰似对黑人作家前辈托妮莫里森的遥遥呼应;
② Susan Strehle在她刊登于 Modern Fiction Studies (J) 的文章 “Producing Exile: Diasporic Vision in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1)中阐明小说的三位叙述者无论是否归属于尼日利亚人这一民族群体,无一例外均是流亡人,同时通过分析他们的流亡经历指出“流散”这一现象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这就打破了以往对于流散或利或弊的单一性认识,但其对作品中的流散身份的一并而论仍有待细化分类研究;
③ Madhu Krishnan发表于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J) 的文章 “Abjection and the fetish: Reconsi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2) 将恋人理查德与凯内内作为分析案例,运用后殖民主义的分支理论Exoticism对作品进行解读,并说明Exoticism是如何通过转喻(metonymy)得以实现的。文中对于Exoticism是双向作用结果的强调,无疑是对于霍米巴巴文化糅杂论的肯定,而对于其实现方式的探讨——同语言学相结合,无疑是该研究的一大创新之处;
④密西西比大学的硕士研究生Lauren Rackley在其论文 “Gender Performance, Trauma and Orality in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and Purple Hibiscus”(2015) 中研究了后殖民创伤对于女性行为的影响,并指出这种个人层面的伤痛遭遇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创伤写照,是殖民主义的余波。该论文首次从后殖民创伤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但其认为作品中的创伤乃心理创伤而非肉体创伤的观点仍有待商榷;
上述研究均为后殖民视域下各具体方面的开先河之作,为后续该理论指导下的文本解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流散文学视角出发的相关常识尚显不足,已有研究或是将所有的流散身份一概而论,或是对流散现象的利弊性分析有失偏颇。
2. 从叙事学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
① Emmannuel Mzomera Ngwrra在其文章 “‘He Writes About the World that Remained Silent’: Witnessing Authorship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2) 中指出《半轮黄日》是一部元小说,并阐明其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了Mise en abyme (‘戏中戏’,叙事内镜)这一叙事手法;
②Aghogho Akpome的 “Focalization and Polyvocality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3), Maya Ganapathy的 “Sidestepping the Political “Graveyard of Creativity”: Polyphonic Narrative and Reenvisioning the Nation-State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6) 以及Nida Sarfraz、Rehana Kousar 和Khamsa Qasim 三人合著的 “Reclamation of History: Discerning Polyvocal and Decentering Voices in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6) 等均从叙事视角出发解读作品,分析阿迪奇埃是如何运用去中心化叙事/多声部叙事的写作策略以及该策略所达到的叙事效果。
3. 互文性相关研究:
① 阿迪奇埃与钦努阿·阿契贝渊源颇深,不仅他们同属伊博民族,阿迪奇埃更是居住、成长于这位“现代非洲小说之父”的故居,正因如此,一些学者便关注阿契贝对于阿迪奇埃创作的影响及二者作品中的互文性关联,如来自约翰内斯堡大学的Aghogho Akpome 撰写的硕士论文 “Narrating a new nationalism: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stylistic influence of Chinua Achebe’s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o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2) 和Ruth S. Wenske 的 “Adichie in Dialogue with Achebe: Balancing Dualities in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6)
② Matthew Lecznar则于更广阔处进行研究,在其文章 ”Refashioning Biafra: Identity, Autho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Dress in Half of a Yellow Sun and Other Narratives of the Nigeria-Biafra War“ (2017) 中分析了阿迪奇埃对于以往描绘比夫拉战争作品的继承与颠覆,尤其她对于服饰的改制体现了其女性主义书写。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4. 其他理论关照下的相关研究:
一些学者也从其他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Aghogho Akpome 发表于English Academy Review(J)的 “Narrating a new nationalism: Rehistoricization and political apologia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3),Meredith Coffey 的 “‘She is Waiting’: Political Allegory and the Specter of Secession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2014) 将《半轮黄日》作为一部政治小说来阐释,而 “Sex as Synecdoche: Intimate Languages of Violence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and Aminatta Forna’s The Memory of Love” (2012)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强调了女性写作中“性”与“暴力”密不可分的关系。
相较于国外学术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热况,国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则极为寥寥。自2010年中译本出版后,迄今为止,尚只有数篇评述介绍性文章,如沈磊于2014年发表于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的文章《人性的呼喊—评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的<半轮黄日>》,留下了较大的学术空白和解读空间。故本文试图在后殖民理论的关照下对作品中的“流散观”进行解读。
二.去国还乡,满目皆是流亡人
后殖民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而言的。殖民主义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其他较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经济上的侵略,这种侵略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但随着二十世纪中后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殖民列强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转向了一种更为隐蔽的帝国主义机制--“权力话语”,以期继续牢牢控制东方大地这片“公共游戏场”。一方面国家百废待兴、民族身份亟待建立,另一方面殖民主义的阴影仍弥散不去,后殖民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发展起来的。其中代表人物包括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罗伯特·扬(Robert Young)等人,这些学者在文化场域以激进的立场对殖民主义话语展开批判,从而成为20世纪后期最具活力的批评潮流之一。尼日利亚就是这样一片历史上饱受列强蹂躏、独立后殖民幽魂仍萦绕游荡的土地。1884年的柏林会议确定了英国对其的控制权,并于1914年由时任的总督夫人将其命名为尼日利亚。
这段殖民历史不仅表现为英国对尼日利亚“分而治之”的政治干预,更导致了思维的逻辑怪圈,一方面,早在殖民者到来甚至可能早在殖民国家建立以前,这片土地和在其上栖息劳作的人民就已然存在了;但另一方面,殖民者所创造的概念渗透进每一孔每一隙。作为一名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奥登尼博一方面激愤地表示“他们(学校)将交给你说,是一个叫芒戈·帕克的白人发现了尼日尔河。胡说八道。远在芒戈·帕克的爷爷出生之前,我们的人民就在尼日尔河里打鱼了。但在考试的时候,你只能写是芒戈·帕克发现了尼日尔河。”(阿迪奇埃 2010:13);但另一方面,他在自己主办的文化沙龙与同在恩苏卡大学教书的其他知识分子辩论时,使用的概念亦是殖民的产物:
“当然,当然,但我认为非洲人唯一的真实身份是部落,”主人说,“我之所以是尼日利亚人,是因为白人创立了尼日利亚,给了我这个身份。我之所以是黑人,是因为白人把‘黑人’建构得尽可能与‘白人’不同。但在白人到来之前,我是伊博族人。”
埃泽卡教授哼了一声,摇摇头,把一条干瘦的腿搁在另一条上。“但是你之所以意识到自己是伊博族人,是因为白人。泛伊博族的理念是面对白人的宰制才产生的。你必须认识到,今天的部落概念也与民族、种族等概念一样,是殖民的产物。”(24)
Eghosa Osaghae指出“Negeria was a British colonial creation”(Eghosa,4),相信亦是就意识文化层面而言。
同时,后殖民主义与生俱来的流散性也颇为值得关注。并称为“后殖民三剑客”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以及阿迪奇埃无一例外,均是萨义德口中的“an artist in exile”,他们都生于第三世界国家,但自年少起便学于异国、终居于异国,其特殊的经历赋予了他们得天独厚的从事相关文化研究的条件—熟识两种文化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无论于哪一种文化而言,他们都无法彻底被认同被接受,始终是局外人。《半轮黄日》恰是这样一部流亡人写流亡事之作,但从幻想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先无家终无国的飘零浮萍,流散意味较作家本人经历而言则浓厚了许多。
作品摒弃了以往作家在历史小说中惯用的全知、权威、客观的写作视角,转而采取“多声部”的叙事策略,借助三位民族、性别、阶级迥异的人物视角来看待这一场民族战争,但三者无一例外地都是去国还乡的流亡人。理查德在其间最是明显,从头至尾他在自己选择居留并渴望有所贡献的这片土地甚至从未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即便幼年在英国时,他亦是一个局外人,父母虽十分恩爱,但却“从未有过生他的计划,所以对他的抚育全是事后的安排”(138),在他的父母故去后,在继而抚育他的姑母家,理查德更无归属感可言,因此他多次尝试逃跑,但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跑去哪里”(72),他同样不知道自己在尼日利亚该做什么,看似一直进行的写作究竟要写点儿什么,他无法理解当地民众的互动逻辑—凯内内忙碌的生活,她与马杜上校的亲密关系。缺乏归属感、踌躇困惑,迫切渴求个人与社会双重的稳定团体—理查德代表了典型的流亡者形象。而当“他走到凯内内跟前,伸出胳膊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想感受她的心跳。生平第一次,他感到自己找到了心灵的归属。”(97),同时,他感到“在某一方面,他做尼日利亚人永远赶不上做比夫拉人:他从一开始便在这里;他参与了比夫拉的诞生。他将在比夫拉找到归属感。”(201)。但是比夫拉战败、凯内内失踪彻底击碎了理查德的家园梦,无论从个人亦或是社会层面:
“他眼前一黑,等他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后,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再见到凯内内,他的生活永远都会像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他不论看什么,都将是倏忽一瞥,影像模糊。”(512)
同样地,奥兰娜也是一个对周遭缺乏确凿认知的旁观者。尽管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尼日利亚人,熟识很多理查德未曾了解的文化习俗,但她的海外教育经历、常人可望不可及的财富地位都使她成为了一样国籍、一样相貌的“外来客”。最先不接纳她的就是奥登尼博的母亲,妈妈认为奥兰娜是“异类”,不相信她能正常生育,还为此从偏远家乡带来一个乡村女孩儿引诱自己的儿子:
“他们说你没有含过母亲的乳头。”主人母亲转身看着奥兰娜。“请回去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你没找到我儿子。告诉你的女巫同伙,你没看见他。”
奥兰娜两眼圆睁,盯着主人的母亲。主人母亲提高了声音,仿佛是奥兰娜持续的沉默逼得她喊叫:“听见了吗?告诉他们,谁的药都不会对我儿子起作用。他不会娶一个不正常的女人,除非你先杀了我。除非我死了!”主人的母亲拍着手,随后发出猫头鹰一般的叫声,同时用手掌击打嘴巴,制造回声的效果…….
“不要叫我妈妈,”主人的母亲说。“我说过,不要叫我妈妈。只希望你别骚扰我儿子。告诉你的女巫同伙,你没找到她!”她打开后门,出去大喊:“邻居们,我儿子家里有一个女巫!邻居们!”她的声音尖利刺耳。(115)
奥兰娜对于奥登尼博的迷恋源于他对于本民族团体的强烈拥护。在目睹了售票员给予白人可以优先购票的特权后,“一个身穿褐色旅游装、手握一本书的男子竟然勃然大怒,他就是奥登尼博。他走到队伍最前方,把白人男子送回原位,有对着售货员大吼:‘你这个可怜的蠢货!你看见一个白人,他比你的同胞长得好看?你必须向排队的每一个人道歉!快点!’”(34),但颇为讽刺的是,她本人却不被这一民族团体所接纳。同理查德一样,比夫拉战败、凯内内失踪,无论家、国层面,奥兰娜彻底成为了一个游荡的灵魂。
三.结语
正如萨义德本人所指出的:“For surely it is one of the unhappies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 to have produced more refugees, migrants, displaced persons, and exiles than ever before in history…” ,流亡者去国还乡的悲痛永远无法痊愈。但在颠沛流离的放逐中,他们也认识到作为欧洲舶来品的民族主义,无论在尼日利亚或在比夫拉注定以悲剧惨淡收场。理查德、奥兰娜劫后余生,尽管至此之后无国无家,如浮萍般飘荡游散,但他们跳出了民族主义的夹缝审视比夫拉、凯内内以及对于一个公正国家建立的幻想。这种流散视角虽不能立时发展为多文化主义,但着实提供了多角度审视民族团体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Adichie, Chimamanda Ngozi. Half of a Yellow Sun[M].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4
[2] Osaghae, Eghosa E. Crippled Giant: Nigerian since Independence. London: Hurst, 1998
[3]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3
[4] 阿迪奇埃. 半轮黄日[M]. 石平萍,译. 译林出版社,2010
[5] 杨冬. 文学理论: 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纪嘉莹(1992-),女,汉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国家文学
论文作者:纪嘉莹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7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7/9/5
标签:尼日利亚论文; 奥兰论文; 殖民主义论文; 作品论文; 理查德论文; 阿迪论文; 白人论文; 《知识-力量》2017年7月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