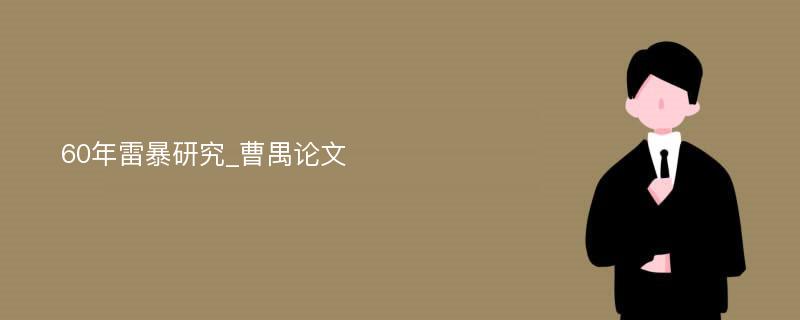
《雷雨》研究6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禺成名作《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雷雨》发表60年来历演不衰,剧本一版再版,深受中国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60年来有关《雷雨》的评论和研究文字其数量百倍于原著。人们对《雷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60年来,学术界对《雷雨》的研究可划分为3个阶段:解放前、解放后17年、新时期。现将3个阶段的研究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
曹禺的《雷雨》是1934年7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的,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35年5月,经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的推荐,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才引起了日本人士的重视,撰文予以评论。同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在国内首次演出《雷雨》,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发表了几篇剧评,作了肯定。以后关于《雷雨》的评论文章就逐渐多起来了。
最初有关《雷雨》的文章是感想式的,是看了演出后的观感,属直感的判断,后来也有了评论,但真正称得上学术性的研究文章,是在40年代才出现的。那时大多数文章对《雷雨》是肯定的、赞扬的,但也有个别人对它持否定态度,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挑了不少的毛病。
1935年5月《雷雨》在东京公演时即有白宁的报道《〈雷雨〉在东京公演》[1]。文章说这出剧“是描写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及残酷的暴露着他们淫恶的丑态。用夏夜猛烈的‘雷雨’来象征这阶级的崩溃”。这是对《雷雨》最早的评介文章。在7月出版的《杂文》第2期上发表了曹禺致中华话剧同好会的信《〈雷雨〉的写作》,杂志的编者给信写了一段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是一个极好的讽刺。”白宁的文章和《杂文》的按语都很简短,但都认为《雷雨》的主题是在“暴露”“现实”,象征资产阶级的“崩溃”,是从文艺的社会功能去解读这出戏剧的。正因为这样理解,按语还指出了作者主观的创作意图与作品在群众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矛盾的,以后不少人沿着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较早对《雷雨》作出高度评价的是郭沫若。1936年1月他在《关于曹禺的〈雷雨〉》[2]中肯定它“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极力赞扬该剧的艺术技巧,“很自然紧凑,没有出现十分苦心的痕迹”。发表较早,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评论文章是刘西渭的《〈雷雨〉——曹禺先生作》[3]。《雷雨》中的“命运观”问题就是刘西渭发现的。他说“这出长剧里面,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但他认为这种观念并不体现一种“天意”。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心理作用里”的,也就是说“决定而且隐隐推动全剧的”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经刘西渭指出后,《雷雨》的“命运观”问题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至今还难说有统一的意见。与此有关的是作者对周朴园结局的处理问题。剧中人物或死、或疯、或走,唯独周朴园活下来了,这样处理恰当吗?刘西渭有独特的看法,他说“从一个哲学观点来看,活着的人并不是快乐的人;越清醒,越痛苦,倒是死了的人,疯了的人,比较无忧无愁,了却此生债务”。这就是说作者是有意让周朴园活下来承受精神上痛苦的,但他认为广大观众却不一定能理解作者的深意。
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4]可以说是对刘西渭提出的问题的进一步发挥,但有些问题理解得过于狭隘,对作品否定过多。张庚是根据曹禺《我怎样写〈雷雨〉》(即《雷雨·序》)中关于“命运”的一段话展开评论的。张庚说悲剧发展的轨迹是“命运、性格、人性一直到社会制度,是以曲线的进行来接近人类生活的悲剧的真理的”,以此标准来衡量《雷雨》,他认为曹禺“不是走着逐渐接近真理的路”而是继承了“由传统中传留下来的”“宿命论”,对悲剧缺乏正确的认识。他据此判定《雷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作者把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不是统一而是混合的,时时出现了裂痕和矛盾”。这一断语未免过于武断,人们难以接受。但是,张庚又肯定了《雷雨》“最成功的一方面是人物”的塑造,他特别称赞蘩漪和周萍,他说由于作者对这类人物很熟悉,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不意地击碎了自己的哲学——宿命论”。虽然“作者并没有想批判什么,可是为了他忠实于他的人物”,实际上是对社会“发挥了痛快的暴露”,使剧作“部分地有了反封建的客观意义”。由此,张庚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在《雷雨》的创作过程中,体现了曹禺“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方法上的矛盾”。这个论断是符合曹遇当时的思想和《雷雨》的实际的,只是张庚对此的分析还不够,以后不断有人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对《雷雨》的评论中不时冒出点奇谈怪论。早在东京演出时,就有个观众写信给剧团进行漫骂,称“此等烝母奸妹之剧……公演于岛夷之邦”有损“国家体面”[5]。1937年黄芝冈发表《从〈雷雨〉到〈日出〉》[6]对《雷雨》的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作品宣扬的是“正式结婚至上主义”,人物是“鬼气森森的”,他说《雷雨》得出的结论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先死,留老年人撑持世界”,因此黄芝冈断言“《雷雨》对青年人的指导上走了歪路”。
针对黄芝冈这种“实在太不公允”的批评,周扬撰写了《论〈雷雨〉和〈日出〉》[7],对黄文的批评进行了批评,指出黄芝冈是以“社会批评”来代替文艺评论。周扬认为反封建制度是《雷雨》的主题,而宿命论则是它潜在的主题。之所以会有这个潜在主题,是由于作者虽然看出了“大家庭的罪恶和危机,对家庭中的封建势力提出了抗议”,但是“他看不出实践的出口”,“他的现实主义在这里停了步,没有贯彻下去”,而这种思想对一般观众“会发生极有害的影响”,也大大地降低了剧本的思想意义。但是周扬联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仍然对《雷雨》作了较高的评价,说曹禺虽然“和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但“对于现实也并没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对现实的忠实描写中,达到了有利于革命的结论”。为了突出反封建的主题,周扬主张去掉“序幕”和“尾声”,“让观众被就在眼前的这种罪恶所惊吓,而不自主地叫出:‘来一次震撼一切的雷雨吧!’”他还批评曹禺把周朴园与鲁大海的矛盾纠缠在血统上去,主张写成“两种社会势力的相搏”,这样“悲剧就会带着更加深刻的社会的性质”,向观众“展示出一个旧的势力的必然的崩溃的历史的远景”。周扬当时是我党在白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的评论自然带有权威性,对以后40年的《雷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0年代初,曹禺修改《雷雨》,基本上是顺着周扬的思路进行的。
40年代出现了对曹禺创作系统的研究,有影响的便是1944年发表的杨晦的《曹禺论》[8]和吕荧的《曹禺的道路》[9]。这两篇综合性质的论文自然要对《雷雨》进行评述。杨晦文艺批评的价值尺度是:文艺作品“应该回答当前观众和读者的要求”,“不如此,不与粗服乱发的老百姓相结合,艺术将不能生存,不能发展”,因此,他批评曹禺处在民族危机之时,而在剧作中却“闻不到一点战争的血腥”。他批评序幕和尾声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他的观点,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正跟曹禺的‘用意’相反。我们不要‘一种哀静的心情’,不要什么‘欣赏的距离’。我们所要求的,是对于现实的认识与了解,是要作者指示给我们:这个悲剧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悲剧在我们现实生活里的意义和影响;并且希望得到作者的指示:我们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悲剧的问题……我们要由了解进而为一种行动。”固然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看重文艺的教育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杨晦似乎功利心太迫切,要求文学作品像社会科学著作那样,而忽视了作家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特殊方式。同时他还罗列了《雷雨》的许多缺点:篇幅过长、时间地点不明确、女性人物均跟丈夫姓等等,显得过于挑剔。
吕荧在《曹禺的道路》中着重论述了《雷雨》的主题。《雷雨》自演出以来一般人都把它的主题归纳为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周扬的文章发表后,更加深了人们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吕荧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剧本描写的“残忍”与“冷酷”正“显示着宇宙‘主宰’的真相的一面”,而“这一主宰是《雷雨》的主题”。但吕荧又指出,曹禺的“主宰”的观念,比鲁妈的“命”的观念要复杂得多。“这‘主宰’,在作者的意识根底上,它是希伯来先知们的‘上帝’,希腊悲剧家们的‘命运’,和近代的人所叫的‘自然法则’,结合起来的一个二元的‘观念’”。但他认为这二元的主题观念中“观念的命运的一元更强于社会学的‘自然法则’的一元”,也就是说“显示主宰的‘残忍’的意义要更强于所谓‘暴露大家庭罪恶’的意义”。吕荧是根据曹禺的创作思想,对作品的实际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作品的客观效果。他说:“由于人物的真实,由于观念的虚渺,悲剧《雷雨》不是作为神秘剧,而是作为社会剧被欢迎了。”吕荧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作品实际的,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直到80年代,人们突破了阶级分析模式时,又从吕荧的观点起步,对《雷雨》的思想作出新的判断。
三四十年代对《雷雨》的研究虽然由直觉式的观后感向系统的理性思考发展,在深度上有所拓展,但在广度上未有大的拓宽,研究的范围多局限于作品的思想意义以及与此有关的作者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而在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时,多以社会效果作为价值尺度,忽视了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审美功能的研究,对作品产生了“误读”。这一研究模式对五六十年代的《雷雨》研究有重大的影响。
二
50年代初,文艺工作者积极学习并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描写、歌颂工农兵的文学作品备受广大读者和评论工作者的青睐,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暂时还没有人去评论、研究。《雷雨》自然也遭到冷落。1951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陷。《史稿》肯定《雷雨》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戏剧创作上稀有的成就”。王瑶说“《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现实意义的”,但作者在处理这题材时却特别强调了宿命论观点,“以情爱与血缘的各种巧合的伦常纠葛来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但是由于“作者所写的人物性格的真实”,观众“是把它当作社会剧来欢迎的”。这种评价实际上与周扬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自此以后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要对《雷雨》进行评介[10]。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后兴起了一股“‘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热”,曹禺的剧作重新出版、演出,《雷雨》也再度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评论家的关注。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随着《雷雨》在各大城市的演出,《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重庆日报》、《成都日报》、《北京晚报》等报纸纷纷发表剧评。这些评论除谈演出外,更多的是对剧中人物的理解和该剧的社会意义。但因当时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评论也多从政治意义、社会效应这一角度来进行阐释的。
1958年学术界围绕《雷雨》的命运观和曹禺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开展了一场讨论。这两个问题在三四十年代就讨论过,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甘竞、徐刚却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曹禺在《雷雨·序》中讲的“主宰”、“命运”、“自然法则”等引起人们争议的思想只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并不构成作家的真正世界观”。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突出‘命运的力量’,把它作为事件发展的主宰”,他们强调作品是“通过偶然性事件来突出地表现生活中已经产生和必然产生的悲剧”;是人物“在各种不同性格的冲突的基础上”“导致悲剧的结局”。甘、徐2位还是认为曹禺的世界观是存在缺陷的,这缺陷就是他脱离实际的政治斗争,没有与工农相结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因此使作品“无法达到高度的历史真实性,不能有力地表现出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情势和广阔的社会背景”[11]。刘正强不同意甘、徐2人的观点。他认为曹禺“在《雷雨》序言里所作的解释正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缺陷,他的这种缺陷同时也影响到作品中的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成分”。刘正强指出,“作者在这个社会悲剧中加上了许多性爱和血缘的纠结,给人的印象是,要解开这个结几乎是不可能的”。“剧中活动着的人物,除了和环境奋斗不幸而失败之外,还有一种命运的权力可以支配人的行动,不幸的发生,好像是注定了的”。“因此这些情节的安排,不能认为只是纯粹为了加强戏剧性,这其中是有许多神秘性和宿命色彩的”。刘正强的结论是:曹禺世界观中有进步的也有不正确的因素。“曹禺的进步的世界观一直是使他能掌握先进创作方法的关键,但也不能否认他的观念世界中那些不正确的因素对他的艺术作品带来不良的影响”[12]。在这场讨论中多数学者认为曹禺世界观中有落后的因素,《雷雨》中有宿命论观念。如建领、君圭认为侍萍回到周宅的情节正是体现了“命运的规律”,而侍萍关于命运的一些台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当然不是全部)思想的”[13]。
这场论争是在“反右斗争”以后,文艺界在学习、讨论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这就不可能不带上“左”的理论色彩。论争双方虽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但认为作家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却几乎是共同的结论。
60年代初,钱谷融研究《雷雨》人物的系列论文的发表是《雷雨》研究的新成果[14]。他针对1959年上海人艺以阶级斗争模式处理《雷雨》的人物关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阶级本质是渗在具体的个性中,而且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个性,则总是比较复杂的,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还常常是盖有各种各样的涂饰物的”。因此,这组论文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来分析人物,而是从作品中人物本身的言行出发,从戏剧情节出发,细致深入地分析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的潜意识、潜台词,避免了当时许多文学评论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谈周朴园的那篇论文中,钱谷融选择了常引起人们争论的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感情纠葛为重点进行研究,指出“不能认为周朴园对侍萍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认为他对侍萍的种种怀念的表示都是故意装出来的,都是有意识地做给别人看的,这样想,就把一个人的复杂心理面貌简单化了”。对第二幕周朴园与侍萍再度相见,第四幕周朴园当众认侍萍时的心理,钱谷融均有独到的艺术发现和精微的心理分析。钱谷融的《雷雨》研究对流行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有所突破,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可说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在当时“左”的简单化的理论影响下,钱谷融的文章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受到了王永敬、王一纲等人的批评[15]。他们认为钱谷融是用“人性论的观点”在对待周朴园,他们否认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复杂的,认为他对侍萍只有兽的“性”和阶级的“残忍”,而没有人的真情怀念。
1960年陈瘦竹、沈蔚德发表《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16]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两部剧的结构艺术,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文章指出,曹禺善于运用结构艺术,精心组织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充分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他的剧作随处都能引人入胜。文章指出,《雷雨》要表现的是30年来周朴园家庭复杂的矛盾,要把这些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展开,曹禺就向欧洲的一些剧作家那里(特别是易卜生)得到借鉴,用“回顾方法”,“以‘现在的戏剧’为主,而将‘过去的戏剧’穿插其间以便产生推动作用”,这种结构方法给作者带来许多困难,“他一方面既要揭开现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前情必须逐步交代”。论文对四幕主戏的情节结构逐幕作了细致的分析,说明剧作是如何以“过去的戏剧”来推动“现在的戏剧”的。论文认为剧作“结构严谨慎密,许多线索彼此交织,互相衔接,几乎牵一发就要动全身,使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也是《雷雨》的一大成就”。
60年代《雷雨》研究中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收获,就是版本研究。《雷雨》问世以后多次印刷,曹禺对它也进行过几次程度不同的修改。致使在社会上流传的有5种版本。第1种是1934年发表在《文学季刊》的刊本,第2种是1936年文化生活书社的单行本,第3种是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剧本选集》本,第4种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曹禺剧本选》本,第5种是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雷雨》第二版本。这些修改反映了曹禺创作思想的变化。对版本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曹禺创作思想的研究。廖立的《谈曹禺对〈雷雨〉的修改》[17]就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反映。论文对《雷雨》的5种版本一一作了比较,认为单行本只对季刊本增加了点演出提示,更适合演出使用。1951年的选集本改动最大,周朴园、周萍、鲁妈、鲁大海的人物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四幕几乎等于重写,“作者改变了原来的悲剧结构,最后也没有死一个人”,原有的序幕和尾声也删去了。这样修改是为了增强作品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于是强化了周朴园的反动、狠毒的一面,也“提高”了鲁大海和鲁妈的反抗性。这样修改的结果“却使这个剧本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后来曹禺也渐渐认识到这样修改的错误,1954年出《曹禺剧本选》时,又保持了原来的面貌,但在文字上作了些合理的修改。曹禺一直认为《雷雨》写得太长,给演出带来困难,需要大大删减。因此,1959年的戏剧二版本,“删去了将近十分之一”,这些删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情节和人物,所以基本保持了原貌。剧本的一些修改、加工,大半是为了演出”。廖立认为,在这5种本子中戏剧二版“是适合演出的,也是较为完整的本子”,至于研究者,还是“应当以解放前的老本子为根据”。
解放以后到文化革命这17年来学术界对《雷雨》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说研究的面不够广阔,多局限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作者的世界观等问题上;又因受阶级分析方法的限制,使得许多问题无法深入下去。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形势,曹禺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百家争鸣。十几年来有关曹禺研究的论文有几百篇、专著20余部,涌现出如田本相、朱栋霖、辛宪锡、曹树钧、孔庆升等一批曹禺研究的专家。研究的问题突破了原来单一的格局,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曹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对曹禺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对《雷雨》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
文化革命中断了一切学术研究,也停止了对《雷雨》的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以说是《雷雨》研究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在廓清“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影响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总体上说,还没有突破30年代周扬所建立的权威模式。研究者们都认为曹禺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雷雨》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18]是“社会问题剧”,把它的主题确定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并认为这是曹禺剧作的“一贯主题”[19]。这些研究实际是当时社会时代思潮的反映:文化革命以后,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强调反对封建家长制,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需要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
从中国话剧发展历史看,“曹禺以前的话剧,几乎毫无例外地把重点用来搬演故事,从曹禺开始才注重塑造人物”[20]。因此,对《雷雨》人物性格的把握与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就成了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钱谷融在60年代研究了周家的4个人后,于1979年又对鲁家的4个人——侍萍、四凤、大海、鲁贵进行了研究,将8篇文章合编为《〈雷雨〉人物谈》[21]。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研究《雷雨》的专著。专著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普遍的赞扬,其中的观点常被引用。对人物的研究虽然也难免要涉及到他的阶级属性,但这已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了。研究者不再是从抽象的阶级性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来分析人物。比如对周朴园,人们更多的是去探讨他与侍萍的感情纠葛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周朴园的“伪装”说是难以成立的。30多年来周朴园和侍萍的感情世界都经历了许多不如意,也就易使旧情长留心中,以致对现在的行动产生影响,所以这两人的感情纠葛是复杂的,“有情”与“无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又如对蘩漪的评价,有的学者就指出她既有旧传统的烙印,又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她渴望自由的爱情生活,但她的思想性格和环境使她以乱伦的方式去追求爱情,但“乱伦本身无疑是一种畸形的关系,而不是反封建的标志[22]”。
30年代以来,也因时代思潮的影响,人们更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学术界对《雷雨》的研究也就偏重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与人物形象的分析,对它的艺术成就涉及不多。这一时期,人们更加看重文学的审美功能,提出“将文学还给文学”的口号,因此,开拓了《雷雨》艺术研究的新领域。研究它的戏剧风格,剧作结构,语言成就等。孙庆升的《曹禺论》,田本相的《曹禺剧作论》,朱栋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华忱之的《曹禺剧作艺术探索》,辛宪锡的《曹禺的戏剧艺术》等专著均有不同程度的对《雷雨》的艺术性的研究。华忱之在其专著的第二章就专从艺术的角度对《雷雨》进行探索。专门对《雷雨》作艺术研究的论文也不少。朱栋霖认为曹禺是“用激情、凭直觉去感受生活”的,因此“产生了风格中突出的感情因素,使《雷雨》呈观出沉闷压抑而热烈激荡,表面平静而内在紧张的戏剧风格”[23]。辛宪锡指出追求“诗意”是曹禺的美学理想,《雷雨》就是一首诗。“它的诗一般的意境,是由‘雷雨’的气氛、‘雷雨’的性格、‘雷雨’般猛烈的冲突及其涤荡一切的结局所合成的。”[24]钱谷融指出,《雷雨》的情节线索有明暗两线,“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互相钳制,使得剧情万分的紧张曲折,引人入胜”[25]。对曹禺剧作精湛的语言艺术过去很少有人作专门研究。这个时期陈瘦竹、沈蔚德《曹禺剧作的语言艺术》[26]和钱谷融《曹禺语言艺术的成就》[27]作了专题研究。钱谷融认为“强烈的动作性,浓厚的抒情性和鲜明的个性化,以及以强烈的动作性为主的这三者的密切结合,构成了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总的特色”。在陈、沈2位的论文中还结合《雷雨》对这些特色进行具体的分析,使人们对《雷雨》的语言艺术有更深刻的理解。
80年代中期以后,《雷雨》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80年代初中国话剧界展开了“戏剧观”的讨论,有人提出要突破传统话剧主要依赖写实的手法,“借重写意手法”,强调主观情意的抒写。在这场话剧艺术革新的浪潮中,曹禺被重新发现,《雷雨》等剧作中长期被人忽视、批评的“非现实的”因素,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研究。8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兴起了方法热,人们也试图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视角来审视《雷雨》。这些都使《雷雨》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雷雨》中的“命运观”历来都被评论者视作消极因素加以批评的,但是青年作者新雨在《宇宙的永恒‘憧憬’——作为悲剧的〈雷雨〉及其命运观之探索》[28]中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角度。作者首先肯定“命运观对于《雷雨》具有一种质的限定性”,“它渗透了整个剧作”,而“命运观不同于宿命论”,“《雷雨》的命运观表现了一种积极抗争的激越之情,而不是匍伏于‘命运’之下的诚惶诚恐和消极顺从”。作者还认为“《雷雨》正是由于命运观才使它超出一般社会问题剧而获得一种具有哲理性的深沉意蕴”。文章还联系序幕和尾声进行考察,认为它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永恒‘憧憬’”。这篇论文的有些观点还可以商榷,但论者力图摆脱社会效果的论证模式,而从剧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出发进行探索,无疑是《雷雨》研究的新途径。
新时期曹禺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从宗教文化的影响来考察曹禺的剧作。曹禺从小就接触过基督教文化,大学时代又反复研究过《圣经》和《圣经》文学。这些是否对曹禺的创作产生影响,过去没有人涉足此领域。80年代后期宋剑华写了一系列论文用基督教文化来阐释曹禺的创作。在《试论〈雷雨〉的基督教色彩》[29]中,宋剑华指出,曹禺在创作《雷雨》时感到宇宙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使他感到迷惘,于是“试图从宗教中去寻求大千世界的真蒂”。论文从结构模式、中心人物、环境布局3个方面来探讨基督教对《雷雨》的浸透影响。论者把《雷雨》中的人物关系绘制成一幅矛盾关系网络图,从中提取出22对矛盾。他认为对这些矛盾只能用“基督教的‘原罪’与‘报应’思想对《雷雨》整体构思的影响”“才能科学地解开《雷雨》之谜”。曹禺设计乱伦这一中心情节就是依据《圣经》中的戒语:犯了“与继母行淫”“与姐妹行淫”罪,“上帝”要用最残忍的灭族手段施行严厉的制裁。从中心人物周朴园发展轨迹来看是“人性战胜了兽性,灵魂也由‘邪恶’走向‘忏悔’。他的性格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序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忏悔意识”。从《雷雨》的环境布局看,作品借助“雷雨”、“教堂”、“巴赫的宗教音乐”等等使基督教的色彩直接外现出来。因此,论者指出《雷雨》的客观效果是:“弱小者的悲剧,能唤起强暴者的忏悔意识,使人间充满‘和谐’与‘仁爱’”。这种愿望当然是幼稚的。《雷雨》虽然浸透着基督教色彩,但它仍是一件不朽的艺术作品。曾广灿、许正林也撰文论述了《雷雨》的基督教意识。他们也论述了《雷雨》的“原罪情结”和“神秘性”,同时突出地论述了《雷雨》中的忏悔意识。他们指出“《雷雨》序幕让周朴园走进教堂,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就好像是周朴园深蕴内心的长长的忏悔祷文”[30],对序幕和尾声作出了新的解读。
对曹禺的比较研究早在30年代就有了。《雷雨》发表不久,郭沫若、刘西渭、栾星等人的评论中就指出它受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响。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模仿乃至抄袭外国剧作,忽视了曹禺的独创性。这种研究后来中断了。到了改革开放年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比较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80年代以来对曹禺的比较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这一领域作出贡献的有:陈瘦竹、朱栋霖、周音、金延泽、潘克明、刘珏、王文英、焦尚志等人。这时人们不是把曹禺的作品与外国戏剧作简单的类比,而是着重总结曹禺借鉴外国戏剧的经验。正如陈瘦竹所说,曹禺“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31]。朱栋霖在《曹禺——自我突破中的完成》[32]中指出“《雷雨》的‘回溯式’戏剧结构,主要得力于易卜生戏剧与古希脂悲剧”。但曹禺却有所创新。易卜生的《群鬼》以成功地揭示过去的戏剧动作著称,而“现在”的人物关系没有多大变化。“而《雷雨》以表现‘现在的戏剧’为主,将‘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紧密结合起来,用前者不断来推动后者的急剧发展,从而把戏剧的几组重要冲突交织重合到一起,‘现在的戏剧’被激发得炽热火爆,难解难分,急剧奔向最后高潮”。
在比较研究中,论者除了把曹禺与外国剧作家进行比较外,还注意到与我国同时代剧作家进行比较。韩日新把曹禺与夏衍的剧作进行一番比较[33],胡润森将曹禺和郭沫若的剧作风格作比较[34],通过比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曹禺的创作特色。就《雷雨》而言,有的把它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作比较[35],有的把它与老舍的《茶馆》作比较[36]。这种比较有助于对《雷雨》艺术结构的探讨。
近年来,一些学者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研究《雷雨》,为《雷雨》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孔庆东的《从〈雷雨〉演出史看〈雷雨〉》[37]。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作品的本质是“建立在从它不断与大众对话产生的效果上”。“作为一部话剧,它的接受史毫无疑问要以它的演出史为主”,而“研究一部话剧的接受史,无疑应该把导演、演员、观众做为主要的客体”。因此,孔庆东从1935年4月《雷雨》在东京首次演出到1989年北京人艺第4次排演《雷雨》这50多年演出史中“架设了十几处观测点”,考察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雷雨》演出时导演、演员对它的不同理解、不同的处理。最后,论者将《雷雨》的演出归纳为几种类型:1.作者“原意”型,即试图按作者原意(有序幕和尾声)演出;2.“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型(这两种演出都不受欢迎);3.“唯艺术”型;4.“反封建”型(这两种类型能受到中国观众的喜欢);5.人物“共性”型,即1989年北京人艺的演出(“强调出各个角色共同的痛苦、共同的良心和共同的劣根性。淡化了人物的社会身份和道德评价”,表现人物“灵魂上的自我搏斗”。论者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孔庆东对大量史料的述评,向人们展示了《雷雨》强大的艺术生命力,预示这种生命的运动还会“继续延伸下去”。随后孔庆东的导师钱理群建立了“作家—作品—读者(包括研究者)”的三维研究空间,从作品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统一与运动中去把握曹禺的作品。钱理群的专著《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38]把曹禺剧作放在更广阔的接受背景(演出过程和研究过程)中去研究,为曹禺研究开创了新局面。王卫平则从接受过程中常出现的“误读”现象切入对曹禺的3部戏剧进行研究。他指出曹禺创作《雷雨》的本意与观众接受意的背离:“曹禺原本要表现的是整个宇宙的残忍和冷酷,所有的人都难以摆脱痛苦和不幸,而观众却觉得《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是反封建;曹禺在《雷雨》中探讨的是自然中人的命运,人的悲剧,观众却认为《雷雨》象征了资产阶级的崩溃,说明了资产阶级不会有好的命运”。产生误解的原因,论者认为一是“剧作家所要表现的精神世界与导演、观众的接受期待视界的分离”,二是“作者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分离”,三是“时代、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39]。
在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曹禺剧作的还有胡润森的《论曹禺悲剧情节的分布程序与时间——因果联系》[40]。该文根据俄苏形式主义者的情节理论探讨了曹禺悲剧情节分布的规律特征,认为“《雷雨》是对称式情节分布程序的范式”。《雷雨》通过序幕和尾声既“造成欣赏的距离”,又呈现出“哀静”的情境,“中和缓解了主体情节阶梯式上升的过分惨烈火爆,实现了以动静张驰的对比对称与相反相成为特征的充满张力感的美的均衡”,因此,论者否定了删掉了序幕和尾声的《雷雨》修改本,认为这样“使原著富于弹性的美的张力态白白地失去了”。
6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人们对《雷雨》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是,《雷雨》是一个非常丰富深刻的世界,正如一位学者说的,对它任何一种新的解释,都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角度,不可能是对它认识的穷尽。对《雷雨》的认识过程还将不断地持续下去。
注释:
[1]《杂文(质文)》创刊号,1935年5月。
[2]《东流》第2卷第4期,1936年4月东京出版。
[3]天津《大公报》1935年8月31日。
[4]《光明》1936年6月创刊号。
[5]信载《杂文(质文)》2月号,1935年7月。
[6]《光明》1937年2月第2卷第5期。
[7]《光明》1937年3月第2卷第8期。
[8]《青年文艺》1944年9月第1卷第4期。
[9]《抗战文艺》1944年9月、12月第9卷3~4期合刊,5~6期合刊。
[10]严格说来,在文学史中评介《雷雨》王瑶还不是首次,1938年12月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戏剧史》(徐慕云著)就对《雷雨》有了评介。
[11]甘竞、徐刚《也谈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兼论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处女地》1958年第2期。
[12]刘正强《曹禺的世界观和创作——兼评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处女地》1958年第6期。
[13]建领、君圭《对〈雷雨〉讨论中的几点意见》,《处女地》1958年第4期。
[14]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研究了周朴园、蘩漪,写于1959年,发表于1962年第1期《文学评论》,1979年又陆续写了几篇,汇编为《〈雷雨〉人物谈》一书,1980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5]王永敬《读《〈雷雨〉人物谈》后的异议》,《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王一纲、张履岳《周朴园的“深情缱绻”——评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上海文学》1963年第8期。
[16]《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17]《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18]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19]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
[20]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21]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
[22]晏学《蘩漪与周萍》、《戏剧论丛》1981年第3期。
[23]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
[24]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25]《曹禺和他的剧作》,载《〈雷雨〉人物谈》。
[26]《钟山文艺丛刊》1978年第2期。
[27]《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2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2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
[30]《曹禺早期剧作的基督教意识》,《文史哲》1993年第1期。
[31]《世界声誉和民族特点——谈曹禺剧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32]载《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33]《三、四十年代曹禺和夏衍的剧作比较》,《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34]《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中州学刊》1987年第5期。
[35]江震龙《〈雷雨〉与〈法西斯细菌〉结构艺术比较》,《福建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36]宇丹《〈雷雨〉和〈茶馆〉的不同结构模式:兼论电影改编》《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
[37]《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38]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39]王卫平《接受与变形——曹禺剧作的主观追求与观众的客观接受》,《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40]《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