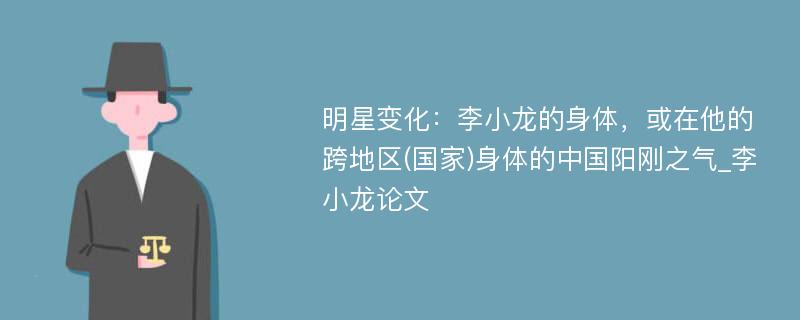
明星变迁:李小龙的身体,或者跨区(国)身躯中的华人男性气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躯论文,气质论文,男性论文,身体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1-0094-11
李小龙的明星形象传遍世界银幕,如此举世瞩目是因为他惊鸿一瞥的成功。仅仅才拍完四部功夫片。李小龙就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年仅三十三岁的时候意外逝世,从一个国际新星变成一颗耀眼的流星。他出生于美国,从香港演艺界脱颖而出,在世界银幕上大放光彩,但是,当他刚刚成为第一个世界级的华人电影明星时,就突然陨落了。在此后的岁月里,不少长相酷似李小龙的人努力尝试填补这个空白,却终归于失败:他们只是再次成功地强调了李小龙独一无二的超凡魅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李小龙在电影中所钟爱的身体展示。衣服脱到腰间、强健而充满愤怒力量的肌肉、时刻准备出击的袒胸的李小龙形象经常出现在书、DVD的封面以及影迷网站的页面上。
人人喜欢李小龙的身体,或者似乎如此,但是喜欢的理由却不尽相同。李小龙的身体是一种跨区(国)的身躯,这种身躯是由李小龙在美国和香港的个人经历以及瞄准李小龙电影的各种跨区(国)市场对他的影片的具体接受情况所共同塑造的。如果说为了追求最大利润,所有的大众文化产品都欢迎阐释的话①,那么,这种具有多种阐释可能性的跨区(国)文化产品就更应该这样了。李小龙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赢得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斗争的武器进行展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亚洲或者第三世界受压迫者的胜利;李小龙的身体展示也已经被放在不同的男性气质模式和不同的理想化的身体理念中进行理解,当然,每一种模式和理念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最后,李小龙的身体展示还引出了酷儿式的解读,这种酷儿式的解读已经和理解李小龙身体的其他方式和途径交织起来,有时令人愤怒,有时则被女性主义或者支持同性恋的目标所利用。
对李小龙所作的各种不同的阐释,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都根据当时当地的境况得到了发展,它们都是植根于具体环境的。一些评论家非常清楚前人的相关评论,但是,总的说来,每一种分析话语都是相对独立地进行的。从被压迫者角度出发的种种阐释很少体现关于男性气质的话题,并且,尽管有关男性气质的讨论应该承认是李小龙所象征的被压迫者的胜利,但是它们很少将这种胜利与李小龙所发展的男性气质类型联系起来。本文试图说明:李小龙的身体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跨区(国)的身躯(体格),而且可以把关于李小龙身体的各种阐释理解为一种跨区(国)的体系(framework)。在这个跨区(国)的体系中,有两种情况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作为被压迫者的胜利的叙述,它的载体也是一个华人;第二,这个华人所体现的特别的男性气质将情欲化的男性身体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跨区(国)的体系上(transnational framework),使我可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我曾经随便地提到:当其他所有的人都喜欢李小龙的身体时,我感到更加困惑。在对李小龙的明星身体的星际运动(stellar transit)更加仔细地观察之后,另一个总体说来并不醒目的“小行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回顾李小龙所走过的足迹,他在由美国现代性所主导的跨区(国)体系和后殖民体系中对华人男性气质的改造,揭示了李小龙作为中国男性气质的典范在获得成功时所付出的特殊代价。由此,我认为,李小龙的身体是极度痛苦的身体,陷入了双重强迫性的束缚之中:一方面不得不回应现代美国男性气质的挑战;另一方面不得不克服(作为这种回应能力的前提条件的)既厌恶同性恋又带有种族色彩的自我厌恶(心理)。
一、被压迫者的胜利
李小龙作为第一位世界级的华人影星的重大成就,仅仅是由他生前作为成年人所拍摄的四部影片所奠定的。在李小龙的传奇中,这种巨大的成就被叙述为被压迫者的胜利和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②。李小龙1940年出生于美国,在香港长大;50年代,他是香港的电影童星;十八岁时回到美国,并且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在美国的电视中获得了一些成绩③,直到在争取扮演《功夫》里的凯恩角色的竞争中,意外地输给高加索白人演员大卫·卡拉丁。美国的武打明星查克·诺里斯据说是这样评价的:“卡拉丁的功夫就和我的表演一样好。”④ 回到香港以后,李小龙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在1971年的故事片《唐山大兄》中露面。该片打破了香港的电影票房纪录。1972年,他接着主演了《精武门》,该片再次刷新了香港的票房纪录。为此,李小龙得以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并为该公司自编自导了《猛龙过江》。1973年,他为华纳兄弟公司拍摄了詹姆斯·邦德风格的影片《龙争虎斗》。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李小龙却死于神秘的脑肿疡。李小龙的第五部影片《死亡游戏》,是后人根据李小龙生前拍摄的部分场景,再加上一些(他死后)利用替身拍摄的新素材拼接而成的。
每一部电影都是“被压迫者的胜利”这一主题的变奏。在《唐山大兄》中,李小龙(郑潮安)是一个中国移民,在泰国的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做工。尽管母亲叮嘱他不要和别人打架,但是在工友接二连三地失踪和死亡之后,他还是被迫起来反抗。出于对李小龙(郑潮安)的武艺的赏识,工厂老板提拔他当了工头。但是,当李小龙(郑潮安)发现自己正在被利用,而且所谓的工厂实际上是一个从事毒品走私和卖淫活动的窝点时,他怒不可遏。影片结束的时候,李小龙杀死了可恶的老板,自己则被警察带走了。
《唐山大兄》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泰国的华人族群内部,所以它看起来更像是关于阶级和阶层的而不是关于民族和种族的电影。《精武门》是李小龙民族主义色彩最浓的作品,故事发生在1908年半殖民地的上海,根据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精武门的创始人霍元甲的死亡——为基础拍摄的。李小龙在影片中扮演霍元甲的徒弟陈真。当他发现是前来挑战的日本空手道馆害死了自己的师父之后,李小龙(陈真)通过一连串以牙还牙的杀人行为打破了师门关于禁止炫耀武力的禁令。日本空手道馆派人送来一块写有“东亚病夫”字样、用来污辱中国人的牌匾,向陈真挑衅。陈真只身来到空手道馆,砸了这块牌匾,并且在回精武馆的途中砸了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影片在李小龙与日本武馆请来的俄罗斯武术(空手道)冠军之间的打斗中达到高潮。当警察来抓捕李小龙的时候,他向警察和摄影机镜头飞去。影片在李小龙高高跃起的定格镜头中结束,我们只听到一阵李小龙特有的怒吼和警察嘭嘭嘭嘭的枪声。
正如托尼·雷恩思所指出的,《猛龙过江》把《唐山大兄》中的移民工人的主题与《精武门》中的竞争或者竞赛主题结合起来⑤。一个来自香港新界的乡巴佬,李小龙坐飞机到罗马去帮助他的堂姐,因为她的餐馆受到当地流氓的威胁。叔父告诫他不要打架,但是,李小龙没有听从叔父的劝告,而是教餐馆的服务生学会还击。当地的流氓请来了一位美国打手(由查克·诺里斯扮演)。影片意味深长地在罗马圆形大剧场的打斗场景中达到高潮。之后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后来才知道,他的叔父正在和当地的流氓秘密勾结。
这些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促使《龙争虎斗》得以问世,该片由罗伯特·克洛斯导演、华纳兄弟影业公司负责国际发行。模仿大名鼎鼎的《邦德》,李小龙装扮成人们熟悉的国际警察,去和一个非常富有且作恶多端的坏人战斗。李小龙的角色(李)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少林高手,他的对手是一个名叫韩的少林叛徒。李小龙和一个高加索白种美国人威廉姆斯(吉姆·凯利/Jim Kelly饰)以及一个非裔美国黑人澳哈拉(罗伯特·沃尔/Robert Wall饰)潜入韩的孤岛要塞,非裔美国黑人被杀害了,但是,李小龙和他的高加索白人同事一起捣毁了韩的孤岛要塞,并且将韩挫败。
在作品小小的篇幅内,范围广泛的族裔关系和民族归属感很难构成批评家们所谓的印有艺术家个人签名的创作整体。一种可能的例外就是打斗场景的编排与设计,这是李小龙集中参与的一个环节。大多数评论家都指出,李小龙对不需要弹簧垫、烟火和剪辑技巧帮助的真实打斗场景的支持与奉献,以及他自己创立的跆拳道风格⑥。但是,甚至就是这个问题,在导演方式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变奏。李小龙只是参与编剧和导演了一部电影,那就是《猛龙过江》。澄雨指出,《唐山大兄》和《精武门》的导演“罗维喜欢用蒙太奇,用剪接来拍摄打斗场面。更喜欢特写对手中拳或被踢中的场面。他的镜头是主观的,常出现李小龙面对镜头连踢三脚或连打数拳的画面,但在《猛龙过江》中,李小龙却喜欢用中镜和长镜,李小龙和对手不是站在镜头的左右两边,就是九十度的互相对峙”⑦。对于《龙争虎斗》,托尼·雷恩思并不是惟一的一个贬低导演罗伯特·克洛斯的人。他指出:“他没有能够理解拍摄武术动作电影的基本规律——那就是,如果演员的运动将会构成电影剧情的动力的话,那就必须展示主演者的整个表演过程。”⑧
这种变化延伸到影片叙事的同时,也延伸到影片的导演风格中,观众如果想要“弄懂”李小龙所代表或主张的意思的话,就不得不对这些变化进行选择性的解码。理解李小龙是被压迫者的胜利,通常流行的有四种主要的、而且常常相互重叠的可能性,它们要么表现香港的胜利、“漂泊”的华人的胜利、第三世界的胜利,要么表现为亚裔美国人的胜利。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把意义归功于李小龙的功夫,对打斗风格的形式主义的审美也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在考虑到《精武门》和《猛龙过江》中李小龙所面对的高加索白人对手时,张建德(Stephen Teo)对这种研究方式提出了正当的质疑⑨。
很多人认为李小龙代表的是香港身份,他们的根据是李小龙在香港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并且在去美国之前曾经是香港电影童星。但是,罗贵祥(Lo Kwai-Cheung)对这种观点的反应是,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而言,李小龙并不意味着一个清晰的香港身份。不仅因为李小龙很长一段时间都呆在美国、持有美国护照,而且因为他一般都是以华人的身份、而不是特别地以香港人的身份出现在他的影片中(《猛龙过江》除外);另外,李小龙电影中说的都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话,而不是香港常用的广东方言(粤语)。这种香港特征的缺乏,使得一些评论家将李小龙的胜利看成是华人移民社群自豪感的一种隐喻。朱英淇(音译,Chu Yingchi)是这样说的:“没有别的任何一位香港明星能够像李小龙这样清楚地表达移民意识。他那三部最著名的影片……表现的是居住在由外国人统治和控制的地方的华人故事。”⑩ 张建德采取一种相似的视角,将李小龙的“事业”看作是“文化民族主义”,一种以族裔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形式,含蓄地区别于以政权/国家为基础的国家民族主义,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是有所区别的(11)。但是,罗贵祥对这同一种特征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他相信香港的居民会认同于李小龙电影中的中国想象,正是因为“李小龙的身体不能为确定一个‘香港’本质或概念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罗贵祥在这种不明确的身份认同与香港自身在告别英国的殖民地位、融入中国大陆社会的过程中的精神面貌之间看到一种异体同形的东西(12)。
同样,民族/国家具体特性的缺乏,成为从第三世界的角度读解李小龙的基础。焦雄屏(Chiao Hsiung-Ping)曾经指出,李小龙的反西方侵略“不仅对于中国人是适合的,而且对于所有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屈辱的人(南美人、阿拉伯人和东方人)都是适合的”(13)。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ad)不仅记得在印度观看《龙争虎斗》的情形,而且将它与《邦德》进行了如下的比较:“詹姆斯·邦德是英国国际刑警(MI-5)中堕落名单里的代表,而李小龙却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堕落行为……利用他的赤手空拳和双节棍,李小龙给年轻人带来这样的意识和观念:我们终究会胜利,就像越南游击队员一样,抗击着国际资本主义的毒素。”维杰·普拉萨德认为,李小龙是在与(他在其他文章中)称之为“穿着黑色宽松裤的军队”(黑社会)进行战斗。为了做出这样的阐释,维杰·普拉萨德不得不忽略一个极其不便的事实,即在《龙争虎斗》中李小龙本人也是一个国际刑警(MI-5)的代理人(14)。另外,很多华人移民观众对共产主义所怀有的恐惧心理,压制了任何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李小龙形象。
在李小龙电影发行的当时,普拉萨德深情回忆的那种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正如他详细介绍的,在美国是与少数族裔的政治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大卫·德塞(David Desser)曾经追溯过李小龙的电影在非裔美国观众中大受欢迎的原因(15),以及非高加索白人观众对于后来进入美国电影市场的香港动作明星比如成龙和李连杰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与他们合作的美国演员的族裔身份上面,例如,与他们合作的那些演员往往都不是白人(16)。但是,正如詹·雅金森(音译,Jachinson Chan)所指出的,如果在香港,对于李小龙是否能够算是地道的本地人这个问题都还犹豫不决的话,那么在美国,李小龙作为亚裔美国人的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17)。也许,在这种环境下,关于亚裔美国文化的著作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到李小龙,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吃惊的了。除了詹·雅金森的著作之外,惟一重要的例外就是马圣美(Ma Sheng-mei)的著作。她将李小龙的民族主义看作是更加广泛的中国和亚洲现象的一部分,包括亚裔美国文化(18)。但是詹·雅金森将李小龙当作亚裔美国人表现中的一个突破,因为之前的亚裔华人在美国电影中都是一些女性化的形象,比如付满洲(Fu Manchu)和陈查理(Charlie Chan)。
二、对抗性的男性气质
作为关于亚裔美国人男性气质的专题著作的一部分,詹·雅金森对于李小龙的讨论,既分析了对于被压迫者的胜利的叙述,又分析了李小龙的男性气质,这是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中比较独特的。绝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没有能够将被压迫者的胜利和李小龙所展示的那种男性气质联系起来思考。甚至在詹·雅金森的著作中,男性气质也是单独存在的,并没有关于男性气质的不同存在方式的讨论。也许,这正是为什么其他作者不讨论李小龙所体现的那种男性气质的原因;也许这样再“自然”不过了:只有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才能够象征人们在他的叙述中看到的那种属于大家所有的“重新授权”(communal re-empowerment),“男性气质”只有一种形式。
例如,罗贵祥在提到马修·图勒(Matthew Turner)的关于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向“现代西方的健康、仪态和心理模式”转向的研究时,加上了这样的话:“西方的健身/健美运动与中国功夫无与伦比的结合(詹姆斯·邦德的空手道与中国大陆的轻功/飞行动作相互渗透),在李小龙的形象中得到完美的展现……”(19) 这是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观察,它指出了其他类型的华人男性气质与西方的肌肉型文化(muscle culture)之间的张力关系,但是罗贵祥没有沿着这条调查线索继续追问下去。同样的,伊冯·塔斯克尔(Yvonne Tasker)在她的关于中国武侠动作电影中的种族和男性气质的论文中,略微提到了不同的男性气质,她是这样评价的:“华人英雄常常为了群体、并且作为群体的一分子而战斗,但是,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英雄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孤立的形象(孤胆英雄)。”(20) 但是,伊冯·塔斯克尔在这里含蓄地将华人的群体意识和美国的个人主义当作一些固定不变的文化品质/特征,而不是作为处于动态争论中的不同形象,即在各种不同的但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到来而不断相互连接的空间中,一个真正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动态的争论中的不同形象。
雷金庆(Kam Louie)最近出版的关于华人男性气质的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他详细说明了两种长期存在的男性气质,这两种气质在华人社会都是根深蒂固的。“文”或者优雅的男性气质是以孔子和文人作为象征的,强调的是文化内涵而不是身体能力。文人气质对于女性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文人可能会与妇女嬉戏调情,但是到了最后总会放弃情欲的快感,以成全他的道德伦理义务;“武”或者尚武的男性气质是以关帝(吴宇森的很多电影中都供奉着他的塑像)以及居住在民间社会之外的神秘空间(江湖)中的武侠形象作为象征的,这些英雄人物强调身体的力量和技术。除非是酩酊大醉,他们完全避开女人。他们主要的承诺是针对他们的歃血为盟的兄弟的。尚武英雄的身体比文人书生的身体更加暴露,文人书生的身体往往被包裹在飘逸的袍子里面。但是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下,男性的身体都不是被情欲化的:尚武英雄的身体仅仅象征着他的武术力量(21)。事实上,“肌肉”一词直到19世纪从西方解剖学研究中被挪用过来之前,中国语言里并不存在这个概念(22)。早期中国文化中男性身体的这种特殊的“不可见性”,是与在与西方世界接触之前的中国艺术中更大范围内的“身体缺席”密切相关的(23)。
雷金庆指出:“李小龙的银幕角色具有忠诚、正直和义气三大品质,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尚武英雄。”他还指出:“就像传统叙事中的武侠英雄一样,即使(甚至)他周围的女人都渴望着他,李小龙的角色也不会像文人常常会做的那样去和那些美丽的女人柔情蜜意,他总是首先献身于他的社会责任和义务。”(24) 詹·雅金森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的男性气质,所以只是在美国男性气质的传统框架内阐释李小龙的行为。他说:“李小龙所塑造的形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长制的或者厌女症的人物。李小龙的各种角色既不压迫女性角色,也不表现出对詹姆斯·邦德式的夸张的异性行为的歧视。”(25) 但是,在尚武的男性气质传统中,李小龙的行为不是取悦女人的,而是非常家长制的、厌恶女性的(视红颜为祸水的)。他要么出于自己与她们的家庭之间的关系,将保护她们视为自己的责任;要么将她们当作分散注意力的危险物,然后置之不理。
这种阐释的差异也清楚地表明,亚裔美国人和传统华人对尚武英雄的不同期待之间具有潜在的张力关系。对詹·雅金森而言,李小龙令人失望地“塑造了西方文化替亚洲男子建构的无性欲角色,并且从来没有和片中的女性角色过过夜——这在詹姆斯·邦德影片中是不可思议的”(26)。但是,美国文化传统中体现男性成就的行为,在华人尚武的男性气质传统中,很可能就是一种失败的标志。(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要论述的范围,这些紧张关系仍然困扰着华人男性功夫明星进军跨区(国)市场的努力,李连杰和成龙他们对性活动的尴尬的处理恰好揭示了这些相互冲突的文化期待之间的困境。)
雷金庆既没有把这两种华人男性气质当作一成不变的气质,也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封闭的、不受世界其他文化影响的实体。他声称,国际性的成功将李小龙现象塑造为“华人尚武男性气质在国际舞台上的胜利”。但是,按照罗贵祥对于60年代香港健身/健美狂热风潮的评价,他也指出:“美国媒介对世界的统治意味着,很多美国影像和图像所表现的西方男性偶像在中国已经获得越来越普遍的接受”,并且承认,李小龙对自己身体的展示、连同关于他在银幕之外(私生活中)乱搞女人的谣言一道,共同违背了传统的尚武男性气质,因为这种展示“流露出很多性欲的元素”。因此,李小龙不仅意味着“对尚武男性气质的再度肯定”,而且意味着对这种男性气质的修正,“以便适应华人移民新的混杂的文化”(27)。
但是,雷金庆很可能低估了李小龙对于已经确立的尚武男性气质典范的背离。首先,对于情欲化的身体的展示就是对过去所有武术明星的令人震惊的背离。早期香港动作电影中英雄人物出场的时候,不仅穿着衣服,而且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完全不强调身体本身。这种情况不仅对于电影中的剑客是存在的,而且对于像李小龙本人这种首先以武术动作为基础的功夫影星也是一样的。比如,在50、60年代非常流行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中,扮演黄飞鸿的关德兴总是穿着黑色的长袍(28)。这种情况只是在张彻的电影中才开始改变。
尽管李小龙的自我身体展示在武术电影类型中曾经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健美的身体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标志,在中国电影中已经有了很长一段历史。早在30年代,黎莉莉就穿着泳装和运动衣出现在《体育皇后》(1936年)中;在《大路》(1935年)中,男性电影明星扮演的筑路工人也把衣服脱到腰间,被迫敞着胸膛、光着膀子替日本鬼子修路。这部电影描绘了一个著名的男性裸体场景,但是这种幽默的刺激在1949年之后消失了。身体展示仍然在新中国的电影中继续着,但是完全被限制在健康地、积极主动地参加国家建设的活动中。例如,在极度降低情欲化的运动类型电影《女篮5号》中,为国家篮球队打球就是一个将自己投身于国家建设的隐喻。
考虑到这段范围更广的历史,李小龙对华人尚武男性气质和美国男性气质的糅合,就不能被相互割裂地解读,而是要与对李小龙电影中被压迫者的胜利的叙述,所进行的各种民族主义的和反殖民主义的阐释结合起来解读。在李小龙通过他的电影和银幕形象为华人/亚洲/第三世界维护权益的同时,他也通过对男性气质的坚持来达到这一目的。
另外,在一个动态的华人语境中,李小龙也意味着这样一种选择:选择“尚武”的男性气质而不是文人的男性气质,来完成为华人/亚洲/第三世界维护权益的使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正如雷金庆所指出的,一般而言,人们对于“武”的评价不如对高雅的“文”高,“文”通过凌驾于扩张与暴力之上的道德伦理来强调对秩序和规则的服从,而扩张与暴力都是与“武”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李小龙电影中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就是,推翻墨守成规的“文”的必要性,因为“文”坚持反对使用武力。在《唐山大兄》中,李小龙的母亲曾经警告他不要打架,但是到了最后,为了追求正义,他不得不出手。在《精武门》中,精武门的师父在教徒弟时,都告诫他们要把武术当作一种强身健体的手段,但是李小龙不能让自己的师父白白地冤死在日本人手里。在《猛龙过江》中,王伯父告诉年轻的服务生,给敲诈他们的意大利流氓付钱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打架,但是事实证明,他已经被坏人收买了。
根据澄雨的观点,这种叙述模式是与“中国人对挑衅的忍耐力非常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这种性格是相一致的(29)。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释放自己的武力,但是《猛龙过江》也标志着对一般规则的重要背离,那就是,李小龙从美国传统中借鉴来的现代的、跨区(国)的“新武”男性气质。通常,“武”的暴力所造成的(即使是)合法的、道德的惩戒(破坏),也必须最终被消除,即使武力是用来恢复秩序的,也绝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李小龙在《唐山大兄》的结尾被逮捕、在《精武门》的结尾被华人租界警察射杀的原因。但是,在《猛龙过江》中,李小龙不是被逮捕或者被枪杀,而是与他的堂姐道别,让她继续和平地经营餐馆,自己则回到香港。这种情况在美国的西部片中有一个对应物:在挽救了她的生命和家园之后,遗憾地留下那个年轻的寡妇,牛仔骑着骏马朝着夕阳走去……在《龙争虎斗》中,李小龙更加全面地借鉴了美国枪战片中的男性气质套路,比如,他被(MI-5)雇佣来专门去抓坏人韩。
李小龙的“新武”男性气质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借鉴了美国的男性气质传统。李小龙不再委曲求全,不只是出现在因为愤怒至极、以典型的“武”的方式全力与敌人战斗的时候。这样的时刻还常常出现在李小龙脱掉衬衣、暴露出强健的上身的时候。不像其他所有的华人武术电影明星,李小龙尽情地展示他的强健的肌肉,就像50年代的“剑与凉鞋”(sword-and-sandal)电影明星曾经做过的那样(30),以及施瓦辛格和史泰龙在后来的电影中将要做的那样。另外,女性角色对李小龙的反应表明,李小龙的身体展示不仅是一种武器或者武力的展示,而且是一种情欲的契机。但是,李小龙的“新武”男性气质和美国男性气质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别,这还可以在《龙争虎斗》中看到。李小龙的两个同伴,无论是那个白人还是那个非裔黑人,他们都不会对在比武的前夜和韩送来的女人睡觉感到疑虑或者内疚——实际上,那个非裔美国黑人的角色是依照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纵欲过度的原型设计的。相反,李小龙拒绝了所有的这类诱惑,保持了“武”的核心价值,避免与女人搅在一起,以免她们伤了自己的元气或者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三、李小龙与酷儿身体
并不仅仅只有女性才对李小龙健硕的身体着迷。李小龙的身体在电影和批评性的著作中都被挪作酷儿的视觉愉悦(观看快感)之用。在《猛龙过江》中,魏平澳(Wei Pingao)再次扮演了《精武门》中的那个汉奸翻译。在《精武门》中,他为暗杀霍元甲的日本空手道馆卖命,这一次他却是为意大利的流氓服务。在《精武门》中,他表现了“东亚病夫”体质的羸弱和摇尾乞怜的嘴脸,但在《猛龙过江》中,他已经从男性气质阙无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娘娘腔的同性恋。他不仅穿着各种70年代约翰·艾尔顿风格的外套到处招摇,而且一点都不掩饰他对李小龙角色(唐龙)的诱惑。托尼·雷恩思提到了其中两个特定的场合,“让他抚摸李小龙(唐龙)的二头肌和胸大肌”。事实上,在第一次试图强迫李小龙为意大利流氓卖命的时候,魏平澳确实发现,当自己的手指摸过李小龙(唐龙)的(穿着衣服的)胸膛时,禁不住喃喃自语:“好结实的肌肉!”但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碰面则更能说明问题。在第一次试图恐吓餐馆的行动的最后,魏平澳第一次结结实实地撞到了正要出门的李小龙身上。刚开始他还有点恼怒,但是当他后退几步仔仔细细地把李小龙打量一番之后,他的语气变了。李小龙的衣服带子正在两腿之间晃来晃去,魏平澳伸手将带子抓起来塞进李小龙的裤腰里,柔情蜜意地对李小龙说:“看看你要做什么。”这个掩耳盗铃的动作无疑告诉人们,魏平澳希望李小龙像他那样做。
对李小龙身体的酷儿审美也体现在一些批评性的著作中。张建德固执地认为,他对李小龙所作的“文化民族主义”阐释才是惟一正确的阐释。对他而言,把李小龙与酷儿联系起来会糟蹋了李小龙对自己事业的忠诚:“这些批评家提到李小龙的‘自恋’,一个同性恋意象的代名词,仅仅只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李小龙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还指出,“一部分同性恋批评家”还把“《猛龙过江》里面,李小龙在自己的房间里练功时,通过镜子观看自己”的那个场景描述为“自我满足/自慰”。同时他还指出:“一位西方的批评家甚至到了引用李小龙妻子的话的程度,就是为了说明‘李小龙有一个没有完全下垂的睾丸’,以便证明他受到了自卑情结的折磨……导致他后来生活中的健身/健美、练武和自恋情绪。”(31)
实际上,以上所有的这些引文都来自同一个渠道——托尼·雷恩思(Tony Rayns)。暂时把张建德愤怒的问题放在一边,在雷恩思关于《猛龙过江》的讨论中,有一个有趣的契机症状性地泄露了他对影片的身心投入。雷恩思确实把这个练武的场景描述成“自慰过程中的自恋(因为这个过程牵涉到镜子)”,并且还说“观众通过李小龙角色(唐龙)的表姐的眼睛,带着窥淫癖的心理来观看这个场景,表姐是悄悄地溜进房间的”。雷恩思然后观察到:“在后来的场景中,观众的替身就是流氓团伙中那一个翻译,他在两个场合下,被命令抚摸李小龙的二头肌和胸大肌。”(32) 事实上,在李小龙(唐龙)的堂姐和魏平澳所扮演的角色霍先生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正如雷恩思所描述的,李小龙的表姐是在监视他,因此观众的视角就是表姐的视角,但是,在魏平澳羡慕李小龙的那两个场景中,观众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第三者的视角,因此没有视点镜头。换句话说,要在这个时刻如雷恩斯的滑移所暗示的那样,认同霍先生的同性恋愉悦,还需要一种旁观者性质的心理投射。
张建德针对托尼·雷恩思的讽刺性的愤怒,既揭示了酷儿理论对李小龙的挪用与将李小龙当作被压迫者的胜利的各种读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表明李小龙“新武”男性气质的跨区(国)的传播已经将他置于美国男性气质的世界中。首先,酷儿理论的挪用与被压迫者的阐释之间的张力关系,是视以下两种情况而定的:1.李小龙的身体展示是怎样被理解的;2.强调的是哪些具体的场景。在被压迫者的阐释中,李小龙在与敌人战斗之前极度愤怒时刻的身体展示,是作为超级身体武器展示来强调的。在同性恋的挪用中,瞪着镜子中自己裸露的胸膛,是作为男性与男性之间自恋的基础来强调的,这也是同性审美得以建立的基础。
在被压迫者阐释中,李小龙的身体是维护力量的工具;在同性恋挪用中,李小龙的身体是被欲望的对象。当然,李小龙可以被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阳刚的男性来渴望。事实上,阮黄晋(Tan Hoang Nguyen)的解释是这样的:李小龙的明星形象,为某个同性恋色情演员给自己起一个与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相同的名字、并且成为在同性爱行为中处于“男人”的位置而不是“女人”的位置的亚洲影星的故事提供了基础。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从观众认同的主体到被欲望的对象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另外,如果同性恋的观众也被想象成白人,就像托尼·雷恩思那样,那么,李小龙看起来是在为中国、第三世界以及亚裔美国人观众所保留的愉悦,就好像被他们象征性的压迫者所再次地加以挪用或者“偷窃”。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张建德以及其他一些人对于那些西方“形式主义的”阐释感到不满的原因,因为这些形式主义的阐释只是欣赏李小龙优雅的运动,但是完全抹煞了其中重获的授权的政治意义。
对于同性恋及其意义的焦虑,进一步揭示了李小龙的“新武”男性气质与美国男性气质的相互混杂、并且被置于全球化的美国男性气质之中的程度。同性恋恐惧症及其护理者的焦虑是全球化的美国男性气质内在的组成部分。但是,根据雷金庆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在与现代西方社会接触之前,这些既不是“文”的重要特征,也不是“武”的重要特征(33)。人们只能推测其中的原因。如果早期的“文”和“武”的男性气质提供了一种可供模仿的榜样,那么这种模仿就是建立在不同的机制之上的,而这些机制则与现代的美国男性气质密切相关。书面的和口头的叙事排除了凝视健硕肌体的可能性。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中的演员都是穿着衣服的。惟一的例外可能是杂技表演,但是杂技中叙事的缺席很可能限制了产生认同心理的可能性。相反,像电影或者印刷图片这一类的视觉媒介,则是鼓励认同美国的男性气质,以加强对健壮的身体进行展示的重要性。
在这些视觉环境中,作为动作主体的男性身体和作为欲望对象的男性身体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关系。像拍摄男性身体、展示胀鼓鼓的像装甲一样的肌肉或者将动作定格于这一类的技巧,被用来克制对象化过程中女性化所隐含的威胁以及根据现代男性气质规则看来,同性恋泛化带来的威胁(34)。但是,对于潜在的同性恋状况的焦虑,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现代的美国男性气质。不仅因为这种身体展示正在被动摇,而且因为这种男性气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获得另一个男子的认可。如果羡慕和尊重变成了渴望与欲望的基础,这种同性社交(homosocial)也可以轻易地掉进同性恋的怪圈,因此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应该予以严加注意(35)。
正如罗宾·伍德(Robin Wood)所指出的,动作电影可以被理解为这些张力关系得以解决的场所。在这把象征性的伞盖下面,男人之间的暴力转移和改造了欲望的威胁。当拳头打在对手的身上时,似乎就可以用同样的暴力将欲望的威胁赶出体外(36)。李小龙的“新武”男性气质带着这种同性恋厌恶症结构的全部力量,但是它被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进一步复杂化和具体化了。正如常常被提及的,在李小龙的对手中,还存在一个种族间的等级制度。对付别的中国人或者日本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简单的开头),高潮的检验往往是一个高加索白人对手,就像《精武门》中日本人雇佣的俄国冠军(佩特洛夫/Petrov),或者《猛龙过江》中意大利流氓请来的查克·诺里斯(科尔特/Colt)。
另外,在李小龙的一些电影中,李小龙对付不同对手时的方式具有显著的差别。面对亚洲的对手,他总是很轻蔑地就将其击溃;相反,对付高加索的白人对手,则需要严阵以待。在《猛龙过江》里罗马圆形竞技场那个场景中,李小龙直到最后才击败了查克·诺里斯,甚至对诺里斯的处理还很尊重。澄宇指出,李小龙避免“他常用的喊叫、装怪相或者嘲笑对手等战术”(37)。对澄雨而言,这标志着朝向写实主义的发展,但是在维杰·普拉萨德看来,这种格斗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与走向繁荣的红色东方之间的战争”(38)。另一方面,对于马圣美而言,坐飞机到罗马并且在圆形竞技场打败敌人,是对在抗拒殖民价值的同时又服从殖民价值这种双重意识的经典表现形式(39)。托尼·雷恩思从这个场景得出的结论(与张建德对他的评价——对民族主义拒不承认——完全相反)是,“《猛龙过江》……构成一种进取性的身份主张,既是通过武术实现的作为个人的身份,也是作为华人的民族自豪”。但是,在张建德看作同性恋代名词的“自恋”的标题下,托尼·雷恩思也写道:“这整个段落都被放在战斗双方相互尊重对手的武艺的基础之上……李小龙杀死了对手,但是在精神上非常尊重他。在杀死对手后,李小龙将对手的外衣和黑色腰带盖住他的尸体,然后默默地跪在旁边。”(40)
李小龙(唐龙)必须战胜查克·诺里斯的必要与李小龙(唐龙)对诺里斯的尊重之间的张力关系,这再次证明了马圣美对于“双重意识”的观察。它同时也表明,李小龙是多么渴望从美国对手那里获得承认。在一个隐喻的层面上,它也泄露了由李小龙所象征的重塑男性气质的反殖民主义政治主张内部的张力关系(41)。如果李小龙的明星形象印证了华人男子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获取胜利的能力,那么,他也同时印证了华人男子对现代美国男性气质的承认。这种张力关系与同性性欲(homosexuality)和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了共鸣,而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正是塞吉维克在现代美国男性气质的核心价值中强调的。
另外,圆形竞技场中钦佩性的同性社交与魏平澳的角色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这些完全被蔑视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具有作为对手的地位。结果,在其他作者的讨论中,他们甚至不能在李小龙对手的等级体系中的最低级别里占有一席之地。在《精武门》中,李小龙第一次报仇杀死的人,是谋害李小龙师父的两条走狗: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华人。他们在一个简短的打斗场景中就被打发掉了,李小龙愤怒的拳头像狂风暴雨一样倾泻在他们的肚子上,第二天,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挂在路灯杆上。魏平澳扮演的汉奸翻译是下一个被除掉的对象,但似乎不值得为他安排一个用来除掉刺客的真实的打斗场景。一天晚上,李小龙乔装打扮成魏平澳雇佣的黄包车的车夫,将他拉到一个黑灯瞎火的小巷子。李小龙连人带车将魏平澳掀翻在地。李小龙的目的是要让他交代,到底是谁指使人暗杀了自己的师父。魏平澳早就被吓成一滩烂泥,对于他的外国主子也没有半点忠诚可言,马上就告诉李小龙,是日本空手道馆的铃木指使人暗杀了精武门的师父。他不停地讨饶说,他只是“按照别人的命令办事”。但是,当李小龙转过身去时,他抓起一块砖头就砸向李小龙。李小龙愤怒地转过身来……但是,影片并不认为值得向我们展示除掉这个卑鄙小人的实际过程。影片直接切到第二天早晨,魏平澳的尸体也被挂在路灯杆上。在《猛龙过江》里面,李小龙甚至不愿意屈尊俯就地碰霍一个指头。更有甚者,在圆形竞技场那个场景之后,当霍跑到唐伯父那里去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时,他的意大利老板也开车追来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意大利人杀死了。换句话说,他完全被当作一个“马后炮”。
李小龙虽然在圆形竞技场杀死查克·诺里斯,却对他充满敬意;同时,却把魏平澳所扮演的角色当作害人虫来处理。这两种态度之间的鲜明对比发人深思。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在李小龙“新武”男性气质的秩序中,曾经用来标志优雅的文人气质的修长身体,现在被用来指代“软弱性”、甚至“东亚病夫”?在“新武”的秩序中,曾经将“文”的优雅与教育结合起来表示智慧以及明显优于单纯体力的脑力的文质彬彬的身体,连同懦弱和背信弃义捆在一起,被用来指称失败的华人男性气质、脂粉气的男子、甚至男同性恋者。在《猛龙过江》中,霍是李小龙的同性渴望者,但是詹·雅金森对李小龙针对霍的表现非常乐观。他将李小龙对于霍引诱所做出的禁欲主义的反应,与精力充沛的美国英雄可能会采取的反同性恋的暴力行为相比,应该是一种容忍的态度。但是,“新武”思想之内的总体处理、以及魏平澳在《精武门》和《猛龙过江》中扮演的角色的命运,都将李小龙的表现界定为:不值得对他们采取暴力的回应。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交换机制和翻译机制在起作用。阮黄晋注意到,在同性恋色情明星李国豪的形象(Brandon Lee/李国豪,此李国豪并非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只是借用李国豪的名字)的如意算盘中,他相对被同化的美国特征与他经常搭档的移民和底层人物的亚洲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可能是以李小龙的“新武”男性气质作为原型的、范围更广的形象模式的一个子集。通过借鉴现代的美国男性气质的元素,李小龙给“武”带来了新的活力,在抛弃旧式华人男性气质的许多落后因素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力量。这样,李小龙银幕形象的轨迹与拉康式主体的经典产生过程极其相似,通过一个征服/服从的过程,某个人(自我)凭借对父权制度的回归,获得了承认并被赐予主体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女里女气的男子”或者“同性恋的男子”作为自我内部令人讨厌的成分被生产出来,而且被压制或者象征性地被消灭。但是,在李小龙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在“新武”男性气质的生产中,在殖民性与男性气质的交叉区域,把“脂粉气的男人”或者“女兮兮的男人”标定为华人,把值得渴望和效仿的榜样标定为白人。在李小龙其他方面完全不具有讽刺意义的银幕形象中,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要以克服所有的差距并且打败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但是,这只有通过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实现。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中,我只好回到米甘·莫瑞斯(Meaghan Morris)将李小龙作为教师的讨论中来结束本文。她讨论了关于李小龙的电影中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影片表现的是:李小龙和他的妻子琳达·艾米莉(Linda Emery)正准备一起去看电影,他们观看的影片是《蒂凡尼的早餐》;当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可能是非常幽默的角色(Mr.Yunioshi)出现在银幕上时,观众都哈哈大笑,琳达开始也笑了,但是当她注意到李小龙冷漠的表情时,才不笑了。莫瑞斯关心的问题是:琳达是怎样学会跨越文化鸿沟并最终和李小龙走到一起(结婚)的(42)。在观看李小龙电影时,我个人也有相似的不舒服的感觉。在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不禁注意到,李小龙“新武”男性气质中具有的同性恋恐惧症的特殊的种族化结构。将女性化的男人与中国划上等号,和将理想的男性气质与美国划上等号,不仅是具有同性恋恐惧症的,而且在华人重新树立阳刚之气的过程中刻下了自我厌恶的痕迹。
注释:
①John Fiske," Television:Polysemy and Popular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No.3 ( 1986) ,pp.391-408.
②关于李小龙的书籍和网站非常多,我在本文中主要利用的是Little的材料。该书是与李小龙的遗孀合作撰写的,它并没有沉溺于围绕李小龙死于台湾女星床上这件事所引发的各种谣传,这些谣传在那些“没有授权的”说法中随便可以找到。较早的传记包括Lee Thomas和Clouse。
③早期在美国电视上播出的《青蜂侠》中,李小龙饰演老是戴着面具的配角。见Darrell Y.Hamamoto,Monitored Peril:Asi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TV Represent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p.59-63; Ma Sheng-mei,The Deathly Embrace:Orientalism and Asian American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p.60-61.诺里斯在这里是开玩笑的,因为他显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④Richard Meyers,Amy Harlib and Karen Palmer,From Bruce Lee to the Ninjas:Martial Arts Movies,New York:Carol Publishing Group,1991,p.221.
⑤Tony Rayns," Bruce Lee and Other Stories" ,in A Study of Hong Kong Cinema in the Seventies,Li Cheukto( ed) ,Hong Kong:Urban Council,1984,pp.26-29.
⑥举例,Chiao Hsiung-Ping," Bruce Lee:His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Kung Fu Genre."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9,No.1 (1984),pp.30-42.焦雄屏认为,李小龙的舞蹈艺术般的风格,不仅可以放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来理解,而且可以同时理解为与强调吊走钢丝、以及其他特技手段的中国式奇幻风格相对照的西化套路。事实上,这种奇幻风格一直是剑侠电影中的主流,后来才被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所取代。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很多早期的功夫电影,比如著名的“黄飞鸿”系列电影的打斗场面,也相对而言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
⑦(29)(37)澄雨:《李小龙:神话还原》,李焯桃编《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香港:市政局,1984年版,第21页,第24页,第25页。
⑧(40)Tony Rayns," Bruce Lee:Narcissism and Nationalism" ,in A Study of the Hong Kong Martial Arts Film:The 4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April 3-18,1980,City Hall,Lau Shing-Hon ( ed.) ,Hong Kong:The Urban Council,1980,pp.110-112,p.112.
⑨Stephen Teo," True Way of the Dragon:The Films of Bruce Lee" ,in Overseas Chinese Figures in Cinema:The 16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10.4.92-25.4.92,Law Kar (ed.),Hong Kong:The Urban Council,1992,pp.70-80.从形式主义到影迷崇拜,西方对武术电影出于利己考虑的读解,往往忽视殖民与后殖民的动力关系、因此不断地重复殖民动力,这样的引语资源多得不可胜数。
⑩Chu Yingchi,Hong Kong Cinema:Coloniser,Motherland,and Self,London:Routledge,2003,p.38.
(11)Stephen Teo," Bruce Lee:Narcissus and the Little Dragon," in Hong Kong Cinema: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p.110-121.
(12)(19)Lo Kwai-cheung," Muscles and Subjectivity:A Short History of the Masculine Body in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in Camera Obscura,No.39 ( 1996) ,p.111,pp.106-107.
(13)同注释6,p.37.
(14)(38)Vijay Prashad," Bruce Lee and the Anti-imperialism of Kung Fu:A Polycultural Adventure," in 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al Critique 11,No.1 ( 2003) ,pp.54-64,p.63.
(15)David Desser," The Kung Fu Craze:Hong Kong Cinema' s First American Reception," in The Cinema of Hong Kong:History,Arts,Identity,Poshek Fu and David Desser( e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9-43.
(16)举例:Gina Marchetti," Jackie Chan and the Black Connection," in Keyframes: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Matthew Tinkcom and Amy Villarejo ( eds.) ,New York:Routledge,2001,pp.137-158.
(17)(25)(26)Jachinson Chan,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New York:Routledge,2001,p.75,p.77,p.89.
(18)同注释3,pp.54-55.
(20)Yvonne Tasker," Fists of Fury:Discourses of Race and Masculinity in the Martial Arts Cinema," in Race and the Subject of Masculinities,Harry Stecopoulos and Michael Uebel ( ed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316.
(21)(24)(27)Kam Louie,Theorizing Chinese Masculinity: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22,p.145,p.147,p.148、p.13,pp.147-148.
(22)Larissa Heinrich," The Pathological Body:Science,Race,and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1770-1930" ,Ph.D.diss,p.123.
(23)John Hay," The Body Invisible in Chinese Art? " in Body,Subject & Power in China,Angela Zito and Tani E.Barlow ( ed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42-77.
(28)关于《黄飞鸿》系列影集的论述,见Hector Rodriguez,"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as an Interpretive Arena:the Huang Feihong Series," in Screen38,No.1 (1997),pp.1-24.
(30)译者注,原意指古罗马的着装风格,后来指代古装剧的一种亚类型,其内容多取材自《圣经》以及神话传说。本文中所指为意大利西部片流行前在意大利流行的一类低成本电影,主题多为角斗士和神话传说。这些电影多半剧情荒诞,对白低智,演员表情木讷,特效粗糙。因为主角多半是肌肉男,这些影片像是健美比赛,无意中成为同性恋圈内流行的低俗笑话。
(31)同注释9,p.77、p.75、pp.70-71.
(32)同注释8,p.111.关于没有正常下垂的睾丸的叙述见第110页。
(33)Bret Hinsch,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The Male Homosexual i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诺里斯这里的话不能当真,因为他显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性恋”那时在中国被接受、甚至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相关论述见Frank,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5,p.145; Sang Tzelan D.The Emergent Lesbian: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p.45-46; Fran Martin,Situating Sexualities: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Film and Public Culture,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p.32.
(34)关于“作为甲胄的身体”,见Dyer,On photographing action poses中Meyer对于Rock Hudson和其他明星的比较,pp.261-262。
(35)Eve Kosofsky Sedgwick,Between Men: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36)Robin Wood关于《愤怒的公牛》的讨论非常具有代表性。Robin Wood," Two Films by Martin Scorsese," in Hollywood from Vietnam to Reag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45-269.
(39)同注释3,p.58。
(41)我在此借用了Susan Jeffords关于" remasculinization" 的概念。
(42)Morris Meaghan," Learning from Bruce Lee:Pedagogy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Martial Arts Cinema," in Keyframes:Popular Cinema and Cultural Studies,Matthew Tinkcom and Amy Villarejo ( eds.) ,New York:Routledge,2001,p.180.
标签:李小龙论文; 男性气质论文; 猛龙过江论文; 精武门论文; 李小龙肌肉论文; 龙争虎斗论文; 唐山大兄论文; 香港论文; 武打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