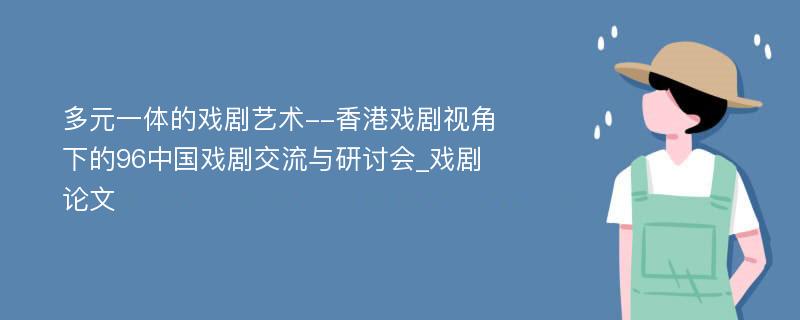
多元整合的戏剧艺术——’96中国戏剧交流暨研讨会香港戏剧观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香港论文,研讨会论文,中国戏剧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届中国戏剧交流暨研讨会上,有三台香港话剧:《次神的儿女》(香港话剧团)、《少女梦》(香港演艺学院)、《苦山行》(香港沙田话剧团)。它们呈示了香港90年代戏剧艺术渐趋成熟多样的态势和多元文化的化解力。其成功与不足之处,相信会引起大陆戏剧界的重视。
一
杨世彭翻译导演的《次神的儿女》(Children of a lesser God)是美国剧作家马克·麦道夫(Mark Medoff)70年代的成名作。原剧曾获1980年度百老汇托尼奖、外围剧评家奖和报界剧评家奖三大奖。改编成电影后,获1986年度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奥斯卡电影奖。它讲述失聪少女莎拉·罗门同青年唇语教授杰姆斯·李兹由恋爱到结婚而失败的故事。其主题的多义性隐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哑语手势和相对单纯明了的情节线索之中。这对青年在智商、情感方面对交流都不存在能力问题。杰姆斯开朗、能干、正直,热爱本职工作,技高一筹,掌握主导,直至成婚;在理解问题时,坚持来自切身体验的个人观点和个人方式。这种理解相当深刻,甚至不为所有人所理解,甚至导致婚姻毁灭;这种理解不可更改,因为代表一种价值,一种经验,一种存在方式。剧中涉及聋哑人应有的社会权益问题,他们的社会处境并不算好,他们的困难常常得不到帮助,他们不能享受同正常人平等的权益,其它他们本来应该得到比正常人更多的关怀和照顾。他们的教育还存在不少弊端和问题,需要社会关注并解决。由于问题严重以及社会的遗弃和歧视,他们需要呼吁乃至抗争。这一层面上的受害者、呼吁者和抗争者,当以奥伦为代表,虽然他的抗议和交涉主要针对校方,但问题属于残疾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歧视的和非正义的社会之外,也还是有一个例如以杰姆斯为代表的爱的和正义的社会。女律师和莎拉的母亲等也包括在内。他们能够理解和帮助奥伦们,但是怎么也理解不了莎拉们。
莎拉同那个只热衷于爱的小计谋的李蒂亚完全不同。对她的深入理解涉及语言人类学领域,特别是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语言与社会性别方面的研究。这里关乎三种关系:语言行为(包括说话和沉默)、社会性别以及运用权力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日常语言行为中,语言与社会交往的关系,即什么人说什么语,而且在什么情况下说某种特定的话;还有,语言怎样反映了社会性别,特别是女性的意识,女性语言行为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研究本身渗透着诸如格兰西的“霸权”、波尔度的“实践论”和福科的“权力”等概念、理论和观点。研究的理论影响表明,对客观现象的表达或再现实际上是对社会关系的控制,它可能是强制性的,有明显冲突发生的情形,也可能是共轭或互补互利的关系。但是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视角,这些理论没有女性主义的观点,即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与阶级和族群意识不同,不仅产生于日常生活,而且也受到日常生活的挑战。把作为社会关系的性别观念引入有关权力与语言行为的关系的概念之中,是女性主义人类学对语言学的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与表现和再表现的文化政治关系。
在剧中,所有人都要求莎拉进学校学说话,即使遭到拒绝。健听人或正常人总是怜悯失聪人,但似乎这是一种不顾及接受的怜悯。其实这是失聪人的不幸;同时,由于这是一种遭到拒绝的怜悯,一种不理解对方的怜悯,因此,这也是健听人的不幸。莎拉(有时加上奥伦)不得不一再声明:“不要可怜我,我宁愿做我自己”,“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帮助”。健听人认为失聪当然是残障,但失聪人并非都很赞同。莎拉说:“耳聋并非听力的反义词,而是一种充满声音的寂静”。随即她向杰姆斯描述一种感触敏锐、心智绝高的人才能“听”到的“声音”:春天冲破冬天死亡的声音。她也能通过空气的波动“听”杰姆斯播放的交响乐。她还借演讲稿宣示手语的优越性:“我的语言跟你们的一样好,我的交流能力其实跟你们的一样强,也许更强:因为我用一个手势描述出来的形象和意念,你们恐怕用五十个字都说不清楚。”也许这涉及所谓健听与失聪的哲理,关乎形与意、语与义、声音与寂静的关系。具备辩证意识和宽容精神的人也许能够理解和接受。
但是,真正关键而又潜隐的冲突是由失聪人的特殊而又似乎合理的要求引发的。莎拉代表了这种要求:自由的权益,不学说话的自由,她说:“他们从来不学我的语言,从来不——太艰难了。人们总盼望我能学会讲话,可是我又不愿讲话,我不愿讲话,我不愿做我做不好的事情!”奥伦也对杰姆斯的意图一针见血:“你骗不了我们,你要我们学手语,是因为你可以和我们交谈。你以为你想改变我们,我们就一定愿意被你改变吗?”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敏锐,揭穿健听人合理要求的不合理性:单方面考虑的出发点,由此带来强制性和自私性。由于这种自私的强制要求是日常的,更迫使失聪人反抗:起诉和离婚。他们要保护自己自然的正常的存在方式,同健听人完全平等的那种自然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我们当然也会注意到如莎拉这样的女性失聪人的来自同诸多男性健听人性交往的切身经验:他们往往以身体语言相待,而并不开口说话。在莎拉看来,他们的说话与沉默,只是出于对待她的不同需要而已。他们不同的语言方式就是不同的性别压迫方式。而莎拉对语言方式的选择就是对女性存在方式的确认,其实也是女性政治意识的表现。在这方面,奥伦同莎拉显然有着不同的语言行为。前者属于男性失聪人的激进,而后者属于女性失聪人的激进。两种激进并不在同一层面:语言中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男性试图以自己的语言来垄断社会(包括女性)的权力。莎拉当然作出抵制(拒绝奥伦代表她发言的要求)并以自己的讲演取得成功。换言之,在维护女性失聪人的性别权益方面:莎拉是警觉的,哪怕对待“同志”;莎拉是成功的,虽然代价巨大。
如果从区域主体或民族主体的角度,也可作区域间共存和民族间共存如何和谐平等的解释。小区域或少数民族以看似激进的方式生存的合理性能够唤起观众的同情吗?此外,人际理解显然是剧情生发的主题。不同世界沟通的桥梁是否存在或怎样建构?杰姆斯和莎拉从认识开始就交错着理解和误解,直至最后婚姻破裂。这是否意味着对进入误区的性别、世界、区域、民族、语言、权力、自由、平等和爱情等都是一种风趣和温情的警示呢?
在北京的演出效果,据编导称,不如香港等大陆以外都市。这里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北京观众带着文化隔膜观看,毕竟比较吃力。台词似乎还可更加精练,既减少表演的沉重,也消除观看的沉闷(顺便一提,观众并不喜欢过多的、基本不懂的手语;当然,还有过满的声音空间),同写意的道具布景也更加协调,并且更容易生成诗化的哲理。表演的层次、节奏不够清晰,这同对男女主角情感发展变化和不同性格的理解尚待深入相关。关键处若处理更加着力,全剧或许更有思考和动人的力量。此外,舞台空间的分割似乎尚有改善的余地。
二
《少女梦》是采自明代汤显祖作传奇剧本《牡丹亭》的音乐剧。此剧基本保留了原作中杜丽娘梦而死、死而生的奇幻情节主干,情与理的矛盾也有所涉及。但是,并不重在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它歌颂或渲泻染的是世俗爱情的幸福,但并不宣扬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古典浪漫主义被波普化了,虽然构思依然奇特,人物心理刻画依然细腻。
原作曲词优美,文采缤纷,而《少》剧场面瑰丽,舞魂翩跹,怨曲绕梁,艺术精神可谓也有相通之处。当然,从剧本的角度,该剧的文学性不够:起码歌词文字欠缺功力。从表演的角度,它和《苦山行》一样,用粤语表演。它的歌词是用字幕投射在台框一侧,而且并不清晰。这给粤港以外观众的接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据杨世彭导演介绍,香港话剧团只有六名演员能用普通话表演,相信包括《少》剧组在内的香港其他戏剧团体能用普通话表演的演员也不多。这给香港同大陆在戏剧方面的交流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一出充满生命活力的音乐剧,其中舞剧的因素较多,而话剧的因素相对较少等。虽然,从舞剧方面的情节性来说,还是基本足以支撑全剧的。这也是古典名剧生死离合情节的遗泽所惠。该剧的歌剧因素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代替话剧因素的作用。编导有意让“好看”的因素突出出来:少男少女、娱乐舞蹈、梦幻场景、薄如蝉翼、情节完整、怨曲缠绵、交合妙境、色彩缤纷和用光变化。主人公的特定意境同群体舞蹈的表现功能相谐调。看得出,编导有意将话剧导演的基本要素同舞蹈语言和音乐语言本身相结合,加上话剧结构原则,从而创作出这样一部音乐剧。台词变成歌词,其实又起到解说词的作用。同时减少了象征形象和比喻手法的运用。借观赏性对古典名剧进行世俗包装(包括我们所注意到的少男少女群体的舞蹈服装并非符合剧情需要的古代式样),这也是高度发达的国际都市在商业化中发展或利用高雅艺术的文化策略吧。
在原传奇剧本中,反封建的主题由于以皇帝出面调解,全家大团圆受封作结而弱化;而在《少》剧中,原主题进一步弱化,爱的美丽和生的重要被置于首要位置。主题本来的政治和历史深度几乎完全被削平。悲剧内核被抽取,只化解成生死转换的浪漫爱情故事结构框架。市民娱乐审美价值正是通过观赏性、浪漫性来取代反抗性、悲剧性而取得的。
这出音乐剧的组合方式基本属于十九世纪末德国作曲家、戏剧家瓦格纳提出的所谓三T主义的戏剧理论。因此,《少》剧编导的综合意识多少来自欧洲戏剧传统的基因。从综合意识的现代出发点来看,各组合因素的运用,都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散发市民文化气息的歌词自不消说;编舞也是民族舞和现代舞以及其他各种舞蹈语汇的自由使用,并尽可能地表现只有现代都市青年才能表现的青春活力、爱情追求和幸福理念;音乐则是民间和仿古的杂糅。音乐剧在当代大陆尚属正待发展阶段,《少》剧来京上演,对于大陆戏剧界,无疑有着现场观摩、直接感受这一戏剧类型的积极意义。
三
香港沙田话剧团演出的粤语话剧《苦山行》是一出小剧场话剧,它以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香港慈善机构负责的“苗圃行动——行路上广州”的筹款活动和到湖南及广东贫困山区助贫兴学的事迹为题材。编导有意“重申剧场的社会性功能,并望透过创作剧的媒介和小剧场的形式去继续剧艺上的探索”。在小剧院既定而狭小的空间中表现“行路”那么流动而现实的题材是一种自我挑战。然而,总的看来,表现是成功的。虽然风格并非写实,但仍然传达出一种高度的真实感并给予观众思想的空间。它借“苗圃行动”的艰难旅程,象征和表现人生之旅;借“苦山”隐喻亟待拯救的世界和苦难中的芸芸众生;借东西方神话传说扩大深化人类普遍哲理。同时,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和间离效果说、格洛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理论以及布鲁克的神圣戏剧说,努力探索现代戏剧的艺术可能性。
《苦》剧从布莱希特那里采用了重视唤起观众理性的做法,排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性因素,没有什么人物性格塑造和情节性或传统戏剧性。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分教育剧、寓意剧和历史剧三类,并且有许多作品带有表现主义色彩。而《苦》剧的强烈寓言表现欲望和宏大哲理以及启蒙情结,都恰好适于布莱希特的戏剧语言。
在对待格洛托夫斯基的理论时,虽然并没有达到所谓“与观众打成一片”,但由于它是地道的小剧场戏,与观众的关系比较直接。朴素、简洁的追求也是基本成功的。直观地看,该剧的道具、布景、服装、化妆、台词都聊胜于无。当然,这方面的问题又比较明显:场面和内容过于拉长。问题的根源在于象征和意象在内涵和设置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同编导在哲理提升上的简单化和对作为哲理提升前提的各种生存环境在理解上过于笼统直接相关,特别是前半部分。从结构上看,全剧共分四部分二十四场:(进场)1.友谊之舞2.走路组曲(受惠者篇)3.山4.罪恶箱子5.我不是诗6.玄黄再造7.山区阿妈8.苦9.伟大愿望10.希望之舞(步行者篇)11.神仙不再12.起步仪式13.美味唐僧14.争先恐后15.群魔乱舞16.互相扶持17.连体怪物18.坚持己见19.难以禁锢20.终点起点(终极篇)21.责无旁贷22.鞠躬尽瘁23.礼成24.苗圃之舞。由此看出,各场次意义不够清晰,来源于视角不一,主观容量偏大,提炼乏力。其实,场面处理如果紧扣“苦”之主题,精选相关意象,并借舞台手段强化、扩展、充实,相应地,去除一些场面、形体运动,观感还会更好。毕竟有个“度”的问题:走台走多少圈合适?给观众的印象较深的场景如:走路组曲、山、罪恶箱子、山区阿妈、苦、希望之舞、起步仪式、互相扶持、连体怪物、坚持己见、终点起点等。总的来说,“质朴”或“贫困”的概念对于全剧还是相当鲜明的。看来,对于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理论的理解,恐怕不能限于道具、布景、服装、化妆、台词等,而需要扩展到整个戏剧艺术精神。
将贫困剧场同神圣剧场统一起来,是《苦》剧的成功之处。而且使它不至于如格氏戏剧那样沉闷。苦山的苦,苦“行”的苦,做人的苦,同舞台表演的苦融合成戏剧形象,强化了编导观念。导演采用贫困剧场中演员苦行修身的训练方法,演出时超乎常人的体力及精神状态,特别是演员形体语汇的表达能力的充分调动,已经打破了演出同现实的界限。而这又同布鲁克的神圣戏剧有相通之处;布氏要摧毁以往戏剧割断自身同生活一切关系的状态。而且他也主张寻找一种以声音为动作组成的戏剧语言,摆脱语言及文化传统对戏剧的束缚。格氏要求演员根除心理障碍,揭示隐蔽的内心活动。而布氏设计了一些内心冲动——外部表现的练习,引导演员创造新的戏剧语言。这些都为导演所利用。演员对导演的观念和意图,还是比较理解和基本掌握了的。虽然他们获得的训练和经验似乎还不算充分地多。例如后半场比较明快,但前半场确实守于凝重,这当然同剧作本身有关,但也有表演不够松弛的问题。造型、虚拟和抽象的效果较好,行之苦、山之苦、人之苦、苦之义,都是用苦的形体语言充分表达。说该剧基本上是形体化的,也并不为过。
编导善于运用对比:虚实、苦乐、是非、善恶、罪罚、具体苦抽象苦、精神肉体、享受追求、现世来世、苦海无边“敢以身殉”等。总的来说,“苦”是贯穿全剧的。这当然很容易纳入主题之中。苦难意识采用诸如西行取经、基督受难、潘朵拉盒、西绪弗斯等神话传说进行提升、摒弃,从而从社会层面到文化、哲理层面都有了一定解释根据。
在编导看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他的演员体系,实在是一种科技人文主义的表现”;“相信社会改造的布莱希特”,“创办史诗剧场,创用间离效果”,是为了“以收警醒人心之效”。甚至格洛托夫斯基“创办贫困剧场,实在仍然积极地在探索剧场的社会功能”。因此,编导作出两点:“社会关注乃是严肃剧场的主题”;“‘苗圃行动——行路上广州’与牺牲式贫穷或神圣剧场有很相似的地方。”对于后一点,编导认为“值得论述”:“我们亦可以想象这一百几十名的步行者当中都怀有不同的目的参加:有的为了做善事,有的为了向体能挑战,有的为了跟人打赌等等。但是他们自甘吃苦的表现,就像告罗多斯基(格洛托夫斯基)的演员一样,包含了一种‘敢以身殉’的精神。在文学的领域里,类似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浪漫的如《唐吉珂德》,幻想的如《西游记》。在宗教方面,基督被钉十字架去拯救世人,就是最极致的例子。”戏剧的社会功能在编导的处理中,没有变得“肉麻”,这是值得大陆戏剧编导注意的。其实,希望工程一类的题材,很容易被渲染得凄凄哀哀、期期艾艾。但此剧将内容抽象,通过场面和形体表演来表现,使得内容丰富、直至伟大崇高,体现人类终极关怀。而本来这似乎是小剧场所不擅长的。所以,怎样将抽象乃至多少显得空洞的内容表演出来,该剧有方法上的可借鉴之处。例如该剧重复、交接和转场几次,就使观众明白了其中含义;又如用仅一二行字的字幕完全代替台词;声音语言几乎完全为形体语言所代替。这些方式在大陆戏剧中不多见。当然,剧中场面和形体表演,有时顺畅,有时不顺畅。而且编导似乎不强调通常意义上的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忽略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这本来是小剧场最重要的特性。但该剧接近本来意义上的小剧场,则大体可以成立。大陆从80年代起,就产生了不少小剧场剧,但相当一些是将大剧场搬到小剧场:缺少“贫困”精神。这样看来,贫困戏剧并不简单。
戏剧的最高任务和贯穿动作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特有的说法。主要与他对戏剧的社会使命和教育作用的观点相联系。所谓最高任务即终极目标,所谓贯穿动作即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统一的、有机的动作。《苦》剧编导将“苦”的最高任务同“苦”的贯穿动作组织得较好,并且在形体动作方面同格洛托夫斯基的强调形体语汇的要求取得某些一致。关于表演艺术的特性问题,斯氏认为演员艺术是动作艺术;心理形体需要有机统一;舞台生活有双重性。也就是说:这些是体验艺术的特性。斯氏对于表现艺术采取有保留的借鉴的态度。而《苦》剧编导则不然,他们主要的是利用格氏理论,无论是观念上还是方法上。对于斯氏学说,是在社会意义的最高任务方面获得自觉意识;同时,表演并未完全排斥情感或体验成分。所以,说该剧基本上是表现派的,虽然简单了点,但大体符合实际。
该剧利用了小剧场的真实性:例如演员在台上真的炒菜。以此逼近观众,造成舞台与生活的“短路”,构成戏剧的虚实相间。当然,依我看来,在“苦”的前提下,炒菜不如煮菜更真实。香港编导不知大陆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赤贫山区油盐酱醋柴的“珍贵”,也是情有可原。此外,演员表演大陆山区传抢橄榄球,也是对“国情”了解不够:不如换作圆球。因为目前只有在大陆的大城市,才能偶尔见到儿童玩耍玩具橄榄球或外国留学生在校园内练习橄榄球。其他还有可推敲之处:红领巾不是中国式样,而是前苏联式样。红领巾的结的系法也全然不对。这些地方的细究,只是为了情境和道具更加真实和典型,也符合本剧的精神。关于剧中为什么不用真小孩,导演作了这般答复:“一是我团无小孩;二是小孩已死;三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我以为:第三点当然完全牵强;就观赏效果而言,这个总是被背在作为母亲的山村妇女身上的软布小孩的设置完全失败:滑稽丑陋、阴森可怖,也不能让观众弄清他后来因伤病而死的时间界线;而且象征不了什么。当然,处理得好,仍然能够赋予象征意义。
标签:戏剧论文; 编导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戏剧论文; 格洛托夫斯基论文; 剧场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都市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