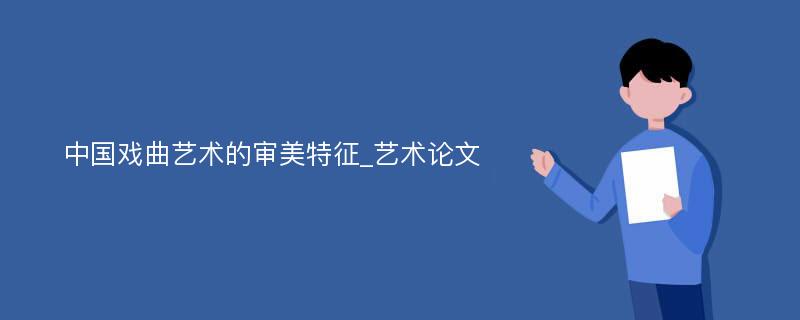
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特征论文,中国戏曲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究竟是什么?诸家学说不一。但有一点则少有争议,这就是几乎大家都公认:中国戏曲艺术有着极其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创作思想、表演形式到欣赏态度,都和西方的话剧、歌剧、舞剧大相径庭,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事实上,由于中国戏曲艺术产生和成熟都最晚,又是一门综合艺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了中国艺术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所以,只有首先弄清了中国艺术的审美意识体系,才说得清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
如果把中国艺术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舞蹈、音乐、诗画、建筑和书法,便可以看作是它美学结构的五个层次:最核心最内在最深层的是舞蹈的生命活力,它表现为气韵与程式;其次是音乐的情感律动,它表现为节奏与韵律;第三是诗画的意象构成,它表现为虚拟与写意;第四是建筑的理性态度,它表现为充实与空灵;最后是书法的线条语言,它表现为抽象与单纯。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中国艺术的精神。
一 气韵与程式
中国戏曲与舞蹈的关系,似乎最密切。
舞蹈,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样式。在上古时代,它被称为“乐舞”。不过,中国上古时代的乐舞,却既不只是音乐,也不只是舞蹈,而是集文学(诗)、音乐(歌)、舞蹈(舞)等多种艺术样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曾经和作为立国之本的“礼义”一起被并称为“礼乐”,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后来,乐舞逐渐消亡了,代之而起的便是戏曲。戏曲和乐舞一样,也是集诗、歌、舞等多种艺术样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些具有一定戏剧性的故事情节。
所以,戏曲也可以说是“有故事的乐舞”。
不过,故事虽然加了进来,却并不怎么重要。中国传统戏曲的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有的几句话就可以说完。有些“折子戏”,简直就没有什么情节。然而,歌舞的分量,却相当之重。而且,越是情节简单,歌舞的分量就越重,“戏”也就越好看,这真是咄咄怪事!看来,中国戏曲要演的,似乎并不是故事情节;观众要看的,似乎也不是故事情节。否则,故事情节早已烂熟于心的戏(比如《群英会》),为什么要看了一遍又一遍?故事情节完整连贯的戏(比如《失街亭》、《空城记》、《斩马谡》),为什么可以拆开来单演(“批零兼营”,既演全本戏,又演折子戏,也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演出方式之一)?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的其他艺术样式(比如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什么并不能取代戏曲?可见,对于中国戏曲来说,故事情节,并不重要,至少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中国戏曲要演的,中国观众要看的,主要是什么呢?是歌舞。中国传统的戏曲(比如京昆),无非三大类:唱工戏、做工戏和武打戏。但无论哪一种,其台词都无不音乐化,其身段都无不舞蹈化。如《文昭关》、《二进宫》、《借东风》,简直就像独唱音乐会;如《挑滑车》、《三岔口》、《盗仙草》,又像是舞蹈或杂耍。更多的,当然还是载歌载舞,唱做念打齐全。这就和西洋戏剧迥异。西洋的戏剧,话剧是话剧,歌剧是歌剧,舞剧是舞剧。有歌就没有舞,有舞就没有歌,要不然就是歌舞都没有。然而中国的戏曲,却集诗歌舞于一体。观众看戏的时候,也是连歌带舞和戏一块儿看。试想,如果没有歌舞,或者只有歌没有舞,像《徐策跑城》、《贵妃醉酒》这样的戏,还有什么看头?
可以说,没有舞蹈,也就没有中国的戏曲。中国戏曲的舞台演出,不但唱的时候要舞,不唱的时候,其舞台动作,也是节奏化程式化亦即舞蹈化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戏曲不但能取舞蹈之形,而且更得到舞蹈之魂。
这个“魂”,就是气韵与程式。
气韵,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核心,就是气。有气,才能气韵生动,也才能气势磅礴、气象万千。什么是气?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中的“气”或“元气”,无非就是人所能感觉到而不能科学地表述的生命力或生命感。但是,这种生命力或生命感,却易于为艺术所体验。舞蹈,便正是体验生命活力的一种最佳审美形式(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先生在其著名的《说舞》一文中有极其深刻的论述)。中国戏曲艺术之所以要借助舞蹈,要用歌舞来演故事,也无非是要体验和保有这样一种生命活力。
所以,中国戏曲艺术,也和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极其讲究风力和骨力。风骨都本之于气。气动万物就是风,动而有力就是骨。具体到艺术,则风讲动人之情和飞动之势,骨讲立人之本和内聚之力。再具体到戏曲,则“手眼身法步”讲究的是飞动之势,“字正腔圆”讲究的是内聚之力。但不论唱做念打,都必须功底深厚,情感投入,意守丹田。因为有功底才有骨,有情感才有风,守丹田才有生命力。厚功底、重情感、守丹田,才能“气韵生动”。什么是丹田?丹田就是人体中聚气的地方。对于练功的人来说,就是“命根子”。用丹田之气来表演,也就是用生命来表演。中国戏曲艺术的感染力,就来源于此。
生命活力纳入审美形式,就形成了程式,何谓程式?程式就是法度、规矩、章程、格局、格式、模式、范式、样式,是一种在长期实践中定型了的东西。中国艺术几乎无不讲程式。诗有格律,画有笔法,词有词牌,曲有曲谱,书法则有格式。“草字不入格,神仙不认得”。岂止是“不认得”?也“不好看”。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一举手、一抬足,甚至某些并不好看的形态(比如醉酒),为什么一到舞蹈当中就好看了呢?就因为它被程式化,变成可以观赏的东西了。所以,程式化也就是审美化。舞蹈,就是通过程式化将生活形态和生命活力变成审美对象的最典型的一种艺术。
因此,中国的许多艺术都通于舞蹈,趋向于舞蹈,甚至可以看作是舞蹈。比如中国书法和绘画中的狂草和写意,简直就是纸上的舞蹈。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戏曲。中国戏曲的舞台演出几乎自始至终会由一系列程式构成:圆场、走边、起霸、亮相,一举一动都有程式。可以说,离开程式,就演不成戏;不懂程式,就看不成戏。正是超模拟非写实的程式,使中国戏曲成为一种可以脱离故事情节来观赏的戏剧样式。因为中国戏曲的程式,就和绘画中的笔墨一样,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本身就是可以独立观赏的东西。一种艺术,如果连它的构成部分和构成方式都有审美价值,它还能不是美的艺术吗?
二 节奏与韵律
以歌舞演故事的中国戏曲,十分讲究节奏和韵律。
节奏和韵律是音乐和舞蹈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是程式不可或缺的东西。程式之所以是可以独立观赏的审美对象,就因为其中有节奏和韵律。你看中国戏曲的程式,云手也好,趟马也好,哪一种没有节奏,没有韵律?许多程式,在表演时,都要伴以锣鼓点儿(比如亮相时就常常伴以“四击头”),就是为了保证和增强节奏感。有了节奏感,程式就变成非常好看的东西了。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四击头一亮相,美极了,妙极了,简直OK顶呱呱!”
但是,只有节奏没有韵律也是不行的。如果没有韵律,程式就会变得僵硬,没有观赏价值了。所以,不但青衣们柔美的程式要有韵律,武生们英武的程式也要有韵律;不但音乐唱腔要有韵律,动作身段也要有韵律。事实上,中国戏曲的舞台演出,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节奏和韵律,这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又一美学特征。
节奏和韵律,使中国戏曲不但近于舞蹈,也近于音乐。
音乐也是中国最古老最受重视的艺术样式之一。中国古代音乐不但水平高,而且地位也高。它甚至被看作一种最高的道德修养境界和社会理想境界:做人,要“成于乐”,才能成为“圣人”;治国,要“通于乐”,才能造就“盛世”。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音乐和天地宇宙一样,具有一种理想的美,——既井然有序,又高度和谐。因此,真正的音乐,伟大的音乐,应该与天地宇宙相通,这就叫“大乐与天地同和”。
什么是“和”?中国音乐和音乐理论追求的“和”或“和谐”,其实是一种情感体验,即“和谐感”。因为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本质无非就是情感的表现与传达。不但音乐如此,诗、舞蹈、绘画、书法、雕塑、建筑,也无不如此。因此,一件没有人情味、不能激起情感共鸣的作品,不但不能算作艺术品,而且简直就不可思议。“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自然尚且如此有情、重情、多情,而艺术品居然无情,那还算什么东西?
中国戏曲当然更不例外。戏,是要有人看的。如果戏中无情,请问在中国又有谁看?事实上,尽管中国戏曲的题材很广泛,但最受欢迎、久演不衰的,还是那些最能打动人心、激起观众情感共鸣的剧目,如《白蛇传》、《秦香莲》、《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玉堂春》、《十五贯》、《宋士杰》、《桃花扇》、《打渔杀家》等等。此外,一些人情味很浓,极富生活情趣的小戏,如《小放牛》、《刘海砍樵》、《夫妻观灯》等,也颇受欢迎。在这些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剧目中,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并不完全是故事情节,更主要的,还是那些世俗的伦理情感,那些可以为之开颜、为之切齿、为之恸哭、为之欢呼的喜怒哀乐。情感是可以反复体验,也是必须反复体验的。因此,这些戏,就会被看了一遍又一遍,而且百看不厌。一出戏,如果情感内容极其丰富,又有好听好看的歌舞,那就更会倍受青睐,成为公认的好剧目。
这样看,中国戏曲又可以说是“以歌舞演情感”。
因此,中国戏曲的节奏与韵律,也就是情感的节奏与韵律。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戏曲好象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概念,舞台上的时间节奏和空间节奏也很混乱。《白良关》尉迟恭发兵北国只绕了一圈,《徐策跑城》从城楼到朝房却跑了好几圈。十万人的大仗,几个过场就完;一个马失前蹄,却演得淋漓尽致。一封书信,洋洋万言,几笔写就;况钟监斩,只要勾一下,却总也勾不下去。宋江坐楼,一夜功夫,不过几个唱段,寻书却寻了老半天。其实,这里讲究的,正是情感的节奏:但凡交代情节的,能快就快,能省就省,而表现传达情感的,则不惜笔墨,着力渲染,根本不考虑时间的长短。甚至在兵临城下杀头在即的紧要关头,剧中的人物(一般是小生、老生、正旦、老旦之类)仍会坐下来不紧不慢地咿咿呀呀唱个没完。那么长的功夫,敌人的箭,早就该射进来了。
然而,中国戏曲舞台是一个由情感的节奏和韵律构成的空间。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生存空间,也是一个充满了音乐情趣的艺术空间。在这里,空间方位和时间节奏都对应着情感的律动,变成回肠荡气的唱腔和优美精彩的身段,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就形成了中国戏曲的另一个美学特征:虚拟与写意。
三 虚拟与写意
虚拟与写意,是中国诗画艺术的美学特征。
中国诗讲虚拟:“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请问谁能坐实?中国画讲写意:“逸笔草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过意似而已。因为中国诗画艺术和中国一切艺术一样,是以情感的表现和传达为本质、为己任的。因此,它们的逻辑,就是情感的逻辑;它们的真实,也就是情感的真实。依此真实,就不必拘泥于外形的酷似、物理的真伪;依此逻辑,就可以反丑为美、起死回生。抽象、写意,是不求外形的酷似;夸张、变形,是不辨物理的真伪;枯藤老树、残荷败柳皆可入诗入画,是反丑为美;与古人对话,让顽石开口,是起死回生。
这样一种艺术观,在戏曲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认真说来,虚拟性,是一切艺术的特性。画的苹果不能吃,画的鞋子不能穿,诗人绘声绘色地描写骑术,自己却不会骑马,就因为艺术是虚拟的。所以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康拉德·朗格则更谓艺术是“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的确,戏者戏也。戏剧和游戏都是那种明知是假,却又认真去做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是一切戏剧甚至一切艺术的共性。
中国戏曲的独到之处,是坦率地承认艺术的虚拟性。西方戏剧基本上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他们的演出,是“现在进行式”,十分重视舞台上的真实感。他们设想演员和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叫“第四堵墙”,设想观众是从“钥匙孔里看生活”。所以,他们的道具、布景等等,总是面面俱到,力求真实。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花钱多不说,也未必有效果。因为道具布景做得再像,也是假的,而且其真实性也总是有限的。比方说,你总不能在演到冬天时让剧场里冷得滴水成冰,在演到夏天时又热得观众满头大汗吧?
中国的戏曲艺术家就高明得多。他们干脆公开承认是在演戏,一切都是假的,不过是“以歌舞演故事”。也就是说,中国戏曲的演出,是“过去叙述式”的。咱们姑妄言之,你们也姑妄听之,对付着看。这样一来,演员自由了,观众也自由了,谁也没有心理负担。遇到演出条件受限制、演员有困难的时候,观众还会出来帮忙,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帮你克服。比方说,舞台上没有水,行船怎么演?演员的办法是用桨划拉两下,意思是:我上船了。观众也默认:行,你上船了,接着演吧!反正咱们演的看的,都是过去的事儿,就不必那么叫真儿啦!
这可真是事半功倍,花小钱办大事情。这种做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极其尊重观众,充分调动观众的积极性,让观众参与到戏剧艺术的创作过程中来。结果,问题得到了解决,观众还很高兴,何乐不为呢?
事实上,尊重观众,也是中国戏曲的一贯作风。比方说,《坐楼杀惜》中刘唐的自报家门就是。刘唐一上场,就对观众说:某,赤发鬼刘唐是也。这原本是不应该的事,因为宋代的刘唐不可能和我们说话。而且,既然是和隔了上千年的我们说话,就不该害怕当时官府的差人听见,然而当刘唐说到“奉了梁山”几个字时,却突然捂嘴,看看四周有没有人,然后才压低了声音接着说“奉了梁山晁大哥之命”等等。可见,中国戏曲虽有虚拟之事,却无欺人之心,能真实的,还是尽量真实。更何况,在中国艺术看来,一切都可虚拟,唯独心理和情感不可作伪。如果心理和情感也作伪,那就不但不是艺术,而且什么都不是,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了。
正因为中国戏曲的艺术构成是虚拟的,因此它的舞台表演也就必然是写意的。一切程式,都不求外形的酷似,只要交代清楚,意思明白,便点到即可,不必苛求细节,斤斤计较,与西方戏剧所谓“无实物动作”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戏剧的“无实物动作”虽然也有虚拟性,但仍要求“形似”;而中国戏曲的“虚拟程式”,却只要求“意似”。从渴酒、吃饭、睡觉、起床,到跋山、涉水、跑马、行舟,都只是“意思意思”,只要在“意思”上相似就可以了,和国画写意中的“意到笔不到”或“逸笔草草”差不多。既然所求不过意似,则“旦角上马如骑狗”,或者揩眼泪时袖子和眼睛隔着几寸远,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相反,由于这些动作都是程式化的,就不但不“假”,反倒能给人一种特殊的、具有装饰意味的美感。
四 充实与空灵
虚拟和写意,体现了一种理性的精神。
我们知道,虚拟和写意的前提,是公开和坦白地承认自己是在演戏和看戏。这当然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即理性地意识到舞台上的真实不等于生活中的真实。演员既不是在照搬生活,观众也不过只是在欣赏艺术。这就不但在舞台和生活之间设置了距离,也在观众和演员之间设置了距离。有距离,就能生美感。美学上的这一规律和原则,被中国戏曲艺术运用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理性的精神,也就是建筑的法则。
建筑是一种分割空间的艺术。中国建筑艺术的哲学,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充实与空灵的辩证法。大体上说,中国的建筑艺术,是既讲充实又进空灵的。比方说,园林别墅要“借景”,是为了求充实;宫廷建筑要开阔,是为了求空灵。总之,中国艺术的法则是亦虚亦实,虚实相生。虚不是空虚和虚无,实也不是僵化和刻板,而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空灵的风格表达着充实的内容,沉着的风骨表现为飘逸的情趣,就像中国许多建筑都有着稳重的石基和灵动的飞檐一样。
这一法则在戏曲艺术里面也同样得到了体现。
中国戏曲舞台,从总体上说,是一个空灵的结构。没有布景和极少道具倒在其次(现代戏就已经有了布景和道具),主要还在于它的时间、空间、物象、环境、动作等等全是“虚”的。比如苏三从洪洞县起解到太原府,路程少说有四百里,行程少说得七八天,可苏三不吃不喝不投店,几个圈圈一会儿功夫就走到了。这种事情,显然只有在中国戏曲舞台这个空灵的结构中才能实现。
空灵的结构是一种诗意的结构,也是一个音乐的结构。驰骋于其间的是想象,充实于其间的则是情感。
所以,中国戏曲艺术也是有虚有实,虚实相生。有不可虚,也有不可实;有不可不虚,也有不可不实。不可虚者,心理是也;不可实者,物理是也;不可不虚者,生活原型是也;不可不实者,生活体验是也。具体说来,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虚环境而实感受。戏曲舞台空荡荡,不要说没有真山真水,就连假山假水也没有。但是,环境可虚,人在环境中的感受却不可虚。这就要求演员必须好象真的看见了山,看见了水,吹到了风,淋到了雨。比如唱“月朗星稀”,就必须先看看地,唱出“月朗”两个字,再看看天,唱出“星稀”。因为人夜间出门,当然是先看地上的路。发现地上一片光明,知道月色很好,这才会抬起头来,看见星光稀少。在这里,月也好,星也好,都是虚的,但剧中人对“月朗星稀”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二是虚故事而实体验。戏曲都是要演故事的。不过故事里的事,可真是“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不但故事本身可能是虚的,对故事的表演也多半是虚的,有的(比如杀头、打人),简直就是徒有虚名,不过虚晃一枪。但剧中人在故事中的体验,却含糊不得。比如宋江寻书,找到了招文袋却找不到书信,便突然将袋底翻转,两眼死死盯住,好象要看到布缝里面去,这种体验,就非常真实,非常实在。
三是虚时空而实心境。在中国戏曲舞台上,三五步千山万水,七八招斩将过关,一个圆场百十里,一段慢板五更天,温长的时间,辽阔的空间,仅仅表现为几个极其精彩优美的动作、身段或唱段。但是,一牵涉到人物的心境,就不怕麻烦,不省功夫了。比如《战宛城》里曹操马踏青苗那一段,为了表现曹操不可一世的派头,志得意满的心境,特地为他设计了一系列身段,随着曲牌的节奏,铿锵交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可见,中国戏曲舞台虽然是一个空灵的结构,其中却有着充实的内容。然而,也正因为这些内容被纳入了空灵的结构,才使得中国戏曲艺术有了一种独特的神韵,并因此而接近于书法。
五 抽象与单纯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书法的结构正是一种空灵的结构。
这样一种空灵的结构当然不是书法独有的。事实上,它是几乎所有中国艺术的结构。因为中国艺术的造型观,不是力求形似的“具象造型观”,而是只求意似的“意象造型观”。“意象造型观”的要义,是“立象尽意,得意忘象”。象,不过是传情表意的手段,是可以不必斤斤计较甚至可有可无的东西(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或“此时无声胜有声”即此之意)。于是,就有了诗画艺术的虚拟和写意,也就有了书法艺术的抽象与单纯。
作为一种纯粹的线条艺术,书法不可能不“抽象”,也不可能不“单纯”。书法当然必须以汉字为素材,而汉字在事实上又以象形为本源。但是,在书法作品中,象形的成份其实已所剩无几,流走于纸上的,只是线条,而线条恰恰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因此,如果说中国画的抽象是“抽而有象”,那么,书法就差不多可以说是“抽而无象”。抽而无象当然“单纯”。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没有具象形象,没有光影、明暗、透视,也几乎没有色彩,可以说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单纯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品位。在抽离了一切杂芜以后,人们面对的便是一片纯净,这难道还不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吗?
中国戏曲艺术的境界也有似于书法。
反映具体社会生活的戏曲也能抽象?这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却是事实。因为中国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又“以程式演歌舞”。程式,正是一种抽象的东西。程式的特点,是概括化、类型化和装饰化。在戏曲舞台上,它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和汉字一样可以识别辨认的东西。把这样一种东西用极富节奏和韵律的身段、工架和唱腔表演出来,岂不就变成了书法?同样,正如不识汉字也可以欣赏书法,不懂程式也不妨碍欣赏戏曲。因为它是抽象的东西,而一种东西越是具有抽象性,也就越是具有普遍性。概念是最抽象的,所以概念也最有普遍性。程式当然不是概念,但它既然具有普遍性,那就一定和概念一样具有抽象性。
程式的抽象性其实是毋庸置疑的。中国艺术的程式,从空间意义和视觉意义上讲,是一种“类相形象”;从时间意义和听觉意义上讲,是一种“节律形象”。(注:关于类相形象和节律形象,请参看吕凤子《中国画法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杜健《形象的节律与节律的形象》,《美术》1983年第10期;钟家骥《书画语言与审美效应》,福建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类相形象讲虚拟与写意,节律形象讲节奏与韵律,表现在纸面上是书法与绘画,表现在舞台上就是戏曲与舞蹈。
什么是“类相形象”?说得白一点,就是一类事物共有的形象。比如画竹的程式,无非“个字形”、“介字形”,而无论是斑竹、茅竹,还是罗汉竹。又比如“起霸”的程式,也是武将这一类人物在做整盔束甲这一类动作时共同的形象,也并不管那武将是谁。什么是“节律形象”?说得白一点,就是由节奏和韵律构成的形象。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节奏和韵律,一旦被抽象出来,就构成了节律形象。比如用毛笔写字,有“提按疾徐”,定格在纸面上,就形成了书法作品的节律形象。又比如人走路都有节奏,用“急急风”之类的锣鼓点儿表现出来,就变成了节律形象。戏曲中的曲牌、锣经,都是节律形象,因此它们都可以作为审美对象来单独欣赏。可见,没有抽象,就没有类相形象和节律形象,也就没有程式。中国戏曲既然离不开程式,就不可能不抽象,也就不可能不单纯。
又抽象,又单纯,岂不没有什么“看头”?恰恰相反,更有看头了。因为抽象不是无象,单纯也不是单调,而是要尽量用纯净的节律、洗练的笔法和简洁的程式来表现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因此,中国戏曲也可以广义地看作是一种“线条艺术”。诚然,对线条的感受、领会、理解和把握较之其他艺术语言要间接得多、困难得多。但是,正是由于感受、领会、理解和把握较之其他艺术语言要间接得多、困难得多。但是,正是由于感受、领会、理解、把握的间接性,才不但给欣赏者留下了自由想象的余地,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不但要“看得懂”书画、画面、字面上的东西,更要“看得出”书面、画面、字画以外的东西。对于戏曲艺术而言,就是不但要看得懂故事,也不仅要看得懂程式,更要懂韵味。戏,不但是要看的,更是要“品”的。北京人说“听戏,瞧电影”,正宗的老戏迷甚至闭着眼睛听戏,一边听,一边摇头晃脑地“品”。品什么?品韵味。什么是韵味?又没有几个人说得清。实际上,它就是中国美学一讲再讲的言外之意、画外之象、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它们表达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艺术的辩证法:最抽象的语言往往最能表现微妙的情感,最单纯的形式往往最能蕴含丰富的内容。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所谓“一以当十,以少胜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中国艺术棋高一着之所在。这是书法的神韵,也是中国戏曲艺术的神韵。
也许,这就是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舞蹈气势、音乐灵魂、诗画意境、建筑法则和书法神韵。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中国艺术的精神,也构成了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神。
标签:艺术论文; 戏剧论文; 书法欣赏论文; 美学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舞蹈论文; 书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