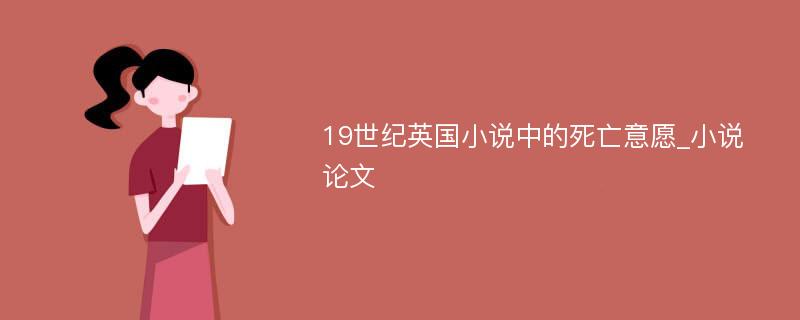
英国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临终遗嘱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遗嘱论文,临终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浏览英国19世纪小说,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临终遗嘱在许多作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有产者去世,宣读遗嘱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在葬礼之后举行,家庭全体成员到场。律师当众打开遗嘱,宣读内容。就在那朗朗宣读声中,多少人的命运起了变化。有关遗嘱的描写在英国19世纪文学中频频出现:丢失的遗嘱、藏匿的遗嘱、篡改的遗嘱、伪造的遗嘱、有争议的遗嘱……它们往往是故事情节的推动力、人物命运转折的契机、现实利益冲突的聚合点。在《傲慢与偏见》中,要不是班奈特先生的地产根据遗嘱的附加条件限定传给男性继承人,那么患有“嫁女儿癖”的班奈特太太的喜剧形象就树立不起来,《傲慢与偏见》也不成其为《傲慢与偏见》了。同样,《简爱》全部事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老罗彻斯特先生要把全部产业完整地传给长子的决定。这样,他的次子,小说中的爱德华·罗彻斯特先生,便不得不为三万英镑而奔赴西印度群岛去娶“疯女人”伯莎·梅森为妻。简·爱出走与奋斗的“正剧”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得以演出。甚至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呼啸山庄》的布局也与遗嘱及继承权有密切关系:“画眉田庄”的老林敦先生立嘱规定,如果儿子爱德加没有子嗣,那么“田庄”就要传给女儿伊莎贝拉及其子嗣。希思克利夫正是掌握了这个情况才要娶伊莎贝拉为妻,并通过伊莎贝拉为他生的儿子小林敦而把“田庄”弄到了手。全凭钻遗嘱的空子,希思克利夫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才树立起来。总之,按照许多小说中的描写,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把自己的所有赠给他人似乎是人们的共同心理。甚至连《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那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孤儿约翰尼在死前也还要把自己的几件玩具留给指定的小病友。(第2部第9章)
英国的继承法是很复杂的,并且经历了许多变化。作家不可能像法学家那样掌握其全部复杂的内容,一般都只是借助其基本精神来展开情节、发挥主题。事实上有的作品就在继承法问题上出现疏忽。如《呼啸山庄》中的小林敦病逝时尚未成年,根据法律他没有资格立下遗嘱把“田庄”留给父亲。这也就是说,希思克利夫最终掌握了两处地产、达到复仇目的是没有现实根据的。此外,故事结束的时候,一对年轻人海里顿和小卡蒂结婚后好象当然成了两处产业--“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新主人;而事实上,从法律上严格地说,希思克利夫死前没有立嘱,他的产业应由王国政府没收,一对年轻人除爱情以外将一无所有。可这样的结局不仅违反作者对全书的设计,而且读者从心理上也难以接受。我们只能原谅作者的疏忽而不去过分追究。从来重视细节真实的安东尼·特罗洛普在《奥尔利田庄》中,虽然对围绕地产继承权的纠纷的描写具有心理刻划的深度,却忽略了继承法本身,使其布局整个建立在对法律条文的误解上而贻笑大方。在这方面,应该说乔治·艾略特最为严谨:她为写《激进派费立克斯霍尔特》而特地向当时的一位法学专家费德立克·哈里逊请教有关财产继承法的知识。时至今日,哈里逊的复信总是附在该小说正文的后面,以帮助读者弄清作为全书基石的特兰孙庄园继承权的疑案,这可算是小说中处理遗嘱问题的典范。
总之,文学作品中的临终遗嘱问题常常牵动着英国19世纪小说中那些最常见的主题:财产、家族、人际关系、人生的意义、时间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如果把这些描写横向联系起来,就会拼成一个新的故事,一个关于立嘱权和继承权的“寓言”。这个“寓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立嘱权是对立嘱人的“诅咒”,继承权是继承人的“陷阱”以及权力的否定,即“超越”。
一、立嘱权是对立嘱人的“诅咒”
关于临终遗嘱所体现的权力的性质,英国19世纪的许多作家都有描写,而且各具特色。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玛契》第35章描写了宣读费瑟斯通先生遗嘱的前前后后,是富有代表性的一例。无子嗣的老费瑟斯通的三亲六戚都抱着希望在他的床前尽孝,但又感到老头的心思难以捉摸。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戒备。作者冷冷地指出,当初诺亚方舟中各种动物看着方舟上那有限的饲料,大概就是这种心情。老费瑟斯通下葬之后,遗嘱终于被公开了。原来这狡猾的老头耍弄了大家,白白吊他们的胃口,骗得他们在床前尽孝,实际上却分文没有留给他们。受打击最重的是老头的外甥费莱德·文西。费莱德从小不长进,一心指望继承他姨夫的产业。在那一字千金的时刻,他的命运大起大落。根据宣读的第一份遗嘱,他的名下有一万英镑。弗莱德喜形于色,眼看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债务、婚姻、前途。可是紧接着宣布第二份遗嘱,弗莱德分文未得。第二天早上,父亲要他拿主意,决定谋生之路,“弗莱德说不上来。二十四小时以前,他还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了”(第36章)。老头几易其嘱,别人的一辈子就随之变了样。艾略特写道:“老费瑟斯通不是哈巴贡……他爱钱,但他舍得花钱满足自己的特殊嗜好。他尤其喜欢以钱为手段叫众人尝尝他的厉害。”(第32章)作者在这里把话说穿了:立嘱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他人的命运并从中得到满足。面对一个个准继承人的沮丧,我们好像听见了老费瑟斯通隔着坟墓的笑声。这是老年人对青年人的整治,只因他们年轻;这是死人对活人的报复,只因他们还活着。在《米德尔玛契》里,还有一个遗嘱的故事与老费瑟斯通的故事遥相呼应。当费瑟斯通的殡葬队伍在庄园的大道上经过时,教区长夫人兼罗威克庄园的女主人多萝西亚站在窗前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完全没想到自己与那些送葬人的联系。而实际上她跟他们一样都是受立嘱人摆布的对象。她的年长体弱而又多疑的丈夫紧接着就在自己的遗嘱里为她设下了侮辱性的圈套。艾略特把《米德尔玛契》中的这一卷定名为“死人的手”。
如果“死人的手”可以概括临终遗嘱的本质,那么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司卡伯罗一家》中的立嘱人创造性地处理继承权的各种应变的方案,则简直使这只死手达到了复活的地步。这部小说的标题本身就具有讽刺性,因为司卡伯罗先生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家庭或亲属而只有“继承人”。他为排除挥霍成性、债台高筑的大儿子的继承权竟宣布其为非婚生子,不惜羞辱自己已故的夫人。这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控制未来,而且还要改变过去,修改历史。在打发掉大儿子的诸多债主以后,司卡伯罗先生又宣布了一项秘密婚约,从而恢复了长子的继承权而排除了心术不良的次子;虽然他明知道,这样下去,他苦心经营的一片产业将彻底败在长子手里。如同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在战场上大叫:“一匹马!一匹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他为赢得战争宁肯以自己的王国换一匹马,而那场战争本身却正是为王位而打的。同样,在司卡伯罗先生这里,权力欲,摆布他人命运所带来的满足已上升为目的,而产业的分配则退居次要地位--作为立嘱人,他正走向自己的反面。这种本末倒置表明,立嘱人的权力欲无限膨胀,导致立嘱对象的被否定:权力是一切,产业的存亡无关紧要。
艾略特、特罗洛普的精彩篇章都揭示出立嘱的权力对立嘱人的腐蚀,使他们成为人格化的遗嘱,家庭里的暴君。狄更斯则把这个“寓言”更向前推进一步,把立嘱人看成他本身权力的受害者、一个因为拥有这种权力而受到诅咒的人。
狄更斯第一次访美归来后写出的《马丁·瞿述伟》反映了他的小说艺术的一个变化,从早期松散的流浪汉体而转向布局严密。《马丁·瞿述伟》扣紧一个中心观念--无所不在的私欲。为了揭示这私欲,即“最普遍的恶”的方方面面,狄更斯牢记总的目的与总的设计而处处约束自己,不让情节像分期连载时那样漫延开去。书中对私欲的谴责到处可见,有时采用叙事人的口气,有时通过人物的感叹。约纳斯·瞿述伟为遗产早日到手对父亲安东尼下毒手,接着又杀人灭口,最后自己落入法网,这是全书中最阴暗的部分。伪善者裴克斯匿贪图老马丁·瞿述伟的财产而耍尽阴谋诡计。他既是喜剧化的丑角,又是私欲的一种凶恶的表现。书中著名的喜剧角色,贪杯的看护妇甘泼太太,转述假想中的哈丽恩太太的话而滔滔不绝地自卖自夸,也是私欲的一种滑稽化的表现。至于美利坚共和国的“伊甸园”,那更是一个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的乐园。总之,《马丁·瞿述伟》呈现了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图景,有时采取正剧或悲剧、有时采取喜剧或闹剧的形式,间或还流于通俗情节剧的程式。
不过,私欲的面面观还是在书中中心人物老马丁·瞿述伟的故事中展现得最充分。
《马丁·瞿述伟》全名很长:“马丁·瞿述伟的生平经历、他的亲戚、朋友和仇敌。包括他的意愿,他的道路;他所作所为,他未作未为,均照实纪录;还有,谁继承了传世餐具,谁为银匙而至,谁为木勺而来。凡此种种构成瞿述伟家开门启户的全套钥匙。”①这个陈述乍看起来似有些故弄玄虚,实际上精辟地切入了全书的核心问题,即财产继承关系在人们之间自然关系上的投影。老马丁处在众多的自然关系当中,包括他的兄弟、他的侄子、他的孙子、他的表弟、他的外甥,加上其他沾亲带故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配偶、子女等等。可是,在他们的眼里,老马丁不是人,而只是一份人格化的遗嘱。反过来在老马丁的眼里,他们也不是人而只是一只只伸过来的手。小说中有关“家庭聚会”的场面都是富有深意的。如老马丁病在路上,他的众亲朋都赶来,为遗嘱而争吵不休。老马丁乘他们不备,拖着病体悄悄溜走了,活像个在逃的罪犯。他深感自己已被上帝唾弃和诅咒,绝望地说:“我这人已经身遭天谴了。”②
通过老马丁·瞿述伟颠沛流浪、充满焦虑的一生,狄更斯把立嘱人具有的支配财产、亦即支配他人命运的权力看作一种“诅咒”、一种“天谴”、一种“祸根”、一种“罪孽”。立嘱人被上帝诅咒固然在于他本人被腐蚀,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权力本身对他人的普遍腐蚀。“凡是伺侯过我的人,”老马丁说,“我都已完全败坏了他们的心术,改变了他们的本性,让他们见钱眼开,生出了许多觊觎之心,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就连亲戚本家,只要跟他们一块儿呆几天,就能让他们骨肉无情,同室操戈,……”(上册第61页)为了射开那一只一只伸过来的手,也为了避免自己对他人的腐蚀,老马丁到处流浪。他第一次出现是在旅途中病倒在一间客栈里,再次出现是在伦敦的托节斯公寓里跟裴克斯匿践约;他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人家问他住处,他说那等于白问,因为他“没有固定住处”。老马丁主观上拒别人于千里之外,客观上自己却落得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在老马丁的形象中,矛盾转化,立嘱人的权力使他成为受迫害者,一个遭天惩的、四处流浪的逃亡者。
《马丁·瞿述伟》全书突出家庭关系,第一章中那篇常常被读者忽略的家谱是理解全书的关键。作者用戏谑的口吻为瞿述伟家庭续家谱,一直上溯到世上第一家--亚当与夏娃--突出强调这个古老的家庭中历来就有杀人凶手和流亡者,这当然是指亚当与夏娃的长子,杀了弟弟亚伯的该隐。《马丁·瞿述伟》中有多处借用《圣经》的隐喻:约纳斯杀人前所做的“末日审判”的梦;故事收场时“末日审判”式的格局;美国之旅的插曲被冠以“伊甸园”的美名等。此外,伪善者裴克斯匿和滑稽丑角甘泼太太也都曾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歪曲引用《圣经》。《马丁·瞿述伟》是狄更斯作品中引用或借用《圣经》最多的一部,其总的效果是把瞿述伟家庭和亚当夏娃家庭联系起来,而这就确认了亚当夏娃家庭中该隐式的角色--杀人凶手和流浪者--在瞿述伟家庭中的相应存在。该隐杀了弟弟亚伯,自己被上帝诅咒和放逐,从此在伊甸园以东的挪得之地流亡。老马丁虽未杀人,但他作为立嘱人身不由已地既腐蚀亲人又排斥亲人,是一种象征性的杀亲。他把“诅咒”一词用在自己身上,又自称不得不“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恰恰是上帝对该隐的诅咒与判决。这些联想与暗示指向全书的核心:老马丁·瞿述伟身上有该隐的影子。一旦确立这个联系,贯穿《马丁·瞿述伟》全书的临终遗嘱的主题就明朗化了:作为立嘱人,老马丁是该隐式的人。这个联系不是对具体人物形象的道德评价,而是作者对立嘱人的命运及其权力性质的最终艺术概括:“诅咒”。
二、“解释”的陷阱
遗嘱有了,下一个环节是遗嘱的解释。这个解释颇费心智,不同的解释能够赋予遗嘱以不同的含义,而后者又直接影响到不同人的不同利益。因此,遗产继承权的斗争首先是遗嘱解释权的斗争。正如《马丁·瞿述伟》中的老马丁说的:“让我操了一辈子心,受了一辈子罪,等我死后,就又该引起没完没了的纠纷,造成难以消灭的恶感。向来都是这样。有钱的人一进坟墓,就不一定引起什么样的热闹官司……”(上册第63页)老马丁的一席话说出了临终遗嘱的又一个方面:围绕遗嘱的解释之争。
早在奥斯丁的《理智与感伤》③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解释”的喜剧形式。庄园主米德尔顿家大少奶奶的独白是解释遗嘱的一篇精妙的文章。她的老公公遗言要他们夫妇尽量“帮助”他们年轻的继母和他们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妹,那么这个“帮助”应该怎样理解呢?从给三个姐妹各送三千镑说起,到各送五百镑,到给她们的母亲年进一百镑的年金,到偶尔给个五十镑“意思意思”,最后降为帮助她们搬出庄园另找住处(这是大少奶奶最关心的)和年底送点野味过去,总之就是把她们娘儿四个扫地出门。大少奶奶对她公公的遗嘱独特解释就这样决定了这娘儿四个的命运。幸好米德尔顿夫人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破译”了公公的遗嘱,说服了丈夫,也说服了自己。她说:“我认为你父亲根本没有让你资助她们的意思。我敢说,他所谓的帮助,不过是让你合情合理地帮点忙,比方替她们找座舒适的小房子啦,帮她们搬搬东西啦,等季节到了给他们送点鲜鱼野味啦,等等,我敢以性命担保,他没有别的意思。”(第6-8页)
可惜不是所有的遗嘱争执都像米德尔顿夫人处理她公公的遗言那样三言两语就能断清的。颇具奥斯丁风格的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成名之作《巴彻斯特养老院》也是从一份遗嘱争执切入主题的,以教会的财产争执来揶揄人性的弱点。巴彻斯特主教区管辖下的“海拉姆养老院”是1434年根据约翰海拉姆先生的遗嘱设定的。这位羊毛商立嘱规定,将他死在里面的那所房子和附近的某些牧场和土地都捐出来,养活十二位衰老的梳羊毛人。他还规定建造一所养老院作为他们的住处,附建一幢院长住宅,院长也从同一份地产收入中支取酬金。近四百年来,这个养老院就这么维持着,由于收成不好,历届院长勉强维持住十二位老人的生计,自己只得一所空房。可是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工业的突飞猛进,薄田上建筑物拔地而起,原地产的价值成倍地增加。然而,十二位老人依旧每人每天按原来的遗嘱得一先令二便士,而院长的俸禄则长到每年80英镑。在19世纪社会改革的浪潮里,当英国教会的特权受到攻击时,养老院受施人和代管人待遇上的这种悬殊便成了“改革派”手里现成的一发炮弹。小小的巴彻斯特教区的所谓改革派和所谓保守派围绕着四百年前的一份遗嘱而斗得不可开交。其中的关键是要确定四百年来遗嘱执行情况是否合乎立嘱人的“原意”。于是好多份约翰·海拉姆的遗嘱、院长的细帐、租约、总帐以及一切可以抄录的和某些不能抄录的文件的副本全被找了出来。然而,要审查执行情况是否合乎遗嘱的“原意”谈何容易!首先要确定何为“原意”,而要确定何为“原意”则又引出新的问题--“谁有权决定呢?”④是遗嘱的执行人,教区的主教吗?他年事已高,从不过问教区事务,甚至根本没有看过遗嘱本文,35年来,他只是凭着自己作为主教的地位而指派养老院院长的人选。是地产的经营者恰德威克先生吗?他们家族祖祖辈辈都经营这片地产,视其为自己的一份正当收入,别无其他。是伦敦的大律师吗?按照大律师亚伯拉罕爵士的法律程序,改革派是无的放矢,因为遗嘱措辞含混,现在根本无法确定诉讼对象。于是遗嘱的“解释”问题无限复杂化,双方的代表人物热烈投入论争,倒把主要问题--养老院院长的薪奉--放在一边。养老院院长哈丁先生,这个善良而又胆小怕事的老头儿,在两派争执不下的混乱中当了逃兵。他顾不上维护教会的传统特权,“只凭着出自衷心的信念”(第213页)毅然决定辞去养老院院长的职务,放弃这个肥缺,以个人的良知解决了纠缠不清的遗嘱“解释权”问题。作者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天才在于他把关于教会肥缺的一场争执变成绝妙的喜剧,勾勒出了“改革派”堂吉诃德式的可笑行径,又暴露了教士黑袍底下掩藏的凡人凡心,既有揶揄,又有理解。在这里,遗嘱解释权的矛盾采取喜剧的形式出现,它的潜在的威胁都被喜剧气氛冲淡了。《理智与感伤》里那份措词含混不清的遗嘱被儿媳妇巧妙地解释掉了;在《巴彻斯特养老院》里,解释被淹没在经院式的思辨里。而在另一些作品里,遗嘱的解释之争却充满了险情。
在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中,贾迪斯控告贾迪斯的遗嘱争执案已拖了几十年,跨了几代人,但始终看不见结案的苗头。小说的女主人公艾斯特是这样描写寻求“解释”的情景:“那些自称参与该案的律师共有二十三位,可是他们对案情似乎并不比我了解多少,他们跟大法官交谈,彼此争辩解释,有人说应该这么办,另一些人又说应该那么办,有人开玩笑地建议翻阅大卷的口供书,这马上引起更大的骚动和笑声,那些与本案有关的人士都懒洋洋的,把审理这案子当作一个消遣,因此谁也没法使这个案子产生任何结果。过了一小时左右,许多人作了发言,而又都被打断了,于是本案便像肯吉先生所说的那样又是‘暂毋庸议’了,在书记还没有把全部公文运到庭上的时候,打开的公文又一捆捆地包起来了。”⑤
在狄更斯的笔下,我们看到,贾迪斯控告贾迪斯一案正在发生奇异的变化。它不仅体现了法律的拖延,或律师的贪婪,而且在这桩案件无休无止的运作中,解释的过程自我膨胀。它本来是确定继承权的手段,却异化为它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纪念碑、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一种没有止境的追求、一桌不散的宴席、一代一代律师磨牙练武的场地、一个以原告和被告为原料的机器、或以活人为祭品的法律圣殿,高悬着的遗产转化为对整个家庭的“诅咒”。(第24章)最典型的例子是年轻的理查德·卡逊先生的遭遇。他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于贾迪斯案件最终的“解释”,当求“解释”的诉讼费吞食了全部遗产、达到了对案件本身的否定时,可怜的理查德当庭口吐鲜血,后来悲惨地死去。如果说立遗嘱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诅咒,那么在《荒凉山庄》中,求解释的过程则像个巨大的陷阱,等着捕捉和吞食那些对它抱幻想的活人。
《理智与感伤》中的米德尔顿夫人轻而易举地掌握了遗嘱的解释权;狄更斯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小杜立特》则表现了“解释”权如同立嘱权一样,给这种权力的代表者带来了威胁与危害。
《小杜立特》情节丰富,布局复杂,而且各条线索好像都牵到一个神秘的中心:杜立特先生到底欠了谁家的债而使全家跟他一起住进牢房?有钱的克兰纳夫人为什么要接济出生在牢房里的少女杜立特?杀人嫌疑犯布兰杜阿为什么总在克兰纳住宅附近出没?愤世嫉俗的单身女人韦德小姐跟声名狼藉的布兰杜阿有什么秘密交道?克兰纳宅的老管家何以敢跟夫人那么放肆无礼?亚瑟在父亲客死他乡以后,回到英国去探索什么秘密?所有这些盘根错结的线索,最终结成一个大的疑团,即克兰纳先生临终时给他夫人留下的三个字D.N.F.,即“永志不忘”的缩写。这三个字指向多年前的一份遗嘱。原来克兰纳先生,即亚瑟的生父,在与现夫人结婚前曾与一位歌女有过一段恋情,生下了亚瑟。他的叔叔吉尔伯特行使家长权力,拆散了这对情人,把孩子强行交给克兰纳夫人作为自己的儿子养育。后来歌女精神失常,悲惨地死去,而亚瑟在严厉养母的管教下长大,成人后便随郁郁不乐的父亲去中国经商。吉尔伯特老人死前动了侧隐之心,在自己的遗嘱里规定拨出一千基尼(基尼价格略高于英镑)给那歌女,另一千基尼给曾保护过歌女的乐师弗德里克·杜立特的后代,即故事中的小杜立特。这都是上一代人的事情,亚瑟并不知情,小杜立特一家如果得到这一千基尼就不至于被囚在马舍赛债务人监狱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然而当家作主的克兰纳夫人没有执行遗嘱的这一部分规定,事情就这样被拖了下来。一晃二十多年,她丈夫临终时“永志不忘”的遗言是提醒克兰纳夫人履行已故叔父的遗嘱,向杜立特一家进行赔偿。但克兰纳夫人几十年来的仇恨未解,对这几个字另有解释:“这句话对我来说意味着不忘他们的罪过,以及我代行惩罚的权力。”⑥当亚瑟带着父亲的遗言从国外归来向她追问根底时,克兰纳夫人怕事情暴露,便指使老管家销毁吉尔伯特先生的遗嘱,但是管家只是把它转移了。这份遗嘱转手多次,后落到杀人嫌疑犯布兰杜阿手里,成了他向克兰纳夫人进行讹诈的凭据。克兰纳夫人擅自行使上帝的职能,凭着自己对遗嘱的解释而眼睁睁地惩罚无辜者,听任小杜立特一家在狱中受煎熬。然而她这样滥用解释权也惩罚了自己,招致了对自己的诅咒。她下肢瘫痪,十多年不离自己那阴森的住房,犹如坐牢。亚瑟相隔20年回国后立刻直觉到母亲(实为义母)的状况与狱中的杜立特有着一种奇特的类似。他仿佛听见母亲的低语:“他在狱中枯萎,我在家里凋零,正义是铁面无情的……”(第542页)克兰纳夫人为自己行使的解释权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三、超越:对权力的否定
从题材的角度看,许多19世纪小说可以说都是围绕如何满足遗嘱的条件而展开情节的。有的是喜剧性的,如《傲慢与偏见》中的那些可爱的少女都圆满地结了婚,不合理的遗嘱条件没有殃及她们。作者巧妙地绕开了矛盾,把合法的继承人柯林斯先生处理成丑角,从而冲淡了遗嘱的威胁。狄更斯早期的《尼古拉斯·尼克尔比》和《奥利弗·退斯特》也是紧紧围绕遗嘱的条件而展开,紧张而热闹。譬如二者都借用了通俗情节剧中“失散的继承人”的套式。小奥利弗的生父立嘱排除其长子蒙克斯的继承权,指定其非婚生子小奥利弗为其继承人,唯一条件是他不得触犯法网。这就是为什么受雇于蒙克斯的窝主发金千方百计想逼小奥利弗入伙行窃,而小奥利弗始终保持清白的原因。他最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有产阶级社会。这类作品确实是一个矛盾的复合,它们即对现存制度提出挑战,同时又在遗嘱问题上默认财产的神圣性,因此还谈不上“超越”。
另有一类作品便在遗嘱问题上,表现了以个人的道德情操超越遗嘱祸害的精神。《荒凉山庄》中的贾迪斯先生洁身自好,与那拖了三代的倒霉的遗嘱诉讼案不搭界,因而内心清静不受诉讼的干扰。而那些盲目寄希望于遗嘱的人们,纷纷堕入陷阱,死的死,疯的疯。这样,对遗嘱的不同态度--是服从还是超越--便成了塑造性格、展示价值观和人格力量的手段。《米德尔玛契》中的女主人公多萝西亚小姐就是一个超越的例子。她出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而嫁给了伪学者卡索朋,把自己无条件地献给他和他那根本不存在的宏伟研究著述,同时也成了他的财产的当然继承人。她那个内心虚弱而又小器多疑的男人企图以自己的一份遗嘱把年轻美貌的妻子紧紧控制住,于是在遗嘱中规定多萝西亚不得改嫁某某,否则要放弃对亡夫财产的继承权。除了财产方面的限制以外,这份遗嘱的恶毒之处还在于它的措辞本身就是对多萝西亚的指控、缺席审判和定罪,似乎她真的与某某有私情。这样一份完全可以使多萝西亚从精神到行动都瘫痪下去的临终遗嘱,后来一旦公布,反倒使多萝西亚认识了卡索朋的真面目和自己的糊涂与盲目,她也终于下决心不顾哗然的舆论、更不顾遗产的得失而嫁给了她理应回避的年轻美貌的拉迪斯劳先生。这是英国19世纪小说中围绕对待遗嘱态度而塑造性格的一个典范,也是个人道德情操超越遗嘱之上、摆脱“死人的手”的一个精彩的例子。此外,前面提到的弗莱德文西,跟《荒凉山庄》中的理查德·卡逊一样,本来也是把自己的未来押在遗嘱上。所不同的是,他有幸得到了一个好妻子。玛丽·加思帮助弗莱德放下了绅士架子,学习做农活儿,经营管理他本来要继承的庄园。是女性的引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挽救了弗莱德,使他避免了理查德·卡逊那样的命运。乔治·艾略特在她的作品里总是不断地思考客观环境的决定性与主观意志在个人命运中的辩证关系,而她这方面的思考正是通过遗嘱的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外,《巴彻斯特养老院》中的哈丁先生出于老实懦弱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在保卫教会财产的斗争中当了逃兵,是一种喜剧性的“超越”。
然而,穷尽了临终遗嘱题材多方面潜力的还是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作为狄更斯最后一部大部头社会题材的小说,从头到尾围绕遗嘱展开故事,简直包容了遗嘱的各个方面:“诅咒”、“陷阱”和“超越”。当时曾有人对书中的描写提出怀疑。狄更斯在“跋”里写道:“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件‘遗嘱案件’比这本书中所想象的要离奇得多。专司审查遗嘱的大主教法庭办公处的大楼里,各种案例堆积如山,那些立遗嘱者写下遗嘱,又加以更改,前后矛盾,遗嘱被藏起来,忘掉,声明作废,未声明作废,每个人写下的遗嘱都比哈蒙监牢里的老哈蒙先生写下的要多得多。”⑦显而易见,狄更斯对遗嘱问题的普遍性是深有感触的。
《我们共同的朋友》一开头就出现有遗嘱而无继承人的奇特局面。靠处理城市垃极发财的守财奴老哈蒙先生生前深受自己财产的折磨。为了钱,他与女儿决裂,致使其伤心地死去;为了钱,他将儿子赶出家门。对自己的财产在身后的处置,他举棋不定,几易其嘱。像老马丁·瞿述伟一样,老哈蒙也是一个疏离了亲人的被诅咒的立嘱人:“我那自己折磨自己的不幸的父亲写过好多份遗嘱,”约翰·哈蒙后来说(下卷第541页)。老哈蒙的遗嘱在他死后公布:他彻底剥夺了女儿的继承权,又规定儿子约翰·哈蒙必须和父亲指定的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女子结婚,否则全部财产将遗留给他的老管家包芬夫妇。那位被老哈蒙用一纸遗嘱定终身的少女贝拉·威尔弗感到自己被随便处置,像一匹马,一条狗,注定要成为陌生人的财产。这份遗嘱的刁钻条件更是老哈蒙对不顺他心的儿子的惩罚。约翰·哈蒙如服从其侮辱性的条件便会贻笑大方,就不会成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可是故事的整个气氛和情绪又使读者期待男女主人公结婚并继承财产。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不致损坏约翰·哈蒙的形象呢?故事开始时,局面好像僵住了。但随着约翰·哈蒙的失踪并被误认为已经死去,局面又活了起来。他隐名埋姓,以穷秘书的低贱身份出现,并结识了遗嘱中指定给自己的姑娘贝拉。姑娘在完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与他相识、相爱、定情。这样的设计既符合遗嘱条款的规定、满足了故事的需要,同时又开辟了空间以展开人物性格。约翰·哈蒙与贝拉·威尔弗都经受了考验:宁舍遗产而取爱情。这样,这一对男女主人公躲过了继承权的陷阱,又体体面面地得到了遗产,既满足了遗嘱“解释”又达到了“超越”。
为突出“超越”的主题,狄更斯甚至不惜画蛇添足,在老哈蒙的遗嘱上继续大作文章,让老哈蒙留下不是一份而是三份遗嘱:第一份规定了对儿子的侮辱性条件;第二份规定把全部财产赠送王国政府;最后的一份,根据法律也是唯一有效的一份遗嘱,索性规定全部财产留给老管家包芬夫妇。人品高尚的包芬夫妇虽然不敢销毁遗嘱,但执意按第一份遗嘱把遗产双手交给约翰·哈蒙夫妇而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所以,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不仅男女主人公超越了遗嘱的影响力,而且连继承权本身也被勾销。约翰·哈蒙与贝拉·威尔弗跟老哈蒙的遗嘱断绝了一切关系,最后又完全得益于他们的“仙教父”和“仙教母”包芬夫妇慷慨的奉送。以遗嘱问题贯穿始终的《我们共同的朋友》,结束在一片浪漫童话的气氛里,达到了完美的超越。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临终遗嘱的题材在英国19世纪小说里的发挥不仅常常是小说布局的支撑、不仅常常是把握历史社会的切入点,而且还能揭示一些普遍的真理,给人们以启示。
注释:
①这是薛鸿时同志根据本书第一次分期连载时的版本而译出的副标题。有些中译本没有这一副标题,是因为所依据的版本不同。
②查尔斯·狄更斯《马丁·瞿述伟》,叶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46页。文中译文均出自同一中译本,不再另注。
③译本见孙致礼译《姐妹俩》,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凡引《理智与感伤》之译文均出自这一版本。
④安东尼·特罗洛普《巴塞特郡纪事》之一《巴彻斯特养老院》,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3页。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中译本。
⑤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黄邦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上册第448页。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中译本。
⑥《狄更斯小说故事总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568页。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中译文。
⑦查尔斯·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跋,王智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下卷第688页。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中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