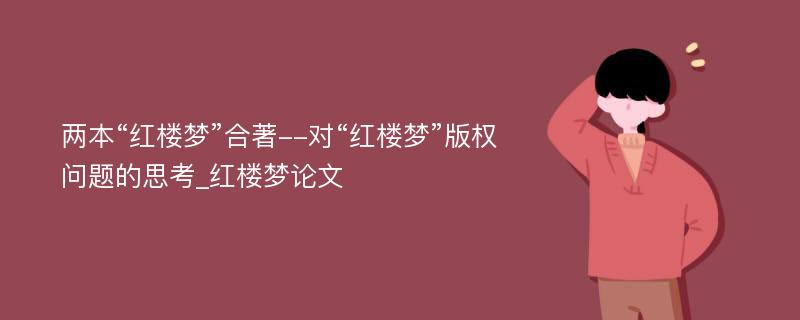
两书合成《红楼梦》——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著作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写作缘起
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的说法已基本成为定论。然而这种雪芹独创《红楼梦》的说法很难解释书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所以七十余年间,不断遇到其他说法的怀疑与否定乃至挑战与抨击。这些说法若以提出的时序排列则为:
第二种,曹雪芹主创脂砚斋参与说。提出此说的代表人物是“新红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俞平伯。早在1921年,俞平伯就说:“我想我们不必全然肯定真作者除了雪芹外没有别人”[1]。到了1964年,俞平伯又说:“我从来不信《红楼梦》出于集体创作;因为不可能同时有好几个曹雪芹,但创作虽非集体,工作却不必限于一人”[2]。
第三种是脂砚斋初创曹雪芹修改润色说。持此说的吴世昌说:“我历年以来曾长久怀疑《红楼梦》的前身——《石头记》或《风月宝鉴》不可能是曹雪芹作品,但还没有工夫详细论证这一重要问题。”“《石头记》的前身是《风月宝鉴》,脂评说得很明白。从棠村序文所透露出来这旧稿的故事素材看,它不是雪芹所作。书中故事有的是曹家在南京时发生的,其时间上限可至1706年和1707年,即曹寅嫁女和康熙南巡之年。这些事情的经过大概由脂砚斋记录,应该是曹氏‘家史’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把家庭中发生的其他事情缩写成小说,曾用《风月宝鉴》和《石头记》等书名。这些旧稿后来由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最后定名《红楼梦》,流传至今”[3]。
第四种就是戴不凡的石兄(曹竹村)草创《红楼》说。他在1979年一年内,连续发表了《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秦可卿晚死考》、《畸笏即曹頫辨》、《曹雪芹“拆迁改建”大观园》等系列文章[4],涉及到《红楼梦》成书过程中许多问题,其核心论点则是:曹雪芹是在《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而《风月宝鉴》旧稿是由化名石兄的曹竹村草创的。
值得一提的是,戴的系列文章,引起了红学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大论战。据《〈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编者的话》的不完全统计,这一论争共发文章近三十篇,而且多是数万字的长文,时间持续了两年。如果不是戴于1980年二月溘逝,这一论战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事后冷静地回顾这场论战,由于戴的结论的尚欠严谨与辩论方式的偏颇,也激起了参与论战者的不无偏颇的理论激情,几乎很少例外地都站在独创说一边,很少考虑在曹雪芹之外是否还有人参与《红楼梦》的创作。然而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这场大辩论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六七年,却给人留下了在曹雪芹之外有没有人再参与《红楼梦》创作的思考。现在,终于由以杜春耕为首的一群自然科学家提出了两书(《石头记》与《风月宝鉴》)合成《红楼》说[5],就是这种思考深入的结果,也是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第五种说法。
严格说来,两书合成说并非最先由杜春耕提出。在戴不凡提出石兄草创说的同时,周绍良就说:“《红楼梦》是有几部内容不同,书名不同的初稿”。“《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的,而《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的。《风月宝鉴》固然是另一部旧稿,而这里所谓《石头记》也是指不包括许多‘戒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与今所见八十回本《石头记》不同的《石头记》。把这两个故事冶于一炉,就成了总名为《红楼梦》的一部大著作。曹雪芹的旧作《风月宝鉴》的下落,就与原来那部《石头记》一起,被熔铸吸收在《红楼梦》中了”[6]。这是最早提出合成说的一篇文章,然而却被当时那场大论战的硝烟淹没了,未能引起红学界的足够重视。杜春耕等人起先并未看到这篇文章,他们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切入《红楼梦》研究,锐敏地觉察到《石头记》与《风月宝鉴》合成的痕迹,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两书合成的证据,这无疑将在红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可能掀起又一次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大讨论。
笔者自己曾是独创说的信奉者,当年也写了《“石兄(石头)说”质疑》的长文与戴不凡辩论[7]。但后来却越来越发生了对曹雪芹独占《红楼梦》创作权的怀疑,因为尽管不断有学人曾从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对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予以合理解释,却仍然难恰人意。年初从哈尔滨“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归来途经北京,应邀参加了《红楼梦》农工研究小组召集的小型座谈会,翌日又与林冠夫、杜春耕作了竟日之谈,获益匪浅。归来后又详细研读了杜春耕的系列文章和其他上述各种说法的代表性论述,再翻检《红楼梦》本文与脂批,经过反复比较,始觉由杜春耕再次明确提出的两书合成说给红学界进一步研究《红楼梦》著作权问题拓展了视野。虽然有些具体观点还不一定为学者与读者所认可,但总体说来却无疑接触到成书过程中的实质问题,为书中许多矛盾找到较合理而又信服的解释,因而笔者愿将自己对此问题的思考写出来以佐杜说。
贾宝玉两个不同的“前身”
贾宝玉有两个“前身”:在《楔子》中是女娲补天时剩下未用的那块顽石,到了故事开头的第1回又变成了警幻仙姑处的神瑛侍者。请看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记载:
……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造,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下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了凡心,也想到那人世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这是一段顽石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后复归青梗峰的完整故事,但到作者申明“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的时候,却变成了这样:
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这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灵河岸上,三山石畔,有绛珠仙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姑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僧道“……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冤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
可以看出,这个神瑛侍者与那块顽石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神话,而且也增出了一个顽石幻形入世的故事里根本没有影儿的绛珠仙草(后既降生为黛玉)。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执笔者想把这两者捏合起来,一是那僧欲“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顽石)夹带于中”,“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二是此蠢物就是经茫茫大士大展幻术后变成扇坠般大小的“通灵宝玉”。不过还没有完全捏合起来,留下了三个破绽:一是究竟将那“蠢物”夹带在“一干风流冤家”中作为一个独立者经历凡尘呢,还是夹带在神瑛侍者身上经历凡尘?从后来的情节发展看是后者,即神瑛侍者脱生为贾宝玉并衔“通灵宝玉”而生,但此处却未交代清楚。二是那块顽石是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的,而神瑛侍者是谁携入红尘的却无明文。三是在执笔者的本意中仍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神瑛侍者入红尘的,但此一僧一道在顽石的故事里“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而后来曾数次出现的这一僧一道却变成了“癞头跣足”的和尚与“跛足蓬头”的道士。尽管脂砚斋在“跛足蓬头”四字旁朱批曰:“此门(处)是幻像”,究竟还是使人纳闷。
后来程高出活字摆印本时,发现了顽石与神瑛各不相干的矛盾,经两次修改才成了程乙本中的如下叙述:
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仙草,十分娇娜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始得久延岁月。……
这样一改,算是将顽石与神瑛合二而一了,即神瑛侍者就是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但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新矛盾。既顽石与神瑛是一而非二,那么在石头故事里顽石是被僧道缩成“通灵宝玉”下凡入世的,到了神瑛的故事里却又因凡心偶炽而入红尘,岂非两次下凡?神瑛侍者就是后来的贾宝玉,而贾宝玉又是衔着“通灵宝玉”(即顽石)而降生的,这岂不又成了神瑛含着自己脱生人世?这如何解释得通?况且如上所述的那些破绽不仅照样存在,而且越来越复杂了。
对这些矛盾(其实矛盾还要多得多)红学家各有自己的解释:独创论者认为是曹雪芹多次修改未能统一的结果,但自己修改自己的作品,为什么费了十年时间却不能统一,他为什么又设计了这两个神话给自己制造麻烦呢,删掉其中一个不就完事了?主独创论者说是脂砚斋参与并干预了创作,二人意见不一,争执不下。不错,雪芹与脂砚在创作过程中是有争议的,但唯独对这两个神话没有争议,而且是企图将二者弥合起来障人耳目的,这在下文还要论述。修改论者说是石兄(曹竹村)或脂砚在初创过程中留下的矛盾,雪芹巧手新裁时尚未来得及统一。但这又留下了与独创说同样的问题,即竹村与脂砚在初创时为什么要自找麻烦?看来较比合情合理的解释还是两书合成说。
《红楼梦》原有两部内容不同的旧稿
《红楼梦》的五个书名在第1回中原本就写清了:“(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诗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8]。这里有五个书名和五个人名。俞平伯认为五个人其中有三个(情僧、吴玉峰、孔梅溪)是虚的,只有脂砚斋与曹雪芹实有其人,其实也未必。如甲戌本第13回第3页正面就有署名“梅溪”的一条朱眉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我疑心这个梅溪即孔梅溪。但是,到到了甲戌本《凡例·〈红楼梦〉旨义》中只剩下三个书名了:“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作梦,梦中又有曲名《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事,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这里在五个书名中只提三个,不提《情僧录》,否定了《金陵十二钗》,只承认《红楼梦》、《风月宝鉴》与《石头记》,而且明确指出《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红楼梦》自不必说,而《风月宝鉴》与《石头记》是内容截然不同的。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这个《凡例》是后人伪加的[9],《红楼梦》根本不存在两部内容各不相同的旧稿。那么我们再看看脂批的提示与说明。这里用红学界的惯例,通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各本的所有批语为脂批,需要时才指是脂砚、畸笏等。
在甲戌本上引成书过程指明五种书名的一段眉端有朱批曰:“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段被红学家反复引用的脂批,都以为乃脂砚斋所批,我却以为系在孔梅溪名下更加合适,因为它是“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的批文,脂砚斋有什么理由去声明“故仍因之”呢?关键是“旧有”二字怎么理解。戴不凡、吴世昌等认为是曹雪芹过去曾保存有别人写的一部名曰《风月宝鉴》的小说,雪芹之弟棠村曾为这部小说作序。但是,雪芹既然只是保存者而非创作者,棠村只需写个跋即可,何以会去作序呢?这是明显的常识。所以既然棠村作序,就只能理解“旧有”为曾经创作过。为了更慎重一些,也可以两说并存。不过这个事实本身却至少证明《风月宝鉴》的确是《红楼梦》成书过程中实际存在且与《石头记》内容不同的书。何以见得呢?再请看脂批。
甲戌本中有不少“非《石头记》正文”之类的批语。第4回第8页贾雨村乱判葫芦案一段眉端有朱批曰:“盖宝钗一家不得不细写者。若另起头绪,则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呆凡人命一事,且又带叙出英莲一向之行踪并以后之归结。是以故意戏用葫芦僧乱判等字样,撰成半回,略一解顾,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又注冯家一笔更妥,可见冯家正不为人命,实赖此获利耳。故用乱判二字为题,虽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辞耳。但其意实欲出宝钗,不得不做此穿插。故云此等皆非《石头记》之正文。”这儿的《石头记》,当然不是指与《红楼梦》同书异名的《石头记》,而是指《红楼梦》初稿之一与今见之120回内容不尽相同的《石头记》。既然“非《石头记》正文”,非《风月宝鉴》而何?当然,为了不至以臆取义,也可理解为“乱判”一段非《石头记》正文,欲出宝钗才是正文,那就不存在另一部书了。可是再请看第5回“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过的鸳枕”正文旁朱批曰:“一路设譬之文,迥非《石头记》大笔所屑,别有他属,余所不知。”很明显,此曰《石头记》者,显指《红楼梦》初稿之一的《石头记》,“别有他属”意即出自另一部与《石头记》内容、风格都不尽相同的书稿,虽未指明,却系《风月宝鉴》无疑。至于“余所不知”,只能是卖关子的话。接着在同页“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正文旁朱批曰:“此梦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梦,又用秦氏出梦,竟不知立意何属,唯批书人知之”。眉端又有两段墨批:“何处睡卧不可入梦,而必用到秦氏房中,其意我亦知之矣。”“我亦知之,岂独批书人”。这儿的“批书人”,显然指知道创作内情的脂砚斋。与上批合观,显指秦氏之文出自《风月宝鉴》而非《石头记》。到了警幻仙子出场的那段赋,其眉端又朱批曰:“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指宝玉与警幻仙子)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见其妙。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所谓“此书《凡例》”,若指甲戌本前所列之《凡例》,却并无“本无赞赋闲文”之则,那么只能是初稿《石头记》的凡例了。但今见之所有脂评本及程高本,均无此凡例。检甲戌本被脂砚斋称为《楔子》,即叙顽石幻形入世后复归青梗峰遇见空空道人,向空空道人叙述《石头记》好处时批评历来野史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或可反证原《石头记》中有“无赞赋闲文”的《凡例》,不然即直指上引《楔子》中语。无论何属,这段批评显出自知情者,则非脂砚斋莫可。脂砚既指明《石头记》原“无赞赋闲文”,可知警幻仙子赋原非《石头记》笔墨,应出自《风月宝鉴》。且脂砚对此赋持否定态度,正与前之“非《石头记》大笔所屑”批文一意贯穿。
或云:脂砚诸批只能证明上述诸文非原稿所有,乃雪芹在修改过程中增加的,却并不能证明《风月宝鉴》是与《石头记》并存的另一部内容不同的旧稿。脂砚明指“别有他属”,第12回癞头和尚送给贾瑞诊病的那面镜子又明明白白地写着“风月宝鉴”四字,若还否定《风月宝鉴》的存在,岂不是视而不见?或云:《风月宝鉴》与《石头记》虽是两部内容不同的书稿,但都出自雪芹之手,是《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所造成的。是否如此呢?还是让脂砚先生来回答吧。庚辰本第39回第892页贾母称刘姥姥为“老亲家”下有双行夹批曰:“神妙之极!看官至此,必愁贾母以何相称,谁知公然曰‘老亲家’,何等现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云作者心中编出,余断断不信。何也?盖编得出者,断不能有这等情理。”又第17—18回第386页写元春与贾母等人相见场面处朱眉批曰:“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第77回第1906页写王夫人命搜检宝玉房中之物一段批曰:“此亦余旧日目睹亲问(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旧(臼)相对。”凡此类之批在书中不胜枚举,这分明是说批文所指之正文皆出《石头记》原作者之手,非雪芹之得于闻传靠别人提供素材者所能写出来的(后文还要论及)。脂砚一面不断指出某段某事非《石头记》之正文,另一面又不断指出其某段某事非雪芹所能写出,这说明哪些出自《石头记》,哪些出自《风月宝鉴》,他是一目了然的。也证明《红楼梦》原有两部内容不同的旧稿,《石头记》作者尚待考订,《风月宝鉴》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由曹雪芹将自己原写的《风月宝鉴》与别人的《石头记》经过巧手新裁合成的。
《红楼梦》中的“风月”旧影
其实明显的“风月”故事是不难辨认的,如秦可卿与贾珍的故事,凤姐与贾瑞的故事,贾琏与尤二,多姑娘与鲍二家的故事,司棋与潘又安的故事,还有薛蟠、秦钟、妙玉、尤三、香怜、玉爱、傻大姐等人的故事。这些早有学者指出,不必细说。还有一些“风月”故事,在《风月宝鉴》中是可能大写特写的,但进入《红楼梦》以后,却删削得只剩下一束淡得几乎令人难于辨认的影子。这里首先要提到珍大奶奶尤氏和她的公公贾敬。这不是我的发现,先后提起此事的是俞曲园、俞平伯和我的先师朱宝昌[10]。也不是故作惊人之笔,而是有据可查的。第5回《红楼梦》曲第13支《好事终》曰:“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宵秉月貌[2],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甲戌本眉端有墨批曰:“敬老悟元(玄)以后,珍、蓉辈无以管束,肆无忌惮,故此判归咎此公。”此批非障人耳目即故意曲解,让珍、蓉掩盖了贾敬之罪过。深知拟书底里,也可能是脂砚斋在“箕裘颓堕皆从敬”句旁朱批“深意,他人不解。”又在“宿孽总因情”句下朱批曰:“是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这实际上是提醒读者不要放过此曲的每一个字,尤其是那个“敬”字。曲中的明言“箕裘颓堕皆从敬”,为什么单只归咎于珍、蓉呢?柳湘莲悔婚时曾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哩。”焦大骂山门时说:“那里承望到如下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在“爬灰的爬灰”句旁有批曰:“珍哥儿”,其实还是让“珍哥儿”的爬灰,掩过了贾敬的爬灰。这是否冤枉了这位老实巴脚的珍大奶奶?那么再请看第74回后半“避嫌隙杜绝宁国府”吧。抄检大观园时在惜春丫头入画那里查到了男人靴袜银锞等物,尤氏已证明是贾珍送给入画哥哥的,既奸脏,亦非盗脏,“嫌隙”本已冰消。可是惜春却对尤氏说:“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排上了。”尤氏不由得问道:“谁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惜春冷笑道:“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还有一句话,我不怕你恼,好歹自有公论,又何必去问人。古人说得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况且你我二人之间,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有事别累我。”当时议论的问题非奸即盗,那么惜春话里的潜台词是什么还不明白吗?看来“爬灰的爬灰”,是从贾敬与尤氏就开始了的,这就是“箕裘颓堕皆从敬”的确切含义。无怪乎在“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未删之笔”里,尤氏只是装病以泄愤懑而未大闹,因为她也有把柄在珍大爷手里。再联系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的题文,方知包括钗、黛在内的“群芳”,只是尤氏这个“独艳”的衬托,今日的半老徐娘,当年也是风流过的。
除了尤氏之外,贾宝玉这个“风流种子”也难逃“风月”的干系。就在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句话旁,甲戌本有墨批曰:“宝兄在内”,眉端有朱批曰:“一部纰搜淫邪之处,恰在焦大口中揭明。”在宝玉问凤“什么是爬灰”的眉端,又有墨批曰:“反他来问,真邪?假邪?欺人邪?自欺邪?然天下人不易瞒也!呵呵!”这几段批语虽未署名,却非脂砚斋莫属。因为直到如今,红学家们还未发现第二个如脂砚斋那样熟悉《红楼梦》创作过程的。“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在现在的《红楼梦》中连影儿也找不到可他却明确指出是“宝兄在内”。那么究竟谁在“养”宝玉这位“小叔子”呢?在现在的《红楼梦》中也很难对上茬。那第三段批语更令人纳闷,难道宝玉还牵扯到“爬灰”一案?如果是真的,第5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时,由可卿引梦,由可卿出梦,警幻仙子又“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阁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世之情景哉?”宝玉也依警幻之嘱,与可卿“未免有阳台巫峡之会,数日来柔情绻缱,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这段描写是真是幻还是以幻影真,就值得斟酌了。不管怎样,贾宝玉是《风月宝鉴》中的人物大约是没有疑义的,而且《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不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那么纯真,这也是大体可以肯定的。进入《红楼梦》之后,贾宝玉在《风月宝鉴》中的行迹与情节大大被削减了,这一点却由脂批透出了消息。就在上引那段脂批,接着“呵呵”同一笔体写下来的就是:“镜来藏春,任求起减,文情文心真旷抱宇宙也。”
另外,贾雨村、薛宝钗也可以肯定是《风月宝鉴》中就有的人物,而且他们的故事不像在《红楼梦》中那样毫无牵连。第1回写贾雨村未得意时吟了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此处用《论语·子罕》待价而沽典与《洞冥记》神女留玉钗而后化白燕飞去典,对表现这个自命不凡,抱负不浅的奸雄当然是极其贴切的。但这只是表面意义,其象征意义又是什么呢?须知《红楼梦》中许多关键地方常常是一语双关的。甲戌本在上下联中间有朱批曰:“表过黛玉,则紧接上宝钗”。初看似乎是这样:价、贾谐音,黛玉在追求宝玉,宝钗热中功名,待时而飞。但一细思,矛盾就出来了。宝钗乃女流,又安能待时而飞?这是一,更重要的是,上联既是人名对,即黛玉对宝玉,下联也应该是人名对才对得工。那么时飞是谁呢?不就是贾雨村的表字么?前文说他“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这儿他又巧妙地将自己的字运用到下联去,岂不是更能表现他的自命不凡,也恰巧与上联隐合,成了人名的工对么?以前批并没有错,错的是读者不知拟书底里,轻轻地放去了。
再看,就在此联的下方中间,又有朱批曰:“前用二玉合传,今用二宝合传,自是书中正眼。”此批如纯系对此联而下,批者何不曰“上用”“下用”而曰“前用”、“今用”?况且如纯系批此联也对不上茬。上联还勉强说得上“二玉(宝玉、黛玉)合传”,下又怎么作说“二宝合传”呢,一个“钗”字就能包括宝玉、宝钗吗,显然说不过去。但脂砚斋并没有错,他每个字都用得很准确。所谓“前用……”云云,是指第1回开头将《石头记》中所写的由青梗峰下无材补天的顽石而幻形入世的甄(真)宝玉与《风月宝鉴》中所写的由警幻仙子处的神瑛侍者下世脱胎的贾(假)宝玉合起来成为一体,故曰“二玉合传”。至于“今用……”云云,才是针对“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是说《风月宝鉴》中有个宝钗,《石头记》中也有个宝×,到了《红楼梦》中,这“二宝”也合为一体了,这才是“二宝合传”的真正含义。我过去曾说过,“二玉(宝玉、黛玉)合传”构成爱情悲剧,“二宝(宝玉、宝钗)合传”构成婚姻悲剧[12]。这个结论对《红楼梦》来说仍可成立,但从成书过程来看就不对了。在《风月宝鉴》中,宝玉、黛玉、宝钗也许曾有过爱情纠葛,但宝钗最终是“待时飞”,嫁给贾雨村了。这对只熟悉《红楼梦》的读者来说也许使宝钗太难堪了,但在《风月宝鉴》中,贾雨村的对联和脂批是这么说的,只能如此。而且在《风月宝鉴》中,贾雨村似乎是个主要人物,不像在《红楼梦》中,只让他去开头结尾,中间只是个影子。需要顺便说及的是,贾芸与林小红,显然是摆开了要大写的架势,不知为什么却将他们的主要情节与故事都砍掉了。
注释:
[1] 《俞平伯和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
[2] 《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评语》,《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3] 《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红楼研究集刊》1979年第1辑。
[4] 分别见《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第3期,《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红楼梦研究集刊》1979年第1辑,《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5] 杜春耕之说详见《中国经济报》1995年10月27日至12月底副刊所载杜之系列文章。
[6]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7] 拙文刊发于《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
[8] 此据甲戌本,庚辰本则删去“吴宝峰题曰《红楼梦》”,“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两句。
[9] 参阅冯其庸:《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10] 参阅俞平伯《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与《朱宝昌诗文选集》之《读〈红楼梦〉随笔》第一则《谁是书中第一美人》。
[11] 庚辰本及其他各脂评本此句无“宵”字。
[12] 参阅拙文:《冰雪招来露泣魂——论薛宝钗》,《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