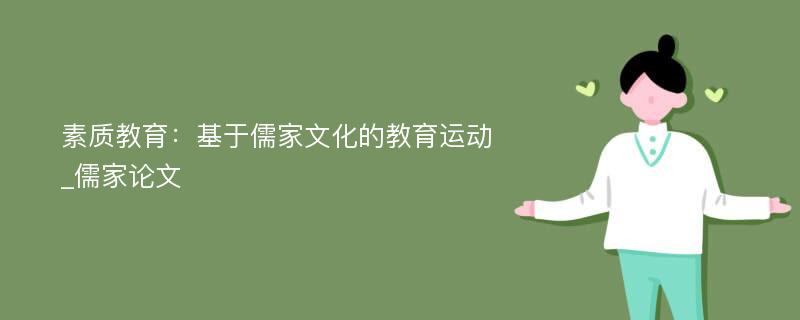
素质教育:以儒学文化为根基的教育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根基论文,素质教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素质教育思想在我国一经提出即逐步演变为一场新兴的教育运动。但这一新兴教育运动本质上也有一个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历史演进过程。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诠释与文化创造活动,它在传递文化的过程中,引导受教育者理解文化、活化文化、超越文化从而达到促进历史文化发展的目的。但教育的文化性演进必须依托于传统,因为“人类的任何发展只能是内在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一旦脱离文化的传统,任何善良的设想与行为都有可能获得相反的结果”(注:高清海《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载《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也只有依循于文化传统进行历史演进性的理念设计,才能获得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从而将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目前有关教育转型研究存在着一种西化倾向,即认为我国的教育理论要真正取得现代突破必须将西方文化作为教育改革的文化动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大力推崇与片面引进。这主要源于对应试教育的个性压抑和人性泯灭的反省与批判。重视个性的培养是西方人本主义教育的典型特色,而中国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恰恰是压抑个性的文化根源,于是许多学者认为传统儒家文化是教育理论现代演进的文化负累,因而认为中国教育的根本改造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方。然而人们在移植的过程中发现西方教育理论精粹一到中国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不能发挥科学的引导作用。其原因主要是忽视了教育理论可行性的文化适应前提,即一种教育理论产生、发展、推行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土壤,要有涵化这种教育理论的文化心理背景,其理论才能真正为人所接受与采纳。但我国至今还没有构建出具有足够融合力的本土教育理论,还不能真正涵化西方教育理论,使它适合我们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盲目学习西方其实无助于自身理论成熟。因而中国教育的根本改观,要从自身的教育文化改造做起,教育的内在转型也只能在以自身传统文化为基本动力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转化与演进。
我们认为素质教育作为一种人文取向的教育思潮,它不仅要吸收西方人本主义的精华,更要以儒家人学思想为原点,重建与拓展传统儒家的人文精华,才能最终促成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实现中国教育理论的主体化与现代化。本文拟从如何承继与拓展儒学人文理念的角度探讨教育的转型,即如何以儒家文化为基本的动力实现素质教育的理论演进。
一、儒家人学思想与素质教育人性基点的确立
素质教育的理论演进是在承继儒家人学思想,对应试教育重知识、重书本,忽视完整人性陶炼的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它重新确立了教育的人性基点,从教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儒学教育人性主题在现代的历史演进。
1.儒家人学思想与儒学教育的人性化基调
儒家人学意识源于对殷商时代忽视人的主体自觉的神启宿命文化的批判。春秋时期,诸侯崛起,周天子权威式微,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传统的神启宗教走向衰落,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身处危时乱世的春秋人最关注的就是人何以生存何以自救的问题。儒学也在天地万物的流行大化中探求人合理的存在方式。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的,以探索“德性与人格之如何形成为其学问的中心”(注:胡伟希著《传统与人文》第77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对人在宇宙中的生存意义进行形而上的理论观照。
儒家针对殷商时代天道神性对人性的压抑,凸现了人在宇宙间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是自身的主宰,是天地的主宰,即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注:《礼记·礼运》。)。他们认为人既为天地的主宰,就应自己承担自己的生命,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全权负责。而人何以能主宰天地,承担生命呢?因为人性本善,具有广大无边的同情心,故能以仁爱待物,珍惜一切生命;因为人具有体道、弘道的内在超拔精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能通过发挥自身的内在善性,以至诚之心,尽己之性,尽人、尽物之性,从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赋予无知无心的天地万物以生命的灵性,营造出大化流行的生命世界。人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儒家认为创化生命、超越生命正是人存在的本真意义。但人的这种创化、超越生命的内在善性、内在伟力不是自然发挥出来的,而是要存心养性,经过后天的教化、熏陶与修养才能充分发展,因而儒家重视人的德性陶炼,强调人的道德完善与社会责任感的培植,将教人做人、使人“人化”作为自己的基本教育使命,并逐步形成了以人为中心、以善为导向、以人的和谐生成为目的的人文教育传统,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性化基调。即将人的和谐生成作为教育的基本目的,认为教育的本义就是培养人,引发人的内在天赋本性,涵蕴人的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人生态度,引导人逐步内化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特性,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儒家教育的人性化基调不仅体现在它将人置于教育的中心,还体现为其教育过程的人生化特性。儒家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是有德性的道德高尚的人,而人的德性生成具有本体性、无限性的特点,这决定了其教育必须立足人生、面向人生、为人生而展开。由此,它既将教育与学生的人生体验紧密融合,主张“见贤思齐”,“反求诸己”;又将德性陶冶贯注于人生实际及人的一生,要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士“志于仁”;并主张教育要充分融合于学生的内心生活,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引导学生进行道德践行,以自求自得安身立命之根,追求德性的圆满。其教育过程就是立足于德的特点,引导学生认德、体道的过程,亦是不断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引导个体走向社会、历史和人类的过程,它是一个学生主体自我发展的过程。
古往今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证明:使人“成人”,正是教育的本质所在,因而儒家教育的人性陶炼及自我生成有其超时代的教育本义,今天的教育理论构建仍要因袭这一教育本义,才能重塑教育的本真形象。
2.素质教育人性基点的现实与历史依托
首先素质教育的人性陶冶基点确立于对应试教育知性模塑观的批判。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那么教育的基点应是人,但我国当前的应试教育将学生看作汲纳知识的容器,看作被雕塑的物而不是自主发展的人,强调知识的灌输与外在的模塑,其教育的基点是知识的获得。但真正的学问过程涉及到整个人每天的具体存在,这种学习不是把某种外在的东西塞进身心之中,也不是使自己获得与自我不相干的技能。他是要学习怎样成为一个人。“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成人,他的生存是一个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他总是不停地进入生活,不停地变成一个人。”(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第197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就是说,人的发展没有终结,没有顶点,这一命题宣告人不像物,一旦塑成即成为定型模式而毫无变动。人是自身发展的主体,他掌握着自身发展的主动权,是自身发展的主人,他的生长与发展既不能被限定亦不能被代替。可见,应试教育的模塑观是反人性、反教育本质的,它不能真正促进人的人性完善。正是基于对应试教育忽视人性陶冶的知性模塑观的批判,有识之士才提出了以人为中心、重视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陶炼的素质教育思想。
其次,从教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素质教育的人性基点确立于对儒学教育人性主题的文化承继。素质教育在我国的提出与产生,决不是空穴来风,它既有广泛的社会时代背景,但更有深刻的文化思想渊源,那就是儒学人文教育的潜在影响。儒学对人的存在的本真看法决定了它的教育影响必定是超时空的。儒学的人性观的现代诠释实际就是:人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生成性存在,人的内心具有对任何事物都要求理解的价值欲求,而人格的内部又潜藏着无尽的价值创造的源泉,所以他总是以人格的生命为中心不断发展着的,这意味着人是能自我完善、自我生成的,这种生成需要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内在精神动力,外在知性只是精神成长的手段与工具,因而教育应关注人性的成长而不是知识的获得。素质教育正是在承继这一人性观的基础上,强调教育应着重通过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去探寻事物的本源,以最大限度的调动与实现人的潜力,充分生成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质言之,它是以人的灵魂关注为核心,通过引导学生反省自身的存在,以唤醒沉睡中的灵魂,陶冶活的立体人格,将人陶冶成为一个内心世界丰富、趣味高尚的人,而不是将人看作一个堆集知识的容器。由此可见素质教育是强调从根本上关注人性,陶冶人性,始终将人生意义,人的生成放在核心地位的教育。这与儒家教人如何做人、关注人性、着重人生的教育基调是一致的。
总之,素质教育是一种力图实现教育人性化的教育思想,它对本真人性的把握是对儒家人学思想的现代诠释,其基本理念与儒家重人、爱人,强调教人做人,强调人的内在精神陶炼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儒学人文教育理念在现代的历史演进。
二、素质教育对儒学人文教育的理性重建
素质教育是儒学人文教育在现代的历史演进。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这就意味着素质教育对儒学人文教育的承继不能简单的重复回归,而要对其作合时代的历史超越,才能促进教育理论的合时代发展。
儒学人文教育强调人是教育的基点,这是超时代的教育理念,但它以道德属性诠释人性,强调人的道德理性,表现出一种泛人伦化色彩,培养的是具有高度道德理性的伦理人。这样的人往往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但却缺乏实现其抱负的技术理性,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道德理性与科技理性相统一的综合理性人,因而素质教育必须依托于传统、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对儒学人文教育进行理性重建,才能陶铸现代社会所需的综合理性人,从而促进中国人文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1.儒家教育的“人伦化”特色及其缺陷
儒家教育是通过人文知识的播化,以培养学生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完善个体的道德心性为目标的教育,它实质是一种人文教育。但儒家人文教育在其人伦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下,以建立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为中心来展开教育,以体认人际的伦常关系为限度和范围来确立其教育的对象、功能、目标,从而忽视了人的独立人格培养,也排除了对自然现象作科学的考察,“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只研究‘事’,而不研究‘物’”(注: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2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稼圃等生产技术乃小人之事,不被孔子纳入教育的范围。后世儒家更是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形器之末”,是典型的重群体轻个体、重人己关系轻物我关系、重道德理性轻工具理性的“人伦化”人文教育。
“人伦化”人文教育对人性提升和心性陶冶的高度重视,使它在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发展人的道德理性上具有显著优势。但它对以技术为代表的科技理性的漠视,却使它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的现实,以致无法助人参与具体的物质实践过程,使“怀德”的君子们常常因缺乏实现其抱负的工具理性,而使其理想流于空谈,使其学问于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作用甚微。解决现代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科技革新和个体技术水平落后之间的矛盾,仅仰仗道德理性,必然力不从心。因而要使儒学人文教育理念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对其进行合理重建与理性转化。
2.素质教育的人文重建有赖于道德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内在整合
从社会的未来发展来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既具道德理性又具科技理性的综合理性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技术已渗透到文明的方方面面,“处于现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人,无论赞成或者反对技术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和技术已密不可分,没有了技术,整个文明就会崩溃”(注:麦基编著《思想家》第101页, 三联书店1987年版。)。科技理性的获得已是现代人适应现代生活的必要准备。但科技理性的发展要以道德理性为先导。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对科技理性的盲目迷信只能导致人格的异化与文明的灾难。科技理性的发展是以征服宇宙为基本特征的,它强调人对外物的占有与掠夺,没有道德理性的制约,科技就会演变为人类发展的异己力量。因而素质教育的人文重建必须在继承儒学人文教育重视道德理性培养的基础上,矫正儒学人文教育过分忽视科技教育倾向,将人文价值的陶冶与技术价值的训练统合起来,“并承认人文价值与技术价值之间的张力结构,且把这种张力作为基本动机纳入到自己的教育计划中”(注:周进著《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第10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才能陶铸融道德理性与科技理性于一身的综合理性人。
综合理性人的培养有赖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内在整合,从教育的未来发展来看,教育的内在整合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转变教育的价值观,矫正儒学人文教育过分强调教育的社会性发展功能,将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统一起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仍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健全的人格,以求人类精神的完善。第二,调整教育内容,矫正儒学教育过分看重传递人文实事知识,而把传递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与传授科学知识和实践技能有机的结合起来,强调教育不仅要传递民族文化的心性精粹,还应教给学生实用知识,以帮助他们形成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社会道德责任感。第三,调整教育目标观,矫正儒学教育过分重视人的道德理性的片面倾向,力求实现道德理性与科技理性的统一,培养既有健全人格,又掌握娴熟生产技能的劳动者,既有明确的生活目标、高尚的审美情趣,又能进行创造性生产的人,即具有全面适应能力、创造能力、建设能力,具备高度责任感和人格健全,能承载人类现代新文化,具有完满人性的和谐全人。
总之,重建后的人文教育,是以科学为基础手段,以人的自身完善和解放为最高目的的教育。其基本特征是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人的主体素质,增进人的智慧和知识,使人在开发自然的同时解放人性,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它既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融统一。
三、儒学“乐教”启示下教育审美境界的追求
教育的审美境界是教育的审美化,它以美为先导,以和谐为最基本的特征,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教育的永恒追求。传统儒家的“乐教”思想对审美教育育人功效的理解及教育境界的审美把握都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儒学人文教育的精华所在。但由于近现代功利主义教育思潮的冲击,中国的“乐教”传统走向衰微,人文艺术教育也淡出校园,教育只求真不求美不求善,导致了学生人格的片面发展,这是呼唤教育转型的内在根源。因而素质教育欲实现真正的教育转型,引导学生趋向真正的自由与完善,也必须承续儒学“乐教”思想的审美价值,扭转当前的无美教育倾向,追求教育的审美化境界。
1.审美境界与教育理想的形式依托
教育的审美境界,是教育的审美化。在这里,所谓的教育审美化不仅仅是对教育形式美的把握,而是教育的整体美育化,是真、善、美三者在教育中的真正融合,是使全部的教育因素、环节和过程都具有美的特质,并由此而形成一种交互的审美氛围,营造出一种高妙的审美情境。只有在审美化的教育情境中,师生才能实现真正的精神相遇,真正的内心交流,学生的潜在本质才能被充分唤醒,使他从内部产生一种自动的超越力量,去进行永无止境的自我寻求,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内在潜能,尽力通向自由之境,从而臻于人性的全面完善。这也正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所在。
人的自由、全面而充分的发展是人类教育的理想追求,也是素质教育的最高目标,而自由的人只有在艺术的熏陶与追寻中才能培养——自由只有在审美的心境中才能产生,审美是人达到精神解放和完善人性的先决条件,亦即“唯有通过美,人类心智的崭新功能才被揭示,艺术在自由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根本性的、不可离异的因素,艺术乃通往自由之道,它是人类心智自由的过程,而这,正是一切教育之真正和最高目的”(注:参见李田《教育立美论》,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8年第4期。)。 这就决定了以培养人为任务的教育必须使自身成为美的王国,才能达到教育的最高境界,实现教育的理想追求。素质教育也只能以自身的审美化来优化教育的整体素质,增强教育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才能实现全面育人、优质育人、和谐育人的目的。
2.儒学“乐教”审美境界的实现历程及其启示
如何才能实现教育的审美追求,营造教育的审美境界呢?儒家的“乐教”思想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儒家因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注:《礼记·乐记》。),对大同世界的构筑具有独特的作用,因而将其提到教化万民的本体高度,给予特别的重视,从而形成了美善相融,借乐育人;美趣相谐,寓教于乐;立美化人,人境合一的“乐教”传统,通过教育的手段、过程、目的的审美化来实现对教育境界的审美追求,其独特的审美教化思想,为我国教育奠立了基本的教育审美境界雏形。
首先,借“乐”(yue)育人,涵泳人格。儒家认为“乐”是依乎自然之理而和谐化的声律形式,乐所表达的情志也是和谐化的,人若浸润于乐中其心灵也就获得了和谐。只有“游于艺”且领悟其美妙的人才能体悟道,修养道,从而成为充实而有光辉的完人。乐也正因“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注:《荀子·乐论》。),而被儒家作为德性熏陶的重要手段。即教育审美境界的营造,完满人格的陶冶要以美的、艺术的形式为先导。因而我国教育审美化的第一步是要实现教育的艺术化。
其次,循情诱“乐”(le)以激发学习情趣。王守仁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因而教育还应寓教于乐,让学生体会到快乐,使其知之、好之,进而乐之。做到“乐是学,学是乐”(注:《王心斋遗集》卷一《语录》。),以至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注:《论语·述而》。)的快乐极致,由此而让学生好学不倦,乐学不辍。这种依循人的本性来诱发学生的心智激情是外在艺术形式的心理化,它是营造教育审美境界的内在依据。因而我国教育审美化的第二步是改进我国当前只重视僵化的知识而忽视鲜活的心灵、只重视机械的灌输而忽视诗意引导的教育操作,实现教育的情感化。
最后,化乐(yue)激思,以达自由妙境。儒家进一步将艺术的特质内化到教育过程中,为学生营造出一种立美教化的精神空间,使学生全心向道,欲罢不能。正如颜回赞孔子营造的育人妙境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注:《论语·子罕》。)孔子正是以高超的诱导艺术将学生引入了思之自由境界,使其主体性得到充分调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审美妙境,这正是教育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即教育审美境界的最终营造是以主体精神的唤醒为标志的,因而我国教育审美化的最终实现要以教育的主体化为依托。
强大的传统在选择了一条科学的发展途径后,它的前景是广阔的,教育理论得以发展的背景文化也将是雄厚的。构建既合于自己的传统,又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素质教育理论,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思路,并踏踏实实地努力,就会不断的接近理想。
标签:儒家论文; 素质教育论文; 教育论文; 国学论文; 人性论文; 教育的目的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人文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