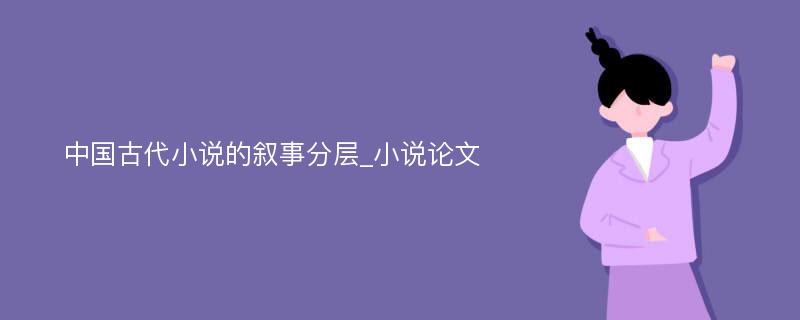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分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小说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又去叙述另一个故事时,小说就分为层次。从理论上说,这种故事中的故事可以无限地讲下去,但实际上一般具有叙述分层的小说只有二层至三层故事。上一层故事为下一层故事提供叙述者,这样,每层故事就都有各自的叙述人,它们不会是同一人。如果我们把占了主要篇幅的层次称为主故事层,那么,为它提供叙述者的上一层次可称为超故事层,由它提供叙述者所讲述的下一层故事,可称为次故事层(注:参见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第七章第二节,三联书店,1989年二月版。)。
具有叙述分层的中国古代小说数量不是很多,但它们也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这个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和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
一
唐以前小说,作者还缺少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我们今天看作是小说的,当时人却并不以为是在进行小说创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六朝志怪书“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之历史的传记一类。”(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从叙述方法上看,唐前小说基本上还是沿袭史著叙事法,即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按照编年的原则做纵向的顺叙,这就很难产生出叙述上的分层。随着小说创作意识的自觉以及小说艺术的复杂,小说的叙述分层开始在唐传奇中出现,这是对史著叙事规范的突破与超越,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具体体现。
较早的唐传奇王度的《古镜记》就有双层叙述,其中主故事层由八段小故事组成,是王度自述得古镜后亲身遇到有关古镜的种种奇事。从中又引出四段次故事叙述,由主故事层中的四个人物分别自述亲眼见到的古镜的魔力。在这两层故事、多位叙述者的叙述中,小说全部采用严格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主故事层的叙述完全限制在主叙述者王度的感知范围内,全部次故事层的叙述均为主叙述者无从得知的。这样,由次故事层的几位叙述者提供的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见到的古镜奇事,对主叙述者王度的讲述,就起到了补证的作用:程雄家婢鹦鹉以被古镜降服对象的身份自述古镜的魔力,更增强了说服力;引发豹生对古镜与苏绰关系的叙述,是因为他看到古镜的前主人苏绰对古镜下落的预卜应验了,豹生成了古镜魔力的见证人;张龙驹的叙述,则是让镜精以托梦自述的方式来坐实它的魔力;最后,主叙述者王度又让自己的弟弟亲身验证了古镜的威力。总之,次故事层的设置,意在说明古镜魔力人所共见,并非子虚乌有。
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视角,对故事作分层叙述,这是史著叙事法中所没有的,它表明此时的小说叙事方法已与史著叙事法分道扬镳。
但是,做为唐传奇的早期作品,《古镜记》的叙事方法又明显地受着史著叙事法的影响。比如,为了加强小说的信实感,作者对一连串的古镜奇事还采用了历史编年的叙述方法;特别是主叙述者不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直用作者本人的姓名王度,这无疑是在仿效中著叙事法,就象历史的叙述者就是历史家本人一样。而到了唐代中期,唐传奇《张佐》(注:见牛僧孺《玄怪录》。)的分层叙述,则完全摆脱了史著叙事法的影响,显现出小说艺术创作的自觉。
这篇小说写张佐向他叔父讲述他遇到奇人申宗的事。故事在时间上采用倒叙手法,按不同叙述者的讲述,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张佐讲述他遇到老父申宗以及再三求老父“赐言以广见闻”的经过,这包括小说开头、结尾的两小段,其篇幅虽不长,从时间上看是最近的,可算小说的主故事层;第二、三层镶嵌于第一层故事中,第二层故事的叙述人是老父申宗,他向张佐回忆自己多年前与占梦者有关的一段经历,其中又引出第三层故事,即叙述人占梦者向申宗讲述申宗的前生因缘。三层故事倒叙衔接,层层递转,给人以幽远迷离之感。《张佐》已完全摒弃了史著的信实观念,它以叙述分层来创造一种虚幻的境界,追求美学的效果,如果说《古镜记》的叙事方法还是在史法规范基础上的变革与创新,那么《张佐》就已经是在自觉地运用小说构思法了。
二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来源于讲故事,它不像文言小说那样,直接脱胎于史传文学,它有着更为独立的一套小说叙事法。但是,较早的白话小说如宋元话本,大都是以架设书场格局的方式,叙述者以说书人的身份来讲述故事,这样,由于叙述行为过于直接,难以虚构出新的叙述者,所以在白话小说案头化以前,话本的叙述者基本上就是作者本人,它不像后来的文人小说那样,作者与叙事者之间出现了有意识的分离,有着多种复杂的关系,因此在话本小说中不见有小说的叙述分层。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创型的长篇白话小说,首先出现了次故事层的叙述。小说第三十九回写官歌寄名和潘金莲生日时,在吴月娘房中由两个尼姑来讲述禅宗五祖的前生故事,故事说五祖前生是张姓财主,有八位妻妾,家财无数,后来证明这些妻妾对他没有一个是真心的,于是出了家,死后投胎成为五祖。故事由说因果、念偈、唱曲几部分组成,篇幅占了将近一回的三分之一。《金瓶梅》在主故事层的叙述中嵌入这一大段次故事叙述并非毫无意义,这里的财主张员外实际就是西门庆的影子,故事的教训是对西门庆一家的劝诫,但西门庆当时并不在场,在场的妻妾说说笑笑,听了也没有醒悟。这是插入一个清心寡欲的佛世界故事以与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相观照,这段次故事叙述相对于主故事层来说,有着暗示主题的作用。这是《金瓶梅》的作者基于案头小说艺术的需要,首次在白话小说的创作中对于叙述分层的运用,相对于直捷、明了的说话艺术,它适应并建构了案头阅读者的欣赏趣味。其后,随着文人白话小说的成熟,在《西游补》中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次故事叙述。
《西游补》的主故事层是叙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后,被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在虚幻的世界中,见到了古今世界的形形色色。在叙述时间上,作者异想天开地构思了“古人世界”、“今人世界”、“未来世界”,并不时地打乱客观时序,比如让唐代的孙悟空去审理宋代的岳飞、秦桧案。小说在主故事层之下,又嵌入多段次故事叙述:从叙述时间上看,有追述既往的,如第二回扫地宫人自言自语地讲述风流天子的故事,第三回踏空儿讲述小月王凿天的故事,第七回项羽自述生平等;有展示当今的,如第四回万镜楼中,镜里映出秀才放榜的故事;也有古今重合的,如第十二回无目女郎隔墙花说唱弹词。这些次故事叙述,多侧面地展示了人生世相,与主故事层的事件、旨意相对照,加深了读者对小说主旨的领会,同时通过叙述层次与叙述时间的穿插混淆,造成一种虚实错综、扑朔迷离的幻想,表现了作者对小说美学效果的有意追求。
刊刻于崇祯元年的《警世阴阳梦》,则在小说叙事法中首次创造了叙述分层中的复合叙述者形式。《警世阴阳梦》是在魏忠贤阉党垮台不久,最早反映这段实事的小说。书中《阳梦》、《阴梦》两部分,《阳梦》述魏忠贤发迹而覆亡事,《阴梦》述魏党在地狱遭报应事。这部小说自治至终都是以一位说书人的口吻面对读者讲故事,不过,在小说《阴梦》的结尾还点出了另一位叙述者,即《阳梦》故事的参与者和《阴梦》故事的观察者长安道人,说他从阴世目睹魏忠贤受惩还阳后“提笔构思,写出《阴阳梦》”。这两位叙述人的关系,在《阴梦》开篇语中交待得很明确:“说话的,俺北京城,如今是有道之世,阳长阴消的时候,有什么阴梦,你说与咱们听着。看官们听小子说。……如今又有个长安道人,新编阴梦,听咱道来。”这就是说,除“阳梦开篇语”、“阴梦开篇语”两段超故事叙述是由说书人叙述者单独讲述外,有关魏忠贤的主体故事是由两位叙述者共同讲述的。其中,长安道人是故事的编述者,说书人是故事的转述者。由两位叙述者共同讲述一个故事,构成了叙述分层中的复合叙述者形式。
这部小说所以采用复合叙述,是由这部小说的性质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决定的。此书写的是当世时事,魏忠贤于天启七年十月畏罪自杀,第二年(崇祯元年)六月这部小说便写成付梓。这距魏忠贤死仅半年,亲闻目睹魏忠贤事的大有人在,做为一部反映时事的小说,为免遭讥评,小说不便于过分虚构夸大。为了强调此书系多据事实敷衍成篇,小说的卷首“题识”还特意交待了本书故事的参与者兼叙述者长安道人与魏忠贤的关系:“长安道人与魏监微时莫逆,忠贤既贵,曾规劝之,不从。六年受用,转头万事成空,是云阳梦;及既服天刑,道人复梦游阴司,见诸奸党受地狱之苦,是云阴梦云云。”长安道人与魏忠贤是否曾有过莫逆之交无从考证,但长安道人的见证人身份,使这部小说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不过,如果长安道人仅以事件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的身份叙述故事,小说只能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这就不便于表述作者斥奸、惩奸的鲜明情感。看紧接此书之后,崇祯年间又相继出现同题材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可知魏忠贤祸国殃民事,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是十分巨大的。《警世阴阳梦》的编者长安道人难于用冷静客观的第一人称叙事,于是他就把故事交与一位假定的说书人叙述者共同叙述。这样,就可以在《阳梦》中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更深入地揭露魏忠贤的种种内心隐秘,以便“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注:《警世阴阳梦》首《醒言》叙。);《阴梦》写道人梦游阴司的见闻,则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长安道人只冷眼旁观,以冷峻客观的笔调写魏忠贤在地狱遭报应的种种惨状,虽属虚构,却能给人以亦幻亦真之感。总之,小说采取这种复合叙述法,既可以表明此书信实有征,又可以便捷地表达叙述人的主观情感。
出现于清代初年的《红楼梦》,则把上述的叙述分层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摆在《红楼梦》作者面前的难题是,这部小说既非纯属虚构——它有隐去的“真事”,又非全为实事——它究竟是用“假语村言”写成的小说,如何让读者理解“其中味”?作者曹雪芹正是利用分层叙述以及与之相应的对不同层次叙述者的巧妙安排,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红楼梦》首先出现了独立完整的超故事层叙述。在《红楼梦》的主体部分,即石头自录的“幻形人世”“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开始之前,小说开卷有一篇楔子,楔子开篇说:“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注:笔者认为,庚辰本开首“作者自云”一段应属凡例,正文从“列位看官”开始。)便是楔子的叙述者的指点。楔子的最后一句“按那石上书云”,仍然还是楔子的叙述者的按语,下句“当日地陷东南,……”则是主层故事《石头记》的正式开始。因为楔子与主故事层不是同一个叙述者,楔子提供了主体故事的叙述者,所以楔子是居于主体故事之上的超故事层。
超故事层叙述了石头以及《石头记》的来历:石头是女娲补天所遗一石,《石头记》是石头“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超故事层是这样点明《红楼梦》主故事层的叙述者的:石头自录的故事,“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看到石头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石头要求空空道人抄去,空空道人才“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成章回,……。”遂成为供读者阅读的《石头记》。这里交待得很明白,“石头”是故事的直接记录者和叙述者,“空空道人”是叙述的传递者,“曹雪芹”是“披阅增删”者,或者说,是故事的转述者。空空道人只在“石头”与“曹雪芹”之间起传递作用,从而将“石头”与“曹雪芹”分隔开来,他并未直接面向读者参与故事的讲述,所以,把主体故事讲给读者的叙述者应是“石头”和“曹雪芹”两人。
这在主故事层中表现为,故事是用第一和第三两种人称叙述的。其中,除少数片断如十七、十八回元春省亲时石头的插话等,是用石头的自称之词“蠢物”、“自己”等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的绝大部分都是“曹雪芹”用第三人称讲述的。深知作者创作构思的脂砚斋就曾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在《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句下,庾辰本脂批道:
神极之笔。试思袭人不来同卧亦不成文字,来同卧更不成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正是来同卧不来同卧之间,何神奇妙绝文矣。真好石头,记得真;真好述者,述不错;真好批者,批得出。
这里,脂砚斋把“记者”、“述者”、“批者”分得清清楚楚,明确告诉我们把故事传达给读者的,既有“记得真”的“石头”,又有“述不错”的述者”——“曹雪芹”。《石头记》的主体故事是由“石头”和“曹雪芹”复合叙述的,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红楼梦》的主体故事所以要采用复合叙述者以及与之相应的两种人称来讲述,是由作者的创作意图来决定的。第一人称是叙述者的自称,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往往给读者造成故事就是叙述者的亲身经历的感觉。“石头”以第一人称偶尔出现,这就造成了一种其中似乎确有“其事”的效果。第三人称叙述,则能起到将叙述者与故事间离的效果,这时叙述者成了故事的局外人,他的讲述,令人感到这究竟又是一部“假语村言”的小说。对叙述者的这种安排,正体现了《红楼梦》亦“真”亦“假”的艺术构思。
《红楼梦》的叙述分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作者还让超故事层人物进入主故事层,通过“跨层”,使两个层次间的人物、故事交织起来,从而加强亦“真”亦“假”的神秘气氛。超故事层是个“荒唐无稽”的神话故事世界,主故事层是个“追踪蹑迹”的红尘故事世界,二者本不相通。但是,超故事层中的“一僧一道”,即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他们不仅将顽石携入红尘,而且以“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的面貌,多次进入主故事层,他们在第一、三、八、十二、二十五、六十六等回中,为主故事层中的人物,或解救灾难,或指点迷途,表现了高于主故事层人物的能力,使一段真实的红尘故事蒙上了一层梦幻的神话色彩。
总之,《红楼梦》的作者正是运用叙述分层,完成了他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的创作意图。
三
《红楼梦》的叙述分层对晚清小说影响很大,一些晚清小说作者纷纷模仿《红楼梦》的叙述分层艺术。不过,他们不是像《红楼梦》的作者那样,用分层叙述将“真事隐去”,使小说更具生活的概括力,相反,却是通过叙述分层来强调说明小说的主体故事有某种来源,以强调其真实性。这种倾向与当时的小说界革命有关,所谓“新小说宜作史读”(注:佚名《读新小说法》,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直接制约了此时小说叙事分层艺术的发展,受其影响,作家借助叙述分层更强调了小说的“实录”性质。具体说,晚清小说的叙述分层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发现手稿式,一类是让故事中的人物跨出故事来说明主体故事的来源。
以发现某手稿、日记等形式设置超故事层,在晚清小说中,较早的有序署年代为1858年的魏子安的《花月痕》。《花月痕》第一回,一位自称“小子”的叙述人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此书的来历:
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小子寻亲不遇,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以樵苏种菜为业。五年前,春冻初融,小子锄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铁匣,内藏书数本,其书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详年代,小子披览一过,将俟此书中人传之。
然后从第二回,《花月痕》的主体故事才正式开始。更为典型的是发表于1906年的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第一回楔子叙述“死里逃生”在上海偶然从一位读书人手里得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手稿,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他披阁一番以后,将其“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了若干回”寄往横滨新小说社逐朝刊登。小说主体故事从第二回才以“九死一生笔记”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口吻,途述了“九死一生”的见闻。其它如发表于1907年的王浚卿的《冷眼观》,写成于1905年,直至1916年才梓行问世的《梼杌萃编》等,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些晚清小说家看来,设置这种发现手稿式的超故事层,就可以进一步表明,小说本身并非“凭空杜撰”(《花月痕》第一回语),“其中类皆实人实事”(《冷眼观》第一回语),这样,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小说改良社会的作用。
出于同样的原因,另一批小说不采用发现手稿的形式,而是让故事中的人物跨出主故事层交待本书来源。这大约也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启发。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结尾处,写超故事层中的空空道人来到急流津觉迷渡口,找到贾雨村,要托他把再度抄录的又增添了将石兄“后事叙明”一段“佳话”的《石头记》,传遍世人,贾雨村却指点他到悼红轩中去找“曹雪芹先生”。这就出现了空空道人从石上抄下的故事中的人物跨出故事来指点空空道人的怪事,这是有悖情理的,这或许是《红楼梦》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造成的。某些晚清小说家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借鉴。
滕谷古香的《轰天雷》的结尾,故事中的人物鹣斋就说“吾前日在图书馆买了一本小说叫做《轰天雷》”,随后故事中的另一人物敬敷还“向鹣斋要《轰天雷》小说来看”,并看到小说序文里说一个叫阿原的人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邮包,原来正是朋友临终前托付给他的《轰天雷》小说手稿。这样,就由《轰天雷》的故事中的人物交待了《轰天雷》的来历。
与《红楼梦》的结尾有所不同的是,这些晚清小说的结尾,故事中的人物跨出主故事层没有走向另一个虚构的神话世界,而是来到了现实世界,直接面向读者对故事进行说明交待。这就使小说本身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故事的虚构世界,一个是故事外的现实世界,当故事中的人物走出虚构世界时,这似乎是要我们相信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相通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法国的日奈特将小说这种叙述层次的转化,称做“转喻”,他借用博凯茨恰的话对这种“转喻”的意义做了说明:“假如虚构作品的人物可以成为读者或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做为他们的读者和观众,也可以变成虚构的人物”。(注: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见《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李伯元《文明小史》的结尾,就是这种“转喻”的一个典型例证。小说结尾写平中丞奉命出洋考察新政,书中所写到的各色人物都想来当随员,以“图个进身之阶”平中丞就挖苦他们:
诸君的平日行事,一个个都被《文明小史》上搜罗了进去,做了六十回的资料,比泰西的照相还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画还要画得透露些。诸君得此,也可以少慰抑塞磊落了。将来读《文明小史》的,或者有取法诸公之处,薪火不绝,衣钵相传,怕不供诸君的长生禄位吗?
虚构与现实的界线模糊了,当人们读到这里时,不禁一怔:书中虚构的人物突然都从故事中走出来,变成了现实。谁不担心:“做为他们的读者和观念,也可以变成虚构的人物”而进入小说呢?
晚清小说家利用叙述分层艺术,使小说更贴近社会现实,以达其“改良群治”的目的,这使小说的叙述分层艺术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内涵,从这一角度说,这也是小说叙述分层艺术的又一发展。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古镜记论文; 读书论文; 古镜论文; 红楼梦论文; 曹雪芹论文; 花月痕论文; 金瓶梅论文; 张佐论文; 文明小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