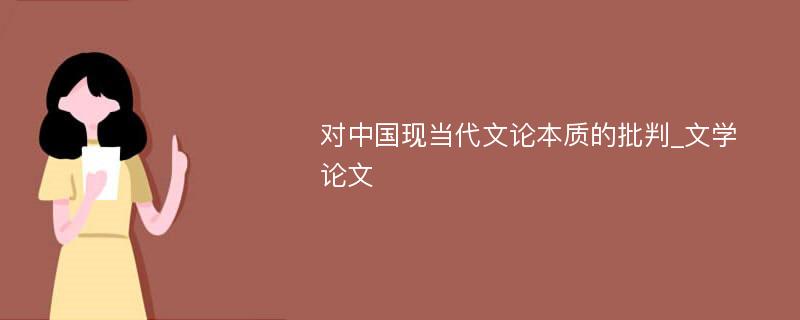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本质真实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论文,本质论文,现当代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2-0138-07
艺术的真实性是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历来受到文学理论批评家们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来说,由于其与现实世界有比较相近的对应关系,真实性更成为人们探究的焦点。因为艺术的真实性问题,不仅关涉到人们以怎样的艺术立场、观念去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表征出艺术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借此牵连着如何去看待作品的意义、价值和功能等问题。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理论批评家们为何一直将艺术的真实性视为艺术的生命,倍加呵护。
通常的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活原生态的形式和按照生活逻辑的推演来构建作品人物、情节的真实性,二是作者的真情实感。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自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兴起后,与之伴生的有特定社会政治历史本质内涵的本质真实论便开始占据了艺术真实的核心,延续至今。这种超越了具体的审美艺术形态而上升为理性准则的本质真实论,明显有悖于艺术的形象性、虚构性和诉诸于人的情感性等基本特质,其合理性是很令人怀疑的。笔者对此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现拟从本质真实论的历史演化和自身性质上做一番批判性的考察和剖析,进而就文学对世界的把握,即文学到底能表现世界的什么这一特质给出一种尝试性的阐说。
一
文学本质真实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演化,乃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和文学结盟的必然产物。严格地说,在文学与政治的一般关系中,只要坚守以文学为本位的艺术立场,这样的命题是很难提出来的。然而,当政治主宰着文学,或者说文学完全被纳入政治的轨道之后,有着特定政治指向的本质真实论也就理所当然地强行着陆了。
应当看到,中国文论历来就有重道的传统,且在近现代愈演愈烈。从孔夫子“温柔敦厚”的诗教,到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再到梁启超关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示的便是文学的宣教功能。然须明确的是,此类载道之说,与文学的真实性并未建立明确的直接关系,二者尚处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中国古典文论中对文学真实性的论述,多半都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对作者主观情感之真的阐发,诸如太史公的“发愤著书说”、李贽的“童心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及至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罗家伦、茅盾等从方法上谈创作时,真实性也只是停留在科学观察意义上的现象之真。所谓“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1]这两件法宝,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说法。但到革命文学兴起,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后,文学的真实性开始与阶级的政治的欲求直接挂起钩来,真实性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对既存思想观念通过文学来载道、宣教的外在要求,转而内化为一种创作准则,即文学形象应对社会历史本质、阶级本质、政治本质等进行真理般的探求和表现。中国文学理论史上首次出现了本质真实的理论观念。
从理论发生角度看,本质真实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理论的核心地带,依循的是这样一种貌似正确而实则错位的逻辑:首先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前提地位,继而以世界观取代创作方法,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来认识、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将文学真实的问题,引向了一条哲学化的道路,把艺术的把握和表现等同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对历史真理、阶级本质、政治本质的探求,使“本质”这种理论性命题变换为艺术性命题。冯雪峰提出:“要真实地全面反映现实,把握客观的真理,在现在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做到。所以,无产阶级的作家,首先要有坚定的阶级的立场,和伊里奇所说的坚定的党的立场。”[2]周扬发表了更为明确的看法:“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到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3]219在世界观决定论下,文学与政治合一了:“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3]213而左联执委会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规定和提出的诸多政治性文学任务[4],则从组织意义上显示出整体性的这一变化。
这种将阶级、政治、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直接画上等号的本质真实论,太过漠视艺术的特殊性,不久就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从1933年底开始,周扬撰文评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上批评了机械论的、忽视艺术表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注意到了文学的特殊性,在理论上做出了较为辩证的解说[5][6]。这个结果,使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结合具备了某种合理的理论面目,披上了形象化、个性化的漂亮外衣,尽管此中存在着不少应予理清的问题。于是,以一般的认识论方式来要求、看待艺术问题,反而更加牢固地得到确认。特别是典型化方法在此期间的确立,与本质真实论结成了手段和目的的紧密关系。周扬在肯定了正确世界观的保证作用后指出:“艺术作品不是事实的盲目的罗列,而是在杂多的人生事实之中选出共同的,特征的,典型的东西来,由这些东西使人可以明确地窥见人生的全体。这种概括化典型化的能力就正是艺术的力量。”[6]341胡风亦表达了类似看法:“作品里的人物所表现的是社会群体底特征,是能够说明那个社会群体底本质的特征,也就是……生活底真实,客观的真理。”[7]由此,艺术的抽象、概括、集中等,成为解释创作方法最有力的术语。
左翼时期这种具有明确无产阶级政治指向的本质真实论,奠定了之后的文学理论在真实性问题上哲学化的社会本质的基调,即以本质与非本质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社会思想性内涵。这样,文学艺术便由精神情感的形象把握转向理性的社会认识,由现象的描写、表现走向本质的概括、抽取。
到了抗战时期,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之下,本质真实论发生了一点微调,其阶级性内涵的理论表现在前期有所淡化,阶级性的本质隐含在“以抗日为最高政治”与民族性的统一之中[8]。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之后,阶级论的文学观再度在解放区活跃并占据中心,革命现实主义和典型化的方法重新被推到独尊地位,本质真实论中的阶级本质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在周扬看来:“现实主义应当是艺术真实性与教育性结合,也就是艺术性与革命性结合。”[9]828塞克则认为,艺术技术“是同思想意识、感情结合得紧紧的,凡是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表现的一切形象,都是有阶级性的……一离开无产阶级,他再也找不到真理”[9]308。艾思奇和艾青直接从典型问题上强调阶级本质:“我们的文艺通过所刻画的各阶级人物的典型,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来指示新民主主义的具体道路。”[9]230“人物是阶级的典型,写人物必须赋与他的阶级所决定的、一定的思想和气质。”[9]289而整风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的提出[10],更使文学上的本质真实不仅具有了批评理论上的权威根据,同时还显示出一种政策意义上强大的外力支持和保障。当时关于“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暴露”之类争论,实质上就是这种本质论文学观的产物。
建国后,延安整风运动的文艺思想和精神在统一政权之下得到全面承袭和实施,本质真实论有了无比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观念统率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学批判风潮的强烈荡涤,所有封资修的文学思想在本质真实的唯政治文学标准之下再无藏身之所,“政治挂帅”成为覆盖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通用术语,阶级的政治的本质论渗透到了文学领域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较之延安时期的论述,此阶段的阐释显得更为精致和深入,具有了较强的自身逻辑的合理性。周扬、张光年、林默涵、陈涌、周勃等人的相关论析[11],充分显示了这一理论进展。只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对反映本质真实的描写对象有了新的提法。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和茅盾的报告均专门阐述了“塑造好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2],使其成为之后阶级性政治性本质诠释的新焦点。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和文学气候之下,一旦有人稍有逾越,哪怕是在保持本质真实的前提下,提出“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写中间人物”等,立即便会遭到无情的批判。文革时期“三突出创作方法”的极度提纯,更使本质真实论走向极端,赤裸裸地用图解概念的方式去表达所谓的阶级政治本质,导致文革文学只剩下“一条金光大道和八个样板戏”的凋零局面。
新时期来临,文学理论发生了较大的多元化的变化,阶级性的相关论述从理论话语中逐渐淡出,但其政治性的内涵仍继续发挥着适应时代要求的重要作用,“主旋律文学”之类的提法,便是极好的例证。与之相应,本质真实论的阐释也不再固执于以前那种直接性的阶级、政治内涵,作出了重新调整和修正,使之具备了更大的包容空间。由高校文论教师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可以说具有相当突出的代表性。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表述为:“综上所述,艺术真实是文学创造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作家的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在其营构的假定性情境中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特别是那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的认识与感悟。”[13]刘安海主编的《文学理论》则视“艺术真实是按照文学反映生活的特点来检验其意识属性的一种尺度”,从而将普遍性、规律性、本质真实等概括为三个测度:“即通过反映的测度以满足理解生活的需要,通过表现的测度以满足对真情实感的需要,通过心理的测度以满足读者接受的需要。”[14]艺术真实有了可喜的多层次多角度理解,但仍无法也没有去摆脱本质真实论的苦苦纠缠,留下了一旦需要便可反弹的巨大空隙。
纵观本质真实论产生以来的历史,虽然存在着具体阐释上的个别差异和受社会时代影响而导致的不同提法,但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质一直未动摇,那就是文学要反映、表现社会政治历史的本质。同时,不管是居于前台或隐于字面之下,特定的社会政治立场总是规范和制约着这一本质的文学表现和价值取向。在本质真实论者眼中,文学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工具,它与自然科学真理的探索,人文社会历史领域对真理、理论本质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方式上有别。周扬在本质真实论产生之初就提出文学真理与政治真理的同一说,区别只在文学是以形象来反映[3]。而冯雪峰在抗战期间大谈艺术与科学、历史真实、客观真理、政论等的一致性及方式上的差异性[15],形成更大影响。直至新时期,杨汉池还撰文专论文艺真实能与哲学认识、科学真实达到同样的本质性、规律性认识[16]。这种殊途同归说在理论光环的照耀下,成为支撑本质真实论的强大理论基础,获得了文学理论界的普遍认同,现在也该一并予以批判性清理。
二
从阶级的政党的以及统治者的欲求来说,利用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宣传教育功能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要求文学作品反映历史的阶级的政治的本质,有其特殊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从文学理论的角度上说,本质真实论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理性思考,其中亦不乏某些有价值的见解。然而,文学到底是文学,它必须首先是艺术的审美的,而后才能在符合艺术原则的基础上承载一定的有限的社会思想观念,可谓“先乐而后教”。所以,任何文学要求的扩大化和绝对化,一旦越过了艺术的质的界限和文学自身的表现能力,就难免产生错谬。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本质真实论,立足于特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以反映、表现社会政治历史真理、本质的标尺来作为文学的准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难以成立的,也经不起对文学本性的追问和其表现能力的考量。对此,我们可从下述几方面给予辨析。
首先,从哲学角度看,本质真实论是缺乏实在意义的虚论。
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没有无本质的现象,也无脱离现象而产生的本质。换言之,无论何种具象的文学作品,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本质真实论者以二者的统一来阐释文学的本质真实,无异于说出了一句貌似正确的废话。进一步说,任何事物皆是多重属性的统一体,不容分离,所谓的本质与非本质,无非是取决于认识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对其在理论形态上展开的剥离和抽取。就此而言,这对作家选择何种题材和何类人物来给予文学表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为做出怎样的文学选择是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联系在一起的。紧随而至的问题是,形象化的文学能否表现抽象化的本质?答案是否定的。在笔者看来,作家的主观意图不等于文学对象的本质真实,而理性本质的剥离和抽取也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典型化方法的概括和集中来实现。文学形态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聚合体,作为一种具象化的存在,它包裹着多重属性,而各个人物的自身品性以及相互关系也是一种多方面交织网状扭结的集合态,倘若要将这些水乳交融、筋肉相连的东西进行本质与非本质的割裂,不妨试想,这个本质论之下的文学作品将会是怎样一个残缺不全的怪胎?世间不可能存在赤裸裸的本质现象,亦无脱离了非本质的文学。如果有,那就只能是人造的概念图示。不过,文学的本性也会因此丧失殆尽。这样的东西还能算文学吗?
其次,从文学认识和理论认识的性质区别来看,二者根本不可能达到殊途同归。
文学认识指一种艺术认识、形象化认识,完全不同于一般性质的理论认识。文学认识是作者经验性的感性的对世界的体验和悟解,其中虽有作者既存理性东西的渗入,但它仅处于观念性的指导层面,带来的只是作者对对象的倾向性和情感态度,并不指向事物本身性质的探究。因此,在艺术的意义上,文学并不关心表现对象在理性认识层面上的真伪和本质,它追求的是在符合艺术逻辑的基础上去塑造出一个崭新而鲜活的艺术形象,以此满足人们审美的和精神情感上的需要。事实上,在审美活动中,没有人会对文学作品要求得到本质真实之类的东西,谁真有这种需要,一定会去看相关的理论专著而不是去读文学作品。可见,文学认识乃是一种建立在形象方式上的审美性的情感性的活动。它可能关联着某种本质真实但却拒斥着在自身中去进行理性的追寻。而理论认识则是一种思辨性的概念化的精神方式,它要超越经验的感性的表浅层次,尽力排除主观情感的干扰,透过纷纭繁杂的诸多事物的表象,以抽象的方式去达到对事物本身性质的认识。同时,就文学的表现能力来说,文学是一种个性化的存在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形式,它展现的无非是一种当下的个别的感性状态,无力呈示抽象的共性。我们绝不可妄自从这种孤立现象中去抽取出某种社会本质、真理。即使是描写阶级、政治之类的题材,也不能简单地直接从作品中去得出本质真实的结论。因为人文社会领域中的本质探讨,需要的是从大量的无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去概括、综合、凝练、提升诸现象中的共性。再就表达方式而言,文学认识最终是以某种艺术逻辑和形象方式来展开的,并不是以条分缕析的理性方式去作概念化的准确论述。而这种文学形象一经塑成,也就即刻摆脱作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第二性世界”的含义。以此之故,文学形象具有多义性、变移性、模糊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名言,亦充分说明了文学形象的这种感性特质。显然,要形象化的文学去表达思辨的理论本质,表现出概念的抽取、剥离、推演和诸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等,从而实现对事物本质准确清晰的界说,断不可行。
本质真实论者从未就文学认识和理论认识的关系作过深入的探究,便武断地将二者在所谓的最终目的上等同起来,完全是缺乏根据的。他们自认为最大的理由,大概要算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小说的评价。杨汉池在此方面的“理解”堪称典型:“巴尔扎克作品的艺术真实同这些科学的科学真实有一致之处。‘一致’不是‘等同’、‘重合’,而是一种‘交叉’、‘相切’。因而可以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角度来对待巴尔扎克的某些描写,从中把握艺术和科学双重意义上的真实性。”[16]309我们真能将作为文学的小说提升到理论高度及现实历史对象的同一界面吗?但凡稍具哲社理论素养者,恐怕均难以认同。是的,恩格斯的确称赞过巴氏小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7]462-463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一个前提,那就是恩格斯在此进行的是文学批评,其视野本身就超越了文学自身而达到理论研究的层面。所以,无论杨汉池所说的“一致”,还是“交叉”、“相切”,都掩盖不了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之间的本性差异。不可否认,恩格斯的评价有过誉之嫌,但我们仍能肯定的是恩格斯在巴氏小说中获得了感悟,同样还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引起感悟的对象不是政治经济理论本身。巴氏写的是小说,是对社会经济现象某种程度的艺术展示,即使恩格斯由此而思考到某些深刻性的东西,那也不过是他的理论头脑对现实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在小说中得到一定印证的产物。因为说到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现实的社会土壤上进行的,小说至多只是他们在某种研究情状下的某种补充,不可能真正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更不用说小说本身根本就无法表达出某种政治经济理论和提供真确的可靠数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只能是列宁所说的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18]。设若殊途同归说能够成立,那我们真得建议所有搞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人都应将巴氏的《人间喜剧》作为必读书来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再次,从创作角度看,本质真实论的提出严重阻遏和抑制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和百花齐放的原生态局面。
笔者在前面已经从理论上否认了本质真实论文学的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其对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却是极其严重的。
从本质真实论的产生到文革结束前,文学在追求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的本质、真理的过程中,一切文学行为都打上了这种本质真实论的印记,以此作为判断文学是非、高低的标准。尽管这种理论不时会加上一些艺术因素的东西以保持文学形式的面目,但由于未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导致了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标签性文学作品的出现。而以本质真实、典型化方法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不仅高踞独尊地位,甚而成为取代其他文学艺术方法、形态的不二理论。在此情形之下,文学的多元化方法、多样化形态要么接受现实主义的“收编”,要么遭到批判和炮轰,抑或根本就无栖身之地。新时期以后的今天,本质真实论虽已有了较为宽泛的内涵,影响力亦大打折扣,且在实际上已经容忍了非本质真实类文学的合理存在,但骨子里的政治性本质论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继续充当着判别文学高下优劣的标尺。不少人提出的所谓坚持“时代精神”、“历史使命”之类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本质真实论”变换的漂亮言词而已。这么些年来全国各类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大奖,花落谁家,内中的缘由是不言自明的。如此文学导向,多少欠缺公平,极不利于充满自由本性的原生态文学多元多样的丰富发展。
最后,从文学批评方面看,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足以成为探究或阐释社会政治本质和历史真理的可靠根据和材料。
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研究活动,它的根本职责是对作品审美的艺术的性质及因素的发掘,以及从精神意识情感的层面去解析作品的内在蕴藉。质言之,即对作为艺术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于原在意义上的精神文化特质进行阐释。可以说,审美—艺术与精神情感才是最符合文学本性的两大分析元点。当然,文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子系统,就此而言,探究文学与社会诸关系间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亦是应有之义。不过,倘若将文学作品推到表达社会政治本质和历史真理的高台上,那就会产生严重错位了。因为对于社会政治本质历史真理之类的研究、阐释,必须在社会的整体层面及宏阔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进行实在的考量,涉及的是大量而复杂的历史事实,而文学仅是个性化的充满偶然因素的某一或某类现象的精神艺术产品,根本就无力承受跨越中外古今的历史之重,也不属实生活之列。的确,文学也在反映、表现社会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虚构性才是文学作品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本特性,特别是在叙事性的小说和影视文学之中,表现尤为突出。直白地说,它与实生活之真比较而言,乃是一个“假的世界”。难怪就连老百姓在对其进行审美观赏活动之时,针对观者的喜怒哀乐,亦会戏谑一句:“莫替古人担忧!”意思就是莫把故事当成真的现实。多年前,曾有一位历史学者就某人以姚雪垠《李自成》来讨论李岩是否确有其人时,意味深长地告诫:莫把文学当历史。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是与之对应的现实历史,这应该成为我们探讨文学真实性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此尚需声明,我们否定从文学作品中直接要求和得出本质真实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反对就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及政治方面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本质结论与社会政治历史意义分析必须以批评者对现实的认识为基础前提,将社会政治历史本质性的东西和作品的表现结合起来进行。前者是本,后者是影。同时还应注意到,由于文学艺术在叙事逻辑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其发展线索和情节只能按照故事与人物的需要来设置,这与理性本质的探求是建立在纵横交错的广阔的社会现实之上的思维品性是不可能吻合的。因此,这种本影关系实际上存在着强大落差,作品之影仅是在某些点面上且经由批评者的增补,才能与批评之本联系起来。否则,作品在该问题上是无法进行自我论证的。换言之,社会政治历史之本质真实是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的,文学为此能作的仅是些辅助性、印证性的功夫。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文学批评,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诸如前述恩格斯对巴氏小说的评价,马克思对拉萨尔作品的批评[17]339-342,都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历史认识与文学作品在社会批评上的结合。当然,在这样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批评者们的社会政治历史批评是否真能达到本质真实或真理的高度,那就是见仁见智,有待评说了。
三
对于文学本质真实论的批判,最后都集中指向一个问题:文学到底表现什么?或者说,文学和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种把握关系?这实际上是对文学本质特性的追问,当属文学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此姑作扼要阐说。
世上没有可治百病的药,也无包打天下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乃是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及不同方式和方法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思曾就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作过下述经典的概括:“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19]这一立足于哲学高度上对人类一般活动的性质论断,无疑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文学艺术的根本出发点。
在笔者看来,这四种基本方式揭示了人们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的目的指向:理论方式——事物本质、宗教方式——虚幻精神、艺术方式——审美观照、精神—实践方式——评价、改造世界。文学归属于艺术,自然是以其特有的审美的艺术的方式去把握世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方式。我们必须看到,文学在其本性上不是世界固有的存在物,而是人类精神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作家的主观精神创造的成果,尽管其来源和基础仍深刻关系着那个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正是人的这种特殊的艺术生产方式,表征着人的自由精神,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其独具的主观化的精神方式占有着世界。诚如马克思所言:“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20]艺术行为如是,文学行为如是,审美行为亦如是。
足以见出,不同方式的把握指向的是(依据主体能力)对对象不同属性的认识。应予强调的是,艺术认识乃是在主体的审美观照下才得以实现的,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性和主观性。就文学来说,不管是以何种创作方法,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无不是在审美的意义上对世界的一种形象化展示。显然,形象化的东西是不能以理性认识的方式去推行的,而是按照艺术的假定性,即形象逻辑的真实性规则(生活逻辑、事理逻辑、超验逻辑)[21],在一种可感可触可视的感性状态中展开,诉诸人之审美情感体验。康德曾对审美特性作过精彩论述,值得借鉴。出于构建哲学体系的需要,康德曾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并作出心理机制上的区分:“认识机能,愉快及不愉快的情感和欲求的机能”[22]15,以此对应认识论、美学(艺术)、伦理学,将审美判断力限定“在悟性和理性之间”[22]14,认为审美判断“不基于对象的现存的任何概念,并且它也不供应任何一个概念”[22]28。剔除康德三大批判的逻辑关联,仅就其对审美的艺术的看法而言,确乎抓住了要害本质。文学艺术这种形象的感性的东西是个别的、特殊的,其形态本身不会自动呈现理性认识的意义,只能展示人们原生态的或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之情感。质言之,艺术认识在这里把握的就是人的审美化情感。在审美化情感的本性上,它既不指向物自身的本质认识,同时又排斥了社会功利性的介入。即以理论界常提到的真(包括事实层面)善美来说,三者固然有统一的一面,但前两者也并非美之必要条件,假与丑(恶)绝不意味着艺术上一定不美,而真与善也不肯定就美。因为艺术评判只有在审美的艺术的立场上去进行,才能获得自身的有效性。而真善与假丑等则必须在此前提下给予重新审视,才能获取艺术上的新意义。大家应该明白,人类思维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辨清自己的行为是在何种意义上的什么性质的活动。比如,面对一件珍稀古瓷器,我们是作物质性的探讨,或历史价值的认识,抑或经济价值的评估,这些都与对其进行艺术鉴赏是绝对不可混为一谈的。
根据上述认识,从人类精神活动的层面上反思,文学无论是稚嫩时期的童真表现还是成熟时期的争奇斗妍,以及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各种审美形态,均无不表现出文学在艺术地把握世界上的三种基本元质:(1)一定的艺术(审美)形式;(2)形象化个性化的表现形态;(3)寓含在物态中或直接显露的人们的精神情感。三元质有机联系,从不同层面共同构成了文学和艺术不可或缺的基本特质。这可以说是文学之为文学或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规定性,也是对文学怎样表现世界的一个基本回答。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作出一个结论:文学的本质真实论是一个伪命题,它与文学和艺术的本质特性是冲突的,不能自足成立。
收稿日期:2007-09-15
标签: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