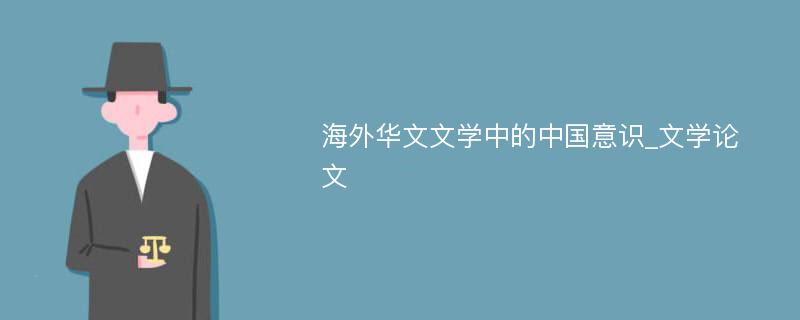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意识论文,海外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国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三种具体表达方式:对“乡土中国”的眷恋。对“现实中国”的关切、对“文化中国”的向往。中国意识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关键词 中国意识 海外华文文学 乡土中国 现实中国 文化中国 审美风格
一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20世纪那样,“中国”一词及与此相关的“中华”、“华夏”、“炎黄”等语汇,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本之中。“中国”一词在种种操作中,意义在种族(Race)、民族(Nation)、国家(State)之间滑动,呈现模糊不清的面貌,再加上“爱国主义”、“祖国”之类情感意味极浓的语词经常与“中国”一词混用,使涵义变得更加微妙。“中国意识”这样一种表述,也许能涵盖“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祖国”、“传统”、“现代”、“炎黄文化”等词语群所包含的全部种族本能与拯救理想。
从苏1978年创作的小说《中国人》中一位人物以强烈的情绪色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意识”的体认:“家和中国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中国,中国人!这多么荣耀,又多么沉重的名词呀!中国,这闪烁着过去荣耀和未来许诺的名词。中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体系,中国是历史,是传统,中国是黄帝子孙,孔孟李杜,中国是一种精神,一种默契,中国就在你我的心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中国,有说中国话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是亿万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性理性的希望和向往。”
这种“中国意识”的形成是由外力,确切地说,是由于西方的压力所引起的。1840年开始的西方势力的入侵,驱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在此之前,“中国一词,在古代课本里意为世界的文明部分,余者皆为蛮族”[①]。“但是,现代知识的光束揭示出它只不过是许多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并把它的美置于一个陌生的背景上,同时把它的阴暗面暴露无遗”[②]。异质文化的对照,被征服的屈辱,迫使中国人不得不作出形形色色的反应,而各种反应都是基于一种“民族”意义上的求生存意志:如何在外在的压迫下求得中国的新生?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混乱不堪,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无所不有;然而,这些思想的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现代性”的求索,而“现代性”的求索根本上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构成近现代中国历史主旋律的,正是这种创造“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意识”。“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建立国家的过程无疑是对西方反抗的过程,因为非西方是通过西方为‘他性’——‘敌人’的方法来建立国家的”[③]。
在此种历史背景下,文学也无法避免“中国意识”的围绕。梁启超于政治改良失败后退向文学领域,提出“小说救国论”;鲁迅则将文艺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此类借文艺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创作取向。正如夏志清所观察到的,“中国现代作家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④]现代文学的两位奠基作家从不同的方向塑造文学的“中国形象”,在鲁迅的小说、杂文中,“中国”一词散发出阴暗、腐朽的气息,而在郭沫若的诗中,则是新鲜、华美的气象。这在日后几乎成为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基本模式:摒弃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用毛泽东简洁有力的话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⑤]。这里的逻辑是:只有推翻旧中国,才能出现新中国。带有民族解放色彩的“中国意识”与“新旧”“传统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命题相纠缠,形成革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支配着文学创造的理念,也支配着政治、思想的运作。
上述的简单分析只是想说明,从1840年代开始,在中国本土,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生活层面,“中国意识”已普遍觉醒,并成为不同政见、不同思想、不同流派潜在的共同出发点,昭示出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中国这样一个衰败的文明古国如何面对挑战,如何重新辉煌的心路历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国意识”与古代的以君主、家族为核心的“爱国情怀”完全不同,这里要求个人的不是对某种权威的膜拜,而是以公民或民族的一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效忠与认同。
只有本土的觉醒,才可能导致海外华人的觉醒。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尽管早在7世纪中国人即向海外移民,但中国政府一向对此不予鼓励,尤其在明代,更有政策规定:禁止私人海外贸易,视那些未经官方准许而出国的人为非法。清朝在相当长时间里延续了这一政策,乾隆皇帝的一段话颇能反映这一政策深层的心理背景,他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⑥]!因此,在长达几世纪的历史中,“海外华人”完全没有进入中国本土政府或民众的视野,他们只是以个体的身份在海外自生自灭,至于他们内心对于异域及对于“祖国”的情感,也依稀地浓缩在残存下来的蛛丝马迹之中。这是一段基本上暗哑的历史。基于教育、政治诸方面的原因,那时候的“海外华人”没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声音。一直到19世纪,随着中国与西方交往的日益的频繁,一些出使海外的中国官员渐渐注意到海外华人的存在,并意识到政府有责任保护她在境外的人民[⑦]。1893年,清政府正式解除海禁,1909年又颁布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国籍法。海外华人终于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与中国国内事务发生联系。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在南洋、美洲等地华人中的活动,促成了海外华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在1900年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访问南洋之前,南洋华人中间并未独立产生民族主义领袖”,“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一种热情的自我发现所决定的,而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受过教育的华人巧妙游说所决定的,他们能揭示和证实华人一切苦难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一种从外部训出的民族主义,它把华人的一切问题都归纳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保护他们,因而更有切肤关系”[⑧]。从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外华人从总体而言,与中国本土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大多自认是“中国人”,并接受“华侨[⑨]的名称,尤其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人的参与热情给本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乃至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之母”的说法,而一般的中国人也习惯上将“华侨”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但在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在身份界定上出现了变化,最主要的标志是他们必须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外籍人士[⑩],不再是“华侨”。这样,他们一方面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也要忠于自己的“故土”,这种摆荡在多变的政治、外交空间,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在欧美,虽然由于50年代大量知识分子的移民,使得该地区的华人对于中国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怀,但对于早期的华工移民而言,却早已经历了从“华侨”到“美籍华人”的身份、心理转变,他们的后裔可能连中文都已遗忘,除了血缘、种族外,已成地道的美国人。即使是5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移民,现在也大多已成为美籍华人,而非“华侨”。
在二战以后,甚至在这之前,海外华人与中国本土的关系,以及从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中国意识”,都不是单一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能包容的,也不是“爱国爱家”之类的陈述所能包容的。在最本能的“种族意识”或“血缘意识”之外,因时因地因人,中国意识的涵义及表达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在华人定居的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发现三类华人:第一类华人十分关心中国的事务;第二类华人主要想维持海外华人社会组织力量;第三类华人则埋头致力于在居住国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11)]。另外,还可以这样历时地划分:一类是从未到本土的华人,他们甚至已完全不会中文,或者只是拥有中国血统而已,一类是有过本土经验的华人,但在这一类别中还可分出“新到者”与“定居者”的区别。国籍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已入异国国籍的与保留中国国籍的、以及那些正在争取获得异国国籍的。凡此种种,组成了海外华人千姿百态的众生相,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也显得摇曳多姿。
从根本上说,华文文学的写作本身标帜着“中国意识”的延伸与存在。一个在异域,坚持用汉语写作,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华人还是外国人,都说明他对于中国有着某种层面上的亲和,都是一种“中国意识”的体现。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正如海外华人的身份有过从“华侨”变为“外籍华人”的过程一样,海外华文文学也有过从“中国文学的支流”、“侨民文学”演变到“×国华文文学”的过程,也就是从原先的“中国文学”边缘地带,划入某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在这样的变迁中,海外华文文学整体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以及其中的“中国意识”,都会被有意无意地修正、改造。
因此,“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这样一个论题,触及到一相相当敏感的领域,对于本土的研究者而言,尤其应当抱持审慎的态度与客观的观察,否则,会引起诸多误解,也会混淆许多问题。当我们具体展开论述,仍要重申,此文中引用的“中国”一词不是目前东南亚地区所理解的政权意义上的狭义的“中国”,而一个非常宽泛的更偏于文化意识的用语,是上述我们分析过的所有意义的综合。
二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首先体现在对于“乡土中国”的书写。
人类对于自己的出生地或自己民族、祖先的出生地、发源地,总是怀着天然的眷恋,在这种眷恋中,人所要追寻的是他从何而来,从而确定自我的形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方“乡土”,可能是个体的起源地,也可能是祖先、种族的起源地,既是个体记忆的表征,也是集体记忆的表征,既是有形的山水,也是无形的意象。借文学的写作,纾解乡土情怀的焦虑、感伤,是人类常见的精神活动之一。世界文学中无疑存在着一种“乡土”的母题,反映着文学写作与“家园”记忆之间的独特关系。
中国古典诗词及现代文学中,不乏“思乡”的哀吟与乡土的描绘,有人甚至认定中国民族性中有重土安迁的一面,或者,以“乡土文学”来命名这类文学现象。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乡土中国”自然与古典的、现代的中国文学传统有着联系,但在根本上,却相当不同。因为后者发生在本土,而前者则发生在本土以外的异域。对于海外华人作家而言,空间的隔绝引起的思念、怀想、追溯等,不尽是古代的“游子”意识所能概括,也不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对于“乡土”(与都市相对应)的留恋与哀叹所能等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中,忆念中的“乡土”从乡音到山川、往事,不仅是人情的自然牵挂,而且是抵御自我迷失的良药。当文学将这些形象一一捕捉,使刹那成为永恒,作家通过意象的隧道,与他自己的过去对话,也与他无数的祖先对话。在对话中,作家观照到他内在的自我之源,更延续着自我与“民族”之间的深刻联结。
海外华文文学最显著的共通点就是飘溢着“故乡”的芬芳,由不同的“故乡”,凝成宏伟、深远的“乡土中国”的影像。童年的往事、故乡的人物风景,穿越时空,成为当下的文字。心笛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真美中的至美
乐声里的美乐
我突然发现
那最美的声音
是来自故国故人的乡音[(12)]
林牧则说“最难以忘怀的,是老祖母慈祥的笑容,以及那千变万化的奇特美丽的故乡的云。”[(13)]乡愁,确如岭南人所说“是一杯浓浓的功夫茶”[(14)],无论怎样的艰难,无论怎样的风雨,在异乡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印尼的柔密欧·郑沉痛的倾诉:
酒精暗起乡愁的涌动
那一年
不提名儿 不提祖先
精神镣铐
夜长黑多
孤掌拍不成赞美
总算教人沉重
可要我怎样偿付
三十年的日月阴晴
上一代长期的担忧
下一代终不说母语
在这片失去方块字的土地上
繁衍了一个年头又一个年头
不得不把希望扩大
那如诗如画的乡土啊
让游子多得一张复印好吗
以共享未来可爱的如愿[(15)]
在失去了母语的空间,以及外力的干预下,“乡土”仍珍藏在游子的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人,“故乡”是实在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益鲜明的景致,这类作家几乎都写过故乡题材的作品,例如,梦莉与司马功描写过故乡已消失的或仍存在的石狮子,于梨华则完全以家乡为背景写过长篇小说《梦回青河》,等等,数不胜数。对于那些从未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作家,“乡土中国”是由父母或祖父母的口述流传而下,另有一个出生地也是“故乡”,他们对于中国怀着的可能是一种遥远的、淡淡的情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依恋。更有一些作家,主要是欧美的华文作家,他们的“中国”由于政治的因素被人为地割裂成“台湾”与“大陆”两块,他们往往出生于大陆,成长于台湾,移居于欧美,或者出生于台湾,成长于欧美。于是他们“思乡”的情愫在“岛”与“大陆”之间游移,闪烁不定。
除了个人性的“故乡图景”,在海外华文文学中,还充满了大量的人文景观表示着“华人”共同的“故乡”。最常见的是“长江”、“黄河”、“长城”、“江南”等,这些饱含着历史、文化意味的地理名词,指示着一个悠远而广博的“故乡”,是由历史与文化凝聚而成的“乡土”。尤其对于那些从未到过本土的人,这些名词唤起的,可能就是“故乡”的全部含义。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体现在对于“现实中国”的关切。
在这一层面上,海外华人作家承担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中国的变乱、前途表现出莫大的关注、焦虑。在从事此类写作时,作者自身仍是将自己作为“中国人”,并从“中国人”角度来看中国的现状及社会问题。大体上,欧美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偏于这一类型,而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则较少这一类型,尤其在战后,几乎完全没有。
知识分子,或一般民众的远避海外,本身即折射出文明古国的式微与国内政治的混乱。在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中国国内的政权更迭频仍,战事不断,受制于列强,而1949年后又有文革的“内耗”、两岸分裂的惨痛,带给中国人的是无限的辛酸,正如白先勇、张系国人的小说常常出现的一些华人形象,只是为躲避战乱、“秦祸”才远涉重洋,定居彼邦。但是,心中的“家国感”仍难以泯灭,因而,又常常为了自己不能为国家分忧而自责不已。张系国小说中有一句感叹:“假如你真的爱这片土地,你又何必出去?![(16)]但是,假如留在国内,又会怎样呢?白先勇的短篇《夜曲》与陈若曦的长篇《归》最能代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白氏的小说写到一对男女在40年代末的美国因志向不同分手,男的留在了美国,成为著名的医生;女的回到大陆建设“新中国”。近30年后,当年满怀爱国激情的小女子已变成历尽沧桑的老妇人,竟然又移居美国。在街头与当年的男友相见,不胜唏嘘,男的自责:“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女的却安慰他:“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17)]。在这里,白先勇表现出一段沉重的情绪,个人的热情与国家的现状相抵触,回去了出来,出来又想着回去。彷徨无主,仿佛是有家归不得的悲愤。陈若曦本人有过回归祖国的经历,因而她的《归》写的更为细腻,是白先勇作品中女角经历的放大,作品中的主人公听从祖国的召唤,回到祖国,但在文革期间受到种种屈辱,最终又在70年代中期出走,再度定居美国。这种回归——出走的模式,颇能代表本世纪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及亲身经历,展现的是本世纪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或爱国情怀在腐败的政治下受挫折的悲剧。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盛,必须要依赖民族主义精神所造成的凝聚力,而凝聚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国家、民族、种族三种意义上的“爱国感情”的和谐。否则,民众的“爱国感情”会成为分裂的态势。30年代的华侨领袖陈嘉庚说过:“余……所可望者祖国政府能治理良好,领导人民团结,为华侨作模范,则华侨当然响应。若祖国政府不能领导人民团结,欲望华侨先行,则无异于缘木求鱼……”[(18)]。本世纪中国社会的离乱背景,在相当长期内影响着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心态,成为他们抒发“家国之恨”的主要依据。当这种政治因素与自身的飘泊相纠缠时,更是引发一种深深的被放逐之感。而“中国”在作家心目中的形象,会因对于现实的正视而变得阴郁、黯淡。在往昔的回忆中,因为时间的洗刷或思乡本能的调节,“乡土中国”是温暖的,人情味的,是精神的慰藉,但聚焦于社会现实,不能不面对种种恶浊的现象,就像当年闻一多身在美国时,想念中的“祖国”如同花一样美,但一踏上国土,他写出的诗句却是:“不,这不是我的中华!”那么,另一个中华在哪里呢?恐怕只能在诗人的心中。印尼作家黄东平也说过:“我原以为,到了唐山,到了自己的故乡,就不必再像在海外拦风怕雨。却不料一动身,就碰到荷兰鬼重重的把鬼门关上;待到踏上咱们的国土上,遭受的还要惨……”[(19)]余光中在美国期间创作的《敲打乐》很能表达对此种现实的复杂感受:
中国中国你令我早衰
中国中国你是一场惭愧的病,
缠绵三十八年,该为你羞耻?自豪?
中国中国你令我昏迷?
何时,才停止无尽的争吵,我们
关于我的怯懦,你的贞操?[(20)]
一方面是患了梅毒的母亲仍是你的母亲,另一方面是不自禁的困惑、质疑。矛盾的心情折磨着海外华人作家,在陈若曦、张系国、于梨华等作家笔下,回去还是留下?该不该出来?该不该回去?总是构成叙事的主要线索,牵动着人物的行为。而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被这样的自我追问弄得恍惚迷离,不知身在何处。
80年代以后,由于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上述的情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逐渐消失。陈若曦在《向着太平洋彼岸》这篇小说中,借一位遭受文革祸害而后移民到美国的人物说:“时代变了,时代也是前进的。而中国,带着她的人民和土地,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永远等候在那里。”[(21)]就在这一篇小说中,她让一位海外华人最终决定回到祖国,因为改革开放中的祖国需要人才。在聂华苓的一系列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意向。也许经过一段血泪翻腾的历史,在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刻里,中国人,无论海外的,还是海内的,都能告别那种畸形的、分裂的“家国之恨”,而拥有一种全新的、健康、平和的“中国形象”及“中国情怀”。
第三,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体现在对于“文化中国”或“美学中国”的渴求与向往。这是一种更深幽的乡愁,追寻的并不是童年的记忆或故乡的怀恋,也不是对于中国现状的关切、焦灼,而是要回到永恒的“古典”,因到那种超越于时空之外的气韵,回到由孔子、老庄、屈原、唐诗、宋词等等积淀而成的“美的家园”,“回到一个纯真的起点”[(22)]。
叶维廉曾说:“由于空间的切断而产生的游离不定、焦急的心理状态,如何在诗的创造里找到均衡,在传统与现实切断的生活中重建文化的谐和感而重新可以沐浴于根生于古典的美感经验中。”[(23)]叶氏透过诗的创造作着这样的努力,从60年代至今,他孜孜不倦的,是铸就一种纯净的汉语,酿成一片自然的诗意,其中的背景令我们联想到老庄哲学。在他的部分诗作中,几乎有着神话般的调子,在一唱三叹的大神秘中,唤起的是对于“古典”的无限联想,倒如他最近的诗作。
来来往往
纵来
纵往
横来
横往
斜来
斜往
合而分
分而合
合而复分
来来往往
无休止地
来来往往
为等待 那 一朵花开?
为等待 那 一只鸟鸣?
为等待 那 期待多年的女子?[(24)]
在最质朴的文字推演中,心的玄思与惆然,尽在其中。“来来往往”的循环,为的是等待一朵花、一只鸟、一个女子,时间隐退成虚无,凸出的是要等待的三种意象,而此三种意象暗示的正是“古典美学”的不同侧面。
杨牧、郑愁予等有着相同的努力,他们也喜欢以古诗词的意境,来整合现实的支离破碎。杨牧将自己幻化成“敲着木鱼流浪”的小沙弥,“在维多利亚的书房中/然后回到唐代,在黄金的亭台上”[(25)]。郑愁予认为诗人应当有一种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并不是政治上,而艺术上的”[(26)]。
“文化中国”或“美学中国”的塑造,是基于中国文化在五四以后的破坏气氛中不断断裂的情势,作出的一种自我延续的反应;海外作家由于身处海外,空间的疏离更加强的此种反应。如果联系到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从最低的层面到最高的层面,都呈现出被肢解、被蹂躏、被遗忘的命运,那么,我们就能格外领会这种文化或美学的中国意识的独特含义。当然,这种意识与政治上的复古主义完全不同,它只是一种审美的产物。
三
作家的中国意识对于他(她)的美学风格无疑会有所影响。当一个作家有意地要通过写作来呈现“中国意识”,他的写作策略必然地会与另外一些作家——比如那些有意地要表现普通人性的作家有所不同。在叙述或抒情中,他会用本国的文化与语言去组织眼前陌生的、零乱的经验,从而迷离于错失的时空与不和谐的景象。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倾听到两种意识状态的声音,一种由汉语所制约着的中国世界,另一种是现实的生存世界;他会倾向于用前一种世界去比附、去整合后一种世界,甚至试图让后一种世界淹没于前一种世界中。最典型的文本如凌叔华的散文《我所知道的槟城》,几乎所见一景,都联想到中国的类似的影像,整篇文章与其说在写槟城,倒不如说,在借眼前之景写心中之景。因而,这类文学作品的基调是感伤的或悲剧性的,总是潜藏着一个被记忆磨炼成美丽的从前世界,总是面临着被割裂的恐惧,在冲突中寻求和谐、在飘荡中渴望归宿。叙述模式总是基于主人公与当下环境之间的磨擦、交锋;一方面是被同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要留住的欲望与冲动。意象营造则偏于烘托纯粹的古典意味的中国境界,但一触及当下的情景,就会变得无所适从、无法调和。这一类文学作品还有焦虑的一面,这与整个“中国”在现代的式微息息相关,回复旧日汉唐气象变成内的情结,使语言也仿佛因焦虑而呈撕裂的态势。
总之,感伤、悲剧、回忆、焦虑是理解这一类作品美学风格的关键语汇。文字织染层叠的经验世界,暂时或永久地庇护着那些失去了“家园”的人群。在“中国意识”的诗化过程中,我们目睹并感觉到了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一个种族的蜕变过程,其间的痛楚和悲壮,都以故事或意象无声地诉说,为一段重要的历史时刻存真。
最后,我们要想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海外华人作家都具有“中国意识”,他们或者只是保持了最基本层面的汉语,或者完全转向另一种语言,只是残存着一点点体内的血脉。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指责他们“不爱国”或“数典忘祖”。实则上,文学中的“中国意识”与政治的“爱国主义”可能并不统一。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活动,是否表现“怀乡”,是否表现“故国现实”或“文化”,也许并不能决定一个作家的价值。作家有权利选择他所要表现的东西,关键在于他是否达到了“真善美”的境地。事实上,90年代以后,本土的研究界可能要矫正一个错觉,那就是:一提到海外华文文学,便浮现起一张张思乡的脸庞。我们必须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无关“中国意识”的海外作家,如近年来相当活跃的虹影,她的作品几乎看不出一点“海外”的痕迹,她追求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风格。这类作家越来越多,其实说明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已经使海外的华人不再那么迫切地感到“中国”问题的压力。在这样的状况下,海外的汉语文学也许更能够发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注释:
① ②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③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④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叶维廉主编,台北联经1977年版。
⑤ 出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⑥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一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2页。
⑦ 例如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等人的著述中都留下了当时他们所见海外华人的生活状况,而且行文中充满“民族主义”色彩。
⑧ (11) 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1912—1937年》,载《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⑨ “华侨”的称谓意味着“暂时居住”,最终仍要回到中国;所以,华侨一词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可否认的。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废弃了血统主义的原则,规定一旦加入外籍,即自动放弃中国籍。
(12) 《海外华人作家诗选》,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3页。
(13) 《泰华文学》,香港文学世界社1991年版,第534页。
(14) 《泰华文学》,香港文学世界社1991年版,第537页。
(15) 柔密欧·郑:《变》,载澳门《浮蝣体》1994年第2期。
(16) 张系国:《地》,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41页。
(17) 白先勇:《夜曲》,载《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0页。
(18) 《陈嘉庚文集》第1卷,第34页。
(19) 转引自潘亚暾:《反压迫争自由之歌——黄东平〈赤道线〉序》。
(20) 余光中:《白玉苦瓜》,台北,洪范书店1974年版,第3页。
(21) 《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60页。
(22) 《海外华人作家诗选》,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5页。
(23) 《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台北,源成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476页。
(24) 叶维廉:《气象之歌》,载1993年冬季号《创世纪》。
(25) 杨牧:《异乡》,载《杨牧诗集》,洪范书店1978年版。
(26) (27) 参见彦火:《海外华人作家掠影》,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83页。
标签:文学论文; 海外华人论文; 华侨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中国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