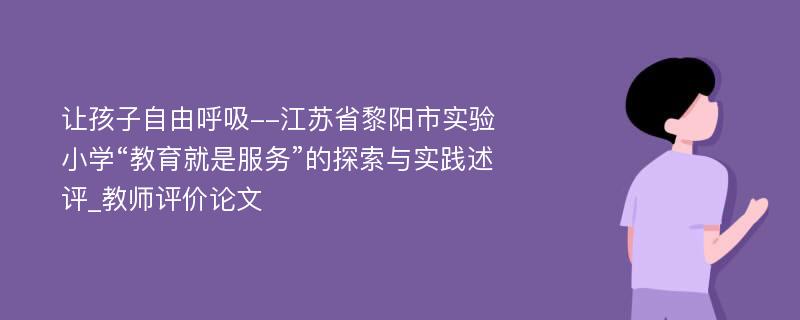
让儿童自由地呼吸——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教育就是服务”探索实践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溧阳市论文,侧记论文,江苏省论文,实验小学论文,呼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儿童的视角,儿童的立场
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实小”)有点“怪”。
许多名校都以考试成绩、各种竞赛活动名次第一为荣,实小却认为,总想得第一,总想超过别人,教育反而上不了档次。校长芮火才笑称,自己喜欢看武侠,发现那些一心要争天下第一的人基本没有好下场,“要争第一就得练特别的武功,而特别的武功总是对人有害”,教育也如此。
许多学校谆谆教导学生,见到老师长辈要首先问好,这是文明。实小却反其道而行之,校长见到老师,校长首先要问好,老师见到学生,老师首先要问好,否则,老师、学生对校长、老师可以“置之不理”。
许多学校若发现了学生踩踏绿地,首先想到的是教育学生要保护环境、爱惜花草。实小的第一反应,却是检讨学校自身的问题:建绿地的时候,留给学生的过道是否太窄了,以至影响了学生通行?
许多学校考评教师,来得早、走得晚是兢兢业业的表现,要表扬。实小恰好相反,除非特殊情况,来校太早、离校太晚的教师要挨批,因为他们很可能侵占了学生的自由时间。
……
种种“怪现象”,都与实小的教育追求密切相关。
那就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实践的“教育就是服务”的理念。
何谓教育就是服务?简言之,就是学校教育必须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引导和校正其不合理需求,丰富和提高其单一、浅层次的需求。其灵魂就是“以学生为师、为学生服务”。其要害就是重新调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使校长、教师由高高在上转变为与学生、家长平起平坐,真心实意服务学生、服务家长。
这是彻底颠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把儿童真正置于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这无异于一场教育革命!
1998年前后,芮火才提出这一理念的时候,同行质疑,专家反对,至今仍争议不断。然而他与实小义无反顾。
1981年中师毕业就从教的芮火才,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教育是什么?他读了很多理论著作,听了许多专家讲座,但没有一个答案令他满意。
直到两个不太起眼的教育事件发生。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还只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两周一次的校行政例会如期举行,主题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研究进一步改进的策略。大家发言热烈,行政人员一致认为,老师们工作尽心尽力,极其出色,各项改革成绩巨大,学校工作上了新台阶。似乎一切都很完美。
偶然地,有人提议,是否开一个学生座谈会,听听学生的意见?
谁曾想,学生座谈会与行政例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人赞扬学校工作,而是纷纷提出尖锐的意见:有的说学校操场太小,应该重建一个大操场;有的说走廊太窄,应该改宽一点;有的说许多同学喜欢排球,应该开办排球兴趣小组;有的说学校组织的活动太少,建议多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为什么学校管理人员、老师自认为工作圆满,学生却还有如此多的意见?
芮火才陷入了沉思:是的,我们一直在让学生达到我们设定的理想教育目标上下工夫,却从未考虑这样的目标学生能否理解、接受;我们一直千方百计去促进学生的成长,但往往只是满足了学生的部分需要或者部分学生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学生的整体需求和不同学生的需求;我们一直努力去爱学生并以爱的名义去教导学生,但往往忽略了随着社会的开放、信息时代的到来,儿童的独立意识、权利诉求空前增强。
必须为新时代的教育注入崭新的内涵!
另一件小事也同样震撼着芮火才。
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为了加强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作为学校政教处负责人的他,要求值周教师每天早晨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进校时是否主动问候值周教师。一旦学生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不但要扣除其班级常规管理的得分,还要求其退出校门重来一次。芮火才还多次到校门口亲自督察,并板着脸训斥过不少学生,也批评过那些所谓工作不得力的班主任。“那时候觉得这天经地义。”尽管如此,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不但主动问好的学生没有多起来,就是主动问好的也多是迫于学校“压力”,根本谈不上文明的自觉。“我们感慨学生的文明素养怎么这么差!”有一次,一位学生悄悄问芮火才:为什么我们向老师问好后,有的老师却不理睬我们?又有一次在学生座谈会上,一个学生质疑:为什么一定要学生先向老师问好,能不能老师先问我们好?
是啊,要让学生有道德,老师先要有高尚的人格。教师作为道德的示范者,为什么不能先向道德人格尚在成长中的学生问好呢?“敬人者,人恒敬之。”要赢得学生的尊敬,老师首先要善待学生、尊重学生。
然而我们的教育常常颠倒过来。因为我们一直缺乏儿童的视角、儿童的思维,因为我们一直不理解儿童、不相信儿童。
芮火才想起了陶行知的一首打油诗:“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小,便比小孩还要小!”
作为教育者,我们怎样才能不比小孩还要小?芮火才的答案,就是把曾经颠倒的校正过来,把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指南针”,用儿童立场来审视学校教育的一切。
这就是“教育就是服务”。
当然,芮火才并不否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制度文化对儿童的“规范”,但他认为这种“规范”应以充分尊重儿童为前提,以不扼杀儿童的个性为基础,以儿童的自我认同和积极参与为过程;他更不否定教师在学生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但他强调教师不应是学生发展的“主宰”、传授知识的“权威”,而应是学生前进道路上的引路人、学习研究的合作者、发展进程中的服务员、共同成长的好伙伴。因此,笼罩在教师身上的神圣光环必然暗淡,但不必担心教师尊严的丢失;学生个性必然得到充分的张扬,但无须担心学生主体发展的迷失。
由此出发,芮火才和实小对一些教育“常识”便有了新的理解:
学生上课不守纪律,是学生的问题吗?不一定。很可能是老师的教学不精彩,不然为什么同样的学生上别的老师的课很守纪律呢?
学生作业不能及时完成,是学生的过错吗?不一定。很可能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有问题,或是太难,或是太多,或是没有了解到学生的特殊原因。
班级里有40位学生,其中39位发展得很好,只有1位同学不理想,是这位学生的责任吗?不一定。既然39位同学在老师的帮助下都获得良好的发展,为什么就不能让这1位也发展得好呢?很可能是老师还没有找到满足他需求的方法。
教室门窗的油漆用什么颜色,能由学校总务处决定吗?不能。应该听听大多数学生的意见,然后选择他们喜欢的颜色。
……
用这种思维方式思考学校教育工作,便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按成人标准建造的楼梯跨度太大,影响了学生上下楼梯的行走;按教师视线设计的橱窗太高,影响了学生阅读;按教师的价值取向张贴的伟人语言与学生的生活相去甚远,学生并不理解,等等。
1998年,开始担任校长的芮火才,毅然按照“教育就是服务”的理念,去改造实小的管理制度、课堂教学模式、学生活动组织方式……实小的教育生活由此焕然一新,前述种种“怪事”便见怪不怪了。
学生的生命需求,决定学校的教育追求
有什么样的教师评价,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教育。
“教育就是服务”要转变为学校教育的现实,首先必须革新教师评价。
芮火才的第一板斧,就是砍向教师评价这块硬骨头,真正把选择、评价教师的权利交给学生、家长。
这就有了实小的“学生、家长选师制”、“教育投诉制”和“信任投票制”。
○选师权,教育的“自由恋爱”
2000年8月30日,一条新闻轰动了溧阳中小学:实小新入学孩子的家长现场自由选择老师啦!
那一天,实小人流如潮。一年级300多名学生的家长全部参加了选师活动。许多家庭一家三口悉数到场,有的还拉来亲朋好友当参谋。他们仔细阅读学校的宣传资料——两天前,学校要求每个老师上交200字左右的个人介绍,如今已张贴在展板上;有的还直接与教师交流,深入了解每个教师的个性特长、教育理念,末了,他们还与孩子商量,最后慎重作出选择。
尽管学校已经充分考虑每个班级师资的均衡,但是,还是出现了选择的“偏向”:有两个班选择的人数远超过班容量,还有两个班正好相反。
无奈,学校只好采用事前与家长约定好的办法——“抽签”:抽中者进入,其余调剂到人数少的班级。如愿以偿者如同中了彩,激动得跳起来。没有“中彩”的也很大度,说:“有选择的权利总比没有好!
好一个选师权!
良好的教育应该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自由恋爱”,互相欣赏,互相信任。
然而传统的思维方式,分班是学校的“专业权利”,不需要征求孩子、家长的意见。当然也考虑学生的情况,比如性别、成绩,但这主要是出于“竞争”的需要,而与师生之间、家校之间建立融洽的教育关系无关。教师还是这些教师,学生还是这些学生,他们之间的相遇却总是难以碰撞出“教育的火花”。
必须给被教育者选择的自由。
学生、家长对教师的选择多一分自由,教育就可能多一分美好。
教师的压力增加了,但这是“真实的压力”。“有些学校,老师动不动就把家长喊来训一顿,动不动就给学生脸色看。”芮火才说,“我们的老师相反,看的是家长的‘脸色’行事。”实小的教师必须在乎学生、家长的利益、需求,“因为他们是被学生、家长选的,如果还高高在上,人家不买账!”
教师的面子似乎没有了。每次选师活动,面对几百个家长“上下打量”、“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的老师觉得自己就像菜市场的商品。但实际上,选师选出的是家长的信任、教师的尊严。首届选师活动亲历者肖爱琴老师对此深有体会:“因为选择,所以信任。老师跟家长、学生相处得特别好。每次开家长会,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都心有灵犀。家长之间很熟悉,你说一句,有人支持有人反驳,非常融洽。老师、学生、家长,就像一个联盟。教师很有成就感、幸福感!”
○有意见,投诉
随着首届选师活动的成功实施,实小的选师从一年级扩展到三年级、五年级,即意味着小学6年,学生、家长有3次选择教师、班级的机会。但是,从本质上说,“选师制”仍只是对教师工作的一种事前评价。
重要的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过程进行及时、准确的评价、监督。
以往的做法,主要是检查备课笔记、听随堂课、查阅教师批改作业的情况等。这种自上而下的外在评价,既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教师教育行为与学生教育需求的对接,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管理实效。“我们学校有120多位教师,平均每位教师每学期至少有260节课,全校每学期就有31000多节课,而所谓的学校管理者不到20人,每人每学期一般也就听课40节,不到总课时的百分之三。”这样的过程管理只能是蜻蜓点水。
怎么办?
芮火才认为,只能让接受教育服务的学生、家长成为评价、监督的主体。
其具体形式,就是“教育投诉制”:任何一位学生和家长都可以对学校和教师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对学校和教师工作中不满意的地方进行投诉。学校在24小时内对投诉的情况进行核实,把处理意见反馈给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投诉人作出向投诉人赔礼道歉、扣发被投诉人奖金、学校解除与被投诉人的聘用合同等处理。
家长可以书信投诉、当面投诉、电话投诉等,但最为人称道的是网上投诉——在实小的网站上,专门设置了一个“互动平台”。
“这个‘平台’,不但我们的家长看,溧阳所有的教师都看。”因为在这里,可以听到家长、学生真实的声音;不但如此,教师也可以自由地向学校、校长提意见,乃至发泄不满。
学生、家长真的敢摸“老虎”(校长、老师)的屁股,尤其是像实小这样的名校?就不怕说尖锐了遭到报复?
五年级学生家长朱女士说,这不是问题。“在‘互动平台’上,我们都是匿名的。即使暴露了身份,也不用担心。现在大家维权意识都很强,如果老师真的报复,可以投诉,学校会处理他的。”她就曾经投诉过一个老师,当时,那个老师正训斥一个学生,情绪有点失控,她看见了,就在“互动平台”上提了意见。学校很快进行了核实,结果“那个老师向被训斥的学生道了歉,学校还在‘互动平台’上公布了这件事”。
○教师工作好坏,学生(家长)说了算
最后一环,是对教师工作进行事后评价,即“信任投票制”。
每个学期,实小至少要组织一次全体学生、家长对任课教师的信任投票活动。对老师的评价就分成三个等第: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如果学生或家长对某位教师工作的满意率达不到50%,该教师便不能再担任该班孩子的教学任务,处于待岗状态;如果达不到90%,取消评优资格。如果学生或家长对某一年级组教师工作的总体满意率达不到80%,就不能被评为先进年级组。
当年芮火才宣布这个改革时,校内校外一片哗然。
学生懂教育吗?家长理解教师的工作吗?凭什么让他们对教师的专业行为品头论足!
近年来,教师评价已经尝试倾听学生、家长的声音,但仅仅是尝试,被教育者对教育者的评价,不过是作为一种参考。
从理论界到实践一线,有一个共识,即学生、家长不可能科学评价教师。
芮火才不以为然。
“学生、家长对老师的评价是学校评价老师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评价权利不交给服务的对象,就不会有好的评价。学生、家长不太可能把一个好老师评得差,相反也不太可能把一个差老师评得好,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必须把评价教师的权利真心实意地还给学生、家长!
改革之前,他特意举办了一场辩论会:学生、家长能不能评价教师?
提前1周,学校让教师自愿报名、自愿组成正反方。辩论那天,还邀请学生、家长代表参加。那天的主角是教师,没想到学生的即兴发言反而抢了老师的风头。
“老师辩论完后,学生自然分成两派进行争论。”芮火才回忆,“一个说:学生不能评价老师,如果老师对学生严格,学生会报复的。另一个说:这不可能。老师对我们好,我们是知道的。如果他严格,学生就报复,说明他严格的方法不对。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家里养了一只狗,每天回去我都要抱抱它,我还没到门口它就来迎接我。有一天我心情不好,见到它就一脚踢过去,第二天它见到我理都不理。狗都知道主人好不好,更何况人呢!有的说:家长不懂教育。有的不敢苟同:我爸爸的水平就比教师还要高。有的说:家长接触老师少,怎么知道老师的好坏?马上就有人反驳:家长评价老师的工作主要是看我们身上发生的变化,通过我们身上的言行就能判断老师的工作好不好!”
多么精彩!
学生、家长能够评价教师的观念,逐渐为实小人所接受。
但是,困惑又来了,学生、家长的评价科学吗?
是的,学生、家长评价教师,“用的不是我们专业人员的语言,也不是我们的标准,而是他们的直觉、感觉”。哪个更科学?
芮火才认为是后者。“我们的评价就是一张表格,把老师的工作切割成师德、科研等几个部分,即试图用这张表格把教师的工作还原出来。其实这是做不到的。教师的工作效果有滞后性,同时具有集体性,是学科老师、班主任及学校其他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要评价其工作效率是困难的。”但是,“学生、家长的直觉、感觉,是在与老师相处很长时间至少一个学期的基础上得出的,他们与老师有很多交流,这个感觉是整体的、真实的,相对来说反而比较准确。”
对芮火才来说,学生(家长)评价老师不存在任何问题,包括幼儿园的孩子。他的重外甥在实小幼儿园就读。学期末,孩子把评价表带回来,家长不在,就找到芮火才:“姨公公,你读题目,我来打分,你帮我填上去。”带他的一个是朱老师,一个是李老师,每个老师5个问题。“朱老师全部打满意,李老师全部不满意。”为什么?“朱老师对我们太关心了,虽然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从来不乱批评。李老师在我们中午睡觉的时候,和其他小朋友讲话,有时还吃东西。”
仅凭两个细节,就把老师评价为差,科学不科学?“科学。”芮火才认为,“人的教育素养总是通过若干细节表现出来的。你和小朋友讲话,影响其他人睡觉;吃东西就更不应该了。一个好的幼儿园老师是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的。”
就这样,实小把评价教师的权利真正还给了学生(家长)。
有人担心:这样,学校教育是否会被家长、社会牵着鼻子走呢?否。
芮火才一再强调,“教育就是服务”理念的核心,是要满足学生、家长合理的需求,是让学校向家长开放、向学生自由的心灵开放,而非一味迎合。
2008年,实小学生食堂管理进行了改革。有的家长不太满意,就提意见:现在家长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每天让孩子在学校吃食堂,要么就一餐也不允许学生在学校吃”,方便了学校,为难了家长,因为“学校平时的伙食很差,而且孩子回来总说吃不饱”,就没让孩子在学校吃,遇到下雨天,孩子的午饭就成了问题,“这样的(管理)模式很不人性化”!
芮火才很快作了回复:食堂改革,不仅方便学校管理,更重要的是厉行节约,保证学生吃饱,争取让学生吃好,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用餐习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改革后,“家长们并非只有两种选择,如遇特殊情况(包括特殊天气),你可以请班主任带孩子到食堂就餐,餐费直接付给班主任”。另外,如果孩子不挑食的话,吃饱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伙食是否很差,“这要看你与什么地方的用餐相比”,与高档餐馆比,学校食堂的确要差些。
这不是有点针锋相对吗?
是的。如前所述,引导和校正学生、家长的需求,是“教育就是服务”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这种引导、校正,是基于对学生、家长的尊重,是基于教师、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人格平等。
学生(家长)的教育“话语权”有了充分的保障,教育者勇敢地宣称“我们,站在孩子这一边”,学校才可能自觉把儿童生命成长的需求转化为自身的教育追求,教育才可能拒绝浮躁、回归朴实,拒绝功利、回归常识。
个性,自由的个性
从实小走出的学生,身上都有深深的“烙印”——有个性。
“初一的老师往往‘讨厌’我们的学生。”芮火才说,“上课时我们的学生会插嘴,作业负担重一点他要抗议、投诉,老师讲得不对他要提出来、要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
初一时,来自实小的孩子学习成绩往往靠后,但是到了初二、初三,他们强大的学习后劲爆发出来,“到初三毕业,后来居上的学生大多都是实小的”。即使一直学习较差的学生,也很阳光、自信,有主见;他们见了老师也不怕,有的遭到老师不合理的批评,还会还嘴:你以为我以后没有出息呀!
初中老师对实小学生是爱恨交加。有的初中校长就对芮火才说:芮校长,你要适应我。芮火才回敬道:你错啦,是你要适应我,不是我要适应你!
学生的个性,是芮火才和实小的老师们有意“惯出来”的。
芮火才认为,只有给予学生最大的自由,学生才会有最大的发展。
他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每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10%的学生,老师每天不要布置作业,让他们自己决定做什么。“6年下来,这些孩子比那些天天做老师布置的作业的,发展的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这当然无法实现。实小除了严格执行国家规定——一、二年级不布置作业,中年级作业基本在学校做完,还进行寒假作业、暑假作业“革命”:老师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好,成绩好的学生就把简单的题目全部划掉;后进生就把难的全部划掉,只留努力后能够做出来的。“我们只让孩子做有价值的作业。”
同时,建立“清校制度”:下午4点40之前,学生必须全部离校。个别学生需要辅导,老师必须征得学生(家长)的同意,否则一律禁止。
这样,就留给学生大量的自由时间,他们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有的家长甚至“抱怨”:实小的作业太少了,孩子太轻松了。
芮火才就给他们讲农民插秧的经验:刚插的秧苗,如果施太多的肥,很快就长得绿油油的,非常喜人,但长大后,稻穗风一吹就倒下去了,稻谷也多是瘪的,产量反而不高。小学阶段就像刚插的秧苗,还没到狠命施肥的时候。
芮火才和实小从不把学生的分数看得太重。
在实小,分数是学生的隐私,教师没有权利公布学生成绩。因为他们不鼓励学生进行分数竞争。
他们在乎的是孩子的童年生活是否丰富多彩、自由快乐。
他们把课时压缩为35分钟,每天因此多出一节课,这节课谁也不能侵占,而是留给校本课程:一年级“动手做”、二年级“经典诵读”、三年级“小足球”、四年级“棋类”、五年级“地方戏曲”、六年级“篮球”。
他们在乎的是孩子的民主意识是否得到保护、话语权是否得到尊重。
他们提出“服务型课堂”的理念,认为教师的职责主要是创造适合每个学生学习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不断满足并转化学生的学习需要,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和谐发展。于是有了“10+6”教学模式,要求每节课老师讲授时间不超过10分钟,学生笔练时间不少于6分钟,把课堂空间尽可能留给学生言说、表现、锻炼。
他们变“学校的艺术节”为“学生自己的艺术节”。艺术节项目的设置、方案的制订、活动的组织、节目的评判,都由学生自己做主。这样的艺术节就真正成了每个学生的节日。
他们提倡学生自治,成立学生自主发展联盟,把管理权交给学生,最大范围地让他们管理与自己发展有关的活动;推行班级自治,让学生自己制定班级愿景、班级公约、推选班级管理服务小组或考评监督小组、参与学期评优等。芮火才一再对老师讲,学生之间发生矛盾后,老师先不要自己去处理。“首先让两个当事孩子自己谈判,看看两人能不能把事情摆平。谈判的过程就是他们学会与别人交流、与人相处的过程。他们俩谈不拢,再发挥班级委员会的作用,让学生自己调解。实在不行老师再出面。”这样孩子从小就懂得规则,懂得民主。
他们精心呵护学生的独立人格。
他们与学生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一次,芮火才与三年级孩子一起打篮球。学生突然问:“芮校长,你读小学时有女孩追你吗?”芮火才没有板起面孔,而是笑眯眯地回答:“没有,我长得丑。”旁边的伙伴指着这位学生:“有人在追他!”芮火才还是笑眯眯:“是吗?”“有女孩子送东西给他吃,因为他长得帅,成绩好。”芮火才一笑了之。
他们特别能包容孩子的“冒犯”。有一次,芮火才在路上遇到一位学生。那个学生大喊:“芮火才!”旁边的孩子说:“你找死呀,怎么直接叫校长的名字!”芮火才赶忙说:“没有错呀,我就叫芮火才。我还要感谢你呢!”“你听听,校长就是校长,不和你一般见识。”学生还向同伴炫耀!
他们特别能欣赏孩子独特的内心世界。一天,芮火才在学校碰到一位学生,独自一人坐在操场边,不去上体育课。他问:“锻炼是好事情,你怎么不去锻炼呢?”“校长,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锻炼?”“你额头上都没有汗嘛。”“我额头上没有汗,你怎么知道我身上其他地方就没有出汗?”愣了一下,芮火才又说:“和同学们一起上体育课,参加集体活动不是挺好吗?”“哼,那群泛泛之辈!”他又愣了一下,最后说:“哦,人有时孤独一下也蛮好。”事后,芮火才感叹:学生都是天生的哲学家!
如此,实小的孩子渐渐“不安分”起来。
几年前,上级督导评估组来实小检查,听完课后。提了一条意见:其他学校的孩子都彬彬有礼,你们的孩子上课插嘴、调皮,课堂有点乱,应该加强规范教育。
其实,在芮火才看来,孩子有主见,活跃一点,正是教育应该追求的目标。
他常常向老师们推荐一本书:《夏山学校》。他心仪的教育正是这样: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
他的教育理想,是创造一个有几分像夏山样子的自由校园。
在这个校园里,孩子们心灵自由、思想开放、人格独立、个性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