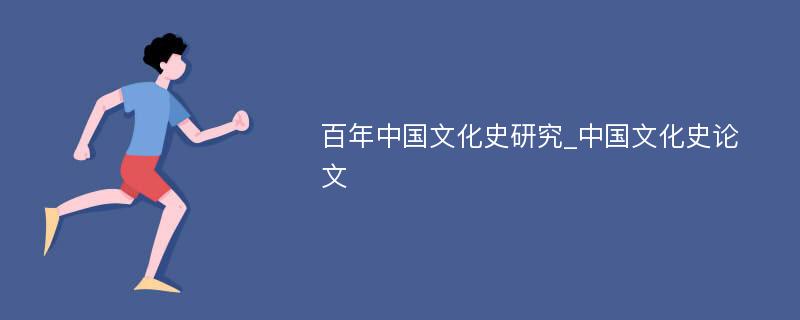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研究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国力陵夷,声势迫蹙”,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是“怀百岁忧者,常有故国文物,日薄崦嵫之感”。另一方面是“欧化”思潮弥漫一时,“西洋皆好,中国皆坏”差不多成为“国人自命为明达者之普遍观念”,“全盘西化论”的提出更把这种思潮推往极致。民族自信力的丧失,成为当时极为严重的现实。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唤起民族自信心。陈登原在《中国文化史·叙意》中便语含深情地指出:面对“莽莽欧风卷亚雨”,“斤斤以中国文化自傲”固然不足取,“然故家乔木,终有令人可以式仰者”。“观于吾国文化之大而且高若此,则使国民得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者,必有在矣,必有在矣。”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要略·叙例》亦陈词云:“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他撰著《中国文化史要略》以振奋民族精神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萧一山在该书的序中明晰揭示王德华的这一意蕴说:“王君是书,殆亦感于国难之严重,而欲借史学以启发民族精神,当经世致用之旨欤?”“王君是书,……窥其大意:一曰发扬民族精神;……一曰发扬士人之正气。”《书林》1卷3期评价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时,也着意阐扬陈著的现实意义:“吾人欲起其(国势)沉而救其衰,不可不知近世的史实。欲使文化的程度有进步,以发扬我故有的光明,迎头赶上他国,亦不可不知近世的史实。这是此书作者著作的美意,实为吾人所切需而必读者。”大半个世纪后读这些文字,仍然令人感到激情潮涌,并对我们的先行者深怀由衷敬意。
80年代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对建国30年来“阶级斗争史学”的反拨,但在更深层次上,同样回应着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的改革开放迅疾向纵深推进,它广泛涉及传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中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双重价值意义。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或系统意义上是一种反映、说明和维系传统经济局面和政治局面的思想体系,因此,它势必抗拒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面推进,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必然对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产生强大的冲击,提出建立一种积极的、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价值体系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只能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点上,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源头活水。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其全部意义正在于此。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前景”等等论题才会在80年代以来被一再提出来加以讨论,而每一次讨论,都必然伴随改革进程的深入,展示出不断更新的思路,得出新鲜的结论,从而推动文化史的研究成为持续性的热点,迸发出极大的魅力。从这一意义上言,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不仅是史学范式的转型,而且是中国现代化思潮中的有机部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血肉的联系。
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
美国史学家卡尔在60年代末曾宣称,社会学越是向历史学靠拢,历史学越是向社会学靠拢,双方的得益便越大。20年后,文化史学家亨利在《新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也许,不久的将来,另一位卡尔会宣称,历史越是向文化研究靠拢,文化研究越是向历史研究靠拢,双方的得益便越大。”这种得益实际上十分鲜明地体现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之中。
首先,文化史研究综合了不同学科的学术立场和视野,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献学、地理学、生态学都成为文化史研究借鉴的领域。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史并不是一个范围或内容的问题,而是一个方法问题。说得过头一点,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因此有多多少少可以包括在文化史的领域之内。如上两大基本特点赋予文化史活跃的思维和宽广的视野。文化史研究之所以生机蓬勃,文化史论著之所以具有广泛吸引力和极大魅力,其奥秘正在于此。
然而,文化史研究固然视野宽广,却绝非泛漫无际。它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正是这一思维线索,确定了文化史与传统史学以及其他专门史的不同风格和路向。本世纪100 年中相继问世的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王毅的《园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冯天瑜等著的《中国文化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都在探索、展示民族精神的生成与延伸上有独到的成绩。文化史研究的特点还在于,它既不是形而上一路,也绝不是形而下的。它研究物质,一定要看到其间内隐的精神;它研究精神,一定要注意它的物化的外显的形态。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研究方法,都赋予文化史研究“新史学”的色彩。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史学,其革命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100年过去了,这是一个个体生命难以逾越的长时段, 但对于经历了“中绝”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一切仿佛才刚刚开始:文化史的概念有待于进一步厘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研究有待于推向深入。然而,只要我们确信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可以同样确信,文化史研究将一定会以蓬勃锐气和旺盛的生命力走向成熟和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