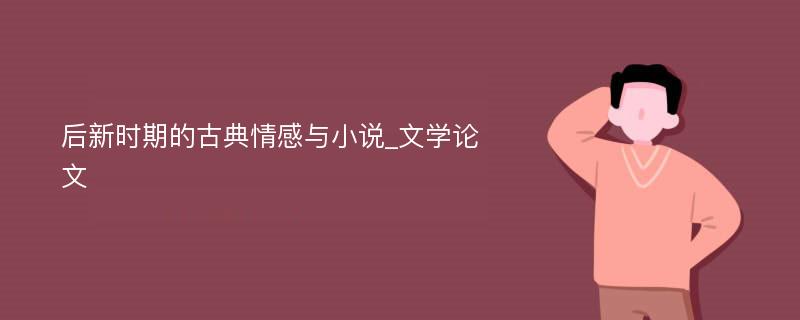
古典主义情怀与后新时期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情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整个新时期将近20年的文学发展,一般都以80年代末来划分前后两个阶段,与前新时期相比,后新时期文学分化剧烈,没有主潮。
没有主潮的文学是相对自由的文学,边缘化的地位能产生边缘化话语。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边缘化话语的涌流,自由自觉创造性活动的展开,前提条件之一是,依赖于摆脱载道工具的后天宿命的完全自由形态的文学,一种非逻辑的精神表达方式,其源头不在《诗经》和《楚辞》,而在解构了政治功利主义原则的庄子散文。后新时期小说里,张炜为之意醉神迷的故土野地和那个仿佛遗世独立的“小村”;贾平凹意象世界的商州山水和“云层上面是阳光”的生命境界,那种乌托邦寓言式的精神寄托方式,其历史端绪正指向庄子。
然而,自由是一柄双刃剑,过分“失轻”的文学难以承担起存在之重。当价值成分被大幅度抽取出文学话语,当无情的解构超越了一定的限度之后,文学也就失去了它虚实相生的天空和大地。更何况,在大多数作家那里,“自由”目前还只是个奢侈品,是个“远方的金苹果”,受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经济又成了他们“巨型话语”的诠释对象。故而,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便造成了文学“持续多年的精神恶化”(王晓明语),这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缘此而发。
对“精神恶化”现象的感受竟是如此普泛,致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学者卷入了这场讨论,人们有理由对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小说表示不满,在市俗化、商品化、非意识形态倾向和浓重的后现代情绪造就之下的文学风景线里,语言的膨胀过剩和意义的萎缩消解已是一种明显的趋势,尽管我们明白,短短几年的文学,实质上仅是一种对旧有的破坏,是一种发展、变革的极其重要的过程,但是作为文明社会的当代人类,总要有点什么精神,不可能也不应该丧失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忘却对人生存在、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解构如果仅仅是作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对立的一方对解构的企图表示怀疑,则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拒绝了一切,也就拒绝了人类自己;如果毁灭了一切,也就毁灭了存在之境,文学不可意识形态化,不可道德伦理化,但还应该有些认真思考,因为文学最终还是写人和作用于人的。
应该承认,对文学来说,价值尺度的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发展。我们固然不满意一些虚无主义的作品,但也常常对那些以圣主的口吻来对凡俗之众发布严法峻律的“教谕”式作品敬而远之。因此,在大讨论中张承志那种对绝对“清洁的精神”的召唤难以和大多数人产生情绪上的真正共鸣,也就势所必然了,人文精神的合理尺度,的确在于“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需求”。 [①]作为概括性的提法,我认为现在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古典主义情怀,它是对我们整个精神状况的深刻回应。
对于古典主义情怀的认识,首先它是一种恒久性的精神价值,所谓传统性和现代性这种形而上的机械的两分法,是难以框囿住它绵延不绝的时间界限的,古典主义情怀的某些部分,可能产生于古代,但它绝不仅仅属于古代,比如我在下面想要针对后新时期小说予以具体分析的人间温情、世俗关怀和价值追问,这些由中外古今伟大文学艺术融铸而成的生命意向和价值热望,就是亘古难绝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典主义者,在杰出作家的创作中,总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汇合,即发生在我们所称的“古代”,另一股则蕴蓄深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经受过岁月风雨的洗礼,其中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就留存了下来。更何况,不同的时代形态和历史结构,里面一些必然元素,又能有多少差别呢?“倘若历史总是重演同样的事件,历史就会是无聊的。倘若历史仅有千差万别的形态,历史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于是乎,也同样就会是无聊的。历史在陌生中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饶有趣味,人们在历史中挖掘得愈深,历史就愈具有典范性;最后,人们达到永恒人性的层次,在这里,事物虽然披着绚丽多彩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循环往复的。”[②]虽然我们难以完全赞同这种历史循环论,虽然我们承认人都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生物体,但我们必须接受某些人性的永恒存在,接受某些人性的典范性稳固性,包括在喧嚣时世中的怀古情结。因此,这种由历史存在积淀而成的无尽情怀,沟通了现在和未来。反过来,我之所以不用“永恒的情怀”这个更为直接的字眼而采用“古典主义情怀”的表述字眼,是因为它能产生类似于萨克斯管音乐所给人的温馨感受和悠长的回忆。
其次,古典主义情怀更多地诉诸于人的情感,它固然不乏某种理性因子,但绝非时下所称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的倡导,目的在于“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针对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的普遍现象。[③]这个口号的目的和出发点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其具体的意义指向却不适合于文学艺术。不错,过度的对非理性的追求确会导致意义和价值的解构颠覆,但是,归根到底,“艺术活动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作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别人所表达的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④]这无疑暗示了文学的基本指向:感性、情绪、本能、直觉、冲动、潜意识,而这些是与理性精神原则相反的基本指向,充满感性的文学话语将使个体生命在理性的窒压下恢复其应有的柔软和弹性,也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在这前提下,作家从另一种意义上承担起社会责任,他“更多地作用于分散的个体,并且在心理学的范畴内起作用”,他“为社会保存了另一种声音,另一种精神向度,另一种尺码”。[⑤]倡导“新理性精神”者,有必要回想一下欧洲中世纪理性时代文学的黑暗命运。在公元四世纪到十三世纪约一千年里,理性哲学变成了蒙昧神学,这种神学体系排斥和仇视世俗的文学艺术。我们现在的文学艺术,刚刚从文革时代的政治一元化阴影下摆脱过来不久,才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虚幻走向实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虽然步姿趔趄,不如人意,但是与那种无我无欲,扼杀基本人性而秩序井然的蒙昧时代相比,总是进步了。故而,为了让文学在感性的天空里更加自由地翱翔,为了使文学承担起部分价值责任,有必要提倡文学的古典主义情怀。
二
勿庸讳言,古典主义情怀属于文化意义上的范畴,而文化则是民族精神和人类生存方式的体现,它“怀抱每一代刚出生的人成长并将他们塑造成人,提供他们信仰、行为模式、情感与态度”。[⑥]对于全体人类而言,文化的具体内容指向和价值形态是纷纭繁杂、千差万别的,但就某一具体民族和某一特定时代而言,这些内容和价值就显得相对清晰可辨,尤其是当我们把研究的视线投注于它们在后新时期小说里的体现之时,就愈发显得清楚了。综合从80年代末发展而来的小说,无论是“先锋派”后期、“新写实”还是“新体验”、“新状态”、“新市民”、“文化关怀”等转型期的小说景观,它们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表现了新的人的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内容,其精神立足点时而向前,时而朝后,确实显得游移不定,招来一些并不一致的看法。然而,就其总的发展态势而言,后新时期小说还是力图超越物欲和感官的压抑,追寻着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尽管这努力的行进轨迹显得并不那么清晰,有时也并不按直线方向伸延。一般来说,只要做些艰苦细致的辨析工作,提炼出以下方面的特征,还是足以描述这一时期小说的人文精神倾向的,那就是本篇所界定的古典主义情怀。
首先是人间温情。
以关心人、描写人、作用于人为本位的文学,较之政治、哲学、法律和科学等领域,表现出更多的人间温情,即便是在苦难世界里它也充盈着对人的理解和宽容,它同情弱者,抚慰不幸者,体恤孤苦无告的受难者灵魂,面对政治的逻辑铁律,面对历史的客观化推移,面对技术化时代的意志蜕变,这种文学自觉地立足于非中心的边缘化位置,在人的心灵世界这一能够起到最大作用的领域里洒下生命的阳光。它正视“恶”,但更保护“善”,它的情绪化碎片是以“善”为中心尺度的,在这方面余华的《活着》是个值得重视的创作现象。
在这部不长的长篇小说里,首先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一连串的死亡现象。福贵的女人、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都死于种种特殊的意外事件,这些事件在作家的心目中是些政治化和历史化的“恶”的遭遇。而死去的这些人,用小说里不断出现的一个定位调整,就是“实心人”,即在传统的和民间化的伦理观念混合之下的一些大好人,而恰恰就是这些大好人,接连不断地死于残酷的非命,这体现了余华对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一部分重要看法,那就是“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⑦]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位从80年代中期的先锋派骁将发展而来的青年作家沿袭了他在《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等重要小说里的精神力量和叙述才华,与上述看法联袂而出的,是余华对人性世界的一个深刻追问:人类在这种残酷的非理性非常态世界里,何以获得生存和延续?何以葆有生命应有的自由和尊严?不消说,在这部主要以“饥饿和匮乏”作为生命现象之否定的小说里,对生存问题而非尊严问题追问得更为彻底,在这问题上,余华的另一重要观点是:人依靠从自身内部迸溅而出的灵魂力量以求存活,依靠对生命执念的拥守而得以延续。这种执念,古朴、原始,最简单又最复杂,无法说清,无以界定,只能简单地说就是“活着”。作者在小说末尾写道:世界召唤“活着”的人,“就象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通过这种双重观念之下的审视和追问,作者对大地子民表现了深沉的温情。这种温情,并不廉价,因为它以艰苦的哲思作为后盾;亦不甜蜜,因为它正视星月景野下真实的苦难,它只是沉重而有力,裹挟着受苦受难者去顾盼生命的洪流。在余华十几年的创作生涯里,很少为自己单独某篇作品写创作谈,而对《活着》,是个例外,可见作家对自己这篇小说的重视程度。我特别注意这样几句:“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⑧]是的,《活着》确实高尚,它是余华在苦寒世界里的温情之作。
其实,这种情绪的流露,在余华先锋期的长期小说《呼喊和细雨》里就已见端倪。那部小说主要写了在“丧父”的荒谬世界里一个顽童拒绝成长的不妥协过程,但它也同样写了一些人性的碎片,书中王立强夫妇对“我”所体现出来的感情,与《活着》中的人间情绪是气息相通的。他的最新力作《许三观卖血记》,也有这种精神特质,同样赋苦寒以灵魂的温情。
这一时期的重要小说,有很多都具备了这方面的特征,包括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张欣的《亲情六处》、叶兆言的《去影》等。即便是毁誉不一的《废都》,透过庄之蝶表面的生活现象,也透示着在绝望的生活里人间温情尤其是来自异性的温情对疲乏心灵的镇抚和慰恤。对于文学作品表现人间温情的艺术化作用,李泽厚先生有过这样的阐释:这种感情“如果保存下来,对于后现代也好,对于现代化过程也好,都能够起一种制衡作用”。[⑨]这种制衡作用,我的理解是:增强人类情感的柔和度。
三
其次是世俗关怀。
这个特点和上面一点有所联系,但有差别,主要之处即在于:“人间温情”是被得到的,而且着眼面较广,所注意的问题呈普泛化;而“世俗关怀”则是要施及于人的,而且着眼面较为具体,有时甚至近乎琐碎,所寓目的问题较有针对性,如果说表现人间温情之作有时带有某些象征意味,那么,叙写世俗关怀之作则多有现实生活中的实在气息。因此,由此角度而言,在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的后新时期里,以广义的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手法的“新写实”和“新市民”等小说类型中,最为丰富地表现出这方面的命题意向。但是,给这一时期的整体小说招来非议的,也正是这一类。
表现这方面命题的,在我看来,以关注小人物在冲突激烈的时世下的生活遭遇和命运走向为出发点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艳歌》、《单位》、《一地鸡毛》、《风景》、《虚证》、《白涡》和《女人之约》等一些小说,都可在未来的文学史上拥有哪怕是只被三言两语作点评述的一席之地。我们清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也是人的喜怒哀乐,小人物的卑微的向往追求也是人的向往追求,这方面的作家与生活的哀乐相通,将无数的眼泪、叹息和欢笑转化为转型期粗旷而稍显毛糙的固态雕塑品,他们无意将生活里的油烟和人心里的欲望提炼为生活的“诗”和人心的“思”,也无意将人生的具体难题抽象为形而上的追寻。这些固然是它们的缺陷,但也正是这些群体作品的力量所在。
我在这里更想给予具体阐释的是被有些人目为“痞子文学”的王朔小说。这是些在我们以往的文学史上很难找到“挂靠单位”的怪异之作,它们的都市平民化体验,入骨的玩世不恭,没心没肺的调笑,政治话语的“下流”化;它们的锋利和妥协,激进和中庸,机智和傻态,油滑和严肃,都使得《橡皮人》、《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和《许爷》等世俗化畅销小说打上了“王氏制造”的印记。王朔有他自己的叙述策略,那就是解构的适度,按王蒙的话说,就是他“绝非一概不管不顾”,有些话语“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剌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⑩]这其实是从技术角度剖析了王朔小说受人欢迎的第一个原因,这原因,从内在层次来说,就是撕开社会生活中伪学家的面具;更进一步讲,就是他让老百姓放下不必要的精神包袱,返朴归真,过一种本真状态的生活,正是在这意义上,王朔的那群“痞子”顽主的神貌,多少带有点庄子放浪形骸的遗风,在这些精神意义上的流浪者身上,同样体现了未来人生的某些新鲜的价值观。这就是王朔的直面世俗之处和对人生的关爱之处,他的小说人物,鲜有“崇高”之念,不当救世主,也不去充殉道品。他们不偏执,与大众同乐,活得轻松、痛快、平庸和俗气,在嘲笑和调侃中,逐走异己的世界,破坏人所共憎的神象。他的小说,是一部分人生活态度的希望图牒,满足了他们的“犯规”冲动。故此,这些人物,在平民世界里并不招人反感,反倒被同情、赞赏,甚至于认同。可见王朔触的一极是适度的解构,另一极却指向古朴无伪的生活态度,这正是他在平民世界里的第一个立足点。
第二个立足点是对情感的挚念。王朔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男女之间的欢爱和纠葛?在言情的策略下他到底掩藏了些什么?当解构了一切之后,他心中的退守之地在哪里?这些问题,可以一路问下去。但是,一旦直问到底,裸露出来的海滩上存而又存的,就是些晶莹的情感贝壳。在茫茫无际的海天一色之下,这些贝壳闪烁出“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古典成色。对情感世界的执著追求,越来越成了疲滞的现代人仓惶退守的最后一块神圣之地,言情不单是王朔的商业策略,更多地是他寄托灵魂的温柔乡邦,是他对这个现实社会的仅存的温馨瞥视,是他生活意义的寄寓。正是通过言情,王朔与大多数人发生了心灵的共鸣,拥有了无数的崇拜者。
人间有许多情,王朔也并不单单写男女之情,在男女之情以外,《我是你爸爸》写了使人流泪使人思索的父子之情;以“好人一路平安”为主题歌基调的电视剧《渴望》和同名小说表达了更为广泛的人间感情,特别是对弱者、善良者和受损害者的无上祷福。但是,相对而言,在男女世界里,更容易做感情文章,更容易寄托最纯粹、最圆满、最复杂、最微妙、也是最容易得而复失和失而复得的旷古之情。但王朔的言情不同于琼瑶的言情,他特别清醒地写出了爱情的残酷性一面,抛与被抛、伤与被伤,始终伴随着顽主们的爱情征程。所谓“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就是残酷的爱情与温馨的爱情的双面象征。王朔既执恋爱情古老的初始意蕴,又写出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异态和畸势;既参透世俗,又隐藏着他非常个人化的人生体验,这就使他成了一个视点格外向下的平民化作家,比起转型期的有些作家,他频频关注世俗社会里的芸芸众生,搔一搔他们神经和精神上的“痒筋”,在发笑之余和流泪之际,有他小说里沉重的一面。王朔的创作,是能够让人思索和玩味的,其世俗倾向性,也是同样明显的,后一点,当然是他受到世俗男女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
四
再次是价值追问。
文学乃至文化的价值问题,是这几年“人文精神讨论”的争议点,争议的症结在于文学到底是否陷入了价值危机?价值如何定位?价值的可能性意义与终极关怀之间的关系?在激进论者的眼里,现在的文学和人文精神已陷入了危机,是一片“旷野上的废墟”;在这个“价值崩溃的时代”,只有“二张”的文学(即张承志和张炜);精神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就是终极关怀。
然而,只要承认生活的丰富性,承认历史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更主要的是,把文人地位的失落与文化精神的失落区别开来,就容易对人文精神达成某种“普通主义”的认识,从而放宽精神价值的限阈,承认精神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意义。在这基础上,“二张”之外的文学也就容易进入研究领域。
从大处而言,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其价值所在。但价值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有大与小之别,我们这里所谓的价值追问,自然是就价值的严肃性和深广性而言的。史铁生的以《我与地坛》和《务虚笔记》等作品为代表的注重个人性存在焦虑、韩少功的以《昨天再会》和《火宅》等作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理想、梁晓声的对现实的严峻批判、麦天枢的对民粹主义精神的弘扬、北村的宗教性精神迷津等等,都无不昭示了后新时期小说在价值追问上所做的可观努力,更不必说张承志的《心灵史》对于千万现代人的深刻的精神震撼。无如如何,张承志始终是个在信仰上站得住脚跟的值得尊崇的作家,《心灵史》的出现也应被推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有数几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之一,他信守“哲合忍耶”的教义走在“荒芜”了的英雄路上,以人心、人道、理想、真诚和正义为出发点,触及了一个十分深刻的生存命题:“关于生命存在的处境问题,特别是关于生命、处境与美的问题”。[(11)]对这个命题的答案的寻找,是他继《大坂》、《黑骏马》、《北方的河》、《九座宫殿》、《金牧场》、《残月》和《黄泥小层》等一系列价值追问之作的进一步延续。然而,对于张承志,所要正视的问题乃在于:对一己信仰的执守容易转变成信仰和理念上的专制;“神示的诗篇”稍一过火,就会失控成为神示的“檄”篇。这个时代,哪怕是在十分严肃而崇高的精神领域里,也并不需要和欢迎讨檄之作。
其实,相对而言,我对骨子里是个十分古典的浪漫的忧伤的诗人化小说家张炜更为欣赏。他的“融入野地”的《九月寓言》使我留连忘返,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诗性力量对技术化无价值无意义生存之境的摧毁,领略到清冷而浪漫的月辉照纳“小村”万物(哪怕是仅存一丝亮色的污垢)所蕴蓄着的文化包容性的积极意义。后出的《柏慧》,火气确实足了点,把他最为可贵的诗性逐出了小说。对价值的一路追问,痛快固然痛快,但当涤除了一切之后,这份价值也就成了一个荡荡的可疑空物,在这种创作背景下,张炜的最新之作《家族——你在高原》就显得十分可喜了。它的主体故事的构架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有某种可通之处,但精神氛围却迥然有别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胶东半岛上显赫的曲府和宁府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个名叫“○三所”的科研机构里,涌现出那么多生存反抗和精神背叛的故事,故事中又充斥了那么多诗意朦胧的关于美和真理的爱的意象,让我从残酷和失败中读出了精神的昂扬和激情的飞翔。“人的视界里有一只飞翔的鸥鸟,一只永远的鸥鸟……!”鸥鸟的飞经之处,给人的是一连串的思索和沉重的追问,就其本质而言,《家族》是一部含义丰富的深刻寓言,但是,它又和盘托出了二十世纪我们这个国土上所滋长起来的种种争端和纠葛的原始出发点,以及正义者对生命和信仰所做的种种不屈不挠追求的最初动力源。从这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是对当下这个世界的一种纠偏和纯化。
上述任何一种创作特征,一旦越过某条临界线,就很容易走到自身的末路。比如,人的温情就容易转变为人间滥情,失却其原有的深广的历史内容;对世俗的关怀则容易转变到无关痛痒的唠叨和丑恶之态的展览,而丧失其应有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力度,更容易招来美学意义上的硬伤;追问理想就容易蜕化为狭隘自恃的专制化情绪,而遗失其应持的广阔性和人间性。正是在这些朝着反向延伸的创作特征上,才能察觉到被一些严肃的批评家所苛责的“颓败”景象和反击者所嘲讥的“红卫兵情结”。故此,小说家们在具体创作时,是有必要慎防那一条无形之界的。
当然,这已经是古典主义情怀的某种变异了,对膨胀了的物欲的抑制和对精神价值的崇尚,不特仅存于今。翻翻文学史,几乎每一代的作家群,都差不多遭遇过相类似的困惑,尤其是在那些社会价值呈分化和多元趋向的转折发展期。时下的疑虑,在某种程度上恰似久远年代的回声,难怪荣格要说:“真正的现代人往往只有在那些自称为古董者当中才能找到。”[(12)]作为相应的精神性情感体现,古典主义情怀更多地是这一特殊时代馈赠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注释:
①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载《东方》1994年第5期。
②引自[德]古茨塔夫·勒纳·豪克《绝望与信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④[俄]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载《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⑤南帆:《知识·知识分子·文学话语》,载《上海文化》1995年第2期。
⑥[英]伊·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⑦⑧余华:《〈活着〉前言》,载《余华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⑨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载《东方》1994年第5期。
⑩王蒙:《躲避崇高》,载《读书》1993年第1期。
(11)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2)[瑞士]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活着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王朔论文; 余华论文; 张承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