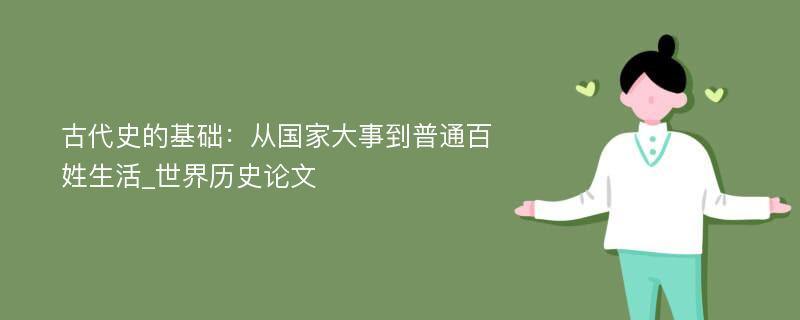
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大论文,事到论文,古典论文,百姓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31年,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发表了名作《论李维》。①在该书的“前言”中,马基雅维利如此定位古代史的功能与角色:
最杰出的史书昭示于我们的,乃是古代的王国与共和国、君王与将帅、公民和立法者以及为自己的祖国而劳作者取得的丰功伟绩,它们虽受到赞美,却未见有人效仿。其实,世人不分大事小事,对它们唯恐避之(不)及,故而古人的这种德行,在他们身上已踪迹全无……在整饬共和国、护卫国家、统治王国、举兵征伐、控制战局、审判臣民和扩张帝国时,却不见有哪个君主或共和国求助于古人的先例。②
因此,马基雅维利写作《论李维》的目的,是“根据我对古今事物的了解,记下我认为必须给予更好理解的内容,使读过这些陈述的人,更易于让他们所欲掌握的史识发挥功效。”③对古代史这样的定义,让马基雅维利更多地关注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建设和内外政策,特别是罗马统治阶级稳定国家和建立帝国的方略,即属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政策。今人相当关心的经济与文化生活,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外,基本阙如,就连对宗教的讨论,也被置于政治史的背景中。至于个人和家庭,如果出现,也主要从其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稳定,而非他们作为家庭、团体乃至自身固有的价值的角度论及。《论李维》也因此更多地被视为政治思想史名著,而非正宗的历史著作。
时隔近500年后,英国著名的布莱克维尔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了由爱丁堡大学古代史教授安德鲁·埃尔斯金主编的《古代史指南》。④该书近700页,共分8个部分49章,分别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专家执笔。由于该书预设的读者对象和作者队伍的国际特性,它的结构和体例大体上代表了西方古史学界对古代史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大众对古代史的期待。⑤埃尔斯金表示,“它意在给古代史研究中的关键主题提供一系列便利的介绍,包括证据的形态、问题和路径,以及当前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可是,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要提出确定的概论,不如说是意在反映学术前沿的活力与兴奋点。这个潜在主题是如此巨大,因此某种程度的选择乃是必需。虽然核心是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我也留意不让两者被孤立看待,而应将它们置于更宽广的背景中。”⑥值得注意的是,埃尔斯金的选择,不仅是把马基雅维利觉得最为重要的政治史变成了古代史八个主题中的一个。而且是相对次要的一个,篇幅不足全书正文的十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讨论日常生活的“生与死”占了正文近20%的篇幅。如果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地理、经济与宗教部分包括在内,则该部分篇幅占了正文的50%。⑦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史的这种变化并非始自这本指南。早在1980年由丰坦纳公司推出的古代史系列丛书中,丛书主编奥斯温·默里撰写的《早期希腊》,就已经是“一本描写希腊人的饮酒习惯、性风俗与描写他们的政治史篇幅一样多的书”。⑧那么,西方的古代史研究从15—19世纪国之大事一统天下,何以在近百年来的时间里,演变成为今日之局面?难道说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冲击下,政治史真的就不如面包价格的变化重要?⑨它的演变,又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哪些启示?
一、近代早期的古代史:政治和军事活动的舞台
大体说来,从马基雅维利时代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所谓的古代史,主要是以政治和军事为主线、以伟大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这一点与古代中国政治史的主题有所类同,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希腊罗马史尤其如此。首先,古代的历史写作,用约翰·马林科拉的话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精英为精英写作的产物,它所导致的是如下几个典型的特征:个人的突出地位,无论他们是雅典的将军,希腊化世界的国王,还是罗马的高级官员和皇帝;关注统治阶级的活动,或者是发动战争,或者是在国内掌管国家;持续关心荣誉和责任的分配,并据此对历史上活跃的个人进行考察和评价;以及用讨厌或鄙薄的口吻描述下层阶级的倾向(如果说对他们有描述的话)”。⑩古代史学的这个基本取向,决定了政治和军事活动在古代历史中的核心地位。第一个撰写历史的希罗多德固然兴趣广泛,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风土人情无所不记,然其写作历史的目的,如其在《历史》的开头所说,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11)全书的主体,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在他之后的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强化了希罗多德以政治和军事为历史主线的传统。及至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希腊人开创的政治和军事史传统,在波里比阿、费边、撒鲁斯特和李维等人的著作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实际上,对古代城邦的普通公民而言,他们关注的中心也是政治和军事。作为古代城邦的主人,战争乃公民生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国家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扩张是否成功,公民的生活相当程度上也为城邦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左右。(12)也就是说,与近代世界相当不同的是,在古代世界,政治和军事活动,是相当一部分公民的“职业”。公民的所谓美德,不是积极履行军事义务,就是积极参与政治。在如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古代史学家,如果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为社会接受,大多只能把自己的眼光盯在政治和军事上。影响所及,以至于帝国时代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塔西陀在其《编年史》中需要为自己的写作辩护,原因是在他之前的史学家所提供的,是“国土的描述、战事的起伏、在战场上光荣战死的统帅”,而他所提供的,不过是“一连串残酷的命令、接连不断的控告、被出卖的友谊、被残害的无辜者、导致同样后果的各种不同的案件”,因此不大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13)但是塔西陀给我们描绘的,仍然是帝国时代罗马皇帝与元老们的活动;行省事务,如果不是与罗马或者军事征服有关,一般不会进入他的视野。普通的大众,除了偶尔因普遍不满以骚动者的集体身份进入历史外,一般来说是沉默的一群。
古代确立的史学传统,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尽管可供历史学家研究的资料在增加,学者们的世界观在改变,观察历史的视角也有所变化,但政治和军事在历史著作中的主角地位,特别是大人物的活动和攻城略地的事件,像在古代著作中一样牢不可破。拉雷爵士的《世界史》叙述了从创世到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历史,其基本框架根据圣经的时间设定,基本内容则是基督教的传说、希伯莱人的活动和大国之间的征伐,以及大帝国的兴衰。(14)18世纪英国出版的大量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无论是最早的劳伦斯·埃查德的《罗马史》和托马斯·亨德的《希腊史》,抑或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出版的米特福德的《希腊史》和亚当·弗格逊的《罗马共和国的发展与衰亡》,(15)无不以政治史、实则是政治事件的历史作为核心。法国学者中,巴黎大学教授查理·罗林(Charles Rollin)的《古代史》和《罗马史》篇幅都奇大无比,动辄数千页,然基本是对古代文献的转述。最能体现近代早期古代史写作特征的,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罗马史》,他千余页的著作涵盖了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代,然而其共和国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罗马的扩张史,罗马人似乎马不停蹄地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帝国时代则更像皇帝的家谱,从第一个皇帝恺撒逐个写到第41任皇帝君士坦丁。
历史写作为精英阶级垄断、而且为精英阶级服务的基本状况并无根本改观,是近代早期的古代史写作仍为政治事件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时的史学家中,虽然不乏温克尔曼(J.Winckelmann)那样出身相对贫穷的子弟,但他们中的多数,非富即贵。18世纪英国的上层阶级形成了独特的精英文化。对他们来说,接受古典教育,游学欧洲,参与政治,是他们的主要活动。(16)“吉本是个富家子弟。他祖父善于经商,积产达十万英镑以上,购买了许多田地,在伦敦和乡下都有房屋。”(17)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吉本一生除了游历、学习和写作,就是担任英国国会议员,不曾为生计犯愁。与他大体同时的米特福德,同样家资丰厚,除与吉本一起服役于英国民兵外,一辈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了8卷本的《希腊史》。(18)这样的状况,甚至到19世纪也无根本改观。众所周知,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希腊史专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就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本人也是银行家兼国会议员。其他古史学家如康沃尔·刘易斯(Cornwall Lewis)、康诺普·提尔华尔(Connop Thirwall)等,也都出身豪富之家,在政界或教会任职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历史写作乃业余爱好。即使在专业史学相对发达的德国,由于但凡研究古代历史者必须接受严格的古典学训练,需耗费大量时间学习古典语言,因此德国古史学家中相当多的人自必出身于上层阶级家庭。(19)在这些以政治为业的绅士、议员或教授的笔下,政治和军事以及精英阶级的活动,当然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
同时,古代史的写作意图,也让近代早期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政治事件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欧洲学人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与强大,自由通常被视为稳定和强大的源泉。民主政治则普遍被认为不具有稳定性,是暴民的统治,而且会侵犯自由与财产这两项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目为神圣的权利。(20)相应地,古代世界是近代世界的主要参照系统,其民主与共和政治,因为主要文献来自上层阶级,被描写为混乱、帮派和无法无天的暴政,成为上层阶级汲取历史教训的主要来源。18世纪英国出版的大量希腊史与罗马史中,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作者大多宣称,他们的目的是鉴古知今。最为典型的是苏格兰皇家御用史学家格利斯所写的《希腊史》。在该书给国王的献词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希腊史暴露了民主政治那危险的骚乱,谴责了暴君的专制;通过描绘各类共和政府政策中无可救药的恶行,它将彰显因世袭国王的合法统治和制度良好的君主政治的稳定运作无尽的益处。因此,本书献给尊敬的陛下—世界上最自由国度的主权者,是再合适不过了。”随后是对国王统治下英国各类学问大发展的颂词。(21)就希腊而言,他公开批评雅典,将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与雅典进行比较,比较稳定的斯巴达受到他的推崇,“这种社会的政体达到了人性可以期望的最高境界和辉煌。”(22)其他作者如亚当·弗格逊,威廉·米特福德等,也无不把借古讽今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并借此肯定当时的英国政体。(23)
二、21世纪的古代史:经济与社会
21世纪古代史研究的基本取向,也许用布莱克维尔出版的各种指南作为代表比较合适。这套丛书从2003年开始出版,列入古代史部分的指南包括《古风时代的希腊》、《古典希腊世界》、《希腊化世界》、《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晚期古典世界》、《古代近东》、《古代埃及》、《罗马军队》、《恺撒》等(均省略“指南”一词)。该丛书的目的,是提供有关古代史不同时期深入且权威的概论,每卷一般由25—40位学者执笔。丛书自称其读者对象包括学者、学生和一般公众。因此,它既足以表现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又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因为读者面比较宽,所以多少也代表了出版商和读者对古代史的总体期待。
新世纪古代史研究的特征,首先体现在这些指南的总体框架上。只要将这些著述的目录与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同类著作加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就一目了然。所有指南几乎都以对资料和方法的讨论开篇,详尽介绍有关文献及研究路径,尤其重视资料本身的特点与不足,反映了19世纪史学研究专业化以来,历史研究逐步科学化的基本趋势。资料之后,是对地理和人民的讨论。在这里,地理条件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地理,而是与古代的历史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当说,它体现了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的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所确立的传统,无论是有关希腊还是罗马的各卷,地中海及其周边的人文与地理环境,都占据了每部指南的显著位置。希腊与罗马的独特性,大多为地中海的独特性所取代。在历史内容的取舍上,广义的社会经济史成为主体;叙事性的政治史,主要是精英阶级的活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由拉夫劳勃(Kurt A.Raaflaub)主编的《古风时代的希腊指南》(24)中,叙事性的政治史不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内容被宗教、地理、城市、经济、圣地、节日、性别、阶级、文化水平等占据。由金泽(Konrad H.Kinzl)主编的《古典希腊世界指南》(25)虽然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政治叙事,但主要内容仍是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经济、种族认同、宗教与崇拜、知识的组织、艺术等。《罗马共和国指南》的两位主编虽然都是研究政治史出身,但该书有关罗马政治史的叙述,仍不足全书正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对罗马人的政治结构、社会、政治文化、罗马认同等主题的分析。同一系列中的其他著作,大体体现了类似的取向。(26)即使是有关罗马军队和恺撒的指南,有关内容也都力图贴近社会史。《恺撒指南》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传记:叙事”,“传记:主题”,“恺撒的现存作品”,“恺撒在罗马的名望”和“恺撒在历史上的地位”,只有第一部分可以划入传统的政治史叙事,其他部分,尤其是有关恺撒的名望和恺撒在历史上的地位两个部分,近乎恺撒形象的接受史。《罗马军队指南》虽然遵循了传统的历史分期,但每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大多是军队的社会史,涉及军队与宗教、后勤、宣传、城市精英、婚姻、家庭和生存等貌似与军人活动无关、实际却与普通士兵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指南的取向,特别是把婚姻、家庭、性别、形象的传播与接受、宗教及其社会功能、社会秩序、政治控制等变成古代史有机组成部分的努力,把古代史变成了多学科、多层面、生动而具体的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在传统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和主题,借助于社会科学方法,逐渐占据了古代史舞台的中心。为方便说明,这里仅以《古代史指南》为例,略加分析。
《古代史指南》需要覆盖的对象,是西方学者心目中传统的古代世界,即使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标准,它也涉及上下1500年(从荷马时代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从苏格兰高地到美索不达米亚、从北极圈到尼罗河中上游和撒哈拉沙漠的广大地区,可谓是希腊、罗马世界的综合。由于范围广阔且课题众多,如何取舍和设计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这类通论性著作的成败。该书正文由八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证据、问题与路径、人民与地区、遭遇神灵、生与死、经济、政治与权力,以反响终篇。
证据部分放在第一位,对于历史著作来说是惯例,布莱克维尔的其他指南也都是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在该书出版之前,有关古代近东、古典希腊、希腊化世界、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古典晚期的各卷都已出版,而且每卷都已讨论过与之有关的史料。《古代史指南》如何既能概括地介绍古代历史的各种资料,又能避免重复已有指南的内容并有所创新,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从各章的标题看,它似乎相当传统,分别讨论了史学、碑铭学、纸草学、钱币学、考古学、演说、文学文献等七个方面。但在具体内容上,则体现了主编的匠心独运。各章作者在概要介绍该学科历史发展的同时,尤其着重指出在运用和解释各类资料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即资料本身的缺陷和研究方法的不足。关于史学乃古代的精英阶级为了精英阶级的兴趣写作的评论,提醒我们在分析和使用古代文献时,绝不能忘记了古代史主要资料的缺陷。即使是对于我们一般认为比较可靠的考古、钱币、铭文等相对客观的史料,也需要适当的警醒。就铭文资料而言,“公元前800年到公元300年标志着碑铭学历史上一个不同的时代。其间希腊人发明了字母,制造了公共碑铭,罗马人传播了拉丁碑铭,其他人接受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字与碑铭习惯,创造了地中海地区独特的碑铭文化。由于它们的相互影响,最好是说古典时代存在一个独特且多面的碑铭文化,一个为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统治、但原住民的语言如卡瑞亚语仍能为人们阅读的文化。”(第52—54页)因此,碑铭史料也存在语言上的偏见。碑铭如此,纸草文献、钱币和考古等,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
第二部分可以视为对第一部分的深化和具体运用,分别讨论了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族群与文化、人口与历史人口学、妇女史、环境史以及对神话的解释等,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古代史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理论和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解读、使用资料的问题,提醒我们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有关各章大体反映了当今西方学者的兴趣、态度和方法,可以视为对古代史研究现状的述评。第三部分为叙事,大体按照地区和族群分类,分别叙述了从古代埃及到北欧各地区的古代史。这个部分本来比较难于处理,因为既不能将之写成各个地区的简史,又不宜写成民族志之类的介绍。但有关作者根据古代史的特点,尽可能在揭示各地区和族群古代历史发展一般趋势的同时,重视它们各自的命运和不同特性。北非一章通过分析北非与撒哈拉沙漠以及地中海的关系,指出该地区的历史发展实际深受周边文明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也绝非人们想象的不可逾越,从而对北非孤立发展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关于小亚细亚和西班牙的两章,则重点揭示了它们对罗马化的反应以及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该部分的有关叙述,仍然可以视为如何解读史料和理论的延伸及具体运用。
第五、六、七部分可以视为对古代文明社会生活的展示,也是该书最具创见的部分,分别讨论古代世界的生与死、经济、政治与权力。与过去不同的是,政治被“排挤”到了比较边缘的地位,在三部分共18章中,政治只占了4章。即使在仅有的4章中,所讨论的也都并非传统的政治史,而是影响政治生活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家结构、法律体系、公民权和战争,突出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公民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框架以及影响古代公民的诸种最重要因素。经济部分既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兴趣,涉及劳动、财政、资源和技术,但更体现了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地中海成为古代经济的基本背景,地区间的差异在“诸种经济”(economies)这个术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乡村的作用得到强调,尽管作者认为,片面强调乡村或城市的作用,不免是站在今人的立场论古人。也许对古人而言,除特殊情况外,城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重要。非自由劳动包括奴隶劳动的作用得到重视。经过战后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冲击,众多学者如今都承认,奴隶制是古代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者的讨论并不打算涉及奴隶的具体数量等老问题,而倾向于从芬利的路径出发,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体背景中的奴隶以及其他形式非自由劳动的功能进行讨论。
如果说古代政治和经济提供了希腊人和罗马人活动于其中的基本框架,古代人的一般生活状况,则体现在该书第五部分的“生与死”,即关于个人生活的部分。它从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开始,依次讨论了古代的食物、爱与性、居住、娱乐、教育、医药和死亡。编者的规划,显然希望以此揭示古代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让今人对古人有更加具象的认识。有些问题,例如教育和家庭,虽然曾经得到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并非从个人生活着眼,而是更多地关注诸如妇女、儿童之类的群体。另外一些领域,例如居住、爱与性、医药、死亡等,则是20世纪末以来的新兴研究领域。不过,如果作者仅仅限于对古代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则不免把历史变成了个人生活琐事的介绍,哪怕这个介绍的着眼点是古代的所有人,意义仍然有限。该部分最为可取之处,在于相关作者一方面概要介绍有关研究的起源和进展,另一方面则试图借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手段,写出各个专题的社会史,进而描述古代人比较真实的生活场景,努力让现代人理解古代个人的经历。以家庭一章为例,众所周知,家庭史研究对古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已经把历史学家们从直到20世纪最后数十年仍倾向于占支配地位的、单纯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引开。它已经让大多数历史分析包括了私人和家庭领域,从一个可以说是孤立的男性世界领域,转向一个也有妇女和儿童居住的世界。焦点的变化,也造成了方法论的明晰以及对资料——文字的、视觉的和物质的——更加精细的解释和分析。为了发现不同于政治家和将军(他们常常是古代世界历史的主要作者)的‘个体’(或者说,至少是‘类型’),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用新的方式处理证据;观察那些群体(妇女、儿童、奴隶、非公民、被视为外人的团体),他们不曾写作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在精英阶层男性的作品中,他们并非不经常地作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出现。”(第330页)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解读,两位作者发现,借助于人类学的方法,古代史料描绘的家庭,往往是非常态时期的非常态家庭,“家庭的实际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异。”罗马共和国后期,家庭关系就发生了缓慢却重要的变化。妇女的地位尤其与我们印象中的男权统治不同,“在雅典和罗马社会,人们接受和期待的是,妻子和母亲事实上掌管着家庭。”(第338页)至少在婚姻问题上,男性家长并不能包打天下。因此作者提醒我们,“社会理想(文学的、男性的和精英的)与社会现实,尤其是对那些不曾自己发出声音的群体,需要小心解释。”(第330页)对食品、死亡、居住、性等方面的研究,一方面让我们注意到此前鲜为人知、但却是古代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揭示出古代社会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历史学中适当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无论是在资料的发掘和解释,还是在丰富历史的内容更全面反映历史面貌上,都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三、古代史的功用:个人经历与集体意识之视角
古代史有什么用?如前所述,对近代早期的历史写作者来说,作为近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参照体,古代史的功能根本不是问题。可是20世纪以来史学的专业化,让社会公众与专业学者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其他知识门类,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应用性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法学等的发展,让历史学的空间日益逼仄,以至于到20世纪前期,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已经在讨论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他最后的结论虽然积极: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美感,有娱乐的价值,史学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前景。(27)不过他的辩护是就历史学整体而言,而且在那之后,史学无用,史学危机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就古代史,特别是古代希腊罗马史来说,它的价值何在,也曾有学者论及。莫尔利(Neville Morley)承认,历史确实有用,它虽然不可能让人们根据对过去的认识预见将来,也不大可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不是法律或者医学那样的职业学科,但从实用的意图来说,它培养了人们“处理和分析大量资料;构建合理的论证,创造新的思想;清晰而且有说服力地提出论证;参与讨论等方面的能力”。(28)但他也认识到,其他学科同样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训练,因此这些实际用途不足以解释历史学科存在的理由,尤其是不断建构和解构过去的理由。但他随后提出论证:过去需要研究,因为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会影响人们现在的行动;现在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历史学在不断解构过去的过程中,也不断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认同,并且通过塑造过去来改造现在。(29)但他的论证仍很难把古代史从质疑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仍然是就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而非古代史的特点立论,而且拘泥于个人直接应用层面。
李剑鸣将历史学的功能分离成个人和群体两个层次:
历史的“用”带有某种群体性质。对个人而言,历史或许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人丝毫不懂历史,照样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但对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群体认同和文化赓续的起点……历史不是可以带来直接效益的实用性知识,它的功用具有长期性和价值性。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研究历史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解决一种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社会如果不重视这个道理,贬低甚至排斥史学,最终只能导致文化的堕落。(30)
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历史研究确实“可以解决一种实际问题”,但这样的解读,显然能够把历史学从斤斤于实际应用的泥潭中解救出来。古代史研究既然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了价值。但正如李剑鸣也意识到的,许多人仍会从个人角度看问题。对于那些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那些普通读者和公众来说,希腊罗马的古代史到底有什么用,仍然需要更具体的讨论。《古代史指南》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全书开头的“个人视角”,由五位来自不同国家、研究古代史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个人经历思考古代史的功能,然后是书末的侧重于集体意识的“反响”,借用莫尔利的话来说,是“神话”。(31)个人视角中,五位作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其中麦克林(Neil McLynn)曾任教于日本,可以视为亚洲的代表。主编的意图,显然是希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现身说法”,以彰显古代史与其研究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五位作者中,奥伯(Josiah Ober)为美国学者,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知名,并由此涉入政治学,讨论过当代民主以及雅典遗产的价值问题。他比较重视古代史综合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叉对其研究和认识政治,包括古代和现代政治的作用。他批评当今的政治学过于狭隘,“将权力与合法性、合法性与正义割裂开来;忽视了阶级差别,将政治想象为超级精英的游戏;有些专注于论辩、批评或信仰,有些专注于制度、决策过程与人格;有些专注于偶然性、环境因素或技术变迁;有些专注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还有些专注于变化与稳定问题。古代史则给那些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特殊的好处,可以避免因狭隘和非历史主义造成的错误,因为它既广泛,又有限,就时空范围论,它是巨大的;但就可以牢固确立的相关事实来说,与现代比较,又是狭小的……古代史让我可以梦想一种‘统一的政治场域理论’,在那里,可以对权力、合法性和正义做总体的考察。”(第3页)彼得·德鲁(Peter Derow)生前供职于牛津大学,以研究希腊化时代历史见长,他引用波里比阿《通史》开头关于罗马征服世界的话来论证研究古代史对于当今的意义,指出“古代史研究能够(而且应当)对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提升我们对身居其中的事件的认识,做出贡献”(第3—4页),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人终归是人,对古代史的研究,涉及一个微观的年代框架中的人对政治和其他环境(在地方和全球的层次上)的反应。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文研究,考虑到它使用的资料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它需要的智力投入和活动,那也是乐趣”。(第5页)其他三位学者对古代史的功能,也都有程度不同的阐述。澳大利亚的古代史似乎颇受学生欢迎。据新南威尔士州统计,中学的最后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历史,多数又选择古代史。在大学历史系中,选择古代史的学生似乎也超过近现代史。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澳大利亚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是因为“古代史让我们接触与过去的严肃争论,以及后代不断重新阐释古代(不仅仅是古典古代)的不同方式。在我们研究古代史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许多不同的历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的、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拿破仑以及他对埃及和罗马帝国主义模式的运用,还有费边社和斯巴达克派的制度,以及西方(与某些非西方)的民主发展”。(第9页)正是这种与过去之间不断的对话,激发了人们对古代史的兴趣。莫尔利的论断,在澳大利亚似乎得到了回应。日本的古代史似乎不那么乐观,毕竟日本的文化不同于欧洲和英语世界,学生大多选择历史作为跳板,而非将其作为专业。但根据麦克林在日本16年的任教经历,他能明显感受到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古代史迥然不同的态度。(第8页)
如果说开篇为古史学家个人就古代史研究的影响所做的证词,那么末尾关于古代史在近现代作用的论述,更多地涉及国家和社会层面,出场的主要是非专业学者,包括政治家、导演和普通人。麦克科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主要从文化遗产角度讨论古代的意义,勒维林-琼斯(Lloyd Llewellyn-Jones)的兴趣在于好莱坞的古代史大片。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由埃尔斯金执笔的“古代史与民族认同”一章。它表明对于近现代的欧美世界政治来说,古代不仅仅是个灵感来源问题。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自比曾消灭瓦鲁斯(Varus)的阿米尼乌斯(Aminius),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钟情于恺撒,并写出了两卷本的《恺撒传》,同时尊崇领导高卢起义的维尔琴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强调法国的高卢—凯尔特特征。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正足以揭示拿破仑三世个人的需要与法国近代民族认同间存在的冲突;1911—1912年,当意大利介入北非冲突时,西庇阿进攻迦太基的史实被搬了出来(第557—558页)。最让人感兴趣的可能是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独立后与希腊之间的一场争论。20世纪70年代在希腊境内维尔吉纳发现的、据称属于马其顿王室的黄金盒子,其盒盖上有类似太阳或星星的装饰。新生的马其顿共和国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也颇为不同。1994年的人口统计使用的马其顿、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等六种语言,足以表明该国民族和宗教的复杂。因此它亟需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其中之一是国旗采用了维尔吉纳的古代马其顿王室徽章标志。但马其顿此举遭到希腊的强烈抵制,并迫使马其顿放弃该做法。因为希腊人担心,马其顿此举有可能引起希腊境内的民族问题,剥夺希腊作为马其顿继承者的权利。为进一步显示自己作为古代马其顿继承者的地位,1992年,希腊将北希腊的卡瓦拉机场改名为亚历山大大帝机场(第561—562页)。
总体上看,《古代史指南》给我们提供的是一部注重古代普通人日常生活、全面反映古代世界社会与经济状况的著作,并对古代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古代史在当代世界的功用有所提示,基本反映了西方古代史学者当前的兴趣、理论与方法。上文对该书的简单介绍,已经表明古代史的研究固然必须从阅读古代文献开始,但学者们对古代文献的态度,观察它们的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他类型的史料,如考古的、碑铭的、纸草文献的、地理和人文的,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正在古代史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对古代人婚姻、家庭、居住、葬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让古代史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以政治和军事为核心的精英阶层活动的层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益占据舞台中心。
四、古代史研究的拓展:中国与世界
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古代史研究走到今天,实际上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邦制度让公民成为国家舞台上的主角。(32)无论是古代传下来的史料,还是近代根据古代文献撰写的以政治和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史,如梁启超早已意识到的,都是“民史”而非“君史”,即公民群体的历史。在那里,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公民大会及其选举出的官员的活动。立法、司法、内政和外交等军国大事,大多由公民大会和他们的代表决定。大人物固然受到重视,但大多被置于城邦活动的基本框架之内。从希罗多德到李维,公民群体的活动始终是主体。即使到帝国时代,古代的共和与民主政治,仍鲜活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狄奥·卡西乌斯虽然生活在帝制已经确立后近250年之时,但他对于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运作仍有生动的描绘。对构成国家群体的普通公民的关注,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传统。
古代遗留给后世的史料,大体确定了近代古史著述的主要内容。无论近代早期的古史学家是否赞成古代的政治体制,他们也都不能不把公民活动作为叙事中心,尽管政治和军事的主导让恺撒之类的伟人更为显赫。同时,对于政治和军事活动支配的古代史存在的问题,西方学者也早有认识。早在17世纪末,洛克(John Locke)就已经对当时的古代史表达了不满。他主张不要给孩子们过早教授历史,因为在那里,“所有关于历史的娱乐和谈论,除了战斗和屠杀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给予征服者的荣誉和名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人类的屠夫),会进一步误导正成长的年轻人。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会认为屠杀乃值得赞扬的人类事物,是最为英雄的行为。由于这些原因,非人的残忍就会植入我们心中。”(33)同时,古代史的其他方面,从来没有完全被忽视。即使在政治和军事史最为盛行的18世纪,也有伏尔泰的《风俗论》和休谟关于古代世界人口和道德的讨论。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也不仅仅是从政治和军事立论,还关注了罗马人的土地问题以及道德和风俗。那些认为近代远胜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会给予经济、文化和道德更多的考虑。19世纪专业历史学诞生之时,古代经济史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博克的成名作是《雅典国家经济》,米特福德等人论述过斯巴达的黑劳士问题;穆勒的《多里安人》已经涉及斯巴达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和风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古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德国学者波尔曼(R.von Poehlmann)、迈耶(Eduard Meyer)和贝洛赫(Julius Beloch)已经尝试通过经济发展解释古代历史的变迁;法国学者格罗兹(Gustav Glotz)、英国学者齐默恩(Alfred Zimmern)、爱尔兰古典学家马哈菲(J.P.Mahaffy)等,也都注意到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虽然《剑桥古代史》的第一版仍然让政治和军事史唱主角,但20世纪70年代陆续推出的新版《剑桥古代史》(1—2卷为第3版,后续各卷为第2版),已经是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层面的古代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古史研究,已经不是政治和军事史的一统天下,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34)年鉴学派的整体史之被普遍接受,如果脱离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总体基础,将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新世纪的新古代史,实为西方学人数百年来文化和学术积累的成果,绝非一日之功。
中国的历史学虽然源远流长,有雄厚的史学传统和独特的方法,但就西方古代史研究领域而言,不免过于年轻,基础太过薄弱。中国人之开始了解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始自19世纪中期,其目的非常功利,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史学的文化建设功能从属于政治功能。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也确曾翻译过一些西方的古史著述,撰写过一些介绍和研究古代历史的著作,但缺乏独立和原创性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中国大学的历史系模仿当时的苏联模式,普遍采用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并立的课程体系,世界古代史作为通史课程的一部分,一般占有一个学期的课时量。希腊罗马史作为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被比较系统地传授给学生。作为制度上的表现,是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设置。然而,模仿苏联体系建立的中国历史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需要的烙印,即历史被高度简化了。(35)具体到世界古代史,则是证明人类社会系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模式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虽然20世纪50—60年代的学者们为古代史研究在中国的奠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是编辑出版“世界史资料丛刊”、《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翻译介绍古典文献以及西方学术名著,但当时学者们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性质、历史分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奴隶制问题,而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以承认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为前提。任何敢于挑战或者否定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都被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资料的限制和理论上的独尊,让许多问题的讨论变成了语录官司,多的是火药味,少的是实证性研究。(36)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1979—1980年,实际由日知先生规划和组织的《世界上古史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日知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也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两书都对古代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产生的形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城邦到帝国的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并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为充分的论证,引起了对有关问题更深入和具体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中,虽然仍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采取了更加平和与实事求是的态度。(37)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更多古典文献和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渐展开,古典语文教育的起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与世界接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题著作和论文。这些作品或者具有独特的中国学者视角,或者借鉴和使用了不少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部分论著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似乎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38)
然而,如众多学者都承认的,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毕竟起步晚,基础薄弱。在资料积累方面,我们仍有不少缺陷。一些基本的文献和参考书,例如雅可比的《希腊历史残篇》,考古资料中的《希腊铭文集成》,仅有东北师范大学收藏,且后者刚刚购入。部头更大的《拉丁铭文集成》,似乎仍无任何大学和科研机构购入。19世纪以来西方出版的大量考古报告,其中绝大多数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可能闻所未闻。此外,中国的古史研究者中,能够熟练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者并不多见。正因如此,不少古代史研究者难以从事精深的、原创性的研究,很多时候是二传手—把西方的学术成果消化后传播到中国(必须承认,在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这样的研究仍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所写出的论文中,不少属于宏观的、一般性的介绍,少有个案和专题研究。更多的学者主要是应付日常的教学,无力从事任何研究。社会对古代希腊史的需求,也还停留在相当一般的水平,从而影响到古代史研究在整个历史学科中的地位。除资料和实证研究能力的限制外,我们还缺乏自己应当具备的系统的理论。不少论著,尤其是最近20年来出版的古代史教材,虽然力求在理论和体系上有所突破,但如何将它们落实到具体研究之中,易言之,如何把宏观理论转化为比较具体的古代史设计框架,并体现在历史进程的具体叙述中,仍不能说特别成功。在揭示古代社会的特征之时,除政治和军事史不免仍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外,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历史被简单地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板块的做法,仍统治着大多数古代史学者的心灵。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理和生态背景的具体作用,经济的一般特性和不同地区的特征,总之,古代人的生老病死及其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价值观的关系,仍缺乏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很难追踪学术前沿。相应地,古代史研究的影响相当有限,不少学者,特别是非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在说明古代史上的问题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时,仍把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当作万应灵药。
那么,中国的西方古史研究出路何在?众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相当全面。(39)笔者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欲做出第一流的成果,首要的是古史研究者苦练内功。因为无论是追踪学科前沿,还是组织大规模的、与现实有关联的课题,都必须以知识的可靠性和理论的科学性为前提。除必备的理论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对历史学者的基本要求外,具体到古代史学者而言,窃以为内功主要是研究者所须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既能较好地掌握古代语言,尤其是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相关文明的语言,又能掌握至少两种以上的现代外国语言,并熟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掌握古代语言是古代史研究的基础。虽然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大量古典文献已经被译成现代语言,尤其是英语。而且由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新的译本,需要不断的翻译,因此不少古典文献的现代译本不止一个。中国的古典世界史研究,如果缺少了翻译,无论如何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但翻译同时也是解释,体现了译者的立场和时代的取向,因此在不同的译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细微的差异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则可能影响其观点和结论。威特马什(Tim Whitmarsh)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2卷有关特尔西特斯(Thersites)的描写为例,指出三位现代译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拉提摩尔(Richmond Lattimore)完全忽视了普通士兵特尔西特斯与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地位上的差异,其他译者则明确暗示两位争论者地位上的差别。(40)两种不同的处理,当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再如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当霍布斯翻译时,他将伯里克利定义民主政治的那句译成“我们的政治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府在庶民(Multitude)手里,不是在几个人手里”。(41)但在企鹅丛书的华尔纳(Rex Warner)译本中,变成了“我们的政府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42)洛布古典丛书的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译本此处被译成“我们的政府确实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管理权不在少数人而在多数人手里”。(43)比较而言,三个译本的主要差别在于政权到底是在庶民手中,还是在全体公民手中,抑或是在多数公民手中。三者含义区别明显,第一种显然带有贬损意味,第二种当然比较肯定,第三种则介乎两者之间,可褒可贬。核查原文,则用“多数人”表达希腊语的pleionas更为准确。霍布斯是个民主政治的批判者,他对普通人殊无好感,相应地讨厌雅典人,因此把修昔底德的书名译成比较中立的“希腊人战争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把民主政治译成“庶民的统治”,华尔纳和史密斯都是在20世纪完成自己的译文,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的著作译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暗示他们接受了近代人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的立场(伯罗奔尼撒人发动的战争,犹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在有些英文译本中成为The Persian War)。不过略有不同的是,史密斯的译本为洛布古典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比较强调忠实和直译。此外,他的译本完成于1919年,当时民主政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已经逐渐变成褒义词,所以他并不介意将民主政治与多数人的统治联系起来。而华尔纳译本初版于1954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民主政治相当巩固,并且在社会文化中成为完全正面的术语,他本人可能对民主政治有更多的好感,干脆就将民主政治变成了全体公民的统治。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古典语文的基础,就只能跟着译本(而且可能只是某一个译本)走,一旦译本错误,则前功尽弃。此外,更多的文献,如考古的、碑铭的、纸草的、陶片的、甚至部分文学的,都没有现代文字译本,只能直接利用原文。由于西方古典学的历史已经有数百年,传统文献几经爬梳,除非奇迹降临,否则很难再有新的重大发现,但考古、碑铭、纸草文献学等学科,却在不断提供着新的史料。19世纪末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发现是一个显例,后来的米南德(Menander)喜剧的发现,则是另一个影响重大的例子。因此,古典语文的基础既是我们从事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也是新资料的主要来源。
不过,古典语文绝非万能。《古代史指南》已经表明,当代的古史研究,早已成为一种深厚的学术传统,社会科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让古史研究的资料和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而言,阅读古典文献固然是必需的第一步,但如果仅以阅读古典文献为满足,似乎自己的所有结论都只是从直接阅读古典文献而来,不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毕竟古代史学科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17—18世纪得到初步发展,到19世纪专业史学奠基,经过20世纪的繁荣走到今天,西方学者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继承前人已有成果,是古代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前提和基础。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尤其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我们作历史研究,本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并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到人家的成就,承认它(而不是掠其美)以作为自己的起点,又看到人家留下的真正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否定它,扬弃它来进行我们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是真的,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价值。”(44)可是,对古代史研究而言,它最初发端于意大利,后在法国、德国和英语世界成熟、发展,前苏联和东欧在古代史的某些重要领域,例如黑海地区希腊人的殖民、古典文明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等,也取得过辉煌成就。因此,古代史上众多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用多种现代文字写成。以古代经济史研究为例,从博克的《雅典国家经济》诞生以来,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学者进行过多场论战,从19世纪末的迈耶、贝洛赫和布彻尔(Karl Blaecher),经韦伯(Max Weber)、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和哈斯布鲁克(Johannes Hasebroek),再到芬利(M.I.Finley),乃至最近的戴维斯(J.K.Davies)、奥斯邦(Robin Osborne)等,历时百余年。(45)有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从18世纪法国学者罗林,英国学者弗格逊等,经19世纪的麦里瓦尔(John Merivalle)、蒙森,到20世纪的格尔泽尔(Malthias Gelzer)、莫泽尔(F.Muenzer)、塞姆(Ronald Syme)、斯卡拉德(H.H.Scullard)、尼科莱(C.Nicolet)、布隆特(P.A.Brunt)和米拉(Fergus Millar),再到新世纪的莫斯坦因-马科斯(Robert Morstein-Marx)和莫瑞特森(H.Moritsen)等,观点、模式、史料和方法都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46)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些有益的成果,又如何继承?没有继承,又从哪里寻求创新?可是,要真正有所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至少掌握两种以上的现代外语。缺少了这个前提,所谓的创新,很可能成为刘家和先生所说的“足以摧毁科学生命的”“形似而实非的‘创新’”,其结果,恰足以破坏真正的学术研究。(47)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进展的作用似乎不用多说。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确实是一门叙事的艺术,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李维和塔西陀,都以叙事见长,于叙述中寓褒贬。但现代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则是日渐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琼斯在论述雅典民主时仍采用传统的叙事,但80年代以来的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研究,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芬利对古代与近现代民主关系的讨论,奥伯有关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分析,圣克莱尔(R.K.Sinclair)关于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大众参与研究,莫斯坦因-马科斯对公共交往理论的应用,莫瑞特森对共和国后期罗马城政治地理的考察,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现代政治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百年来有关古代经济的讨论,更与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密不可分。《古代史指南》对古代普通人从生到死的论述,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恺撒指南》中有关恺撒形象的传播,显然是利用了传播学与接受学的理论和方法。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十分时髦的种族与民族认同研究,以及希腊人与蛮族人、罗马人与蛮族人的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在被引入古史研究后,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48)至于荷马研究与文学、考古、人类学的联系,在帕里(John Parry)、洛德(A.B.Lord)、芬利、纳吉(Gregory Nagy)等众多荷马研究的成果中,早已得到生动体现。(49)希腊史研究中对阿卡狄亚等地区新近的关注,固然与资料的积累有关,但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也将无从解释。(50)基于此,我们或许可认为,对资料的新解读,新课题的发现,新视角的采用。新领域的开拓,总之,当代古史学中的任何创新,或多或少都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采用有联系。社会科学确实在侵蚀着古代史研究,但与此同时,古代史研究也借助于社会科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形态。
注释:
①关于《论李维》的写作背景与年代,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哈维·曼斯菲尔德:《导论》”,第31—33页。
②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43—44页。
③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44页。
④Andrew Erskine,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Hist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必须指出的是,在英语背景中,古代史与中国学人通常所说的世界古代史不同,它仅仅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古代史,即希腊和罗马史,只是因为古典文明从埃及和西亚文明中汲取了太多的养分,因此一般的古代史会包括埃及、两河流域的历史。《剑桥古代史》第一版的主编约翰·伯里明确宣布,“《剑桥古代史》的目标,是欧洲民族连续历史的第一部分。”但是,“欧洲的历史开始于欧洲之外,它的文明是如此深刻地受益于埃及和西南亚更古老的文明,以至于对研究欧洲文明的发展而言,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远较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生活在欧洲范围内的人类的野蛮生活更加重要。那些意欲从其起源追寻他们自己历史发展的人,首先必须熟悉埃及人的、苏美尔人的、赫梯人的、闪米特人的以及东北非和西南亚其他民族的文明。”因此,部分国内学人动辄把《剑桥古代史》作为批判古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靶子,似乎并不合适。参见J.B.Bury,S.A.Cook and F.E.Adcock,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4,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p.v.《古代史指南》中的古代史,主要也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本文所说的古代史、古史学与古史研究,也主要指古希腊罗马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古代史。
⑤该书作者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但也有来自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爱尔兰、以色列和日本等国家者,见该书第xiii-xviii页的作者介绍。
⑥Andrew Erskine,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History,preface.下引该书一律夹注页码。
⑦全书正文共579页。政治史被“驱逐”到了第七部分,一共只有37页(第497—533页)。“生与死”部分100页。如果把地理和经济加入,共322页(第175—496页)。
⑧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序”。
⑨关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参见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一87页。
⑩John Marincola,"Historiography," in Andrew Erskine,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History,p.13.
(11)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页。
(12)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101-121.
(13)塔西陀:《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4页。
(14)Sir Walter Ralegh,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Five Books,London:J.J.and P.Knapton,1733.
(15)Laurence Echard,The Roman History,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to the Perfect Settlement by Augustus Caesar,9[th] ed.,London:R.and J.Bonwicks,1724; Thomas Hind,The History of Greece,2 vols.,London:S.and J.Sprint,1707; Adam Ferguson,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a new edition with 5 vols.,revised and corrected,Edinburgh:Bell and Bradfute,1799; Oliver Goldsmith,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6[th] ed.,London:L.Davis,1769.
(16)Maura A.Henry,"The Making of Elite Culture," in H.T.Dickinson,ed.,A Companion to 18[th] Century Britain,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2,pp.311-328.
(17)《吉本自传》,戴子钦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译者的话”,第4页。
(18)Frank M.Turner,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92-194; William Mitford,Esq.,History of Greece,a new edition,with numerous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to which is prefixed a brief memoir of the author,by his brother Lord Redesdale,8 vols.,London:T.Cadell,1829.
(19)例如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的父亲是个大旅行家;博克(August Boeckh)曾在语法学校受过良好训练,显然也是贵族家庭出身;蒙森(Theodore Mommsen)则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2页;下册,第764页。
(20)H.T.迪金森用“自由和财产”概括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流,应当说抓住了根本。参见H.T.Dickinson,Liberty and Property: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London:Methuen and Co.Ltd.,1979.
(21)John Gillies,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vol.1,London,1792,dedication,p.iii.
(22)Quoted from Elizabeth Rawson,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91,p.356.
(23)Frank M.Turner,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pp.192-204.
(24)Kurt A.Raaflaub and Hans van Wees,eds.,A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
(25)Konrad H.Kinzl,ed.,A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26)例如《古代近东指南》(A Companion to Ancient Near East,edited by Daniel C.Snell,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和两卷本的《古代埃及指南》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edited by Alan B.Lloyd,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0),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也都只占很小的篇幅。近东一卷中,正文部分430余页,有关政治史的叙述不过60页;古代埃及的两卷正文1150余页,政治史部分不过180页。占据全书主要篇幅的是国家与经济结构、社会秩序、语言与文学、视觉艺术、埃及和近东的遗产等内容。编者的意图,显然是力图展现一个文明的全貌。而所谓全貌,在编者心目中,更多的是与当时人的生活有关的方方面面,帝王将相的活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所以在埃及卷中,它只是全书七大主题之一;在近东一卷中,它是全书的五大主题之一。而且即使是在政治史叙事部分,作者也都注意尽可能贴近日常生活,注意其对普通人的影响。
(27)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译者“序言”,第2—7页。
(28)Neville Morley,Writing Ancient History,London:Gerald Duckworth & Co.Ltd.,1999,p.134.
(29)Neville Morley,Writing Ancient History,pp.150-161.这一点让人想起霍布斯鲍姆《史学家: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的有关论述。
(30)李剑鸣:《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第9页。
(31)Neville Morley,Writing Ancient History,pp.154-155.
(32)芬利认为,在古代世界,只有希腊和罗马世界这种以公民群体为中心的活动才有资格被称为“政治”,固然使政治变得过于狭隘,但多少体现了古典世界政治的独特性。参见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33)Quoted from Paul A.Rahe,"Antiquity Surpassed:The Repudiation of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in David Wotton,ed.,Republicanism,Liberty and Commercial Society,1649-776,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46-247.
(34)关于近代以来西方古史研究的发展,参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特别是第四章以下的论述。
(35)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文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总编辑部的话,第1—2、7页。
(36)这里不宜详论20世纪50—60年代有关古代史问题的讨论,请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第401—429页;有关奴隶制的争论及其意识形态色彩,请见《胡钟达史学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1—250、276—292页。
(37)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世界通史体系、特别是在胡钟达、廖学盛、刘家和、张广志、伍新福等学者有关奴隶制问题的讨论中,基本是就史实和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38)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请见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162页;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第401—429页;王敦书:《林志纯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郭小凌:《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郭小凌、祝宏俊:《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近况述评》,《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杨巨平:《日韩中三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之比较——参加“日韩中三国世界古代史学术研讨会”有感》,《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
(39)如刘家和:《谈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要处理好的一些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郭小凌:《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杨巨平:《日韩中三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之比较——参加“日韩中三国世界古代史学术研讨会”有感》,《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等。
(40)Tim Whitmarsh,"Ancient History through Ancient Literature," in Andrew Erskine,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History,p.80.
(41)Thucydides,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the third edition,faithfully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by Thomas Hobbes of Malmsbury,London,printed by P.Morre,1723,p.144.
(42)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enguin Classics,London:The Penguin Group,1972,p.145.中译文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7页。
(43)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rans.C.F.Smit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pp.322-323.
(44)刘家和:《谈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要处理好的一些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5)有关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的争论。请参看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46)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史,请见晏绍祥:《显贵还是人民——20世纪初以来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点的争论》,《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47)刘家和:《谈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要处理好的一些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8)关于古典文明及其对周边民族的认知问题,近代以来已有众多学者涉及。但20世纪90年代以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古代民族认同问题研究的勃兴,既是现实世界巨变的刺激,也是利用多学科方法的结果。有关讨论请见Jonathan M.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16.
(49)帕里和洛德为验证自己的口传诗歌理论,曾亲赴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积累了大批有关口传诗歌创作、表演和流传的理论,并深刻地影响了对荷马社会的认识。参见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50)如 Catherine Morgan,Early Greek States beyond the Poli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Roger Brock and Stephen Hodkinson,eds.,Alternatives to Athens:Varietie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Gree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etc..
责任编审:姚玉民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罗马市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罗马史论文; 古代史论文; 论李维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基雅维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