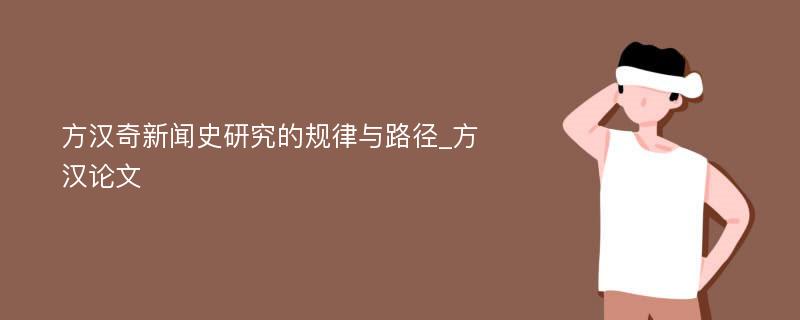
方汉奇新闻史研究的法则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法则论文,史研究论文,新闻论文,方汉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研究是史学家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 史学家的身上,流淌着历史的血液。对史学家的研究本身也是在梳理历史、还原历史、思辨历史、借鉴历史、校正历史和据实书写正确的历史。 作为“自然人”的方汉奇在其已经走过的80多年历程中,从踏上社会的第一步起就选择了新闻史研究的道路,而且一走就是60多年,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新闻史研究的成果贡献社会,每一个阶段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又都烙上了鲜明的社会和时代烙印,成为认识中国社会60年发展历程的见证人,折射了中国社会在60年间经历的巨大时代变迁历程。其次是作为“社会人”的方汉奇代表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60年间的政治学术和心灵历程。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是从旧社会过来、真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思想改造,但受到过不公正对待、改革开放后获得政治学术新生,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则是作为“学术人”的方汉奇及其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间的新闻史学道路,再现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轨迹[2]。 法则与路径1:“以为历史打‘初稿’而为乐事” 方先生曾经说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想当初,他选择新闻,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记者而赢得“风光”,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使他走向了新闻史的研究。虽说原来设定的“目标”没有完全“命中”,但他还是幸运地打到了与新闻工作有关的“擦边球”。带着对新闻史的兴趣起步,从开始时的四顾茫然,到渐次探明前进的道路,再到“痛并快乐”地不断往返穿越新闻史,他在收集、购买旧报纸中找到乐趣,在深入到新闻历史人物之中来感知新闻与社会、新闻与时代等,在不断的积沙成塔中找到新闻史带给他的乐趣。方汉奇告诉我们:做学问的原动力和最直接的动力是选择好自己乐意而为之并且能够从一而终的事。 法则与路径2:“先盘家底、再补缺货” 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方汉奇等为代表的手中基本完成了一个“定式”,学科框架、学科内容、学科规范等趋于认识上的一致和在解读上达成共识。可以说方汉奇等人成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集大成的代表。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方汉奇本着“先盘家底、再补缺货”的原则,在前人的基础是完善、提高、发展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正如《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所介绍的那样,他在盘清家底的基础上,向诸多的空白领域拓展,对已有的资料进行核实与矫正,修正与补全了诸多的历史空白点。 法则与路径3:“挖深井与竭泽而渔” 无论是对新闻史通史的研究还是对个案、个例的研究,方汉奇都把能够、应该找的资料竭泽而渔,在研习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挖深井,如他的代表作《中国近代报刊史》、关于对邵飘萍的研究都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而取得成绩的。 在方汉奇看来,“作为历史学家,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每一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必须对新闻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仔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证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3]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方汉奇曾经研究太平天国的问题,他把当时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成果和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统统找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有3000字左右。事实证明,关于太平天国的这方面研究,无论怎么研究与撰写,很难再在那3000字左右以外鼓捣出新的观点出来。因为他做到了“竭泽而渔”。 法则与路径4:“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就是研究者亲临第一线,在完全现场化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研究,它的核心是实证,就是研究者置身于真实环境之中,以自己的所学、所见、所闻、所访、所查、所探、所参与、所体会、所思考、所总结等等为出发点,进行全面、立体的解读和剖析。实证研究可以直接寻找问题的答案,避免隔山买牛,也能够保证与时代的同步[4]。 在方汉奇新闻史研究的道路上,实证研究的案例不胜枚举:1992年5月,方汉奇访友路过美国旧金山,专程造访一代名记者黄远生的遇难之地,将实地考察与新闻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后写出了校正黄远生人生重要史实的文章;1988年访日期间,他除了参加会议、讲学和参观访问之外,于横滨看了梁启超办报活动的旧址,访完横滨,方汉奇又抽空“开始了在东京寻访中国人办报遗址的活动”,包括《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洞庭波》、《粤西》、《晋乘》、《云南》和《民报》等多家近代著名报刊的旧址。通过现场勘察,方汉奇认为,东京的神田地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办的报刊选择在这里出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原因是:第一,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往来和活动较多;第二,这一地区的书刊印刷出版业比较集中[5]。 方汉奇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然而,方汉奇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固然与其秉性和社会关系有关,但是,如果将“行万里路”与“事实是第一性的”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行万里路”可以为“事实为本”这一治史理念服务[6]。 法则与路径5:“注重口述历史” 方汉奇曾经说过: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既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新闻史的记录不是特别完整,而一些与此直接相关的人除了不会写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而没有把事实留存的打算,而且这样的人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少的。为此,他以“抢救”的意识和行动,采访了许多“活口”,掌握了许多“一手材料”,不仅使史的内容更翔实、更宽泛,而且也多了认识的视角和对待问题的看法。在尝试口述历史方面,他曾经4次访谈罗章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在1981年,年方56岁的方汉奇先生就在《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载《新闻战线》1981年第11期)一文中呼吁加强新闻史人物研究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和抢救工作”。因为“一些早期参加革命报刊工作的老同志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年事已高,要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把那些蕴藏在他们记忆中的宝贵资料挖掘抢救出来”。次年他又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呼吁“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去世的新闻人物要研究,目前还健在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有关材料也可以先着手搜集起来,以便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参见《方汉奇文集》第31页)。 法则与路径6:“多做个案研究” 早在1981年12月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方汉奇就强调要“加强对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7],为此他组织开始了对《申报》、《新闻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字林西报》、《益世报》、《中央日报》、《热血日报》等各种类型的报纸进行个案研究。1992年6月在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时,方汉奇“为了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影响的新闻媒体(如:重点报刊、重点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和新闻工作者,“应该逐个进行个案研究”。1999年,方汉奇在提交的“五十年来的香港、中国与亚洲”学术研讨会论文《新中国五十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一文中继续倡导:“加强深入的个案研究,包括个别报刊个别新闻史人物和个别专史的研究”。2006年方汉奇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中,继续强调“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 2010年,方汉奇在给《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1978—2008》一书作序的时候,也再次提出并强调了“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8]。个案研究成就了他的全与大,个案研究也为更多的新闻史研究者指明了一条道路。 法则与路径7:“团结协作、薪火相传” 方汉奇一生广树桃李,自己培养的学生很多,但他一直秉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团结了诸多同道之人以求“众人划桨开大船”。笔者能够融入新闻史研究的队伍之中,与方先生早年的接纳、指导、引路不无直接关系。不仅如此,他几十年耕耘在新闻教育的讲台上,培养了几代研究新闻史的人才,其中直接就学于他的人,如今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作用和贡献大家是知晓的,他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把所有这一领域的人团结起来,大家群策群力,集体攻关,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如洋洋百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及《大公报百年史》等就是其中的成果。 法则与路径8:“焚膏继晷、行胜于言” 据《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一书附录统计,在几近一生的研究中,方汉奇出版有专著、教材、工具书、文集等17部;发表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206篇;写了书序与书评112篇;有未刊稿31篇。 这个生于1926年的老人,如果从他1948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新闻史研究的论文算起[8],到2013年年末为止,在65年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年撰写或编写各类著作0.26部、论文3.16篇、书评书序1.72篇,未发表的各类文章0.47篇。按照一般的法则,一个学者在35岁之前基本应该是处于“进货”阶段,到了65岁以后,“出货”工作基本结束,有效的产出时间跨度是30年。方汉奇的产量大部分也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这样算起来,他每年平均数是:著作类0.56、论文类6.86、书评类3.73、未刊发类1.03。平均2年编写1部著作,一个月要写一篇论文等。如此的高产,如果没有“焚膏继晷”与“夜以继日”,恐怕他就是神,也难以为之。他用行动向社会说明了一切,这是一个学者最响亮的声音。 法则与路径9:“敢于认输” 方先生后期的部分作品有对前期的否定,因此就有了后方汉奇否定前方汉奇的说法。如在邵飘萍的问题上,争议和反复出现了多次,但方先生最后还是用正确纠正错误,以一种“敢于认输”的态度,“善后”了自己的作品。他说,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比文过饰非好。他认为“敢于认输是一种对待学术研究的精神”。对学术、对学者、对生活,他都是这个态度。宽容别人的错误,不姑息自己的错误则是他对待“认输”的另外一个态度。自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者和作品问世以来,历来呈现的都是“百花齐放”的局面。正面理解,可以把这种现象解读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繁荣,如果换个角度、再把问题说的“严重”一些,则可以认为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由于没有统一的学科标准、没有基本可以固化下来的研究对象、没有大家能够广泛接受或者套用的整体的学科框架而成为了人人都可以描绘的“小姑娘”。对待学术问题,方汉奇赞同梁启超的态度:“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0] 法则与路径10:“史论、史观” “史识”在时间之流中涉及到选题、史观、立场、知识、阅历、理论、异思等。可用函数表示如下[11]: 史识=F(选题×史观×立场×知识×理论×阅历×异思)。 史观“是指导人们考察和研究历史资料的立场、观点、路径和方法的集合”。[12]史观从根本上影响着个体和群体对于史料的“史识”判断。方先生认为:“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史家要从历史研究中提炼总结出自己的史论、史观,要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来享诸社会。他的研究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需求,用鲜明的史识与史观体现史家的责任担当。 方汉奇承认学术研究中“立场”的存在。他曾引过严复之言“一立论不能无宗旨,一举足不能无方向”,认为“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民族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振兴中华,从公民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遵守法律,以及执行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如果是党的机关报或者是党的媒体,还要讲究宣传的纪律。这个立场是必须有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立场,关键看你屁股坐在哪个地方[13]。 方汉奇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认为:几条“法则”,“只是个人的一种追求,未必都做到和做好了,只是用以律已和取法乎上而已”[14]。 或许,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有了这样的“律己”之规,再辅之以“取法乎上”的手段,会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标签:方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