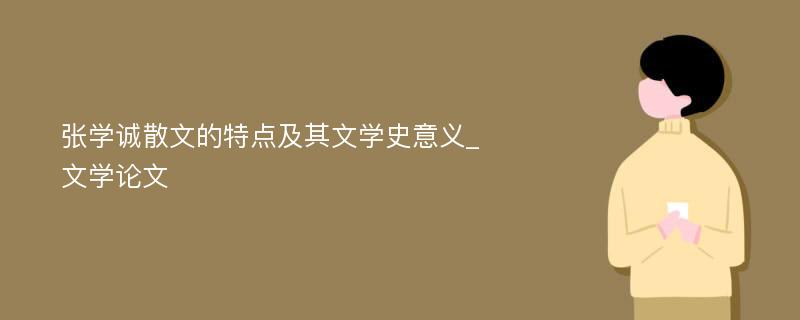
章学诚散文的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文学史论文,散文论文,特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学诚是清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著作合订为《章氏遗书》。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反映了深刻的时代主题。文章朴实无华,条理明晰,才学识兼备,理论性很强,且能把逻辑的说服力和形象的感染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从他那论史、论文、论学的散文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自辟新意的才气和胆识,而且还可以看出其散文奇肆闳通的特征。对于章学诚的散文,目前的研究尚欠深入。其实,章学诚的散文全面展现了他的写作心态,从正面、侧面或反面映照着时代的风云,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一
“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注:《文史通义·知难》。),发抒长期结在心头的闷忧,是章学诚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章学诚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乾隆六年,他父亲中进士,后授官湖北应城县知县,他便随父到湖北。章学诚自幼对史籍异常爱好,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十四五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乾隆二十年后,因父亲被罢职,家境贫困,借寓北京,但他仍苦读不辍。从乾隆二十五年起,他曾多次参加顺天乡试,均落选。后入国子监读书,学士朱筠很赞赏他的才华,特请他到家中设馆。朱筠家中藏书极多,章学诚因而深得遍览群书。不久,朱筠视学安徽,章学诚随从前往。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章学诚就任国子监典籍,第二年中举人,第三年成进士;归部候选,未得官。但他已无意于功名。此后,他先后主讲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涟池等书院。章学诚一生极不得志,为衣食所迫,东奔西走,寄人篱下,但撰写不绝。特别是到了晚年,生活更加贫困,后来眼睛也瞎了,但他仍通过口述,请人抄录,坚持撰述。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因贫病交加,抑郁而终,时年64岁。
从章学诚的人生历程来看,他在当时的确是“知音”甚少。他在给钱大昕的一封信中写道:“学诚从事《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忽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者述矣。苟欲有所挽救,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倡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难矣。惟……著书后世计,而今著书以表暴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注:《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从信中不难看出章氏当时是那样“不合时宜”。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自23岁应乡试起,连续7次赴考,都未中式,生活潦倒,依人作嫁, 直到40岁才中举人,第二年得中进士。仕途坎坷,且又知音难遇,使他思想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情,在他的《感遇》一文中作了尽情宣泄。文章指出,若一个人“趋避不工”,就会“见摈于当时”;然则他又说,假若“工于遇而执持不当”,那也会“见讥于后世”。章学诚既悲叹“士之修明学术,次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之难,却又认为“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因为这是时势所然也。文中指出:“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学文,改尚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途,固其宣也。”所以他认为:“若夫天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而相遇终疎者,则又不可胜道也。”字里行间,章氏的徘徊心绪抒发得尽致淋漓。如果说章学诚在《感遇》篇中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心绪,含“悲叹”成分多一些的话,那么,在《知难》篇中对内心矛盾的发抒,便充溢着对世态不平之“愤慨”。文章一开头,作者便发出极深沉的慨叹:“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接着解释了“知”的内涵。指出:“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与笑貌也。”那么章氏所谓“知”是怎样的呢?他说:“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简言之,章学诚的“知”,就是要“知其所以为言”。可是在他所处之世,“遇合之知”甚难,“同道之知”亦难,特别是在自己的世交中也“迹似相知而心不知”,因此,章学诚在文中再次发出深沉的慨叹:“嗟呼!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注:《文史通义·知难》。)的确,章学诚的处境是极为困窘的,“嬴绌迥殊众”,“往往遭俗弄”(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5页。),就在同道当中,连始终未尝领受过章氏半句贬辞的钱大昕,也“似未能赏识他的见解”(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07页。)。诚然,章学诚也曾想过,“身后之知”也许更加“难言”(注:《文史通义·知难》。),然而他又认为:“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注:《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因此,他又坚信自己是可知之人。虽然“当世之知”“寥寥矣”,但“真知者,自知之确,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待到“浮气息,风尚平”之时,“或千里而外”,自己终究会有“真知者”的。(注:《文史通义·箴名》。)于是,他在《知难》一文中借用庄子“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注:《庄子·养生主》。)的话,从而发挥之。指出:“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黯然自珍,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复杂的心情凝于笔端。若我们把《知难》篇与刘彦和的《知音》、刘知几的《自序》篇作一比照,不难看出,在敢于披露自己内心矛盾这一点上,“二刘”是望尘莫及的;而且章氏又是那样心平气静地发抒,就如同那深深的水,缓缓的流,由胸中自然溢现,绝不是那种疾风暴雨式的狂吼,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气度。当然,在社会的现实面前,章氏只能发出“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知若命”(注:《文史通义·感遇》。)的悲叹而已。但是透过章学诚散文中那郁闷徘徊的矛盾心绪的表露,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有识之士的艰辛际遇。
二
忤逆时趋,放言无忌,“器识闳通”,“议论奇肆”(注:孙德谦:《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是章学诚散文的又一个特征。
章学诚的议论散文,大都能多方论说,善于铺排。缜密而详实。做到条分缕析,给人以一种犀利而以敦实的感觉。如《言公(上)》一文,这是章氏的“得意之作”(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16页。), 主旨是驳斥所谓立言“为私”说。文章首先论述了“贤圣群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公”,认为诗人抒愤言志,是为了“有裨于风教”,“未尝据为私有也”;其次,又从“夫子作《论语》”、“诸子争鸣,推衍学术”、“史家《春秋》之作”、“经师师徒之授”等方面对“言公”之论作了进一步阐述。文章强调:明白古人贯通之文无取虚理,则言有不必出于私而自公;知道古人口耳之传胜于文字,那么言有不得出于私而自公;了解古人专家之文字不重主名,诸子之言每存旧典,则言有不欲出于私而自公。因此,章学诚认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道,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所有也。”文章不算长,却把事理说得清清楚楚。再如《文理》一文,其主要是针对桐城派而发的。文章开宗明义,从根本上提出“学问为立身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接着论述了学与文的关系,并用这种观点去衡量古文学家的评点标识派;最后结论说:“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法所能限”,如果“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心手”,流弊就不可胜言了。文章对桐城文论的针砭是极为深刻的。还有如《说林》、《箴名》、《砭俗》、《原学》等篇,也写得条理缜密,切中肯綮。章学诚的散文能从事物间的内部联系上,透辟地分析说理,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逻辑性。这种逻辑性,不单是靠形式逻辑的推演,而是从本质意义上,反映事物间内在联系,并且能密于综合,使人感到在他的文章中有闳大通达的器量与见识。这是章学诚散文犀利而又敦实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一个史学家与文学家的散文本色所在。
初清的作家,他们的散文大都具备经世致用的特点。就文风方面而言,较纵横恣意。章学诚的散文所以写得文质并茂,自然和他继承前代学者的风格有关,但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他那“逆时趋”的性格有关。章学诚是一个有理想的史学家与文学家,他治学极为严谨。他对刘知几“良史之长,才学识三者不可缺一”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史学家首先要讲究“史德”即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提倡直笔,强调“经世之业,不可以为涉世之交”(注:《文史通义·俗嫌》。),竭力反对“回护”、“讳恶”等文场恶习。他最看不起当时好名之士写的文章,嘲笑他们“风气所趋,竟为考订,学识未充亦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所以,作文除寄托感情之外,还要“有益风化,关系天下”(注:孙德谦:《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他对文章和当前的社会现实的联系看得很真切,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业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易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注:《与史余村书》,《章氏遗书·补遗续》。)又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以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怅触,发奋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注:《又与朱少白书》,《章氏遗书·补遗续》。)所以,章学诚的散文,既有“悻悻得很”的文章,也有反复嗟叹,含有一股浓郁的愤激不平之气的作品。这些散文形式不拘一格,舒展自由;内容丰厚深刻,包容古今,纵横驰骋,奇肆闳通,才气充溢。叶燮曾称贾谊之文为“才人”之文,“天地万物,皆递开避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注:叶燮《己畦文集》卷十九。)若用此语称章学诚之文,也是颇为合适的。
三
长于排比,“深于取象”(注:《文史通义·易教(下)》。),善于通类,“未尝离事而言理”(注:《文史通义·易教(上)》。),是章学诚散文的又一个特征。
在散文中,章学诚敢于提出见解,却又不是一般的书生之见。他的散文,在清人的议论文章中是颇具特色的。章学诚的散文长于运用排比和比喻,形象地说明道理,这其中的形象,是议论的有机部分,但又不同于逻辑推理,本来很抽象的道理,采用比喻的方法,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往往会产生具体而生动的效果。如《说林》一文,作者为了说明“文辞”与“志识”的关系,便运用了生动的譬喻来说明。文章写道:“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毛之翼也。其大鹏千里之身,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晏雀假雕鸮之翼,势未举而先踬矣,况雕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噫!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为了强调说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即文辞与志识)的关系,文中接着运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和比喻:“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文中反复地说明,“志识”是根本,“文辞”只是工具,用通俗的比喻,形象、深刻阐明了内容和形式在创作中的辩证关系。又如《古文十弊》,文中对桐城派作了极为形象的批判,把桐城派“妄加雕饰”之文,比作“剜肉为疮”。章学诚认为,文章要“不讳不恶”,“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所以他把“欲上下左右前后”的作文之法,喻为“八面求圆”;还把只“临文摹书”、“一步一趋”的文风,称之为“削足适屦”;把那“无端而附影者”,谓之“同里铭旌”。说得准确生动,具有说明力。这是一篇针对桐城古文的流弊而发的言之有物的文章,它如响箭,似投枪,直刺要害,而绝不是引经据典空发议论的应制文章。
章学诚不仅长于用排比和“取象”来明辨是非,而且还善于运用类比来说明道理,因为他本身便是一个“通于类”的人。章学诚认为“学者之要,贵乎知类”(注:《文史通义·易教(下)》。),这就使他的议论散文不但深刻生动,而且富有感染力。他在《易教(下)》一文里解释易象时说:“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接着,文章便以生动的类比来说明“象”是“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文中指出:“睢鸠之于好逑,樛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箓之验雨风,甚于傅岩之入梦贲,象之通于《书》也。古官之纪云鸟,周官之清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于《礼》也。歌协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将帅,象之通于《乐》也。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于《春秋》也。《易》与天地淮,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悦有见者。皆其象也。”章氏还认为“象”有二种:“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于是便进一步解了《易》“象”如何通于《诗》的问题。文章指出:“《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这样,便把“象”诠释得极为清楚。这类文章,往往易流行于讲抽象的道理,但由于作者巧于通类,使人毫无抽象枯燥之感。
章学诚还把抽象的说理与引证历史事实相结合,阐明事理。抒发“知之难也”的慨叹,是章氏《知难》一文的主旨,为了深刻地说明“遇合之知所以难言”这一问题,文章列举了历史事实来论证:“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徘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于势不得不然”;“贾生远谪长沙,其后召对宣室,……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刘知几负卓绝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文章通过韩、马、贾、刘四位历史人物,即讲清了“遇合之难”的道理,又使人感到证足据实。
出于说理的需要,章学诚散文的语言明快流畅,挥洒自如。文章骈散结合,以散为主,“文句有长排作比偶”(注:《与史余村简》,《章氏遗书》卷九。)。章氏要求作文要用“通俗语言”(注:《陈东浦方伯诗序》,《章氏遗书》卷十三。),他自己在文章中也努力实践这一主张。胡适曾这样地评价章学诚:“实斋先生若生晚二百年,他一定赞成白话”的(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4页。)。当然胡适的话未免有些绝对化,但从章学诚的文章来看,胡适的推理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章学诚散文的风格特征,我们不妨把他的文章与同一期其他作家的文章略作比照。我们读姚姬传的文章,总觉得更多些丽辞俊语、雅洁之言,因为那是桐城之文;我们读戴东原的文章,觉得理通辩实,锋芒毕露,因为那是思想家、考据家之文;我们读钱大昕的文章,觉得更多些古朴而板质、温柔而敦厚之语,因为那是学者之文;我们读梅曾亮的文章,觉得峻洁至极,笔锋婉转,因为那是政论家之文。而章学诚的散文,有着史学家的“疏通知远”(注: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店1929年版,第11页。)、“探颐甄微”(注:张尔田:《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亦有辞赋家的蕴藉风采;也有纵横家器识闳通、议论奇肆的骋辩余韵。这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四
“甄疑似,明正变”(注:刘承干:《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自辟新意”(注:孙德谦:《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敢于“持世而救偏”(注:《文史通义·原学(下)》。),富有批判精神,是章学诚散文的再一个特征。
章学诚生活在18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初叶。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清王朝建立政权已有一百多年,其统治政权已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在学术领域中,被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汉学”成为显学,垄断地统治着一切学术领域。章学诚正处于这“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虽有大力而莫敢逆”(注:《家书(五)》,《章氏遗书》卷九。)的乾嘉时代。面对“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注:《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九。)的局面,他没有被世风所困,而认为“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注:《家书(五)》,《章氏遗书》卷九。),他的“持世而救偏”的思想,在其散文中得以充分反映。
空谈义理,是乾嘉时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由于统治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士大夫们往往脱离实际去谈“理”说“道”。他们提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论点。章学诚针对这一思想,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大胆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注:《文史通义·易教(上)》。),并引用《易经》上“道”与“器”的关系,阐明有器才有道的观点。他在《原道(上)》篇说:“天地之前,则吾不得已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行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五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不得已而后起者也。”这就是说,有了人,才有人的活动,才有了“道”。人越多,活动越广,“道”才能昭彰明著,积渐发展,成为礼教,成为制度。这就把人看作第一性的物质,而道是第二性的意识,给空谈义理的唯心主义者重重的一击。当然,“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而阐发其义的,但是,在清代考据学盛行,经书考订解释占第一位,同时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当时人们很不重视史学的时代,章学诚能这样地提出问题,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章学诚不仅反对空谈义理,而且能看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不但承认世界是物质的,而且还认为社会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原道(上)》篇中说:“人之初生,至于什五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土娄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所谓吾必如是而可异于前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这说明社会的发展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圣人”只是因势利导,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左右。所以文章最后指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又认为只有学于众人,才能成为“圣人”。在封建社会里,“圣人”是至尊无尚的,“圣人”的聪明才干是先天地而生;而章学诚则提出了相背的观点。他认为“圣人”的聪明才干是学自众人的,“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向众人学习,才能成“圣人”。这个观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不足为奇。然而,在当时“不仅不敢触犯活人,而且不敢触犯死圣人”(注: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的时代,章学诚提出这一论点,是颇具胆识的。
“因袭矫揉,无所取材”,“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这是当时统治文坛的桐城派的流弊。面对这种桐城文风,章学诚敢于独树一帜,“能窥前人未到之处”(注:《家书(三)》,《章氏遗书》卷九。),提出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对标举义法的桐城派和揭橥性灵说的随园派,对清代文坛的形式主义和种种模拟倾向进行了有力尖锐的批判。首先,他认为“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注:《文史通义·朱陆》。),对古文家之空言无实,斤斤于法度规矩、音节神味,进行了抨击。指出:“可授者规矩方园,其不可授者心营意造”。“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注:《文史通义·文理》。)特别是对姚姬传倡言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结合为一,章氏则运用批判的眼光,指出三者的流弊。“骛于博者,终心弊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注:《文史通义·原学(下)》。)这种批判精神,是非姚姬传所敢望的。他在《答客问(中)》又指出:“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而闻也。”由此亦见其破除迷信、大胆创新的精神。其次,章学诚强调文学要写其“中有所见”。他在《文理》篇中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朗朗,如锦工秀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作楚怨也,不亦傎乎!”文学追求神似,以“形似”为目的模仿古人,这正是沈德潜、翁方纲的通病,也是桐城派只求法式而不求“中有所见”的弊病,对此,章学诚的批评,无疑是十分中肯的。对于无病呻吟、以“媚世”为能事的作品,章学诚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也!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注:《文史通义·质性》。)。这对当时的文坛无疑具有针砭作用。
与此同时,章学诚还认为文章要能表达自己的创见,要有明确的目的,而文辞只是表达的一种工具,所以他认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文生于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注:《文史通义·砭俗》。),“质去而文不能独存”(注:《文史通义·黠陋》。),“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这些理论在今天还不失其应有的价值。
诚然,章学诚的这些“新意”和“创见”以及他那批判精神,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所重视,没有激起多大波澜;但是他提出的这些主张,“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对清代中叶的学风和文风,对晚清文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1999年1月收到。
标签:文学论文; 章学诚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章氏论文; 散文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文史通义论文; 史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