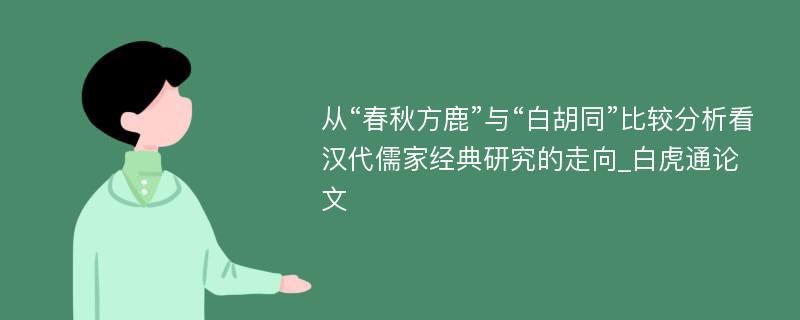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汉代论文,视角论文,春秋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8)01-0062-07
一、引言
在汉代经学的发展过程中,《春秋繁露》与《白虎通》是两部较有代表性的经学著作。《春秋繁露》为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所作。汉武帝置五经博士①后,做经学博士者,多是儒学大师,而五经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国家重要决策都试图从经学中寻找理论依据。经学博士作为经学的权威、官方理论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影响很大,每每皇帝遇大事总要策问经学博士,经学博士则多秉承旨意,从经学中寻找皇帝所需要的理论依据。因此举凡一切重大决策,皇帝都要诏举经学博士参与其议。如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董以发挥《公羊春秋》作答。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继武帝设经学博士后,经汉宣帝增立《谷梁春秋》诸经博士,平帝立《逸礼》诸经博士,到东汉光武帝立十四家经学博士。博士数目不断增多,而同时今、古文经学两派及一派之内对同一经的解释又各有不同的家法,造成了经义(对经的解释称为“经义”)的分歧,令学者无所适从。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汉章帝建初四年汇集群儒于白虎观召开会议,“讲议五经同异”,试图通过讲议五经异同,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统一各家对经义的歧解纠纷,进而做出融合各家各派的规范性结论。汉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简称《白虎通》②。
在《春秋繁露》里,董仲舒发扬《春秋公羊传》中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之学术精神,主张为政“必也正乎名”,通过发挥天道观、阴阳五行思想,进一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性。《白虎通》的思想体系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性阐发,也是通过对天道观、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吸纳当时的谶纬神学来完成的。前者是在今文经学独大的西汉,后者是在古文经学与谶纬兴起的东汉,通过比较二者思想内容及论证方式,我们可以从一定角度勾勒出汉代经学发展的轮廓。
二、二者天道观的对比分析
汉代经学的突出特点是因应旧有的宗教神学秩序的崩溃与出于重建政治信仰的需要而“神道设教”,在天道观的基础上,把传统阴阳五行说引入经学的领域并巧妙地结合,借助并发挥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性,并以神学复归的形式重新阐释天(神)人(君)关系,树立对天道的信仰,进而建立起一个与政治一统相呼应、以儒家价值观、伦理观为旨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抬出一个具有神秘意志的主宰之“天”,论证天人合一的同时,也借“天”的权威性来约束君主。《白虎通》继承了《春秋繁露》中的天人之论的神秘因素,论证方式上更为严密,内容上则强调制度层面上的信仰与约束。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天道观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种自觉努力。董仲舒从公羊学立场出发,《春秋繁露》首先提出天人感应论。以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论证天人合一,抬出一个带有神秘意志的“天”。进而以“天”为人道之本,由天道贯通人道。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面,“天”带有神秘意志,天道分阴阳二气,阴阳生成五行,五行之间相互生克,由此产生万物。《春秋繁露》的经学思想是由天道、阴阳五行、儒家的纲常伦理贯通而下的。
《春秋繁露·顺命》中认为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1](顺命第七十P940)既然人与万物都是为天所生,自然会有“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阴阳义第四十九P767)进而,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从人的生理构造、道德情感方面论证了人和天是同类,即“人副天数”。不但如此,天还通过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并指导万物和人类,相互感应,“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1](顺命第七十P944-947)天既然为人与万物的主宰,君主又受命于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1](尧舜汤武P215)“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宣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1](深察名号P648)君主还要效法天教化臣民,实行德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1](基义第五十三P788-791)这里,不但君权神授,而且儒家的伦理纲常也是来自于天道,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是,君权神授也必须受到来自于天道阴阳的道德伦理约束,如果君主逆天而行,不行德政,天自然会通过警告与天谴来惩罚君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1](二端第十五P346)董仲舒在强调天人感应的同时,发扬公羊学的《春秋》大义精神,要君主“屈君而申天”,[1](玉杯第二P48)借助天来约束君主,使其不违天命。
在董仲舒的天道观里,他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全部视为天的意志。在他的《春秋繁露》中,天道就是人道最好的指示灯!这种天道观在思想内容上带有很强烈的神秘色彩和宗教信仰特征,论证方式上也是较为粗糙直观。这正是汉代经学初期的特点。
相比于《春秋繁露》中的天道观,《白虎通》中对天道观的发挥与论述更为严密,而且强调信仰的同时更强化了一种制度层面的约束。
《白虎通》中的天道观一方面继承了董仲舒天人之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强调天的至高无上性,“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2](天地P420)另一方面,已不再像《春秋繁露》中那样偏重强调天的神秘意志与主宰性,而是着重论述天的神圣性与秩序性。从天的神圣性、秩序性出发,以天道推人道;进而以人道反证天道,表现出比《春秋繁露》更为严密的论证方式。
在强调天的神圣性方面,《白虎通·五经》中指出圣人为“象天五常之道”而作“经”,以“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而“经”因此获得了来源于天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也正是汉儒的共同信仰。而在强调天的秩序性方面,《白虎通》借助被汉儒强化了的天道崇拜对现存制度、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如《白虎通》受当时谶纬的影响,在《天地》篇中构想出一个由天—地—元气(太初)—形(太始)—质(太素)的宇宙创造万物的过程:“天……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初布,庶物始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性情,性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2](天地P420-421)进而《五行》篇中,又将阴阳、五行说与四季、四方、四色、五音、五帝、五神相配合,形成一个以天为首,阴阳五行为框架的严密而有序的系统。③
在论证方式上,《白虎通》从天的神圣性、秩序性出发,不但以天道的合理性来推阐人道的合理性,而且以人道来契合天道,进而以人道反证天道的合理性。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比《春秋繁露》更为严密的论证方式。《白虎通·天地》篇中谈道:“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周者,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也。”[2](天地P422)《白虎通·日月》篇则言:“日行迟,月行几何?君属臣劳也”[2](日月P424)这是以君臣之义,来比拟天道运行,并试图对其做出伦理化解释。《白虎通》借此来说明君臣之义与天地日月运行,都具有天然合理性。而且王者与天又是相通的,他们“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2](封禅P283)与此相应,操纵在帝王君主们手中的政治制度也一样神圣、合法,不可侵犯。这又衍生出儒家思想学说的道德伦理的教化功能由神秘性宣扬进入到制度上信仰的层面,进而儒家思想学说成了制度性内容。这比《春秋繁露》的仅从天道信仰的神秘性上展开的粗糙论证要高明的多,表现出汉代经学在发展中无论从内容上还是理论的论证方式上,都进一步成熟。
三、对二者阴阳五行思维框架的对比分析
汉代经学的突出特点还体现在重建天道信仰的过程中,借助并发挥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性。但在引进发挥传统阴阳五行学说这一问题上,《春秋繁露》和《白虎通》有很大的不同。《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思想来构建天道,以此来模拟人事,突出道德伦理方面的说教,同时,以阴阳论德刑,以五行论官职,构建起一个天道——阴阳——五行——万物——人事体系。相比于《春秋繁露》言阴阳五行,《白虎通》则侧重言五行,并继承《春秋繁露》中的阴阳主从关系来论证封建等级秩序,把人间社会的一切纳入之一体系,进而论证礼乐与道德教化的可能,对儒家的伦理纲常展开论证。可以说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是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被丰富发展的过程。显示了汉代经学在发展过程中借助并发挥阴阳五行说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突出特点。
在董仲舒的公羊学里,天道观是以阴阳五行为框架来构建的。在《春秋繁露》中,他将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一整套更为系统、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④“《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3](P215)在这一点上来说,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相较于以前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更加完备,也是战国以来阴阳家学说的继续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提出:“凡物必有合。”[1](基义第五十三P788)作为事物跟自己的对立面是个分不开的合体,阴阳相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1](基义第五十三P788)显然,阴阳的关系成了一切事物的根本关系。《汉书·五行志》中班固也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里的“始推阴阳”,就是从自然现象中推断阴阳二气的运行状况,以探求天意,借以纠正人事的错误。董仲舒“推阴阳”的同时,也结合五行思想来进一步以天道模拟人事。天地之气分而为阴阳,列为五行,五行之气涵盖了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方方面面。儒家的纲常伦理和君主的政治运作概莫能外。这也是汉代经学对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解。
但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较之以往此类理论有着突出的道德伦理化的特征。他明显将之比附社会人事,指出“阳贵而阴贱”,“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贵阳而贱阴,天之制也。”[1](天辨在人第四十六P753)“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1](基义第五十三P788)董仲舒还将阴阳与五行联系起来,将五行也赋予儒家的纲常伦理属性,“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1](五行之义第四十三P711)例如五行相生,恰如父子之间“厚养生而谨送终”[1](五行之义第四十三P714)之义。非但如此,“阳贵而阴贱”是不可动摇的,“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楚庄王第一P29)如此一来,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就被纳入阴阳五行家的宇宙图式之中了。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较完整的天道、阴阳、五行之体系,天之上有“元”,“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1](重政第十三P320)元之下,才是天,天又分阴阳二气,“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1](天地阴阳第八十一P1089)同时,“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1](五行相生第五十九P833)不难看出,元——天——阴阳——五行——万物——人,构成了董仲舒的经学世界。
《春秋繁露》中言阴阳与五行,分列篇章而谈,而且各自的倾向也不同,言阴阳侧重点在论德刑,而言五行侧重点在论官职⑤。在《春秋繁露》中,阴阳五行的变化,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天道尊阳卑阴,阳是天之恩德的表现,阴是天之刑罚的表现。君主要推行其政治,不但需要利用赏罚制度来保障,同时还需要凭借天数任官设职,“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以此观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1](官制象天二十四P493)在这一问题上,董仲舒通过对阴阳五行的阐发来论证君主之赏赐刑罚与任官设职等重要制度问题。如此一来,君主取法天数与阴阳五行,设官任职,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从不可怀疑的角度上保证大一统君主政权的畅通行使。
相对于《春秋繁露》中分列《阴阳》、《五行》篇,《白虎通》中只列《五行》篇,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白虎通》论阴阳没有充分展开,而是着重论五行思想⑥。其实,《白虎通》也讲阴阳,只是没有像《春秋繁露》那样明确将阴阳与五行各自分列篇章。另一方面,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到《白虎通》,阴阳五行思想在这一阶段的经学发展过程中,是有一个逐步完善与体系化的过程。董仲舒之时阴阳五行理论只限于将五行归于少阴、少阳、老阴、老阳,还没有形成完备的阴阳之数合成五行之数的复杂理论和五行图式⑦,而《白虎通》中体现了阴阳五行理论在汉代经学发展中的这一明显过程⑧。具体而言,《白虎通》论阴阳五行,与董仲舒多有相同者,但相较之下,更为详细。同《春秋繁露》一样,《白虎通》用阴阳概念主要用来构建封建等级秩序,阴阳之间的主从关系是不变的,同时结合这一阴阳观展开对五行思想进行阐发。
在《白虎通》中,天地之间阴阳五行的法则,都是天道、天意,是人道效法的榜样。不但王者制定礼乐要法天地之阴阳,“乐以象天,礼以法地。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2](礼乐P93-94)包括军事、政治以及社会道德在内,都可以在阴阳五行生克关系中找到效法榜样,都是“欲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2](乡射P250)由此以来,社会人事、政治制度,都是法天地阴阳而来,帝王君主在人间建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无一不是天意的体现。
在《白虎通》看来,帝王之所以能对百姓会进行礼乐与道德教化,正是由于人是禀天地五行之气而生,含有五常之性。“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涤荡,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泆,节其奢侈也。”[2](礼乐P94)五行是从天道贯通人道的一个环节,帝王君主据此进行礼乐教化,其政治原则是设“三教”,“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2](三教P369)“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也。”[2](三教P371)而“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而成。”[2](三教P371)教,就是上行下效。不单靠社会法度,更要靠道德自律。然而,“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2](爵P15),《白虎通》跟《春秋繁露》一样,天道是人道、社会生活的最高指示,是“百王不易之道”[2](三正P365),是永远不变的。
在《白虎通·五行》中,五行还是侧重于儒家的纲常伦理进行展开的。“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2](五行P166)但 “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灭火,报其理。”[2](五行P189)“五行各自有阴阳,木生火,所以还烧其母何?曰:金胜木,火欲为木害金,金者坚强难消,故母以逊体,助火烧金,此自欲成子之义。”[2](三正P190)经学思想里的阴阳五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论道德上来的。这一点,《白虎通》与《春秋繁露》都是一致的。
由上可见,尽管《白虎通》没有像《春秋繁露》那样单列《阴阳》篇,但是用阴阳思想来论述儒家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同样存在,并且言阴阳并没有离开五行思想。一方面,《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以来的今文经学道德伦理化了的五行思想;另一方面,《白虎通》受到谶纬的影响,试图用阴阳五行思想来解释一切现象。这反映了经学在发展过程中更加依赖阴阳五行这一思维框架并用来解释一切社会人事的现象。在今天看来,这不但增加了其自身的牵强附会的成分,而且也加重了荒谬程度,更是汉代经学走向衰落的一个先兆。
四、对二者纲常伦理思想内容的对比分析
汉代经学宣扬天道崇拜,发挥阴阳五行学说,最终目的是为了论证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框架构建以君主为中心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并进一步为其提供天然合理依据。这一点《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也是一致的。董仲舒依据天道与阴阳五行学说推证三纲五纪的合法性,并借助天的权威宣扬儒家名分,《白虎通》不但继承了《春秋繁露》三纲五纪思想的基础,而且又进一步丰富为三纲六纪,进而借助阴阳五行思想解释伦理纲常的来源并论证其合理性,赋予帝王政治体制下的儒家伦理以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也显示出经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天道推阐人道,进而来论证纲常伦理的合理性的内容上更加丰富,论证方式上更加严密。
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董仲舒讲:“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常者,斯可矣。’”[1](深察名号第三十五P676)《基义》中又讲:“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基义第五十三P788)董仲舒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正是王道之纲纪。同样在《基义》、《五行之义》、《五行对》、《离合根》、《五行相胜》、《仁义法》等篇中,董仲舒依据天道与阴阳五行学说推证三纲五纪的合法性,并借助天的权威,宣扬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应各尽其分,这一思想后在纬书《含文嘉》中被推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三纲思想又为后来的《白虎通》所采用,进而推为儒家所奉的天经地义,成为君权制度的护符。
《白虎通》在发挥天道观、阴阳五行学说论证纲常伦理的合理性上,不但继承了《春秋繁露》三纲五纪思想的基础,而且又进一步丰富为三纲六纪,尤其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没有详细解说的“五纪”展开为“六纪”,并将此推为天经地义。“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纪纲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2](三纲六纪P373-374)这里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等传统社会中的各种人伦关系网罗其中,在各种关系之中,“民臣不可一日无君”,[2](爵P33)“天下之大,所共尊者一人耳”。[2](爵P47)如此,从高高在上的君主到普通百姓,他们的等级、名分、称号等等,在三纲六纪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地位。
而人道的三纲六纪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合理性又在哪里呢?在《白虎通》,人道的基础与合理性建立在了天道上,社会上的一切纲纪、制度皆取法于阴阳五行,是取法天地。“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2](三纲六纪P374)“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又施化端也。”[2](三纲六纪P375)帝王取法于天,天授予其合法性、超越性与神圣性,他不但是人道的核心,而且高高在上,“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2](爵P1-2)高居人道顶端的帝王成了天之子,且既受命于天,就自然能受命改制,非但如此,帝王君主的地位还是排他的、不可动摇的,帝王“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2](三正P368)这样,以帝王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就取得了天经地义的合理性。
相较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圣人发挥天意“深察名号”,借助经典发挥微言大义,《白虎通》这种论述无论从内容的丰富程度上还是从论证方式的严密程度上,都远超过了《春秋繁露》,显示了经学发展中以天道推阐人道来论证纲常伦理的合理性的内容上更加丰富,论证方式上更加严密。
五、《春秋繁露》对谶纬的影响与《白虎通》对谶纬的吸纳
汉代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其理论原则和思维导向直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汉代经学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这种经学思维模式的“异化”使得在以后的经学发展中,阴阳五行化的思维模式使其阐释越加精细繁琐,在今人看来,这使经学更加流于神秘主义的一面。同时这一过程,也体现了汉代经学在发展过程中对谶纬的吸纳与融合⑨。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手段来演绎经义、论说灾变,已为谶纬先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谶纬之学,《白虎通》成书后,谶纬更被改造为论证儒家三纲五常的论据和工具。进而谶纬又被经学吸纳进来并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经学内容,使经学自身进一步成为论证王道政治的工具。这一方面加剧了汉代经学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标志着在汉代经学的发展过程中今、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由分歧、斗争开始走向统一融合。
如前所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手段来演绎经义、论说灾变,这已成“谶纬之滥觞”(刘师培语),是典型的西汉今文经学家们所流行的天人感应说,它为经学与谶纬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点。如《春秋繁露·二端》中提出神秘灾异、谴告说的同时,并主张“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二端第十五P346)把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的关系概括殆尽。君主为政的好坏,会直接感召出天的祥瑞与灾异。类似这种论说在《阴阳义》、《离合根》等篇中并不鲜见。董仲舒的这种祥瑞、灾异说对于谶纬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当时的《汉书·五行志》以及当时的纬书中也会经常看到这类论说。可以说,董仲舒之后的谶纬之大规模产生、发展及纬书的形成,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说,有着一定关联,其后的纬书从形式到内容,都难免受到《春秋繁露》的影响。
董仲舒之后,随着经学与谶纬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经学谶纬化思潮,到两汉之际达到极盛。到白虎观会议召开及《白虎通》成书后,谶纬更被改造为论证儒家三纲五常的论据和工具。《白虎通》中神化君主,多利用谶纬中现成的说法,不必通过逻辑论证,很方便地就突显了君权神授的神学信仰。如《白虎通·爵》篇说:“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也,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复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称天子也?以法天下也。”[2](爵P1-4)天子“王天下”是天命所赐,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附加条件。这种看似不证自明的天命神学氛围,正是由董仲舒天人感应、灾异说思想到谶纬盛行逐渐演变而成的。而在这种谶纬被改造为论证儒家三纲五常的论据和工具的同时,又被经学进一步吸纳,经学自身也更加成为论证王道政治的工具。由此可见,一方面,谶纬发展了董仲舒的神学思想;另一方面,《白虎通》吸收了这些说法,进一步系统地采用谶纬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资料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性。总体看来,在汉代经学与谶纬交织发展过程中,经学影响了谶纬的发展,同时,谶纬又被经学吸纳进来并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经学内容。当然,从另一个消极角度看,这又加速了汉代经学的衰落。
从《春秋繁露》所表现出来的今文经学独大,到《白虎通》以今文经学为主吸纳谶纬、融合古文经学,把各家各派所阐发的纲常伦理思想,融会为集大成的经学著作,这标志着在汉代经学的发展过程中今、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由分歧、斗争开始走向统一融合。
通过对《春秋繁露》与《白虎通》这两部汉代经学代表性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白虎通》的基本思想实质上和《春秋繁露》一样,都是建立在汉代经学的天道观基础上,以纲常伦理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但它不像《春秋繁露》那样只是《公羊》学派的一家之言,而是以今文经学为主,又综合了各家思想成果尤其古文经学与谶纬之学。这代表了当时所达到的认识水平,从而把董仲舒以来的汉代经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诚如今人余顿康先生所言:“从汉武帝到汉章帝这两百年间的经学发展,经学是一个时代思潮。如果说董仲舒是这个思潮的起点,《白虎通》则是这个思潮的顶峰。”[4](P88)从思想内容上看,《白虎通》中贯穿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把天的神秘权威性拉到政治制度中来限制君权,同时,从天道推出人道,又从人道反证天道,贯通天人,为现存典章制度的合理性寻求形而上的终极根据。这一方面推动儒家经学思想向政治体制中渗透,强化了儒家思想在封建帝王政治运作模式中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出今、古文及谶纬的融合的端倪,不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并用,而且谶纬之学和经学并用。从经学发展的角度看,《白虎通》作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由分歧走向统一融合的产物,最终适应了东汉政权加强统治的需要,也标志着经学开始走向统一与融合。此后,今、古文以及谶纬神学进一步融合,并为谶纬之学的泛滥、经学的最终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
收稿日期:2007-03-22
注释:
①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史籍所言博士,实指经学博士,与先秦及西汉初的官职博士不同。就汉代官制而论,博士只存在于西汉初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存在的只是经学博士。自班固以来,各种著述都将博士与经学博士混而为一。清代胡秉虔、近代学者王国维和当代学人周予同先生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今人黄开国先生对此问题也有详细论述。
②统一经义乃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这种事情在西汉时代就做过,如《汉书·宣帝纪》中载汉宣帝于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
③此处材料部分取自今人程勇先生与葛兆光先生相关论述,详见程勇《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53-54页,101-102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390-391页。
④董仲舒在公羊学里对阴阳五行说的全面运用,使汉代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得以发展和完善。包括此后京房将五行学说全面引入易学领域,董仲舒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今人张涛先生在其《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对此问题有较详论述。
⑤限于篇幅,此处不做展开。另,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已论及五行与官职问题。详见其《两汉思想史》第二卷236-23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⑥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中论及《春秋繁露》的阴阳五行观与《白虎通》的五行观认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分阴阳、五行分列各篇,并且将少阴少阳太阴太阳视为与五行平衡的二物,由此认为董仲舒的五行之气乃是与阴阳平行之气,并且说这是董仲舒的一大“滹漏”,而《白虎通》把五行纳入阴阳统贯之中,阴阳为五行分化的五种状态,这是在传承中弥补了董的“滹漏”。他举例《天辨在人》第四十六中“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笔者认为这是不确切的,首先,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里,少阴、少阳、老阴、老阳是对阴阳消长的一种状态描述,本身不是整体的阴阳,徐先生将这二者对等起来,是有待商榷的。其次,董仲舒在《阳尊阴卑》第四十三中与《天辨在人》第四十六中对这一问题,有过详细的论述,《阳尊阴卑》第四十三中“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故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于发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是;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很明显,这是在说,正月阴气衰极(老阴之后),阳气复起(少阳),而这个阶段,以五行论正是孟春木始生发之时。春天万木生发之时正是阳长阴消之时,是从时间和方位上对这一问题作描述的,而不是说这里的阳气等同于五行之气。“阳气出于东北”、“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天辨在人》第四十六)”正是说明,阳气初长之时,正值生长的木气,在这个时空点上助长春天之生机。
⑦到扬雄,将五行之数“分阴分阳”,与阴阳之数进一步结合,而到刘歆五行生成图式已经比较完备。
⑧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详见今人王葆玹先生《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62-466页。
⑨尽管《白虎通》以今文经学为主,但也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古文经学的思想,成为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肇端。限于篇幅,本文对此问题不作展开。清人庄述祖《白虎通义考》与近人沈瓞民《〈白虎通引书表〉补正》对《白虎通》此问题有较详探究。尽管《白虎通》中古文经学的部分占的篇幅并不大,但这毕竟标志着汉代经学发展到东汉初期,开始突破了西汉以来壁垒森严的师法、家法之禁锢,开始走向今、古文经学融合的阶段。至东汉末年,郑玄出而以古文经为主遍注六经,兼采今文家之说。则标志着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走向高潮。
标签:白虎通论文; 春秋繁露论文; 董仲舒论文; 儒家论文; 阴阳五行论文; 经学论文; 阴阳学论文; 汉朝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天道论文; 五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