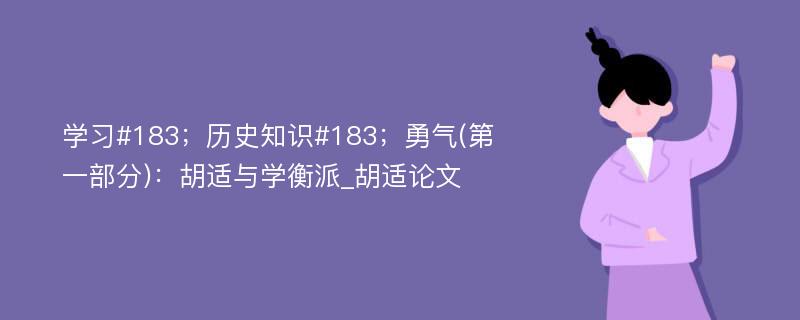
学识#183;史识#183;胆识(其一):胡适与学衡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胆识论文,学识论文,史识论文,学衡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分子首重“学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正是这个“学识”,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学识”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有了“学识”,才成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学识”不是生而知之的,也不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直接的感觉、感受和体验积累起来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的传承——首先是学校教育——从前辈和前辈的著作中接受过来的。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直接的感觉、感受和体验获得的知识是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只局限在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之内,所以很难形成有系统的知识和有系统的思想。只有通过学校的教育接受的前人的知识和思想,才有可能是有系统的,因为那是前人在整理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之后集中表述出来的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通过整理,就有了系统,各种知识和思想观点之间就有了联系;有了联系,也有了相互之间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知识或思想观点都不是整体,整体是由所有这些知识和思想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联系起来的(现在有时也称作“编码”的过程),并且其中还留有大量的空白,容许后人将新发现的知识、新形成的思想放在这个系统里,并取得它在这个系统中的特定的位置,获得自己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古代的孔子思想、老子思想、墨子思想、庄子思想、韩非子思想等等,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思想学说,被我们称之为各种“主义”的外国思想学说也是这样一些思想学说。当我们接受并掌握了其中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我们的知识和思想也就有了系统性,我们就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了。我们接触到一个事物之后,除了像老百姓一样感觉、感受和体验到它本身之外,还会将它放在自己的知识系统和思想系统中感觉它、感受它、理解它,我们对这个事物的感觉、感受和理解就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了,我们也就成了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的人,成了“知识分子”。看不起我们的老百姓称我们是“书呆子”,看得起我们的人称我们是“知书达理的人”、“有教养的人”、“有学问的人”。这都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与他们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了“学识”,这种“学识”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当我们追溯到中国现代学术奠基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下列两类知识分子:其一是像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这样一些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派”,其二则是像林纾、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这样一些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是当时的“文化革命派”,还是当时的“文化保守派”,实际都不是目不识丁的“引车卖浆者”之流,不是没有“学问”、欠缺“学识”的一些“普通老百姓”,而是一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是一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如果说林纾在“学识”上还是一个有明显缺陷的人,还是一个对西方文化知识缺少必要的了解的人,那么,“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则不同了,即使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他们也是不让于那些“文化革命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他们在出国之前,都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实际就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教育),而后到美国留学,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教育,接受了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成为中国第一代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信徒。——在“学识”上,他们与“文化革命派”一样,都是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识渊博”的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除了“学识”之外,还有一种“史识”。“史识”也包括在“学识”之内,没有“学识”的人,也不会有“史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学识”。“学识”是空间性的,“史识”则是时间性的。“学识”是将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纳入一个空间性的结构之中,将其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①《春秋》是一部历史书,为什么孔子作了《春秋》,“乱臣贼子”就“惧”了呢?因为《春秋》叙述的虽是一些历史的事实,但所贯穿的却是孔子的一套伦理道德的思想。人们掌握了这套伦理道德的思想,对“乱臣贼子”就有识别力了,就有对付的方法了,“乱臣贼子”也就不能不“惧”了,所以《春秋左传》被编入“五经”之中。“经”就是“思想”,就是“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空间性的。“史识”则是将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纳入一个时间性的结构中,将其构成一个前后继起的链条。这些历史的事实也是通过阅读前人的著述逐渐掌握起来的,因而也是“学识”,但将其作为前后继起的变化过程看的这些知识和思想,构成的是人的历史的意识和历史的观念,增强的是人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变化脉络的寻绎和思考。“究天人之际,述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这就有了“史识”。到了清代,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就是说连儒家的思想,也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在历史上演变的,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大量的历史知识。 当我们想到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学识”,但当我们想到胡适,就应该首先想到他的“史识”了。胡适也是有“学识”的,其“学识”也是很“渊博”的。在出国前,他也像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一样,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文化传统的教育。出国后,他接受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学说,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弟子。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但是,当我们考虑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他提倡的白话文革新的时候,仅从他的“学识”想是想不明白的,而应当从他的“史识”上来想。事实上,胡适凡是讲到“五四”新文化革命、新文学革命和“五四”白话文革新的地方,主要讲的就是“历史”,就是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书面语言历史发展的看法。这种“史识”,胡适称之为“历史的眼光”,是与一般的“学识”不同的。胡适说:“国内一班学者文人并非不熟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的看法。譬如孔子,旧看法是把他看作‘德侔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圣人,新看法是把他看作许多哲人里面的一个,把孔子排在老子、墨子一班哲人之中,用百家平等的眼光去评量他们的长短得失,我们就当然不会过分的崇拜迷信孔子了。”③胡适说的“旧眼光”,实际就是作为“学识”看的孔子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是无所不包的,是能够容纳下中外古今所有事物并给以特定的感受和认识的,而胡适所谓的“新眼光”,则是他的“史识”,在这种“史识”中,孔子只是中外古今思想家中的一个。这就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的思想不同了。 实际上,“学识”与“史识”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社会、认识历史的方式,用一种“史识”完全取代一种“学识”固然是不可能的,但用一种“学识”完全取代一种“史识”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学识”以及“学识”与“人”的关系有一种更精确的认识。如前所述,所谓“学识”,是通过学习从前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一种有系统的知识和思想,这使“学者”具有了较为完整、系统地感觉、感受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超越了没有文化的社会民众,也超越了原来童蒙未开时的自我,成了“知识分子”。但是,这种超越,只是对没有社会思考能力的人的超越,也是对各种分散的、零碎的知识(事物)和思想(想法)的超越,而绝对不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超越。在这时,“学者”还只是“被构成”的“客体”,还不是构成性的“主体”。他像是住进了一个别人已经布置好的房间,他知道将自己使用的生活用品应该摆放在房间的哪个部位,也知道如何打扫房间使自己的房间更加整洁和舒适,但这个房间却不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还没有按照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独立设计一个房间的能力,更没有按照别人的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设计一个新的房间的能力。与此同时,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上,这样的“学识”都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在中国古代,有孔子的思想学说,也有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的思想学说,它们都是在自己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并在自己特定的视角上建立起来的知识和思想的系统,都是可以起到整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思想的作用的“学识”,也都能通过师承关系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这就有了不同的“学统”,不同的“学统”有不同的“学识”,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概念系统,不同的学理系统,它们是通过自己的概念系统、学理系统组织和整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孔子思想传统中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等概念;老子哲学中有“道”、“德”、“有”、“无”、“自然”、“万物”、“有为”、“无为”等概念,这些概念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些“学理”,如孔子思想中有“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老子哲学中有“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等,彼此的概念不同,学理不同,所以彼此也是不相兼容的:孔子思想无法将老子哲学完全包含在自己之中,老子哲学也无法将孔子思想完全包含在自己之中。一个后学者从自己的师承关系中拥有了自己的“学识”,也认为自己的“学识”是可以对自己接触到的所有事物做出完全合理的判断的,但他的判断却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庄子早就说过:“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④意思是说,要把老师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呢?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可以师承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胡适当然也可以师承杜威的实用主义。彼此的是非标准先是不同的,仅从学理上是争不出彼此的是非曲直来的。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分子,“学识”是很重要的,但仅仅有“学识”还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学识”都是有限的,自己的“学识”可以帮助自己发现某个范畴的真理,但它也有可能掩盖起更大范围的真理。 孔子思想在中国之所以给人以“德侔天地,道冠古今”的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印象,不是因为它真的具有绝对真理和永恒真理的品格,而是因为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更适于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整个社会和平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因而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直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宋明理学家则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文化传统对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校教育的统治地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学识”,首先就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学识”。在中国,不论一种知识和思想就其来源是怎样的,但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将其纳入儒家文化传统的思想体系和概念体系中进行重新的组织和整理并给以特定的价值评价之后,就都包括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学识”范围之中,使传统儒家文化也有了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和永恒真理的外观。无论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还是胡适、陈独秀、鲁迅都曾在国内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与胡适、陈独秀、鲁迅不同的是,他们在国外接受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也是极为推崇的,这不但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儒家文化传统的信仰,同时也通过儒家文化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神圣化了。这使他们产生了一个错觉,即他们在美国接受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就是“德侔世界,道冠中西”的“学识”,因而他们也有了以自己的“学识”裁判一切是非的能力。周佩瑶指出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预设和期待,即是成为维持‘圣道’、传播‘人文主义’的‘圣人’和‘人文主义者’”⑤。并从他们的这种“身份想象”阐释了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说是掐住了他们的思想命脉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历史”永远不是仅凭“学识”和“学理”就能推断出来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具有多么丰富的“学识”,不论有着怎样忠贞的信念,都无法预见将有一个叫做英吉利的国家会用它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会使中国从此走上一条不同于过往的历史道路。这里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即在那时,英吉利和它的大炮根本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识”范围之中。对于他们,这些东西是从“无”中冒出来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希望依靠自己的“学识”预见未来的历史,但历史却不是依靠“学识”就能预见的,因为不论“学识”多么渊博的知识分子,在其背后都有几乎无限的知识和思想的空白——“人”,不可能成为无所不知的“圣人”。对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革新运动也是这样,因为它根本不在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的“学识”范围之中,既不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学识”范围之中,也不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的“学识”范围之中,而是在他们思维空间之外“横空出世”般地掉落到他们的面前的,或曰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夹缝中冒出来的。 实际上,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并不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要预见鸦片战争那样难以预见“五四”白话文革新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因为所有这些都产生在像他们的留美同学胡适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内心感受和内在的思想演化中,产生在他们内心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不满中。他们也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已经有着那么多“辉煌灿烂”的东西,也知道西方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轻而易举地被创造出来的,但他们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不满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现状、思想现状、文化现状不能令他们感到满意却是实实在在的。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不满,使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仅仅盯在那些中国已有的事物、已有的文化上,而总想从这些已有的文化现象中发现出一条隙缝来,并通过这条隙缝穿过已有的文化传统走到一个更加宽阔光明的世界中去。在这时,他们重视的往往是别人并不重视甚至不知道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东西。那个怪人钟文鳌关于“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的小传单,对于其他美国留学生,像是在空中飘过的一粒无臭无味的花粉,甚至连“它有没有用”的意识也没有留下,但在胡适的意识中却撬开了一扇中国文字语言改革的大门。当胡适在东美中国学生会“文学科学研究部”提出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当年文学股学会的论题时,这个问题也只是胡适思想中的一个“空间”,是用他的主观愿望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撑开的一片新天地,还没有具体的“学识”内容,他此后关于白话文改革的所有“事实根据”和“学理根据”,都只是展开这个“问题”并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更充分展开的文化空间的方式。正是在这个空间里,他开始了白话文改革的试验,开始了白话诗写作的“尝试”。⑥也就是说,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包括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并不是首先产生在已有的事物、已有的文化和已有的“学识”之中,而是首先产生在人的内心愿望、内在意识之中,产生在人对固有传统的不满中,产生在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愿望而进行的现实追求中。它像一股股地下水一样先在人的内心流动,要想感觉到它的流动必须首先了解自己和自己同时代的人、感受和理解自己和自己同时代人的内心愿望和要求,仅凭自己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和思想是不行的,仅凭自己已有的“学识”也是不行的。它也需要“学识”,它的“学识”也是来自“传统”。但这时的“传统”,这时的“学识”,对于一个有历史追求的人,更像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大库房,它不是一个展室、一个展室地被陈列出来的,而是根据人的现实需要从库房的不同储藏室中挑选出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组装起来的。他组装起来的是过往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东西,正像胡适用中国文字写作的是过去未曾有过的白话诗一样。在这里,“学识”是为他们开路的,而不是堵路的;是提供给他们自由的,而不是干涉他们自由的。如果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不是立于旁观者的立场上仅仅用自己的“学识”从外部衡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非曲直,不是为了堵住这些革新者的路,而是站在同情和理解他们的立场上并能够沿着他们的思路思考问题,对于他们,“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是不难理解的。但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学识”了,他们对自己的“学识”的自信使他们不再关心自己身边这些普通人的内心感受和思想愿望。岂不知他们的“学识”也只是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形式,他们用这种组织形式完全遮蔽了自己眼前的人,也遮蔽了他们原本可以理解的人的内心愿望和要求,因而也遮蔽了他们原本可以拥有的“史识”。不论是他们在国内教育中接受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传统,还是在美国教育中接受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都是通过历史上的“通儒大师”和他们所宣讲的一些“学理”构成的。他们的“学识”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似乎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这些“通儒大师”用自己的思想宣导国人的结果。(“故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⑦)胡适、陈独秀这班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睛里,显然不是这样的“通儒大师”,因而也不相信这些知识分子就有革新中国文化的能力,至于他们所提出的那些“事实根据”和“学理根据”,更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学理”不合(“盖诡辩家之旨。在以新异动人之说。迎阿少年。在以成见私议。强定事物。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至其言行相左。诒讥明哲。更无论矣。吾国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颇亦类是。”⑧),这就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个地关在了他们思想的大门之外。实际上,像白璧德崇尚的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类历史上的“通儒大师”,在他们同时代的同辈人眼里,也是像胡适、陈独秀这样的一些普通的人;他们的思想学说,在他们同时代的同辈人眼里,也无非是一些“新异动人之说”。它们的“圣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思想的“圣人之道”的形象都是被他们的传承者所重新塑造过的,这使他们看不到自己同辈人对现实世界的内心感受和愿望了——“学识”,离开对现实社会和现在还活着的人的感觉、感受、同情和理解,有时也会蒙住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原本可以看到的事物和真理。 “史识”并不首先产生于“学识”中,所以单凭已有的“学识”也无法正确评价“史识”。“史识”的正确性及其程度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在历史上实际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史识”要通过“史实”来证实,尚未转化为“史实”的“史识”仍然只能作为一种“假说”保存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而不能做出正确与否的最终判断。直至现在,仍然有许多学者试图根据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或西方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论证“五四”白话文革新的“错误”,甚至将其视为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给人造成了一种白话文不如文言文的感觉,但所有这些理论都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即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再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语言载体。人们很难想象,现代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会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而不用胡适首先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网络文体等文学体裁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语言载体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文言文的时代。对于我们,这已经是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决定这些事实的是“存在”,而不再是对其存在资格的论证。不论我们还能为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做出何种形式的辩护,不论我们对他们所信奉的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还能做出何种形式的评价和解说,但他们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言论和举动做的都是一些无用的功。这已经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是用语言擦不掉的。——历史不是想怎样描绘就能怎样描绘的,否则,历史就不需要研究了。 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就其性质属于“史识”,是他对中国语文、中国文化前景的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判断,但在其表现形态上,同时也是一种“胆识”。中国知识分子首重“学识”,次重“史识”,但却常常轻视“胆识”,因为“学识”和“史识”都直接表现在一个理性的结论中,而“胆识”则好像是“非理性”的,像“撞大运”一样“撞”上的,并不被人视为是理智的,理性的。实际上,“胆识”也是一种“识”,一种见解,一种认识,只不过在它发表出来的时候,还说不上有充足的理由,也很难做到令当时大多数的人心服口服。它的根据是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后来人的感受和理解一点一点地补充起来的,但即使这样,仍然无法被人直接作为一种“学理”、一种“规律”来运用。实际上,胡适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也是这样。当他提出自己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反对他的人有一大堆,同情他、理解他的人却没有几个,但他公开提了出来,并且坚持了下去。他成功了,直到现在,几乎连反对他的人使用的都是他所提倡的现代白话文,但我们却并不认为他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举动有多么了不起。我们从其中好像发现不出多么深刻的思想,也找不到多么了不起的“历史的规律”。对于我们,尽管享用着他的白话文改革的成果,但他的白话文改革的举动和理论,却像一次性的筷子一样,没有用处了。在课堂上,我是这样向学生解释胡适白话文革新的意义的:我把他和西方的哥伦布相比。哥伦布没有想到他会发现一个新大陆,但他确实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并且因此而改变了世界的地图,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胡适也是这样,他的白话文改革能否成功,这个成功的意义将会有多大,他在当时是不会有清醒的意识的,因而也无法将他的白话文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做出更有理论深度的理解和阐释,或者在一个严密的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历史规律”的高度。他的成功,令人感到得到的太轻易,太突然,既不那么严肃庄重,也不那么深奥玄虚,但又像拉开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总开关一样,整个中国文化都亮了起来。——实际上,这就是“胆识”的作用。当一个新事物、新思想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常常听人说:“其实,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有说出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当时也知道,只是不喜欢说出来。”“其实,我也知道,但当时说话不自由,我没有敢说!”……岂不知“胆识”与一般“识见”的差别就在这“说”与“未说”、“敢”与“不敢”之间。 真正的“胆识”之所以宝贵,是因为“胆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真正的“胆识”也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学识”和明敏的“史识”的基础之上,没有“学识”就没有“识见”,更不会有“胆识”;没有“史识”,就不会有超于一般“学识”的超前的“识见”,因而也不会有“胆识”,所以构成“胆识”的基础的是“学识”和“史识”。如前所述,“学识”是空间性的,“史识”是时间性的,“学识”和“史识”构成的则是一个知识和思想的时空结构。尽管这个时空结构并不意味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不意味着人类文化知识和思想的总和,但却具有激活各种知识和思想的内在潜力,也有将其激活的任何知识和思想纳入这个时空结构并使其在这个时空结构中继续发展变化的可能。这正像一个天文学家不但能够看到人类已经发现的星球,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发现过去尚未发现的新的星球,并在发现之后纳入自己所掌握的整体的天体结构中、继续追踪其在这个整体的天体结构中运动和变化的轨迹。具体的“学识”是明确的,因为它在一种思想学说中的空间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做出一个理智的判断。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忠于皇帝的官僚就是一个“忠臣”,不忠于皇帝的官僚就是一个“奸臣”,这个结论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具体的“史识”也是明确的,因为它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链条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可以做出一个理智的判断。“伽利略奠定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基础”,这个结论也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但在整个时空结构中,任何一个点的位置都是极不明确的,很难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理智的判断,因为整个时空结构就是像老子说的“道”一样是个混沌的整体,是可感而不可说的一种存在状态。真正的“胆识”就产生在这种可感而不可说的社会感受或文化感受的基础上,其中有“学识”,也有“史识”,但所有这些已有的“学识”和“史识”共同构成的却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在胡适提倡白话文改革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存在着中国古代大量用文言文写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其产生和演化的历史。也存在着大量用西方文字语言写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有其生成和演化的历史,同时也存在着中国古代大量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有其生成和演化的历史,他并没有读过其中所有的作品,也并不了解其中变化和发展的所有细节,但这个整体的时空结构却是存在于胡适的意识之中的。这个结构,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在其“学识”基础上形成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也有丰富的“学识”,他们所“知道”的并不比胡适更少,但在他们的意识中,整个世界文化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圣人之道”统领下的文化,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圣人之道”,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圣人之道”,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就是将东西方的“圣人之道”都囊括其中的当代世界文化的“圣人之道”。这个结构只是一个由“圣人之道”统领的巨大空间,“天不变道亦不变”,它是不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的,因而他们也感到现实中各种事物都是清晰的,明明白白的,可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而胡适当时意识中的这个结构,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结构,同时也是一个时间结构,这个时空结构没有一个核心,也没有一个能够统领所有这一切并决定其如何发展变化的“圣人之道”,但他却能够用心灵感受到它。在他的感受中,这个时空结构不是完满的,特别是当代的中国文化,给他的是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感觉,“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⑨。因而他也像女娲一样感到必须以自己的力量将它补齐,这就有了他提倡白话文改革的想法。他的这种想法就是一种“识见”,并且是一种大胆的“识见”——“胆识”。没有他对世界文化的广泛了解和文化变迁的意识,亦即没有丰富的“学识”和明敏的“史识”构成的这个知识和思想的混沌整体以及对这个混沌整体的缺失感觉,这种“胆识”是产生不出来的。——浅薄的思想只产生浅薄的冲动,而无法产生真正的“胆识”。 真正的“胆识”不是从任何别人那里获得的“识见”,也不是已经纳入任何别人的思想体系里的“识见”,所以它是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是根据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价值标准判断胡适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的,他们的思想就是白璧德的思想,他们的“识见”就是一个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者的“识见”,不具有他们本人的主体性品格。对了,证明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正确性;错了,证明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局限性。与他们本人内在的社会、文化、人生的感受和体验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但胡适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却是与他本人的内在的社会、文化、人生的感受和体验无法分开的,它甚至无法纳入到他所信奉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之中去,因为并不是所有信奉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够感到中国书面文化有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必要的。这是他个人的见解,个人的“识见”,在当时不属于任何其他一个人。“胆识”的这种主体性,决定了它的“真诚性”,决定了它所表达的是这个人的真实的“识见”,是在自己亲身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是言不由衷的话,不是人云亦云的话,不是谄媚豪右的话,也不是吓唬老百姓的话,而这也是“胆识”较之一般的“识见”具有更强烈的思想征服力的原因。它像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样吸引着没有先入之见的人们去接近它、感受它和理解它;这种主体性还决定了它的“自信力”。鲁迅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很少‘坚信’。”⑩凡不是建立在自己亲身感受和体验基础上的“想法”,都不会有“坚信”,但一当一个人的“想法”是在自己亲身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生成并发展起来的,他则没有怀疑它、放弃它的任何理由,因而也是充满自信的。所以,“胆识”体现了一个人内心的强大,体现了他的坚定的信念。胡适本人给我们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坚强勇敢的男子汉的形象,但他对他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却从来没有动摇过、放弃过。他对他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是有自信力的,倒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只是高涨了一阵子,此后就力衰气消了。他们虽然始终没有成为“五四”新文化的积极拥护者,但也不再是“五四”新文化的激烈的反对者。这里的原因实际很简单,因为他们虽然根据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的原理能够说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弊端,但在他们的实际人生感受、社会感受和文化感受中,却绝对不会像他们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认为胡适、陈独秀这一班“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只是一些浅薄无聊的无知小儿,只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捣乱分子。他们对胡适、陈独秀这一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蔑视充其量只是做出的一种文化姿态,当他们的反对没有取得自己预想的现实效果的时候,在他们的内部就找不到继续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动力了。与此同时,在他们最初的感觉中,仅仅根据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学说,就足以证明胡适、陈独秀一班人提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时空结构中生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二者既没有直接的顺应性,也没有直接的对抗性。仅仅根据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学说的基本原理,是不一定能够得出从根本上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论的。到了梁实秋,信奉的仍然是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但他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也用着现代白话文写着现代的白话散文。——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无法成为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 真正的“胆识”是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的,是属于一个特定的人的“识见”,但这种“胆识”本身却是关系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不属于一个特定人的“识见”,不是“胆识”:“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是共产主义者的集体意志和共同信念,不是“胆识”;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识见”,也不是“胆识”:“我一定要当世界冠军!”这是个人的决心和意志,也不是“胆识”。“胆识”一定是知识分子个人对社会、对社会文化的见解和看法。所以,真正的“胆识”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个人的愿望和要求,个人的感受和思考,个人的意志和追求,也包括知识分子个人对社会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对社会的主动承担精神。它是知识分子个人与其社会融为一体的根本途径和方式。必须看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是通过知识和文化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出来的,它诉诸人的感受和理解,诉诸人的信从,而不能仅仅诉诸人的服从或屈从,所以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群众的社会生活不是绝缘的,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群众的社会生活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但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文化却不是借助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群众的社会舆论的力量而产生的,也不能借助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群众的社会舆论的力量加以推行,因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群众的社会舆论的力量是可以跨过人对知识和文化的实际感受和理解而直接转化为人的言语和行动的,是可以跨过知识和文化具体生成和演化的思维过程而直接运用其最终的结论和成果的。这能造成人的内在意识运动与外在言行方式的暌离乃至相互的对抗,既破坏了人的内在意识成长和发展的正常机制,也破坏了人的外在言行的正常的实践功能,是造成文化对人的异化的主要方式,是社会人心趋于虚伪和社会生活趋于紊乱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感到,“胆识”恰恰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本体性特征,也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的主要人格特征。如前所述,知识分子可以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有着各种不同的“学识”和“史识”,但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所有具有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则是相同的。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1)这里突出的其实就是具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不屈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压迫的特征。庄子说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12)。这里突出的其实是具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不屈从于多数人的世俗见解的压力、不被个人一时一地的荣辱得失所左右的特征——有“胆识”的人是在自己“识见”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荣辱得失的价值感觉的。所有这一切,都和“胆识”自身的性质和特征息息相关。没有“胆识”的人,就没有这一切,就不会有这一切。 胡适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是他个人首先提出的主张,是具有他个人的主体性的,但这种主张却是关系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其中包含着胡适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整体关怀,包含着他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自觉承担意识和主动承担精神,因而也体现了胡适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当时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中都是感觉不到的。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几乎只有一点:他们与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打拼的是“学问”,是“学识”,以向公众证明,胡适、陈独秀等一班人并没有资格领导现代的中国社会和现代的中国文化,而有这种资格的,应该是他们这些掌握了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因而也遵从着当代世界文化的“圣人之道”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地这么说。 胡适白话文革新的主张在其本来的意义上更是一种个人的“胆识”,它之所以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人所接受、所倡导也因为它是一种“胆识”。这种“胆识”是建立在胡适本人对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亲身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之上的,是他对中国现实社会文化及其发展前景的一种关怀,一种自觉的承担,而不仅仅是根据前人的某种思想学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显而易见,在胡适提出白话文革新的主张之前,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还未曾形成关于白话文革新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仅从“识见”,仅从“学识”,他们彼此实际是极不相同的。他们对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之所以能够迅速做出赞同性的反应,不是因为与胡适有着完全相同的“学识”基础,也不是因为彼此的“识见”完全相同,而是因为他们都不满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都有改革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愿望和要求。亦即他们都是一些有“胆识”的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现代教育思想,陈独秀的思想革命的主张,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对新文学的追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主张,胡适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在当时都是一些个人的“识见”,都是一些“胆识”。“胆识”首先是个人内心的愿望和要求,是需要别人的同情和理解的,所以他们在本能上也愿意同情和理解别人内心的愿望和要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知道,他们之间实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拍即合,并且在相互的理解和同情中将各自的“胆识”连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一个集体性的“胆识”——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直至现在,中国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独立的思想学说能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概括起来,形成像中国古代的孔子思想、老子思想、墨子思想、庄子思想、韩非子思想、道教思想、佛学思想、禅学思想和西方各种“主义”那样相对明确的思想学说,所以至今它还无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学识”并像中外那些著名的思想学说一样通过师承关系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但作为一个文化革新的历史运动却又是为所有人所无法忽视的。——它是“历史”,不是“学识”。 但是,胡适到底也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且正处于求知欲望强烈的青年时期。所以,他也是一个更加重视“学识”、更加重视自己的学术羽毛的一个人。相对而言,他并不那么看重“胆识”,也不愿别人将他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仅仅视为一种似乎没有多么坚实的“学识”基础的“胆识”。当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公开亮出了自己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旗帜的同时,胡适也公开亮出了自己的美国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旗帜。这就给人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胡适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而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之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是因为胡适接受的是美国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而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接受的是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这就将胡适和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之间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暴露出的矛盾和差异降低到了“学识”与“学识”的矛盾和差异的层面上,降低到了当代美国两种不同的思想学说的矛盾和差异的层面上。它同时也将“学识”与“胆识”之间的不平等的竞争关系歪曲成了“学识”与“学识”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因而也歪曲了他们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差异的实质意义。 在我们的学术界,经常看到的是这种“学识”与“学识”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古代,有儒墨之争,儒道之争,佛道之争等等;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不但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而且从西方传入的各种“主义”也在中国各不相让、彼此争斗。实际上,如果学界只有这种“学识”与“学识”之间的论争,还是不会有实际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因为不同的“学识”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就是不同的,不论怎么争,都是争不出一个结果来的。关于这一点,庄子早就说过:“即使我与若辩,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13)意思是说,既然不同“学识”之间的是非标准就是不一样的,即使我与你辩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过你,也无法证明你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我胜了你,你没有胜过我,也无法证明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谁是,谁非,还是都是,都非,通过这样的不同“学识”之间的辩论是永远辩不出个头肚的。不同“学识”之间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辩论也是无法做到彼此的相互了解的。既然彼此的是非并不清楚,也无法依靠别人的判断纠正彼此的看法。如果让与你的观点相同的人纠正我们的看法,他既然与你相同,与我不同,怎能纠正呢?如果让与我的观点相同的人纠正我们的看法,他既然与我相同,与你不同,怎能纠正呢?如果让与我和你的观点都不相同的人纠正我们的看法,他既然与我和你都不相同,怎能纠正呢?如果让与我和你的观点都相同的人纠正我们的看法,他既然与我和你都相同,怎能纠正呢?对于这些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的“学识”,庄子提出的意见是“和之以天倪”,即承认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有差别的形式共存于现实世界,各按自己的形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开拓自己的社会空间,谋求各自的发展,不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不同的思想学说,不同的“学识”。实际上,庄子的这种思想观念,并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他将不同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学说视为现实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事物,山有山的标准,水有水的标准;同为树木,松树有松树的标准,柳树有柳树的标准,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彼此之间怎能分出一个绝对的是非呢?“和之以天倪”就是让松树像松树一样生长,让柳树像柳树一样生长,不用一个标准要求不同的事物。庄子的这种思想,实际也就是中国最早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思想。只不过到了后来,儒家思想统治了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庄子这种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思想也就成了一些空话。——当一种思想学说已经在整个国家政治权力的维护下具有了法律的意义,具有了对一切社会思想差异的最终裁判权,所有其他的思想学说除非公开与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宣战并在这种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自己对现实社会和现实社会文化的独立作用之外,其自身就不再有可能对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影响,即使形式上仍然存在着,也只成了一些聋子的耳朵——空摆设。 不难看到,在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就是在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整体背景上同时存在、同时发挥着各自的社会作用、也同时通过各自的师承关系在美国社会思想的历史上得到传承和传播的。实际上,在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体现的只是美国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念和文化观念,它是以卢梭之前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欧洲文化为样板的。那时的欧洲文化,实际就是欧洲贵族阶级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文化。他们已经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整个欧洲社会和欧洲文化中具有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也建立起了自己以人为本位、以科学和文艺为主体内容的近代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化,在欧洲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但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上,贵族阶级仍然是与社会平民有着严格区别的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也负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社会使命。所以那时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就是当时的国家文化,当时的高雅文化。它体现的是国家集体的愿望和要求,体现的是国家的统一的意志,是有着统一的社会规范的文化,也更接近中国儒家伦理道德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在文学上的新古典主义,提倡以“理”节“情”,也与中国儒家的文艺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欧洲的社会思想,在其整体上,到了卢梭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社会教育的发展,使更多的平民知识分子开始进入社会文化的上层,原来的贵族知识分子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沦为平民知识分子,并以更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平民的生存状态及其愿望和要求。这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从国家统一的意志之中解放出来,以“国家”为本位的文化逐渐转向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人的精神发展中的自然主义和社会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为欧洲社会思想的主潮,这在经济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则瓦解着贵族阶级的专制统治,欧美各个主要国家相继建立起现代的民主政治,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则是这个历史时期相继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学思潮。但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既有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也有不断积累的一个侧面,旧的传统从来不会从人类文化中完全消失,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包容在新的文化传统中,并成为新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继续发挥着它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特殊作用。正像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在文艺复兴之后仍然通过宗教组织作为一种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传承下来一样,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通过像白璧德这样一些学院知识分子、精英知识分子在欧洲和美国作为一种独立的世界观念和文化观念传承下来。这些通过学校教育直接进入上层社会并远离中下层现实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精英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对于新古典主义时代崇尚健全的理性、重视人伦礼仪关系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教养和习惯情有独钟,而对卢梭之后在现实社会矛盾和斗争的旋涡中发展起来的崇尚情感、注重个性发展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则有些格格不入。但在这时,它早已不是欧洲和美国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早已无法体现这些国家社会民众的统一意志和要求,虽然像白璧德这样的一些学院知识分子、精英知识分子仍然以“圣人之道”的传承者自居,但他们在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和社会文化中,早已失去了作为社会、社会思想领导者的“圣人”的地位。总之,在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整体背景下,它只是诸多思想学说中的一种思想学说。它与其他思想学说的关系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与此同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虽然体现着美国当代社会思想的主要特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与当代美国的国民性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尽管如此,它也只是在美国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整体背景下的一种思想学说、一种“学识”,而并不代表美国社会文化的全部,更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如果说白璧德打出的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旗帜,杜威的实用主义(又译为“实验主义”)在总体上则是一种科学主义,它是以“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为基础的。胡适在介绍实用主义哲学时说:“‘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试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这一派哲学的始祖皮耳士常说他的新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14)显而易见,“试验室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态度,但却不是唯一的“文化的态度”,甚至也不是唯一的“科学的态度”,而更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态度”,“物理学的态度”。在“试验室”里,一切前提条件都是从无限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挑选出来的,都是经过人为的加工被纯净化了的,所有无关的因素都被排除了,所有的复杂性都被摒弃了,一切都有了一个量化的标准,然后则是严格按照早已设计好的固定程序进行的。这样得出的是一个明确而又具体的“客观的真理”,但这种明确而又具体的“客观的真理”,又是无法脱离开它的那些被提纯了的前提条件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研究,除了应该具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之外,还应该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具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无法代替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无法代替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美国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大背景下,二者是平等竞争的关系,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是和非的差别的。 但是,当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旗帜插到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化阵地上,并向“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起了公开挑战的时候,情况就有了一个根本性质的不同,因为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整体的文化背景,它的整体的文化背景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构成这个文化专制主义整体背景的就是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的统治历史的儒家文化传统,它是明确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而被历代政治统治王朝自觉地加以灌输和推行的,是具有立法性质的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则是在这个文化专制主义的整体背景下通过极少数中国个体知识分子的努力刚刚产生、还处于“乍暖还寒”状态的文化,并且它是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为自己明确的追求目标的。也就是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虽然也是作为个体知识分子而出现的,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的背景,但他们将从美国接受过来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却是直接嫁接到当时中国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整体背景之下的,是公开反对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为自己的明确的追求目标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这就使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从美国接受过来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带上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性质。这种性质并没有转化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没有实际起到扼杀“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作用,但它仍然作为一种潜在的能量表现在它的“学识”自身的力量中。 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视“学识”,因为“学识”也是一种力量,一种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通过对固有文化资源的占有而实现的。知识分子占有了相关的文化资源,也就占有了相关领域的思想,使其在与其他人的竞争关系中具有自己的优势性。“学富五车”,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占有了更多的文化资源,其受众群体对其思想和言论是可以信从或不得不信从的,而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因为不占有任何的文化资源,其思想和言论也是不值得信从的。与此同时,不同的思想学说,不同的“学统”和“学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对固有文化资源的一种分配形式。直至现在,我们仍然常常认为,只有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才能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资源做出合理的阐释和利用;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才能对中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做出合理的阐释和利用。这就在无形中将不同的文化资源分配给了不同的思想学说,不同的“学识”和“学统”。只要从这个角度看待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从美国接受过来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和胡适从美国接受过来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学说,我们就会知道,仅就“学识”而论“学识”,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它们虽然都是从外国思想家那里接受过来的一种思想学说,都是一种“学识”,但二者在当时的中国所占有的文化资源却是有天壤之别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所拥有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在内容上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至卢梭之前西方文化史上的整个人文主义文化传统,虽然它在西方文化中早已不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它作为当代美国学院文化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学说,对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同样体现了美国当代文化的“现代性”和“先进性”,而它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直接结合,则使它可以与儒家知识分子共享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全部文化资源。这就使吴宓、梅光迪、胡先骕通过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便把东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化资源尽数揽入自己的怀中,使他们在当时的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之中拥有了学贯中西、汇通中西、驾驭中西文化的文化幻象,因而也更能获得当时的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信赖和遵从。胡适从美国接受过来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有所不同,虽然它也是美国当代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一种思想学说,虽然这种思想学说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具有美国当代文化的“现代性”和“先进性”,但在当时的中国,除了胡适,甚至包括“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在内的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更莫说对这种哲学思想的信赖和运用了。而通过胡适输入中国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建立起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联系,因而它也不占有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资源。总之,仅就“学识”而论“学识”,胡适仅仅依靠他从美国接受过来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是无法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从美国接受过来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相抗衡的,是无法成为他的白话文革新主张的思想基础的,这恐怕也是当初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并不把胡适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放在眼里”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我们可以断言,真正支撑着胡适“五四”时期的思想的,不是或主要不是他在美国接受过来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不是或主要不是他的“学识”,而是他的“胆识”,他的个人主义的“胆识”。 什么是“胆识”?为什么真正支撑着胡适“五四”时期的思想的是他的“胆识”,是他的个人主义的“胆识”?这,我们通过他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就能看得十分清楚: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5) 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地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16)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泻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样的“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样的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 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17) 什么是“胆识”?胡适这里说的就是“胆识”! 为什么这种“胆识”不会被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的“学识”所颠覆?为什么将从古希腊到卢梭之前,整个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和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逐渐积累起来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都涵盖于其中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所传承的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也无法颠覆像胡适这样一个青年学子的“胆识”? 显而易见,这是因为真正属于“胆识”的“识见”和“认识”,有为一般的“学识”所无法进入的一个独特的思维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胡适在这里所叙述的个体人对外部的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和现实社会文化的整体感受和整体关怀的空间。如前所述,作为这个个体的人,也是有“学识”和“史识”的思想基础的,但他的所有从前人和前人的著作中接受过来的“学识”和“史识”都无法直接说明他当下对他所处的外部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具体的感受和了解。他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并且这种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也一定会包含着他对改善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和现实社会文化的具体途径和方式的思考。显而易见,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时代,没有文化的广大社会群众由于社会视野和文化视野的局限性都不可能真正形成自己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独立的整体的思考和把握,因为这种独立的整体的思考和把握不仅仅依靠自己极其有限的直接的感官感受和印象,还必须依靠从前人的思想和文化中接受过来的更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更多样的理性把握现实的方式,而能够拥有更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更多样的理性把握现实的方式的广大知识分子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或不敢正视自己面前的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因而也不会从这种整体感受中产生出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整体关怀,仅仅满足于自己从前人和前人著作中接受过来的现成的知识和思想,这就使这些个体人的“识见”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表现为一种不被人同情和理解甚至被多数人排斥的“胆识”,这种“胆识”只有经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坚持和努力才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同情,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运用。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周围的人仅仅依靠自己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从前人和前人的著作中接受过来的固有的知识和思想也无法改变这些个体人的独立的“识见”,无法从根本上瓦解这些个体人的“胆识”。具体到吴宓、梅光迪、胡先骕那些反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言论,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这些“道理”即使从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所有这些“道理”,都是从前人和前人的知识和思想中接受过来的。它们无法改变胡适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具体感受和了解,因而也无法改变他提倡白话文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与此同时,“学识”是从前人和前人的著作中接受过来的知识和思想,这种接受是通过语言和对语言的记忆而获得的,与外部世界、外部社会、外部社会文化构不成相互连带的紧密关系,也没有经历过这些知识和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形的全过程,因而它在一个人的心灵中还是飘忽不定的,与其对事物的主观感觉、感受、情感、情绪、意志构不成相互呼应的连带关系。而“胆识”则不同,“胆识”本身就是在一个人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中产生的,它有一个从无到有、从飘忽不定到成为坚定的信念的生成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伴随的不只是语言和对语言的记忆,还有他的主观的感觉、感受、情感、情绪和意志的状态。有“学识”的人往往很“理智”,但压力来了,也容易动摇;有“胆识”的人在外人看来并不那么“理智”,但压力来了,也不会轻易动摇,因为它的根据在其内在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感受和体验又是与其意志的力量纠结在一起的。“胆识”往往是在经过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之后才渐渐被别人所接受的。不难看出,在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反对胡适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和胡适坚持自己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的关系中,情况也是这样。 总之,胡适的白话文改革的主张更是他在对中国文化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中形成的一种个人主义的“胆识”,而不仅仅是从美国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接受过来的一种“学识”。 ①(11)《孟子·滕文公下》。 ②(西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③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的《导言》),《胡适文集》第1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以下所引《胡适文集》各卷版次相同。 ④(13)《庄子·齐物论》。 ⑤周佩瑶:《“学衡派”的身份想象》,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⑥参看胡适《逼上梁山》,见《胡适文集》第1卷。 ⑦⑧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32、128页。 ⑨(西汉)刘安:《淮南子·冥览训》。 ⑩鲁迅:《且界亭杂文·运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12)《庄子·逍遥游》。 (14)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第208~209页。 (15)(16)(17)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第476、482~493、488~489页。标签:胡适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白话文论文;
